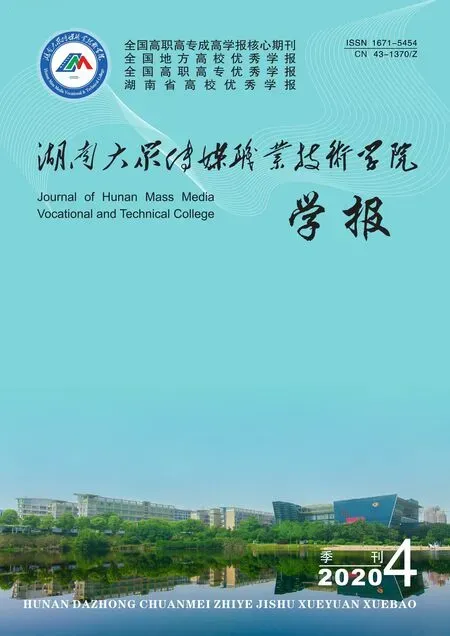《民法典》时代影像创作者如何避免侵权
尹孝勉
(湖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得益于相机与智能手机的发展,人人都能成为影像创作者。技术的进步给拍摄者带来便利,同时,侵犯被摄对象的权利也随之变得更容易和低成本。影像创作有法律的界限,尊重他人的权利是创作的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的出台标志着国家法制化的进步,进一步保障了每个人的权利,也对影像创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创作过程中避免侵犯他人权利,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拍摄,是每一位影像创作者应当恪守的法律底线。
一、影像创作者可能侵犯他人权益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为拍摄者的创作自由提供了最根本的法律保障,具体体现在《宪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但任何自由都有限度和制约,一旦突破了行使自由的边界,便可能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一)未经权利人许可侵犯肖像权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九条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可知,在不同的摄影类型中,侵犯被摄对象肖像权的方式有所不同。纪实摄影多以重大事件、百姓生活或社会风貌为拍摄对象,因而与人的肖像密不可分。摄影师多以抓拍的方式再现生活的真实情景,即在被摄对象不知情也未明确表示许可的状况下拍摄,这就容易使纪实摄影作品产生侵犯被摄对象肖像权的问题。而人像摄影中,由于拍摄者通常会在拍摄前与被摄对象约定好拍摄的时间、地点、服装或妆发等拍摄细节,意味着被摄对象以行为的方式认可了拍摄者的拍摄行为,但许可拍摄并不意味着许可使用。人像摄影作品承载着创作者的著作权与被摄对象的肖像权,如果拍摄者与肖像权人没有约定人像摄影作品的使用或公开的范围,例如拍摄者将作品复制、发表或展览,依旧存在侵权的可能。新闻摄影却是例外,由于新闻的突发性与真实性,摄影记者在拍摄时没有条件得到被摄对象的许可,属于《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合理使用的情形,不属于侵权行为。
(二)图文不符侵犯名誉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列举了名誉权的侵权形式,禁止使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新出台的《民法典》在结合上述规定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名誉权的保护有了进一步的规范。拍摄者对被摄对象名誉权的侵犯主要在于图文不符。例如在新闻报道中,照片与图片说明共同揭示报道的主题,“文字说明是新闻摄影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闻摄影的两条腿之一。”[1]摄影记者在撰写图片说明时应当客观、真实,不得用侮辱性或明显倾向性的语言描述画面中的人物。但在实际中,往往有摄影记者对客观事实认知不准确,图片说明的描述不恰当,从而对被摄对象的名誉造成侵害。此种侵害名誉权的情形不仅发生在新闻报道中,网络用户在微信朋友圈中拍摄的图片、视频与文字描述不符,或者在抖音中对发布的短视频掐头去尾、断章取义,造成对他人的社会评价造成影响,都可能存在侵害他人名誉权的情形。
(三)拍摄私人领域侵犯隐私权
人类传播信息的速度不断提高,摄影器材的不断优化与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也愈加明显。《民法典》第六章中既界定了隐私的概念,又明确了禁止实施的侵害隐私权的行为类型。《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拍摄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不得拍摄他人的私密活动、私密部位等。因客观记录的特性,摄影在表现真实性的同时,也有可能将被摄主体具有隐私性的、不愿公开的一面展现出来。如在新闻摄影报道中,虽然客观、真实是基本要求,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拍摄。拍摄者在进行拍摄时,往往为了挖掘更深入的内容而进入被摄对象的私人范围,一旦拍摄行为超出了被拍摄对象的许可范围,或非法进入某种被限制的场合拍摄,都会造成对隐私权的侵犯。如湖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以下简称都市频道)与周玉名誉权纠纷一案中,[2]上诉人湖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称公开的内容不属于隐私权保护范畴,被上诉人周玉辩称上诉人到家中拍摄并未经过其同意,并提出反对播放的意见后未及时停止播放。法院最终认定都市频道侵犯了周玉的名誉权、隐私权,驳回了都市频道的上诉请求。
二、《民法典》对影像创作者提出的新要求
随着肖像权纠纷不断增加,我国肖像权保护的立法缺陷日益突出。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民法典》的一大亮点,该编明确了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这也对影像创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侵犯肖像权不再要求必须“以营利为目的”
过去对肖像权的保护,主要依据的是《民法通则》第一百条规定。认定对肖像权的侵犯,必须符合“未经本人同意”和“以营利为目的”两个构成要件。自然人的肖像权是一种人格权,主要体现的是精神利益,只强调以营利为目的,与民法保护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立法本意不相符。一直以来,对于肖像权的侵权要件讨论中主要分为两派,即宽派和严派。双方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将“以营利为目的”作为构成要件,实质是对自然人肖像权保护范围宽狭之争。[3]多数理论工作者主张宽派,即“使用他人肖像,只要未经权利人同意,即可构成侵权。”[4]然而审判实务中多采取传统的做法,坚持“以营利为目的”作为肖像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结果便是对肖像权的保护非常有限,实践中许多侵犯肖像权的行为不能受到法律规制。《民法典》将“以营利为目的”从法律条文中去除,使得肖像权的保护范围扩大。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八条第一款及一千零一十九条第一款,丑化、污损、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他人肖像,或者未经肖像权人同意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都被认定为侵犯肖像权的行为。在拍摄中,纪实摄影或人文摄影往往是在被摄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过去拍摄者往往认为,只要没有将摄影作品用于商业目的就不构成侵犯肖像权。这种观念在《民法典》时代已经不再适用。
(二)肖像的确认标准为“可识别性”
在《民法典》颁布之前,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公民享有肖像权,但是肖像的内涵是什么,外延有哪些,却没有以法律的形式界定。《民法典》一千零一十八条将“肖像”定义为:“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过去对肖像权的确认标准多为“以面部为中心”,《民法典》进一步加大了对肖像权的保护,将确认标准变更为“可识别性”,即以外部形象与特定自然人之间建立对应联系,此种联系成立与否可综合该外部形象呈现的方式、场合、所附文字以及权利人的知名度、社会交往范围等因素予以认定。尽管肖像属于外部形象,但不再限于面部容貌,侧脸、体貌、背影乃至局部特写,只要符合条件均可获得肖像权保护。因此拍摄者在拍摄过程中,未经肖像权人的同意,即使没有拍摄权利人的面部特征,仅拍到背影、侧脸、剪影或者局部特征,只要能够被识别为特定的自然人,或者通过局部特点能够使人们直接对应特定的自然人,都可能造成对肖像权的侵犯。
(三)未经许可著作权人不得使用或公开肖像
根据《中华人民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规定,在委托创作的作品中,如果没有明确约定,著作权应归受托人所有。在人像摄影中,由于双方对拍摄的约定,可以将拍摄者认定为受托人,所以拍摄者在创作人像摄影作品时,如对著作权无特殊约定,著作权应归拍摄者享有,而肖像权应归被摄对象享有。由于摄影作品上既包括拍摄者的著作权,又含有肖像权人的肖像权,而著作权与肖像权不归同一主体,所以在实践中经常产生冲突。虽然肖像权人也有侵犯著作权人的可能,但实践中更多地体现为著作权人对肖像权人的侵害,[5]如著作权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使用其肖像作品。深圳市薇爱施华洛婚纱摄影有限公司诉胡贤娟等肖像权纠纷一案中,[6]上诉人深圳市薇爱施华洛婚纱摄影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龙水林、胡贤虽签订了《婚纱摄影协议书》,但未在与被上诉人约定的范围内使用肖像作品,二审法院认定为该行为侵犯了被上诉人的肖像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未经公民同意利用其肖像做广告、商标、装饰橱窗等,应当认定为侵犯公民肖像权的行为。”这条规定亦适用于著作权人,但是如果著作权人通过展览或者评奖等方式使用肖像,未以营利为目的,那么是否可以据此规避法律的规制?人格权高于著作权是一般原理,《民法典》进行了完善,在第一千零一十九条中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据此,虽然肖像作品上承载了著作权与肖像权,著作权人权利的行使需要尊重肖像所承载的人格利益,不得侵害权利人的肖像权。
三、避免拍摄行为侵犯他人权益的对策
为避免侵犯他人权益,影像创作者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及时熟悉相关法律知识
影像创作者想要避免侵权行为的出现,就必须熟悉相关法律法规,知晓行为的边界。首先,在拍摄与发布作品的过程中,要有规避侵权行为的意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侵权主体正是因为对相关法律法规不熟悉,无意识地对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其次,对由侵权行为带来的法律后果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拍摄者往往认为侵权的主体多,而被侵权人维权成本高,所以会放弃向侵权人主张权益。“法不责众”的心理并不可取。《民法典》第一千条规定:“行为人拒不承担前款规定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发布公告或者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等方式执行,产生的费用由行为人承担。”这一规定将有效遏制此类现象产生。最后,熟悉与自身相关的法律法规。拍摄者只有在熟悉相关法律和解释的基础上,才能对自己的行为及产生的后果进行预判,例如什么样的场景可以拍摄,什么样的场景拍摄之后可能对被摄对象的隐私权或肖像权造成侵害,从而避免因侵权事件陷入法律困境。
(二)获得拍摄对象的许可
在没有得到权利人许可的情况下,制作、使用或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都是不被允许的,除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外,因此获得被摄对象的许可尤为重要。
从方式上来看,许可分为书面许可和口头许可。摄影是一门瞬间艺术,好的瞬间可遇而不可求。在人人都可以成为摄影师的时代,要求拍摄者随时携带书面许可协议似乎难以奏效,但如果是提前知道拍摄对象的拍摄类型,可以事先准备好肖像权书面许可协议,约定好许可使用的范围、地点和期限等方面内容,避免后续因约定不明而引发争议。若没有达成书面协议的条件,则只能达成口头约定。由于单纯的口头约定无法当作证据在法庭上出示,故应当对口头约定进行录音录像,以兼顾肖像权人的许可及拍摄的效率。
从时间上来看,许可分为事前许可和事后许可。拍摄者应当以事前许可为原则,以事后许可为例外。在人像摄影等情况下,摄影师有条件在拍摄前与被摄对象进行沟通,应当在拍摄前获得被摄对象的许可。而纪实摄影或街拍等类型,为了还原被摄对象真实自然的一面,很容易在作品的拍摄和使用上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拍摄事后获得被摄对象的同意。如果肖像权人对拍摄的行为表示拒绝,则应当立即停止侵权,并删除照片。
(三)在题材选择上符合“合理使用”的范围
《民法典》的规定并不是意味着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一切公开他人肖像的行为都是禁止的。为了平衡保护肖像权与维护公共利益间的关系,《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九条规定,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可以合理使用肖像。《民法典》一千零二十条规定,合理实施个人学习、新闻报道、国家机关依法履职或为展示特定公共环境而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例如,以赞美白衣天使为内容的拍摄行为,团体照片中的每个人都是必不可少的部分,构成不可避免的肖像利用,符合合理使用的情形,不需要征得肖像权人的同意。
尽管法条已经作了明确的列举,但是在个案中拍摄者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予以把握。首先,“合理使用”的范围。以新闻报道为例,“合理使用”的范围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第一,使用具有新闻价值的人物肖像;第二,为报道集会、游行、仪式、庆典或其他公共场所的活动、事件;第三,为报道国家机关执行公务而使用公民的肖像;第四,为公民本人利益而使用其肖像;第五,行使正当的舆论监督而使用他人肖像。[7]其次,“在必要范围内”如何界定?例如街拍行为,如果是艺术学院学生的学习作业视为合理使用,若将摄影作品用于个人手机图片则超出了学习范围,侵犯了肖像权人的合法权益,不能认定为合理使用。而且必要范围是有弹性的,应当视具体情况而定。最后,何谓“展示特定公共环境”?例如在拍摄时,画面中以特定的公共环境为主体,如公园、建筑物或草地等,且占据画面的主要位置;人物在画面中作为陪体、前景或背景的方式出现,画面不以人物为主体。
——以肖像权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