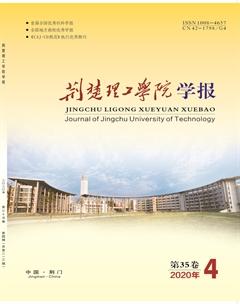凝视困境与深度写实
高超
摘要:第56届台湾金马奖热门影片《阳光普照》和《热带雨》以对现实生活细腻的典型刻画以及隽永的主题表达,引发了关于近年来华语电影现实主义创作的热议。作为杨德昌电影剧作的当代延续,上述两部影片的成功,反映出该创作思路在对接当代日常生活以及反映人的精神困境层面时的有效价值。其中,凝视困境与深度写实的表达姿态,甚至可以将之视为当下华语电影创作的一种独特叙事美学。
关键词: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精神困境;世俗理想;悲剧性
中图分类号:J9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4657(2020)04-0092-05
作为台湾新浪潮电影的主将之一,杨德昌电影以其鞭笞现实的叙事习惯和冷静内省的主题表达,对华语电影创作可谓影响深远。通常,对台湾新浪潮电影的观照往往倾向于探讨其群体性艺术表征或典型个体创作特点,对杨德昌创作的思考多忽视了历史性研究视野的重要意义。2019年的特殊社会形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第5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参赛影片格局,但从热门获奖影片引起的观影舆论依然可以看出其背后写实主义传统下独特的创作生命力,其中的原因或许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杨德昌剧作模式的延续与创新奠定了这些华语电影作品的艺术高度。同时,通过审视新世纪以来的华语电影创作,不难发现,杨德昌剧作模式秉持一种凝视困境与深度写实的创作姿态,为如何从现实世界及时代主题出发进行人本主义的典型电影书写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路径。我们将以第56届台湾金马奖的获奖热门影片《阳光普照》与《热带雨》为文本,结合杨德昌经典影片范本进行比照分析,力求洞见杨德昌剧作模式承袭的电影叙事创作思维。
一、现实的困境及潜在的意味
(一)时空运用:时间与空间的“镜框式”呈现
自上世纪30年代欧洲现实主义电影思潮发端以来,时空处理在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理念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台湾新浪潮电影运动秉持现实主义姿态的一系列创作,在根本上也延承了欧洲现实主义电影以来的时空处理观念。杨德昌电影作品中的时空设置通常会对叙事结构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如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时间背景设置上鲜明的过去时态以及在事件推进过程中对于如当下与未来、此刻与流逝等时间关系序列的呈现;《麻将》中时间既是当代社会恩怨存在的前提,也是其消逝的必然结果。在杨德昌的电影文本中,时间常以历时性姿态出现,角色身上带有强烈的时间背景,是人物性格和戏剧矛盾甚至主题意蕴产生的重要依据,其对于时间元素的运用着重寻求既静止又恒变的哲学况味,因此,人物在暗藏戏剧色彩的现实时间中更容易体味关乎人生的玄妙之意。对于空间的处理,杨德昌通常直接截取世俗生活的日常场景,但却无形中对场景的典型性进行了叙事强调及象征,这些场景既有世俗礼仪秩序的集中展示舞台,如《一一》中的婚宴酒店宴会厅等,也有人与人发生隔阂或矛盾的封闭空间,如《独立时代》中发生争吵或沉默的电梯间、《恐怖分子》中行凶争斗的酒店房间等,还有人的心境的外化象征,如《一一》中婷婷邂逅爱情的带有斑马线的街头、《麻将》中“金屋藏娇”的偷情公寓等。这些最为日常化的场景空间,其实都不约而同地带有人生阴晴聚散的荒诞感和存在主义的哲思意味。
《阳光普照》带有台湾电影青春叙事的类型色彩,时间一方面作为青春成长主题的必然注解,将常见的叛逆少年成长与人生风雨磨练的主线叙事肌理交代清晰,另一方面又将青春类型纳入更为宏大的家庭史叙事建构中,将传统伦理秩序和现代生存内涵的主题加以重音强调,最终形成了现实主义创作姿态下现实生活与戏剧事件互文并行、人物个像与社会群像交融共存、日常纷扰与人生命题彼此注解的史诗性叙事格局。在空间运用上,影片并没有刻意分化不同空间叙事类型的表意倾向,而是非常灵动地以人物的叙事流转为轴心进行空间切分,空间附着在人物身上成为角色建构的规定情境,同时因人物之间聚合离散的戏剧关系,空间又互相交织,彼此呼应。
由此可见,该影片虽然强调常态化生活空间的世俗性、趣味性,但对这些空间的意义进行了富有意味的叙事创设,核心场景由此也实现了较为清晰、系统的叙事象征,如驾校训练场、家、课堂等一系列空间序列,形成了宏观叙事层次的内指性整体风格。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仍需注意到这些空间序列建构的内在逻辑,尤其是反类型的空间运用,即如何有效规避类型空间的常规叙事表意指向并重新建构起遵从家庭、伦理、青春、成长等史诗倾向的复合类型逻辑。
《热带雨》则在叙事格局与主题深度层面较《阳光普照》稍显局促,但其叙事完成度和影像质量却并不逊色,虽然故事背景和具体事件设定都定位在异乡主题的叙事语境中,却也依然带有明显的杨德昌电影创作模式的痕迹。从某种程度上,这部电影可以被视为一部女性成长史, 时间的设置如同故事格局一样凝练且集中,时间是生活流叙事的催熟剂,更是女主人公离乡与返乡这一段心路历程的主题写照。叙事过程中鲜被提及的日常时间存在,成为事件从开始到结束的灵魂牵引,既不乏哲思般的超脱感,又透露出宿命般的荒诞意味。在处理空间的手法上,《热带雨》与《阳光普照》也有共通之处,但相对而言,《热带雨》更注重空间的简化处理,具有明确的两点一线式特征:家与学校作为最平凡的日常空间,不仅承担着交代人物身份变化以及具体行为动机的叙事任务, 并且在女主人公离乡——返乡的内指性叙事逻辑的观照下,二者也产生了深层的符号象征意义,隐喻了现代社会女性深陷泥泞的生活姿态,以及内心世界对于世俗生活的挣脱与逃离的现代理想。
(二)叙事姿态:生活真相与生命体验的二律背反
杨德昌电影以对现实世界深刻的洞察力而被誉为“台湾社会的手术刀”,不可否认,杨德昌在其电影中始终保持一种冷眼观之的叙事姿态,使得生活總是带有几分严酷色彩,凸显出“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的尼采式哲学意味。严肃沉郁的戏剧风格,同时也让现实书写少了几分回旋的圆润,随之将生活的真相推向一种极致化的生命体验,因此杨德昌电影中关于人物命运的设置总是不免引向宿命或极端的终结。
在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导致人与现实出现尖锐冲突时,杨德昌式的叙事姿态显然是对现实生活最敏锐直接的反应,犹如一面放大镜洞悉浮华背后物欲的残酷与人世的荒凉。随着社会加速转型趋向稳定,日常生活中现代性矛盾趋向暂时的缓和,“我们正在进入后现代性的阶段,那就意味着,社会发展的轨迹正在引导我们日益脱离现代性制度,并向一种新的不同的社会秩序转变”,即“一种新的社会-政治议程逐渐形成”[1]41,而“在现代社会活动数不清的背景中,构成日常生活的种种彼此相遇(Encounter)的,是被霍夫曼称之为‘世俗的不经意(Civilinattention)的东西”[1]70,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由之前较为明确的对抗转变为含混、朦胧的默认。而如杨德昌般试图从相对残酷的生活真相中攫取生命体验的电影叙事,恰恰可能会偏离了生活真相。不难发现,当代人探究生活真相的热情早已经被投注于生命体验的注意力所掩盖,因此电影书写中常常着重以戏剧性目标需求下的生命体验作为叙事中心,进而探讨生活的真实面貌,二律背反则是生活真相与生命体验无法从根本意义上统一的主要原因。
在《阳光普照》中,人物命运设定具有鲜明的戏谑感,故事开篇整个家庭形象的建构从父亲对于两个儿子的态度开始,兄弟二人两极化的人物对比,完全照应了中国传统社会关于子嗣家训的判断标准,传统意义上的多子多福的家庭观念在这里却遭到了现代性质疑,顽劣忤逆的小儿子似乎成了这个家庭的“肉刺”,这样的设置也暗示了平凡生活中暗流涌动的矛盾。在大儿子深夜突兀地选择了自陨之后,关于阳光普照的生命主题才逐渐显露出来,纵使影片在叙事旨向上彰显出强烈的人文关怀,着意引导我们秉持传统道德的理想信念不畏苦难继续向前,却依然无法掩盖戏剧背后的事实,毕竟生活的底色是悲凉的。同样的叙事姿态在影片《热带雨》中也有体现,看似简单的两点一线的日常生活,却令人陷入漫无止境的烦闷与苦恼,这正是关于热带雨主题象征的立意所在,一份带有青春叛逆色彩的中学生的情感依恋,虽然在人生冷色调婚恋生活中有如休止符一样偶然出现,却也未能避免地陷入不伦之恋的含混暧昧,生活真相的揭示带来的是平添烦扰的无奈的生命体验,主人公经历了人生的风雨,兜兜转转的归乡之举,纵使心灵得到了短暂的慰藉,也难免带上了对世俗生活的思辨姿态。影片创作中所运用的这种叙事姿态,借助常规人物关系之间的戏剧奇观建构,充分放大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落差,实现了现代社会秩序中人自身无法突破的困境书写。
二、世俗的理想与理性的思辨
《阳光普照》与《热带雨》在叙事立意层面同样地运用了象征隐喻手法,因此也被认作是后杨德昌创作规律的证据之一,这些创作手法与杨德昌电影叙事中常运用潜文本意义指涉的创作习惯在艺术理念层面是一致的,是一种对于后现代文化秩序中世俗的不经意的深切关注与内涵阐释。事实证明,这种方法使得现实主义创作的世俗化取材和主题表达有效形成了潜在、多层的对话关系,更能够有效突破世俗生活流叙事在主题表达上含混散淡的局限。
现实的苦难千姿百态,如何以一种近似平和的姿态开启生活叙事,以便揭示人的精神世界,这是自欧洲现实主义电影浪潮之后绕不开的核心问题。时代化、本土化的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离不开原生生存境况、生活周边问题书写,因此将这些原生性生活片段进行贴合时代精神和审美心理的意象处理是必不可少的过程。在《阳光普照》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把握时间、掌握方向,这是父亲在驾校工作的座右铭,也是他人生理想和信念所在,带有鲜明的存在主义色彩,强调积极的市侩进取姿态,与传统儒家倡导的中庸思想大不相同,这一主题之下的现实叙事也展现出时代变迁的彻底性。而荒诞的是,时间与方向这两个表面看起来带有现实意味的人生概念,却同时又是虚无玄妙的哲学问题。当平凡人生的不平凡苦难突然降临,被父亲视如时间、方向的长子,选择了以悄然的自我结束离开,这一变故对整个家庭而言几近釜底抽薪,也是对父亲作为中国式家庭权威迎面一击的嘲笑,千百年来维系的传统伦理与秩序似乎在这一瞬间轰然倒塌。回顾杨德昌电影的叙事创设手法和主题表达,不难发现,强调当下性对传统性的颠覆和反叛,以此形成精神诘问,同样也是解读生活与理想关系的不二方法。《热带雨》开篇是亚热带雨季即将来临的雨天行车情境,这种带有鲜明象征意味的生活暗示,与其将之视为阴郁的心理书写,倒不如视其为对现实人生进行的隐喻影射,是一种《雷雨》般古典戏剧式的开场模式。在叙事情节的外在表现形态上,该影片则采取了在生活流中发现典型矛盾的现实叙事倾向,强调了情节基调的节奏,并实现了主线矛盾信息节流。与《阳光普照》不同的是,《热带雨》并没有像父亲希冀的有关时间与方向的那样玄妙高远的理想,有的只是一个女人关于伦理天性的世俗书写,在其人物塑造上强调的是作为妻子与母亲身份的最平凡期待,然而生活依然以一个不大不小的情感玩笑中断了这样的世俗希望,恰似命运回赠的一记既痛又痒的耳光。这种现实荒诞话语表述的背后,依然继承的是杨德昌剧作式的现代悲剧性主题精神,“现代都市的人群大多数都带着面具生活,而且我们的内心总是在逃避我们”,这种书写“从表象和内心的关系上抓住了人性,也抓住了现代都市生活造就的人与人之间日渐孤立和疏远的关系的悲剧性”[2]。
面对生活与理想之间的落差,到底该如何在世俗中继续前行,这才是人生的难题。这些影片延续了杨德昌电影中直面现实的书写姿态和主题精神,摒弃了冷面单调的批判面孔,转而以更为温和的思辨口吻提出了当代人灵魂深处的疑问。
三、庸常的身份与奇遇的人生
杨德昌电影擅长编织复杂多变的人物关系图谱,寄携着各种现实矛盾的角色相互交织在一起,织绘成了复杂多变的现代人物关系图谱,有如观赏一个戏剧情境继发的万花筒。这些人物大多是拥有平凡人生的小人物,在作为他们丈量人生的唯一“标尺”的日常生活面前,他们却能以带有思辨色彩的戲剧存在感映照出现实社会的失序与冷漠。存在主义哲学主题的宏观叙事理念,使得人物庸常的身份具有了深层的戏剧表现力,因此,在主题观照下的戏剧可能性也透出鲜明的黑色审美意味。奇遇的人生,不仅是对难以琢磨的命运的感慨,更是对当下人类生存秩序变迁的诘问。
对个体人物身上游离感的强调,使得每个角色与混乱的社会秩序通过表意互文联系起来,这是杨德昌电影剧作中整体人物书写风貌形成的重要原因,也为当下的电影创作个体形象及建构人物谱系提供了有效的借鉴。总览每个家庭成员的身份和家庭地位,我们会发现《阳光普照》中的这个家庭更似一个拼凑而成、杂乱无序的群体组织,传统伦理认知中家庭的凝聚力已经荡然无存,母亲是一个夜总会的化妆师,父亲是一个驾校的教练员,大儿子是一个临考大学的学生,小儿子是一个胡混“江湖”的服刑少年,个体人物本身临近社会边缘的身份与职业,在这种家庭景观下更带上了疏远、孤独的群体特质,使得这个家庭构成呈现为一个反传统概念的存在。将这些主体人物置于生活化的叙事场景中,不啻为一种对人物生活的反向书写,在他们身上发生着的,并非如生活化场景一样的存在,而是在生活流掩飾之下类型化的戏剧冲突:黑帮少年寻仇入狱、未婚先孕少女上门、突如其来的中年丧子、忤逆少年的家庭回归、暗中护子的驾车杀人……在这样的类型叙事序列按照人生奇遇的叙事逻辑重组之下,其人生也展现出具有深层意义指涉的陌生化现代叙事特质。因此,这些人物自身的社会定位并非构成其美学气质的唯一因素,而对生活流叙事中以审美震惊为目标的类型化情节靶向甄选才是其形成的基础条件。这种戏剧效果既遵照了杨德昌电影剧作对现实主义典型化人物及事件的处理手法,也对小人物人生奇遇的叙事模式做出了试图超越时代书写的有效尝试,关于这一层面的探讨将在后续论述中集中展开。
《热带雨》中的女教师作为一个到新加坡定居并工作的移民者,在学校承担的课程也是被轻视的中文课,边缘人的身份与庸常的世俗生活一样,都带有强烈的自我注视放大意味,因此影片创作者将主人公的日常生活通过家庭与学校的二元场景逻辑进行了戏剧简化,但从叙事层面有效强化了情节背后主题书写的注意力,在场景戏剧性强弱对比层面又直接突出了校园情境下发生的触及伦理底线的师生恋,伦理禁忌在沉闷压抑的异乡叙事下显得更具奇观色彩。这种人生之路的异化转向,如果洞察其叙事创意,则会发现不过是杨德昌电影以来关于青春爱恋母题的逆向书写。
四、传统家庭的衰落与现代性亲缘书写
在上述两部影片中,关于生活暗流的书写也有自身共性的特点,都是从生活书写开端,最终以理想书写收尾。《阳光普照》以少年犯的江湖恩仇展现生活秩序的错位与矛盾,结尾以父亲护犊平仇、母亲坐上儿子的脚踏车重新实现家庭秩序的回归,完成阳光普照的主题阐释。《热带雨》以异乡和单调压抑的生活常态开端,以返乡和一段生活的告终、另一段生活的开启结尾,这种叙事开端与结局的设置,代表了一种现实主义创作对于时代生活叙事解读的思维方式,事件处理的开与合,都是建立在现代社会生活的不稳定性的前提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秩序与传统社会秩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关系,传统社会生活作为形成社会行为准则标准的惯例,在其辐射下的任何当代生活书写都带上了对照的批判意味。无论上述提到的影片中有游离感的人物形象,还是缺乏凝聚力和沟通感的家庭形象,都昭示着传统家庭的衰落,其现实存在的风险性自然成为了戏剧创设的核心依据。在杨德昌的电影中,关于传统家庭危机的书写一般都采取直接的书写姿态,人与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内在关系,一地鸡毛的日常纠葛,传统家庭形象与家庭的作用在这些叙事文本中退到了无关紧要的地位,甚至传统的家庭观念成为人物精神世界的一道枷锁,因此传统家庭关系也不再作为能够展现人的精神内核的基础条件。
在《阳光普照》中,亲情与阳光公平性的主题象征形成了叙事层面的表意互文关系,有效地解决了传统家庭形象消散之后如何观照亲情的逻辑矛盾,也让家庭形象在影片结尾重新回归应有的伦理秩序,表现出现代犬儒主义倾向下的理想情怀。《热带雨》中的家庭镜像就更为鲜明地表现出日常残缺感,家庭成员的构成主要是儿媳和瘫痪在床的公公,而丈夫不过是难得出场几次的“过客”,异国他乡的家的形象充满了人生驿站的落寞意味。
杨德昌电影剧作模式下的现代性亲缘关系书写,不再强调以血缘、亲缘关系为本的伦理秩序,而是着重刻画该秩序崩坏后现代社会中以家庭为基本载体的亲缘危机,在此影响下日常生活的家庭秩序甚至社会秩序也随之变得捉摸不定。对于现代性亲缘关系的书写,在《阳光普照》和《热带雨》中都作为直接关系主题表达的核心要素存在。依此审视,《阳光普照》中的父亲与小儿子之间的关系变化,正是亲情从失去到回归的重建之路;《热带雨》中师生之间由熟悉的陌生人到具有“俄狄普斯”母题意味并介于师生、母子、爱人多重身份的戏剧性关系,每种关系无不是对传统伦理关系的颠覆及改写。现代性亲缘关系,不仅仅让整体剧作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戏剧可能,也充分反映出现代社会伦理关系对于人的存在的多义性价值。
如何有效处理现实社会于人的存在的矛盾关系,典型化呈现人的内在精神困境和世俗理想,并形成具有独立审美品格的影像表达系统,已经成为制约全球化影像传播局势下华语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关键问题。通过对第56届台湾金马奖两部热门影片的简略梳理,其凝视困境与深度写实的艺术姿态和举重若轻并化繁为简的戏剧化叙事策略,可谓在处理内涵复杂多义的现实基调故事时为我们提供了卓有成效的影像呈现思路,同时也赋予华语现实主义电影创作深广的创作潜力及艺术信心。不难发现,杨德昌剧作模式影响下的华语电影创作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切实的进步,并在逐渐形成现实主义创作姿态下的倾向于内指性主题表达以及深入的时代性生存书写的特有剧作模式,这一创作趋势也定将为华语电影后续创作跳出传统现实创作窠臼提供有效的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1]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 何佳.一座城市和一种文本的焦灼生长——试析杨德昌的电影剧作[J].当代电影,2007(6):34-35.
[责任编辑:王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