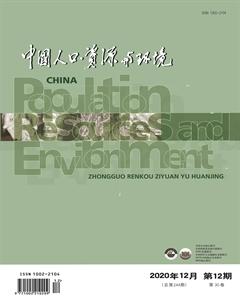农户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
李芬妮 张俊飚 何可



摘要 文章利用湖北省1 061份农户数据,构建二元Logit模型与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结果发现:①外出务工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具有显著影响,而村庄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家庭总收入、环保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住所周边垃圾集中处理设施亦能有效推动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②对于村庄认同程度不同的农户,外出务工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作用存在差异。随着农户的村庄认同增强,外出务工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正向作用得以强化,尤其是当农户的村庄认同度超过门槛值时,外出务工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将由负转正,即村庄认同在外出务工影响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上可以发挥扭转乾坤之效。③在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使用在村居住年限作为工具变量进行IV Probit估计,结果发现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是稳健的。文章揭示了外出务工作为资本要素涌入乡村的纽带,非但不必然引起农村衰败,反而为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等公共事务创造了禀赋条件,但只有触发村庄认同这一关键机制,方能实现外出务工“扬长避短”效果的发挥。基于此,从培育与增强村庄认同程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大环境保护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及增加垃圾集中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四方面提出了推动农户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改善建议。
关键词 外出务工;村庄认同;人居环境整治;IV Probit;门槛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20)12-0185-08DOI:10.12062/cpre.20200424
垃圾围村、污水横流等现象不仅严重威胁农村居民的生活与健康,更困扰着我国农村可持续发展[1]。为此,自2014年开始,党中央一号文件连续6年聚焦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问题。然而,据《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三五”规划》统计,截至2017年,全国仍有40%的农村生活垃圾未能得到合理处置,78%的农村缺乏配套的污水处理设施。在已实施的人居环境整治项目中,农民认为实用性不足[2],环境整治效果不够理想[3]。可见,政府主导下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效果尚未达到预期。究其原因,或在于对农民环境治理的内在需求及引导农户参与积极性的关注度不足[4]。為此,如何充分调动农户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成为关系我国农村环境改善和美丽乡村建设成效的重要问题。
1 相关研究综述
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是造成农户参与村庄建设动力薄弱、农村公共事务陷入“治理困境”的根源之一[5-6]。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离开户籍所在乡镇的外出农民工总量达1.73亿人。如此庞大的外出务工群体将导致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缺乏有力的参与者[6],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亦不例外。对此,学术界普遍就外出务工的负面影响达成了共识[6-7],指出农户作为农村人居环境的建设主体[8],其外出务工意味着农村优质劳动力脱离本村,转而在外地谋生,这将引发农户生活面向的转移[9]与家庭决策主体的变化[7,10],从而降低农户对人居环境整治等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度和关心度。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上述研究视角忽略了农户在心理认同上的差异,即在农户们均踏上外出务工的路途后,村庄认同的差异或许将引致农户在人居环境整治参与上出现分歧,从而走向不同的终点。具体来说,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决策是对比成本与收益后的结果。高村庄认同度的农户往往对村庄事务参与拥有较低的心理成本,对于参与整治所带来的村庄环境改善、环境提升后的自豪感和荣誉感等结果预期较好。因此,即便其外出务工、身居千里之外,出于对村庄的热爱与依恋,这类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依旧不减。相反,低村庄认同度的农户不仅容易出现在外务工难以享受环境改善等整治好处的不平等心态[11-12],同时,外出务工所引致的空间距离还将削弱其同村庄之间的情感联系及社会关联[13],导致他们在参与整治上的预期收益较低、心理成本较高,从而对人居环境整治等村庄公共事务兴致不高。可见,不同程度的村庄认同将导致外出务工农户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方向与程度上产生差异。如若忽略农户在村庄认同上的差别而进行分析,或不足以完全阐释外出务工影响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内在机理,所得结论也恐难以有效指导农村环境治理实践。由此,现实中,村庄认同能否推动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并在外出务工影响农户人居环境整治参与行为中发挥作用?上述问题的回答对于调动农户参与整治的积极性、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效果,进而实现绿水青山、美丽乡村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研究为本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仍有改进空间:第一,研究内容上,已普遍关注到外出务工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等农村公共事务的负面影响[6-7],但大多忽略了农户在村庄认同上的差异,将目光聚焦于村庄认同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研究并不多见;此外,现有相关文献尚未关注到村庄认同与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之间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这或将对经验判断产生严重干扰。第二,研究方法上,已有文献在分析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时,多基于案例或定性分析,利用农户调研数据展开实证研究的文献相对有限[1]。基于此,本文利用湖北省1 061份农户数据,构建二元Logit模型与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探讨二者之间的作用逻辑,并选择工具变量克服村庄认同和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以期为农村环境整治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并为建设美丽宜居农村、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供一定参考。
2 理论分析
2.1 外出务工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
外出务工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产生负向影响。一是外出务工将引发农户生活面向由村内向村外转变,进而影响农户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热情。在农村价值生产能力趋于弱化的背景下[9,13],农户通过外出务工不仅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入,同时还在村庄之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就使得农户对村庄的依赖程度降低[6,13],生活重心更偏向于村外的务工地,而对村内的环境建设问题缺乏关心和参与热情。二是外出务工将引发家庭决策主体的变化,即女性决策占比增加[7,10]。由于男性往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力军,女性被迫成为了家庭事务的决策者[14]。但不同于男性关注公共领域、愿意在公共事务上积极发声以显示自身的影响力,女性更多将目光与精力聚焦在私人领域与家庭事务的处理上[7],从而对人居环境整治等村庄事务缺乏关心[15-16]。
但事实上,外出务工也可能通过对农村劳动力资本禀赋的强化[17],以形成对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参与行为的正向影响。农户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不仅容易接受较为先进的环保思维和理念[18]、增强环境整治认知水平,城市整洁环境还激发了农户改善家乡生态环境的强烈欲望及提高居住环境品质的迫切需求[18],加之外出务工还有利于推动农户经济实力的增强[19-20]以及信息获取渠道的扩展等,从而使得农户具备了对环境整治的支付能力、追求优质环境的条件及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行动能力。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竞争性假说1a和1b:
假说1a:基于外出务工引发农户转变生活面向与女性决策,外出务工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参与行为存在消极影响。
假说1b:基于外出务工强化农村劳动力的资本禀赋,外出务工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参与行为存在积极作用。
2.2 村庄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
村庄认同指农户与村庄在生活和成长过程中相互作用形成的认同、依恋、归属等情感联结关系[21],包括对村庄的身份、文化和價值观的认同[22]。村庄认同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影响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一是村庄认同有利于减少农户以破坏村庄人居环境为代价的利己行为:高村庄认同度会推动农户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23],并对村庄形成稳定的未来预期[9],从而促使农户从长期利益出发,主动在村庄人居环境整治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以谋求村庄的长远发展。二是村庄认同有利于推动农户树立保护村庄环境的行为目标:高村庄认同度会促使农户形成共同体的感觉,推动农户将个体行为目标转移到集体层面[24-25],并降低农户参与村庄事务的交易成本,增进村庄内部农户之间的交流互动[26],增大就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达成合作的可能性。三是村庄认同有利于促使农户表现出对村庄环境更友好的态度:人文地理学的相关观点认为,人们对资源环境的态度和行为受由地方依恋等形成的“人-地关系”影响[27],地方认同和依恋能促使人们表现出对环境保护的支持态度和亲环境行为[28-29],而“地方”的概念可延伸到“村庄”[21]。由此,当农户拥有高村庄认同时,将对村庄人居环境表现出更友好的态度,从而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2:村庄认同对农户人居环境整治参与行为存在直接的促进作用。
不同村庄认同度下外出务工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即随着村庄认同的增强,农户将外出务工积累的资本禀赋用于人居环境整治上的可能性越大。具体来说,当农户是低村庄认同度时,其自身与村庄的情感联结关系较弱,而外出务工所引致的空间距离将导致农户与村庄之间的纽带联系愈趋脆弱[12],因此,该类农户即便通过外出务工积累了一定禀赋,低村庄认同也使得他们不愿意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到村庄人居环境整治中。相反,当农户是高村庄认同度时,意味着其与村庄的情感联结关系较强,这类农户即便是长期在外务工、不在村庄,也将格外关注村庄事务动态、心系村庄建设[9],故而,他们不仅会积极响应环境整治行动,将部分务工收入所得投入到人居环境整治中,还将借助其在外务工的信息获取优势,主动积累有利于村庄环境改善的技术、方式等。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3:村庄认同会增强外出务工在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上的正向作用。
3 数据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课题组2018年7—8月对湖北省鄂州市、黄冈市、武汉市和荆门市农户开展的抽样调查。选择湖北省作为调查区域的原因在于:根据《湖北农村统计年鉴2018》的数据显示,湖北省2017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达1 129.99万,是我国中部地区劳务输出大省。选取这4个地区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经济发展水平。武汉是湖北省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荆门和黄冈处于中等水平,而鄂州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弱。二是外出务工状况。黄冈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位居省内第一,武汉和荆门分列第八位与第十位,而鄂州的外出务工人数位居省内倒数第二位。三是环境质量状况。四地均属于国家推广环境治理行为的重点区域,在研究农户人居环境整治参与行为方面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次调研采取分层逐级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选取样本农户,具体的抽样过程为:在每个县(市)随机选取3~4个乡镇,再在每个样本镇随机选取2~3个样本村,最后在每个村随机选取10户农户进行调研。剔除无效问卷后,适用于本研究目的的有效问卷共1 061份。此外,数据的收集由调研人员与农户“一对一”访谈入户和观察所得,调研问卷的编制和管理均为接受过相关培训的调研人员负责,问卷内容涉及家庭特征、农业生产经营状况、环境治理认知、参与意愿及行为等方面。
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为:男性户主占比达89.92%;户主多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比达50.42%;户主受教育程度多为初中及以下,占比达85.39%,受到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户主较少;73.61%的农户家里没有党员或干部;家庭规模多以3~5人的中小型家庭为主,占比达57.68%;家庭年收入集中在1~10万元之间,占比达69.46%。根据《湖北省统计年鉴2018》的数据显示,2017年湖北省农村居民平均每户家庭可支配收入为5.15万元,户均常住人口为2.87人,由此可知,本文研究样本基本符合湖北农村现实情况,具有一定代表性。
3.2 模型选择
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户是否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基于数据的有限性,并参考闵师等[1]、唐林等[22]、李芬妮等[25]的研究,用农户是否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予以表征。之所以选取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原因在于:生活垃圾的随意丢弃是造成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的重要源头之一,农户能否集中处理生活垃圾不仅是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最迫切的工作,更关系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11]。由于农户是否
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属于二分类变量,因此,本文选择构建二元Logit模型。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式中,Y.*是不可观测的潜变量,LM是外出务工变量,VI是村庄认同变量,Control是控制变量,α、、δ为待估系数,ε代表随机扰动项。
进一步地,在(1)式中加入LM与VI的乘积项,以检验村庄认同在外出务工影响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中的作用,并构建门槛回归模型,比较不同村庄认同程度下外出务工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其中,Yit代表农户是否参与人居环境整治,q是阈值变量,即农户的村庄认同程度,γ是要估计的阈值。(2)式可以写成:
式中,ε服从独立齐次分布,I是指标函数。估计原理是基于最小残差平方和(SSR)。(3)式可以有效识别出不同村庄认同程度下,外出务工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在阈值以下和阈值以上的差异。
3.3 变量说明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为外出务工与村庄认同。就外出务工而言,本文参考王翌秋和陈玉珠[30]、钱龙和钱文荣[20]等研究,以“外出務工人数占家庭总人口比重”作为表征。村庄认同方面,本文参考唐林等[22]、李芬妮等[25],设定了“我认同本村的传统文化习俗”“如果搬离村庄,我会感到很留恋”“我与村里其他成员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我很喜欢生活的村庄”“我非常关心村庄事务”5个指标。参考李芬妮[25]的做法,本文进一步对表征村庄认同的5个具体指标进行等权重加总取平均,求得农户总体的“村庄认同”。
此外,村庄认同可能同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相互影响,产生内生性问题,导致回归结果的估计有偏。这是因为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后,随着整治带来的村庄环境优化与改善,农户可能会增强其对村庄的认同度。为解决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在村居住年限”作为工具变量。选择的原因是:首先,一般来说,农户在村的居住年限越长,农户对村庄的认同度会越高,满足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相关性的条件;其次,农户在村的居住年限同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本身并没有直接关联,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因此,“在村居住年限”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
为排除干扰,本文还设置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收益特征、认知特征和地区特征可能会影响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控制变量。所有变量的含义与赋值见表1。
4 结果分析
4.1 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
本文运用Stata15.0软件,通过逐步引入解释变量构建二元Logit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发现,随着变量的逐步纳入,模型的伪对数似然值和伪决定系数逐渐提升,说明回归模型的解释力也在逐步提高;此外,模型1~模型3中各变量的系数符号基本一致,显著性水平也未发生变化,Wald chi.2值在1%检验水平显著,表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1)外出务工。由表2中模型3可知,外出务工在5%的统计水平上负向显著,表明外出务工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具有负向作用,这与高瑞等[6]、贾蕊和陆迁[7]的研究发现类似。可能的解释是,家庭外出务工成员占比越大,农户的生活面向越倾向于村外,引发女性决策的可能性越大,同时,其所能享受到人居环境改善等整治利益的程度越少,因此这类农户参与整治的积极性较弱。
(2)村庄认同。由表3中模型3可知,村庄认同在10%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表明村庄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具有积极作用,假说2得到验证。农户的村庄认同度越高,意味着农户从心理上接受并认可村庄成员身份[31],不仅愈发重视与关心村庄的长远发展与建设[9,22],同时对参与整治获得的宜居生活环境等共同利益的认知越多,从而响应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可能性更高。
(3)控制变量。由表2中模型3可知,家庭总收入、环保政策的了解程度与住所周边垃圾集中处理设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家庭总收入在10%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表明农户的家庭收入越高,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更高。一般来说,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对居住环境的品质要求更高[32],对改善生活环境卫生状况的需求更强烈;加之其具备较好的经济实力,能够负担一定的环境治理成本,因而越有可能选择参与整治。环保政策的了解程度在10%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表明农户对环保政策的了解程度越高,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可能性更高。可能的原因是,农户越了解环保政策,往往也更能意识到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仅有助于村庄整体生态环境的改善,同时也有利于为自身创造一个整洁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故而参与整治的积极性更高。住所周边垃圾集中处理设施在1%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住所周边具备垃圾集中处理设施不仅有利于减少农户自行购买垃圾桶等人居环境整治的交易成本[22],同时还增加了农户集中处理生活垃圾的便利性,从而有效调动农户参与整治的积极性。
4.2 村庄认同在外出务工影响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中的作用
为了探究村庄认同在外出务工影响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中的作用,本文将外出务工与村庄认同的交互项纳入模型。考虑到交互项与原变量之间可能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在构建交互项之前,本文对原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即将原变量分别减去其均值后重新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中模型4可以看出,外出务工与村庄认同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表2中模型3的回归结果一致,说明模型估计结果是基本稳健的。进一步可知,外出务工与村庄认同的交互项在5%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表明村庄认同在外出务工影响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中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进一步,本文采用门槛回归模型,探究农户不同村庄认同度下外出务工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不同村庄认同度下外出务工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存在差异,且存在明显的门槛值。当农户的村庄认同度高于一定门槛值时,外出务工的系数将发生变化,即随着农户的村庄认同持续增强,外出务工的正向作用得以强化并促进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4.3 内生性检验
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在村居住年限作为村庄认同的工具变量进行IV Probit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由IV Probit一阶段回归结果可知,在村居住年限在1%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表明随着农户在村居住地时间越久,对村庄的认同度越高,同时这一结果意味着在村居住年限满足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且F统计量为33.78,大于10,表明在村居住年限不是村庄认同的弱工具变量。由IV Probit二阶段回归结果可知,Wald检验拒绝了村庄认同是外生变量的原假设,故可以认为村庄认同是内生变量。在村居住年限对于内生变量村庄认同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4.4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结果的稳定性,本文采用“外出务工收入占比”替代“外出务工人员人数占比”进行重新回归。表6为替换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表2、表3结果相似,表明本文结果是稳健的。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湖北省1 061份农户数据,构建二元Logit模型与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并试图回答村庄认同在引导外出务工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上“同途殊归”的问题。结果发现:第一,外出务工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具有显著影响,而村庄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家庭总收入、环保政策的了解程度与住所周边垃圾集中处理设施亦能有效推动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第二,对于村庄认同程度不同的农户,外出务工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作用存在差异,随着农户的村庄认同增强,外出务工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正向作用得以强化;尤其是当农户的村庄认同度超过门槛值时,外出务工的影响将由负转正。第三,运用IV Probit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外出务工及村庄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仍然显著。
本文的研究有利于重新审视外出务工在中国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作用,同时揭示了村庄认同的内在功效。虽然学术界普遍就外出务工引发的乡村事务“治理性困境”达成了共识,认为劳动力大量外流削弱了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但本文的结果表明,外出务工并不必然引起农村的衰败,相反,一方面,农户依靠外出务工增强了自身实力,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以外出务工为纽带,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得以较快地由城市流向乡村。因此,对于以人居环境整治为重要任务的乡村振兴战略而言,劳动力外出务工为其顺利实施注入一剂强心针,既衍生出挑战,又提供了机会。但需要强调的是,外出务工虽然实现了人才、资金、信息等要素的流动,但只有触发村庄认同这一关键机制,方能实现其“扬长避短”效果的发挥,即在村庄认同的驱动下,外出务工将通过强化农村劳动力资本禀赋实现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作用。因此,如何培育与增强农户的村庄认同,成为建设美丽乡村和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对此,本文提出政策启示,希望能对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推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有所裨益。
一是发掘村庄特有的历史记忆,增强农户的文化认同。一方面,村庄在改造与变迁的过程中,应注重对祠堂、寺庙、牌坊等原有传统风貌的保护,留住农户的家乡记忆与情感载体;另一方面,挖掘和传承村庄特有的风俗习惯、社会礼仪等物质与精神财富,合理、有序地开展祭祀宗族、舞龙舞狮舞灯等節庆民俗与集体文娱活动,为农户提供丰富多彩的公共生活,唤醒其乡土情结和家园意识。二是完善村庄治理模式,增强农户村庄生活的舒适度。依靠公众号、微信群等互联网平台,采取电子村务、网络参政等形式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提高农户对村庄事务、发展现状等信息的知晓度,也方便在外务工人员及时、便捷地获取村庄动态、参与事务决策,增强自身对村域事务的参与感。同时,村干部和党员等基层工作人员也应主动加强与外出务工人员的联系互动,始终把他们的意愿、诉求记在心上,使其时刻体会到家乡的关怀、记挂与温暖,从而强化外出务工人员对村庄的认同意识。
此外,鉴于家庭总收入、环保政策的了解程度与住所周边垃圾集中处理设施等亦能促进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因此,还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鼓励和引导人才、资金、技术等更多要素流向和投资农村,为农户创造更多的增收机会。二是强化环境保护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创新生态环保知识的宣传手段,如借助微信公众号、微博等互联网平台,扩大宣传普及范围,提升农户对环保政策的认知水平;同时,充分利用墙画、标语等生动形象的方式向农户普及人居环境“脏乱差”的危害性及其可能引发的健康损害,以增强农户对环境整治重要性的充分认识。三是增加垃圾集中处理等基础设施的修建投入,在指定专人定期清理、维护与检修设施的同时,引导农户主动监督并爱护设施,延长其使用寿命,降低农户参与环境整治的活动成本。
参考文献
[1]闵师, 王晓兵, 侯玲玲, 等. 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因素:基于西南山区的调查数据[J]. 中国农村观察, 2019(4): 94-110.
[2]杨欢. 少数民族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研究[D]. 贵阳:贵州大学, 2015: 62.
[3]孙慧波. 中国农村人居环境公共服务供给效果及优化路径研究[D].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 2018: 71.
[4]付文凤, 姜海, 房娟娟. 农村水污染治理的农户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8(4): 119-126,159-160.
[5]KLANDERMANS B. How group identification helps to overcome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2, 45(5): 887-900.
[6]高瑞, 王亚华, 陈春良. 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 26(2): 84-92.
[7]贾蕊, 陆迁. 外出务工、女性决策对农户集体行动参与程度的影响:以陕西、甘肃、宁夏3个省份农户调研数据为例[J]. 农业技术经济, 2019(2): 122-134.
[8]李伯华, 刘沛林, 窦银娣. 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自组织演化机理研究[J]. 经济地理, 2014, 34(9): 130-136.
[9]贺雪峰. 新乡土中国[M]. 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8-24.
[10]周春霞. 农村空心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选择:以默顿的结构功能论为研究视角[J]. 南方农村, 2012(3): 68-73.
[11]伊庆山.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问题研究:基于S省试点实践调查[J]. 云南社会科学, 2019(3): 62-70.
[12]程志华. 农户生活垃圾处理的行为选择和支付意愿研究[D]. 西安:西北大学, 2016: 85.
[13]王博, 朱玉春. 论农民角色分化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基于政策实施对象、过程和效果考评视角[J]. 现代经济探讨, 2018(5): 124-130.
[14]杨玉静.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妇女与环境关系评析[J]. 妇女研究论丛, 2010(4): 15-20.
[15]DOSS C R, MORRIS M L. How does gender affect the adoption of agricultural innovations: the case of improved maize technology in Ghana[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1, 25(1): 27-39.
[16]杨翠萍. 社会性别、比例政策与女性参与:以天津川村村委会选举为例[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4): 12-18.
[17]邹杰玲, 董政祎, 王玉斌. “同途殊归”: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8): 83-98.
[18]吴建. 农户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费用的支付意愿分析:基于山东省胶南市、菏泽市的实地调查[J]. 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24(2): 27-31,41.
[19]李宾, 马九杰. 劳动力转移是否影响农户选择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基于鄂渝两地数据的研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5(1): 182-191.
[20]钱龙, 钱文荣. 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生产投资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的实证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8(5): 109-121,158.
[21]胡珺, 宋献中, 王红建. 非正式制度、家乡认同与企业环境治理[J]. 管理世界, 2017(3): 76-94,187-188.
[22]唐林, 罗小锋, 张俊飚. 社会监督、群体认同与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基于面子观念的中介和调节作用[J]. 中国农村观察, 2019(2): 18-33.
[23]王亮. 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归属感的形成[J]. 求实, 2006(9): 48-50.
[24]CHEN X P, WASTI S A, TRIANDIS H C. When does group norm or group identity predict cooperation in a public goods dilemma: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idiocentrism and allocentris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07, 31(2): 259-276.
[25]李芬妮, 张俊飚, 何可, 等. 归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北省1 007个农户调研数据[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0, 29(4): 1027-1039.
[26]辛自强, 凌喜欢. 城市居民的社区认同:概念、测量及相关因素[J]. 心理研究, 2015, 8(5): 64-72.
[27]HERNANDEZ B, MARTIN A M, RUIZ C, et al. The role of place ident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in break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0, 30(3): 281-288.
[28]VASKE J J, KOBRIN K C. Place attachment and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001, 32(4): 16-21.
[29]CARRUS G, BONAIUTO M, BONNES M. Environmental concern, regional identity, and support for protected areas in Italy[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05, 37(2): 237-257.
[30]王翌秋, 陈玉珠.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農户种植结构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苏和河南的调查数据[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 37(2): 41-48,111.
[31]吴晓燕. 从文化建设到社区认同: 村改居社区的治理[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50(5): 9-15.
[32]张童朝, 颜廷武, 何可, 等. 资本禀赋对农户绿色生产投资意愿的影响:以秸秆还田为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8): 78-89.
(责任编辑:刘照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