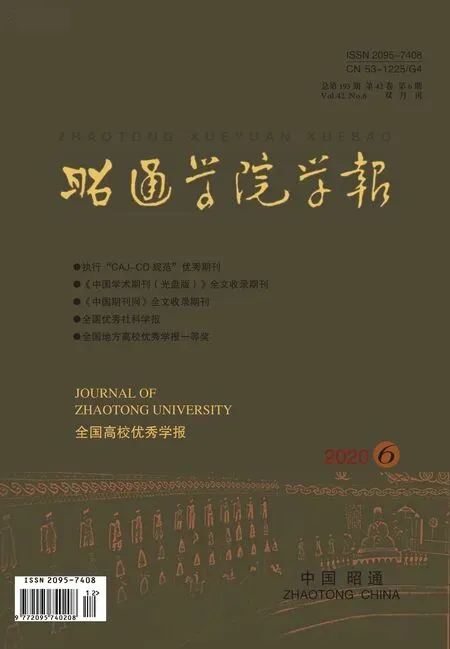林清玄散文的生态审美意蕴
刘 斌
(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
1962年,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标志着世界性的生态文学创作繁荣时期的到来。生态文学的创作中心是反思“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统治下,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失衡,主张回到“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大化流行的原始和谐状态。当代生态文学的建设方向就是在环境危机、生态平衡被破坏的大背景中,重建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
相较同时代的创作者,林清玄生态散文的特殊魅力体现在其自觉的生态理性以及叙事中的民间立场使其生态意识具有强烈的情境性、连续性和实践性。同时,世界眼光和学理深度也使得林清玄的笔落走向不完全受情感的牵掣而具有理性内核,进一步推动他转向对现象背后人与自然的生存矛盾、社会转型期人性普遍失落造成的精神危机的思考。可见,林清玄散文中蕴含的独特的生态审美意蕴,既是特殊时代背景赋予他的使命,也是他个人独特思想光辉的闪现。
一、林清玄生态审美意识的历史渊源
地理环境、经济政治等因素深刻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和生活方式又会影响一个民族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风尚,而每个艺术家的审美体验必然会与其相关创作挂钩,所以审美主体在进行艺术创造之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林清玄生态散文的形成渊源与他对童年记忆的理性触摸、老庄哲学的反思以及独特的佛学修养密切相关。
林清玄生态审美意识的萌芽与其童年农村生活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林清玄小时候和父母生活在乡下,清新芳香的空气、淳朴善良的乡亲、勤劳恩爱的父母、周边多种多样的花鸟鱼虫共同构成了鲜活的艺术创作现场,奠定了他生态散文最初的基调。自年少背井离乡后,林清玄的乡愁情怀愈演愈烈,他对童年记忆的理性触摸在散文中突出地表现为对家乡劳动者的生存方式、民俗风情、花鸟草木等多方面的体谅和关照。如《是天空的,也是海洋的》中,故乡穿蓝衫、黑裤的客家女子是林清玄笔下女性形象构成的基本要素之一;如《时到时担当》里,家乡俗语“时到时担当,没米就煮番薯汤”[1]106为他恬淡风格的形成输入了乐观和积极的力量。除了对童年场景的追忆,林清玄生态思想中的故乡情结还表现为对旧时生活状态的反思。一方面,林清玄叹息旧时物质生活的匮乏,可另一方面,林清玄又向往贫苦生活背后那简单、充实的生活方式。这种矛盾的心理或隐或显地贯穿了林清玄整个创作历程。
相比对童年记忆的钩沉,独特的佛学体验成为事实上的林清玄的生态审美意识的发端。林清玄三十二岁时为使精神免受生活的苦役,毅然决然地入山修行,深入经藏之中,以祈求灵魂的净化和肉体的涅槃新生。佛教文化在形成林清玄万物平等意识和悲悯情怀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独特的佛学创作视角。往后,林清玄便以佛门居士与自由作家的双重身份游走于世间,无论是在意象选择、艺术风格还是生命感悟方面,林清玄都擅长通过将佛学体验与散文创作相结合的方式体现他的生态审美诉求。林清玄擅长取材于佛学,这从他的许多散文标题中就可以直接看出:《色与空的追寻》《空中自有无限的层次》《清净之莲》《木鱼馄饨》《佛鼓》《金刚经二帖》《黄昏菩提》等等,这类散文的意象都是来自于佛教典籍、作家自身的佛学经历与感悟。更具体的例子在于,在佛教中,观音、佛祖以莲花为座,普法于人世,而莲花在林清玄笔下出现的次数最频繁,这与林清玄深厚的佛学修养和独特的佛学旨趣是分不开的。此外,因为作者的情感个性浸透了佛学的深刻影响,所以他始终保持着平稳的思考节奏和恬淡、诗性的文风。总之,林清玄将佛教文化融入文学领域,用散文语句弘扬、阐释佛法,不仅让读者领略到一系列久而弥笃、新颖独特的佛理意象,还为后人的写作方式创立了典范。
最后,林清玄还受到南派六祖慧能的“顿悟”禅学的影响,主张审美“刹那的直觉”,即主体在美感活动过程中完全摆脱功利、道德等实用因素的干扰,孤立绝缘、聚精会神地欣赏事物的形象,并且创作出一个活泼玲珑的意象世界。这点可以从他悟“道”的三种方式而见出:第一种,从动植物中悟“道”:由蜜蜂酿蜜悟出人只有付出千辛万苦的努力才可以换来生活的甘甜、由夏天小狗跑到空调下乘凉悟出万事万物都有生存与繁荣的权利等;第二种,从平凡人与事中悟“道”:由学插花悟出表面最严苛形式的事物实际上具有最大的自由、由总统林肯的经历悟出旁人善意的批评是锻炼健全性格必不可少的因素;第三种,从阅读书籍中悟“道”:如阅读《观公孙大娘底子舞剑器行并序》时便惊叹想象力不可思议的美,悟出人们应该摒除五色对我们的叨扰学会用心去感应万物。
此外,老庄哲学在林清玄的生态散文创作环节中也处于枢纽地位。就审美对象来看,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2]117宇宙万物一切都是从道衍生而来,本质都是“气”,并没有等级之分,且万物自己运动,充满活力。因此,林清玄在选择创作对象时,无意识地将万物入诗并发掘自然内在的生命力。如在《一滴水汇入大海中》中他就巧妙地发现“水”时刚时柔的动态性质,从而“以我为主”地推论出万物都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从审美心胸的角度来看,老子主张“涤除玄鉴”,庄子主张“心斋”、“坐忘”,两者都突出强调主体必须超脱利害观念才能解放创造力、实现对“道”的观照,达到“至美至乐”的境界。林清玄的生态审美精神也常常是超脱的、清洁的,他批判人的浊乱内心一旦与现实世界的脏乱相遇便会发生化合作用,致使各种眼花缭乱的龌龊鄙夷之事来,而这种危险的情境若不能追本溯源,从源头治理,便会形成难以撼动的常态,久而久之,世界则“法已末,道已穷”,天地之间再无灵气往来。
二、林清玄生态审美意识的表达和多维呈现
林清玄在生态散文的书写过程中,并不局限于简单描述地自然现象,他的内在思想和外在文字表现皆是朴素审慎、去人类中心主义的,他擅长观察并取材于万物,跳脱自身的主体性限制以辩证的第三视角对待周边人情与物象,并且站在“天人合一”的立场上将万物的审美形象与审美价值和主体的生命意识完美融合。林清玄这独特的生态审美旨趣一方面加深了他散文丰富的审美内涵,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一位生态散文家的学术尊严与治学态度。从这个层面来看,林清玄的生态散文具有典型意义。
通观林清玄的散文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其生态审美意识主要由三个维度构成:物无贵贱的平等观、体物入微的实践观、物我同一的境界说。
(一)物无贵贱的平等观
林清玄认为天地万物同属于地球这个整体,都是生物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动植物无论对人类有害或无害、色泽明或暗、样貌美或丑,都有各自不可磨灭的生存意义。所以林清玄在创作时致力于建设自然万物在文学体系中的正宗地位,尤其给予动植物以特别关注,使人与动植物之间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同时,林清玄还尝试对文学进行“祛魅化”以还原万物的本原面貌,并以“无所为而为”的态度欣赏事物本身的形象。从美学角度来看,林清玄物无贵贱的生命平等观是完全经得起学术史检验的。客观物本身并不足以构成“美”,既然谈“美”就必定会涉及主体的审美趣味判断,所以对客观物的价值判断乃是主观与客观相互统一的结果。反观文学作品中经常涉及到世间万物利害、美丑、明暗之分,其实是将美的“认识论”与美的“本体论”相混淆的结果。
林清玄的生命平等观体现在作品中,首先表现为各种植物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分。如在《红心番薯》中,林清玄描写番薯花和牵牛花:“番薯花的形状和颜色都像牵牛花,唯一不同的是,牵牛花不论在篱笆上,在阴湿的沟边,都是抬头挺胸,仿佛要探知人世的风景;番薯花则通常是卑微地依着土地,好像在嗅着泥土的芳香。在夕阳将下之际,牵牛花开始萎落,而那时的番薯花却开得正美,淡红夕云一样的色泽,染满了整片土地。”[1]9林清玄身居高楼大厦中多年,却依然能够清晰地记得番薯花与牵牛花的姿态、颜色、花期、时节,想来若不是心居万物并且时时刻刻把记忆拿出来擦拭一番是定不能如此清晰生动地描绘出这幅形象可感的画面的。不可忽视的是,尽管本文的主角是番薯,但是林清玄在比较番薯花与牵牛花时,并没有指出何者为好何者为坏,也没有采用贬低一物来衬托另一物的对比手法,他站在故事之外,用冷静、客观的笔触将万物本来的模样展现出来:番薯花是依偎在土地上蓬勃生长的番薯花,而不是存活在林清玄笔下的番薯花;牵牛花是昂首挺胸,爬上竹篱笆的牵牛花,而不是仅仅绽放在书本中的牵牛花。
同样,人与动植物之间也没有价值贵贱的区分,相反,这几种相异质的生命体之间是平等甚至是可以相通的。再以《红心番薯》为例,作者回忆起有一次自己站在家门口,看见漫山遍野的菅芒花,在凉风中茂密地生长着,竟然和人一般高。在那些摇摆的菅芒花中,有一株菅芒花的晃动幅度非常大,凝神注视,才恍然发现原来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竟走进了这片花丛里,他的头发和秋天的菅芒花是一个颜色,人与花在自然背景中紧密融合,让人难以区分何者为人何者为花。林清玄描写人物的语言非常有特色,他并没有从寻常处落笔,即从身高、体重、眼、鼻、嘴等通用方面照相式地直接呈现给读者一个平面的形象,而是擅于借用大自然的风景为人设增添风姿风采,以意役象将菅芒花变作一个漂亮的形容词用于父亲身上,使得父亲的形象更加饱满、有力量,和平铺直叙的手法相比多了一些亲切感,一丝动态美,一番妙趣。
(二)体物入微的实践观
林清玄生态审美意识的第二个维度与他的实际实践要求是分不开的。林清玄所生活的传统工业化时代,标准化的高速生产线不断带来以“复制性”为主的批量产品,致使工业化环境里的现代人类习惯了快节奏、缺少创新性的生产模式。建立在高新技术和大众传媒基础上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也加剧了人类精神的“无政府状态”。以上物质状态、审美状态的失衡,使得主体本应该拥有的完满人性和本质力量变成了一种脱离现实的假象概念。面对精神世界和文化领域的乱象,林清玄从哲学和历史维度重新反思了当下人类的生命体验。他正确地意识到如果将自然界机械地分割开来看,则中间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是短暂而脆弱的,但是若将每一个个体纳入到机的自然整体之中,并且在宇宙生命的不断更新中反复体验到生命的伟大力量,它则是永恒发展,生生不灭的。所以林清玄鼓励人类应该时常突破当下生存环境的封闭性限制,进行大量的审美实践,使得个体狭隘的自我通过艺术活动在永无止境的时空中获得新的价值与意义。
那么该如何进行审美实践呢?就林清玄本人而言,最好的方法便是“甘愿做自然的学徒”,从自然智慧中发掘人生的价值。在体物入微的实践观指导下,林清玄对一切动物都抱有崇敬、尊重、学习和模仿的态度,如《一杯蜜是炼过几只蜂的》中,作者钦佩蜜蜂经过许多生命的熬炼才炼出一杯香甜可口的蜂蜜茶;《一只毛虫的圆满》中,赞美毛虫总是要经过多年的踽踽独行才能化蝶;《养着水母的秋天》中,由水母的死亡引起时光一去不复回的哀叹。此外,林清玄对植物也存有一颗爱怜的心。如《翡翠白菜》中便宜却营养丰富的大白菜;《采更多雏菊》中从生到死都保持着原有的姿势,完全融入一个纯粹天真的片刻的雏菊花;《有情生》里生命力旺盛的非洲红和常春藤。除上述植物外,还有梅花、菊花、青草、翠竹、仙人掌、兰花、菅芒花、玫瑰、芒花、刺花等等,他以文学家独有的感性情怀,主张淡化肉体的隔阂,回归自然,学习自然的智慧以指导人生。
在林清玄看来,宇宙大化流行全在一“生”字,这个“生”字包含着丰富的意蕴:一方面,天地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小小的花儿、蜜蜂体内也蕴含着无限生机与力量;另一方面,人处在不断成长、发展之中,拥有巨大的价值与尊严。人类就是通过大量实践,在与自然的不断冲突、协调中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
(三)物我同一的境界说
在最后一个维度中,林清玄散文消除了物我的隔阂,主张人与万物一体、物我同一的境界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分别,“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树立尔。”[3]2所谓“无我之境”即作者的主观情趣在作品中让位于自然景物自身的审美形象。林清玄在对自然的观赏中,通过“涤除玄鉴”以获得一种“形而上”的慰藉与自由解放感,从而“与物冥合,玄同彼我”,最终回到万物一体的精神家园。如在《拈花四品》中,林清玄谈到:“台湾乡下,有时会看到野生的菊花,各种颜色各种大小的菊花,那也不是真正野生的,而是随意被插种在庭园的院子里,它们永远不会被剪枝或插瓶,只是自自然然地长大、开启与凋零。但它们会失去傲霜的本色,在寒冷的冬季,它们总可以冲破封冻,自尊地开出自己的颜色。”[4]202林清玄认为单单从时空角度而言,花和人虽相互分离,却可以在审美活动中由物我二分达到物我同一,进而上升到到物我两忘、花与人不分的境界。
三、林清玄生态审美思想的现代启示
工业文明时代,物质材料与劳动主体相分离的机器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传统的“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而是在物质需求的指引下从自然界获得原材料并运用高科技手段对材料进行大规模加工,造出一个异于原始自然生态环境的“新自然”。这种“新自然”的出现使得人与原始自然的关系岌岌可危。林清玄在此背景下衍生的生态意识,是一种反映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新的价值观,它强调从生态价值的角度审视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探索人生美化的途径。
(一)于当下环境中悟出人世真理
席勒认为:“古希腊人既有丰富的形式,同时又有丰富的内容,既善于哲学思考,又长于形象创造,既温柔又刚毅,他们把想象的青春性和理性的成年性结合在一个完美的人性里。”[5]13随着希腊黄金时代的逝去,现实的背景是处在大规模机械化时代的人类亟需找寻一条适合物质——精神持续发展的道路。林清玄生态散文的智慧之处便是在于他的文字充满了警醒、劝诫,他的写作立场并不是站在追忆那个已经远去黄金时代的角度上,而是立足于当下环境中,充分发挥人的本质力量。比如《生命的酸甜苦辣》里,林清玄就曾引用“孟婆汤”的传说来启示读者“人生既然是壮美的便不可能一帆风顺,处处尝到甜头,既然苦难是不可避免的,不如抱着一颗从容的心态过好每一天。”[4]180
作者认为除了坦然地面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之外,更重要的是学会在逆境中保持精神的高洁,怀有不卑不亢、顽强生长的力量。因此在《本来面目》里所提出的“人们习惯了戴上面具行走在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界中,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时的荣耀、利益、快乐,然而只有本来面目辉会让我们感觉到人生的完整、独特、充满生机和意义。”[6]59真正的超脱并不是与世界隔绝,活得不食人间烟火,而是站在这个污浊世界里,在这个无法摆脱的环境中吸取营养,把污泥转化为一朵清新的花。
此外,林清玄还鼓励人们要主动学会欣赏困境、苦难的美。如《沉香默默》里,林清玄反问到 :“如果莲花不是生长在淤泥当中,而是长在芳香洁净的土地上,那么它还会有出淤泥而不染的美誉吗?那么它还能称作荷花吗?它的美丽还会那么让人难忘、心动吗?所以,我们应该肯定世间一切臭的污秽事物的气魄,肯定它存在的价值与意义。”[4]204
最后,林清玄肯定人作为生物链的一环,即便身处不利的环境中,自身也拥有无上的力量。他曾多次在文中突出人类的光辉与尊严,以一种启发性的方式把人类和世界联系起来。他认为倘若为了强调动植物的独特性,而不加节制地贬低、忽视人类的价值,把人类视作万物的敌人,这种“反人类中心主义”同样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整体主义”,而这往往是许多生态学者所忽视的。
(二)于利害之外实现内心的虚静
为了实现人生的净化、美化,林清玄提出人们应该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运用理智与自制力保持内心的虚静。那么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
第一条路径便是独立于尘世现象之外,辩证地审视世俗的“得”与“失”。导致现代人类生存状态的异化的主要原因往往集中于对金钱、权利、利益的欲望和对生死的恐惧,而林清玄却认为人生的种种色相、感受、念想、行为、简介都是因缘所聚合的,因缘生、住、异、灭,最终归于空无。他曾在《水中的金影》中用回忆过去人们欢聚一堂在庭院聊天、散步、赏月的简单幸福的生活来批判当代人们膨胀的欲望:“现代人住在三十平米的房子,觉得要有五十平米才够。有汽车开了,还追求百万的名车。吃得饱穿得暖,还要追逐声色。到最后,还要一个有排场的葬礼,和一块山明水秀的墓地。”[7]109针对毫无节制的物质生活,林清玄在文末呼吁大众:“停下脚步,让扰动的池水得以清净吧!抬头看看,让树上的真金显现面目吧!”
积极面对,返璞归真是实现内心虚静的第二条路径。林清玄在《身在江湖》一文里分享了自己儿时在水缸里沉淀自来水的故事,并得出结论:真正可怕的不是当下的环境,而是面对不利的环境而又无法脱身、选择放纵的自己。所以与其选择去刻意去追求功名利禄,不如调整自己的心态,以出世的态度积极入世。
(三)于城市中促进精神的“乡野化”转变
人与自然万物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二者休戚与共,密切相关。通观原始社会以来人们与自然共处的历史经验,不难发现其中的关窍:顺应自然规律、取之有度,人类就能与自然和谐共存;违逆自然规律、豪取抢夺,人类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大自然的灾难惩罚。
以文化发展为例。传统文化经验系统形成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人类通过大量狩猎、播撒种植、制作石器木器工具等与自然的正面接触的方式获得基本的生存资料,“传统艺术和审美活动,就诞生于这种‘艺’它们围绕着身体——手工劳作与物之物性之间的‘交互转换’的话语逻辑和语境形成。”[8]60而在当代,大量的土地流失以及由水泥钢筋构成的现代建筑隔断了人与土地的直接亲肤的交流,使得现代人不可避免地产生出一种无法挣脱的背离家园般的流离失所感与悲凉感。同时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关系共同刺激下,生产主体与生产资料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工厂日以继夜的机器运转声,日复一日琐碎、贫乏、单调的劳作无形中将人的身体机械化、退化成社会运输链上一个快速生产出的产品,一个简单的碎片化符号。
林清玄在文中多次用诗意又不乏冷静的笔触来描绘这一幅人间炼狱图:台湾民众经常为了昂贵的菜价而沸腾,可即便是好不容易买来的蔬菜也因为大量人为加工的痕迹而失去了本真滋味;因为人为的肆意采掘而引发的矿坑灾变,牺牲了无数人的性命;身居闹市,每日聒噪的儿童吵闹哭泣声、街头疾驰而过的飞车党、邻里间的唾骂声不绝于耳,脏兮兮的小摊、乱七八糟的人体艺术避之不及、可怜的人们只有脱离了纷纷扰扰、脏乱不堪的闹市……在经验异化的处境中,林清玄提倡精神上的“城市化”向“乡野化”的转变,呼唤人们看到城市之外的自然,时常回归乡野,感受原生态自然的魅力,进行新时代的思想和精神唤醒。除了身体上的乡野之旅,林清玄其实更注重引导都市人培养敢于打破常规思维的习惯,谋取必要的生活资料的同时也需要培养自己的审美能力与趣味,细心发现周边寻常风景的美。为了避免陷入审美冷淡,应该时刻保持着一颗好奇心、积极培养审美新鲜感,多读书,多行走,获得独特的生命体验。
作为一个有着深厚生态责任意识的艺术家,林清玄将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人文关怀和忧患意识灌输进入散文中,以文字代替自然“发声”。他的散文具有净化心灵的现实意义,并对我国生态文学的建设具有理念、制度和方法论层面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