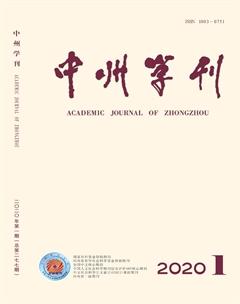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王莲峰
摘 要:为有效遏制商标恶意注册行为,净化营商环境,我国2019年修改的《商标法》总则部分新增条款,明确规定禁止商标恶意注册,并对分则部分相关条款进行修改,旨在加大对商标恶意注册行为的处罚力度。但是,修改后的《商标法》对商标恶意注册行为的规制条款过于抽象,存在法律适用上的困难。为提升我国《商标法》实施质量,建议借鉴欧盟和德国对商标恶意注册进行规制的实践经验,明确商标恶意注册的审查标准和考量因素;对疑似恶意申请注册者,商标审查机关可要求其提供使用意图的证明;对恶意进行商标注册和诉讼者,可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追究其民事责任。
关键词:商标恶意注册;法律适用;欧盟商标法;德国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中图分类号:D92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01-0052-08
近年來频繁发生的商标恶意注册现象,不仅严重扰乱我国商标注册秩序,而且侵害其他市场主体的正当权益,对我国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造成恶劣影响。因此,有效遏制商标恶意注册成为我国《商标法》第四次修改的主要任务。2019年4月23日,《商标法》第四次修改通过。其中,第4条第1款明确规定,商标恶意申请不予获准注册;第33条、第44条第1款分别新增条款,将恶意注册作为异议和无效宣告的理由;新增第68条第4款并修改该条第1款,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及恶意提起商标诉讼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商标法》从总则到分则相关条款的修改,无疑为有效打击商标恶意注册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然而,该法既未在相关条款中明确商标恶意注册的内涵、认定标准和考量因素,也缺乏对恶意注册者承担法律责任的具体适用条款。换言之,修改后的《商标法》虽然对商标恶意注册进行规制,但存在法律适用上的难点,相关法律规范缺乏可操作性。鉴于修改后的《商标法》已于2019年11月1日生效,商标确权机关和法院急需统一法律适用的标准,本文借鉴欧盟和德国对商标恶意注册进行规制的法律适用方面的经验,提出解决我国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适用问题的建议。
一、欧盟和德国对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规制
对恶意的商标注册行为进行规制,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完善商标法制进程中极为关注并深入探讨的问题。欧盟及其成员国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磋商,建立了一套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国内层面相统一的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体系。这套严格的法律制度采取注册前不予获准、注册后无效宣告、追究侵权行为的民事赔偿责任等机制和方式,对商标恶意注册进行有力打击。下文以欧盟为例,评介区域法层面对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规制;以德国为例,评介国内法层面对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规制。
1.欧盟对商标恶意注册进行规制的法律体系
为实现欧盟商标制度一体化,经过多年磋商和会谈,欧盟逐渐构建了两套平行的商标法律制度:在欧盟内部统一且独立于各成员国国内法的《欧盟商标条例》①,以及用于调整各成员国国内商标法律制度的《欧盟商标指令》②。欧盟希望通过这两套法律制度,逐步达到欧盟法规与各成员国国内法律相统一的目标——消除欧盟范围内因法律差异而产生的影响,减少内部市场交易成本,保障商品自由流通,提高法律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欧盟商标恶意注册法律制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其成员国经历十几年的讨论和磋商,最终建立起来的。③在《欧共体商标条例》的拟定阶段,荷兰于1978年提出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立法构想,即恶意的商标注册不予获准。④德国于1984年提出关于真诚使用意图(bona fide intent-to-use)的提案,即商标注册人应当具有在特定商品或服务上使用该注册商标的意图。⑤随后,德国放弃这一主张,转而支持荷兰提出的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建议。德国的主张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是基于对现实情况的考虑。德国当时存在注册商标以便待价而沽的不当行为(trade mark trafficking),这种行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⑥如果将恶意注册纳入阻碍商标注册的绝对理由,就好比新增一个安全阀,在授予拟制的商标权利之前,将恶意申请直接排除在外。最终,1988年《欧共体商标指令》以及1993年《欧共体商标条例》都采纳对商标恶意注册进行立法规制的建议,欧盟范围内初步建立了一套统一的商标保护标准。
2.德国对商标恶意注册进行规制的立法及其特色
1995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商标法》是在当时商标法欧洲化的浪潮下,依据1988年《欧共体商标指令》转化而来的。1995年《德国商标法》对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转化采取较为保守的态度,只把“商标恶意申请”作为商标无效的理由之一:根据该法第50条第1款第4项,利害关系人有权对恶意注册的商标提起无效宣告。⑦后来,德国立法加大对《欧共体商标指令》的转化步伐,2004年《德国商标法》第8条第2款“绝对理由”的具体情形中新增第10项“恶意的商标申请”⑧,即将恶意的商标申请纳入阻碍商标注册的绝对理由。此举有利于将不正当的商标申请扼杀在萌芽阶段,减少由此引发的商标无效宣告和诉讼,达到节约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保障法律稳定的目的。⑨
值得关注的是,德国对商标恶意注册的立法规制不仅体现在商标法中,还体现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于2015年修订,对原第3条的一般条款进行拆分,实现了该法内部竞争者保护与消费者保护之间的平衡。⑩对竞争者利益的保护主要规定在该法第4条,其中第4项“阻碍竞争”是该条的兜底条款。从《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4条第4项关于禁止不正当地阻碍竞争者的规定分析,具体的阻碍竞争行为包括散布谎言以损害竞争对手的名誉等。B11申请人恶意注册商标,意在侵害与其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标志所有人的正当利益,该行为在无法受到《德国商标法》以及《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4条第4项之外其他具体条款规制的情况下,可能归于“阻碍竞争”的范畴。B12在现实生活中,面对案情较为复杂的商标恶意注册案件,德国专利商标局的行政纠错制度暴露出局限性,对此,利害关系人可依照《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寻求司法救济,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B13
二、欧盟和德国对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执法实践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欧盟和德国在立法层面对商标恶意注册的规制设计了具体的规则,如将商标恶意注册作为禁止注册的绝对理由,相对人可以请求司法救济等,但对“恶意”的具体判定标准并无明确规定。值得肯定的是,欧盟法院以及德国法院在具体判例中逐步明确了“恶意”的法律内涵及认定标准,并对恶意注册对他人造成损害时利害关系人依法寻求救济的途径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1.德国法院对商标恶意注册的内涵及类型的界定
商标恶意注册不同于一般的商標注册,对其进行认定需首先对“恶意”进行界定,而对于“恶意”一词,《欧盟商标条例》《欧盟商标指令》《德国商标法》均未给出明确的定义。在“世界杯2006”案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解释了“恶意”的法律含义。该案的基本案情是:德国专利商标局于2002年至2003年初核准了国际足球联合会(法文简称FIFA)提出的在多个类别的产品和服务上对“FUSSBALL WM 2006”和“WM 2006”的商标注册申请。B14随后,德国专利商标局收到大量的无效宣告请求书,认为这两个标志因“恶意申请”而不得作为商标获得注册。依据《德国商标法》的规定,恶意申请属于禁止注册的绝对理由。德国专利商标局随即宣告这两个商标无效。对于这两个标志是否具备商标注册的构成要件,是否属于恶意注册,各方争议不断。最终,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定这两个商标无效,主要理由是:社会公众普遍认为这两个标志是对足球事件的客观描述,标志本身缺乏显著性。但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否认对“恶意注册”标准的适用,原因有二:其一,法院无法认定FIFA在商标注册时缺乏真诚使用该标志的意图;其二,同样无法证明的是,FIFA对上述商标申请注册仅出于有悖于公序良俗的目的。在该案判决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恶意”的法律内涵予以明确:“商标注册人取得拟制的商标权,是以日后达到对第三方不正当或是违反公序良俗的阻碍为目的的,认定为恶意。”B15换言之,该案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所谓恶意,是指申请注册商标的目的是阻碍第三方竞争,而非自己使用,具有非正当性或者违背公序良俗。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世界杯2006”案,对“恶意”这一法律术语进行了解释。分析其判决书的表述,并未创设新的法律含义,而是以既有成熟的法律标准为依托,以《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条第1款(关于不正当性的一般条款,规定不正当的商业行为是不合法的),以及《德国民法典》第826条关于违反公序良俗的规定(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故意加害于他人者,有义务向该受害人赔偿损害)为参考。B16这一解释不仅适用于1995年《德国商标法》第50条第1款第4项规定的商标恶意注册的无效宣告B17,还适用于2004年《德国商标法》新增条款(第8条第2款第10项)规定的阻碍商标恶意注册的绝对理由。B18
2.德国专利商标局采用“明显恶意”的审查标准
上文谈到,《德国商标法》引入“恶意商标申请”作为驳回商标注册申请的绝对理由,但立法者不希望将不合理的调查责任强加给商标主管部门以加重其审查压力。因此,德国专利商标局对《德国商标法》第8条第2款第14项规定的绝对理由进行审查时,采取的是“明显恶意”标准。对此,《德国商标法》第37条第3款明确规定:“仅当欺骗的可能性或恶意明显时,才根据第8条第2款第4项或第14项驳回申请。”B19换言之,德国专利商标局一般推定商标注册人具有使用该注册商标的意图,但存在“明显恶意”的情况能推翻此推定。B20
德国专利商标局采取“明显恶意”的审查标准,这种折中的办法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在申请商标注册的过程中,有些申请虽然满足“恶意”的内涵,但这种“恶意”的显露很可能因缺乏明显性而使该商标申请仍获核准。对此,《德国商标法》作了立法体系化设计,并配合德国专利商标局采用“明显恶意”标准对商标申请进行审查。在商标获准注册前,在先权利人可以根据《德国商标法》第42条,在商标注册公布之日起3个月内对注册商标提起异议。B21在商标获准注册后,依据《德国商标法》第50条第3款,德国专利商标局在商标核准注册之日起2年内,可主动宣告恶意注册的商标无效。依据《德国商标法》第54条第1款,任何人有权不受时间限制地向德国专利商标局提起无效宣告的请求,但申请人应提供具体材料以证明商标所有人具有第8条第2款第14项规定的“恶意”。德国商标主管部门以及自然人都可以对此类恶意注册的商标启动纠错程序,而且自然人的无效宣告请求不受时间限制。这些立法规定和审查标准,足以说明德国立法对商标恶意注册的容忍度之低。但基于商标权的私权属性,德国立法并没有设立对商标恶意注册的惩罚机制。
3.欧盟法院提出的认定商标恶意注册需要参考的因素
2009年,欧盟法院在“Lindt & Sprüngli诉Franz Hauswirth”案中对“明显恶意”的认定提出了具体考量因素。在该案中,原告Lindt & Sprüngli股份公司是一家注册地在瑞士的巧克力和糖果公司;B22自20世纪50年代起,原告就生产一款与该案诉争商标相似的小金兔形巧克力;1994年起,原告在奥地利销售此类巧克力,并于2001年将此类巧克力包装为一只坐着的金色巧克力小兔,脖子系一条红色丝带挂铃铛,且兔身标明棕色“Lindt金兔”字母,该立体标志被成功注册为欧盟范围内的共同体三维商标。被告Franz Hauswirth有限责任公司为注册地在奥地利的巧克力和糖果商,其于1962年起销售小金兔形巧克力。原告在注册该诉争商标前,就以奥地利竞争法或奥地利工业产权法对与其小金兔形巧克力外形相同的巧克力生产商提起诉讼;原告成功注册该商标后,对与其小金兔形巧克力的外形有混淆可能的巧克力生产商提起诉讼。该案中,原告宣称被告生产和销售的小金兔形巧克力在外形上与其三维商标易引起混淆,认为被告侵害其商标权并要求被告停止在欧盟范围内的侵权行为;被告提起反诉,认为原告恶意注册此三维商标,并依据《欧洲共同体商标条例》第51条第1款b项(现为《欧盟商标条例》第59条第1款b项)请求宣告原告的三维商标无效。对此,奥地利最高法院请求欧盟法院先行裁决。
欧盟法院在该案裁决中强调,各国法院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将商标申请人提交商标申请时的所有相关因素都纳入考量范围,特别要考量以下3点。B23第一,商标申请人知悉或者应当知悉他人在相同或近似的商品或服务上在先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且存在混淆可能的商标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欧盟法院明确表示仅满足这一条件并不能直接推导出商标申请人的注册恶意。B24第二,依具体的客观情况推断商标申请人具有阻碍意图。商标申请人的阻碍意图是构成商标恶意注册的关键,但阻碍意图作为主观要素,只能参照具体的客观情况予以评定。B25欧盟法院还特别强调,缺乏商标使用意图的商标注册行为阻碍第三方进入市场,应直接认定为存在阻碍意图。B26第三,考虑在先使用人和商标申请人的正当利益应受保护的程度,权衡双方利益。如果在先权利人具有正当利益,如部分社会公众已将该注册商标理解为在先使用人的来源指示,就应认定商标注册人存在注册在先权利人商标的恶意。B27
欧盟法院在该案先行裁决中的措辞是“考虑所有相关的因素,特别是以下几点”,这表明上述3方面评价具有指导性意义,但并不绝对。各国法院在判决案件时应注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综合考量案件相关因素。为保证欧盟法律的统一适用,欧盟法院的这项先行裁决对各成员国均有约束力。换言之,德国专利商标局和各级法院对商标恶意注册进行认定时必须参照这项先行裁决确立的标准。
三、《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商标恶意注册的利害关系人提供救济
《德国商标法》对“恶意商标申请”的规定并不排除其他法律的适用。依据《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4条第4项,如果申请注册商标以排除和阻碍他人的商标使用为主要目的,适格当事人就可请求司法救济,以“阻碍竞争”为由提出停止侵害的请求,以撤销该注册商标。比如,在“AKADEMIKS”商标纠纷案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被告抢注他人商标的行为,可推定为具有阻碍意图,可能落入“阻碍竞争”的范畴。换言之,注册人抢注商标的不正当商业行为,意在侵害与其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标志所有人的正当利益,在无法受到《德国商标法》以及《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其他具体条款规制的情况下,利害关系人可以适用《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4条第4项“阻碍竞争”条款进行维权,请求撤销已注册的商标。
“AKADEMIKS”商标纠纷案的具体案情如下。原告是一家成立于1999年的美国公司,专卖“Hip Hop风格”的服装,该公司1999年4月4日在服装类别上申请注册了包括“AKADEMIKS”文字和图形的商标,2000年7月4日获得商标注册;经过原告广泛宣传,2000年春季,该品牌服装已在美国和欧洲服装行业享有较高声誉;2002年6月25日,原告以“AKADEMIKS”文字和图形向欧共体市场协调局申请注册欧共体商标。被告是德国一个纺织品零售批发商,成立于2000年9月8日,也售卖“Hip Hop风格”的服装;被告于2000年10月18日向德国专利商标局申请在服装和鞋帽商品上的“AKADEMIKS”文字商标,2001年3月1日获得商标注册。2003年2月,被告通过其被许可人警告原告在欧洲的特许经销商构成商标侵权,原告遂根据《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4条第4项向法院起诉,认为被告属于恶意抢注并以阻碍竞争为目的,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停止侵害,撤销被告抢注的“AKADEMIKS”商标。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最终支持原告的部分主张,主要理由有4点。第一,根据商标权的地域性原则,只保护本国的商标注册权,但在特殊情形下,申请人已知晓他人在先使用的商标可能导致其申请行为具有不正当性,此时商标法的地域性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不相冲突。结合本案,原告没有可在德国受保护的商标法上的权益,因其既未证明被告抢注商标时其已在德国使用该商标,也未充分证明被告抢注商标时其在德国有足够的知名度。结合相关案情,被告作为申请人应该知道国外已有人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注册了相同或近似的商标,而且已注册商标的商品可能进入德国境内,但被告依然申请注册与该商标相同的商标,此时可推断其申请行为具有不正当竞争性。第二,被告應当知晓原告的商标但依然进行注册,主观上存在恶意。因为原告的商标是臆造词汇,而被告注册的商标与之完全相同;另外,原被告双方均为从事时尚服装的行业,被告应了解原告商标的知名度,被告的行为具有“傍名牌”的嫌疑。第三,根据商业惯例,企业发展多是先立足于国内,随后扩展至国外市场。结合本案,原告于2000年春季在美国市场获得成功,其影响力已超出美国市场范围。被告的商品尽管在德国市场有较好的销售,但主要源于原告商品的商标和品牌在美国的影响力,可推定被告知晓原告将会进入德国市场进行销售。第四,被告具有阻碍竞争的意图。尽管被告将注册商标用于自己的商品上,但其注册的商标和原告臆造的商标一样且复制了原告商品的设计和款式。同时,根据二审中的陈述意见,被告在与原告的和解谈判中要求独家销售权。根据以上事实,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推定被告使用商标的目的不是进行自由竞争,而是将原告排除出德国市场,被告申请“AKADEMIKS”为注册商标的行为具有不正当性,可以适用“阻碍竞争”条款进行规制。B28
在德国司法实践中,恶意的商标申请主要有两种情形。第一,属于欧盟法院强调的意图阻碍第三方进入市场而注册商标的行为,特别是“投机商标”注册。B29“投机商标”注册指商标申请人在无使用意图的情况下注册商标,只为日后向他人收取注册商标许可使用费。B30第二,属于“阻碍商标”的注册行为,即商标申请人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已知他人对某一标志存在受保护的利益,仍在与他人相同或相似的产品或服务上注册与该标志相同或相似的标志,以达到阻碍他人行使在先权利或继续使用这一标志的目的,或者以注册商标的排他性作为不正当竞争手段。B31上述“AKADEMIKS”案中就存在此两种情形。此两种情形也是《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4条第4款“阻碍竞争”规制的典型行为,即通过取得标志权以阻碍竞争对手。B32德国法官审理此类案件时,一般进行两步检验:首先,考虑商标注册人是否存在阻碍或排挤竞争对手的主观意图;其次,考察竞争对手开展商业活动是否实际或可能受阻。法官还会考虑双方当事人的商标相似度、商品包装装潢和样式的近似度、商标知名度、行业惯例等因素,并衡量双方利益后作出判决。
四、我国对商标恶意注册进行规制的法律适用建议
为提升我国《商标法》的实施质量,笔者借鉴欧盟和德国的实践经验,对我国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适用提出以下建议。
1.明确商标恶意注册的认定标准和考虑因素
我国《商标法》第四次修改后,第4条1款新增“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恶意申请”应予驳回的规定,其中“恶意”的界定是一个法律适用难点。欧盟和德国对商标恶意注册的认定标准和考虑因素,值得我国借鉴。鉴于当前我国商标恶意申请注册愈演愈烈的严峻局面,笔者建议,相对于欧盟和德国的“明显恶意”标准,我国可采取更严格的标准,即“可能恶意”标准——对可能存在恶意的商标注册人,商标局可要求其提供善意使用或使用意图的证明文件。此处的“可能恶意”,应理解为商标注册人可能具有阻碍他人正当使用商标的目的。具体而言,注册人明知或应知第三人已使用该标志却仍进行抢先注册,或者注册人投机性地批量进行商标注册,均可归入“可能恶意”的范畴。
对“可能恶意”的认定,可以借鉴欧盟法院对“明显恶意”的评定,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第一,对可能构成注册他人在先使用标志的行为,可以考虑两种情形。其一,商标申请人知悉或应当知悉他人在相同或近似的商品或服务上在先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且存在混淆可能的标志;其二,依具体的客观情况推断商标申请人可能存在阻碍意图,即以达到阻碍他人行使在先权利或继续使用這一标志为目的,或将注册商标的排他性作为不正当竞争手段,如恶意转让或诉讼等。第二,对可能构成囤积注册商标的行为,可以根据客观情况,对商标注册人的主观因素进行评定。主要审查注册人是否具有商标使用意图,是否对一定数量的商标进行投机性注册,是否存在以囤积注册商标为牟利工具的目的等。上述关于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的评定因素,与我国商标局发布的《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对《商标法》第44条第1款中“其他不正当手段”的审理要求B33大体相似。二者的区别在于,采取“可能恶意”标准时,申请人应当提供善意使用或使用意图的证明文件。
2.商标局对疑似恶意注册的申请人可要求其提供使用意图的证明
实践证明,欧盟和德国将商标恶意注册作为实质审查的绝对理由,能有效遏制此类不当行为。我国现行《商标法》第4条第1款也规定对恶意的商标注册申请应当驳回,商标局对商标恶意注册可以实施主动审查。为强化审查机构的职责,笔者建议:对疑似恶意注册的申请人,商标局可要求其提供善意使用或使用意图的证明文件;申请人无法提供相关文件的,不予注册。申请人提交相关证明文件时,其“可能恶意”即可排除。一方面,商标局有权对可能恶意的商标注册申请实施主动审查,其职权范围得以扩大。另一方面,申请人可以通过提交相关文件证明其注册并非恶意,以保障自身权益。随着我国商标注册申请数量不断增长,商标局的审查任务日趋繁重。如果要求商标局对所有申请主体进行善意使用或使用意图的审查,只会增大其审查压力,降低行政效率。因此,商标局进行善意使用或使用意图审查的对象应限于可能存在恶意的申请人,而非所有申请主体,从而不会撼动我国“申请在先注册取得”的商标确权模式。
如果商标局认为商标申请人存在“可能恶意”,该申请人又无法提交相关证明文件,此时申请人不被获准授予商标权。商标主管部门主动承担这一审查任务,能在一定程度上制止恶意注册的不法行为。当恶意的商标申请未被实质审查阻挡在外时,根据我国现行《商标法》第33条,任何人得以在规定时间内依据该法第4条第1款提出异议,或者根据该法第44条第1款,由商标局宣告商标无效或由其他单位或个人提起无效宣告请求。如此,打击商标恶意注册的立法就能毫无缝隙地穿插在各个环节,让恶意注册者无从遁形。
3.适用《侵权责任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追究恶意注册者的民事责任
商标恶意注册者滥用商标权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严重扰乱商标注册秩序,不仅浪费行政资源,还损害公共利益。对此,我国现行《商标法》第68条增设1款,即“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的,根据情节给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对恶意提起商标诉讼的,由人民法院依法给予处罚”。该规定与《商标法》第47条第2款“因商标注册人的恶意给他人造成的损失,应当给予赔偿”相呼应,进一步明确了恶意注册人在一定情形下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但是,如何适用上述条款,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司法实践中,在我国《商标法》第四次修改之前,人民法院一般适用《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在先权利人提供民事救济。比如,2017年“科顺诉共利”案中,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只要是滥用商标注册制度,恶意注册商标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均属于侵权责任法规制的范畴。”B34恶意注册人的不当行为致使他人遭受损失,满足一般侵权的构成要件,因而具有侵权法上的可责性。该案中一审、二审法院都适用《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判决恶意注册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B35
在近年来的其他案件中,法官们也开始适用《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的条款,判定“知产流氓”承担侵权责任B36,并探索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构成要件及赔偿标准B37。此外,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是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重要法律依据之一。所不同的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并无类似于《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阻碍竞争”条款的竞争者保护条款。对于商标恶意注册,我国法院一般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即该法第2条B38进行规制。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水宝宝”案是此种法律适用的标志性案件之一。该案中,恶意注册人将拜耳集团旗下的一款防晒霜的两个图案注册为商标,随后对拜耳集团发起一系列大规模、持续性投诉,导致拜耳集团遭受严重的声誉贬低及经济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明知原告对涉案图案享有在先权利并在先使用于涉案产品上,仍利用原告未及时注册商标的漏洞,将该图案的主要可识别部分申请注册为商标,并以该商标对涉案产品发起投诉以谋取利益,欲通过直接售卖商标而获得暴利。被告的获利方式并非基于诚实劳动,而是攫取他人在先取得的成果及积累的商誉,属于典型的不劳而获,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应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认为该案被告注册他人商标并进行恶意投诉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最终判决被告赔偿拜耳公司70万元的经济损失。B39该案的裁判体现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不仅将“职业商标抢注人”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范围,而且从司法上表明了在无其他可具体适用法条的情况下,单独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打击职业商标抢注人的可能性。“该案件的审理也为日后有类似境遇的其他企业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打击恶意抢注、恶意投诉行为时提供了突破性的解决方案。”B40恶意抢注人不仅会无利可图,还会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和恶意诉讼而承担更为严重的赔偿责任等法律后果和违法成本,这无疑有利于打消潜在行为人通过商标恶意注册获得利益的动机。
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商标法》对商标恶意注册行为进行了规制。为统一法律适用,可以借鉴欧盟和德国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实践经验,明确商标恶意注册的认定标准和考虑因素,授权主管部门在商标核准阶段对疑似恶意的商标注册行为实施严格审查,要求申请人提供使用意图的证明;对恶意提起侵权诉讼的,相关权利人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抢注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增加其恶意注册的成本,阻断其不劳而获的路径。
感谢郑敏渝博士对本文德语案例资料的翻译及整理工作。
注释
①1993年《欧共体商标条例》经过数次修订,最新版本改名为《欧盟商标条例》,于2017年6月16日对外公布。
②1988年《欧共体商标指令》经过数次拟定,最新版本改名为《欧盟商标指令》,于2015年12月23日对外公布。此后,欧盟各成员国有3年时间将该指令条款转化为国内法。
③“商标恶意抢注”分别规定在3个条款中,即《欧共体商标条例》第51条第1款b项(现为《欧盟商标条例》第59条第1款b项),《欧共体商标指令》第3条第2款d项(现为《欧盟商标指令》第4条第2款),《欧共体商标指令》第4条第4款g项(现为《欧盟商标指令》第5条第4款c项)。其中,第3个条款涉及的是恶意抢注其他成员国内部在先使用的标志的情形,此种情形本文不作讨论。
④Sitzungsbericht über die siebte Sitzung der Arbeitsgruppe 'Gemeinschaftsmarke', 13-16.2 1978 EC III/D/34/78 p.20.
⑤Schreiben der deutschen Delegation doc. 12 October 1984 9755/84 pp.7-8.
⑥Alexander Tsoutsanis. Trade Mark Registrations in Bad Fa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63.
⑦该条款为现行《德国商标法》第54条第1款。
⑧2018年12月,《德国商标法》修改后,“商标恶意申请”为第8条第2款第14项。
⑨B17Paul, Strbele/Franz, Hacker/Frederik, Thiering, Markengesetz, 12. Auflage,Heymanns Kommentare zum gewerblichen Rechtsschutz, Kln 2018, MarkenG § 8 Rn. 891; Reinhard, Ingerl/Christian, Rohnke, Markengesetz. Kommentar, 3. Auflage,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10, § 8 Rn. 295.
⑩B18參见柴耀田:《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体系化功能——德国201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改革对中国修法的启示》,《电子知识产权》2016年第10期。
B11Ansgar, Ohly/Olaf, Sosnitza,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Kommentar, 7. Auflage,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16, § 4.4 Rn. 78.
B12《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4条第4项规定:有目的地阻碍竞争者的,构成不正当行为。
B13Ansgar, Ohly/Olaf, Sosnitza,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Kommentar, 7. Auflage,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16, § 4.4 Rn. 78; Paul Lange, Marken-und Kennzeichenrecht, 2. Auflage,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12, § 5 Rn. 2424.
B14B15BGH GRUR 2006, 857–FUSSBALL WM 2006.
B16参见《德国民法典》,陈卫佐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318页。
B19参见《德国商标法(德国商标与其他标志保护法)》,范长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28页。
B20BPatG GRUR 2012, 840–soulhelp.
B21《德国商标法》的保护客体不仅包括注册商标,还包括商业名称,即商号和作品标题。此处的在先权利人指所有受《德国商标法》保护的标志所有人。
B22B23B24B25B26B27EuGH GRUR 2009, 763–Chocoladefabriken Lindt & Sprüngli.
B28Vgl. GRUR 2008, 621 Rn. 26–AKADEMIKS.
B29BGH GRUR 2001, 242, 244–Classe E; BGH GRUR 2012, 429–Simca, Rn. 10.
B30Annette, Kur/Verena, von Bomhard/Friedrich, Albrecht, BeckOK Markenrecht, 13. Auflage, München 2018, MarkenG § 8 Rn. 958.
B31BGH GRUR 2012, 429–Simca, Rn. 10.
B32Helmut Khler, Joachim Bornkamm, JrnFeddersen,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37. Auflage,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19, § 4.84ff; Ansgar, Ohly/Olaf, Sosnitza,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Kommentar, 7. Auflage,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2016, § 4.4 Rn. 79ff.
B33《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第6条规定了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商标注册的审理标准,指出下列情形属于本条所指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1)系争商标申请人申请注册多件商标,且与他人具有较强显著性的商标构成相同或者近似的;(2)系争商标申请人申请注册多件商标,且与他人字号、企业名称、社会组织及其他机构名称、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等构成相同或者近似的;(3)系争商标申请人申请注册大量商标,且明显缺乏真实使用意图的;(4)其他可以认定为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
B34参见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民初267号民事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a38cecd68af840168ce1a8ef00a53d91,2018年5月29日。
B35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终37号民事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223ab1c7bfe64166a9faa8e300a8b911,2018年5月17日。
B36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知)初字第22620号民事裁定书,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8a35890ae9694930b16ea9c60031a68d,2018年12月31日。
B37比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7年审结的一起案件的裁判要旨中提出:“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无事实或者法律依据,仍以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故意针对他人提起知识产权诉讼,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其构成要件有:1.行为人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无事实或者法律依据。常常表现为行为人没有知识产权权利或者行为人虽然享有形式上‘合法的知识产权,但因该知识产权系恶意取得等多种原因而不具有实质上的正当性。2.行为人提起诉讼在主观上具有恶意。在行为人恶意取得知识产权的情况下,其取得知识产权时的恶意,可以作为认定其提起诉讼时具有恶意的依据。3.行为人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给他人造成了损失,且损失与行为人惡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具有因果关系。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本质上属于侵权行为的一种,恶意诉讼行为人承担的赔偿数额应当以受害人的损失为限。在受害人的损失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可以综合考虑受害人现实的经济损失以及预期利润的损失等相关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该案中,二审法院最终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的规定,判决被告在《法制日报》登声明以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100万元。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民终1874号民事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cf6bfcd6e52d42ae8846a9c0017b0c4e,2018年12月25日。
B38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1款规定: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
B39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18627号民事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ad440951f070438ca05fa8f500ad76cf,2018年6月6日。
B40参见广东海法律师事务所:《还敢恶意抢注商标?职业商标抢注人首次被判不正当竞争!》,搜狐网,http://www.sohu.com/a/244524591_99901874,2018年8月1日。
责任编辑:邓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