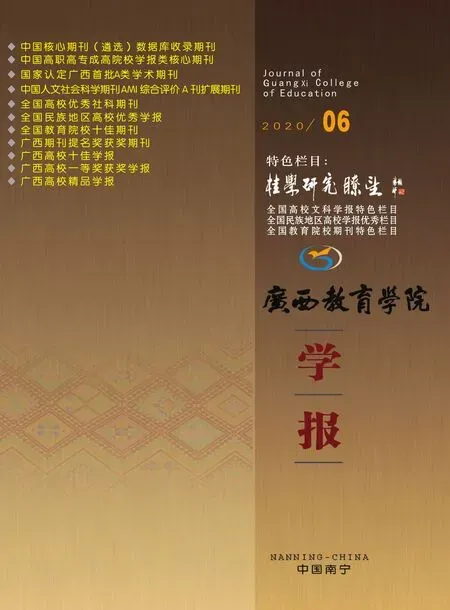混乱的隐喻:《无可慰藉》中的记忆书写与身份认同
张颖坤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文化基础部,上海 201808)
石黑一雄的小说《无可慰藉》于1995 年出版,它与前三部作品风格迥异,是一部颇具实验性质的小说。在《无可慰藉》的世界中,主人公瑞德搭乘酒店电梯从一楼到三楼需要二十分钟,入住的酒店房间是儿时的卧室,陌生人结果是他的妻子和儿子,市区的酒店大厅位于僻静的乡间房舍的门后——现实生活中的时空逻辑被打乱,取而代之的是无法用理性逻辑解释的混乱和荒诞。在小说中,从到达酒店的那一刻起,瑞德就一直饱受市民琐碎请求的搅扰,不断偏离原定目标,在他终于能够登台演奏时,却发现音乐厅里的坐席已被撤掉,观众早已散去。“石黑一雄的笔触从一开始的舒缓柔和到后来的荒诞迷离再到最后的几近恐怖,为读者揭开了这座貌似平和安宁实则危机重重的城市的神秘面纱,带我们窥探了困在这个城市中的形形色色人物的人生百态。”[1]这个荒诞离奇的故事使读者仿佛置身于梦境之中。在谈及创作初衷时,石黑一雄坦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想写一些能够反映我内心开始感受到的不确定性和混乱的东西。我想写一个身处混乱之中、被同时朝着不同方向拉扯而不知原因的人”[2],“我把旅程中的混乱作为一种隐喻”[3],“我对于这种梦幻写作和‘梦幻语法’很感兴趣。……这是一种大多数人熟悉的语法,因为人们会在梦中遇到它。正如前三部小说是在一个国家完整的冒险经历,我觉得《无可慰藉》是在另一个国家的冒险”[4],“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关于一个人的传记,……我们往往挪用其他人。我们也许并没有看到他们的本质,而把他们变成了有用的工具”。[2]在小说中,瑞德“挪用”他在这个城市里遇到的人来代表在他内心深处的某人和他的过去,“一定程度上,他在这个城市里遇到的这些人的确有他们存在的理由,但是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利用他们给你讲述关于他自己的故事。因此,你其实在了解他、他的父母、他的童年,还有他对于自己未来可能性的恐惧。”[3]瑞德在梦幻世界中漫游,在那里他遇到了早期的和未来的自己。他把自我的生活经历投射到其他人物身上,通过他人的故事来迂回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鲍里斯和斯蒂芬是瑞德童年和青年时期的映像,而布罗茨基映射出了瑞德面对未来而感到的迷茫和恐惧。瑞德在这个城市里度过的四天三夜不时被童年和青年时期的记忆碎片所裹挟,记忆的断裂、创伤的写入导致自我建构的可能性破碎了,“一切都是对他的过往的表达和对未来的恐惧”[5]。
一、个体创伤记忆与身份认同
在小说开篇,瑞德初到酒店之时便忘记了日程表上的安排。“很显然,这座城市对我的期待不仅仅是一场独奏音乐会。但是当我试图回忆有关这次行程安排的细节时,却什么也没想起来。”[6]15向斯达特曼小姐坦白自己忘记了行程在瑞德看来是莫大的尴尬,因此他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自我欺骗在《无可慰藉》中被夸张到了荒谬的程度。他审视周围,锚定那些情感方面需要的东西而屏蔽其它。他会忘记几分钟之前发生的事情并且对它重新书写。瑞德忘记了与记者的约定,忘记了与伯爵夫人和市长的会面,忘记了与市民互助小组的讨论,他甚至忘记了自家公寓的地址和那个是他妻子的女人。对于有些评论家把它称为失忆症,石黑一雄评论道,“人们说他得了失忆症,对此我是一直不开心的。……它更像是在漆黑一片的暗室里举着火炬前行。……你能看到一片光亮,但是你看不到前面是什么,除非你回过头来看你刚刚经历了什么。我头脑里有这样一个形象,瑞德可以记住在他之前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此之前发生的事情已经没入黑暗之中。他能够看到前方不远的地方,但不是太远。关于他的太太,并不是他真的忘记了他的太太……我们就像这个人经历这四五天那样来经历人生。当他前行的时候他能够清清楚楚地感受到这片光亮,但是认为我们可以仔细地规划人生是一种错觉。更多的情况是,我们一路跌跌撞撞,时不时地停下来判断一下形势。……你被其他人的日程安排和意外遭遇呼来唤去,一直都在努力对自己说,‘是的,我是有意识这样决定的。’我们往往并没有我们所想的那样可以把握人生。瑞德看起来有点奇怪,因为他答应孩子的事情转身就忘记了。纵观人的一生,我们这辈子都是在这样做。……只有当你从某种角度来看生活并且把它压缩到几天之内,它才会看起来像是奇怪的行为。”[5]
瑞德通过躲进回忆的层面,避开了现实的直接压力,把他自己的生命虚构化。他与自己的存在不再共时,而是分裂成一个经历者和一个观察者;作为观察者他赶到了事件的前面,并像一个陌生人一样回顾已经结束的事件。酒店里铺的垫子使瑞德回想起童年的情景。被写入心灵石板最深处的东西是不可销毁的,因为它是从不外露的。“回忆向我袭来,我想起某天下午我沉浸在塑料士兵的世界里,这时从楼下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吵得如此凶猛,以至于像我这样六七岁的孩子都意识到了这不是普通的争吵。”[6]16父母争吵的场景如同恐惧的闪电留下了一个像照片一样精准的图像。家庭暴力的心灵强力就像一颗流星穿透了瑞德记忆的外膜,并且摧毁了它的结构。心灵的石板上镌刻的是父母的争吵与冷漠,这个创伤性的写入使瑞德在童年时遭受了心灵上的伤害,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世界,创伤带给他的是一个破碎的世界和分裂的自我。童年时期的经历尽管存在于他的体内,但它们深深地隐藏在某处,潜伏回忆存在于一种悬置状态,它们或是从这种状态中下降到被完全遗忘的黑暗之中,或者被取出放置到重新回忆的光线里。
瑞德在画廊外面看到了父亲的那辆旧车的残骸,他撇下索菲和鲍里斯,独自钻入车内,回忆起了那天他跟父母去一位老太太那里买二手自行车的情景。“我意识到在这位老太太看来,我们一家人代表了幸福家庭的理想。紧随而来的是一阵剧烈的紧张感,……我相信任何一个迹象,哪怕是某种气味,都会让这位老太太意识到她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我生怕会出现她突然被吓得呆若木鸡的那一刻。”[6]264瑞德被一种非意愿回忆所袭击。回忆突如其来地闯入意识之中,并且冲破了意志和愿望的所有模式。被深深遗忘的图像不可抗拒地从心灵深处升起,在一个瞬间被投射到意识的表面。这个回忆尘封了数十年,但被一个突如其来的旧车残骸的激发所释放。思想的复用羊皮纸上写入的回忆被无法消除地刻入了,尽管它们总是被遗忘所掩盖。创伤记忆的身体文字会毁坏身份认同的可能性。一个被损害的自我失去了任何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对于环境的控制,它的语言也失去了所有积极掌控的内涵。创伤巩固经验,使意识无法通达到那里,只能在这个意识的阴影中作为一个潜伏的存在而固着下来。瑞德童年时期所经历的家庭失和在他的心灵中永远是一块异物,就像身体里一颗无法开刀取出来的铅弹。尽管它是不可丢弃的一部分,但是它却不能被同化进身份认同结构之中。它是一个异物,冲破了传统逻辑的范畴:它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既是在场的又是不在场的。瑞德九岁时开始进行一种特殊的“训练课程”——当他感到孤独恐慌需要父母陪伴时,就强迫自己推迟回家的时间,“我一发觉自己有想回家的冲动,就会跑到小巷尽头的大橡树底下,在那里站上几分钟,把我的情感压制下去”[6]172。面对家庭暴力的伤害,年幼的瑞德选择采取压抑和否认的情感防御机制。
成年后的瑞德选择把创伤经历融入到音乐中,音乐的韵律能够制衡混乱,那既是一种诗学的也是一种治疗的尝试。瑞德作为全世界最好的钢琴家在即将到来的“周四之夜”登台演出,他渴望父母参加他的音乐会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和认可。但是事实却是父母从未参加过他的音乐会,在“周四之夜”当晚瑞德试图通过钢琴演奏和演讲来解决小城危机的愿望不仅落空,人们甚至没有给他登台演出的机会,他不得不面对一个没有观众的舞台。瑞德情绪失控,只能从接待员斯达特曼小姐编造的谎言中寻求安慰。斯达特曼小姐谎称瑞德的父母曾经来到小城访问并且受到热情款待。讽刺的是,那些关于瑞德父母的信息都是斯达特曼小姐的不确定的记忆及猜测。瑞德的想象既神秘又美好,经由记忆的支撑,他能够在时时刻刻的回想中找到某种稳定感、安全感或归宿感,以此来弥合现实中的孤独与痛苦。在他的精神生活中,回忆具有强大的乌托邦功能。他的秘密情感记忆没有介入他的现实生活,或者说,并没有参与到他对现实自我的建构及对现实生活的日常规划中来。那只是他意识深处的死火山,是被压抑和潜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一部分,它不仅没有被实现的机会,甚至也不可能转化为关乎言语、举止、表情等实践性的行为,它是确凿无疑的、完全思想化的过去。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不得不承受分裂和痛苦的代价,不得不在达到职业巅峰的同时体会人生的虚空。
受童年创伤的影响,瑞德无法与家人融洽相处。他很少陪伴家人,始终沉浸在个人世界之中。在一家人难得的晚餐之后,瑞德寻找借口匆忙离开家,“我终于来到一条我熟悉的街道上,开始享受夜晚的宁静还有与我的思维和脚步声独处的机会”[6]289。瑞德童年时期的“训练课程”在此发挥了作用:逃避与家人之间的紧密关系。受到情感机能障碍困扰的瑞德无视妻子和儿子,他在无形中复制了童年时期机能失衡的家庭模式,也在无形之中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父亲和丈夫。瑞德忽视家人和朋友,沉浸于个人世界,这会阻碍个体认同的形成。德国“文化记忆”理论创始人扬·阿斯曼指出:“自我的形成,即个体的认同的形成,若不经过于他人的交往和互动,是不可能完成的。个体的认同是关于自己本身的意识,但同时也是关于他人的意识:他人对自己的期望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7]139尽管事业有成,瑞德却没有承担起作为丈夫和父亲应尽的责任,未能履行对索菲的承诺。索菲在挽救婚姻的种种尝试失败之后失望至极,主动选择放弃。随着索菲的离去,瑞德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瑞德的创伤经历束缚着回忆,那些回忆挣脱了所有的经验的连续性,而这些经验的连续性是行动能力和身份认同建构的条件。身份认同不再是一个可以遵循线性历史发展而得以确认的时间过程,身份既抛弃了过去,也不向往未来。而缺乏未来的维度,认同就只变成了一个在共时性的层面上临时构建的框架,充满了差异化而无法完成。
二、集体创伤记忆与身份认同
回忆之地是一个失去的或被破坏的生活关联崩裂的碎块。关于地点,石黑一雄认为:“我一直感觉我和那些同时代的作家就像电影制片人,寻找着地点。”[8]小说中瑞德在和鲍里斯去旧公寓取玩具的路上把鲍里斯抛在一边,跟随两名记者来到萨特勒纪念碑前拍照。瑞德站在纪念碑前面大笑拍照的表现引起市民的极大愤慨。有关萨特勒纪念碑的回忆给前进中的当下投下阴影,并像一块乌云一样伴随着它。“马克斯·萨特勒——为什么这个人,还有他在这座城市的历史中那一整段的故事,对这里的人们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实在叫人搞不清楚。理论上,它不足以成为意义重大的事啊。是的,没错,那差不多已经是一个世纪前的事情了。……萨特勒在本地居民的想象中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可以说,他的影响力已经变得神乎其神了。有时他令人害怕,有时他令人厌恶。而在其他时候,有关他的记忆又受人崇拜。”[6]374扬·阿斯曼指出:“一个集体在回忆中建立了与亡者的联系,从而确认自己的认同。记住某些名字这一义务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对一种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认同的承认”[7]58-59,“记忆不断经历着重构。过去在记忆中不能保留本来面目,持续向前的当下生产出不断变化的参照框架,过去在此框架中被不断重新组织”[7]35。
萨特勒纪念碑固定了对历史事件的记忆,成为回忆之地,在这里历史得到了空间上的具体化和印证。通过一个符号——命名——这个地方就被写入了群体的记忆之中。纪念碑是双重符号:它既编码了遗忘,也编码了回忆。文化符号可以得到建立并重新拆除,但地点的持久性即使在一个地缘政治的新秩序下也不可能完全消逝,它的持久性要服务于一种长期记忆,这种长期记忆除了为当下提供规定性的关联点之外,还要关注这些规定性的关联点是如何在历史的记忆中发生位移的。
虔敬的态度是人们对待过去应有的态度。怀着应有的虔敬读懂纪念碑的符号,使得过去在回忆中重新获得活力,体现了文化中古典主义的诉求,这种文化在遗忘的黑暗的时代之上架起了一座传承和回忆的桥梁,把这永恒的城市的痕迹从时间的侮辱和创伤中拯救出来。“你就这样来了,好啊。站在萨特勒纪念碑前面!笑成那样!然后你就一走了之。但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这儿的人来说,却没那么简单啊。萨特勒纪念碑!”[6]370在纪念碑之上投射了一个回忆的空间,也可以把它称为一个掩饰性回忆:在小城发生的回忆的文本空间在当地被投射到了纪念碑上。萨特勒纪念碑故事的讲述被个人的心理压力或者团体的社会禁忌阻滞了。罪孽、耻辱、强制、命运、阴影这些表述都是禁忌词汇、掩饰概念,它们并没有传达而是屏蔽了不可言说的东西,并且将其禁锢在它的不可通达性里边。在这个场地上被压抑的东西上演着回归场景。记忆在复活的同时也存在着记忆的缺失、空白和断裂。小城市民关于萨特勒纪念碑的回忆仅有只言片语,无法将这些记忆的细节连缀成有因果关系的整体。
关于历史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石黑一雄认为:“我理应创造我自己的世界,而不是从现实的表面复制事物。……我希望人们读我的小说不是因为他们想从中了解某段历史,而是因为我能够与他们分享一些更加抽象的人生观和世界观”[9],“我利用历史作为编曲来带出我的主题。我不确定我是否曾经扭曲了任何重大的事情,但是我最关心的问题不是精确地展现历史”[5]。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回忆和身份认同的联系又获得了新的现实意义。随着东西方世界边界的倒塌,两个唯我独尊的学说的极端对立造成的冰盖消融了,冻结的回忆的时代结束了。在东欧,族群的身份认同又回来了。人们曾经追求过解放,但这种解放在宣告了一个自己描绘的未来的同时,也意味着与过去和源头告别,现在解放的口号让位于对身份认同的问询。我是谁?这个问题被提出,并进一步发问:我们是谁?石黑一雄表示:“从根本上讲,我的确认为我大量书写了我那一代人和我周围的世界,也就是说,20 世纪70 和80 年代的西方,而不是试图去重构某些历史时期。……社会道德价值观经历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吸引着我。我们这一代人需要肩负起把本世纪所发生之事的记忆保存起来的责任。”[10]石黑一雄关注的不是如同历史学家那般准确地再现某段历史的事实,而是从作家的角度获取写作素材和表现人文主义的关怀。
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无可慰藉》中瑞德生活在寻找失去的时间的道路上,而同时代的人们则生活在当下,他们体现了使小城得以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重生的梦想。这座城市已到了危机边缘,许多家庭对视为理所当然的幸福深感绝望,小城的危机问题是事关未来和整个城市认同的问题。市民丧失的身份认同可以通过记忆重建来疗救。小城先前的文化生活领军人物克里斯托弗痴迷于现代音乐,那离奇古怪的节奏、破碎的节奏、断裂的拍号所代表的极端的东西对于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来说是陌生的。人们意识到文化记忆的断裂和遗忘导致通往过去的直接通道被阻塞。当下的危机使人们更加怀念往昔的美好时光,议员卡尔·佩德森回忆:“音乐厅真是座美丽的古建筑……那是个公众聚会的理想场所……这里还有个城市交响乐队,每月的第一个周日人们都会聚集在音乐厅门口的空地上。”[6]97各种类型的集体都倾向于将回忆空间化。城市建造了音乐厅并对其加以保护,因为音乐厅不仅是市民交流的场所,也是他们身份认同的象征。扬·阿斯曼认为:“每种文化都会形成一种‘凝聚性结构’,它起到的是一种连接和联系的作用。凝聚性结构可以把人和他身边的人连接到一起,其方式便是让他们构造一个‘象征意义体系’——一个共同的经验、期待和行为空间,这个空间起到了连接和约束的作用,从而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并且为他们指明了方向。”[7]6这个文化视角在小说中以音乐的形式得以呈现。音乐是小城市民的凝聚性结构,在音乐厅这个回忆空间里,人们相互信任,温柔以待。音乐会这个象征意义体系检视和保留了值得回忆的、构建身份认同的和指向将来的东西。
伯爵夫人是小城精英文化圈和权力阶层的化身。“弄到那么多留声机唱片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她动用了一位在柏林的行家采购商,把这事儿办成了。”[6]112伯爵夫人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圈不仅是高雅音乐的捍卫者,也是政治权力的操纵者。音乐不仅起着协调众人行为意志的作用,而且还担负了政治的使命。“从广义上而言,‘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都属于话语,从狭义上讲,话语是提出有效性主张的‘语言形式’。”[11]作为权力阶层的代言人,伯爵夫人的话语在话语场域中是占有合法地位的主流话语。官方话语常常会向其它形式的话语施加压力和规约的权力,最终产生排斥的效果。权力阶层的参与使得克里斯托弗所代表的文化精神风靡一时之后被社会抛弃,整个城市遭遇了文化危机,乐队指挥布罗茨基被包装成新的艺术灵魂人物。那些极端的东西是城市文化记忆的断裂。文化记忆在人格由于创伤而分裂的情况下成了生命的源泉。重新激活这种记忆意味着将离开毁灭和压迫的怪圈而获得一个更高的视野。音乐是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的灵魂。在经历了布罗茨基带来的刺耳狂躁的音乐之后,市民们意识到想要一些不那么极端的东西。文化连同它所包含的所有规范、价值、机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现实中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一种全然绝对的世俗秩序。文化的这种独特性和约定俗成性相对于个体而言就会变成隐藏不可见的东西。“与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共同认可的价值紧密相连、对共同拥有的过去的回忆,这两点支撑着共同的知识和自我认知,基于这种知识和认知而形成的凝聚性结构,方才将单个个体和一个相应的‘我们’连接到一起。”[7]6-7文化认同会巩固并且再生产一个文化形态,因而集体认同得以建构并且世代相传。布罗茨基因为酗酒过度和意外车祸而在舞台上摔倒晕厥,市民企图依靠布罗茨基挽救城市文化危机的愿望落空。舞台上苏醒过来的布罗茨基试图重新赢得妻子的爱,但是柯林斯小姐最终意识到她和音乐不过就是布罗茨基从中寻求安慰的情妇而拒绝了他。布罗茨基终将伴随着婚姻破碎、事业失败、尊严沦丧的精神创伤踽踽独行,在黑暗的角落里孤独地舔舐自己的伤口,最终遭到所有人的唾弃。
那些受到内心驱使追逐无望的个人抱负的市民把瑞德看作是救世主似的人物,使瑞德背负了城市文化和精神领袖的重任,因而在瑞德的个人愿景和市民的殷切期望之间产生一种奇怪的错位,二者之间的张力导致混乱丛生。功成名就的瑞德总是试图逃避过去的痛苦经历,期待从他人的赞美中寻求安慰。瑞德作为国际著名钢琴家取得成功,在艺术场域获得了地位和话语权并且对周围的人施加影响。公共历史和依赖环境界定的个体“我”之间的联系戏剧化,暗示着人文主义世界观中无把握的自我在政治中寻求官方的认可的渴望。石黑一雄在小说中把音乐作为一种隐喻,“虽然瑞德是音乐家,但是音乐并未以现实的方式发挥它在现实世界中的作用。音乐似乎发挥了政治的作用:什么样的音乐家应该被颂扬和降级的问题就像是谁应该出任首相和总统的问题。他是音乐家,他又不是音乐家。”[2]音乐成为政治问题的隐喻,这种音乐某种程度与把握人生和失去对生活的掌控有关。音乐形式变得如此复杂,而且对于生活品质而言至关重要,但是市民无法理解复杂的音乐,因此期待权威人士引导他们,而瑞德就是市民的音乐阐释者。他与市民分享音乐创作和音乐欣赏等领域的技巧和感受,彰显了他深厚的艺术造诣;在隐喻的政治层面,他发表自己对于当下政治和精神文化危机问题的见解,借由官方语言的正当化和合法化建构,维护权力阶层的宰制地位和社会等级。
小说中冯·温特斯坦市长做了演讲,指出城市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建构了市民的集体认同。“凝聚性结构……将一些应该被铭刻于心的经验和回忆以一定形式固定下来并且使其保持现实意义,其方式便是将发生在从前某个时间段中的场景和历史拉进持续向前的‘当下’的框架之内,从而生产出希望和回忆。”[7]6石黑一雄小说中的人物大多采取一种对支配者和控制者的认同性话语修复。从原先被欺骗被控制的地位转而反身成为中心话语的支持者,并且因为自己拥有了理想或信仰而获得精神上的价值感。用一个没有过去的幻影是不能够实现从过去和当下进入未来的跨越的。通过遗忘和回忆,人们能够冲破过去的魔圈走向未来。小城“就像绳结突然断开,厚重的幕帘掉落在地,然后展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充满阳光与温暖的世界”。[6]418
四、结语
小说的题目“无可慰藉”准确反映了包括瑞德在内的所有人物的心理状态。他们带着心灵的伤口怆然行走在一个危机重重的城市,各自书写着混乱落寞的人生,难以与人沟通,也无法从外界获得慰藉。瑞德陷入各种琐事无力脱身,他心心念念的“周四之夜”以失败告终,也未能修复与索菲的婚姻;鲍里斯重陷缺少父爱的困境;古斯塔夫直到离世也没能与女儿索菲冰释前嫌;布罗茨基遭遇车祸,与分居多年的柯林斯小姐重归于好的希望落空;酒店经理霍夫曼貌似名利双收,却无奈囚禁于冷漠失衡的婚姻之中;年轻钢琴家斯蒂芬再次体验了无法令父母满意的苦果;瑞德儿时的密友菲奥娜和桑德斯没有等来与瑞德的相聚,继续孤苦无依的生活。《无可慰藉》的发展态势不是事先既定的,而是一直到结尾都是开放式的。这是一个寻找和发现身份认同的过程,其中被忘却的传承、文化的集体记忆都为此给出了决定性的参照点。这个身份认同的更新是和文化相关联的,通过讲述和回忆重新得到。石黑一雄把小说描绘成一个没有结局的过程,对于主人公瑞德来说——从探索的意义上讲——没有结局,对于读者来说——在参与的意义上——也是没有结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