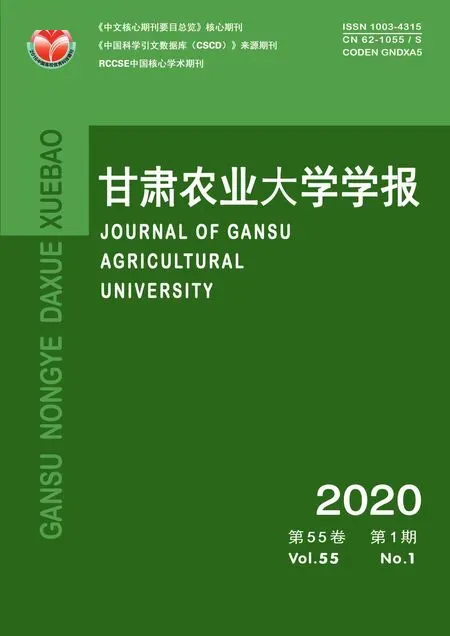不同演替状态下高寒嵩草草甸植物功能群分异特征
周春丽,林丽,朋措吉,李以康,曹广民
(1.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 西宁 810008;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高寒草地面积为5 800万hm2,占我国草地总面积的34.3%,为青藏高原的主体[1].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草地生态系统资源被过度消耗,严重影响了其生态系统功能,导致草地发生大面积不同程度的退化[2].高寒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是过度放牧而并非增温[3].过度放牧对草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牲畜对草地植物采食、踩踏和粪尿排泄物等作用,它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植物的生长发育、物种组成与地上生物量,改变植物群落数量和结构特征,甚至对群落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特征产生深远影响.
高寒嵩草草甸是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它对高寒畜牧业的发展、农牧民的生产生活以及中国乃至亚洲周边地区的生态安全皆具有重要的意义[4].高寒嵩草草甸的退化演替过程呈现多态性、渐变性和阶段性.由于不同演替状态的植物群落结构和景观特征呈现不同程度的分异,导致草地恢复所采取的措施明显不同[5-6].因此,认识草地的退化演替过程及其生态构件的响应机制,对探讨扰动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维持机制,指导退化草地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7].
高寒草甸的被动与主动退化假说认为,在放牧条件下高寒嵩草草甸的退化演替过程分为“四个时期、三个阶段、两种动力”[8].依据高寒草甸特征将其退化演替进程划分为禾草-矮嵩草群落、矮嵩草群落、小嵩草群落和杂类草-黑土滩四个时期,又根据小嵩草群落的草毡表层特征,将其细分为草毡表层加厚、开裂与塌陷3个子时期.
三个阶段分别为被动退化阶段(禾草-矮嵩草群落向矮嵩草群落的演替)、主动退化阶段(矮嵩草群落经小嵩草群落到杂类草-黑土滩的演替)和过渡阶段(矮嵩草群落).两种动力指气候变化与超载放牧,且一般认为,人类放牧行为对高寒嵩草草甸退化演替驱动效力高于气候波动[9].
本文主要研究了高寒嵩草草甸退化演替过程中草甸的关键状态,即禾草-矮嵩草草甸状态(A)、小嵩草草甸草毡表层加厚状态(B)和小嵩草草甸草毡表层开裂状态(C).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大,高寒嵩草草甸植被由禾草-矮嵩草群落—矮嵩草群落—小嵩草群落—杂类草黑土滩次生裸地的演替,这既是牧草优势种群的取代过程,也是植被对放牧干扰的主动抵抗过程[10].因此这3种草甸状态也代表着不同程度的放牧强度,且放牧强度依次增大,即:A 本研究综合应用生态系统过程学理论,采用时空转换的方法,以不同干扰强度下草地生态系统植物功能群数量及多样性特征变化为研究主体,主要考察草地所处演替时期、植被类型、优势群落组成、地表状况、草毡表层特征等因子,通过计算植物种群的重要值(物种相对盖度、相对生物量和相对密度的均值),比较了不同功能群在不同演替状态下的生态位差异,即不同植物功能群对放牧强度的响应情况. 研究区域年平均降水量为523 mm,主要降水集中在5~9月,年平均温度为-1.4 ℃,属于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 研究设置于青海海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人类干扰对高寒草地影响过程观测平台”.该平台建立于2005年,样地为冬春草场,在1995年前,草地归属于生产队统一管理植被分布较为均匀,处于禾草-矮嵩草草甸群落状态.1995年后的土地承包,草场分给4户牧民,围栏分割,由于牧户放牧制度的不同,使得各牧户草场地表特征、植物群落组成结构发生明显分异,形成了1个天然的放牧演替梯度.本研究选取高寒嵩草草甸退化演替过程的3个关键阶段,分别为禾草-矮嵩草草甸状态(A)、小嵩草草甸草毡表层加厚状态(B)和小嵩草草甸草毡表层开裂状态(C)(表1),为研究对象,对其植物群落及功能群数量特征进行监测,样地概况信息如表1所示[9]. 表1 样地概况 野外调查于2017年植物生长盛期8月下旬进行. 调查指标为群落各物种及植物功能群(禾本科、莎草科、豆科、杂类草)的盖度和生物量.盖度采用目测法,生物量采用收获法,样方面积为0.25 m×0.25 m;3次重复. (1)重要值: 式中,Ci为物种相对盖度;Bi为物种相对生物量;Di为物种相对密度. (2)生态位宽度指数:采用Levins宽度指数. 式中,Bi为种i的生态位宽度;Pij是物种i在第j资源位上的重要值占它所在全部资源位上重要值的比例;r为样方数. 植物功能群累计生态位宽度: 式中,B为植物功能群的累计生态位宽度;S为功能群物种数;Bi为种i的生态位宽度. 采用Excel 2003和SPSS 20.0对不同放牧强度下植物功能群数量的分异特征进行分析,其中单因子方差分析(ANOVA)最小显著差数法(LSD)显著性系数为0.05. 以植物物种数及物种重要值作为表征草地对放牧干扰的量化指标,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高寒嵩草草甸的物种数呈现持续的下降趋势(表2).其中,处于状态A的物种数有35种,隶属于13科28属,重要值大于10%的物种有小嵩草(19.28)和针茅(14.57),占该群落的33.85%.状态B有27种,隶属于12科23属,重要值大于10%的物种有小嵩草(19.82)、美丽风毛菊(15.54)和针茅(11.88),占该群落的47.24%;状态C有23种,隶属于11科21属,重要值大于10%的物种有针茅(22.54)、美丽风毛菊(16.28)、小嵩草(11.38)和矮火绒草(10.31),占该群落的60.51%.即针茅和小嵩草是高寒嵩草草甸的原始群落优势种,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草地丰富度呈持续下降趋势,被以美丽风毛菊和矮火绒草为代表的杂类草所替代,演变为杂类草草甸. 将植物功能群分为禾草科、豆科、杂类草和莎草科四大类,以功能群重要值作为其度量指标,评价其对放牧干扰的响应.杂类草是高寒嵩草草草甸的主体,其功能群重要值为43.07±3.92.其次是莎草科与禾本科,分别为23.91±5.73和21.12±2.65,豆科最小,为11.43±2.35.不同植物功能群对放牧干扰呈现不同响应特征(表3).其中,随着放牧强度增加,杂类草功能群物种数减少,A、B、C状态下物种数分别为21、18、14种,状态B、C物种丢失速率分别为14.3%和33.3%,丢失的主要物种包括银莲花、卷鞘鸢尾、繁缕、摩苓草等物种.然而杂类草功能群的重要值却随随着放牧强度的加重呈现持续增加的变化趋势,由状态A的37.53显著增加到B、C状态的46.1和45.58(P<0.05),B、C状态无显著差异(P>0.05).这种变化主要是由菊科的美丽风毛菊和矮火绒草重要值改变所致,其中美丽风毛菊重要值由状态A的7.76显著增至B、C状态的15.54和16.28(P<0.05),矮火绒草重要值由状态A的1.19增加到B状态的4.46,和C状态的10.31. 组成高寒嵩草草甸的莎草科植物主要有小嵩草和矮嵩草,放牧作用对莎草科植物物种的影响作用甚微.小嵩草的重要值是矮嵩草的2.3~2.5倍,随放牧强度的增加,莎草科植物的重要值由状态A向状态B的演替略有增高(P>0.05),而由状态B向状态C的演替,发生显著的降低,状态C较状态A、B分别降低了42.8%和44.1%. 随着放牧强度增加,禾本科植物功能群物种数减少,A、B、C状态下物种数分别为5、4、3种,丢失的主要物种分别是溚草、藏异燕麦和双叉细柄茅.而其植物功能群重要性呈现“V”型变化趋势,状态A与C差异不明显(P>0.05),而状态B与状态A和C均达显著性差异(P<0.05),且这种变异主要是由针茅重要值变化所致,状态A演替到状态B,重要值降低了18.5%,而由状态B演替到状态C,重要值增加了89.7%. 豆科植物功能群对放牧干扰极为敏感,由状态A演替到状态B和C,其物种由5属7种下降到3属3种,丢失4个种,分别为多花黄芪、黄芪、花苜蓿和青海棘豆.随着放牧强度增加,杂类草功能群的重要值亦呈“V”型变化趋势,状态A与C差异不明显(P>0.05),而状态B与状态A和C均达显著性差异(P<0.05),这种改变是披针叶黄华和异叶米口袋的重要值的演变所致.其中,披针叶黄华由状态A的4.79和状态B的3.46显著上升至状态C的6.97,异叶米口袋由状态A的2.04和状态B的2.34显著上升至状态C的6.10. 将高寒嵩草草甸植物功能群分为:禾草科、豆科、杂类草和莎草科四大类,以功能群的生态位宽度(niche breadth)作为度量指标,来评价该类群生存所必需的生境最小阈值、对资源利用的能力及其对放牧干扰的响应过程. 四大植物类群,其生态位宽度的相对大小为杂类草>豆科>禾草科>莎草科,其生态位宽度分别为2.03±0.38、0.55±0.31、0.45±0.09以及0.22±0.00.其中,杂类草在群落中的生态位宽度最大,在放牧干扰下逐渐演化为草地泛化种,而莎草科植物生态位宽度最小,逐渐为草地特化种.高寒草甸退化演变的终极状态是“杂类草-黑土型次生裸地”也与此有关. 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高寒嵩草草甸的生态位宽度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其对放牧干扰响应的变率亦表现为杂类草>豆科>禾草科>莎草科,其值分别为46.03%、32.74%、11.00%和0.07%.这也代表了不同功能群对放牧干扰的敏感性.而基于生态位对能成为处于不同演替状态优势功能群的评判,尚需结合生态位宽度及其对放牧干扰的应变率,其量化特征尚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表2 不同演替状态下植物群落物种组成及其重要值 表3 不同演替状态下植物功能群的重要值 同行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etters on the same line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图1 不同演替状态下植物功能群的生态位宽度Figure 1 Niche breadth of plant function groups in different succession state 地上生物量是反映植被生长状况和草地生产力的关键指标,对群落结构和功能对放牧干扰响应的变化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11].高寒嵩草草甸地上生物量为341.91±13.93,杂类草、禾草科、豆科和莎草科各功能群对其的贡献分别为48.90%、23.05%、14.10%、13.95%.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大,高寒嵩草草甸地上生物量呈现“V”字形变化,最低值出现在状态B,且与状态A、C呈现显著差异(P<0.05).状态A和C差异不显著(P>0.05). 放牧干扰对不同植物功能群地上生物量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放牧强度的改变,使得植物功能群数量特征发生一定的变化,从而影响了其在群落中的地位及作用.随着放牧强度增高,草地中的豆科和禾本科植物均表现为先降低后增高的趋势;杂类草功能群表现为显著的增高的趋势,莎草科功能群表现为一定程度的降低趋势(图2).从禾草-矮嵩草草甸向小嵩草草甸转化的过程中针叶型植物总体表现为下降趋势,而阔叶植物总体表现为上升趋势. 图2 不同演替状态下植物功能群的地上生物量Figure 2 Above ground biomass of plant function groups in different succession state 表4 植物功能群对放牧反应的相关性分析 **表示差异显著(P<0.01). ** indicat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1). 根据功能群对放牧响应的相关关系规律,将其分成3种类型,1种为协同型,代表功能群为禾本科同豆科功能群,2者对放牧强度改变的反应相似;1种为互补型,代表功能群对组为杂类草同禾本科,和杂类草同莎草科,杂类草同这两种功能群之间对放牧强度改变的响应相反;第3种为中性型,代表为豆科同莎草科,豆科同杂类草,禾本科同莎草科功能群,它们彼此之间不敏感. 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对研究植物群落中种群之间的资源利用能力、种间关联、种间竞争等均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区域草地处于相同地理单元下,具有相同的地形、地貌及气候特征,且草地土壤发育具有同源性[12],但是当相同草地在区别化经营后,植物群落数量特征发生了明显的分异,而引起该分异的主要原因为放牧压力的不同. 本研究发现,随着放牧压力增加,植物群落地上生物量呈下降趋势.引起植物群落地上生物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为优良可食性牧草(禾本科和莎草科植物功能群)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在小嵩草草甸演替状态,禾本科和莎草科植物的消长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草地的退化,并且这种变化受到气候波动的影响较为明显,因而表现出一定的随机性[13-14],但其总的变化趋势是两者之和有减缓草地地上生物量降低的趋势,这同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监测结果相似[15]. 此外,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可食性优良牧草在群落中的地位和作用容易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这同绝大多数放牧草地生态系统的研究相似[16].而当可食性优良牧草被抑制以后,杂类草表现出对剩余资源利用能力的优越性[17],即在小嵩草草甸草毡表层加厚状态,禾本科、豆科和莎草科植物功能群的地上生物量都被不同程度的抑制时,杂类草的地上生物量仍可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从植物功能群在群落中的权重上看,杂类草功能群同禾本科和莎草科功能群在重要值上表现为随退化演替变化的强负相关关系,说明杂类草所利用的资源很有可能是禾本科和莎草科被放牧抑制后的剩余资源空间. 豆科植物同禾本科植物功能群之间有强正相关关系,说明两者之间有可能是互惠功能群.首先禾本科植物一般为喜氮植物,这在速效氮匮乏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中[18],豆科植物的增加有助于改善生态系统的氮素供给能力,提高禾本科植物对逆境的抗干扰能力.高寒草地生态系统总体的特点是随放牧强度增高,植物群落生物量被抑制,但随着草地退化的进行,草地地表出现不同强度的裂缝[5],一定面积的裂缝(5%~30%)对改善土壤的透气透水情况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易形成沃岛效应,使得原本被抑制的多种植物功能群得以恢复,出现了退化过程中系统地境改善,实现自我调节的恢复过程. 高寒草地生态系统植物群落总体同外界干扰具有一定程度的协同进化关系,草地的进展演替过程伴随着植物群落R对策植物数量减少而K对策植物数量增高,而退化演替过程则相反.随着放牧干扰强度的增大,植物群落的生存环境发生恶化,K对策植物,如垂穗披碱草等一些禾本科植物在群落中的比例降低,而R对策植物比例升高,如美丽风毛菊等杂类草.且不同植物功能群组中R对策与K对策植物的比例变化亦不同. 随着放牧强度增加,比例升高最为显著的R对策植物是杂类草功能群,其中又以菊科植物最为明显.菊科中一类是以矮火绒为代表的短命速生植物,该类植物的特点是生命周期短,适应性强,且没有明显的光周期.该类植物属于喜光植物,在郁闭度较高的禾草-矮嵩草草甸中,高大的禾本科植物对光线的遮挡影响了其生长发育,导致其长势较弱,而在高大的禾本科植物被抑制以后,低矮和相对覆盖度较低的草被植物可以一定程度的提高矮火绒的成活率,提高其在群落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类菊科植物以美丽风毛菊为代表,其特点是多年生且种子产出量极高,1个母株在生长季节中可以产生种子,且母株可以存活多年,其种群扩充能力极强,当环境中优势种被抑制后,很容易间接促进该类群的发展,这一方面表现为植物群落对环境资源利用能力的种间调节,另一方面表现为生态系统可以通过种间调节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减弱外界干扰对系统生产能力的影响,实现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最大程度维持. 当然,由于在根据生产利用能力划定的草地功能群中,包含了多种生态功能型植物,因此本研究中,同一功能群类别中的许多植物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表现.因此,如果未来研究中能够寻找到更好的表征植物群落生产和生态特征的且划分标准较为简单的分类方式,可能对解释植物群落总体对外界干扰的响应与适应具有重要意义. 高寒草地生态系统是1个集草地、植被、家畜、人类管理于一体的自然经济复合体,草地生态系统的自然资源层面的发展是整个复合体经营运转的基础,而生态系统构建中的植物、土壤和地境同外界干扰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的机制. 草毡表层就是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应对放牧践踏而形成的1种自我保护和缓冲[12],但草毡表层的过度发育必然影响土壤的通气透水能力[20],成为草地养分和水分循环入渗的限制性因子及草地恢复的瓶颈因子.而草地生态系统的裂缝则可以缓解这一作用,裂缝是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地境特征,一般出现在高寒小嵩草草甸草毡表层开裂状态,形成原因同植物群落中密丛型植物在群落中和单位土壤表面的比例、数量、活力、放牧强度大小等因素有关[9].一定宽度、长度和面积的裂缝有助于改善土壤的通气透水情况,有利于草地的恢复,在本研究中表现为在小嵩草草甸草毡表层开裂状态(C)禾本科植物和豆科植物功能群的数量和地位的升高,从B状态到C状态,豆科植物的重要值由8.14增加至13.52,禾本科植物由17.48增加至23.70.同时裂缝中也具有较好的土壤环境状况,形成沃岛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生态系统的退化进程,促进草地的恢复. 生态系统在外界干扰条件下具有明显的自我调节能力,其目的是促进环境资源利用最大化,其手段是充分利用不同植物对干扰的响应策略;同时生态系统也可以通过系统内部各构件对干扰的响应程度不同,缓冲干扰对生态系统的影响;高寒嵩草草甸具有较为明显的自组织稳定机制,如果被破坏,也将成为草地恢复的契机,如裂缝的出现.1 研究区概况

2 试验方法
2.1 采样方法与时间
2.2 各项指标的计算
2.3 数据处理
3 结果与分析
3.1 物种数对放牧干扰的响应
3.2 植物功能群对放牧干扰的响应
3.3 不同放牧梯度上植物功能群的生态位分析



3.4 地上生物量对放牧干扰的响应


4 讨论
4.1 植物群落可以通过不同水平的生态位分离维持系统的相对稳定
4.2 植物通过生存策略改变适应干扰环境,最大程度利用环境资源
4.3 草地地表特征的改变同植物演替及稳定性维持机制的响应与耦合关系
5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