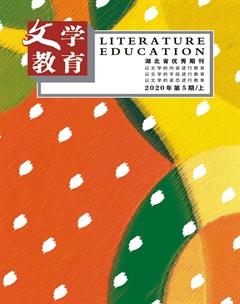打开文学的视野
朱一帆
贺桂梅,1970年生于湖北,文学博士。教育部2015年度青年长江学者。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研究和当代文化批评。已出版专著《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2003)、《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2005)、《“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文化研究》(2010)、《思想中国——批判的当代视野》(2014)、《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2014)等,另有学术随笔《西日本时间》(2014),并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说起来与贺桂梅老师的第一次“神交”,是痛并快乐着。快乐是因为阅读《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之后,惊异于贺桂梅老师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开阔的文学批评视野。要知道,这之前学界关于4、50年代之交的文学现象阐释,大多从简、从单,多把当代文学的开始描绘为是国共两个区域两支队伍的“会师”,较少阐释这其中的复杂性。至于痛苦,则是因为我的画虎不成反类犬。其时作为研究生的我,也从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出发,草拟了《萧乾文学创作发生学探析》的硕士论文题目,因为学识不足、积淀不够等一些随处可见的漏洞,这篇论文未能成形便“流产”而亡。和成长期的其他“事故”一样,这一“事故”也被我深埋心底,鲜少拿出来检视,至于它的“残骸”,也早已转化成我的人生经验,构成生命的底色。只是机缘巧合,多年后,面对要为贺桂梅老师的文学批评作素描时,这一历史的“沉渣”又泛上心头。如今的我,如果能重返“历史现场”,只想轻拍那个“她”的肩膀说:贺桂梅老师文学批评的视野与使命,你真的了然于心了吗?
一
贺桂梅老师出生在湖北嘉鱼县,一个取《詩经·小雅·南有嘉鱼》之义得名的县城。因地处长江中游,这里每年6、7月份梅雨不断。在混合着青春期感触和粘稠阴雨气息的江南水乡里,贺桂梅度过了她的青年时代。1989年,她凭借优异的高考成绩,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这之后,她在北京大学接受了完整的本、硕、博阶段的高等教育,并于2000年毕业。面对这十年的学生时光,贺桂梅本人在日后鲜少有回忆性文字进行描述。可以见到的,只是蔡翔老师写于2005年的文章《贺桂梅印象》。在他看来,这一时期的贺桂梅“少年老成”,“寡言”的很。只是在昔日中文系老友们眼中,北大学生时期的梅梅,是和他们在小南门外酒馆儿一起读过诗,一块儿吞过烟的热血女青年。至此,北大学生时期的贺桂梅形象,便也如说不清道不明的思绪,消散在时间的阴影里。但是,与时间的阴影相交织的光源——作为文学批评者的贺桂梅形象,却正恰如其分地打开。
1993年,本科四年级的学生贺桂梅,为完成老师张颐武的“当代文学专题”课程作业,提交了《新话语的诞生——重读<班主任>》这篇文章,之后其被发表在1994年第1期的《文艺争鸣》上。贺桂梅在谈到这篇文章时,她说:这是“最早的一篇,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文章的粗糙和幼稚自不待言,今天重读它,颇有隔世之感,很难回想当时写作时的具体思路。”这显然是自谦之词。多年后的我在看到这篇文章时,还是惊讶于文章用笔的老道,以及对新学说使用的深入浅出。而且,从贺桂梅老师多个论文选本都将其收录这一事实看,她应该是非常珍视这篇文章,哪怕将其视作是贺桂梅老师学术道路的起点,也并不为过。两年后的秋天的晚上,那些黄昏的时辰退进大海,夜的想象涌上来的夜晚,研究生二年级的贺桂梅,和其他现当代专业的同学,一起在中文系五院的会议室,借着钱理群老师组织的“40年代小说研读”课程,听见秋天微风拂过木质课桌的声音,看见微光透着玻璃走入教室的脸庞。贺桂梅在堂上作了《沈从文<看虹录>研读》的报告。报告中有语:“《看虹录》对女性身体与鹿身体极端精微的凝视和呈现,正是出于表现生命本质的企图,他悬置了任何关于身体的‘情欲‘道德等的理解,而仅将其看成‘生命的形与线的‘形式,‘那本身的形与线即代表了最高德性即神性,人由此获得与上帝造物相通的处境。”这一老成、干练的话语表述,实在很难与一个研究生二年级的小女生联系在一起。有感于学生贺桂梅在报告中吐露的观点,钱理群老师在课堂上说:“我想就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的角度,来谈谈沈从文在《看虹录》里所作的实验的意义——这也是贺桂梅同学的报告中已经涉及的,我不过再作一点发挥而已。”经师易遇,人师难遭。钱老的谦卑,不仅映衬出他自己的学术风范,同时也显露出学生贺桂梅“未若柳絮因风起”的才情。不出意外地,这篇课堂报告《沈从文<看虹录>研读》日后发表在1997年第2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朝来庭下,博士三年级时,贺桂梅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批评的增长与危机——90年代文学批评研究》。她在该书中对九十年代批评的主要问题和主要批评话语类型,作了资料清理和观点述评。不难看出,这一以史料为出发点的学术研究,深受其导师洪子诚治史风格的影响。只是也如同门刘复生指出:“对于洪子诚的历史研究而言,给历史叙述提供支撑的其实并非所谓‘史料……而是他的历史哲学与逻辑判断……但彼时的贺桂梅显然无法达到这种史料背后的判断,也就是说,她还没有获得准确的判断立场或立足点以及足够的理论穿透力。”
“人生的道路虽然十分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尤其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千禧年前后的贺桂梅,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凭借学术报告《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当代文学学科建制》留在母校,成为人师。而且,她开始第一次尝试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处理文学以外的当代文化问题,并由此推出《世纪末的自我救赎之路——对1998年“反右”书籍出版的文化分析》这篇文章。日后抚鳞追昔时,她说:“如果说我确实由比较纯粹的文学研究开始向着相对广阔的文化/理论视野的‘转向,那么这篇文章应该算是一个重要开端。”如何在一种更大的视野中重新理解文学的位置,及文学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成为日后脱离了学生身份的教师贺桂梅主要考虑的问题。文学的视野,也在教师身份的贺桂梅那里,被恰如其分地打开。
二
2000年,贺桂梅以教师身份站上讲台,开始为北大中文系的学生讲授课程。这个讲台,实话讲,不那么好“站”。而要努力的在那些和自己年龄相差无几的学生面前“为人师表”,也不那么容易。贤良如孔子,也不曾逃过学生子夏的发问:“然则四子者何为事夫子?”转型期灵魂的如何安放,确实让初为人师的贺桂梅苦恼了一阵子。如果说这是初入职场的每个“小白”都会遭遇的问题,那么对自己“学院派”身份的审视与反思,则最终塑造了贺桂梅独一无二的教师形象。“学院派”三个字,在贺桂梅工作的第一天便和她如影随形。面对这样一个身份标签,贺桂梅倒也坦然,她直言:自己是“一个置身当代文学学科建制内的文学研究者”,是“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接受系统的学院训练而成长的当代文学从业者”。但是得益于贺桂梅气质鲜明的自反性批判立场,即对自己站立的位置,有自觉地分析和审视,她的文学批判风格,有着“学院风”气息,但是却也不拘泥于“学院风”。她曾说:“随着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走上‘正轨,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置身的学术生产体制的影响……意识到自己生活于种种知识生产机器当中,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可以超然其外。我的困惑在于,我可以多大程度上拓展这份被‘给定的空间,同时我又如何被这文化空间所限……不让自己为专业所限,尝试打通一些可能的学科、领域的隔绝,是我之‘拓展的另一种方式。”辩证法的光芒在这里闪现,自我反思的扣问精神,也在这里彰显。之后沿着跨学科的批判视野,贺桂梅完成了自己从纯粹文学批评向跨学科文学批评的转型,也树立了自己“文化批评”“思想史”“学科史”和“文学史”的基本学术格局。
贺桂梅老师在2003年出版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是个绕不过去的文本。因为这一文本是她首次用自己的“语言”和问题从事学术工作,并最终实现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转型。面对90年代之后的“全球化”语境和世界格局的变化,贺桂梅敏锐捕捉到了当代文学/文化史中先前被遮蔽的、现如今正在浮现的繁复内涵。从此角度入手,在全书中,她以开阔的历史视野,揭示了40-50年代转折期蕴含的复杂文学内涵和文化内蕴,着力呈现了深陷其中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和精神脉络。这一对先前当代文学学科领域内已成定论的问题的再考察,对后来者如何理解当代文学史,尤其是探讨整个20世纪文学现代实践的复杂多端,无疑都有着重要意义。之后,沿着跨学科批判的道路,她在2005年推出了专著《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该书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探讨了在“文革”后30余年的时间跨度中,当代中国一些前沿性的思想、文化和文学问题。典型如对20世纪80-90年代的思想状况作整体观照;从世纪之交的文学与文化角度入手,对80-90年代小说中的北京记忆作书写;从当代文学学科视野入手,考察“现代文学”的确立与50-60年代的知识生产与学科体制。2010年,贺桂梅老师出版了《“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一书。该书从20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寻根”思潮、“文化热”、“重写文学史”思潮、“纯文学”实践等六个文学与文化思潮入手,对80年代的整个思想状况进行了知识社会学的考察。在谈到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时,她指出:80年代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并不能完全用五四传统加以统摄。即便是“文学性”“人性”“现代”“传统”这些看起来很五四的话题,在80年代的具体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是由“80年代中国”这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场域中,不同的思想与文化资源构造出来的。更重要的是,我发现,80年代谈论的“五四传统”以及“现代化”“民主”“自由”“人性”等范畴,与五四时期中国语境中对于这些范畴的理解并不相同,实际上是一种由6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界塑造出来的、并在70-80年代发展为某种全球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不管有意或无意,都与这种新的知识范式/意识形态关系更密切。五四传统只不过在这个认识论“装置”中得到了重新阐释而已。如果不去关注这个“装置”,而只关心这个装置里面的五四表述,大概就只能说是舍本逐末、还是在“新启蒙”的历史意识内部谈问题。
这一看待问题的角度与方法,很“贺桂梅”。从文学领域“跨出去”获得“整体性”的公共意识,之后“再回来”,把文学问题放在一个开放的问题域中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思考,这是贺桂梅老师在从事文学批评时的方法与态度。孟繁华和张清华老师也称赞她“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已远远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它是综合了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一起提出来的。但是,它又没有离开当下中国的问题场,并且仍然是文学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70后一代,有如此宽广的视野,实属不易”。
90年代的北大,语言在这里激辩,思想在这里迸发。如何分析80-90年代转型,如何理解“人文精神”大讨论,如何看待知识界所谓“新左派”与“自由派”的论战,这些话题不仅在课堂上被唇枪舌战,就是在课下的小饭馆儿里也是“头牌”“座上宾”。中文系里洪子诚老师的文学史研究、戴锦华老师的文化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钱理群老师和汪晖老师的思想史研究、陈平原老师的学术史研究,张颐武老师的后现代主义批评等等,是“贺桂梅们”暗夜里一闪而过的灯火,造就了他们夜的神迹。至于结构——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学说,让“贺桂梅们”身披利剑,在学术领域挥毫泼墨。受到如此多大师的影响与指点,自然是一份幸运。不过,这些“学术上的‘父亲”,对贺桂梅也难免带有壓抑性的意味。好在,贺桂梅不断努力,以一种“跨出”文学的社会性视野,去重新理解文学的位置,思考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走出了一条对“父辈”们创造性继承的学术道路。当青沥的夜色褪去,阳光亮堂堂地照进院子里,成为教师的贺桂梅,打开文学的视野,走出“影响的焦虑”,用学术这一“语言”,想象着一种更好的生活的能力。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