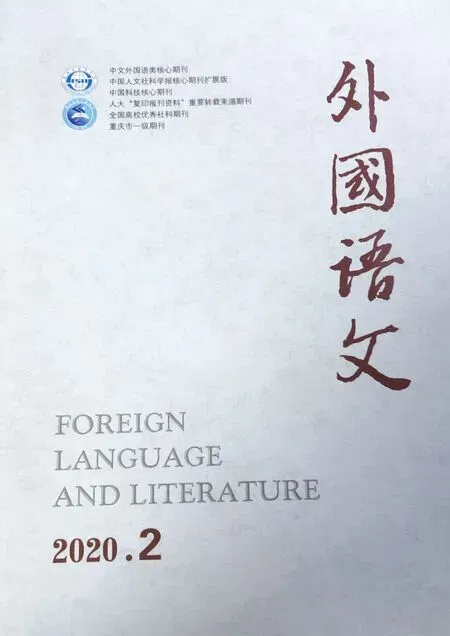古希腊“神话”词条
刘小枫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刘小枫,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法德系德语专业,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责任教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博士生导师;与外语相关的代表作有:《凯若斯:古希腊文教程》《巫阳招魂:亚里士多德诗术绎读》《以美为鉴》《拥慧先驱》,译著《柏拉图四书》。
0 引言
即便在当今的学术出版物中,古希腊“神话”这个语词出现的频率也相当高,但在《牛津古典词典》中,我们却找不到myth词条。
原来,myth这个语词源于古希腊词语mythus,其原初含义是“言说、叙述”,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时衍生为意指带娱乐性质的听起来未必可信的“故事”。罗马人用fabula来对译mythus,后来的欧洲人由fabula衍生出fable。直到18世纪中期,刚形成甚至正在形成的欧洲知识界才逐渐回到希腊人自己的mythus。
1 《牛津古典词典》中的“神话”词条
在《牛津古典词典》中,我们可以找到Fable词条,但这个语词通常译作“寓言”。按这个词条的解释,fable指“古希腊民间传统和其他古代文化中的短小故事”。这类故事通常呈现某种带“冲突”性质的“境遇”,而发生冲突的角色从动物、植物到各色人或神,混而不分。词条作者还提醒我们,尽管这类短小故事所呈现的冲突往往与生死有关,可以说非常严峻,但叙事本身(无论诗体还是散文体)又大多带“搞笑”的谐剧色调。
词条作者提到的首个“寓言”范例即“伊索寓言”,我们难免会问:“寓言”等于“神话”吗?这位作者说,在希腊文学中,寓言作为一种文学“范式”所采用的轶事要么是“神话性的”,要么是“纪实性的”(historical),当然也有纯属虚构的,并说“这始于赫西俄德时代”。这无异于说,“神话性的”叙事不是“纪实性的”,也不是纯属虚构的,但作者没有说,“神话性的”叙事是什么。按词条作者的解释,“寓言”故事大多来自口传传统。即便有了这样的解释,我们仍然无法搞清“寓言”与“神话”的差异。事实上,所谓的“神话”故事大量见于荷马、赫西俄德、品达和雅典的戏剧诗人,而当时的人们并不把这些故事称为“寓言”。
《牛津古典词典》没有myth词条,却有一个名为mythographers的词条,译成中文应该是“神话作者”。词条作者把这类graphers(作者)解释为“收集英雄神话”的人,比如教诲诗人赫西俄德、史称第一位纪事家(史学家)的赫卡泰厄斯(Hecataeus,约公元前550—前480)等等。据说,在他们的作品中,myth(神话)构成了实质性的内容。这个词条的作者还说道,早在希腊化时期,已经有学人整理古诗作品中出现的mythus(神话)。比如,有一本书的书名就叫MythographusHomericus(荷马的神话作者),该书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整理出数百个“纪事”(historiai),加以归类和解释。在这位希腊化时期的学人眼里,所谓“神话”就是他们希腊人的“历史”。
《牛津古典词典》中还有一个名为Mythology(神话学)的词条,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到对“神话”的解释,当然是现代的——更准确地说是后现代的解释。词条的作者告诉我们,迄今还没有学界普遍接受的“神话”定义,但德国的古典学家布克特(Walter Burkert,1931—2015)作为“神话学家”所给出的定义大体比较稳妥,即“神话”是“附带某种具有集体意义的东西的传说”。对这种几乎等于没下定义的解释,求索释义的读者难免不会感到满意。一旦得知如今要为“神话”下定义有多难,我们就能够体谅这类似是而非的解释(杭柯,2006:52-65)。倘若如此,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搞清楚,一部现代的古典辞书给“神话”下定义为何很难。
2 现代辞书的兴起
编写辞书是现代欧洲文明兴起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与“人文主义”精神倡导“人文教育”有关。在16至18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意识形态仍然占据支配地位,若要与这种意识形态作对,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恢复古希腊的“神话”意识形态。
关于这两种意识形态,布鲁门伯格(1920—1996)有如下说法(布鲁门伯格,2012:244-245):
在古典世界的文本流传之中,(古希腊)神话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刺激、驱动、孕育和催化了想象力以及欧洲文学的正式规范,耶稣基督(诞生)之后,《圣经》的世界对(欧洲)两千多年意识的渗透之深无出其右,尽管如此,在文学表现层面,《圣经》的世界几乎是个空白。
这无异于说,基督教的“教义”意识形态抑制欧洲人的文学想象力,而古希腊的“神话”意识形态则相反。然而,布鲁门伯格的大著《在神话上劳作》(ArbeitamMythos)以“实在专制主义探源”为题,由此挑起应该如何理解古希腊“神话”的问题,着实令人费解。在解释赫西俄德的《神谱》之前,布鲁门伯格(2012:28)这样写道:
如果神话的功能之一是,将神秘莫测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名分上的确定性,使陌生的东西成为熟悉的东西,让恐怖的东西成为亲切的东西,那么,当“万物充满神灵”之时,这个转换过程就ad absurdum(走向荒谬)。
这话让笔者不禁想到17世纪的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他撰写的卷帙浩繁的《历史与考订辞典》(1697年首版,1702年增订版)算得上现代的第一个辞书里程碑。在出版以后的一百多年里,这部《辞典》一直具有广泛影响力,几乎成了读书人的《圣经》。培尔当然不是撰写辞书的第一位现代学人,16世纪的法国著名人文学者卡洛·斯特芳(Carolus Stephanus,1504—1564)编的《诗学历史辞典》(Dictionariumhistoricumadpoeticum,1553),史称法国的第一部百科全书。培尔的辞典被视为现代辞书的里程碑,原因在于他以科学理性的批判精神纵论古今,不仅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百科全书》构想(伏尔泰、卢梭、狄德罗无不崇拜培尔),也成了哲人休谟乃至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和美国的立国之父杰斐逊、富兰克林等各色历史人物崇拜的对象(Cazes,1905;Dibon,1959;Bayle,2000)。
一部辞书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历史作用,盖因欧洲历史当时正经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变革。在《历史与考订辞典》中,尽管也可见到“有罪的女人”(Women who was a Sinner)之类的词条,但培尔拟定的词条大多属于如今所谓的思想史范畴,显得颇为哲学化。培尔编写这部辞典的意图,首先是要纠正他自己在阅读各种史籍时发现的所谓“错误”,尤其是针对莫雷利在1674年出版的《历史大辞典》中的错误,这就是critical一词的首要含义(Moreri,1674)。但是,培尔的意图并不仅仅是学究性的,通过编写词条,这位加尔文派信徒更企望让世人明白:人类有记载以来的种种“真理”都是不可靠的意见,世间到处可见的只有轻信的积习。
培尔把笛卡尔的理性精神推到尽头:理性最终能够证明的仅仅是怀疑一切,而非理性地相信什么。不仅基督徒的信仰因违背自然法则是荒谬的,理性主义者自以为凭自然理性获得的知识也经不起怀疑的检验。人的自然理性根本不可能发现自然的真理,理性的作用和力量仅仅在于它是一种“批判”手段(Bayle,1965:XIII-XIX)。
笔者所能见到的培尔《辞典》是19世纪的版本(Bayle,1740/1826),虽然有四卷之多,仍然是“摘选和节译”(selected and abridged),其中没有fable词条。由于检索学术文献受到限制,笔者无法查到18和19世纪出版的两个全本,无从得知其中是否有fable或mythology词条(最全的英译本和法译本是:Bayle,1734-1741;Bayle,1820-1824)。如果没有,那就有些奇怪。毕竟,在培尔时代,凭新的数学理性揭露种种古典叙事(所谓“神话”)的虚假,已经蔚然成风(Manuel,1959:24-46,314-315)。
3 启蒙百科全书中的“神话”词条
接下来最著名的辞书,恐怕非狄德罗(1713—1784)和达朗贝尔(1717—1783)主编的《百科全书》莫属。狄德罗起初应出版商邀请翻译英国皇家学会会员钱伯斯(Ephraim Chambers,1680—1740)的《百科全书:或艺术与科学通用辞典》(1728),据说由于如今所谓“版权”问题,狄德罗于1747年邀约朋友达朗贝尔一起另起炉灶,共同组织一帮新派文人编写《百科全书》。
1751年,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主持编写的《百科全书》第一卷(字母A条目)面世,编者署名为“一个文人团体”(狄德罗,2007;Diderot et al.,2008)。六年后(1757),《百科全书》第七卷(字母F-G条目)出版,其中由达朗贝尔执笔撰写的《日内瓦辞条》惹来日内瓦当局抗议,引发政治风波。紧接着,卢梭发表了抨击这一词条的《致达朗贝尔论剧院的信》,导致“百科全书派”内部分裂,达朗贝尔以及其他一些撰写人退出了这一划时代的编写事业。狄德罗坚韧不拔,在伏尔泰(1694—1778)鼎力支持下,于1765年完成了《百科全书》后十卷的编写,同年一并发行,轰动欧洲。在这部《百科全书》中,狄德罗亲撰的词条达1269条,最长的词条有140页,无异于一部专著。
钱伯斯的《百科全书》中有fable词条,但篇幅比如今《牛津古典词典》中的同一词条长很多:12开本的双栏页面足足两页半(等于5栏),差不多是一篇小文章。作者区分了ratioanl fables-moral fables-mix’d fables,我们可以见到,当时的学人所具有的学术观念与今天有不小差异。但是,作者提到的第一个fable作者同样是伊索,随后又说到荷马,似乎没有区分“寓言”与“神话”,这又与如今《牛津古典词典》中的同一词条有类似之处。在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中,没有fable词条却有mythology词条。词条作者(C. de J. Louis)区分了fable与myth,并提到巴利耶神父(Abbé Antoine Banier)的专著《依据史学解释神话和寓言》(LaMythologieetlesfablesexpliquéesparl’histoire,Paris,1738—1740),似乎此书首次区分了fable与myth(Fontenelle,1932;de Lavaur,1731)。《牛津古典词典》中的mythology词条作者说,直到18世纪,欧洲学人才区分fable和myth,或者说让fabula回到mythus的原义,看来没错。但他说这是哥廷根大学的古典学家赫伊涅(C. C. Heyne,1729—1812)建立Mythologie(神话学)这门学科时(1760)的功绩,就未必准确了。
无论如何,至少在18世纪中期,欧洲文人已经意识到,虽然从形式上看,“寓言”与“神话”都是短小叙事,却有性质上的差异。17世纪以来,写“寓言”的欧洲文人从不乏人:从法兰西人拉·封丹(1621—1695)到德意志人莱辛(1729—1781)再到俄罗斯人克雷洛夫(1769—1844),欧洲各民族文学的兴起似乎都有“寓言”作家代表。但谁要写“神话”就很难行得通了,相反,解构“神话”的书写倒会有市场。
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中的“神话”词条篇幅并不长,就学术分量而言甚至不及钱伯斯《百科全书》中的fable词条。但作者关注古希腊“神话”与“纪事”(后来称为“史学”)的关系,给笔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作者在古希腊的思想语境中讨论这个问题——尤其提到普鲁塔克,可见这位作者的确眼力不凡。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第一卷在巴黎出版时,已经是著名文人的伏尔泰正旅居柏林的普鲁士宫廷,他深受鼓舞,并应邀参与了《百科全书》词条的撰写。随后伏尔泰又觉得,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构想过于宏大,而且卷帙浩繁,不便于读者随身携带阅读。于是,伏尔泰决意自己撰写一部简明扼要的启蒙辞书,名为《袖珍哲学辞典》(1764)。伏尔泰去世后,这部《袖珍哲学辞典》与他为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和《法兰西学院辞典》撰写的词条合并在一起,以《哲学辞典》(Dictionnairephilosophique)为名作为《全集》第一卷出版(共613个词条,四卷本,中译本选译不到100个词条)(伏尔泰,1991/2009)。
这部《哲学辞典》中有Fable(寓言和传说)词条,伏尔泰(1991/2009:498)在词条一开始就说:
通常认为是出自伊索手笔的那类寓言和传说,其实年代比伊索更远,而且似乎确是亚洲最初被征服的民族创作的。自由的人们倒不一定经常需要隐匿真情实意,不过,对一位暴君说话。却只能借用比喻,即便这样转弯抹角,也还有伴君如伴虎之险。
伏尔泰毕竟是伏尔泰,撰写词典这样的大事也做得来不同凡响。与钱伯斯的同名词条对比,伏尔泰明显不像个学者。但他把“寓言”说成政治作品,应该说不乏见地,可紧接着又对“寓言”作了完全相反的解释(伏尔泰,1991/2009:498):
由于人们总爱听隐喻之谈和故事,也很可能是有才气的人们为了解闷编点儿故事给人们听,并没有别的意思。不管怎样,人类天性即是这样,寓言和传说比历史记载的年代就更悠远了。
与培尔的辞典对观,我们不难看出,伏尔泰的辞典写法与培尔的风格一脉相承(Mason,1963)。此外,伏尔泰把寓言与传说混为一谈,强调这类叙事与“历史记载”的差异,以及哲人不相信寓言和传说等等,凡此看起来都像是在说“神话”。伏尔泰并没有区分“寓言”和“神话”,这证明了fable与myth的区分在18世纪的确还仅仅是开始。
4 古希腊“神话”的人类学解释
《牛津古典词典》中的mythology词条作者说,古希腊神话的现代研究始于18世纪的法国,但研究重镇很快转移到德意志学界,那里有更多古典语文学家。上文提到的赫伊涅被视为如今所谓“神话学”理论的创始人,他提出的观点与伏尔泰的说法刚好相反:任何民族的“神话”都是这个民族的早年经历的记录,以至于可以说神话即最早的历史记载。
这位词条作者谈到了古希腊神话的一大特点:荷马和古风时代的诗人虽然传承了大量“神话”,但他们也试图抹掉其中荒诞不经的细节。换言之,古希腊诗人喜欢改写口传的神话传说,这无异于以重构神话的方式改写传统神话。词条还提道,由于古希腊诗人习惯于凭传说中的“神话”编织新的叙事,引发探究自然的爱智者(哲学家)和热衷历史的纪事家不满。但这些新知识人一方面批评诗人凭“神话”传说“说谎”;另一方面他们又以自己的方式重述“神话”,从而开启了对待神话的所谓“理性化”态度。在这位词条作者看来,18世纪中期兴起的现代神话学接续的是这种早在古希腊雅典时代就已经出现的“理性化”趋向。但是,19世纪晚期以来,欧洲学界的现代神话学又经历了一次重大发展,即用人类学的民俗宗教论来看待所有能收集到的古老神话。事实上,《牛津古典词典》的mythology词条本身就带有浓重的人类学神话理论色彩:词条收尾时提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布克特注重神话的解释性功能和规范性功能的“仪式”研究,言下之意,它代表了人类学神话理论的最近进展。
严格来讲,现代神话学的人类学取向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代已见端倪: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中的mythology词条作者一开始就说,“神话”无不属于“异教”(pagan religion),伏尔泰的fable词条甚至把《旧约》的纪事书(有别于“律法书”的“历史书”)也视为“神话”传说。维柯的《新科学》虽然在18世纪没有产生影响,但他无疑是人类学式神话理论的伟大先驱(比较沃格林,2019:127-136)。
所谓“异教”(paganism)是一个典型的基督教欧洲的语汇,指与基督教相异的宗教。基督教的“传说”不能称为“神话”:“把耶稣复活称作神话,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粗暴的侮辱。”(杭柯,2006:54;比较罗杰森,2006:77-88)换言之,现代神话学在欧洲的兴起与基督教欧洲的“去基督教化”有内在关联。
18世纪以来的现代神话学绝非仅仅关注古希腊的神话传说,而是把世界上所有能找到的古老传说都纳入神话研究范畴。由此便出现了一个问题:古希腊神话与所有其他民族的古老传说都不同,没有哪个民族的古老神话像古希腊神话那样曾在西方文明内部引发思想争端,并因此而葆有持久的生命力——既然如此,人类学化的民俗理论能让人们深切理解古希腊神话吗?事实上,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经不断有研究古希腊神话的学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柯克,2017;韦纳,2014;费希,2017)。
由此看来,《牛津古典词典》的mythology词条几乎完全从人类学理论的角度来描述古希腊神话,结尾时甚至说人类学神话理论的新进展再度复兴了古希腊神话的研究旨趣,难免有些滑稽。如今我们若要像古希腊人理解自己的神话那样理解古希腊神话,就得走回头路。即便是狄德罗《百科全书》中的mythology词条,更不用说钱伯斯《百科全书》中的fable词条,都要比20世纪《牛津古典词典》的mythology词条更让人接近古希腊神话。
我们能否以古典方式编写古希腊“神话”词条呢?笔者不揣冒昧,不妨就来尝试一下。
5 古典式的古希腊“神话”词条
如果把神话与另一类叙事[history(探究)]作对比,神话的特征就清楚了。从叙事形式上讲,神话和纪事差别不大,都属于散文体,区别在于:纪事讲述实际发生过的事情,神话讲述编说的事情。
古希腊的神们是个关系复杂的大家族,内部充满争斗,宛如另一个世间。用现在的时髦学科术语来说,古希腊“神话系统”集宗教、文学、哲学、历史、自然科学(天象学、植物学)等学科知识于一身(因此,无论从现在的哪门人文-社会学科角度来研究古希腊的“神话系统”,都会不乏兴味),但对古代希腊人而言,这一“神话系统”却是其“生活方式”及其政制的基础。
5.1古希腊神话的“原典”
神话起初都是口传,要成为“经书”还得由这个民族杰出的诗人形诸文字。
古希腊神话的“原典”在哪里?坊间有不少“古希腊神话”之类的书,20世纪60年代我国就流行过一部翻译过来的名著《古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我们以为这就是古希腊神话的“原作”,结果往往对古希腊的“神谱”越看越糊涂。后来才知道,《古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一类的书,其实是赝品,即把“原作”中讲的故事搞类编。这类赝品作法早在古代希腊晚期就有了,但大多佚失,《阿波罗多洛斯书藏》是唯一留存者(1)N. Festa编,Mythographi Graeci,Leipzig,1902;R. Wagner编,Mythographi Graeci,Leipzig,1926;F. Jacoby编,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Leiden,1957;R. L. Fowler,Early Greek Mythography,Oxford,2000。今人编的古希腊神话故事一类,除了看着玩没什么用。比较汉密尔顿,《神话:希腊、罗马及北欧的神话故事和英雄传说》,刘一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做古典研究,最有帮助的是神话词典。这方面的词典很多,最好的当推Benjamin Hederrich编,Gründliches mythologisches Lexicon,Darmstadt,1996,有1251页。汉译文献有鲍特文尼克等编,《神话词典》,黄鸿森、温乃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晏立农、马淑琴编,《古希腊罗马神话鉴赏辞典》,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研究文献:赫丽生,《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谢世坚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古典时代的希腊文人往往只是简单地提到某个神话的片断,很少完整地讲述一个神话。要直接了解古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得读真正的原著——荷马的两部史诗、赫西俄德的《神谱》,它们分别代表了古希腊神话的两大源头性原典。在希腊的古风时期,记叙神话(或者说采用神话口传来写作)的诗人可能还有不少,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流传下来而已——“俄耳甫斯诗教”就是一个例证。俄耳甫斯与荷马、赫西俄德一样,首先是个会作歌(诗)的歌手,由于其作品没有流传下来,后人无从着手研究,其名声远不如荷马和赫西俄德。不过,俄耳甫斯的“身位”并不亚于荷马和赫西俄德,因为他后来成了一种神秘宗教的神主,被信徒们秘密敬拜。倘若读肃剧诗人和柏拉图的作品,我们会有这样的印象:荷马、赫西俄德的诗教是政制性的宗教,俄耳甫斯秘教则似乎像是如今所谓的“民间”宗教(与狄俄尼索斯酒神崇拜有密切关系绝非偶然),在当时已经相当有影响。无论如何,要完整了解古希腊的宗教生活(政制)秩序,必须了解俄耳甫斯教的原典(政制和宗教不可分、经典和神话不可分)。但既然是民间性且秘传的宗教,原始文献在历史中大量失传是可想而知的事情。关于俄耳甫斯及其教义,如今能看到的仅是古人闲说时留下的“辑语”(能见到的唯一原始文献,也许是“德维尼斯抄件”)。但从希腊化时期的一部“祷歌集”中可以看到,俄耳甫斯诗教也提供了一个与赫西俄德的神谱系统有别的神谱(吴雅凌,2006a,2006b)。
5.2神话中的主角
顾名思义,神话说的就是“神们”的事情。其实,这种理解大有问题。应该说,古希腊神话中的主角有三族:诸神、英雄们和怪兽们。因此,荷马的诗作和赫西俄德的诗作也会被算作“神话”。


在柏拉图的《会饮》中,这段神话中的英雄故事是这样传衍的:

再说,唯有相爱的人才肯替对方去死,不仅男人这样,女人也如此。珀利阿斯的女儿阿尔刻斯提向(我们)希腊人充分证明,这种说法是真的:只有阿尔刻斯提肯替自己的丈夫去死,虽然她丈夫有父有母,她对丈夫的情爱却超过了父母对儿子的疼爱。
据柏拉图笔下的普罗塔戈拉说,古希腊的智者喜欢讲神话其实有政治上的原因。在《普罗塔戈拉》中,他说:

[316c6]毕竟,一个异乡的人物,在各大城邦转,说服那儿最优秀的青年们离开与别人在一起——无论熟悉的人还是陌生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来跟他在一起,为的是他们靠与他在一起[316d]将会成为更好的人——做这种事情必须得小心谨慎。毕竟,这些事情会招惹不少的妒忌,以及其他敌意乃至算计。

[316d3]要我说啊,智术的技艺其实古已有之,古人中搞[d5]这技艺的人由于恐惧招惹敌意,就搞掩饰来掩盖,有些搞诗歌,比如荷马、赫西俄德、西蒙尼德斯,另一些则搞秘仪和神谕歌谣,比如那些在俄耳甫斯和缪塞俄斯周围的人。我发现,有些甚至搞健身术,……
这无异于说,神话叙述是一种伪装或政治保护色。倘若如此,现代哲人说在古希腊思想中有一个从神话到逻各斯的发展过程,其实没这回事。要说神话与哲学有冲突,倒是真的(Buxton,1999)。
5.3哲学与神话的冲突
神话所讲的东西真实吗?从启蒙后的哲学理性来看,当然不是。如今,我们觉得神话都是迷信“传说”,听着好玩而已。不过,这种对“神话”的“理性批判”不是现代启蒙运动以后才有的事情。早在古希腊时就有人说,神话是“不真实的故事”——谁说的呢?哲人。看来,神话问题和诗与哲学之争在某种程度上叠合。哲人说,神话是诗人编造的,诗人就是“说谎者”:荷马或赫西俄德被指责为说谎者,就因为他们的叙事作品中大量关于神们的叙事。从这一意义上讲,荷马和赫西俄德的作品是神话诗,与后来的神话(故事)在形式上不同(韵文与散文的区别),实质上相同。

不过,我觉得,传说中说的所有事情都发生过——因为,倘若仅有(名称)叫法,关于它们的传说也就不会出现了。毋宁说,肯定先有事情发生了,才会出现某种关于它的传说。

比如,神话中说,俄耳甫斯的琴声感动兽石,帕莱普法托斯说(《不可信的故事》,33):

关于俄耳甫斯的神话也是谎话,(说什么)他弹奏竖琴时,四脚动物、爬行动物、鸟儿、树木都跟着(动)。
俄耳甫斯的琴声具有感动的力量是真实的,但他的琴声感动的是人——秘教信徒们。这些信徒做崇拜时身着兽皮,或者扮成顽石样,手拿树枝。于是,传说就讲,俄耳甫斯的琴声感动了野兽、石头和树木,其实感动的是人而已。
帕莱普法托斯的《不可信的故事》文笔清新、简洁,在希腊化时期算流传甚广的名著,在拜占庭的基督教世界,也许由于旨在揭穿“异教神话”的“假象”,《不可信的故事》一直是学校的教科书,直到10世纪还如此。后来在战乱中散佚,中古后期由僧侣学者根据找到的各种抄件重新拼接。1505年,西方学者再度引进,17世纪以来,成为学校的希腊文课本。后来由于古典学大师维拉莫维茨说了一句:这是一本“可耻的搞事之作”(das elende Machwerk),读它“完全是浪费精力”,此书从此沉寂(3)J. Stern编辑、笺注的希腊文本Palaephatus On unbelievable Tales,B. G.Teubner,1902,英译、注疏、导论版Wauconda,1996;Kai Brodersen德译、简注本,Die Wahrheit über die griechischen Mythen. Palaiphatos’ Unglaubliche Geschichten,希-德对照,Stuttgart,2002。。

欧赫墨儒斯身处亚历山大大帝建立帝国的时代,他的目的也许是为了维护古老的诸神信仰,让铭文成为证明古希腊史诗和抒情诗中的天神的所谓“史料”。古罗马诗人恩尼乌斯(Ennius)曾将其译成拉丁文,相比也是为了教育罗马人。然而,这些铭文也证明,远古神话中的天神不过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并非真的是天神。于是,“欧赫墨儒斯式的说法”(Euherism)被用来比喻一种双刃剑式的说法:史料既可被用来证明也可被用来解构古代神话。
5.4古希腊神话的现代处境
关于古希腊神话在20世纪的基本处境,我们需要知道三件要事。第一,在现代启蒙理性的支配下,不少西方学者(包括大名鼎鼎的古典语文学家)编造并维持着这样一个说法:古希腊思想经历了从神话到哲学的进步。按照这样的观点,苏格拉底还在讲神话,岂不表明哲学在苏格拉底思维那里还没有成熟?第二,19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出现了大量对神话的历史主义或实证主义的研究,结构主义神话学是这类研究的最高、最成体系的成就,让人以为古代神话变得很红火。其实,结构主义对神话的解释仍然是启蒙哲学式的所谓理知性的和历史的解释,不同之处在于解析神话的知识工具(结构主义语言学)。说到底,这类神话解析无异于解构神话——通过解读神话,人类学家要得到的是历史-社会的知识。第三,19世纪以来的西方神话学跨越了古希腊神话的传统范围,向其他民族的神话推进。由此出现了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古希腊神话与其他民族的神话有何差异。
不用说,古希腊神话与西方大传统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在古希腊文教制度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但在其他民族的文明制度中,却并非如此。比如,非洲的某个部落流传的神话与文明大传统没有关系。又比如说,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神话(《山海经》)并不重要,屈赋中的神话已经被融入儒家体系(4)韦尔南,《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杜小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弗兰克,《浪漫派的将来之神:新神话学十一讲》,李双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布鲁门伯格,《神话研究》,胡继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朝戈金编,《神话学导论》,田立年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的人类学式神话学也被我国学者用于解析中国古代的神话诗文。比较苏雪林,《屈原与〈九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5.5柏拉图笔下的神话
柏拉图作品中出现了不少神话,这是对所谓古希腊思想从神话发展到逻各斯这一现代哲学观点的有力反驳。现代哲学的观点让我们不会去想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柏拉图明明知道神话是不真实的说法,为什么他笔下的苏格拉底还要讲那么多神话。
我们需要注意到,所谓神话不真实的说法其实有两种:一种是自然哲人的看法,凡神话都不真实(比如克塞诺梵娜说,荷马、赫西俄德讲的都不真实);另一种是神话诗人之间的纷争。比如,赫西俄德说荷马写的东西不真实,但赫西俄德自己也写神话。后一种说法并未否认神话本身可以讲述真实,赫西俄德争辩的是,谁讲的神话更真实。柏拉图笔下的所谓神话不真实的说法,属于后一类情形——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在《王制》(卷二378d-e)中一方面攻击神话(诗),说神话大都是讲给孩童听的,而孩童无法领会其中譬喻;另一方面又推崇荷马的“谎谝术”。在《斐德若》中,有这样一个著名段落(229c4-230a7),说到神话的“真实”问题:

斐德若:不过,向宙斯发誓,苏格拉底,你信服这神话传说是真的?

苏格拉底:我要是不相信,像那些聪明人那样,恐怕也算不上稀奇(出格)……


如果谁要是对其中的哪个不那么信,要探个真相出来,就得用他那实在粗糙的智能在这事儿上白白搭上好多清闲时间。
柏拉图的作品总体上说是对话体,仍然带有很强的叙述性。这不仅指表演性对话与叙述性对话的区分,重要的是,柏拉图的对话作品中有好些非常著名的神话叙事(《蒂迈欧》整体上讲就是个大神话)。这些神话不仅对理解柏拉图作品的意图相当关键,对理解整个西方思想的根本问题同样重要,近半个世纪以来、尤其近20年来,柏拉图研究成了热门。据说,柏拉图作品中的神话叙事可分为两个大的类型:谱系神话和终末神话。前者主要涉及世界、人和神的诞生,或追溯认知的渊源,后者体现灵魂的最终命运及其重生(马特,2008;张文涛,2010;Brisson,1998)。
在古希腊文学传统中,神话非常常见,写神话的并非只有柏拉图,柏拉图的神话与其他作家的神话有何不同?施特劳斯告诉我们:要把握柏拉图对神话的独特理解,得看他如何用神话。施特劳斯的分析慧眼独到:在柏拉图笔下,神话并非一定是叙事,也可能是论说(逻各斯)——换言之,“神话”具有逻各斯的性质。


尽管你兴许会视为神话,我却会视为逻各斯(论说),因为,我将把我打算讲述的东西作为真实讲给你听。
反过来,论说也未必一定是在讲真实,《普罗塔戈拉》中的普罗塔戈拉就把自己的一段论证(323a8-324d1)叫作“神话”。换言之,论证也可以是哄人的东西。这样一来,神话(讲故事)与论说在传统上的形式区分在柏拉图笔下就彻底模糊了。神话或论说究竟是神话抑或论证,不能看形式上是叙事还是论述,得看说话的人自己把神话或论证视为什么。
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讲神话最多。接下来的问题就成了: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如何理解或运用神话。苏格拉底在《斐多》(61b4)中说:
苏格拉底讲的神话故事大多是在说理(逻各斯),于是,神话与逻各斯的传统区分就被苏格拉底取消了。最著名的例子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的老师第俄提玛讲的爱若斯的诞生故事,从形式上看当然是神话,但苏格拉底没有说他的老师讲的是神话,从而,这段爱若斯的诞生故事是逻各斯。故事有情节,是虚构的,悦耳动听,但在苏格拉底看来,也可以是论说,采用故事的形式不过在于让人明白易懂——这对我们有很大启发:说理的论说并非一定是抽象、思辨的方式。
在柏拉图笔下,神话与逻各斯完全没有区分吗?也不是。在柏拉图那里,神话与逻各斯的差异首先在于:神话没有证明,因此不是知识。知识需要证明,证明为的是清楚展示。神话不是知识,表明神话涉及的事情无法证明,或者说人类对这些事情的分解至少非常困难。
我们无法或很难获得知识的事情有哪些?第一,非常远古的事情,对此我们迄今能够得到的仅是一些骨头化石。在《法义》和《治邦者》中,苏格拉底所讲的神话就涉及这些事情,而且明确说是在讲神话。第二,天体内部的东西也不可知,尽管今人对天体比柏拉图的时代知道得更多些,仍然非常有限——大地内部的东西同样如此。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对这两个领域的说法都是神话:《斐多》最后的“大地”神话和《王制》卷十中的厄尔神话,以及整个《蒂迈欧》都是这类神话。

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灵魂中的东西往往没法说出来。因此,并非说出已经知道的东西才算严格意义上的真实,有些真实我们知道得并不清楚——比如灵魂的真实;说出我们知道得并不清楚或者没法完全说清楚的真实,同样是在言说真实,这种言说就是神话,与自然的真实(无论远古的事情还是天体和地怀的本相)无关——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以及如今的哲学看待神话的观点用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的神话,是无效的。反过来说,问题的实质在于对灵魂真实的解释权:自然哲人力图提出一套有别于诗人的对灵魂的观照(比较亚里士多德《论灵魂》)。
解读柏拉图作品中的神话,首先得留意两个因素:第一,出现在哪篇对话中(及其具体位置);第二,由作品中的哪个人物讲述。
5.6神话与寓意文学


路吉阿诺斯的《真实的故事》中有个关于人变成驴的伤感故事,堪称后来西方一系列变形记小说(直到卡夫卡的《变形记》)的源头。在小说中,路吉阿诺斯让一个名叫Lukios的青年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显然是要加强故事的真实感。


为了顾及中译的行文流畅,可采用不是那么严格的意译:
我急匆匆脱下衣服,给自己全身涂油,我却没变成一只鸟,我这个倒霉的家伙,从我后背竟然长出一条尾巴,手指都消失掉,不知道到哪儿去啦,指甲却还剩四个倒正像蹄子,手脚都变成一头牲畜的脚,耳朵长、脸盘子大。我一打量自己,看到的竟是一头驴!
与路吉阿诺斯差不多同时代的阿普莱乌斯(Apuleius),大约公元123年出生在如今的非洲北部,先在迦太基学习修辞术,大约在150年左右来到雅典,进了柏拉图学院学哲学。后来,阿普莱乌斯成了中期柏拉图信徒中当时所谓的Gaius派的一员,写过不少哲学书。正是这位阿普莱乌斯用拉丁文写作把路吉阿诺斯笔下的Lukios讲的变驴故事发展成一部更大篇幅的小说《变形记》(Metamorphoses,中译本《金驴记》)。这部关于一头驴子的十卷本小说杂糅形色各异的叙事,其中有著名的amor(心)与psyche(魂)的神话。由于语文上的精美,这部小说成了拉丁语修辞学范本。但阿普莱乌斯是柏拉图学派中人,他的Metamorphoses(变形记)绝不会是写着玩儿而已。
上面那段路吉阿诺斯的描写,在阿普莱乌斯笔下发展成这样:
……我赶快扔掉所有的破布,贪婪地把双手伸进油膏里,狠狠捞出来一大把,用它把全身使劲地擦了一遍——我这方面已经作了尝试,用双臂做平衡,像鸟一样动作——但既没长出小绒毛,也没长出小羽毛,都没有,我的头发浓密得成了鬃毛,而我细腻的皮肤硬得像皮革,在我漂亮小手的尖尖结成一单个蹄子,手指的总数也不对了,且在我脊柱的末梢还长出一条粗壮的尾巴。我的五官全乱了套,嘴巴突出,鼻孔张裂,上唇啪嗒啪嗒滴口水,耳朵毫无节制地疯长,在这场恼人的变形中,Photis再不能留着我了,但我的小鸡鸡(Penis)也开始长起来,唯有这一点让我欣慰。我现在无法挽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我偶然地看了一下,发现自己没变成鸟,却变成了一头驴(我已经不能说话,去Photis身边诉苦了)。
与希腊文蓝本比较可以看到,阿普莱乌斯的修辞花哨得多。但倘若考虑到,阿普莱乌斯所属的柏拉图学派特别对所谓“影子”与“实体”的关系感兴趣,我们就不应以为他是在追求荒诞无稽的效果。细读阿普莱乌斯的《变形记》,我们可以从他跳跃式更替的语言风格中看到温柔的爱欲与暴力犯罪、强盗传奇与浪漫温情的精妙融合:在夜晚的篝火旁,一个醉醺醺的强盗祖母讲了amor和psyche的神话,以此安慰劫持来的一位少女。Lukios凄惨的变形故事只是个框架,在自由的精神与可怕现实之间起到某种连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