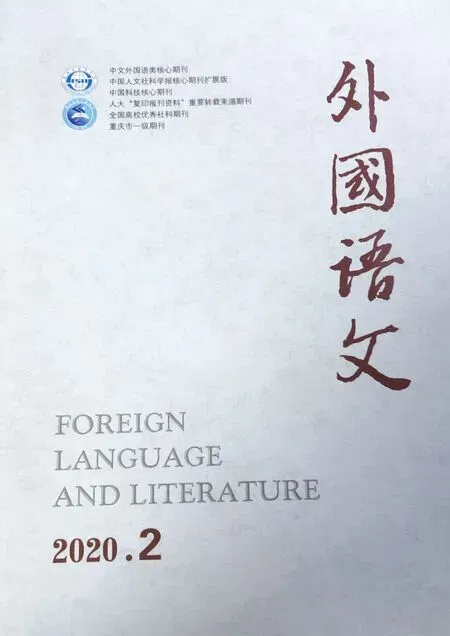从功能语篇分析到翻译研究
——以艾米莉·狄金森的“I'm Nobody”为例
陈旸 王烯
(1.华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0;2.北京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83)
0 对等问题
关于对等,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讨论。其类型可以有形式对等、功能对等、动态对等或其他对等;对等与“对应”(correspondence)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在我国过去几十年的翻译研究文献中,只要谈到对等问题,几乎都要说到奈达(Nida, 1975; Nida et al, 1969)所提出的功能对等概念。但是,本文认同黄国文、陈旸(2014)的观点,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中探讨翻译的对等问题。韩礼德(Halliday,1956、1961)的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研究影响很大,早在1965年出版的题为《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中,卡特福特(Catford,1965: 290)就运用Halliday的阶与范畴语法框架对翻译的对等问题进行了语言学探索,并对“语篇对等”(textual equivalence)和“形式对应”(formal correspondence)等重要概念进行了区分。我们认为,从元功能角度探讨翻译的对等问题,会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
本文根据黄国文、陈旸(2014)的区分,在“元功能对等”(metafunctional equivalence)的定义和框架中,认为经验功能对等是最重要的;评判译文是否与原文对等,主要是看它们是否在经验功能方面对等。本文以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我是无名之辈》(“I'm Nobody”)一诗为例,讨论该诗汉译涉及的一些问题。
1 解读
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镇一个律师家庭,青少年时代受过正规宗教教育,但其生活单调,平静,孤独,从25岁开始弃绝社交,闭门不出,过着女尼般的生活;30年中完成了1700多首诗稿,但生前只发表了七首,其中 《我是无名之辈》即其代表作之一。狄金森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造成了她的生活态度:与世无争,与人无仇,冷眼看世事,并写出了多篇体现这种人生态度的诗篇,《我是无名之辈》就是其中之一。
《我是无名之辈》是一首散文诗(a lyric poem),有不同的版本,其中一些的标题是“I'm Nobody! Who are you?”下面我们以“Poem of Quotes”网站所提供的原文作为分析的例子:
I'mNobody!WhoareYou?
By Emily Dickinson
I'm nobody! Who are you?
Are you nobody, too?
Then there's a pair of us—don't tell!
They'd banish us, you know.
How dreary to be somebody!
How public, like a frog
To tell your name the livelong day
To an admiring bog!
上面这首诗的正文有两节,每节四行。在其他一些版本中,诗的形式有些变化,下面是“poets.org”网站上刊登的版本,其中正文第二、第四、第五、第六和第七行都用了破折号。为了节省篇幅,下面用双斜线把诗的标题和正文的两节隔开,用单斜线把各行隔开。I'm Nobody! Who are you? ∥ I'm Nobody! Who are you? / Are you-Nobody-too? / Then there's a pair of us! / Don't tell! they'd advertise-you know! ∥ How dreary-to be-Somebody! / How public-like a Frog-/ To tell one's name-the livelong June-/ To an admiring Bog! 此外,第四行的“they”第一个字母没有大写,并用了“advertise”(而不是“banish”),第七行的最后一个单词是“June”(而不是“day”)。
这首诗有很多汉译版本。刘宝权(2000)举了其中四个版本,我们下面以汪义群的译本(刘宝,2000:58)作为样板(为了节省篇幅,∥表示节界,/表示行界):我是无名之辈,你是谁? / 你也是无名之辈? / 那么,咱俩是一对——且莫声张! / 你懂嘛,他们容不得咱俩。∥ 做个名人多无聊! / 像青蛙——到处招摇—— / 向一洼仰慕的泥塘 / 把自己的大名整天宣扬!
关于这首诗所表达的意义,基本的含意是:诗人离群索居,与世无仇,甘为隐士,淡泊名利。因此,这首诗也讽刺那些不惜陷身泥淖而自夸之辈。罗军和辛苗(2013: 103)认为,这首诗的语言及其语气和意蕴都体现了诗人从人世间的诸多纷扰、人际关系中的争斗以及人们在名利场上对名和利的角逐等问题的哲学思考,并试图从“与世无争的情怀”“与人无争情感”“与名无争情致”和“与利无争的情操”四个方面考察诗人的厌世主义哲学观。
2 分析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Halliday,1994; Halliday et al,2014,;Thompson,2014)中,有一个元功能假设,就是每个小句都可以从概念功能(由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构成)、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进行分析。这三个元功能注重的是小句的不同特性。
先说概念功能。概念功能中的经验功能主要的考察点是及物性分析,具体说来就是过程类型。原文有九个小句,体现九个过程,其中关系过程三个(第一和第二行:am、are和are),存在过程一个(第三行:is),言语过程一个(第三行:tell),物质过程一个(第四行:banish),心理过程一个(第四行:know);有两个过程没有通过词汇语法来体现,即第五行中的“(it) is”(关系过程)和第六行中的“(it) is”(关系过程)。
正文七个句子只有两个是小句复合体(Then there's a pair of us—don't tell! / They'd banish us, you know.)。就逻辑功能而言,第一个小句复合体中的两个小句是并列-延伸关系,第二个小句复合体中的两个小句则是从属-增强关系,因为“you know”表达的意义相当于“as you know”。
人际功能主要涉及语气和情态意义。就语气而言,正文七个句子中,三个是陈述句(I'm nobody! / Then there's a pair of us—don't tell! / They'd banish us, you know.),两个是疑问句(Who are you? / Are you nobody, too?),两个是感叹句(How dreary to be somebody! / How public, like a frog / To tell your name the livelong day / To an admiring bog!)。在“They'd banish us”中,“ 'd (would)”表示的是一种推测意义,而两个感叹句也表示人际(感叹)意义。
与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不同,语篇功能涉及的是主位结构和衔接关系。诗歌正文中的七个句子的主位分别是:I、Who、 Are you、 Then there、 They、 How dreary和How public。从衔接关系说,这首诗的突出之处是照应关系:I指说话人,you指听话人,they指第三方,us指说话人和听话人。第三行的主位结构中的主位(Then there)是个“复项主位”(multiple Theme),其中“then”是语篇主位,“there”是话题主位(尽管它不是经验成分)。
就原文和译文的元功能对等而言,以汪义群的译本(刘宝权,2000:58)为例,经验功能是对等的,人际功能是对等的,语篇功能基本也是对等的。但是,虽然原文和译文在元功能方面是对等的,但从功能语篇分析角度看,还是有些问题需要讨论的。
3 讨论
就元功能对等而言,《我是无名之辈》的原文和译文(以汪义群的译本为例)是对等的,或基本对等的,但有三个问题值得讨论:(1)话语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2)元功能分析与意义的解释;(3)关于这首诗中“nobody”和“somebody”的翻译问题。
3.1 话语的主体与客体
这首诗中的我可以是现实中的“我”(第一人称单数、讲话人和诗人),也可以是虚拟的“我”(即诗人创造出来的第一人称单数、虚拟话语中的讲话人),这是因为,话语是从“我”说起的。先说自己是什么(“我是无名之辈”),然后从讲话人说到听话人(“你是谁?”“你也是无名之辈?”),再讲到我和你的关系(“咱俩是一对”)。既然“咱俩”属于同一类人,那就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们容不得咱俩”。
关于讲话人与听话人的关系,可以这样来看。在“我”心中,“你”是跟我熟悉的人,我们的关系是亲密的,说话可以开门见山。因此,话语一开始就表明自己是什么人(“我是无名之辈”),然后就单刀直入地问对方是什么人(“你是谁?”),也不用等对方回答,讲话人就用肯定的口气(通过too的使用)设问,“你也是无名之辈?”然后马上就通过“那么”(then)来支持自己的判断。
既然讲话人和听话人属于同类人,所以关系就自然亲密了。这就形成了“我们”(us)与“他们”(they)的对立(They'd banish us)。既然我们是同一拨人,那我们就有共知信息,很多话“我”不用说“你”也会明白(you know)。
诗中所展现的“我们”与“他们”是对立的。既然我们认为自己是无名之辈(nobody),那与我们对立的“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会排挤我们(They'd banish us),因为我们跟他们不是同一类人:他们想做“名人”(somebody),“到处招摇”(public),“把自己的大名整天宣扬”(to tell your name the livelong day)。
从整首诗看,讲话人是话语的主动发起者,他(她)认为听话人与他是属于同一类人,他们在一起,与那些想做出风头、想做名人、看不起无名之辈到处张扬招摇的人是对立的。在“我”看来,他们是无聊的,像青蛙那样,守候一片泥塘,炫耀自己的名字。
3.2 元功能分析与意义的解释
上面我们从元功能的角度对整首诗进行分析。整首诗的正文有九个过程类型,其中两个是没有通过动词体现出来,即是隐性的:

过程类型显性隐性关系32存在1--言语1--物质1--心理1--
就过程类型所反映的现实事件而言,可以区分出“动作的”和“非动作的”。虽然关系过程、存在过程、言语过程和心理过程是有明显区别的(Halliday,2004; Halliday et al,2014,;Thompson,2014),但从“动作性”角度看,它们都属于对非动作的事件的描述。九个过程中只有一个是讲将来可能会发生的动作;之所以说是“将来”“可能会”,是因为这个物质过程通过含有情态词“'d”(would)的动词词组('d banish)体现。这就是说,从经验功能看,整首诗都是在“纸上谈兵”,或者“异想天开”,只有想法、言语和状态,没有动作。
我们不妨用狄金森的另一首诗(A Bird Came Down the Walk)来做比较,该诗共由五节(每节四行)构成(为了节省篇幅,∥表示节界,/表示行界): A Bird came down the Walk— / He did not know I saw—/ He bit an Angle Worm in halves / And ate the fellow, raw, ∥ And then, he drank a Dew / From a convenient Grass—/ And then hopped sidewise to the Wall / To let a Beetle pass—∥ He glanced with rapid eyes / That hurried all abroad—/ They looked like frightened Beads, I thought, / He stirred his Velvet Head.—∥ Like one in danger, Cautious, / I offered him a Crumb, / And he unrolled his feathers, / And rowed him softer Home—∥ Than Oars divide the Ocean, / Too silver for a seam, / Or Butterflies, off Banks of Noon, / Leap, plashless as they swim. 在这首诗中,大多数过程都是物质过程(如came、bit、ate、drank、 hopped、hurried、stirred、offered unrolled、rowed、leap和swim)。很明显,这首诗讲的是一直小鸟在某个时间段的动作(活动),这里是以动作的描述为主(黄国文 等,2017),而不像本文所分析的这首《我是无名之辈》。
《我是无名之辈》所选择的是非动作过程,展示的是一种只注重思考不主动行为的精神状态;从某种程度上讲,诗人(或“我”)只对跟自己亲密的人(或“你”)说说自己的一种看法和感慨,没有改变状况的想法,更没有行动。
从人际功能的分析看,“我”与“你”的关系是亲密的,之间是相互比较了解的;由于讲话人与听话人的这种关系,在语言的体现上就是用缩略式(I'm、there's、don't和They'd)。这样的表述显示了亲密关系和非正式的说话方式。同时,作者在陈述句和祈使句中用了感叹号(I'm nobody!、don't tell!)也表明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因为对熟悉的人说话,就可以直来直去,也可以流露真实情感。另一方面,诗中另外两个感叹句(How dreary to be somebody! / How public, like a frog / To tell your name the livelong day / To an admiring bog!)则表明了“我”对“他们”行为的感叹和不屑。情态词“'d”(would)的使用表明了“我”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的不确定性。
就语篇功能的主位结构而言,话语的起点从“我”,然后到“你”,最后到“他们”。讲话人“我”是话语的主体,是话题的发起人,也是对事情做出评判的人。尤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诗的第三行“then”的使用,它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既然“你”“我”都是无名之辈,那咱俩就是一对了。
3.3 关于这首诗中“nobody”和“somebody”的翻译
关于这首诗歌的翻译,已有人(刘宝权,2000)做了比较。我们认为,从功能语篇分析的角度看,对诗歌的翻译,首先是译者对原文的元功能分析和理解的把握。翻译不仅仅要译意,而且还要译味(黄国文 ,2015)。
就译意而言,“nobody”可以有多种译法。刘宝权(2000:59)提供了下面三种译法,并进行了评论:无名之辈(汪义群)、无名辈(毕欲)和小东西(木宇、关天稀)。他评论说,“小东西”不宜入诗,而且也不能表达作者想作为一个平常人的心理,“‘无名辈’与‘无名之辈’相比,后者在汉语中有这样的成语,而且听起来也比较顺畅”。基于这样的原因,刘宝权也把“nobody”译为“无名之辈”。我们在网络上还看到有人把这首诗中的“nobody”翻译为“无名小卒”;还有人把“I'm nobody”翻译成“我啥都不是”。
与“nobody”形成对比的是“somebody”,现有的译本有的译为“大人物”,有的译为“名人”,还有人把它译为“人物”。刘宝权(2000: 59)认为,译成“大人物”与“无名之辈”相对应,译成“名人”则有点太正式。他认为译成“大人物”更合适,因为“在汉语中我们说某某人是个‘大人物’,不一定指‘名人’”。
其实,译意就是把意思翻译出来,译味就是把味道翻译出来。从功能语篇分析角度看,译意是经验功能所关注的,而译味则是人际功能所追求的(黄国文,2015)。因此,“nobody”和“somebody”译成什么,关键是译者想追求什么样的味道。
从经验功能对等看,无论“nobody”翻译成“无名之辈”(汪义群)、“无名辈”(毕欲)或“小东西”(木宇、关天稀),原文和译文是对等的。同样,把“I'm nobody”翻译成“我啥都不是”,在经验功能和语篇功能这两方面也是对等的。但是,就人际功能的对等看,“我是无名之辈”和“我啥都不是”都与原文不对等;前者比原文正式,后者又很不正式;就对等而言,原文位于两者之间。如果把“I'm nobody”翻译成“我是小人物”,就在三个元功能方面都比较对等。
4 结语
本文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框架中,采用功能语篇分析的方法,分析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我是无名之辈》一诗。通过元功能分析,对原文(原诗)及其汉译文进行观察、解读、描述、分析、解释和评估。本文还从元功能对等的角度说明经验功能对等的重要性,并指出翻译诗歌既要注重译意(经验功能),也要注重意味(人际功能)。本文的意义之一是展现功能语篇分析对诗歌翻译研究的可应用性和可操作性。
诗歌是文学作品的形式,对其解读是因人而异的,因此,一百个翻译者就有可能翻译出一百个版本。此外,采用不同的理论指导、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中,就会有不同的解读、描述、分析、解释和评估。如果我们接受诗歌可译的观点,那就要从不同的方面探讨诗歌的可译性。功能语篇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方法上的选择,事实也证明这种方法给我们的翻译研究带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