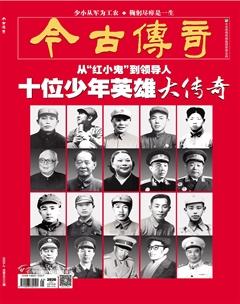康克清:15 岁参加革命 最高职务:全国政协副主席
刘欣 周玉莲 杨笑文


15岁时,康桂秀当选为区妇协宣传委员。1928年万安暴动失败后,养父怕康桂秀被敌人捉去杀头,不许她参加革命,盘算着把她嫁出去,当听说井冈山的红军要到罗塘湾来,就把她关在房子里。当康桂秀从窗户里看见灰军帽上绣着红五角星的士兵经过时,心不由得剧烈跳动起来,这不是日盼夜想的红军吗?康桂秀走上井冈山,改名康克清。康克清从来没有想到过她的一生会和这位伟人写到一起。红军从吉安出发至新余一带,转战赣南宁都、黄防等地,每天跋山涉水,长途行军七八十里,不少小伙子都吃不消了。康克清和战士们一样,自己背着军毯和雨伞,斜挎着干粮袋,腰间还挎着手枪和子弹,紧跟司令部后卫队,从不掉队。朱德知道后,既为她骄傲又为她担心。
17岁的童养媳康桂秀当上了女红军
1911年9月7日,康克清出生于江西赣江沿岸的一座普通小镇万安县罗塘湾,出生时,父母给她取名康桂秀。由于家境贫寒,无奈之下,出生才40天的康桂秀被送到一户叫罗奇圭的人家当童养媳。
康桂秀被送到罗奇圭家时,罗家的男孩刚夭折不久。按当地的风俗,康桂秀叫作“望郎媳”,就是要讨个吉利,等待第二个男孩出生。遗憾的是养母再没有生育。于是,康桂秀实际上成了罗家的养女。
养母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善良、勤劳、俭朴。在她的影响下,康桂秀小小年纪就能干懂事。康桂秀13岁那年,夏天久旱不雨,稻田裂开一道道口子,禾苗也晒蔫了,乡亲们都想方设法洒水浇田,想保住禾苗。可在这个节骨眼上,养父偏巧外出不在家。眼看稻子沒收成,明年全家人就要挨饿,养母急得哭了。康桂秀跑到邻村借来一架水车,母女俩一起上阵,不顾天热劳累,昼夜车水,终于把稻田都灌满了,禾苗又都抬起了头。慢慢地,村里人都知道罗奇圭家有个聪明能干的媳妇,附近一带没有哪一家的童养媳能比得上。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康桂秀无形中成了村里童养媳中的“头头”,偶尔她们发生了争吵,或是打起架来,康桂秀都耐心劝解她们。只要康桂秀一说话,她们都能听。于是,乡亲们把康桂秀称作“媳妇王”。
一天,康桂秀从外面干活回来,刚进家门,就见奶奶手里拿着一套裹脚用的东西,正在等她。
康桂秀大声对奶奶说:“我不裹脚!现在革命了,不兴裹脚。好好的一双脚,裹了怎么能劳动,怎么好走路?”
“养个大脚妹子,将来怎好出嫁?丢死人啦!”奶奶气得浑身发抖。
康桂秀还没见过奶奶气成这个样子,她担心会把奶奶气病,但又不能顺从这个安排。突然,她灵机一动,想了个好主意:“那好,要裹脚,从今以后,家里的水我不挑、柴我也不砍了。”
养母也帮康桂秀说话,因为她自己也是一双大脚。奶奶没办法,只好同意了康桂秀不裹脚的要求。
康桂秀高兴极了,她把自己反抗裹脚的办法告诉了小姐妹们,鼓励她们和父母作斗争,坚决不裹脚。姐妹们都照康桂秀的办法,用不挑水、不砍柴向父母抗议,家长们无可奈何,只好同意孩子们的要求。
1925年9月,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军沿赣江北上,一路势如破竹,把旧军阀的部队打得溃不成军。随着北伐军的不断胜利,罗塘湾的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群众组织,渐渐由秘密转向公开发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迅速在罗塘湾全面展开了。康桂秀在革命的洪流中接受了新思想,很快成长起来。
1926年初夏,聪明能干的康桂秀参加了村里共青团组织办的妇女训练班,不久,由团支部书记罗诗通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她除了干好家里的农活,空闲时间都用来开会、唱歌、演戏,她成了村里的“小忙人”。经过妇女训练班的学习,康桂秀被选为罗塘湾乡妇女协会的常任秘书(相当于现在的妇联主任)。她一面开展本乡的妇女工作,一面参加县里组织的巡视团,到各处去演讲宣传。
不久,康桂秀当选为区妇协宣传委员,她和男同志一样,不管酷暑寒冬,不管晴天雨天,戴着斗笠,率领妇女宣传队在罗塘湾一带发动积极分子,动员妇女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同时宣传禁止虐待妇女,禁止虐待童养媳,反对包办婚姻,提倡男女平等,宣传禁烟(鸦片烟)、禁赌,动员妇女放脚、剪发。
1928年万安暴动失败后,罗塘湾到处是白匪军和挨户团,他们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简直杀红了眼。养父罗奇圭怕康桂秀被敌人捉去杀头,便不许她参加革命,并盘算着把她嫁出去。农历七月底,养父听到消息说井冈山的红军要到罗塘湾来,怕康桂秀知道,就叫养母把她关在房子里,这反而引起了康桂秀的猜疑。当康桂秀从窗户里看见灰军帽上绣着红五角星的士兵经过时,心不由得剧烈跳动起来,这不是日盼夜想的红军吗?于是,她故意把鸡轰出门外,自己乘机上了街。
康桂秀一出去就遇见了本地共产党员柴苟,柴苟对她说:“赶快找妇女协会会员帮红军筹粮食做饭。”第二天,当地工农运动委员会领导刘光万通知康桂秀参加红军召集的本地党、团员积极分子大会。大会由何长工主持,陈毅讲话,当场发出号召:“老表乡亲们!欢迎大家参加红军,扩大我们工农红军!打倒蒋介石和地主老财,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然后指指身旁的刘光万和游必安说,谁要当红军都可以找他们两人报名。康桂秀找到刘光万,和6个小姐妹一起加入了红军万安游击队。
跟随队伍上了井冈山后不久,康桂秀加入了妇女组,她认识了曾志、贺子珍、伍若兰和吴仲廉等同志。妇女组的任务是做群众工作和宣传工作,筹粮、筹款,有时还帮助毛泽东去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每到一处,妇女组一住下来,就找群众谈话,了解当地的情况,还经常张贴朱德、毛泽东发布的布告,写大标语。康桂秀一边做这些工作,一边从布告上和大标语中学认生字,同时领会一些革命道理。
每天行军、工作都十分紧张,生活虽苦,却使康桂秀感到精神充实。不过,康桂秀对家里给起的这个名字,总感到太女孩子气,一直想改,却找不到合适的人商量。不久她又在吉安遇到刘光万,他听了康桂秀的想法,表示赞成,想了一下说:“你看叫康克勤怎么样?”一边说一边掏出一张纸写在上面,递给她看。康桂秀觉得他起的这个名字不错,也好听,只是勤字笔画多,写起来比较费事,又觉得一个人光是勤快还不够,还应当对自己要求高一点,就说:“把勤字改作清字吧,这样我写起来比较省事,而且还表示我要沿着一条清清楚楚的正确道路前进,你觉得怎样?”刘光万连连点头说:“好好好,以后你就改名叫康克清吧!”
18岁的她,不但是朱德的夫人,更是一名红军战士
康克清走上井冈山时,朱德的名字早已和毛泽东连在一起了。康克清从来没有想到过她的一生会和这位伟人写到一起。
康克清第一次见到朱德是在离开家乡向井冈山进发时。到达遂川,陈毅命令部队就地休息待命。几十名刚参军的万安年轻人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充满喜悦。过了不久,前面的人突然一排接着一排地站了起来,同时有人大声喊道:“朱德军长来了!”康克清起先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心想,那不就是传说中朱毛红军的革命领袖吗?她挤到前面,真的看见了和战士们走在一起的朱德,魁梧的体格,浓密的胡须,敞开的衣领,脚上穿着草鞋,身上满是风尘,显出长途跋涉的辛劳,全然没有想象中的神奇色彩,完全是个普通战士的形象。
这时,朱德走到万安农军前停了下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周,把举起的双手向下按了按,示意人们安静。然后,朱德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讲话了:“你们万安的同志吃了苦,受了国民党的压迫,死了好多人。我们这次来,救出了一部分同志,今后还要救出更多的同志来……”康克清和同志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朱军长对万安人民的关怀。
康克清随红军上井冈山后不久,国民党就集中了湘、粤、赣三省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4个月的战火纷飞,敌人始终没能得手。1929年1月,红军前委决定:留下彭德怀一部,红4军其余主力下山到敌人后方开辟革命根据地。就在红军下山的途中,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朱德的夫人——伍若兰同志在一次突围战斗中不幸牺牲了。朱德忍受着巨大的悲痛,日夜操劳,指挥红军同敌人展开英勇战斗。
战事告一段落后,朱德身边的战友惦记着要给他再找个伴侣。当时,曾志、康克清等十几名女战士同在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做民运工作,任务是随主力部队开进,每到一个新地方,就在当地做群众工作,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参军筹粮。她们是军部直属队,行军作战常和军部一同行动。有时在行军途中,朱德还会到她们这里来鼓励女战士克服困难,努力完成任务。渐渐地,朱德也就认识了这些女兵。
曾志是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民运股长,同朱德等首长们比较熟悉。她一直在暗中观察周围的姑娘,想为朱德选个好伴侣。在曾志的介绍下,朱德与康克清渐渐互生好感。
到了3月初,红军在大柏地消灭了敌人一个团,随后进入东固休整。这天下午,村边的稻场上传来战士们嘹亮的歌声。曾志带着康克清和其他几名女战士来到朱德的住处。她们先和朱德聊了一会儿,在曾志的暗示下先后都退了出去,只留下康克清和朱德两个人。于是,他们俩坐到了一起,热情地谈起话来。
“当我初次和他接触时,并没有立刻浪漫地对他钟情。不过因为他跟战士一样,又做着士兵的工作,所以非常喜欢他。当时所有的人全都敬爱这位革命领袖。我们两人是最要好的同志。但过了这个过渡时期后,我已不能不承认我大概对他产生了爱情。”这是1937年康克清接受一名美国记者采访时说的一段话。虽然没有任何浪漫色彩、引人入胜的插曲,但它真实地记录了当年康克清和朱德的爱情经过。
3月下旬,红军进入闽南,在长汀县消灭了敌人一个旅,击毙旅长郭凤鸣,建立了闽西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长汀县是闽、粤、赣三省的边陲要冲,也是闽西最繁华的县城,在这里红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胜利的喜庆中,康克清和朱德在长汀县城“辛耕别墅”——一间8平方米的房子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婚礼,大家纷纷举杯祝贺他们两人喜结良缘。
从这以后,不论是战争年代枪林弹雨的艰苦岁月,也不论是和平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康克清始终伴随着朱德,他们相敬相爱,共同度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对于自己的选择,康克清曾坦率地说:“我的婚恋观就是无产阶级的婚恋观,只要革命坚决,品德高尚,对党的贡献大,真的志同道合,我就不计年龄,不媚权势。”
康克清同朱德結婚后,战友们都为她高兴。可也有一些人觉得她地位变了,相处时客客气气不像过去那样亲热了。这种评价,使康克清感到特别苦恼。她忘不了朱德对她说过的一句话:“我们都是农民的后代,是红军的普通一员。”她决心以此自勉,用行动证明自己不但是朱德的夫人,更是一名红军战士。
结婚后,康克清本来可以和朱德生活在一起,受到应有的照顾。但她没有这样做,而是像过去那样回到了自己的部队,同大家生活在一起,生活上没有半点特殊。她身上的一套军装穿得补丁缝补丁,大伙儿都劝她去总供给部领一套新的穿。她严肃地说:“不,大家现在不都只有一套军装吗?这衣服补好了,还能穿个一年半载的。”
按照当时的制度,她和别人一样,只有到了周末和节假日,才回到朱德那边去。她从不叫朱德为丈夫,总是以同志相称。有些好奇的姑娘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们虽然是夫妻,但又都是红军战士,叫同志好。”
有一次,部队到达吉安,晚上朱德突然发起高烧。康克清得知后立即赶到朱德身边,熬药、用湿毛巾冷敷,一直忙了大半夜,朱德的高温才降了下来。第二天,她按时返回部队照常工作。到了晚上,战友们都非常关心朱德的身体,一个劲儿劝她在朱德身边多待几天,几个手脚麻利的姐妹还捆好了康克清的行李。大家都认为她这几天不会再来了,可天一亮,康克清的身影又出现在操场上,同志们都打心眼里敬佩她。
大家称她“官兵平等的模范”,朱德既为她骄傲又为她担心
1930年6月19日,红一军团在福建长汀成立。不久,党中央又做出决定:将一、三军团联合起来,成立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而康克清被调到方面军总部特务3连任指导员。在特务3连当指导员不同于在司令部机关,对康克清来说是个全新的工作。这里的战士都经过一番挑选,不少是粗通文化的高小学生。当时红军里上过学的人很少,一般把高小学生也看作知识分子。比起他们,康克清是个没有上过一天学校的农民干部。战士的年龄又都同她差不多,工作中的困难自然更多。
康克清分析自己的有利条件:自己参加革命的时间比他们长,革命道理比他们懂得多,政治觉悟比他们高,具备了一定的军事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自己已有了做指导员工作的初步经验,懂得了管理教育的基本方法,也已经能看懂一般的书报了。所以,康克清有足够的信心做好工作。她给自己规定了四条原则:严格要求自己,给战士们做岀好榜样;严格要求战士,不论政治思想、军事训练,都要严格要求;关心每一个战士,针对每个人的思想实际,帮助他们;搞好全连的生活,一定要把伙食搞好。
到特务连的头一天,战士们见指导员是个女的,都在一边窃窃私语,连长也对康克清投来疑问目光。康克清不多说话,只是按自己订的四条原则行事。经过她认真地工作,严格要求,大家同她很快地亲密起来,她成了连队大家庭里的一员。没有人对她另眼相看了,她的工作也一天比一天忙起来。
红军从吉安出发至新余一带,转战赣南宁都、黄防等地,每天跋山涉水,长途行军七八十里,不少小伙子都吃不消了,直皱眉头。康克清和战士们一样,自己背着军毯和雨伞,斜挎着干粮袋,腰间还挎着手枪和子弹,紧跟司令部后卫队,从不掉队。看见旁边有的战士脚步慢下来,康克清主动上前关心地询问:“是不是饿了?”“身体有没有不舒服?”往往不等人家回答,她就抢过枪支、弹药帮他们背。
有时,战士们见她背的东西太多了,就劝她把东西给骡子驮或民夫挑,她说什么也不肯,还温和地笑笑说:“骡马不会说话,如果累死了,公家还要花钱去买。民夫规定挑公物40斤,再加重就是一种剥削行为了。”
战士们看劝不动她,就悄悄报告给了朱德。朱德知道后,既为她骄傲又为她担心。考虑到她每个月有几天行动不方便,朱德想把自己的牲口让给康克清骑一程。她却说:“你是指挥官,指挥官不骑马能行吗?快骑走吧!我不累,保证不掉队。”事后,康克清找到那几个“打小报告”的战士,还“剋”了他们一顿。
1930年12月的头几天,呼啸的西北风夹着雪片往脖子里钻,缺衣少食的战士们冻得直打冷战,一些战士还冻伤了手脚。白天行军还好过些,到了夜晚宿营就更困难了,能找到一处避风的地方睡觉,成了部队的头等大事。有一天晚上9时多,司令部的两名副官有事来找康克清。他们先到宿营的村里比较像样的房子找,没有找到她。问了几个战士,说她到村东头去了。他们找到村东头,才在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用来放农具的小茅屋里找到康克清。
只见康克清睡在临时搭的一块门板上,身盖一床单毯子,上面压着一件棉衣。四面透风的屋子像个冰窖。两位副官看到总司令的夫人竟睡在这样差的屋子里,心里实在过意不去,要给康克清重新换个好一点的房子休息。康克清裹着棉袄摆了摆手说:“战土们都是这样睡的,我是战士,应该在这儿睡。”
时间长了,战士们看见康克清不仅不摆架子,还真诚地关心和帮助战士,都称赞她是“官兵平等的模范”。
王稼祥称赞23岁的康克清:“真想不到你这个女同志,也能这么沉着老练地指挥战士打退敌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抢渡湘江时,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去一多半,只剩下3万余人。为了避开敌人的飞机,红军大多在夜间行军,白天休息。這个时候,康克清主动承担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在司令部的后面做收容工作。为了不让一名战士掉队,她跑前跑后,指挥战士把因伤或因病走不动的战友集中起来,由担架队负责抬着走。“大家跟上,不要掉队。”黑暗中,不时传来康克清急促的声音。
每逢到达宿营地,大家都歇息安顿下来,康克清仍有干不完的工作,查点人员是否到齐、看望伤病员、对驻地周围的情况进行调查,还要考虑明天的行军计划。
行军途中休息时,她还常帮助朱德抄写命令、起草通知。战士们经常看见他们的指导员坐在行李上,把背包放在膝盖上当桌子,抄写着总部下达的命令。不少人都知道,7年前康克清参加红军时还是一个文盲,经过这几年勤奋学习,在同志们和朱德的帮助下,她的文化水平提高很快,但,她肩上的担子也更加重了。
当时,中央机关首脑跟在红军总部后边,康克清常常能遇见一些中央首长。
毛泽东这时在中央还不负什么责任,常常带着几个警卫员徒步行军,很少骑马或是坐担架,显得十分轻松。每当他那高大的身影出现在收容队战士面前,总会出现一些热闹的场面。有几次,身体健壮的康克清身背两三支枪,背包上又摞着个背包走在队伍里。毛泽东见了便打招呼:“你这个指导员真是个大忙人哟,有那么多的东西要你背,行吗?”“没问题。”康克清爽快地回答。毛泽东常向她问起部队的情况和战士们的情绪,康克清一一回答,他们边走边谈,不时发出一阵开心的笑声。四周的战士看见他们那么高兴,那么轻松,也受到感染,脚下的步子似乎轻快了许多。
有时敌人尾随得很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战斗,所以康克清在行军中还要及时了解敌情,事先准备好几套方案,应付突发事件。一天,部队行进在半山腰的一段羊肠小路上,一面是很高的山崖,一面是密密麻麻的荆棘,走起来很困难。突然,后面传来一阵枪炮声,顿时部队有些乱。康克清立即命令一名干部把收容队收拢一下,加快行军步伐,同时做好战斗准备。她紧跑几步,来到中央首长的队伍里:“首长们快些走,后面的敌人追上来了。”“怕啥子哟!”毛泽东停下脚步,又侧耳听了听,觉得枪声还很远,便微微一笑说:“敌人不会那么快追上来,放枪是吓唬人呢,再说后面还有红军。你着急,你们就先走嘛!”说完,他朝康克清摆摆手,就朝前走去。
看见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都那么镇定自若,康克清也放下心来。虽然这次只是虚惊一场,但她的责任心还是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
红军进入贵州以后,康克清被临时派到担架队负责,这可不是一般的担架队,抬的伤病员都是红军团以上干部,其中好几位还是党中央的领导人,王稼祥就是其中的一位。
虽说担架队前面有红军开路,后边有部队殿后,但在绵延起伏的群山中长途行军,首尾相差几十里,要保护好几十名受伤的团以上干部和中央领导,任务之艰巨、责任之重大是可想而知的,康克清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一天中午,担架队与中央机关的队伍相遇。康克清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几位领导同志,立即叫担架队停下来,让开道路叫中央机关先行。周恩来笑着摆手说:“你们不必让了,我们就跟在你们后边,也省得再去另找向导带路了。”康克清一听有道理,便带着担架队先走了。但没想到居然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了敌人。康克清沉着冷静,指挥战士们英勇还击,不一会总部增援的部队到了,一阵密集的子弹射向敌人,立刻倒下十几个人,其余的敌人像野兔子似的惊慌失措地跑回山上。
步兵班的战士高兴地跳起来要上山去追击敌人,康克清立即制止说:“我们的任务是保卫中央机关和担架队的安全,不是消灭敌人。”很快,特务排的同志们也撤了回来,他们还捡回敌人丢掉的两条枪,只有两人受了点轻伤。
从后面上来的中央机关的同志听了情况介绍后,都称赞康克清指挥有方,很好地保护了中央领导的安全。王稼祥从担架上伸出手竖起大拇指说:“打得好啊!真想不到你这个女同志,也能这么沉着老练地指挥战士打退敌人。”
永远的“康妈妈”
新中国成立后,康克清专注于全国妇女解放运动工作,她处事待人和蔼可亲、质朴大方,被大家崇敬而亲昵地称为“康大姐”“康妈妈”。
在长期的妇女工作领导岗位上,康克清一贯坚持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她重视妇女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强调妇女必须提高自身素质,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她十分关心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1979年亲自主持了《婚姻法》的修改工作,她特别关心基层和贫困地区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要求各级妇联干部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强调把妇女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个现代化”的号召,为新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康克清还为增进我国与各国妇女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曾代表我国出席过“国际保卫儿童会议”和联合国妇女十年中期会议,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康克清重视儿童工作。她曾发起建立延安第二保育院,为战区难童和革命者后代的成长呕心沥血。新中国成立后,她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大力兴办各种儿童福利事业,有力地促进了儿童健康成长。
在康克清的亲自帮助下,盲人作家徐白伦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盲童刊物——《中国盲童文学》,康克清还亲笔为刊物题名。这份刊物一诞生,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卷起一个又一个爱的旋涡。
1986年7月14日,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包括9个民族的58名优秀盲童代表齐聚北京——全国第一届盲童夏令营开幕了。他们抚摸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亲吻着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的红旗,聆听着天坛回音壁的奇妙回声,攀登上了世界闻名的长城。他们,用心灵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此时此刻,身在外地的康克清仍然在惦记着这些盲童。她写来了一封祝贺信,并委托秘书在开幕式上宣读:“亲爱的孩子们,得知第一届盲童夏令营开幕了,我非常高兴,并向你们表示祝贺。我现在虽然身在外地,但与你们的心紧紧相连……”
1978年至1992年擔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康克清为加强人民政协建设、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作出了积极贡献。
1992年2月28日,81岁的康克清住进了医院,病因是感冒、发烧。之前她坚持不住院,因为她心里惦记着许多工作: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在医生的劝说下,她终于答应只住两天就出院,然而病魔无情,没料到这一住就再没能回来。
3月初,一些领导同志去看她,她还特别提起即将召开的政协常委会和大会,大家劝她静心养病,可她仍旧挂念着工作。
康克清病重住院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想来看她,她对秘书说:“我是个闲人,不要耽误别人的时间。”可她心里却总是装着别人。1991年,康克清到广州住了4个月,广东省人民医院大夫张碧梧一直陪着她。后来,康克清送给她一床被套。这次住院,康克清得知张大夫有两个儿子,又特意请人买来一床被套带到广州,并捎话:“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有两个儿子。现在补上一床,请收下。”康克清对身边的同志说:“张大夫是个好人,该做的工作她都做了,不该她做的她也去做了,现在就需要这样的人。”
4月初,清明节快到了,病榻上的康克清更加思念她的亲密战友和伴侣朱德。从1976年朱德病逝以来,每个清明节,她都带领儿孙到八宝山去祭扫,即使在外地也要赶回来。这次她实在去不了了,儿孙们带着她的嘱托和对朱德的一片深情来到了八宝山,朱德逝世16年来,她未能亲自去扫墓,这是第一次,也成了最后一次。
不久,康克清病情加重,她呼吸困难,血压下降,医生努力进行了抢救。康克清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她把孩子们都叫到了床前,断断续续地对他们说:“你们要好好地过日子,不要贪污,不要犯错误……我什么都不要,一切后事听从组织上安排……”泪水盈满了康克清的眼眶,她似乎还想说什么,但已经没有力气说下去了。孙子们问她:“让我们把您与爷爷放在一起,是吗?”康克清无力地点了点头。
1992年4月22日12时零4分,这位昔日的贫苦“望郎媳”、如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烈火中炼出的金凤凰康克清,终于平静地闭上了双眼,走完了她不平凡的人生之旅。
(参考资料:《从战士到领导》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红军女司令康克清》《党史纵览》2014年第4期等;作者:潘望等、李新市等)
朱德家风:革命到底
1975年3月6日,朱德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大字。康克清说:“这四个大字,既是对他自己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的总结,也是对我们全家的期望。”
在朱德的遗物中,有一条补了又补的衬裤,上面有17处补丁,无数个小孔。还有一张白麻纱贴花床罩,一边已朽烂,罩面上有6处补丁,这张床罩陪伴朱德度过了晚年生活。后来,康克清又一直用到1992年去世。这张床罩总是破了又缝,缝了又补。这些补丁还是朱德的儿媳妇赵力平缝补的。由此可见,他们传承的不仅仅是一件件物品,更是体现出良好家风。
在领导干部子女用车问题上,朱德从不破格,真正做到公私分明。朱德对家里的所有人都严格要求,一律不准乘坐公家的汽车上学,无一例外,就连康克清都是乘公共汽车去上班。
康克清十分喜爱孩子,但她却终身未生育。朱家的数十个孩子和一大批烈士遗孤,从小到大都是康克清辛勤抚养,她严格的家教,对后代们影响深刻。
这是朱德和康克清在1943年10月28日写给女儿朱敏的一封信,当时朱敏正在苏联国际儿童医院学习,他们便写信勉励她好好学习,全面发展,为建设祖国做准备。
朱敏女儿:
我们身体都好。朱琦已在做事。高洁(贺高洁,朱敏的表姐)还在科学院。兹送来今年上半年的像(相)片两张。你在战争中应当一面服务,一面读书,脑力同体力都要同时并练为好。中日战争要比苏德战争更迟些结束。望你好好学习,将来回来做些建国事业为是。
——朱德康克清
1983年“严打”期间,朱德最小的孙子因触犯法律,在天津被处以极刑。有关部门向康克清通报情况,她的态度很明确:“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康克清从未介入此事,也没有任何领导人找她谈过话。凡事依靠组织,这是她一贯的思想。
康克清曾对跟随她多年的老秘书叶梅娟说:“朱德同志生前有过嘱咐:‘如果孩子不争气,犯了错误,出了问题,你也不用生气,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子孙不争气,你可以登报与他们脱离关系。”对于社会上的种种传说和流言,康克清未予理睬,她说:“当务之急是要做好他母亲的思想工作,使她能认清现实,尊重法律,并从中吸取教训。”
就在朱德的小孙子被执行死刑的次日,康克清外出参加重要活动。行车途中,她平静地对司机刘国和说:“刘师傅,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的孙子犯了罪,昨天给枪毙了。”“我也听说了,但没敢问您。”稍后,刘国和又谨慎地问:“听专车司机们说,您在判决书上签过字?”康克清略显激动地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还用签字吗?”
此后,康克清有时会在饭桌上教育孩子:“你们出了问题,不是个人的事,是在折腾你爷爷!爷爷有话在先,你們如果不争气,做了违法的事,要我登报声明,与你们断绝关系!”
自新中国成立,康克清一直致力于妇女儿童工作,为全世界的妇女儿童的权益保障奔走呼号,直至逝世。如今,康克清纪念馆不仅是“江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被评为了“江西省首批家风家教示范基地”。
(责编:袁栋梁;参考资料《康克清一生革命的“红军女司令”》《井冈山报》2018年2月7日;作者:刘欣、周玉莲、杨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