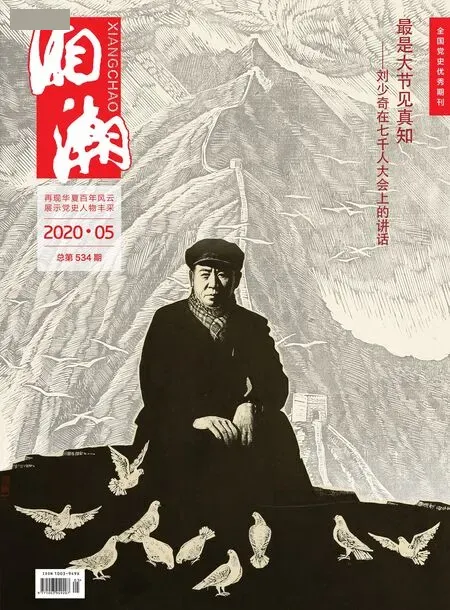“儒将”袁国平
★ 王树仁
袁国平,原名裕,字醉涵。1906年5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袁家台村(今属邵东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38年3月,在毛泽东亲自推荐下,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自小酷爱文学,诗词俱佳,有“儒将”之誉。“皖南事变”后的1941年1月15日,在指挥被打散后一部分部队继续突围北撤的激战中,身负重伤的袁国平为了不拖累部队突围,举枪自尽(遗骸于1955年6月19日移葬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实现了“如果有一百发子弹,要用九十九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做俘虏”的诺言。
和毛泽东《七律·长征》
1935年10月,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的红三军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越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历尽艰辛,胜利到达陕北。袁国平满怀胜利的喜悦,写下许多诗词。
一天,袁国平和妻子邱一涵读到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异常激动。邱一涵对袁国平说:“你会写诗,你就写一首和毛主席的诗,我来抄正。”就这样,袁国平很快就用原韵写了一首题为《和毛主席长征诗》的七律。诗曰:“万里长征有何难?中原百战也等闲。驰骋潇湘翻浊浪,纵横云贵等弹丸。金沙大渡征云暖,草地雪山杀气寒。最喜腊子口外月,夜辞茫荒笑开颜。”诗中的“中原”本指黄河流域,这里指中国;“等闲”指平常事;“潇湘”指潇水湘水,泛指湖南;“云贵”指云贵高原;“等弹丸”指把云贵高原看得像弹丸之地,极力写出红军纵横驰骋的豪气;“茫荒”指无边无际的荒野。
此诗的首联是全诗的纲领,气壮山河地写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远征对红军来说也不过尔尔,其间经历的无数次恶战就好比平常事一样。颔联写红军纵横驰骋、转战湘云贵川数省的战况。突破湘江潇水,攻克黎平,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四渡赤水,在铁流二万五千里征程中捷报频传。颈联“征云暖”形象地写出了红军强渡大渡河和抢渡金沙江时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和敢打敢拼的旺盛斗志,而“杀气寒”则逼真地描绘了空气稀薄、道路险峻的雪山和千里沼泽的草地给红军征途带来的艰难险阻。尾联写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后极其喜悦的心情。腊子口是四川省通往甘肃省的要道,胜利通过腊子口,意味着红军抵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已是指日可待,万里长征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在望。这首七律意境雄浑,通过一个个典型生动的战争画面,描绘了长征的艰险与伟大。
深情寄母诗

袁国平(后排左一)与战友合影,后排右二为周恩来
1935年11月,袁国平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政治部主任,不久调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政委。1936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更名为西北抗日红军学校后,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委。1936年6月,红军大学在瓦窑堡创办,林彪为校长,袁国平为训练部部长。红军大学分设三个科,第一、二科驻陕北,第三科(袁国平任政委)驻陇东环县木钵镇(1937年1月移驻甘肃省庆阳县县城)。因第三科远离红军大学本部,故又称“红大第二校”,对外则称“红军教导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红军大学第三科改称“庆阳步兵学校”,亦称“抗大步兵学校”,由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委。次年,中央军委即以该校教职员为基础,组建八路军随营学校,韦国清任校长,陈明任政委。袁国平则留在庆阳担任中共陇东特委书记。
袁国平自离开湖南老家参加革命后,就全身心投入杀敌战场,一次也没有回去看望过父母。1937年,袁国平在庆阳期间,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他在信中写道:“我已置身于革命,是以牺牲一切为代价的,无法帮助家里,希望家里能够支持我、原谅我。”在表达对母亲的思念的同时,他还把自己在长征到达陕北后拍的一张相片,随信寄给了母亲。照片上,袁国平戴着一副眼镜,骑着一匹花白的高头大马,满脸胜利喜悦地走在乡间小道上。相片的背面,他题写了一首七律:“十载辛酸斗兵戎,愧我吴下旧阿蒙。半壁江山沉血海,满地干戈斗沙虫。北伐长征人犹在,千伤万死鬼亦雄。弹丸挣扎鱼龙变,地覆天翻见大同。”落款为“袁国平一九三七年于甘肃庆阳”。
在这首表达自己献身革命志向的《寄母诗》中,袁国平以“吴下阿蒙”自谦,意思是自己对于革命事业没有重大贡献,十年奋战,还没来得及把国民党反动统治推翻,半个中国又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蹂躏之下,人民遭受敌人的屠杀,死伤遍地。诗中还有许多特指:以“弹丸”喻指日本岛国是弹丸之地;“挣扎”指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垂死挣扎而已;“鱼龙变”借汉代的一种杂技,来指中国的抗战一定会取得胜利;“大同”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统战赠七绝
1937年秋,在甘肃庆阳,洋溢着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浓烈气氛。因庆阳抗日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故国民政府军也决定派团前来参观访问。对此,有人认为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不乐意接待他们。时任中共陇东特委书记兼八路军驻陇东办事处主任的袁国平开导大家说:“对这个参观团,我们不但要接待,而且要接待好。这是送上门的统战工作,这样好的买卖何乐而不为哟!”那些原来思想不通的同志,被袁国平一席话说得茅塞顿开。
国民政府军参观团里有几人是袁国平当年在黄埔军校的同学,相见之后,一位老同学感慨地说:“袁仁兄,军校毕业后,我们分道扬镳了,你朝左走,我们向右转了。”袁国平笑着说:“兄台们,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们去过黄陵吗?离这里不到三百里。诸君若有兴趣,小弟愿驱车奉陪。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面对外族入侵,应当摒弃前嫌,携起手来,一致对外!”还有一位老同学拍着袁国平的肩膀说:“以袁仁兄之大才,若能到我们那边去,定能委以高位、奉以厚禄。”袁国平听罢,笑着答道:“谢谢兄台美意,不才此生别无所求,唯愿为民众、为民族做点有益的事。”
参观团在庆阳参观的两天,对中共领导的庆阳敌后抗日工作有了深入了解,也对袁国平高超的领导才能深表佩服。临行时,他们向袁国平求诗留念。袁国平遂作《七绝》二首相赠:
“三年同学十年仇,百战纠缠一战休。差幸干戈化玉帛,愿从风雨济同舟。”
“逐鹿中原为国是,十年征战听人评。相逢休话阋墙事,莫使神州任陆沉。”
这两首七绝诗,既是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诗意化解读,又表明了共产党人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诗赞爱妻
1929年5月,时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宣传部部长的袁国平来到湖南平江横洞巡视工作,遇上了正在这里坚持斗争的邱一涵。邱一涵是湖南平江芦洞乡丁家源村人,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年22岁。两人由相识相知到相爱,经过革命斗争血与火的锤炼,于1930年结为伉俪。
婚后,邱一涵除了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外,还经常挤时间协助袁国平的工作。1939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新四军军部评选了三对模范夫妻,袁国平和邱一涵是其中的一对。袁国平曾在邱一涵寄给他的照片背面赋诗一首,表达了他们夫妻深厚的感情,诗曰:“不是甜的蜜,不是香的花。好比茅台酒,醇芳与日加。”诗中,袁国平把邱一涵的高贵品质和他们之间的纯真爱情比作茅台酒,年代愈久,其味愈浓,其香愈纯,体现出了革命战士情深似海、追求真善美的婚恋观。
“十年征战感系多,问君何事费蹉跎?愿将头颅抛原野,不随池流逐浊波。”这是袁国平赠给爱妻邱一涵的另一首诗。“愿将头颅抛原野”的背后,却是对妻儿的满腹愧疚。袁国平十分疼爱妻子,然而在长征时,他将自己骑的马让出来驮载伤病员,却让手部受伤、裹过小脚的妻子拉着马尾前行。为了革命事业,他们把一子二女寄养在乡下。由于乡下缺粮少药,以致两岁的小女儿殁于疾病,大女儿13岁被送做了童养媳,儿子8个月大时被送回湖南老家,幼年贫困失学,一度靠牵着双目失明的奶奶乞讨度日。
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建立新中国,袁国平、邱一涵夫妇不怕牺牲、英勇战斗,不顾小家为大家,这是多么伟大而可敬啊!
主创《新四军军歌》
1939年3月的一天晚上,新四军军部在安徽泾县举行欢迎周恩来的晚会。在晚会上,陈毅(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唱了一首《马赛曲》。回到座位后,他感慨地对周恩来说:“我们新四军应当有支歌为好!”周恩来含笑点了点头:“好呀!你是诗人,你就写个歌词吧!”陈毅慨然应允了。
1939年3月30日,陈毅写出了《新四军军歌》歌词的初稿:“光荣的北伐行列中,曾记着我们的威名。我们继承着革命者受难的精神,在南国的罗霄山,锻炼成为钢铁的孤军。这里有革命的反帝的歌声烂漫,飘扬海外,散播农村。我们送出了抗日先遣的万里长征,我们留下来坚持斗争,招引那民族再团结,雄鸡破晓,伟大的抗日之声。风雪饥寒,穷山野营,磨炼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三年隔绝,四围孤立,增添我们独立坚持的勇气。长年累月的埋伏与周旋,把游击战争与秘密工作结合在一起,我们就是这个母亲的儿子,我们铁的纪律就来源于此。啊!这光荣的传统准备了十年,今朝抗日,敌寇胆寒!我们在大江南北,向敌后进军,南京城外遍布抗战的旗旌。我们有共生死的政治团结,鼓舞敌后人民的胜利信心。在日寇封锁线上穿插,在日寇坚城下纠缠,我们惯长于夜间作战,用白刃同日寇肉搏,向敌人巢穴里投进烈火。集小胜为大胜,由相持到反攻,看我们风驰电掣,横扫千军。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高举新中国的旗帜前进!”歌词热情歌颂了新四军继承着北伐第四军、红军第四军和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红色游击队前后10余年的光荣传统及取得的成就,故名《十年》。
新四军政委、副军长项英征得陈毅同意后,指定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以陈毅初稿为基础进行《新四军军歌》的创作,并说袁国平是作词的行家。袁国平领命后,对《新四军军歌》进行了再创作:“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获得丰富的战争经验,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的驰骋;深入敌后百战百胜,汹涌着杀敌的呼声。要英勇冲锋,歼灭敌寇;要大声呐喊,唤起人民。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创造现代的革命新军。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巩固团结坚决的斗争!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1939年7月1日上午,新四军军部为庆祝党的生日,让袁国平布置文化队演唱《新四军军歌》(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队长何士德谱曲)。军部领导听后,当场拍板,将军歌的词曲定了下来。
《新四军军歌》从诞生到后来在新四军中广泛教唱,作为军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付出的劳动是最多的。尽管他是主持《新四军军歌》创作的关键人物,但在词作者的认定上,袁国平始终没有同意加上自己的名字。
绝唱留芳
1940年底,根据党中央指示,新四军军部即将离开驻守三年的皖南泾县云岭,北上到江北敌后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三年的皖南生活,让新四军将士与皖南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带着对皖南人民的惜别之情和对北上抗日的必胜决心,袁国平写下了一首题为《别了,皖南》的歌:“前进号角响,大家准备好,子弹上膛,刺刀出鞘。三年的皖南,别了!目标,扬子江头,淮河新道。哪个来拦路,哪个被打倒!冲过重重叠叠的封锁,冲进日本鬼子的窝巢。我们一定胜利,我们一定到达目标!”
写完后,袁国平把它交给作曲家任光(1909—1941),请他谱曲。袁国平对任光说:“新四军是1938年成立的,在皖南已整整三年了,同志们对皖南都很有感情。新四军即将北渡长江,得给同志们打打气,以振作精神,到江北敌后开辟新的根据地。”听了这番话,任光很受感动,接过歌词便全力投入创作,只用了几天就完成了谱曲。这首又称《别了,三年的皖南》的歌曲,充分表达出江南新四军将士对皖南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也吹响了新四军投入新的战斗的嘹亮号角。
1941年初,根据党中央“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指示,新四军开始陆续撤离泾县云岭,向皖东南、苏北一带转移。因此,这首歌曲又被称为《新四军东进曲》。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多人,唱着《别了,皖南》告别云岭。1月6日,当部队行进到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8万余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政委、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举枪自尽;作曲家任光也不幸中弹牺牲。这首《别了,皖南》,也成了袁国平激励将士抗日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