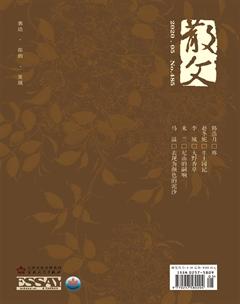争说西施曾醉此
施立松
桃园村并非结义之所,而是槜李之乡。古语云“桃源村里好耕田”,这里既非世外,更非桃源,却是不耕田只种李,桃与李本就不可分,桃李,就应该是满天下的。
以水果命名的所在,在我的记忆里,似乎除了枣庄就仅此一处,山东人的粗犷让“枣庄”这名字太直白浅淡平铺直叙,反倒不如它的本名“兰陵”更来得儒雅传神,与“槜李”相比,更是少了江南特有的诗意和佛性。嘉兴古称槜李,便是以这小而圆,红而甜的果子命名的,散淡,清香,静雅,也端庄。
站在桃园村的槜李林下,似有隆隆征伐之声。早些年,这里的人经常能在李树下挖出些青铜器和锈迹斑斑的古剑来。搜遍了记忆中那些所剩无几的历史知识,有几张面孔似曾相识。他们叫勾践、西施、范蠡、夫差,正是这些名字,组成了历史课本里很是绘声绘色的一章内容。
公元前510年,吴军便是在这里大败越军,十五年后,勾践为父报仇,又是在此地一雪前耻,甚至将夫差的父亲杀死在这里。史书记载:“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屦。还,卒于陉,去槜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三年,乃报越。”槜李之耻成了夫差的心头恨。前前后后长达三十七年的吴越之争,便是在这一片雪白的李花缤纷之中隐藏了刀光剑影。
想不到一树槜李成了这段历史最著名的注脚。俞兆晟的 《吴宫曲》里如此唱:“军声殷殷来槜李 ,犀甲晶莹照秋水。”古来征战几人回?谁看得透史册间那些虫蛀的文字里到底有多少新仇旧恨?那战场上的李子树应该记得吧。它们不声不响,一言不发,努力长高,开花,结果,用绽放为一段历史补白。李白用诗,怀素用字,黄宗羲用画,挣扎者各有各自的武器与方式,而勾践用一枚苦胆和一个叫西施的女子。那么西施又用的是什么呢?一匹纱还是一颗名叫槜李的果子?
历史从来只提出问题却不给出答案。杨贵妃爱荔枝,西施独钟槜李。钱牧斋绝句中有“语儿亭畔芳菲种,西子曾将疗捧心”之句;朱彝尊也说“听说西施曾一掐,至今顆颗爪痕添”,把美味与美人妙手天成。
更有文人雅士学苏轼曲水流觞之意,以槜李为题大抒诗性。光绪十九年(1893),李培增发出《征诗启》,以先世数代培育槜李为题,更尽地主之谊与叙师情友谊为旨,以期“增盛名于尤物,得佳名于奚囊”。后俞樾、张鸣珂等七十余人响应,计作诗百多首,结成《龙湖槜李题词》集传于后世,相形之下,盛况更胜苏轼当年。
中国人爱黄与红,这是骨子里传承下来的,炎即是红,红黄之间便是炎黄子孙。槜李恰好如此,表皮琥珀色,果肉金黄,更是在果子身上常常可见一条弯弧的黄色浅痕,像是指甲的划痕。这个划痕大有来历,后人美其名曰“西施爪痕”。据说当年勾践大败,献上美女西施。西施赴吴途中路过此地,曾享受过此等美味,喜其粒圆果大,兴起随手一掐,于是此后的槜李上便都多了这一条诗意氤氲的指痕。清代刘炳照曾有诗云:“古城遗迹认依稀,朱实离离映夕晖。争说西施曾醉此,长留爪印是耶非。”
人间皆传花魁牡丹上有贵妃指印,而这小小的槜李上就留了西施爪痕。“兴亡常事何须问,且向西施觅爪痕”“美人纤爪空留掐,一捻还堪比牡丹”,这小小的李子,似乎每一个尝过它的诗人都不肯放过西施指、牡丹香,故而又有“爪掐纤痕留颗颗,琼浆吸尽润诗喉”的句子,把美人美句美味合成七言,又千万言不可尽数。
更有记载说西施自幼便有的顽疾胸口痛,就是因为吃了槜李一夜而愈。后来越国复国,她与范蠡驾舟而去,又路过这里,只觉此地人杰地灵,与自己颇为有缘,于是决定在此定居。二人便在湖边栖身,几间茅舍,三两池塘,男耕女织,其乐融融。后来这湖便叫作范蠡湖,西施梳妆处则名为胭脂汇、汰脚湾,这些地名现今仍存。范蠡与西施的动人之处是在大丈夫式的战火离乱之中隐含着小家碧玉般的儿女情长和柔情蜜意,从而让那一段血腥历史有了婉约和细腻,让那些翻阅历史的学者们也不得不叹息一声,把目光投向那些俗世因果、柴门犬吠,而不必对着厚重的复仇、征伐留太多感慨,让人知道,历史的更迭虽然不一定是善的,但却一定是真的,更是美的,它让历史从枯燥之中透出些可爱和温润来。至于传说,毕竟只是传说,倒是那西施一掐的小果子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传说虽不可信,但这小小的果子,却因这美人一掐而诗性天成独尊李子中的头魁。从此之后槜李名声大振,历代皇家都定为贡品,倒不见得只是想尝尝美味,更有一睹美人指痕的雅意吧。没有哪位君王在端详槜李的时候一定会想到勾践,但每一个人都会想到西施,毕竟品尝美味需要从本性出发,也非以教化为目的。它只是逞口舌之快,尽味蕾之欢即可,不必强加于吃一个太伟大的理由。如果一定要以卧薪尝胆开始,很多食客难免会转身而去。这个开始太自虐太扫兴,太索然无味。
槜李天生尤物,不能囫囵吞枣,吃时要极尽美人本色,拈了兰花指捏着,先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慢慢吮吸。有玩心重的就找根吸管插进去饶有滋味地啜吸,与美人齐名的水果,连吃都不能失了风雅。
为一种水果作传,在文采飞扬的中国历史中也不多见,除了蔡襄的《荔枝谱》韩彦直《橘录》之外便要数到朱梦仙的《槜李谱》了。这书虽然只是一种植物的传记,却是集大家之手笔于一身,更极尽美言之能事,民国元老于右任题名,文史学家郑逸梅作序,丝毫不弱于任何一本知名典籍。桐乡的哪一本家谱里没有槜李的名字?哪一个街头巷尾没有槜李的影子?槜李早已超脱出水果的范畴转而成了一种文化概念和地域象征,它饱满、低调,深得儒家精奥,从而成为一种桐乡人文符号和精神内核。
一个种族的全部教义,就这样神奇地在一枚果子的身上呈现了。
桃与李,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着最高等级的文化寓意。想想看,只有品行和德才俱佳的文人才有资格称之为“子”的,孔子、庄子、孟子、老子,凡能以“子”相称的都是人间大才,而在水果里,能称得上“子”的并不多,桃算一个,李算一个,其他的似不足论。
相比于凡树俗花,桃李之上更无果,如此一来,高下立判。
槜李产量极低,故而珍果难求,虽春来遍地雪白,但一枝之上花开百朵,才勉强结果三五而已。槜李从不以数量称雄,那高绝,让人望而生敬。它惯于沉默,用微笑看人,用安然与世界对峙或连接,它等在那里,为迎接秋实做足了准备。
这是种自己哄自己开心的植物,而修成正果,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挣扎了几千年,才熬成今日容貌,养成今日品格,活成今日个性。花开几日便衰,是不与百花争奇斗艳;枝高过丈自枯,是不以魁梧引人注目。那小小的果子,竟透着处世之道,最难的是认清自己,槜李却轻而易举就做到了,它从不妄想补天、填海、逐日,它只是闷着头开自己的花,结自己的果,活得很哲学。受了美人一掐之苦,它懂得安身立命的本质含义,它外表平平,又贵不可言,这禅意,怎能不让它名声在外?
槜李名声响亮,全国各地都想引进,但这小小的果子实在个性太强。记得江南为橘江北为枳的故事吧,槜李也一样。那特别的秉性使之久居故土,“槜李獨钟桐乡,迁地弗良”。这秉性却也和此地民风相仿,历朝历代,无论是王侯将相、游侠商贾、文人墨客,生在桐乡,便坚硬中透着倔强,温润中带着阳刚。
所谓慷慨和豪气,看一个人失意时的自重、贫穷时的大方、受骗时的善良、得意时的谦恭、离难后的自若、跌倒后的微笑。想想看,槜李岂不也正如此?它沉默寡言却凛凛威风,小花小果却大开大放,温厚淳朴又冷艳高傲,不染凡俗又淡泊随意。越是个性的东西,越是性情中物。它自花不孕,更兼有雄蕊粗短雌蕊长,本就互不牵挂,很有些卓然不群的高傲味道。这品性岂非正像江南士子的狂傲孤绝?熬了几千年,甚至加以现代化的培育手段,到2018年的时候年产量不过也才四百二十吨,相比于动辄成千上万吨塞满仓库的大众化水果,这产量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了。
可正是这少少的不值一提的槜李,却像桐乡人那精悍顽强的意志一般,不与俗物相提,只与雅人为伍。梧桐之侧不活他物,槜李的身前身后也很少杂草。它高冷得旁若无人,就如朱梦仙《槜李谱》中所说:“所产之李,甘美逾恒,迥异凡品”,“为最上乘,果大味甘,足以傲睨一切”。槜李虽小,却合了老子那句“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如此看来,哪一种水果,能与之比肩而毫不逊色?
从来不认为从一枚果子身上能参透什么人生真谛,桐乡槜李却让人醍醐灌顶,已似乎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存在了。它朴素端庄,不张扬不讨巧,也不夸夸其谈,却分明又是静女其姝、伊人在水,是植物里的《诗经》。燕之梨、闽之橘、南海荔枝、西凉葡萄、嫩江西瓜、烟台苹果,以特产水果成名之地数不胜数,但争胜者未争已败,唯不争者而莫能与之争。那小小的槜李在枝上一立便是千年。染了千年风雅,看惯冷月清风,它见过美人西施,也见过贩浆走卒;它见过王侯争斗,也见过市井恩怨,它以不变应万变,以不言对万言,活得花香四溢。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