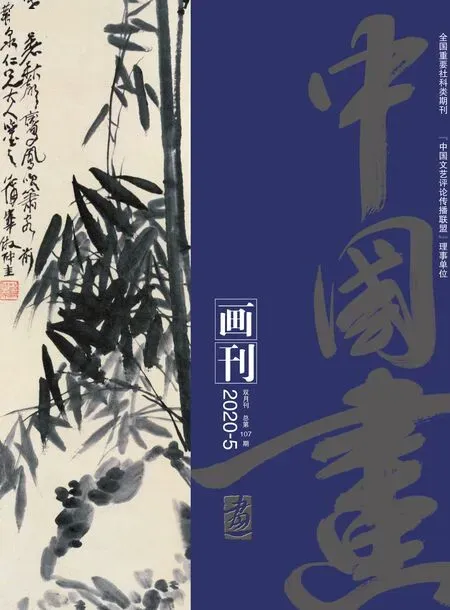画理先行
——罗小珊
写生、写意与写心
文/罗小珊
一、写意:造型与笔墨
中国人物画作为传统美术中最能顺应于时代发展,表现新生活、新现象,体现新风貌、新成就的画种,在中国画近代吸收学习某些西画传统的基础之上,在人物造型和表现上体现出更多的写实影响。这种融合的集大成者之一,即是浙派人物画。作为在新中国美术史留下深刻痕迹的画派,基于写实的造型理念与重新引入光影或者“拟似光影”所获得的强化明暗,使得作品具有深刻的表现力。在中国画漫长的发展历史上,这种对于西画技法,尤其是写实传统的引入,不亚于一种革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保护了中国画的延续。
我从本科开始受教于中国美术学院,作为浙派人物画的大本营,中国美院在人物画的教学上,注重写生、注重造型基础,受此影响,我之前创作大多以写实倾向的现实主义为主。

赶海去 38cm×38cm 罗小珊

不丹行 38cm×38cm 罗小珊

太行山民系列 32cm×32cm×4 罗小珊
目前,主流的主题创作中仍然大量使用拼贴照相手法。拼贴照相,甚至仍然是主题创作中最主要的技术手段,它为构图的便利和资料搜集的简化带来了巨大的改善。从此,画者能够通过对既有素材的调整来实现最初步的创作,在节约时间的同时,免去可能极为困难的从零开始的造型。但是,这种手法的缺陷之一,来自于缺乏足够的独立性。由于受制于既有资料的限制,画者会受困——因为信息充实之故,而无法脱离这种丰盈的困境。于是,作品会滑向对于照片的抄袭——工笔尤甚,写意虽然略有改善,但本质上,依然会透出浓浓的照片的影子。
加之中国画所强调的高峰是作为写意的高峰,写意与意象造型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写实虽然极为重要,在院体绘画之中也闪耀着夺目的光芒,但是,由文化传统中来,我们所崇尚的艺术,还是传心的体现。所以一种与时俱新的写意方式,显然存在其意义,甚至具有更大的意义:我们所需要的,是更加成熟的写意方法与更加成熟的个人艺术语言。这包括两点,一是个性化的造型,二是个性化的笔墨语言。
个性化的造型,是极为显著和容易被观察到的特点,作为作品写意性的体现,在人物画的创作上具有显然的意义,这包括夸张和变形的引入。
夸张和变形,自八五新潮之后,中国美术便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如何变形才能够避免简单的漫画式的处理,而有深刻的思想性的处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梁占岩老师给我们上课时,首先希望我们能够认真地观察被画的对象,带有感情的去看待它。以梁老师的例子来说,就是比如一个农民工兄弟作为你的模特,你要从他破旧的衣服,他的眼神,他的肤色等各个方面,去思考他经历的那一切,把自己的同情心加进去,这样才能够有悲天悯人的作品——而这种思考后得以表达的东西,与传统意义上的写意,便具有同一性。
至于画面的另外一个构成元素,笔墨语言的处理更应该注意整体的重视:这不同于对细部的在乎,因为传统上,注重局部的笔墨,强调局部的好看、精彩是非常自然的意思——换句话说,观者曾经可以单纯地通过欣赏作品局部细节的处理来得到极大的愉悦。但是这种割裂的处理,会导致作品陷入细节性的散漫之中,从而失去对作品整体的把握。从画者的角度说,仅存细节的作品,是对于被传达思想的极大蔑视,显然需要加以克服。

家山守望 240cm×122cm 罗小珊
变形的本质,是对于“意”的追求,也就是剥离掉对于“形”的依附,通过“变”来体现画者的思想——所以画者需要重构既有的形象,拆散、打破、重组从生活从记录上得到的造型,在自身试图表达之物的基础上,以服从于整体的态度,来完成画面。过于重视每一个画面、每一个人的造型的细节——这或许是我们目中所见的常态,画者对于细节的强烈追求,对于“细”的执着,近乎不可抑制的溢出画外——会不可避免伤害整个画面语言的结构,削弱画面的整体性。所以这种变形,实际上是重构目中所见,以心中所思,写笔中之意。藉由变形所带来的对于形象的取舍,便起到同样的作用。这其中对于程度和细部的拿捏,便显出画家的水准。
二、写生:记录和重构
中国画的写生,应该被认为是很特殊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经由长久的训练所习惯的方式,更加近于西画中的定义——重视对于目中所见之物的刻画和记录,并且试图强调对某种戏剧性的搜集,同时,心中又存有对中国画文人画“不重视”象形的印象的强调。
于是,这里会出现一个问题:国画家在进行写生的时候,究竟是在寻求什么?
在中国画人物画方向上,由于表现对象相对于传统范式的特殊性,单纯的“仿某某笔意”之类将名义上的形式凌驾于对象之上的“陈述”显然无法作为恰当的创作母题。只有通过对现实的记录,才有可能推动创作的进行——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写生的过程也是思考的过程:直面对象的记录,可以更多的获取关联情感和状态的记录。绘画所重视的,并不仅仅是对于外形的记录。
由目中所见,生心中所思,得笔下所写……所谓写生,并不以单纯的记录下某种戏剧性状态为目标——并非作为摄影的补充,而是通过尽可能精到、准确地把握形象、动态、场景、道具,即强调对于对象和环境的取舍,对于描述和铺陈的取舍,对于着重和漫漾的取舍——这是一种短暂而瞬间的创作,你没有太多的机会和时间去选择与调整,场景往往转瞬即逝——对于基本技法和观察力的重视于是变得极为重要,唯有依靠经常性的训练与联系,才有可能满足这种突发性的需要。

太行山民系列 32cm×32cm×2 罗小珊
然而作为被倚靠的基础的练习,不是单纯的对于技法的训练。因为这不断重复的过程中,包含了画者的一些取舍和选择。如果仅仅是强调迅速有效地记录下形象、光影之类,则毫无意义——因为如果单纯的追求描摹对象,则没有比照片更好的手段。但写生虽然是记录素材,但绝非是单纯的记录素材——画者需要表现出对于对象的态度,以及对于这种态度的选择。所以这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写意的意味——你记录的是你的意,你的思索,虽然,因为缺乏思考的时间,也没有机会斟酌太多。
但是这种缺乏斟酌并不一定是坏事。当无限的选择环绕在你的周围,更多的,只会妨碍你的判断:“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创作或许是越单纯越好,因为直接,故而直指人心。沉溺于技法和对象的选择,虽然无法说是没有意义的行为,但是较多的机会,是最后模糊掉目标。
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当画者尝试重新回归到新的写意传统,对象的像与不像便不再具有强烈的重要性。画者所重视的细节与情绪成为主题,在未来的创作中,这些才是最具有价值的元素。所以过滤掉不会动心的要素与强调动心的要素,便是创作开始之前的一种预热。现在的写生之于国画家,其目的更多的是一种梳理。

彝族老人 180cm×45cm 2017年 罗小珊

走进湘西系列之一 46cm×70cm 罗小珊

走进湘西系列之二 46cm×70cm 罗小珊

走进湘西系列之三 46cm×70cm 罗小珊
你无需抗拒摄影术进步的优势,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记录下足够多的瞬间。但是也需要清楚,这种单纯记录的瞬间本身,是缺乏太多意义的——画家并非选择镜头来描绘世界,画笔和思考赋予的是一种超过真实的态度。胶片或者CCD只能写下如实的面孔,但绘画能够逾越这种界线,将无法反应的感情和思想呈现出来。
我们在写生上所投入的光阴,是我们浓缩对象感情的过程。在墨与纸的反复中,它堆积、沉淀,最后成为创作的基础——创作并非应对主题的堆砌,而是通过积累得到的升华——这依赖于对写生的重构,对世界的观察,对周遭的态度,以及,对自己的思考。
然而一切的开始,启于对所见之物的记录。
三、写心:真诚的自我表达
随着时代的进步,美术创作也不再局限于表现“特定题材,而是逐步扩展到更加全面、广阔的方向。于是,内容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技法,多元的选择会冲淡既有的陈规。人物画创作给予了画家在表现上更多的选择:能够更多带入自身感受与立场的方式,显然会改变创作的方式。
这种风气显然在最近的十数年中变得普遍而广泛:从一般题材到主题性创作,在符合传统意义上主旋律题材的内容,采用了完全不同于习惯性思维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思路的开阔所带来的各种方面的影响,包括更加强烈的感情的体现、笔墨的强调——在这里,笔墨作为中国画有别于西画的最为核心的根本,其无可辩驳的重要性与意义,在脱离掉写实的禁锢之后,获得了更多的表达机会。中国艺术的面目正出现前所未有的繁盛与多样,比其他诸如文学样式,都要丰富得多,得到更大的空间与更多的包容。
艺术家与所有文化人一样,所能做的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别人需要的精神产品,做得最好的则还可能影响世界——即使只是一丝一毫的改观。但这种改观只有发生在正向,才是有意义的。一切有助于人性生长、保持、弘扬的努力,都是正向的。今天的美术已非文人厢房中“独乐乐”的游戏,而是“美育代宗教”的标杆。所以,只有为普罗大众所接纳,方为正道——而这种接纳的前提,也就是作品的共鸣。
当大家都一窝蜂,甚至只是在形式上追摹所谓当代水墨的时尚时,我并不想说坚持传统就更有价值,尽管也许的确如此,特别愿意强调的是要忠于自己的内心的真诚。比写形更加重要的永远是写心,尤其当下,诸种现代技术的发展与成熟,使形似成为几乎唾手可得的东西,而准确与有特点地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与情绪,并经由画面把它传达给观者,依然是需要创造力的活计。
中国画的传统,强调气、格,强调作者以心中所思写目中所见,所以能获得更多学习的机会,更多静心思考的机会,更多以长远眼光看待未来的机会,这一切都弥足可贵。禅宗有言“南顿北渐”,然所有的顿悟,都积累于平日的修为和思索——艺术亦同,所有的突破都仰赖于平日的积累:不仅是美术,更包括心灵。
艺术家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更近于匠人,这里完全没有贬抑的意思,高超的手艺本来世间稀有且具独立的价值,另一类则富有创造性,更接近艺术的本义。对这类艺术家来说,创造的快乐是首要追求,远远大于仅仅卖出高价或因为从众而得到当下的承认。
越来越多的青年艺术家,已经认识到并正进入忠于内心的创作,不盲目跟风追求时尚,也不那么看重眼前利益,进入随心所欲的创作,像孔子说的那样:“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虽然“游于艺”的超然与洒脱看起来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郑重其事、认真严肃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实际上这是举重若轻。凡做大事业,没有这种超然的态度,寸步难行。
所以说起来也简单,就是两个字,写心。心与心总是相通的,精微或酣畅地表达了自己,也就是表达了别人。艺术的最高境界,亦即天意,是通过己心来达成的。上帝假借某个人的手笔来表述他的意思,一定是那只能够明白他胸臆,而且表达自如的手。达到这样的境界对社会无疑是表率,即便于个人,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

走进湘西系列之四 46cm×70cm 罗小珊

走进湘西系列之五 46cm×70cm 罗小珊

走进湘西系列之六 46cm×70cm 罗小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