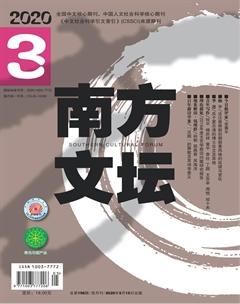不老的钱理群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长文《赤子佛心钱理群》。那次是钱老师让我写的,他的《我的精神自传》要在台湾出版了,出版社提出要一个导读。没想到,钱老师居然让我写这个导读,真是受宠若惊。那篇导读最后写成了“我读钱理群”,这其实也是学钱老师的。钱老师一辈子的学术工作主要是处理他与两个精神导师(鲁迅、毛泽东)之间的关系,“与鲁迅相遇”“我和共和国、毛泽东六十年”构成了他“心灵探寻”的主要历程。钱老师也是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最深的“精神导师”,像我这样的人,北大内外还有很多。这次又有幸写钱老师,我就接着往下写。
一
进入中年以后,我总想着应该多去看看几位老师,陪伴一下他们的晚年,虽然事实上没做到。中年是什么感觉呢?有一句话让我刻骨铭心,就是早晨一醒来,发现周围都是靠你的人,却难得有你可以靠的人。但我觉得,有几个老师还是可以在精神上靠一靠的,虽然他们有的已经连路都走不动了。去看他们,也是上最后一门必修课:学习如何面对老、病、死。
钱老师自从2002年退休以来,在写作上进入了井喷期。然而,近几年来,他的生活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折,一次是2015年夏季搬进养老院,一次是2019年夏季师母崔老师的离世。
钱老师进养老院的新闻最早好像是温儒敏老师在微博里爆出来的,一下引起不小的新闻效应,大家的联想都是“知识分子晚景凄凉”什么的。我和几个闺蜜也赶快跑去看钱老师,结果完全和想象的不一样。这家叫泰康·燕园的养老院确实很超前,像一家五星级酒店。钱老师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参观,钢琴大厅,各种小教室,游泳馆,健身房……吃过午饭后,我们在一个室外的露台坐下聊天。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好,微风吹过四周的绿植,感觉像在欧洲。钱老师上一个居所叫枫丹白露,也是欧洲范儿的。我问钱老师:“您很喜欢这里吧?”钱老师笑眯眯地点点头说:“这里洋气。”然后,又说:“崔老师定的。”
崔老师定的。钱老师的一切,除了学术的事情,什么不是崔老师定的呢?崔老师是钱老师生活的“底”,是定海神针。
我以前只知道崔老师是上海人,好医生,后来看了崔老师临终前编的文集《我的深情为你守候——崔可忻纪念集》才知道,崔老师竟是这样的大家闺秀!她和钱老师可真算门当户对,都出身于学术世家,父辈都做过民国的高官,他们从小都受过最好的西式教育(崔老师读了六年的中西女中是宋氏三姐妹的母校),毕业于最好的大学(崔老师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钱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并且又都在1960年大学毕业时,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按崔老师的话说,“一个跟头翻到了最底层”。然而,他们却完全没有“最后的贵族”式的哀怨,而是立刻投入了基层教育的事业。临终之际,崔老师说,在贵州那二十五年,是她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日子,培养了两千多名学生,治好的患儿(崔老师是儿科医生)不计其数。这些实实在在的成果,比她后来(1984年)调到北京后的“高大上”工作有意思得多。“我虽不是基督教徒,却好像在按照上帝的旨意在做奉献。我不是党员,却在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崔老师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钱老师经常谈起崔老师,有两句话令我印象最深。一个是在结婚前(“文革”尾声时期),崔老师答应了他一个十分苛刻的条件,就是要随时准备他可能进监狱。另一句是,钱老师说,崔老师在任何时候都能让“一切如常”,“事态越是严峻危险,家庭气氛越是宽松平静”。在他们两人调侃时,我甚至听到过这样的话,崔老师唠叨钱老师生活能力差,说他在自己这里享受的是“子女待遇”,钱老师立即自己补充说“是独生子女”。在献给崔老师的著作《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的后记中,钱老师写到:“她是我生活中永远不倒的树。”如今这棵树倒了,钱老师该怎么办呢?
我见到崔老师时已经比较晚了,她在病床上已经躺了好几个月。2018年10月底,崔老师在发现病兆后,自己判断是胰腺癌。在经过几个医院的检查、确诊后,和钱老师不需商量就共同决定:放弃治疗,住进养老院内部医院,不求延长生命时间,只是减少疼痛,维护生命最后的尊严。然后,崔老师高效地处理了一系列事:家里的事、钱老师以后生活的事、自己的后事,包括最后的告别仪式和灵车上的音乐(用的是崔老师自己唱的歌),都一一安排妥当。一切尽善尽美。
在生死大限之际,崔老师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和大能,令所有人叹为观止。然而,这样的冷静决绝却不意带来另外一种格外熬人的痛苦,就是通向终点的那条路太笔直、太单调了,没有一个岔口,没有一点波澜,没有一丝可以混同为希望的虚妄。我去看过两次崔老师,每次都不知说点什么好。崔老师这时已经瘦成一把骨头了,几个月不吃不喝,就靠營养液维持,但依然很清醒。她和我们聊天时,倒是一切如常,包括她抱怨“这也太不人道了,拖这么长时间,也不昏迷”,声调语气也依旧如常。不知道在没有亲朋来探访的时候,只是钱老师一个人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呢?他们会说些什么呢?或许什么都不说吧。这时钱老师自己也查出癌症(其实是钱老师先查出癌症的,但是早期,可治),对于两个看淡生死的强大灵魂来说,阴阳之界可能已经不是什么蹚不过去的河。死神陪着他们熬了半年,也成了老熟人了吧。
我们都担心,钱老师能挺过去吗?最让人担心的是,在此之前,他说,最想写的东西,已经写完了。钱老师的家族有癌症病史,所以,这些年,他都是在和时间赛跑。我记得有一次他说:“我有时真怕最想写的东西写完了,那我该怎么办?”我说:“那您慢点写。”“那我死了,我想写的东西还没写完怎么办?”写作是钱老师存在的方式,如果最想写的东西写完了,还有什么能把他留下来?
不过,事实证明,钱老师的生命力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在崔老师的告别仪式上,那么多人痛哭,我看到钱老师没有哭。我拥抱他,他的回抱也很有力。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接受一切的坦然。送走崔老师不久后,钱老师说,他要去贵州住一段时间。贵州,已经成为他真正的故乡,他栖息将养的地方,那里的学生和朋友于他也更是亲人。从贵州回来以后,我感觉钱老师“又回来了”。去他家里聊天,一切和从前一样。满屋都是崔老师的照片,好像崔老师没有走一样。一切如常。
二
我一直在想,钱老师走的这条面对老病死的路,一般人走得了吗?我觉得走不了,反正我不行。这不仅因为他的精神力太强大了,更在于他的关注点不在自己身上,而在于超越一己之私的价值感和使命感,这就把通常针对个体生命的病魔给“晒”在一边了。
钱老师其实患有几种很严重的病,前列腺癌、糖尿病、高血脂,任何一种都能够把人“拿住”。但钱老师说他“没有感觉”,反正就是三个月打一次针,有时候连糖块都照吃。但如果不在“精神燃烧”的状态里,他也就不行了。他说,有一次他和老同学在宁波聚会,比较无所事事。结果一早起来就打盹打呵欠,精神萎靡。“那就是老年的钱理群!”说这话时,钱老师已经年近八十了。
钱老师确实不老。岂止是不老,他旺盛的工作精力对年轻人来讲,简直是一种羞辱。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是2012年9月那次,钱老师来我家里和学生们聊天。从早晨十点一直到晚上七点,整整九个小时,基本是钱老師一个人在说话。中间还去吃了一次午饭,也主要是钱老师在说话。晚上七点的时候,我接师母指令送钱老师回家,钱老师还说“我不累”,我说“我们累了”。第二天,我果然起不来了。躺到快中午,突然一个激灵,赶紧给钱老师打电话,问他身体怎么样。钱老师说,没事啊,我已经写了三千字了。我说,好吧,您不仅在精神上,也在身体上,摧毁了我们。
钱老师是1939年出生的,上研究生的时候已经三十九岁。据洪子诚老师统计,从1988年出版《心灵的探寻》开始,至2020年1月20日,钱老师出版的著作达九十部,编纂六十五种;这还不算有的论著修订后的多次再版的。洪老师说:“之所以标出准确的截止日期,是时间对他来说很重要,况且他还有多个写作计划(多部的三部曲)在进行中,说不定哪一天又有新作问世。”我记得前两年,钱老师就得意扬扬地告诉我,他已经写了二千多万字了,在上课、讲座、聊天的同时,平均每天两千字。我说:“您可以做网络作家了。”
钱老师不看网络小说,但对通俗文学一直持很开放的心态。我还记得我大四的时候,钱老师在课上说,他虽然不懂武侠小说,但如果有谁想写研究武侠小说的毕业论文找不到指导老师的话,可以找他。钱老师的这句话相当鼓励我,十年前我在北大开网络文学课的时候,所有选课的同学都比我懂得多,我就拿钱老师这句话当旗号。
后来当听到我说鲁迅在网络作家中的影响力很广很深的时候,钱老师高兴极了。在一篇题为《鲁迅杂文》①的论文里,谈到鲁迅杂文与现代报刊传媒的关系时,钱老师甚至说,鲁迅是网络写作的先驱,“其实,杂文很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网络文学,所以大家不要觉得鲁迅的文学很神秘,他的杂文就是今天的网络文学,只不过是发表在纸质上。我曾开玩笑说,大家不要小看网络文学,说不定网络文学作者中将来就会出现一个鲁迅”。
这句话经常被我扯来作为网络文学辩护的“大旗”,另一面“大旗”是钱老师的写作速度。平均“日更”两千,实际上经常是一天七八千字,写五六个小时(个别时候会达到八九个小时)。那可是在写思想史啊!当然,在正式发表以前,钱老师已经有了四十年的积累。即便如此,这个写作速度也是太惊人了!所以,写得快,并不一定就是注水,有的人就是才思敏捷。在师母的技术支持下,钱老师很早就“换笔”了,因为,只有电脑速度才匹配他的思维速度。
其实,我也一直搞不懂,钱老师怎么能写得这么快?我猜想,有一点,钱老师是与网络作者(尤其是那些“用爱发电”的非商业写作作者)相通的,就是他们的写作,本质上都是“欲望写作”。在钱老师这里,所有的写作都是真心想写的,没有一件是“活计”或“苦役”。事实上,在上研究生时,他的导师王瑶先生一直是“压着他”的,让他不要着急发表。一旦开了闸门,就是喷薄而出。钱老师本来起点就高,又极度自信,所以,他的写作过程只是自然上升,没有刻意提高。写作对于他,一直是畅快并easy的,既没有心理门槛,也没有“规范”束缚,从心所欲,驰骋无忌。尤其是退休以后,更是进入完全自由的状态。这种自由,甚至包括文体的自由。他现在最喜欢用的“讲述体”(以历史叙述、讲故事为主,包括历史细节,在此过程中表达自己观点),是他自己独创的,和他讲课、聊天的风格是一路的。写作对于他是一种很high的沉浸状态,是身心喜悦的自我实现。也只有这种high的写作,才能四十年如一日,浩浩汤汤,奔流不息。
三
1998年,钱老师向学生们提出“沉潜十年”,这主要是对70后、80后学生说的,钱老师对他们寄予厚望,认为他们在知识结构和精神基础上都要优于他所属的30后,以及40后、50后、60后,希望他们“潜到自我生命的最深处,历史的最深处,学术的最深处”,拿出些“大东西”来。
然而,十年后,在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时,钱老师却发表了一篇题为《寻找失去的大学精神》的文章。在这里,他激愤地指出,现在的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情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的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最大限度地维护“一己的利益”,这已经成为“他们的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钱老师再一次感叹,这是自己“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的弱点的一个大暴露”,“种下龙种,收获了跳蚤”。
在以后的十几年中,“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成了一个流传越来越广的社会流行词。其实,岂止70后、80后?我们每一代人中都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都有“精致”的部分,甚至特别“精致”的时刻。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钱老师确实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但我发觉,近年来,他的理想主义越来越低调。他总是说“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好人联合起来做好事”,好事的成效哪怕是小数点零点零零零几,“只要是正数就可以”。这种个人的、理性的理想主义,确实是更有操作性。
2017年的春天,我带着新一批学生去看钱老师。钱老师说,对于学生辈,尤其是我们这些80年代在北大上本科的60后学生,他最基本的期望是,“凭兴趣做学问,凭良知做人,组织一个学术共同体”。我当时脱口而出:“我都做到了!”当着自己的学生,确实很得意。
最让我得意的是,我并不知道钱老师有这样的期望,做到这些是自自然然的。我想,只要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做到这些应该不是很难吧?这并不需要勇敢,只需要一定的诚恳,而且是对自己的诚恳——其实,也就是对自己好一些,比较的“胸无大志”。相反,我觉得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价值模式和心理模式倒更惯性延续了传统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模式——为了更长远的利益,牺牲当下的利益——只是在“终极价值”的位置上,用个人价值替代了公共价值。人如果一辈子“毫不利人,专门利己”,应该很难幸福吧?而且难免要做狗的吧?
钱老师确实是喜欢年轻人,这些年我不断带学生去见他,最年轻的一拨已经有1994年出生的了。他总是能吸引他们。一般人想和年轻人打成一片,需要去靠近他们的文化(比如我),但钱老师不是,他就是凭他自己的东西吸引年轻人。大概是因为,钱老师的“赤子之心”和年轻人的心是天然相通的。
有一件事是钱老师说什么也想不到的。现在的年轻人普遍“爱无力”,尤其跟我做网络文学研究的学生,大都生活在“二次元”。她们可以“饭爱豆”,“磕CP”,爱“纸片人”,就是不愿意在现实生活中谈恋爱。然而,有一次和钱老师聊回来,有个同学说:“要是现实生活中有钱老师这样的人,我是想谈恋爱的。”这真吓了我一跳!因为在我们的眼里,钱老师一直是一个“超性别的存在”,一个“精神性的存在”。看来,只有强大的“精神原力”,才可以穿越次元之壁。
等“疫情”结束了,我想带学生们经常去看看钱老师——“带你们去见钱老师”也是我给学生的“特别福利”——让学生们多从钱老师这里借一点“精神原力”,也请钱老师把他那些“写给未来的书”提前给我们讲一讲。“相信未来”的钱老师是永远不会老的。
这个不老的钱理群,也将是不死的钱理群。■
2020年2月27日
【注释】
①钱理群:《鲁迅杂文》,《南方文坛》2015年第4期。
(邵燕君,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