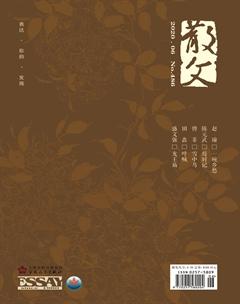塾学往事
刘南陔
一
1947年(当时纪年作民国三十六年),我满六岁,进私塾读书。农家四季皆忙,冬季稍闲些,孩子们去读书识字,所以有人把私塾称“冬学”。教书先生要求也不高,能招呼鼻涕佬就行,私塾先生也被称为“冬烘先生”,是否还有其他含义,不得而知。
蒙师叫叶朝芳,人称“朝芳妈妈”。男人被称为“妈妈”,意在讽刺说话哕唆、办事迂腐,不过也有些许褒揚的成分,如和蔼可亲、待人诚实等。既为蒙师,也不好过多议论。
我进蒙馆是先生主动要去的。那天,我跟着同垮的幺叔去学堂玩,先生见我穿着干净,说话清楚,写了几个字教我念,发现我读音还准,就带信给父亲叫我去上学。父亲有点清高,知道朝芳妈妈的底细,又不好意思回绝,便让伯父带我去了。父亲没打算让我在那里读多久,学名也没让起,写在书本上的是小名“刘金山”。
发蒙倌子都一样,先从描红开起。先生用红笔写下“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几个字,然后教认、教读、教握笔、教笔顺,再回到座位上去读、去描红。这几个字写会了,再往下写。至于字义,先生没教学生也不懂,读书就是认字,字认会就行了。
学堂后边有个大竹园,虽没有周树人家的“百草园”出名,但肯定比他家的园子大。树木高过房顶,桂竹有益子口粗,水竹密不透风。先生家两条大黄狗特厉害,学生娃初来,需要熟人带领,跟狗混熟了,才不会咬你。有一天,那两条大黄狗对着园圃不停地叫,垮里人以为来贼了,大着胆走到园子边去看,发现是一只好大好大的野物,便回来报告说:不得了,园里有老虎!消息很快传开了。乡公所知道了,派枪兵来打击。我们家乡是岗地,山林岩洞在城北,相距一百多里,老虎怎么跑到城南来了,一直是个谜。庆幸的是,我上学没碰着,如果是那样,后面的故事也许就没了。中午时分,先生紧闭大门,把小窗户也用木板堵起来,叫我们一个个趴在桌子上,不要外出,小心枪子误伤。躲了半个时辰,听到几声枪响。又躲了半个时辰,外面有动静了,先生出去看了回来说:老虎被打死抬到集上去了。天色已晚,这才放学让我们回家。
第二天父亲从集上带回一块骨头,说是虎骨,可以泡酒喝。骨头上有血渍,我很害怕,看都不敢看。再后来才知道,其实并不是老虎,是一只金钱豹。不管是虎是豹,反正都是死在大黄狗名下,印证了《增广贤文》的那句“虎落平阳被犬欺”。
二
过了年,父亲把我送到祠堂垮亚强先生学里去读书。据说亚强先生是我们刘姓最有学问的人,他与父亲同辈,见了面应当称大伯。
祠堂垮离我家有两三里路,要翻过两道岗穿越一条冲。祠堂粉墙黛瓦,石磴圆圆的,门槛高高的,漆黑的大门紧闭着。垮里人家也是隔门宝壁,隆向大瓦屋。学屋在亚强先生的厢房里,东西两间。圣人像悬挂在东厢房书案上方,很高大,很威严。亚强先生端坐在书案左边的太师椅上,穿着长袍子,戴着小毡帽,留着小胡须,也很高大,很威严。父亲给圣人上香后,命我向先生行礼下拜。然后先生给我起学名,说:这“南陔”二字是叫你长大后好好孝敬父母,那样子柴集南边的半条街都是你的。家乡人说话,“街”与“陔”不分,先生的话我听不明白,读书不多的父亲也未必清楚。
桌凳需要自备。先生看我离学堂远,又是远房侄子,就找来一套旧的给我坐。不过有点高,要扒在桌子上,两条腿悬在凳子半空。学生娃嘛,就这样也很满足。
课本也需要自备。一本书往往爷爷读了爸爸读、爸爸读了儿子读,所以要十分爱惜,不得损坏。我读的是《国文》,父亲说是托集上的干爹去沙市打货时代购的。有点小得意的是,同学们中数我的课本最新。
亚强先生打人比较厉害,用手指拐敲学生的头。学生头疼先生手指拐估计也不好受,后来他就发明了一个狼牙棒样的东西,拿那家伙敲,学生疼先生不疼。不过我常常受到他的优待,因为我背书很少打阻隔,即使背不出来也只用手揪揪耳朵。先生打人还是很有分寸的。
最快乐的时光是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前垮后垮的学生有七八个。一路上,我们在田埂边抽茅草簪,摘端阳泡;在园圃旁折月季蕻,偷糖梨子。很是开心。私塾没有课表作息时间表,无所谓迟到早退,只有一个硬指标:那就是到校后要“收书”,即向先生背诵前日上的课文。能背出来就万事大吉。
路上也有烦恼,同路的大学生喜欢欺负小学生。小学生要带零食给大学生吃,求得庇护,不然他们会捉弄你。在先生收书的时候故意打岔,分散你的注意力,让你结结巴巴地背不上来,吃先生的狼牙棒。
我还不止一次看大学生们打架,打得泥里水里的。小学生只能站在远处偷看,不能笑。笑了,打败仗的,会回过头来对付你,那力气绰绰有余。
我在亚强先生学里读了将近两年,《国文》八册包本,即从第一册第一课背到第八册最后一课。《百家姓》的大字好像也写到了“井段富巫,乌焦巴弓”。长大懂事后,只记得《国文》开头的几句“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百家姓》也只记得开头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其余的统统交还给先生了。
三
1949年,我八岁。襄河发大水,河东的人逃到了河西。有个姓刘的灾民来我家弹棉花,说他原是教书先生,学屋被水冲走了,学生娃逃荒了,这才出来做点小手艺,为一家老小挣口饭吃。父亲看他衣着打扮言谈举止与其他灾民不一样,就留在垮子北头草房子里住。父亲早就考虑祠堂垮太远,我上学越冲过岭不安全,想换个先生,这下不找上门来了。于是这位灾民成了我的第三任先生。不过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敢问。
出于这种身份与背景,先生当然不敢得罪我,也不愿意得罪其他学生。他做了一把竹签,很长,起初我以为是用来打人的,后来才知道那是一把“尿签”,谁要上茅厕,就带上它,这样有个先后次序,免得撞车。
先生是灾民,根本提供不了课本。不过他有办法,就教我们学珠算。先是“三遍还原”,也就是“见子打子”,算盘装上“123456789”,有口诀的,比如“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等等,每位上是什么数就加什么数,三遍之后如果口诀没念错,珠子没拨错,盘式就变为987654321,就OK了!再学“七遍还原”,那是每遍都加“123456789”,七遍之后盘式变为987654321,非常有趣。再后来学减法,也有“三遍还原”与“七遍还原”两种,不过最初盘式为“987654321”。还有乘法、除法,什么“破头乘”“留头乘”等等,够整十天半月的。
后来父亲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本《修身》,也是分册的,讲修身养性一类的知识,大抵与后来的自然常识课本差不多,也是一句也记不清了。而灾民先生教的珠算我记忆深刻,并在后来为单位管理财务账目时受益匪浅。
四
1950年,我去王家垮科之先生学里上学。
科之先生戴眼镜,说话斯文,写字时手不停地发颤,字写得歪歪扭扭。不过他读书很好听,大有寿镜吾老先生念“铁如意”时把头拗过去、再拗过去的味道。我在他学里读的是《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先生领着读,我也摇头晃脑跟着读,这样形成的习惯后来读中学时都难以改变,常常引得同班捧腹大笑。《诗经》只读了前面几章,又换成《论语》。《论语》只开了个头,科之先生的私塾就停办了。
科之先生住在集上,与学屋有二里之遥,一般来说他会赶来收早书的,也有来迟的时候。来迟了,那几个大学生会帮助收书。小学生要是背不上来,他们可以打。先生授权了的,没办法。收完书要是先生还没来,大学生就会玩“请先生”的游戏,这是一种类似占卜的活动。把两块砚盘滴上几滴浓墨水,然后合起来,由领头的捧着拜孔夫子,其他人毕恭毕敬跪在后面。拜完,再打开砚盘,看墨滴形成的图画,分析先生这会儿走到了什么地方。还真灵验呢!不过有一次,我们刚摆好架势,先生就进门了,大家迅速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学堂快解散的前几天,科之先生叫为头的大学生把我们带到秦屋场参加大会。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禾场上用方桌木板搭起高台,台上用杉木条扎起架子,架子上拉起大幅标语。人也很多,每人手里拿着纸做的小彩旗。亚强先生学里的学生来了,还有许多私塾里的学生也来了。学生们个子小,挤不进禾场去,站在屋山头观看。谁开的会,谁讲的话,都不知道,唯一留下的印象是在大会开始前有人教唱歌,因为这是我平生学唱的第一支歌:“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长大后才知道,歌名是《全世界人民团结紧》,前几句是这样的:“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国兵呀……”
五
秦屋场开会后不久,柴集公办小学成立了,父亲带我去报名。我向接待的先生行鞠躬礼,那先生说:“你今后称我们为老师,见了面不必行礼,问声‘老师好就行!”他问我读了几年书,读了些什么书。我一一作答。后来,老师把我分到四年级,说:能不能跟得上,就看你的啦!
公办学校与私塾最大的区别是:私塾先生坐着讲学生站着听,公办学校先生站着讲学生坐着听,起初很不习惯,觉得这样对老师很不礼貌。还有上课下课的规矩,不像私塾只有上茅厕才有出去玩玩的机会。老师也很多,我在柴集读了三年,老师都没认全。
不过有一位老师我记得非常清楚。
他姓吴,个子不高,是个歪嘴巴,歪得特别厉害。他教我们音乐,教“三只老虎”时边唱边跳,加上他的歪嘴巴,十分好笑。
他是我们学校唯一能把煤汽灯——即烧煤油的汽灯——點燃的师傅。那时候,学校经常搞演出,演《小放牛》《兄妹开荒》之类的小剧目,我也扮过角色,上过舞台。有一次学校演戏,煤汽灯突然灭了,吴老师上来边修边说,又唱又跳,硬是没让戏台子冷场,台下的观众一个劲儿地鼓掌。从此我们对他刮目相看。班主任告诉我们:吴老师是大城市来的人,在表演皮黄戏呢!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是在说单口相声。
也有让我尴尬的事发生。有一次,我“红庚八字”的父亲给她送来油条,顺便交代给“山儿”几根。旧社会农村有“纳八字”的习俗,就是定娃娃亲,这“红庚八字”就是未来的媳妇。私塾并入公办学校时,我读四年级,“红庚八字”读三年级。我整天藏着躲着,生怕碰上她的面。这下倒好,下课后,三年级四年级的男同学女同学争着跑出来,看看“山儿”到底长什么样?真叫我无地自容。好在“红庚八字”没上他们的当。不幸的是,“红庚八字”读五年级时夭折了,才没有更多的故事发生。
1952年土地改革后,由于家庭变故,我失学了。学校来了两位老师,对父亲说:你不能耽误孩子的前程呀!贫雇农、地富农的子女都是国家的未来,我们老师也不会歧视任何一个学生的。不久,我复学了。读六年级时,还当上了学生会主席。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