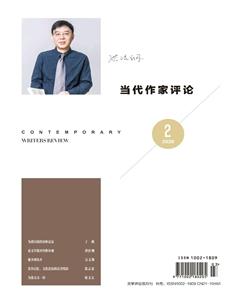“70后”女作家“自我”书写中的主体探寻
张瑷 沈芬
新世纪以来,“70后”女作家的创作表现出多样化的新态势,她们在描写日常生活的表象之下,更注重对女性个体生命体验的独特传达,其文本中的“自我”镜像,折射出这一代女性心理与情感的波动状态。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发展演变的历程中,可以看到“70后”女作家主体诉求的新向度,她们风格各异的创作丰富了女性文学的探索经验,并以此奠定了文学史价值。
一、代际视阈下“70后”女作家的创作态势
“70后”出生的这代人,其成长背景缺失“50后”“60后”曾拥有的“广阔天地”,与宏大历史相对隔膜,20世纪80年代各种思想文化热潮,或许在她们的精神空间投射了些许人文之光。90年代以后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盛行,认同庸常、躲避崇高等观念,具有较强的社会渗透力,这代人突然处在“社会转型的断裂处”,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关于“七十年代人”的对话》,《南方文坛》1998年第6期。一方面心底的理想没有彻底消解,另一方面也在流行文化影响下难免媚俗。
因此,“70后”作家群体虽然缺乏一致的文学追求,但她们在特定的社会环境、时代氛围和文化生态中,自然形成某些相似的文学代际特征。初登文坛之时,由于缺乏丰富的生活积累,她们不擅长对历史、时代进行宏大叙事,也不刻意标榜各种“主义”或“实验”,大多沉迷于个人生活、欲望、话语的书写。相对于“80后”,她们又没有彻底抛弃一些传统文学观,在各类炫酷写作面前显得落伍滞后。新世纪后,“70后”迈向而立之年,這是创作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她们获得了一定的人生体验,创作视野逐步拓宽,开始关注现实社会和底层民众的生活,传达出个人对时代的思考。
“70后”女作家的最初出场有被“炒作”之嫌,一些刊物、出版社有意营造“美女作家”阵容,卫慧、棉棉等一度声名大噪。之后,她们逐渐分化,一部分迎合市场写所谓“好看的小说”,而另一部分以创作实绩修正文学界对她们的偏见,逐步显现出不可忽略的影响力,后者包括鲁敏、魏微、付秀莹、戴来、乔叶、朱文颖、金仁顺、盛可以等。她们以平和冷静而又不失敏锐的眼光,审视社会转型剧变时期女性更为复杂的现实处境和精神困境,同时也理性探寻自我主体的存在本质与嬗变轨迹。
二、“自我”的多面镜像
“70后”女作家小说中各类相似或不同的女性形象,都可以视之为自我观照的镜像,正如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者佳迪娜所说:“女性作家经常利用自身的文本,尤其是那些描写女性主角的文本,作为自我界定的一种过程。”见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Ⅱ》,第9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一)“恋父情结”中分裂的“自我”
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对父亲产生一种特殊的崇拜和依恋,这是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但是有些女孩在其长大后不能淡化这种情结,甚至将其转移到她的婚恋对象身上,形成心理暗疾,就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自我人格的健全发展。
恋父情结的文学书写,多和女作家童年时期父爱缺失的创伤记忆有关。鲁敏的整个童年时期,父亲对她的态度都是冷漠疏远的;庆山在文本中一再表现童年时期的“我”与父亲的疏离、对抗,以及由此带来的情感缺失、自卑空虚。
在女性心理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中,父亲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他是那广大、艰难和不可思议的冒险世界的化身,是超越的象征,是上帝”,因此,父亲对女儿的态度、和女儿的相处模式影响着女儿自我的确认,“如果父亲对女儿表示喜爱,她会觉得她的生存得到了极雄辩的证明……她会实现自我并受到崇拜。……如果女儿没有得到父爱,她以后可能会永远觉得自己是有罪的,该受罚的;或者,她可能会到别的地方寻求对自己的评价”。 ④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全译本Ⅱ),第331-332、332页,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所以,过早失去父亲或成长时期不曾受到父亲关爱的女性反而更容易产生恋父情结。庆山的《彼岸花》中,南生童年丧父,而后只有后妈的儿子和平给予她照顾,于是她至死不渝地爱上了和平。在鲁敏的小说中,晓蓝多次对弟弟回忆逝去的父亲在她心中的理想形象,在追忆中弥补缺爱的苦痛(《六人晚餐》);忆宁从出生到15岁,和父亲相处的日子合算起来不到一年,而在父亲突然死后,他遗留的两本日记却成为她体察内心成长、观照自我情感的私密空间(《白围脖》);丧父的王蔷一心想找一个像父亲那样的男人,当她遇到老温时,年长男人的气息令她沉迷,她甚至直接喊他“老爹”,在这种非常态的爱恋关系中索取安全感(《墙上的父亲》)。
恋父情结中寄托了女性对自我重塑的愿景,是女性弥补主体缺失的书写。所以,“父型”恋人可能成为她的精神模板,引导她完成自我成长,但同时,在“父型”恋人的男权意识与文化心理覆盖下,女性的真实自我被遮蔽,一旦恋父情结被打碎,脆弱自卑的女性就无所适从,陷入绝境。《莲花》中的苏内河,一直渴望“找到一个感情角色来代替从未出现过的父亲”,死心塌地跟着老师私奔,“期许粉身碎骨地燃烧,以此完成自我”。安妮宝贝:《莲花》,第91、65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三个月后男人厌倦回归,向领导认错,求妻儿原谅,而被抛弃的苏内河进了精神病院。建立于恋父情结上的两性关系是一种失衡的、畸形的关系,结局不可避免陷入悲剧,失衡的两性关系也不可能治愈女性内在的创伤。当恋父情结内化成女性的情感归属,就会导致她们“对主体的彻底放弃,在顺从和崇拜中,心甘情愿地变成客体”。④女性完全服从父权的秩序力量,认同自己的客体位置,这是极为可悲的,恋父情结实质是囚禁自我的“死结”。女作家们在感性书写中不乏理性的审视与反省,揭示了自我认识的艰难与矛盾。
(二)“姐妹情谊”中残缺、重塑的“自我”
“姐妹情谊”作为西方女权主义批评术语,指的是“女性间息息相关的意识与体验,是通过女性中心的视角及对女性的定义而产生的对自身的认同及肯定”。谭兢嫦:《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第291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在“70后”女作家文本中,姐妹之间也构成女性彼此反观的镜像。
姐妹情谊一般建立于个性的互补与吸引,或是缘于“受伤者”需要互相慰藉救助。从女性主义宏观视野看,是女性共同反抗父权制而产生的情义,也在理念和行为范畴形成互助联盟。然而,她们互相吸引的依恋、援助的义气以及共同坚守的联盟却恰恰因为“男人”和“男性价值中心”而破碎崩离。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2期 《七月与安生》建构了一座供奉姐妹情谊的神庙,最终却成虚假的幻象。七月是生长在温情家庭的善良女孩,安生则亲情缺失,内心孤独,叛逆不羁。七月怜惜安生,总想把自己拥有的拿出来和她分享,但她没有想到安生“分享”了她的男友,七月被动地等待男友的抉择,男友在纠结中回到七月身边和她结婚,而怀了孩子的安生离散海外,贫病交加。七月知情后召唤安生回来住在自己家里细心照料,安生死于难产后,七月和丈夫抚养她的女儿,过着平淡的生活。这个文本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七月和安生为了一个孱弱寡情、缺乏责任的男人反目,又因为爱他而修补姐妹情谊。无论作者如何粉饰,失去个人尊严的“情谊”是丑陋的,人性也是扭曲的,在她们身上相互反观出残缺的、异化的自我,男人这面“镜子”照出姐妹两败俱伤的真相。
鲁敏《镜中姐妹》中的五姐妹,皆在他者的镜像中被塑造。父亲的视角下,她们是让他失望的女娃,作为有文化的小学教师,虽然他的男权思想不是那么嚣张,但是他内心的不满也常常溢于言表。母亲的视角一部分是与父亲重合的,另一部分是传统女性特有的,在她的“女儿经”中,只有寻觅个好夫婿才有好命运。小五既是观察父母立场而感知性别的多余人(超生女),又是冷眼审视姐姐们的悲剧而抗拒趋同的反叛者。大姐嫁了乘龙快婿,最后发现这个腐败官员已经出轨背叛她;热衷打扮、想要“多活点花样”的二姐挥霍青春,滥交男友坏了名声,最后嫁给低俗的暴发户,新婚之夜,男人竟然因为她还是处女半夜打电话给岳父报喜;双胞胎大双小双好得不分彼此,却因为爱上同一个男生酿出悲剧,小双以自杀成全大双,大双在痛苦折磨中草草嫁人去了西藏。在小五看来,姐姐们殊途同归的命运皆在“婚恋”之祸,所以她名校毕业后自立自强,真正从姐姐的镜像中认识了自我,重塑了自我。
依靠姐妹情谊建构对抗男权社会的“同盟”,固然有助于女性自我身份认同的强化,但是心理壁垒一旦形成又将限制女性精神的健全发展,在两难困境中如何开辟新的出口,正是“70后”女作家所期盼的终极之关怀。
(三)两性关系中博弈的“自我”
两性关系是贯穿文学创作的母题。在快速发展变化的当下,两性关系中的女性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现实处境,但也可以有更加多元化的选择。一方面,她们通过自身努力能够获得独立或强大的经济地位,开创广阔的人生空间和社会舞台,实现充分的自我认同和精神人格自由;另一方面,她们在男权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合谋下可能再度沦为被客体化的“他者”,反而在时代进步的过程中出现倒退甚至沦陷的悲剧。
伴随着时代的剧变,当代女性越来越向往独立与自由,在“70后”女作家的小说中,不少女性表现出婚姻观的超脱和淡漠。比如《二三事》里良生和盈年同居多年却不在意婚姻契约;《彼岸花》中“我”与邻居男人Ben闪婚,没有准备,没有仪式,结婚后Ben可以晚上去酒吧“泡妞”,“我”正常看书写作。这些女性与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有着很大不同,她们自觉疏离男权意识下的性别规约,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女性角色的僭越。
然而,划开婚恋或非婚恋的两性关系表象,也总会裸露出女性种种新的困境。历史上女性在两性关系中一直是作为夫权控制、支配的客体对象,随着女性意识的增强和女性经济的独立,两性关系沿袭的主客体(控制者与被控制者)表层结构模式出现了瓦解甚至顛覆,但内部文化心理与主体精神却难以逆转,形成错位或悖论式关系。乔叶的《失语症》是婚恋新状态下两性关系失范的真实反映。小学老师尤优抛弃恋人程意,选择官场新贵李确结婚,她把李确作为改变自身社会地位和获取优越生活条件的手段,然而婚后的尤优被定位为官太太,李确把她作为辅佐他升官的手段。他们都试图以主体姿态将对方客体化,利用对方的价值来实现自我价值,如此功利化的婚姻必然走向末路。尤优不堪在丈夫划定的“利益场”和感情的坟墓中丧失自我,但她与程意旧情复燃的婚外偷情中,依然也不能排除利用爱情的卑劣动机,“她以和他做爱来回报他为自己做事……她是想要以对不起李确的形式来抵达抛弃李确的实质”。乔叶:《失语症》,《打火机》,第165页,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李确因为一场车祸得了失语症,而尤优则在自我突围与自我审判的悖论情境中“失语”,她心中回响不绝的“离婚”之声,也只能湮灭于“失语症”。
魏微的《情感一种》诠释了非婚恋两性关系中的“主体”博弈和女性的自我沉浮历程。研究生栀子毕业之前是品学兼优的乖女孩,有美好的前途可待,父亲的病逝突然让她强烈地意识到安全感的消失,她需要“绝对的经济和物质”,在找工作焦头烂额之时认识了报社副总潘先生,栀子一开始就明白与这个男人可能会发生的故事,但在她的新新观念中,“身体”不重要,和哪个男人做爱都是做爱,不但为了快乐,更重要的还能得到利益。她如此宽慰自己,并以在心理和精神层面“她与他隔得很远,他们是不相干的人”为自我开脱,似乎坚守了自我“主体”。然而潘先生对栀子身体“性感”的评价、对她“放荡”的定位、轻浮且霸道的调情方式,都一再表明他不关心她的精神,不在意她的价值,栀子内心的“平衡”最终被打破,“在这场游戏里……她失去了尊严,主动权,信念……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失去了她的身体”。魏微:《情感一种》,《魏微十三篇》,第27、57、31、56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栀子的遭遇再次证明,“真正的主体只有在主体间的交往活动中,即在主体与主体相互承认和尊重对方的主体身份时才可能存在”。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第21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魏微让栀子在自欺中清醒,重拾破碎的主体尊严,从被男人始乱终弃的老套中逃逸出来,以失败姿态完成了自我救赎。
三、女性主体探寻的新维度
在漫长的历史中,女性的真实身份是从属于父权的“第二性”,因此,“女权运动”的根本意义首先在于打破社会文化对女性的“卑贱”定位,确立女性的主体身份和精神尊严,如此才能够追求其他的平等权利。中国女性的主体意识觉醒始于社会历史变革的近代,在艰巨的现代转型与漫长的探索发展中,“她们”经历了反叛、抗争、革命、奋斗、救赎、追寻的百年磨砺。女性主体探索在“70后”女作家写作中承传,然而困境与困惑也在延伸,并折射出新的时代特征。
(一)“去社会化/向社会化”:双向的女性主体探寻
女性主体确立的前提是女性获得社会化的独立地位。从五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妇女解放的探索方向是“向社会化”的——挣脱封建枷锁,冲出传统牢笼,在社会中追求经济独立、人生价值、婚恋自由等,女性为自身的独立进行了披荆斩棘的斗争。但是早期的“时代新女性”一如丁玲笔下的莎菲,在严酷的现实中四处碰壁、孤独绝望,反叛的主体在生存困境和男权社会压迫下或湮灭或扭曲。新中国以来,女性勇立潮头,顶起“半边天”,其“向社会化”获得成功的同时也是丧失性别意识的过程。新时期张洁、张辛欣笔下的“女强人”试图追求男性占领的社会价值空间,然而女性“雄化”并不被男权意识渗透的社会心理所认同,所以在社会性别文化夹缝中实现的独立,必然付出婚姻失败的代价。
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各种女权主义思想有力促进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新发展。陈染、林白等女性主义作家大胆披露独属于女性的隐秘经验,试图以女性话语建构女性主体,但实现这一切的前提却是“去社会化”的“私人化”,她们文本中的自我几乎隔离于社会、人群之外,只在幽闭的私人空间“对镜独坐”“对自己诉说”。固然,这一对男权社会的隔绝姿态,是女性主体反抗性的选择,但也因此阻隔了女性“向社会化”的完成,失去了两性对话、互补、平衡的可能,女性主体建构依然困守于迷惘中。
“70后”女作家的写作打破“向社会化/去社会化”对抗或背离的状态,在双向维度中开辟自我空间,呈现了一种新的主体立场。
《莲花》这部小说标志着庆山告别安妮宝贝,刷新了言情写作带给文坛的媚俗印象。这部小说写了一个男人(纪善生)和两个女人(苏内何、庆昭)的故事,他们之间没有情欲性爱,也不刻意追求殊途同归的结局,但是他们彼此映照,展开对话,自我主体在此过程中辨认、质疑、拆解、否定、认同、建构。善生和庆昭都曾经是拼命“向社会化”奋斗的人,最后又毫不留恋地舍弃一切转向“去社会化”的自我寻找。善生从小聪明理性,出类拔萃,成年后拥有令人羡慕的事业、地位、财富、婚姻,但这种“社会化男性身份的认同”无法让荒芜的内心产生光和热;庆昭虽然自觉与社会机构保持距离,但作为曾经红极一时的作家,还是身不由己成了活在出版商、编辑指令下的“工作狂”,突然降临的癌症使她彻悟生命的本质意义。这两个陌路人在拉萨相遇后同行去墨脱,经过艰难险阻、生死考验完成了此生的神圣之旅,但他们真正的引领者是不在场的苏内河——一个由逃避社会转向另一种“向社会化”的“涅槃”者。这里所提出的另一种“社会”不是大众社会而是小众社会,即私人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小范围融合,社会关系相对简化单纯;其社会化目的与宏大抱负、责任、功名利禄无关,而是与个体的生命意义与价值观密切相连。内河经历过青春叛逆的残酷“破茧”,她被美术老师唾弃后堕胎、进精神病院,尊严被踩进烂泥里,背井离乡四海漂泊……她执拗地求索感情来填补内心的黑洞,“强烈地需要来自他人的认证”,而自我停止了“向社会化”的成长——没上过大学,没有人生目标,不求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唯一的朋友善生,从少年时代就可以同床而眠,“她具备引导他内心蠢蠢欲动的心灵的能力”,然而善生以她的堕落为耻,这注定了内河无法在“平等”的异性关系中获得情爱。后来她去西藏墨脱摄影,沉迷于神奇的大自然,出版了摄影集,绝境中的磨砺使她“抵达某种修行的实质”,开始了“清醒自觉”的生活——“还是必须要与世间产生联系”。她喜爱那些与世外隔绝的像野草野花自由生长的孩子,为他们留下支教,找到自我的存在意义,在一次护送学生回家的返途中被泥石流冲入江里遇难,但她的主体价值在另一种意义的“向社会化”探索中完成“涅槃”。小说最后让漂泊的庆昭定居于远离都市的大理开始新的人生,是否也在另一种“向社会化”中重建了自我主体?墨脱在古时候被称作“隐秘的莲花圣地”,正如作者所说:“莲花代表一种诞生,清除尘垢,在黑暗中趋向光。”安妮宝贝:《莲花》,第121、177、156、176、41、3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这正是此作的深邃寓意。
(二)“双性同体”:复合的女性主体诉求
心理学上的“双性同体”,指同一个个体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的人格特质。女权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则这样界定“双性同体”:“每个人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这种存在依据男女个人,其明显与坚决的程度是多种多样的,既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中一性。”〔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99页,黄晓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她强调辩证地理解两性之间的融合和差异。
庆山的作品中塑造了精神上双性同体的女性,这正是作家心中理想的女性。《春宴》中的“我”有时觉得“自己是一个男性和女性的综合体”,女主人公庆长在工作上表现出男性的拼搏精神,“发稿前在办公室里通宵无眠”,为了工作“走遍全国偏远省份”,她不抹香水,不热衷修饰,反而喜欢香烟、烈性酒、刺青,但她的审美又是女性化的,会在白色搪瓷杯里插上新鲜芍药。庆长在精神上既有男性的坚毅和坚韧,又有女性的细腻敏感,同时凸显出独一无二的个性,这一形象寄托了作者對当代女性的审美期待。
双性同体或许能够“穿透我们由来已久的防御,使我们意识到放弃刻板角色和行为模式的必要性”。王喆、马新:《国内外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双性同体”观念的研究述评》,《妇女研究论从》2017年第3期。乔叶在《打火机》中塑造的余真,原先是一个和男同学勾肩搭背、翻墙爬树、满口粗话的“假小子”,16岁那年不幸遭遇强暴,之后她将自己改造成安宁内向的女孩,通过将自己变得符合刻板角色和行为模式来为自己树起防御的盾牌,虽然她结婚生子家庭美满,事业也蒸蒸日上,但内心长期压抑,创伤难以愈合。后来她得到去北戴河休假的机会,到了休假中心发现门没开,于是一瞬间恢复“野性”,翻过铁门进去自己开了门,这个行为寓意着只有“穿透防御”才能够找到自我主体之门。作者让女主人公在北戴河与张厅长“玩火”,以此进一步“穿透防御”,释放本我,然而她有一个意识是清醒的,明白偷情“是对婚姻的羞辱,对丈夫的羞辱,是对自己的羞辱”,乔叶:《打火机》,第63页,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所以她不可能通过出轨逾越社会伦理规范的“角色”,并以此重新建构被强暴过的“主体”。一个被强暴过的女性最深的伤痕是“性别”——这是双性之间难以填平的鸿沟。双性同体这一女性主体的建构,既承载着女性追求自我健全人格的强烈意愿,又承受着男权文化的变异压迫与挑战。
(三)对抗“同质化”:悬置的女性主体重建
在现实人生中,女性常被平庸、世俗的日常生活笼罩,“本我”被压抑,并在社会异化中与生命原初那个真实自我渐行渐远,由此产生空虚、厌倦、绝望心理。鲁敏的长篇小说《奔月》,塑造了欲逃离俗世的小六,她深陷令人窒息的生活模式:
我与底楼这位主妇,或其他任一主妇,可以分饰A、B两角,交叉运行不同的家庭。我和她,都能够在对方床头找到睡衣,很快掌握不同型号的数字洗衣机,准确地从冰箱下层找到不够新鲜的冻带鱼扔到油锅里准备当天的晚饭。丈夫们也一样。鲁敏:《奔月》,第9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这种可复制性、可替代性模式,导致女性主体被“同质化”,女性自我独一无二的特性消失在具有规范性质的日常生活设定当中,重复机械的家务、刻板乏味的家庭生活和夫妻关系,使个体囿于普遍性角色。小六为反抗生活秩序赋予女性的功能,逃离南京到了乌鹊镇。
在乌鹊这个陌生的地理空间,小六发现她仍旧落入生活的窠臼,无法逃开原先的各种设定。人只要处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就必然要陷入相似或雷同的各种关系及其伦理范畴——小六在南京是父母的女儿,是丈夫的妻子,是某某的情人,是某某的同事……到乌鹊后依然被类似的关系纠缠,与她原来的生活在实质上并无不同,在精神世界中她也没有找到新的寄托。逃离不过是让女性主体的重建悬置在了更为迷惘的路上。
女性的主体建构是一个漫长艰巨的过程,之所以漫长艰巨,有现实社会的原因、历史条件的制约、时代文化的导引等,而女性自身的成长经历、知识结构、教育程度、个体情智等因素也都影响着她们自我发现和主体确立。“70后”女作家的主体探寻之路虽然不可避免有误区,有不确定性,但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她们留下了这一代人的行走风景和深深浅浅的履痕。“70后”女性小说作为不断嬗变的动态样本,已传递出更新我们审美观念的种种信息,必然也蕴含着推动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发展的宝贵契机。
【作者简介】张瑷,集美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沈芬,集美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周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