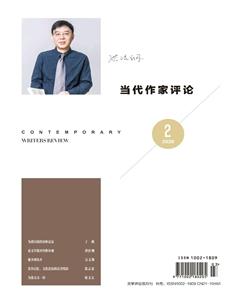观念的嬗变:重评1980年代关于内容与形式问题的讨论
一、讨论现场:要内容还是要形式
1980年代,由于对内容和形式的不同认识,致使文艺界在如何评价文艺作品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和争论。一部分论者认为,文学艺术的本体在于内容,内容决定形式,而形式只是辅助内容呈现的工具,他们将文艺界所涌现出来的种种形式和语言实验,看作是一种空洞的形式主义;而另一部分论者则认为,文学艺术的核心乃是语言和形式,这是文学艺术之所以成为文学艺术的关键所在,因此,各种形式和语言实验,不仅不是所谓的形式主义,恰恰相反,它们开拓和丰富了文学艺术的表达。当然,还有一部分论者认为,文学艺术的构成是内容与形式的相互作用和辩证统一。论争中,诸方各持己见,却也不免有偏颇之处,但是,其中一些论者对内容和形式的辨析,确实促进了文艺观念和创作方法的转型与革新,甚至可以纳入到世界文艺史范围内的内容与形式的论争之中。
新时期之初,一些文艺创作者和研究者就开始对内容决定论表示不满,认为内容决定论使文学艺术附加了太多的外在因素,而忽视了自身的审美价值,文学艺术形式变得越来越模式化和类型化,这不仅桎梏着创作主体的情思和想象,同时也阻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面临全面转型和改革,文艺界也在思想解放大潮的推动下开始清算诸多文艺问题,其中就包括内容决定论,要求和呼吁形式和技巧的革新,关注和重视文学艺术自身独立的审美价值。正是在这样的文艺和时代背景下,1980年代文艺界展开了持续数年的关于内容和形式的讨论。
早在1980年,李陀就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打破传统手法》一文,重新反思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1980年,在《文艺报》召开的一场讨论会上,他又明确地提出“文学形式的变革在文学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当前文学创新的焦点是形式问题”等观点。1981年,高行健出版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以下简称《初探》),专门探讨小说技巧,其中包括语言、结构、形式等。在这本书中,高行健否定了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往往将对文学的研究等同于对政治的研究,同时呼吁文学艺术形式走向审美独立。他认为,“艺术技巧虽然派生于文学流派的美学思想,一旦出世,便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可以为后世持全然不同的政治观点和美学见解的作家使用”,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第106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艺术技巧是超越民族界限的,并不为哪个民族所专用”, ② 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第117、3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然而,“人们往往只讨论作品的内容,而忽略了作品的艺术形式”。②《初探》出版后,李陀、冯骥才、刘心武在《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上,以“通信”的形式发表文章讨论此书。
在冯骥才给李陀的通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对于形式问题的看法:“单就文学艺术的形式来说,是具有一定程度独立欣赏价值的。即在我们确认形式为内容服务的同时,形式美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冯骥才:《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给李陀的信》,《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刘心武在给冯骥才的信中也同样提及:“小说这一诉诸读者第二信号系统的东西,在体现形式美上有着它的特殊规律,这一规律的特殊性,是必须加以仔细研究的。”刘心武:《需要冷静地思考——给冯骥才的信》,《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而李陀在给刘心武的信中又接续地表达了对文学形式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并同高行健一样,对当时仍然盛行的内容决定论表示不满和批判,他指出:“在这样一个文学大国中居然至今没有形成研究文学技巧的风气,居然至今不把文学技巧当作一门重要的、专门的学问,居然至今还没有出几本(其实最起码也应该几十本)探讨文学技巧的专著,这不是咄咄怪事吗?” ⑦ 李陀:《“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给刘心武的信》,《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甚至,在随后的另一篇文章中,李陀还表示应该“建设我们中国的‘小说学,甚而建立‘小说学的中国学派”,李陀在《论“各种各样的小说”》中阐述了“小说学”的范畴,即“世界上自从有小说以来,人们就不断讨论这类问题(指小说的写法,引者注)。这些讨论,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数不胜数的文章和专著,大概都可以划入‘小说学的范畴”。李陀:《论“各式各样的小说”》,《十月》1982年第6期并且,呼应着此前在《文艺报》讨论会上提出的关于“焦点”问题的观点,在这封通信中,李陀又再次强调:“就艺术探索来说,寻找、发现、创造适合表现我们这个独特而伟大时代的特定内容的文学形式,是我们注意力的一个‘焦点。”⑦
随后,王蒙也发表文章支持高行健,他认为,“小说的形式和技巧本身未必有很多高低新旧之分。一切形式和技巧都应为我所用”, ⑨ 王蒙:《致高行健》,《小说界》1982年第2期。并且也如李陀和高行健一样,认为当时对小说形式和技巧的讨论实在太少了,还预言《初探》将“引起相当激烈的争论”。⑨果不其然,《初探》出版后的确引发了诸多争论,比如,陈丹晨就不认同高行健等人将现代小说视为与现代社会相匹配的文艺形式,也就是说,现代化并不要求现代派的必然相随,现代小说形式和技巧并不是必选题。相反,他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关于“物质生产的发展对于例如艺术生产的发展之不平衡关系”为依据,认为“文艺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因而不必“从属于科学技术”。因此,关于《初探》对现代小说写作技巧的肯定和赞扬,陈丹晨是持保留态度的,他仍然认为,现实主义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对于现代派,只可采取研究、探讨的态度。
《初探》出版后,1982年7月28日,《文艺报》就召开会议提出要对这本书予以评论,于是,“风筝通信”发表后,《文艺报》便以“启明”为名,发表了《这样的问题需要讨论》,认为《初探》所引发的讨论文章“涉及到我们的文学是走现代派道路还是走现实主义道路的问题”。启明:《这样的问题需要讨论》,《文艺报》1982年第9期。1982年11月8日,《文艺报》召开“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会”,王蒙、冯骥才、李陀、刘心武、高行健等都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11月10日,《文艺报》的唐达成在编辑部会议上对此前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会”进行总结时说:“他们一头栽到了‘形式里。‘形式固然很重要,但脱离了巨大的历史要求,能建设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吗?他们只从‘形式提问题,西方现代派的思想感情才符合我们的时代。所以,我们之间的分歧是深刻的。”见刘锡诚:《1982:“现代派”风波》,《南方文坛》2014年第1期。在这前后,《文艺报》上还发表了小仲的《能這样‘打破传统手法吗?——就‘焦点问题和‘继承问题与李陀同志商榷》、王元化的《和新形式探索者对话》、王先霈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读后》等商榷文章。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2期 事实上,这一时期,关于内容与形式的讨论经常出现在各种文艺论争中。究其原因,第一,思想解放所构建的新的意识形态将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视为反思对象,具体在文艺领域则是重新审视从旧的意识形态中脱胎的旧的文艺观念和创作方法,而建立与新的意识形态相匹配的新的文艺观念和创作方法。可以说,新时期是一个破旧和立新并行的时代。第二,随着西方译介的大量涌入,西方现代主义所带来的别样面孔,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文艺创作者和研究者们的视界,刺激着他们思考诸多文艺基础问题,比如文艺本质问题、文艺主体问题、文艺形式问题,等等。不过,1980年代初期,关于内容和形式的讨论虽然十分热烈,但并没有更为深厚和系统的理论作为支撑,论争的观点也往往更多是经验性和印象式的。1980年代中后期,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文艺批评,对文艺形式的实践和研究都逐渐走向成熟。一些现代派和先锋派作品也纷纷诞生,像艺术界还形成了85美术新潮。此时,国外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等文艺理论,也逐渐进入文艺批评和研究视界,它们为内容和形式的讨论提供了更多的思想方法和实践方法。比如,1988年,殷国明出版专著《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形式”》,从各个角度各种层面讨论艺术形式问题。他将艺术形式视为一种“普遍的心灵形式”,这种形式既不是内容,也不是技巧,而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固定下来的”心灵形式,因此他得出结论,“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不仅是表现内容的一种方式,而且本身就是某种内容长久沉淀的生成物”。 ② 殷国明:《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形式”》,第19、25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比较难得的是,在这本书中,殷国明虽然肯定了艺术形式的独立价值,并赋予这种价值以新的理解和阐释,但并没极端地从“内容主义”(即内容决定论)走向所谓的形式主义,也没简单化地认为艺术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叠加,而是指出艺术形式的迷人之处,在于“艺术家把某种情感内容转换为形式媒介的整个美学熔铸过程”。②
1980年代中期文艺界开展艺术本体讨论之后,一些关于语言本体论、形式本体论、结构本体论的观点纷纷涌现。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小说本体论讨论的重要文章整理成册,编辑出版了《小说本体研究》,其中收录关于小说本体的文章共计29篇。这些研究是“由文学理论批评中的关于形式和技巧的探索发展演化而来的,但它又显然不同于以前的形式和技巧的研究”, ④⑤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编:《小说文体研究》,第384、215、203、26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可以将之视为对1980年代初期关于内容与形式探讨的进一步深化。比如,王晓明和黄子平都将文学形式具体化为文学语言,并将文学语言视为文学本体。王晓明在《在语言的挑战面前》一文中写到:“文学首先是一种语言现象。”④黄子平同样强调“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并进一步指出,“不要到语言的‘后面去寻找本来就存在于语言之中的线索”。⑤在《小说技巧十年》中,南帆不仅不满长时间以来对小说技巧的忽视,同时还颇有见地地道出:“小说技巧的重大改变毋宁溯源于这一点:作家对于世界的观照、体验、感受、想象和思索这些审美把握的方式、意向与过程发生了重大改变。”⑥可见,较之高行健将小说技巧视为纯粹的写作技法而言,南帆的这一番评述更道出了所谓的客观技巧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微妙关系,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超越。
1980年代,一些论者依循历史惯性,仍然将内容决定论视为文艺规律和真理,坚持认为在文学创作中,是内容决定形式,内容为主导,形式为辅助,内容为主体,形式为工具。长久以来,在中国的文艺传统中,“文以载道”是主流文艺观,20世纪初,虽然由西方传入的各种文艺流派和思想改写着古老的“文以载道”观,但是,在接受现实主义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时,“文艺反映论”代替了“文以载道”继续发挥着文学艺术对社会人生的参与作用和认识功能。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文以载道”还是“文艺反映论”,都强调文艺创作中内容发挥着核心作用,形式为内容服务。直到1980年代,在关于内容与形式的讨论中,一些论者的观点才质疑和动摇了传统的内容决定论,而另一些论者则与之相反,极力维护这一观点,并将现代主义的诸多形式创新和探索冠以形式主义加以批判,于是,讨论中就常常出现这样的观点:“凡形式主义都不合文学发展规律,但独创的部分成功技巧,也不应否定”;林焕平、袁鼎生:《略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4期。 “既反对形式主义,也反对自然主义”。奚静之:《现实主义、写实主义及其它》,《美术研究》1979年第2期。而实际上,现实主义也好,现代主义也罢,写实主义也好,形式主义也罢,都是中外文艺史上诸多创作方法之一种,但在现实主义一枝独秀的历史时期,其他“主义”尤其是现代主义,也就只能游走于历史的边缘了。
二、讨论实质:“内容主义”与形式主义的矛盾与纷争
根本来看,1980年代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对话和交锋,乃是两种语言观和形式观的根本冲突。秉持“内容主义”的论者,仅仅将语言和形式分别视为组建内容、呈现思想的工具,而秉持形式主义的论者,则认为语言本身以及由语言直接构筑的形式本身即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并且,相对于内容而言,形式才是文学艺术之所以成为其自身的关键所在。两种语言观和形式观的不同,致使二者所选择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技巧都产生了巨大差异,同时也是中外文艺思想史上,关于内容与形式问题发生激烈论战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将语言及形式视为内容的工具和附属这一文艺观念都有着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传统,因此,即便1980年代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启动了现代化转型,艺术观念的传统势力仍然顽固而强大,这就使得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在面对新生的文艺观念和创作方法,尤其是现代语言论和形式观时,便以传统的语言论和形式观为标准,对其进行质疑和批判。
在西方文艺史中,“摹仿”一直是一个核心概念,随之而来的“逼真”也是一项重要的文艺准则,在这种情形下,所谓的形式就只能是达到“逼真”的工具和手段。除此之外,文学艺术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和价值就是认识世界,洞悉真理。在认识论的视域中,形式也仅仅是主体达至对宇宙人生的认识的工具和手段,它负责将这种认识有效地表达出来,使接受主體能够获得思想和真义,也就是说,文艺作品意欲表达的内容和思想才是核心,而形式仅仅是推送内容和思想“出笼”的方式而已。如此,形式本身便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
同样,形式工具论也是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之主流。受“文以载道”观的影响,“文”往往是“载道”的工具。孔子虽然强调“情欲信,辞欲巧”“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主张“言”要有“文”,“文质彬彬”,但是在“文”与“言”、“文”与“质”的关系上,“文”仍然处于附属的地位,或者说孔子主张“言”要有“文”的目的是为了让语言更好地表达内容。中国古典文艺的另一支命脉道家思想,在对待语言和内容的关系上也更偏重于内容和思想,主张“得意忘言”,语言文字不过是表达思想观念的象征性符号而已,倘若一种思想和观念能通过其他方式予以传达,那么放弃语言实行“不言之教”也同样可以。南北朝时,沈约等人曾强调诗歌的声律和形式之美,但终未成为中国文艺的主导思想。
20世纪以后,西方文艺被介绍到中国,改变了中国古典的文艺模式,比如,康德的“审美无功利”和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等现代文艺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使文学艺术不再仅仅承担认识和教化功能,其审美功能也逐渐凸显了出来。随着这些文艺观念及其创作方法的深入传播和接受,传统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也发生了错位和改变,当文艺不再被视为认识世界和教化伦理的方式时,形式也就不再被视为传递内容的工具,而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和意义。只是,随着现实主义被历史和时代所选择成为文艺主流之后,此前建立起来的“语言本体”“形式本体”逐渐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和硝烟之中,语言和形式再次成为文学艺术反映社会、再现生活的工具和方法,甚至还一度成为革命和政治的传声筒。因此,1980年代初期,在有关朦胧诗的争论中,“诗的‘好懂和‘不好懂,竟然成为了诗歌发展方向问题,惹出那么大一场风波”。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第27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1980年代,在文艺界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文艺挣脱政治束缚,首先成为了开篇之题,因为,文学艺术要在新时期有新的发展和未来,松绑政治规约,获取创作自由,是重要而必要的前提,其他具体的尝试、开创和转变都必须在获得了这一前提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当然,摆脱政治束缚为文艺理念和方法的探索提供了前提条件,而理念和方法的具体探索又进一步地促进了政治禁锢的破解和坚冰的融化,其中,关于内容与形式的讨论便是隐性地松解政治捆绑、呼唤创作自由的策略之一。也正是在争取创作自由的这个意义上,后来才有学者感叹:“1979年以后,如果没有一场关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讨论,如果没有一场关于形式和抽象的讨论,中国现代艺术要形成一股潮流和力量是不可想象的。显然,如果没有一种新兴的批判精神在艺术家的作品中显现出来,如果没有艺术家勇敢地创造或借用拿来,要出现一次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讨论,对形式和抽象的讨论也是不可想象的。”吕澎:《1979年以后的中国艺术史》,第73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由此可见文艺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间的纠葛与互动,而1980年代文艺界所发生的关于内容与形式的讨论,也可以说是二者之间的张力所引发和驱动的。
但是,从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演进历史来看,内容与形式的对话和交锋似乎也是必然要发生的。任何一种革命的发生当然都有其外部诸多因素的推动,但内在的变革力量,恐怕才是最核心也是最本质的。对此,理查德·谢帕德在《语言的危机》中有过精妙分析:“许多现代人都感到‘人类在他们用自己的智力来解释的那个世界的家里是不很安全的,由于感到失去了统一性原则,现代也就似乎失去了与过去和未来的有机联系。时间变成了一系列支离破碎的瞬间,连续感让位于不连续感。”④⑤⑥⑦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现代主义》,第300、301、302、307、307、307页,胡家峦等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在这种情形下,“语言不再能控制流动不定、无从捉摸的现实,它像一块厚皮捂住了他们的想象力;不再是简明易懂地表现自我的工具,而变成与忧郁的超自我有些相像的东西;不再是交流的手段,而变成一堵不透明的、穿不过去的墙壁”。④当人们对宇宙人生的认识发生了转变的时候,其语言及语言观也必将发生转变,也就是说,传统的话语方式已经不足以表达新的认识和理解,因此,“现代主义诗人抛弃了所有那些认为艺术即描述或模仿的观点;……寻找一种新的语言、新的形式、新的表达”,而不像老一代作家那样,“无意识地主张人的语言结构和外部现实结构之间的一致性”,⑤“假设他们的话语世界就是宇宙”,⑥相反,他们既认为“语言危机是能够克服的”,⑦同时又认为“语言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段——以无法预言的方式获得意义”。⑧因此,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主义所呈现的形式主义特征,当然一方面可归因于语言观的转变,即由语言是意义传达的工具转变为“语言是意义的生产场所”(索绪尔语),语言由工具变成本体,除此之外,还有另一方面,即所谓的形式主义并非单纯地将语言和形式视为本体,而是通过对语言的实验、形式的探索,寻找合适的表达,以应对现代社会包括思想、文化等各方面转型,尤其是哲学观、世界观的转型。
如此,回到1980年代关于内容与形式讨论的历史现场,我们同样会发现,1980年代现代主义的兴起,一方面是在进化论观念的影响下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所造就的。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主义所出自的历史文化环境,与西方现代主义所出自的历史文化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西方现代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应和与满足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和创作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如同西方现代主义诞生时一样,传统现实主义的文艺观念和创作方法都成为一股压抑和禁锢的力量,不足以表达新的时代内容,因此,新时期以后,一些文艺创作者和研究者们要求恢复文学艺术的独立价值,摆脱附加于它的外部因素。正是在这样的要求和呼声中,“语言本体论”“形式本体论”才逐渐浮出了水面,毕竟相对于诸如社会、历史等外部因素而言,语言、形式才是文学艺术的根本和核心。
三、结语
事实上,关于内容与形式的问题自古以来就争论不休,而正像历史上所有争論都有其具体的现实语境一样,1980年代关于内容与形式的争论亦是如此。然而,如果在分析这些语境之后又搁置一旁,仅仅去单纯地考量和辨析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或许会发现,内容与形式这一议题的探讨,很容易被先在地预设出一个二元对立的立场,而这一立场,是割裂内容与形式的。然而,真实的境况是,在主体的创作中,很难清晰地说明是先有内容还是先有形式,内容为主还是形式为主,内容重要还是形式重要。其实,形式即内容,内容也即形式,并且,二者的合一伴随了创作的整个过程,甚至,不仅在创作的过程中,如克罗齐所言,在直觉的阶段,艺术就已经拥有形式了——“直觉必须以某一种形式的表现出现”。①也就是说,并不存在无所表达的形式,也不存在没有形式的表达。甚至“形式与内容的不可分性将作为毫无区别性而实现,这种毫无区别使艺术作为向我们诉说和对我们表达的东西而与我们汇合在一起”。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资本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问题研究”(13&ZD07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邹军,文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在站),大连大学人文学部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周 荣)
①② 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第495、60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