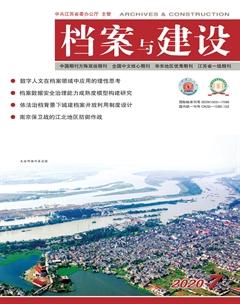数字人文在档案领域中应用的理性思考
摘要:数字人文进入档案领域已是大势所趋,将会对其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对于档案学而言,虽然数字人文不会颠覆已有档案学理论体系,但会扩大档案学的社会影响,拓展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改进研究方法;对于档案馆而言,它将以资源组织者与提供者的服务角色参与其中,发挥对档案数字人文项目的支撑功能和项目知识成果的展示、传播、保存功能;对于档案工作而言,数字人文将推动档案数字化工作进一步提升,促进数字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推广应用,促使面向用户的档案服务平台升级。
关键词:数字人文;档案学;档案馆;档案工作;应用
分类号:G270
Rational Thinking on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in Archives
Pan Liange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Abstract:It is a general trend for digital humanities to enter the field of archives, which will have multiple impacts on it. For archival science, although digital humanities will not subvert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system of archival science, they can expand not only the social impact of archival science, but also research horizons and research fields, and improve research methods. For archives, they will take an active part as the organizer and providers of resources, with the supporting functions of the archives digital humanities projects and the display, dissemination, and preservation functions of the project knowledge achievements. For archives work, it will further promote the archives digitiza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upgrade of the user-oriented file service platform.
Keywords:DigitalHumanities;ArchivalScience;Archives;ArchivesWork;Application
自2001年“数字人文”概念正式诞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形成一股数字人文研究浪潮。我国学术界对数字人文的研究起步稍晚,但发展迅速。截至2020年7月7日(下同),以“数字人文”为主题在中国知网进行篇名检索,得到479篇相关文献,各年度刊发数量分布情况如下:2005(1)、2011(1)、2012(3)、2013(7)、2014(6)、2015(8)、2016(30)、2017(64)、2018(125)、2019(151)、2020(83)。可见,我国对数字人文的研究基本是始于2005年,但直到2016年才进入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
数字人文与信息管理学科有着天然的联系,而最先对数字人文浪潮做出回应的是图书馆学。以“数字人文”并含“图书馆”在中国知网进行篇名检索,得到141篇相关文献,各年度刊发数量分布情况如下:2011(1)、2013(1)、2014(3)、2015(2)、2016(14)、2017(25)、2018(40)、2019(43)、2020(12)。可见,我国图书馆学界关注数字人文研究的时间与国内研究进展基本同步,且年均发文量约占全部相关研究成果的1/3。相比之下,以“数字人文”并含“档案”在中国知网进行篇名检索,得到44篇相关文献,各年度刊发数量分布情况如下:2015(1)、2017(1)、2018(6)、2019(18)、2020(18)。可见,我国档案学界对数字人文的研究较晚,发文量也较图书馆学界少,但从2018年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说明数字人文开始真正进入档案学界的视线,并有成为未来研究热点的可能。
从已有研究主题看,我国档案学界目前有关数字人文的研究重点集中于档案信息(文化)资源的整合、开发、服务方面,这也是档案学与数字人文最为密切的联结点。不过笔者认为,数字人文对档案领域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会对档案馆及其相关业务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也会对档案学学科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1认识数字人文
正确认识并把握数字人文的实质,是分析、研究数字人文对档案领域影响的关键和重要前提。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源于20世紀40年代的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标志事件是意大利神父罗伯特·布萨编制了《托马斯著作索引》,创造了由计算机生成的托马斯·阿奎纳作品索引。这种经由计算机进行的文字检索、分类、计数、词表生成等自动化操作,让学者能够处理超乎想象的大量文本信息。人文计算的这种突出优势,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并被普遍应用,从最初的语言学方面的应用拓展至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地理学等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随后,互联网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对人文计算项目开发与共享协作的需求,人们对人文计算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作为升级概念的“数字人文”便应运而生。2001年英国布莱克威尔出版社首次出版了一部以“数字人文”命名的图书《数字人文指南》(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从此“数字人文”迅速取代了“人文计算”,成为广泛流行的新名词。
尽管目前数字人文的概念还难以界定,但人文计算与数字人文之间已有诸多区别:一是数字人文比人文计算拥有更为庞大的数据库,这不仅仅表现在数据量的增多,更表现在人文计算的对象由以往的电子文本扩展到超文本、图像、视频、音频、数字地图、网页、虚拟现实等多媒体数据,因而数字人文对信息整合、处理与利用的要求也更复杂。二是数字人文不只是强调人文计算能力,还经常应用其他研究方法。“数字人文与人文计算的不同之处在于研究方法的不同。在人文计算时代,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文本,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文本挖掘。而在数字人文时代,‘这一全新的命名明确地启发了一个更大的领域,而且也被用在了一个更广阔的环境里,用以从整体上形容介于人文学科和信息科技之间的活动和结构”。[1]也就是说,数字人文的研究对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文本,而是拓展至人文学科和科技之间的活动领域,如大型图像集可视化、历史文物3D建模、移动创客空间甚至AR游戏等。因而,其研究方法也更加新颖多样,如在历史学研究方面借助GIS技术进行历史知识和历史事件的静态、动态可视化展示,在舞蹈研究方面利用计算机视频捕捉和运动分析技术进行人体运动轨迹的建模,在考古学研究方面利用计算机进行3D虚拟遗址绘图、文物虚拟复原、色彩还原等。
那么,数字人文的实质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是一门新的学科呢?目前并无定论。笔者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般应该具有专门的研究对象、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方法。从数字人文的发展历史看,它的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和自身的研究方法都不够清晰,如何种研究才算真正的数字人文研究,什么样的学者才是真正的数字人文研究者等。当然,对于数字人文是一个目前较为热门且影响力较大的研究领域,人们应该是不会有所异议的,这从目前存在的大量有关数字人文的项目和研究机构上都可以得到印证。不过,“学科是科学研究领域发展成熟的产物,但并非所有研究领域都能发展成为科学”。[2]因此,说数字人文是一门学科还为时尚早。笔者更倾向于认同数字人文是一种研究方法,因为早期人文计算正是作为一种基于文本的研究方法被应用于人文学科研究之中的,而数字人文仍然会被继承使用;同时,作为“一个人文领域知识、学科研究发展需要、数据收集及分析技术、网络与计算基础设施、算法模型等方面发展共同促成的产物,将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深入应用于传统的人文研究、教学和出版等活动的新型跨学科合作性研究领域”,“数字人文给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即数字人文将研究者从十分耗时的材料搜集整理工作中解放出来,使研究者能够从已有的数字化资料集合中借助计算机技术的辅助分析,通过可视化的结果呈现和诠释,以提高研究的速度和效率,转而专注于高层次的学术发现。因此,“数字人文的产生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方法论和研究范式上的创新”。[3]当然,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新颖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较以往任何一种新方法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都更具革命性,它会导致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非学科范式[4])的转变,从而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产生较大影响。
因此,对于数字人文的认识要避免几种误区:一是认为数字人文主要是解决数字技术问题的。数字人文虽是数字技术和人文领域结合的产物,但它的根本目的不是解决人文领域的数字技术问题,而是如何运用数字技术的手段和方法去解决人文领域的各种人文问题,即“数字”要为“人文”服务。二是认为数字人文涉及的“人文”是“数字化的人文”。数字化的人文只是“人文”的一种现时的重要表现形式,理应深入研究,但数字人文中的“人文”事实上包括所有形式的人文现象和问题(与表现的介质无关)。三是认为数字人文只适用于人文科学。笔者认为,“由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大多社会科学如历史学、法学等从研究对象看属于社会科学,但从研究的主旨和研究方法看更属于人文科学,因此不少社会科学往往兼有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也正因很多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具体学科在到底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上存在争议,所以现在更多是把两者合在一起,称为人文社会科学”。[5]事实上,从现有的数字人文应用情况看,就包含了历史学、社会学等传统的社会科学。有学者对数字人文的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数字人文研究的学科范围非常广泛,从传统人文科学逐渐向社会科学、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渗透,凸显出较强的学科交叉性”。[6]因此,将数字人文的“人文”从学科角度理解为“人文社会科学”可能较单纯的“人文科学”更合理些,至少数字人文从纯粹的人文科学向部分社会科学延伸是不争的事实。
总之,数字人文作为在网络环境下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不仅会改变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也能促进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演变。
2档案学在数字人文中的理性定位
数字人文反映在档案领域,首先就是档案学界开始对与档案相关的数字人文问题的重视和研究,如数字人文下的档案信息资源整合、传播、开发利用,数字人文与档案工作的关系及参与路径、机制,数字人文下档案机构的发展等。因此,只有认识档案学在数字人文浪潮中的理性定位,才能清楚档案学在数字人文热中能做些什么以及数字人文对档案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数字人文的产生主要是对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创新,然而这并不会从根本上动摇和颠覆人文社会科学已有的理论体系。在运用数字技术手段进行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时,仍需要运用原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并由人而不是纯粹的机器来进行分析研究。事实上,“目前为止,数字人文研究的大多数项目确实没有推翻传统意义上的预设,也没有产生全新的叙述,只是在量化方面确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内容”。[7]甚至形成了一个“批判数字人文研究”(Critical DH Studies)的小小領域。可见,档案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将数字人文引入档案学,同样不会引发档案学学科范式的转型,不会动摇已有档案学的理论体系根基,因而数字人文对档案学并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不过,由于数字人文的根基是大量数字资源,包括数字化资源和原生数字资源,而这些数字资源“通常来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以及其他信息机构,这些机构为人文科学研究者对结构化数据和半结构化数据中价值的挖掘提供了巨大的机会”。[8]因而,档案学作为一门学科,自然要对作为档案资源保管机构的档案馆在档案工作实践中如何应对数字人文的冲击作出相应回应。可见,档案学在数字人文热中能做的主要是数字人文在档案领域的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的相关研究,如档案馆在数字人文中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什么样的作用,数字人文是否会影响档案馆未来的发展走向,档案工作与数字人文有什么关联,对具体的档案业务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等等,但很难涉及档案学的基础理论领域,至少目前还不大现实。
至于数字人文对档案学的影响,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扩大了档案学的社会影响,有利于学科地位的提高。作为数字化社会的今天,数据的重要性更显突出,档案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数据资源,在数字人文的浪潮中不可能置身事外。由于数字人文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与新兴数字技术交叉与融合的产物,而基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数字技术上的短板,必然需要不同学科特别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学者参与,因而跨学科、跨行业的综合性研究是数字人文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样,在数字人文研究热中,档案学开展有关数字人文的研究,必然要多学科不同学者的参与,这使得档案学能够向不同学科研究领域进行渗透,从而扩大了档案学的社会影响力,提高了学科的社会地位。
二是拓展了档案学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有助于走出档案学研究的困境。目前的档案学研究似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困顿,表现在档案学研究的“泛化”现象,有学者认为原因在于“我国档案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的学科理论体系问题意识淡薄倾向,严重制约了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发展,致使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陷入困境”。[9]笔者认为,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强本身不是问题,毕竟档案学理论体系并非到了十分完美的境地,仍然需要进行拓展和深化,且不同档案学学者个体的研究兴趣和专长不同,因而研究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强并不是问题;但当这种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成为档案學研究中的群体性研究意识和研究行为时,则必然会导致对档案工作实践问题的冷漠与忽视,最终使档案学研究走入死胡同。因此,将数字人文的研究引入档案学领域,在目前看来,可以进一步拓宽档案学的研究视野、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有助于帮助档案学走出研究困境。数字人文的研究在图书馆学中已占据一席之地,档案学虽才开始不久,但研究前景仍是乐观的。
三是促进了档案学研究方法的改进和发展。数字人文的研究范式(重视数字技术,重视量化分析,从数据本身发现并解决问题等)虽然目前还不会对档案学的研究产生太直接的影响,但肯定会对档案学研究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数字人文的跨学科化研究带来的开放多元的价值观给档案学研究带来冲击和洗礼,从定性研究发展到定量辅助定性的研究,大规模的文本、图像、音频和多媒体的数字资源对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档案学)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因而在知识的获取和传播已经发生了革命性改变的数据时代,档案学的研究方法也必然会有所变革和发展,甚至可能形成新的研究范式。
3档案馆在数字人文中的角色和作用
由于图书馆作为支撑科学研究的知识存储、信息服务的知识中心,其科研服务中心的地位比档案馆更为突出,因而在数字人文浪潮中的反应也更为深刻,这也是图书馆学界有关数字人文的研究成果比档案学界要早、要多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档案馆馆藏中毕竟有大量关于历史、文化或证据价值的档案文献资料,且大多又是未公开发表过的孤本,为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所重视,这也是档案馆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联系的纽带,因此,档案馆必须正面回应数字人文浪潮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当然,无论档案馆在数字人文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并不会从根本上颠覆档案馆的社会定位,即档案馆是党和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是永久保管档案的基地,是科学研究和各方面利用档案史料的中心。说到底,档案馆在数字人文中的角色只是档案馆社会定位在数字人文浪潮中的诠释和注解,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会使档案馆自身的发展迷失在数字人文的浪潮之中,毕竟档案馆要面对社会各种各样的浪潮冲击,数字人文终究只是其中一股。
那么,档案馆在数字人文中将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笔者认为,档案馆将以资源组织者与提供者的服务角色参与到数字人文中,而不可能以人文研究的主角出现(主角仍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档案馆要根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需要,以馆藏相关档案资源为基础,通过数字技术将其组织、加工、整合成可利用的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数据,以档案数字人文项目的形式提供给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研究、使用。其实,档案馆早已开展的档案数字记忆工程(如城市记忆工程项目、古村落记忆项目等)与档案数字人文项目就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联性,这为档案数字人文项目的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实践经验。如此,档案馆在数字人文中所起的作用,主要就是档案数字人文项目的支撑功能和项目知识成果的展示、传播、保存功能。由于档案数字人文项目主要依托一定的档案馆(甚至有可能依托档案馆和其他机构如图书馆、博物馆等)而生,因此档案馆必须通过相关的数字技术手段对项目建设的数据、技术平台及后续的运行维护提供政策、资金、技术上的支撑;同时,档案数字人文项目所呈现的知识成果也需通过档案馆向社会进行展示、传播;另外,档案馆也应是数字人文成果的“归档”保存者。
总之,档案馆在数字人文中的角色和作用,从其服务的对象(社会公众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手段(数字技术)、形式(档案数字人文项目)、方式(网络平台)来看,仍大体处在档案馆的社会定位之内,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4档案工作在数字人文中的局部变革
数字人文进入档案工作领域,必然会对档案工作产生一定影响。数字人文对档案工作的影响并不是全方位的,具体体现在档案工作参与数字人文过程中涉及的有关业务活动,从这一角度来看,数字人文对档案工作业务活动最直接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推动档案数字化工作进一步提升。数字人文项目的建设不一定是由档案馆来进行,事实上,大量的数字人文项目是由有关研究机构、图书馆、博物馆等来主导建设的,如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知识库”、上海博物馆“董其昌”数字人文项目等,基于数字人文对数据的系统性要求和对项目支撑的高技术要求,数字人文项目往往是相关机构合作建成的,档案馆因其所藏档案资源具有的特殊意义自可容纳其中,因而可促使相关数字档案资源向有关数字人文项目渗透。当然,档案馆也可根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需要,结合自身的馆藏实际,自行主导建设有关的档案数字人文项目,如天津市档案馆“津沽史料”项目、上海市档案馆“上海记忆”项目等。档案馆不管是参与还是主导数字人文项目建设,前提都是档案资源的数字化。尽管我国的档案数字化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以前的档案数字化工作仅停留在单纯的数字化上面,缺乏对于数字档案资源内容的深度挖掘,离数字人文对于数据资源的要求仍有相当差距。因而数字人文进入档案工作领域后,对档案资源的数字化工作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原有的档案数字化主要目的是为解决存储问题,这些数字化的档案资源往往很难进行内容检索与分析;如今,数字人文会促使档案数字化工作从单纯的“数字化”拓展至“数据化”,即对档案文本和图像中的数字内容进行识别、分类、著录和标引,推动了档案数字化工作升级。
二是促进数字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推广应用。对于数字人文,学者关注的重点是如何从海量信息资源中发现并获取研究所需的数字文献资料,而馆藏档案由于来源主体广泛、类型多样、格式复杂等特点,给档案信息的检索服务增加了难度,在此背景下,数字人文项目中应用的大量数字技术如数字化技术、数据管理技术、数据分析技术、可视化技术等新兴技术成果必然会融入档案工作中去,为档案工作提供新的技术与工具,从而进一步提高档案信息资源建设和开发利用的水平。
三是促使面向用户的档案服务平台升级。目前,档案馆往往通过自身的門户网站向用户提供档案服务,如利用查档咨询、查档预约等,但由于档案数据库资源少、深度加工和整合开发不足、缺乏特色,往往很难满足用户需求,也不能适应数字人文学者的需要。数字人文要求数据资源“整合机构应提供支持各类终端设备的自适应平台服务,实现统一平台的多终端兼容访问,允许用户通过互联网、移动媒体随时随地、交互访问”。[10]因而,通过档案数字人文项目的建设,可促使档案馆现有服务平台的升级,更好地提升自身的服务水平与质量。
5结语
数字人文对档案领域的冲击和挑战是局部的,并不会导致档案学、档案馆及档案工作的全面颠覆。认识这一点十分重要,将有助于我们理性地看待进而妥善处理数字人文浪潮对档案领域的冲击。本文只是一个比较粗浅的思考,有关数字人文在档案领域中的大量问题还需要我们做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林施望.从“人文计算”到“数字人文”——概念与研究方式的变迁[J].图书馆论坛,2019(8):12-20.
[2]马启龙.也论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J].开放教育研究,2014(6):18-26,120.
[3]欧阳剑.大数据视域下人文学科的数字人文研究[J].图书馆杂志,2018(10):61-69.
[4][5]潘连根.档案学元理论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50.
[6]柯平,宫平.数字人文研究演化路径与热点领域分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6(6):13-30.
[7][美]戴安德,姜文涛.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方法:西方研究现状及展望[J].赵薇,译.山东社会科学,2016(11):26-33.
[8]曾蕾,王晓光,范炜.图档案博领域的智慧数据及其在数字人文研究中的角色[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8(1):17-34.
[9]管先海.对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的若干思考[J].北京档案,2009(11):14-17.
[10]张卫东,张天一,陆璐.基于数字人文的档案文化资源整合研究[J].兰台世界, 2018(2):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