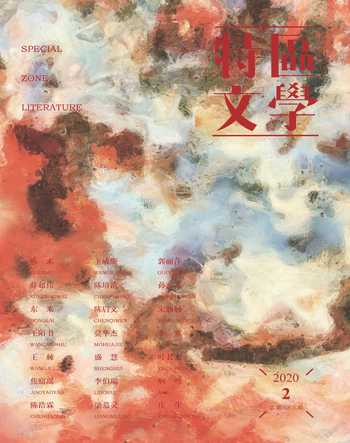风过树梢
郭丽萍,广东工业大学副教授。作品散见于各文学期刊,有作品被选刊转载。获得2015 年广东省期刊作品一等奖。
父亲很小的时候,每天要跑路20里去上中学,有一次遭遇狼。“我听到身后有呼哧呼哧的声音,”父亲说,“我拼命地跑,书包里的空饭盒发出巨大的咣当咣当声,在漆黑的山路上简直吓破我的胆了,比狼的呼哧声还可怕,但我停不下来,就这样一直跑过山后,跑过稻田,跑过坟地,跑到村口,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我脱了力,衣服全湿了,昏睡了两天,生了一场大病。”
或许,父亲是要通过这个故事,表明他童年的艰辛,和逼真细腻的描述能力,他很着迷自己述说往事的腔调。
或许,这是一个梦,描述梦境才会用那种口吻,他从不讲述构成自己大部分生活的平静长久的岁月。这些故事像标点符号,他不断地从井口或房梁上掉下来,或者穿过挂满蛇的树林,以及家里的大花猫帮他捕杀了一只锦鸡和一只黄鼠狼。
这些特别的故事只在特别的场合讲给几个人听,比如全家人一起包饺子的时候,尤其是我母亲不在场的时候。父亲的脸立刻变得丰富多彩,他加入声效,在空中挥舞双手。他眼睛闪烁,有时候有点小小的邪恶。尽管父亲是一位老干部,可他并不想做一个平凡的老干部,当人们错以为他如此,便掉进了陷阱,他会扔出一些奇怪诡异的桥段,他可不愿被想当然了。
一
民国元年。我父亲这样开头讲我们老郭家的家族史。姐姐和我边听边把一撮羊尾巴毛往三枚咸丰通宝的方孔里塞—我们在做毽子。那肯定是冬天,对小孩子来说东北的冬天太冷了,你被冻结在空气里,只能靠踢毽子让身子暖和起来。三枚大钱的重量坠着乳白的羊毛在寒风里温柔地落下,最合乎尺寸的完美造型迎着鞋子安稳自信的承接。这个毽子会让我们姐妹在小伙伴中成为最受欢迎的人,她们的羊毛或鸡毛下面通常只能坠着镙丝疙瘩,厚重的六棱形隔着棉鞋也会让冻僵的脚尖锐地疼痛起来。大钱来之不易,是我祖父从炕洞里找出来的,也由此引发了我父亲的怀古思祖之情。
民国元年,黄河发大水, 一群人从山东寿光县郭家村出发,男人们都挑着担子,一边是孩子,一边是行李,过山海关,一路往北,进入这片原本荒无人烟的地界。
这里面就有我的祖太爷。
几年前,我去内蒙和俄罗斯的边界额尔古纳河,乘游轮漫溯,八月的阳光使整个河谷显得出奇地净洁,巨大的河蚌在岸上晒着白得耀眼的蚌壳,河湾处摇曳着一丛丛的柳树毛子。我在那儿想起了我的出生地,第一次意识到它曾经何其荒蛮。
这是旗人跑马占地划属自己领域的地方,我闯关东来的祖太爷远离故土到这里垦植的就是旗人的土地。从春天开始,他带着郭家村来的人为庄主“耙青”,开垦一片依山傍水的荒滩,到了秋天挖个地窨子,向阳的一面在地上,北面依坡筑墙。收获的粮食一半交给庄主,一半留了自用,来年春天再继续播种。慢慢的地窨子变成泥草房子,这块荒滩就有了个名字,叫“望山堡”,离它不远的另一处地方叫“窝棚”,还有一个叫“三棵树”—大片绵延的荒土,沉默地重复着它们自己,全无视觉重心,这时候一座山,一棵树,一个草棚,就成了标志。如果眼见之处,什么都没有,就叫“四荒地”。
这块土地的产出太过丰富,即使是做长工也很快让他们有了盈余资产。而我父亲更津津乐道家族的传奇而非兢兢业业筚路蓝缕。传说我的祖太爷从山东带来的媳妇不堪漫长酷寒的严冬早早过世,填房是个半傻的女人,这娘们儿有一天上山挖野菜挖到块青石板,掀开石板底下有一坛银子,老郭家开始有钱了。但“旗民不交产,旗民不通婚”,这项法令让他们无法真正成為这块土地的主人。
到我祖父这一代,旗民可以交产,望山堡终于成为我们老郭家的地界。
我的祖父,四十五岁就做了鳏夫,他的妻子,我的祖母,留下她在人间活过的唯一证据—三儿一女,死于不知名的病症。祖父喜欢牲口,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牲口棚里度过,他毛绒绒的大眼睛,四方大脸,简直和他养的最英俊的黄骠马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在家族里,他也跟他养的驴马一样,毫无声息,按时下地,按时睡觉,按时嚼口粮。这个家族却不全是牲口一样静默的生物。我的其他爷爷们,也就是我祖父的其他四个弟兄,他们的足迹要比我排行老四的祖父躁动凌乱,同时也有意思得多。我的三爷在日本人占领东北后,很快就找到机会把自己“嫁”到了旅顺,在那里他跟一个被遗弃的日本女人过整洁舒适的生活,他再也不回乡。他说受不了大炕,受不了南北大炕上都是人,受不了在北炕听南炕大哥和大嫂弄出的动静,“太埋汰了”。大爷、二爷和五爷,也就是我祖父的大哥、二哥和小弟,他们赶着两匹大黑骡子,一辆轻便马车,驰骋在辽河边广阔的河滩地上,穿越暴风雪,傍晚时分,赶去城里有灯火的屋子,推牌九,听二人转,下窑子,抽大烟。我的祖父带着他的牲口们在河滩地上精心地开荒种地,他的兄弟们交游广泛,头脑灵活,给他带回来更多的种子和牲口,还有犁杖。在解放前东辽河边聚集的村落中,这个家族有一度曾被预言:老郭家会成为东辽河一带最大的地主。
跟所有的民间故事一样,家族中最特别也最有运气的总是最小的一个。我的五爷,郭氏家族最小的一个,长得最帅,人也最精明。他娶了一门让人眼红的亲—一个当铺掌柜的女儿,带着我的大爷和二爷在城里过了几年很风光的岁月。后来他把我祖父开垦的土地全卖了,倒不是他精明到能预见这个行为会给日后家族带来“贫农”这个光荣的称号,而是他的老婆得了一种很疼的病,没有鸦片的麻醉就会满炕打滚。短短两三年间,她就把她的嫁妆连同老郭家的一切,抽光了,之后,她疼死了。
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父亲坐在旁边,一边补充细节,一边在一个小洋铁盆里挤着小鲫鱼儿,他要给我做一碗最怀念的儿时的吃食—鲫鱼酱汤。那些往事在小鱼破肚的声音伴奏下呈现出某种喜感。他的态度也从容欢快,但嘴里吐出的词语,却对应着一种我难以完全理解的戏剧性生活,以至于你很容易忽略掉其中包含的艰苦。在这种浪漫化的生活里,人们没有被安排一个固定的角色,或对未来执行某种确定的计划,起作用的是一个接一个流动的念头,如同黑暗海上的零星浮标,指引着独木舟上的水手。他们偶尔划动木桨,但更多时候,只是顺着洋流飘荡,不去费心判断陆地的方向。
二
那大片的河滩地,是我那些爷爷们的后花园,他们在农忙时才会带领一班伙计,像蝗虫一样掠过土地,留下大片整饬的田畴。他们最早实现了规模化的农场管理,用的不是播种机和联合收割机,而是更好使的脑子里装了点牲口的灵魂—像我祖父这样的人,在那块土地上实在太多了。
而郭氏家族的祖屋,那五间泥草房,他们像留下一架马车一样把它留给了我的祖父。他们生猛敏锐又没受过什么礼义教化,根本没想起要修建一座光宗耀祖的房子,也可能他们还太年轻,乱世的城里太多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事物。
父亲出生在老房子里,它在东辽河边上的大壕里面。大壕是哪个年月修的,没人知道。“要想住在十年九涝的河边上,就要有这么一个大壕,古诗有云: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这大壕该叫大坝,壕不是沟么?壕是战壕,是护城河,这是大坝,怎么能叫大壕呢?”父亲每次回乡踏在越来越高的大壕上,都要这么表示一翻不满。他说的对象都是当地儿时的伙伴,他们笑着。父亲最喜欢说他们听不懂的话。
大壕里郭氏家族的老房子,说是五间房,五间房的意思不是它有五个房间,而是它比一般的三间房要长,中间做饭的进门厨房还是普通的大小,东西两边的房间却比常见的三间房格局大了一倍,南北都铺了长长的火炕。它的历史悠久,在我五个爷爷之前,还有他们众多的叔伯父辈睡过这些大炕。虽然是泥草房,却“越住越暖和,烟熏火燎的灰吊子足有两寸厚,多大雪都压不塌”。我父亲得意地在祖坟边望着不远处的废墟,那里是五间房的旧址,也是他即将永远沉睡的地方。
我从没见过那座房子,它却仿佛在那里,有好多人在那里,他们的名字和长相变幻不定。只有我的祖父,面目清晰,他住在炕头,背靠着行李卷。行李卷上方的墙上钉了块小木板,就成了一个置物托架,上面有一包放久了发出哈喇味的油茶,一小卷草纸包的蛇皮。祖父敲着自己的绑腿,叫谁把蛇皮拿下来,他把纸包放在绑腿上打开,抖落的灰尘干燥而温暖,所到之处带着静电噼啪作响。蛇皮灰白的鳞片蜿蜒着,像一条发带。“不能给你扎头绳。”他说,露出老猫一般的笑容。
祖父的蛇皮是用来治疗他的关节炎的,剪成一段一段,烧成灰,冲水喝。解放后他当上了光荣的生产队饲养员,他很喜欢住在生产队的队部里,也许因此落下了毛病。有一年,从沈阳呼拉拉来了一大批下乡知青,青年点儿还没建起来的时候,那些姑娘小伙子占用了他住的东屋,因为整个村子里就属我母亲整理过的房子最符合知青的标准。祖父自己住进了牲口棚,他很享受跟牛马驴老朋友相处无间的时光,也享受队长每次在大喇叭里表扬他大公无私,爱队如家。我的父母却为此忍受着良心上的不安和想象中乡亲们对他们不孝的指责。
祖父喝蛇皮灰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着,我分明一点也不想吃这种东西,嘴里和心里却升起古怪的馋。我找到母亲,告诉她我肚子疼,她用一只勺子在火炉上烤,勺子里放点油,再磕碎一个鸡蛋,最后把一小撮绞碎的头发放到蛋液里。这个很像鸡蛋炒韭菜的一坨东西,在黄铜的汤勺里烤得香喷喷的,让人心生恐惧和向往。每次吃的时候我都是一口吞下肚,怕我的舌头碰到那些头发茬儿,以至于多年后想起它的味道,只剩下滚烫的印象。
头发也是从祖父头顶上的小木板上拿下来的,也用草纸包着,不知道是谁的头发,半截马鞭一样,每次,母亲只绞下一指宽。
三间大瓦房是我父亲工作后盖的,我在那里住到六岁,直到我们全家搬进了城市—除了我的祖父,他坚守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大瓦房也在大壕边上,而且紧贴着大壕,只要站在壕上,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三间窗明几净的大瓦房,东辽河边十几个村子里数一数二的大瓦房。它现在还在,但久已无人居住,它像一节空的木头,像一面回音壁,甚至像一座寺庙,它扩大着,30年前的轻语对话,到了今天还能听个朦胧。
三
我的五爷爷是家族的罪人,败光了家产,却没有任何人敢埋怨他半个字。他是那样挺拔和英俊,能说会道,懂规矩,有见识,即使他一文不名成了鳏夫,他的风度依旧能迷倒半城的闺秀。我的小奶奶是她的父亲在酒桌上划拳输给我五爷爷的,五爷爷手中的当铺虽然卖给了别人,但掌柜的除他之外没人可做。倒驴不倒架儿,他穿着礼服呢的棉袍子,戴着貂皮帽子,拄着文明棍儿,派头十足,不知底细的人以为他前途无量。小奶奶的父亲其实是故意失手输给他,谈笑间把自己最小的女儿许给他做了继室,以便结交下这个青年才俊,于是三十七岁的五爷爷娶了小他二十一岁的小奶奶。
小奶奶如今住在养老院五楼特护房间,因为腿脚不便已经多年没有下过楼,有一次回乡我父亲带我去看望她。
他们—我父亲和我小奶奶,曾经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过一段时间。我五爷爷不能生育,我祖父却有三個儿子,于是把最小的父亲过继给了他。当时他们还住在城里,小奶奶当初被迫无奈嫁给我五爷爷,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她要继续读书,但很快五爷爷就教给她做小买卖的本事,补贴家用,比如在集市上卖“铺衬”。这是我们东北的方言,随着这种东西的消失,这种说法也渐渐绝迹—那是一堆破布,五颜六色的,大小不均,人们买回去可以纳鞋底,补破了的衣裤,做百纳椅垫。布衣服很容易坏,即使是地主老财身上也难免打几块补丁,铺衬基本是每家必备的。
一天我父亲和小奶奶在集市上卖铺衬,那天阳光很好,但是人们没践踏过的地方雪还没有融化。父亲在那里跺着脚,开心地看着一个小伙子在小奶奶面前挑了一块红的又挑了一块绿的,那是那堆破布里最扎眼的两块。完了小伙子还不走,就在她面前用那两块铺衬当手帕,边甩边唱起了“王二姐思夫”。
你怎么能记得那样的事情?是你编出来的。小奶奶说。
“我没编。”我父亲说。
“你编的。”
“没有。”
他们很快共同回忆起那似是而非的一天中钟声和汽笛鸣响的一刻。那是镇上的小火车站的钟在响,汽笛声从三里外的煤矿上传来。世界迸发着欢乐。这是一九四八年冬天,东北解放了。那一年我父亲5岁,小奶奶16岁。我父亲只给他们当了十天儿子,因为野气难收,又被退回老家。
小奶奶在懵懂的年龄嫁给了五爷爷,还没等明白什么是夫妻,就迎来了解放,开始了回乡种田挨批斗的日子。除去了一身行头的五爷爷很快成了一个猥琐的老头儿,而且极端自私自利。饭桌上每出现一道好菜,他就划开筷子说“你吃你吃,你多吃点”,然后用筷子牢牢护在菜盘子上方,除他之外没人能夹走半根肉丝儿。几年之后,小奶奶成了这个乡村最奇异的存在。她一直有好衣裳穿,群众好像能容忍她一直穿着好看的衣裳。她长大了,被他训练得成了一个嘴巴特能说,满口大道理的女孩子—她做女孩子的时光没有随着早早出嫁而结束,五爷爷简直把她当成了自己女儿一样,任由她各种放肆—只要不干涉到他自身的享受。她凌厉又果断,用漂亮这个词来形容她让人觉得太不足够了。她面如银盘,身材丰满挺拔,是个有气场的女人,除了五爷爷之外的人很轻易会相信她所说的一切。
小奶奶曾在二十几岁时离家出走了一年,回来不久生下了我的小叔叔,我五爷爷非常友好地迎接了逃妻的归来,也很自然地过上了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日子。在去养老院回来的路上,我父亲说:“你小奶奶真是个倔强的女人,除了咱们家的人,她谁也不见。”我问他为什么。“因为你小叔是个傻子,她来城里后就决定再也不认这个儿子了,有了孙子也不认。”
我小叔生下来是个胖大小子,村里的孩子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面包”。“大面包”曾经是我小奶奶最得意的存在,她总是抱着他不停地亲他夸他。“大面包”到五岁才把话说清楚,十岁还在读一年级,十五岁还在尿床,却开始跟滞留村里不能返城的知青混在了一起。他们利用他偷鸡摸狗,偷姑娘的花裤衩儿。他脸上总挂着白痴的笑容,却对叫他“大面包”的人挥拳上来就打。
我小奶奶一直拒绝在人前承认她生了个不满意的儿子。在我小叔十岁之前的某一年,她又一次离家出走,去了我母亲所在的钢厂做了几年会计。小奶奶的样子一点也不像农村妇女,几句话就让招工的人相信她是一个管账的好手,来历不凡却不好问个清楚明白,仿佛那是对她的不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口号放在她身上一点也不适用。她天然地被人信任和仰慕,哪怕她不守妇道行为不端,她非凡的气质也让泼妇住口,野狗收声。在我五爷爷去世后,她拼着最后的力气给我小叔娶了个媳妇。五十几岁的她依旧有震撼人心的魅力,以村妇的身份嫁给了城里一个离休的副市长,从此离开了这个让她痛苦半生的村庄。
四
如果没有我小奶奶,我的母亲不会来到望山堡,我们也不会被带到这个世界上,为此她是我母亲一生的闺密,也是半生痛恨的人。在这个闭塞村庄,密友和仇人之于一个人的意义,也相差无几。
我的母亲并不是普通的农村妇女,她甚至不是辽河边上的人。她来自几百里以外的海边城市。外祖父是清末的翰林,家族是当地名符其实的大地主。母亲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她最大的姐姐嫁给了一个日军翻译官,后来成了汉奸,他们的大儿子比我母亲年龄还大几岁。我这个大表哥曾经隐瞒了出身考上了沈阳音乐学院,却最终还是被群众雪亮的眼睛发现,他被取消了学籍,从此成了一个对生活丧失信心的二流子,只能娶一个屠夫的女儿为妻。婚后除了酗酒,他唯一清醒的时分是陪着他毫无音乐天分的女儿练钢琴。为了让自己清醒的时间更长一点,他陪练很有耐心,尤其是假日里,酒钱不够的他坚定地坐在琴凳旁边,让女儿从早到晚不停地弹琴,直到她在一个夏天的黄昏弹完了钢琴十级的曲子《野蜂飞舞》,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
我母亲在数学上很有天分,高中时的表现已颇让老师刮目相看,但我大表哥的惨痛教训让她压根没想过自己能参加高考。她的数学天分跟我父亲的文学天分一样,因为压抑,缩小成一个卑微的硬硬的核儿,又渐渐融化稀释成为他们性格中的一部分。婚后很长一段时间,她都会在一天的家务之后,点起油灯做几何题,就跟我是靠读小说度过黯淡的青春一样,她用简洁利落的方式解析那些几何题,也用这种简洁利落的方式来收拾房间,用来抵抗那个闭塞的肮脏的山村。一直到她婚后多年,她還能辅导那些知识青年,让他们得以利用恢复高考的机会返城。
其实高中的学历在那时已可算是高材生了,母亲很容易就成为一个钢厂子弟小学的老师,就是在那里,她遇到了后来改变她命运的人—我小奶奶。
我的母亲是被我小奶奶在一九六四年带回东辽河大壕下的五间房的。五爷爷隔段时间就去厂里找领导哭诉,小奶奶没法干下去了。在回家之前几个月,她对我母亲进行了心机深沉的策划。她描述了一条美丽的河,河湾处有山,山下有个村子,村子里有一个年轻人,年纪小小就担起了全家的重担,照顾父亲和妹妹,还不放弃读书,是十里八村唯一的一个中专生。我母亲那时已经二十五岁,作为曾经的富贵之家的老闺女,她被宠爱过深,保护过度,见识过于狭窄,用她后来多次的慨叹来说,“很多事儿上都没有开窍”。小奶奶当时比我母亲大不了几岁,可她十五岁就嫁作人妇,我母亲二十五岁还不知道男人是怎么一回事。小奶奶早在认命回家的那刻起,就在物色一个伙伴,在那个无知蒙昧的山村,这个伙伴能让她得以抵抗今后漫长的悲惨岁月。她把我母亲拖进了深渊。
二十五岁的我母亲,她不知道自己已过了人生最好的年龄,也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即使后来回想起她在钢厂的岁月,也曾有几个男同事对她奉献过所谓的殷勤,可十七岁才来月经二十岁才开始戴胸罩的她根本没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也有人给她介绍过对象,在她看来这是污辱。她当时在想些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你姥爷生病了,他不让我回家,我整天想我妈,我妈被批斗,也不让我回家。”我的母亲无家可归,当小奶奶提议让她跟我父亲通信交往的时候,她没有拒绝。她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孩子,喜欢数学,却对写信这个词儿心中泛起一圈圈浪漫的涟漪,正是我父亲满纸毛主席语录的几封信,把我母亲骗到了东辽河边那个破落的村庄。
望山堡稀稀落落的几户破草房竖着。母亲是春天来到的,雪还没化完,到处都是泥,再到那个破烂的五间房一看,她整整沉默了三天。祖父、父亲和我的姑姑住在五间房的东间,西间住着大爷一家。缸里的米快见底了,炕上只有三床烂棉絮。父亲的大哥在祖母还在世的时候就去抚顺挖煤了,二哥在母亲去世不久做了遥远村庄一个独生女的倒插门女婿,他走前带走了他和父亲合盖的被褥。十二岁的父亲气愤极了,追了几十里路抢回了那卷破铺盖。“我一路哭着回来的,脸上都结了冰。”父亲说,“从那以后,我就是一家之主了,谁也别想欺负我们家。他们都叫我‘计计鬼子’,你爷被人卖了还坐炕头上傻点头,我不行,我不答应,我没妈了。”
母亲走了。人们都说她不会再来了。半年之后,她又一次来到了这个村庄。跟她一同来的,是四床崭新的被褥,全是绣花绸缎面儿的,还有一箱子衣服,有丝绸的、羊毛的、呢子的、凡立丁的,也有最时髦的灯芯绒的,以及一箱子锅碗瓢盆。“那些东西比她大十倍,”父亲说,“她没到村口就有人来喊我了,她两手空空被簇拥到我面前,那些东西都在别人手上。我不知道她怎么从火车站走过来的,十几里路。”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在望山堡住的时候,几乎每年,至多两年,我母亲家族中的一个人就会穿过这十几里的山路,带来比他们身体体积大几倍的东西,神奇地出现在村口。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张大圆桌,桌面足够十个人围坐,它像一个UFO一样出现,我望着背着它来的大舅家的儿子,我的表哥。那个黄昏他清秀的面容永远不会磨蚀,他既是一个大力士,又是一个魔术师,还是一个,童话里的王子。
我的外公在我母亲嫁过来之前就已死去,我的外婆我也从没见过,听说她是因为思念我母亲过度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母亲是她最疼宠的小女儿,她支持她远嫁,离开父母受屈辱的地方,嫁到成分好的人家,却在一次次去探望的人口中得知她遭的罪。我的外婆被自己当初的决定折磨着,在痛悔交加中,她一针一线绣了肚兜给她的外孙,如今那肚兜被我姐姐珍藏,据她所在大学艺术学院的教授鉴定,这种镶金纳银的“浮雕绣”,只有上世纪初满族旗人的大家闺秀才能绣得出。我的外婆,是正黄旗的格格。
母亲和父亲结婚的仪式是两只铺盖卷放在一起,炕头是我祖父的铺盖卷,紧接着是我姑姑,在我姑姑和我父母之间,我父亲在房梁上钉了几根钉子,挂上了一块布幔,布幔到炕梢,就是他们的新房。
五
“你母亲进门以后至少沮丧了十五年,”父亲要和我们密谋一般,悄悄地说,“直到你们长大,有了出息。”父亲讲到母亲的话题时我们已经长大,但却并不成熟,至少还没各自成家,但都上了大学。对父亲来说,能培养出三个大学生,是他一生至为骄傲的事情。这部分故事,因为与我们最为相关,因此父亲在讲述的时候用的语气也最为认真,甚至深情款款。不过他不情愿时,不会被哄骗说母亲的事情,如果催促他,他会变得很难为情,拒不开口。
父亲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能来跟他结婚,这是他一生也得不到答案的疑问,因此我们也就无从知晓,母亲是不会讲的,她提起年轻时候,只有一句——“我太傻”。
父亲结婚时还在中专读书,他才二十岁,不知道自己爱不爱这个比他大五岁的沉默的姑娘,但有一个人愿意替他管理这个破家,他心里的感激和期待胜过了一切别的情绪,让他只有接受的份,从未想过自己可以拒绝。何况,我小奶奶的话在家族里占有非凡的分量,我父亲人生中每遇到难题,都要找我小奶奶去商量,这份依赖一直持续到现在。能让我小奶奶不遗余力“骗”来的姑娘,遥远的海边的大家闺秀,大城市里吃过公粮的老师,他在她面前,除了自惭形秽不敢动别的念头。
我父亲原来的家不像个真正意义上的家,母亲的到来使这个家有了家的样子,但对我母亲来说,一夜之间,她从十指不沾阳春水的闺阁少女成为了里里外外都要操持的一家之主。她虽然寡言少语,但说出的话却又冷又硬,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这一辈子还没娶过媳妇呢,”父亲叹息,“没领过结婚证。”
到公社去登记的时候,女办事员看他们两人一前一后离了很远,不太像一对儿,问你们考虑好了吗?父亲说考虑好了,母亲没言语。办事员说我看你俩没考虑好。母亲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咋知道我们没考虑好呢?办事员被堵得慌,倔着就不给办,父亲想上前求几句情,母亲扭身就走了,再不肯去办手续。
我母亲的斩钉截铁,是我父亲一辈子也学不来的,说这件事的时候,他语气无奈,又带着欣赏。
“你们觉得你妈好看吗?”这个问题我的父亲问过不只一次。我们当然都会回答好看。我们无法评价父母的长相是否般配,我们的表情是嘻笑着的,替父亲感觉不好意思。但他却分外认真,一次比一次认真地问这个问题。我难以置信他会在意,谁会问出这种问题?可能只有在热恋中我们才会问别人,他好看吗?怕自己一片热心看重的人别人不喜欢。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你觉得什么样的女的算好看?”父亲很快回答了我,迅速得让我吃惊,仿佛他等这个提问已经太久,答案已经等不及地要冲出口来:“眉毛眼睛会动的,活泼的,会撒娇的!”
我曾经以为我的父母,是因为相爱才在一起的,要不然没法解释在那么艰苦的岁月里,他们怎么能齐心协力创造了望山堡的奇迹—一座崭新的大瓦房。而且从我记事起,从来没听见他们争吵过,顶多是我父亲声音变得急躁尖锐,通常时候我母亲是闷不作声,任随我父亲喊几句,但只要我母亲开口,他马上就会让声线变得温柔。无论如何,在那个年代,和和气气的夫妇如同传奇,这让我从小就感觉我们家是与众不同的。
“你妈最不爱吃高粱米,那时候这里主要产高粱,玉米都少,有点小麦,你妈真不应该上这来。1967年怀你哥的时候整天吐酸水,饿得大脖筋都挑不起来,就想吃点细粮。我偷偷带她去城里下饭店,求人家给她做了碗病号饭,一小盆菜肉馄饨,她全吃了,活过来了。回来三十里地,走半道上路过一户人家,院里有棵杏树,一树青杏,你妈不走了,盯着看。我央求人家卖我几斤,人家不要钱,一看就是小媳妇想吃酸,她坐那吃了一斤,精精神神回了家。”
“我还在读书,放假去你姑奶家,正赶上她家老大买了架缝纫机,老大媳妇嫌120块钱太贵跟他吵吵,我知道你妈喜欢这玩意儿,没事就去你小奶奶那鼓捣裁剪,就让他们转卖给我。那时候手里稍微有了点钱,你妈你姑你爷加上我天天打草,打一百捆草能卖3块钱,一秋天下来,挣了百八十块钱。我表弟骑车去取钱,半天不回来,回来告诉我你媳妇生了,儿子,四斤多,你当爸了。我臊得没法,不好意思连夜回家。”我父亲回忆往事时脸上仍旧浮现出当日的羞赧。
“你妈要说病了,那就是爬不起来了,只要能动她的嘴就闭得死紧,谁也不知道。”父亲说。说这话的时候母亲已躺在病床上,她跟老郭家历代的媳妇一样,将死于不可知的病症或后来被命名的癌症。我的母亲,一碗馄饨,一斤酸杏就能缓过来的人,一生几乎没生过病,最后一下子就是絕症,不可挽回。“她走了,我也活不长了,她不光是我妻子,还是我妈啊。”他对我说,脑袋微微倾斜,礼貌而凝固的声音,飘在医院的小花园里。
母亲去世三年后,父亲找了另一个女人,这是我母亲生前就预料得到的。他对那女人做的饭菜有近乎苛刻的要求,理由是他有糖尿病,但我知道他要求的是母亲的味道。同度一生风雨,她不是他喜欢的那种类型,世间却只有他记得和懂得这个沉默寡言的女人一生的点点滴滴,甚至一次又一次彼此磨损和消化,最终纳入了自己的肠胃。
六
自从有了缝纫机以后,村里人渐渐接受了我母亲这个格色的异乡人,她凭借娘家寄来的几本裁剪书渐渐成为十里八村手艺最好的裁缝。我父亲也毕业了,分配在农机厂做了技术工人,后来又做了厂长。这个家庭渐渐摆脱穷困,在村里也越来越被重视—“你爸是大工人(厂长),你妈会教书又会做巧活,俺们家怎么能跟你们比呀!”我儿时去小伙伴家玩,经常听到那些妇女这样跟我念叨,这养成了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优越感,进城后好长一段时间有些失落。
我父亲在农机厂,生产队的手扶拖拉机出了毛病要找他,谁家焊个猪圈门也要找他,我母亲也经常给乡亲们白做衣服。当我的父母想要盖一座砖瓦房的时候,那些年他们积攒的人情被通过各种形式还了回来。在所有建筑材料都不能随便买卖的岁月,有人帮忙去山里买房木,有人帮忙烧砖上山砸石料。我父亲跟生产队一讲,最豪横的车老板们也很爽快地出了七辆大车,拉了整整一天,把原来紧贴着大壕里侧那块洼地垫得比村东边的坟场还高。
“我爹在哪,家就在哪。”我父亲说,就这样望山堡的标志性建筑三间大瓦房在1970年建成了。不久这房子四周围上了一米高的石院套,院子里打了口洋井,从院门口到房门,红砖铺地,夹道种满芍药花、凤仙花、胭粉豆,一路开到屋门前。这里成了上面派来的干部、逢年节唱二人转的草台班子以及知识青年的落脚点。
那是我父母人生中最年富力强生机勃勃的岁月,对我来說却只是人生的开端。印象最深刻的是离开它的那个季节。西红柿已经罢园,宇宙间满是浓白的秋光,云朵澹澹,霜雪已在孕育。我的祖父站在屋门口向我们挥手,父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向他和房子跪下。“走吧走吧,我不拖累你们了,孩子念书是重要的事啊。”祖父终于因为心疼不过孙子每天往返20里路去上学,做主让父母带着孩子们进城,他因自己的决定惆怅着也自豪着,背着手转过身去,不再看我们。望山堡的小孩儿们嘻笑着爬上我们搬家的大卡车,我骄傲地对他们说,以后我是城里人了。
七
以上,这些所有的故事,都是我父亲说的,包括关于我的部分,也是通过他的讲述才成了我的记忆。几十年间,这些故事换了很多个版本,每次都有新的细节出现或发生微妙的变化,让我们听来并不觉得乏味,所以,这些故事是父亲的讲述在我的记忆中多次冲洗之后的显影定型……
至于离开了望山堡之后,我们家怎样在城市开始驻扎,我的父亲母亲怎样在城里找到自己体面尊严的位置,又是怎样把我们从那座小城送到大城市去开枝散叶,似乎因为与我们纠缠太密切而不必讲述。就是我们做儿女的,仿佛也不觉得它是我们家史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本身就在历史之中,羞怯于自己成为历史人物,又恐惧于它的难以描摹。
几年前的清明节,我们把母亲的骨灰埋进了老郭家的坟地,这并不是她生前的愿望—她一再表示过对望山堡的毫无留恋。天清地明也有时,那天从早晨开始天空中就下起雪来。我是坐飞机从广州来的,已在远离我故乡的那个南方生活了将近人生一半的光阴,不由得惊讶于此地顽固的寒冷。老郭家坟地的一角,土地依旧冰封,刨一个浅浅的只能容纳骨灰盒的土坑,也用了我们和帮忙的十几个本家亲戚小半天的时间。琐琐屑屑的春雪落在包裹母亲的黄绸布上,慢慢融化,晕染开来,在黑土间发出橙色的暖意。
就在这一天,我终于迈开步子向村子里头走去,奇异感丝丝缕缕,说不清它比记忆中更破败还是更繁荣。人家比从前密集,清一色白瓷片塑钢窗的楼座,它不再有昔日的疏朗,却令人更觉空空荡荡。
村路铺着水泥,雪一边下一边融化,像撒了一层薄盐,不再泥泞扬尘。曾经这条路上的蚱蜢像草一样绿,浆果成熟得就要爆裂。我孤独地穿过村庄,四周是弯曲的暗调。从村头到村尾,没有人影,没有母鸡下蛋的傲娇声,猪们饱食后的满足声,马车驴车辗压过土地发出的劳苦声,更没有呼喊孩子回家的母亲长长短短爱和怨的声音。
留守这个村庄的只剩下老人,就是那几位帮忙的本家,年轻人据说都在城里务工或是在外求学。
路的尽头是我家的三间大瓦房,如今它只是行将倒塌的废墟,我的一个本家叔父在跟我父亲商量把它盖起来,争取拆迁时换一套楼房。不久以后这个村庄将不复存在,人们将聚集在城市里,便于在这块土地上进行规模化的现代农场管理。所有散落的村庄——望山堡、四荒地、张家窝棚、严家坨子,将如一百年前一样,重新化为田野,却不再如一百年前一切皆有可能,自然已经定下界限叫我们不能越雷池一步。
不远处的大壕有积雪在闪光,我想起母亲临死前讲她做的梦。她几次梦见自己不停地从望山堡的大壕那边跨到这边,再从那边跨到这边,再从那边跨到这边,就像被卡住的录像带。我说,那你骑在大壕上吗?她说我没那么大的胯—这是她一生中少有的幽默。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老房子前面的几棵黑杨树,是我父亲当年亲手栽下的,无人照管长成蛮横粗野的样子,父亲摸着它们叹息,砍掉后只能当柴烧吧。叔父说,现在还有谁烧柴啊。
历史终究臣服于宏观语境,黎民小事只如附在枝干上的树叶,兀自枯荣。可若没有叶子,树也不是树。
雪停了,风过树梢,四无声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