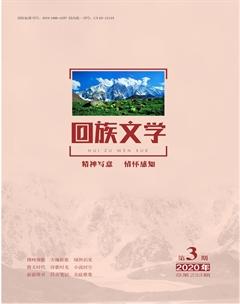新疆记忆
榆树沟记
在我的记忆里,沿乌鲁木齐市水磨沟河东行五公里就到榆树沟了。
据传,清朝乾隆年间,有一批到伊犁戍边的将士,去阜康县征集粮草时遭遇到一场特大的沙暴,人马误入天山深处迷失了方向,等他们东奔西闯地从天山边沿顺着榆树沟走出来的时侯,已经贻误了军令。无奈之下,他们就在榆树沟筑土为家,垦荒种田,植树造绿,繁衍生息,榆树沟逐渐成为一个自然村落。
村庄质朴、浑拙、静穆,人不过百,房是土坯房,冬暖夏凉。家家石块砌墙,户户清一色柴门。主人外出时把门拉吊一扣,只为拦挡牲畜,不提防行人。村庄虽然与乌鲁木齐市近在咫尺,但是村民没有被嘈杂、多彩的都市生活所浸染、改变。也许他们割舍不下自己的羊群,或不愿丢弃上苍赐予给他们的那一片泥土。他们依然保持着农家人朴素、自然的生活。男人们憨厚勤劳,进山放牧牛羊、采集草药,或去采石场开山打石头,女人们料理家务、耕种庄稼、侍弄菜园,只有聪明俊俏的后生、村姑追求五彩缤纷的都市生活,才到市里上班。
榆树沟南北长足有二公里,东西宽约半公里。一股潺潺的溪水从山里流出,村民把水引入沟里,在沟的入口处拦了一道土坝,成为一个蓄水池。池内蓄满了水,水面光洁而幽静,犹如农家女儿丢失在田间地头的一面镜子。
夏、秋季节,村民用池子里的水浇灌农田里的庄稼,菜畦里的蔬菜,也滋润着周围的空气,以及田埂沟畔色彩斑斓的野花、粗细不一的榆树。谁家要是浇麦,浇菜,打开蓄水池的出水口,一股清汪汪的细流就会顺着弯弯曲曲的沟渠款款而下,蕴入泥土。
流水清澈明净,一眼就能看得见鹅卵石筑成的渠底。鹅卵石上的青苔也在水中欢快地摇曳,既贪婪流水的清冽、纯净与多情,仿佛要随流水而去,但又舍不得放弃它们植根的坚硬光滑的鹅卵石,只好在那里摆首弄姿了。
榆树沟底、坡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榆树。大的一人摟抱不拢,小的高不过膝,但郁郁葱葱。到了春天,一树翠绿的榆钱开了,像翡翠、玛瑙、青玉,引来无数的蝶儿翩翩起舞。
看到这满沟散落的榆树,让我想起老家的榆树来。它们高大,挺拔,树冠直插云霄,木质坚硬,是农村盖房时的上好木料,大的当房梁,小的做檩条、椽子。每年的春季,由于粮食的短缺,榆钱还没有完全开放,母亲就开始忙着采摘了,用清水洗净,抓上几把面粉在面盆里一拌,摊在篦子上蒸着吃,或做成榆钱窝窝头。这些饭食,母亲是不让父亲、大哥吃的。母亲说,父亲、大哥是生产队里的劳力,站着像棵松,吐口吐沫砸个坑,不能亏了他们的力气。家里的干粮都得留给出力的人吃,母亲、嫂子、姐姐们则要吃这些榆钱馍。就是靠着这一榆树一榆树的榆钱的接济,我们一家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饥荒的春天。
榆树沟里土地平坦肥沃,施的是羊圈里自然发酵的羊粪,纯天然的有机肥,浇灌的是从大山里石头缝隙里渗出的溪水,是无任何污染的纯天然的矿泉水。无论是玉米、红薯、高粱还是西红柿、黄瓜、豆角、芹菜、韭菜、萝卜,无不生长得葱绿肥壮,口感、质地俱佳。每天早晨,他们采摘的蔬菜都要在溪流里冲洗掉泥土,去掉腐枝败叶,又一把一把地绑扎整齐。蔬菜新鲜、水灵,绿的菠菜、油菜、香芹,绿得玉翠一般,赏心悦目。拿在手里随便一甩,好像就能甩出菜叶里的绿色汁液来。红的西红柿、菜椒、水萝卜,红得鲜亮明净,透着诱人的灵气。熟透了的西红柿被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白纱,白纱颗粒均匀细腻,就像撒在红布上的一把白砂糖。用手掰开,绿的籽,沙的瓤,薄的皮,咬一口,就像沙地里种出来的西瓜,能叫人从头甜到脚。
榆树沟没有通到菜市场的柏油马路,都是高低不平的山坡小道。为方便卖菜,种菜人家里都养有毛驴,装满了蔬菜的架子车套上毛驴,女主人吆喝一声,听话温顺的毛驴就会把蔬菜拉到菜市场。一进菜市场,那些经常买菜的大妈、大爷们一眼就认出这是榆树沟的毛驴、蔬菜、女人。不但她们的蔬菜鲜亮,品质好,人也质朴、大方,不会缺斤短两,更不会哄抬物价。有人吆喝一声,大家都会围过来争相购买。
榆树沟的女人们由于清晨早起摘菜、洗菜、装车,等她们卖完一车菜回家时,早就累得疲乏不堪了。她们倒在空荡荡的毛驴车子里,一会儿就睡着了。这些温顺的毛驴会顺着来时的道,把它们的主人拉回家。等到了溪水旁,口渴了的毛驴低下头会喝一阵子溪水,喝饱喝足,打几个响鼻,啊儿啊儿叫唤几声,惊醒了睡在车子上的女主人。女人们跳下车子,拍打拍打身上的灰尘,抿抿凌乱的发际,捧起溪流里的水喝几口,这时才想起来回家。
冬季,落雪了。寂静、祥和的榆树沟犹如进入了一个雪的童话的世界,再也分不清哪里是农田、菜园、沟渠了。榆树的树冠完全被积雪罩住,只露着低矮的树干。在白雪的映照下,树干变成了黑褐色,褶皱里夹杂着花白的雪。一阵微风过后,簌簌的碎雪末儿从树冠上落下,或惊吓了正在这里觅食的雀儿。雀儿的惊叫会随着山谷的回音传得很远,有时就能惊掉树枝上的雪团儿,雀儿调皮,会抖着翅膀与掉落的雪团儿缠斗一番。
此时,绕村而行的溪流好像比夏季更欢实更活泼了,水也更透明清澈。水里还留有山的体温,冒出腾腾的热气,很快就形成白雾。它们像面纱、像丝绸一样缠绕着,升腾着,笼罩在溪流的四周。阳光下,一小团儿一小团的白雾聚了又散,散了又聚,反复着,永远不知道疲惫一样。冰雪已覆盖周围的泥土、山石、草木,溪两边的积雪已被细微的浪花拍打成冰。冰的形状极不规则,或高或低,或尖或圆,在薄雾里闪着白的光芒,晶莹剔透,五彩缤纷。
骤雪初歇。谁家的白鹅这时候口渴了,或是想到溪水里舒展舒展它们的筋骨了,就从柴门缝隙里穿越而过。白的羽毛,红的掌,顶着浅红的头冠,摇晃着肥胖的身躯,踏着松软的雪来到溪水里。它们伸长脖子,把整个身子潜到水里,又猛地抬起头来,使劲张开翅膀,快速拍打着翅膀上的水珠。水珠四散飘落,毛绒绒的雪地被水珠砸出一个一个的小坑来。白的雪、雾,鹅的羽毛,清的水,让人仿佛置身在江南水乡,或是在画里。不,是在梦里。
榆树沟人家淳朴厚道,崇尚自然,吃的是溪流里的水。水是活水,纯净新鲜,养人。他们认为山溪里的水是从大山里渗出来的,是大山的乳汁,是洁净之物,也是大山对子民的馈赠。但是,他们家家户户不用缸盛水。啥时候一担水桶里的水用完了,拿上桑木扁担,担上洋铁皮水桶就出门挑回一担,几乎每一天都吃到新鲜、洁净的水。
冬季天短,红艳艳的太阳还挂在西山坡上,不知道谁家女子忙着挑水做晚饭了。两只洋铁皮水桶在桑木扁担下打着晃悠,女子柔软的腰肢随水桶摇晃,一件大红衣服披在身上。白雪里,红衣服就像一团燃烧的火焰。火焰上下蹿动着,在溪流里舀水。溪水里袅袅的薄雾想包裹住这一团燃烧的火焰,但它怎么也包裹不住,倒是燃烧的火焰映红了那袅袅的薄雾、脚下的白雪、挂在西山坡上的太阳。
哦,这就是我记忆里的榆树沟!
板房沟记
我曾经在板房沟住过一段时间。
板房沟就是新疆乌鲁木齐县板房沟乡的一个自然村落。村庄不大,稀稀疏疏的房舍散落在一片坡地上,清一色的农家院落,盖着一溜五间堂屋。屋是平房,前后留有大玻璃窗户,明亮宽敞。房屋门脸儿一律用白石灰粉墙,倒显得素雅洁净。一座偌大的院子,一溜泥土院墙,细泥抹出的墙面,光滑而整洁。
家家户户堂屋门口种一架葡萄。每年给葡萄上足了肥料,浇灌了溪水,生长得葱绿茂盛。在密密麻麻的叶子下边,悬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的葡萄,坠得葡萄藤低低地垂着。葡萄是马奶子葡萄,新疆特有的品种,青绿的皮,个个饱满、挺括,青玉一般,成熟后生出一层白霜,像磨砂玻璃,温润、恬静。葡萄架下放有一个木床,床上铺一块绒毯。夜晚,如银的月光泼洒在庭院里,薄薄的烟霭笼罩着葡萄架,透过叶子的缝隙,斑斑驳驳烂银子似的月影落在葡萄架下的木床上、绒毯上、大个的葡萄上,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就着软软的夜晕在葡萄架下的木床上休息或者观天、赏月。
葡萄架外,人们都喜欢植几株月季、夹竹桃:月季花开得纷繁妖娆,轰轰烈烈,浓浓的香气;夹竹桃花儿开得绢洁、素雅、端正,花香清淡悠远。满院里都是花香。
这里人家喜欢在院落里种菜。菜园几乎占据了院子的三分之二,一年时新菜蔬不断。菜园里种的有西红柿、黄瓜、辣椒、豆角、青葱、茄子。他们不给蔬菜打农药,不施化肥,即使蔬菜生了虫子,也是主人蹲在菜畦里一只一只地逮。他们施的是清一色的羊粪、鸡粪,都是农家有机肥。蔬菜长得新鲜,品质好,绿的、红的、紫的鲜艳夺目,都是地地道道的绿色食品。
常有乌鲁木齐市到南山拉煤、送货物的卡车司机经过这里,路边停了车,随便叩开一户农家的院门,想求购几斤菜园的青菜。村里人淳朴厚道,一边忙着往葡萄架下让客,一边吆喝家里的人去菜园摘几把青菜,不管是香葱、茄子、西红柿,摘上一兜送给来客。但主人绝不收钱,总是哈哈一笑道:“自家院子里种的,你尝个新鲜。”
村子南面是山,当地人称作南山。山上是岩石,是茅草,是树林。树有松树、柏树、白桦树、钻天杨。顺着山根就是一条溪流,水是山里渗出的滴滴甘泉水,泉水凛冽、清爽,汇流在一起就成了溪。溪流从村中流过,把村庄一分为二。
这是一条什么样的溪流?七扭八拐,蜿蜒曲折,像截松软的井绳。溪里到处都是鹅卵石,大的如瓮、如斗,小的似拳、杏、桃、梨。卵石黑褐色,浸泡在水里的生有苔藓,苔藓翠碧、鲜亮、灵秀。水面倒不十分宽阔,但溪水清澈,明亮,溪水真干净,洁净得好像没有丝毫的杂质。深邃高远的天空中,闲适的云朵轻轻飘着,在溪水里倏来倏去,水底的卵石更是清晰可见。还有那游来游去的鱼,鱼是“狗鱼”——当地人对哲罗鲑的别称。这种鱼头部平扁,口裂大,鳞极细小,鳞上环片排列极为清晰;背部青褐色,腹部银白;头部、体侧有多数密集如粟粒状的暗黑色小十字形斑点。它们喜欢栖息在低温水流湍急的溪流里。我在新疆其他地方的河流里也见过这样的鱼,它们在卵石的缝隙里蹿来跑去,明亮的眼睛在水里一闪一闪的,轻盈灵活的尾巴在水里摇来摆去。有时它们会正对着激流静默着。
溪流两侧是舒缓平坦的坡地。坡地上也镶嵌着大大小小的卵石,在这些卵石周围的泥土里生长着毛茸茸的杂草、野花。杂草青绿翠碧,像绿色的绒毯。杂草里生长着山菊花、蒲公英,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花,这些缤纷的野花好像是谁绣在绒毯上的。它们开着蓝、粉、红、黄的花朵,散发着悠悠的花香,引来蜜蜂、蝴蝶翩跹起舞,飞来舞去。坡地上稀稀疏疏地散落着一些树木,有榆树、杨树、柳树,枝干粗壮,树冠茂密,不知名的鸟儿藏在里边不停地鸣唱。从牛栏、羊圈里跑出的牛犊、羊羔,在那里撒欢,啃毛茸茸的青草。
溪上建有两座桥。在村子上边,紧靠着山根是一座石桥。是大桥,三孔的拱桥。椭圆形的拱洞映在清澈明亮的溪水里,就像三面明亮的鏡子,让人分不清楚哪是桥,哪是印在溪底的桥影。桥面上铺了沥青路面,是出入山里山外的交通大道。顺着路朝下望,我们就像站在高高的山顶上,黝黑的路面就像一条舞动着的黑色绸带,远方的乌鲁木齐更像扣在苍茫大地上的一只小碗。
另一座是漫水桥。这是供溪流两侧村民生产、生活使用的。开春,南山上沟沟坎坎的积雪融化后的雪水或夏、秋季山里降了大雨,这些水就汇集到溪水里,溪水就会跟着暴涨,河床变得很宽,这个时候人们从漫水桥上赶着羊、牛去放牧,坐着套了驴、牛的地排车子到田地里劳作。
漫水桥的边沿,人们还栽了一溜石墩。一是作为桥的坐标,二是供行人踩着来回通行。一步远栽一个,都是从溪滩里捡来的卵石,样子极不规则,或大、或小、或长、或方,但底部都被匠人凿平了,固了水泥,平平稳稳地躺着或卧在那里。人们上山砍柴,放牧牛羊,收割两岸的庄稼,就踩着一个个石墩通过。溪水涨时,激流的水花拍打着羊的肚皮;怀里抱了鞭子的牧羊人走在石墩上,大声吆喝着羊群。逢到落日时刻,夕阳会把他们涂抹得金黄,影子拉得很长,印在波光潋滟的溪水里。我感到非常美,充满了诗意。可劳作了一天的人,谁会去欣赏这一份美呢?
我不知道这一溜石墩,能算是桥吗?!
漫水桥好像是新疆特有的桥,我在新疆其他地方也见到过这样的桥。所谓的漫水桥就是在水底修筑的水泥路面,水大时,水就从这路上漫过去,冲不塌。牲畜,车辆就可以沿路面涉水而过,无水时这桥又变成了路。
板房沟这条溪水穿村而过后,没有继续顺山势前行,而是朝前奔出一大截,拐了个大弯,便圈出一方土地。这满溪清清凌凌的水便湿润了这里的空气,同时也润泽、滋养了这片泥土。村民开垦了这里的泥土,土是黑土,松软肥沃,生长着土豆、蚕豆、豌豆。豌豆秧苍翠鲜嫩,绿得那样浓,浓得仿佛都能滴出来;嫩得像幼儿的手臂,带着茸茸的细毛,蓬蓬松松;绿茸茸的地块上就像谁泼洒了一地的绿漆。在这翠枝嫩叶间开满了淡紫色的豌豆花,花儿娇小,叶片单薄,但花姿轻盈,倒显得淡雅、端庄、清秀、静美,散发着丝丝幽香,引来成百上千的蝴蝶,在这里追逐,嬉戏。没有等豌豆长成,有口馋想尝鲜的人,就忙着掐豌豆尖,摘豌豆角了。
由于有了水的滋养,泥土的丰润,这里的土豆也比别处质地优良,个头大,光滑,味道甘美。每到秋天土豆丰收了,就會有络绎不绝的人从远路开着汽车来到这里采购土豆。
板房沟南面依山,遮挡住了南来北往的风。这里成了安详、静谧、寂寥的港湾。每当下雪的日子,雪片就悄无声息地,柔美、悠闲地,静静地飘落,很美!此时,这里一片幽静、安谧、肃穆,整个小村庄就像安眠在雪的世界里。
到了冬季,积雪覆盖了这里的一切。溪流上大大小小的黑褐色卵石就像盖了一床松软、银亮的被子,又像戴了一顶顶毛茸茸的银色的绒帽,溪水更加清澈、明净,水里的青苔好像更鲜绿;溪流上方笼罩了轻纱似的薄雾,丝丝缕缕的白色蒸汽在上方笼罩着,缥缥渺渺,白亮得晃人的眼,绕来绕去,一副永远无穷尽的样子。
劳作了一年的男人们到了冬季就停下手头的活计开始冬休了。他们带了夹子、绳套子到积满了厚厚白雪的南山去猎取野物。野物有斑鸠、山鸡、野兔,有时还套着野狗。女人们在家里烧热了火墙,家里炒了瓜子、豌豆,油炸了蚕豆,左右邻舍的妯娌们聚集在一起描凤画朵做针线活。男人打下了野味,就褪了皮毛,大锅炖煮,打开陈年的“伊犁马”老酒,酒是纯粮酿造,味香醇厚,纯正,甘美,大家就大口喝,喝得心热,一时兴起,索性放下酒杯,拿了滑雪板,踏着齐腰深的积雪,来到山坡下,找一块光滑的地面滑雪……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这样。
鲤鱼山拾遗
那时候,我们部队大院后面有一座山,叫鲤鱼山。
鲤鱼山东高西低,东窄西宽,最高处也不过二三百米,最低处只有十几米。山是土山,顶部舒缓平坦,山上无人居住。在西南方的山脚下,依傍着山势零星地散落了几户人家。这些人家的门外有平坦肥沃的黑土地,他们在这些土地上种菜,菜有油菜、莲花白、芹菜、西红柿、水萝卜、青葱、黄瓜。到了冬季,蔬菜收获完了,土地又被皑皑白雪覆盖,积雪多达一尺多深。门口是几棵粗壮的榆树,在两棵树之间绑了一根长木杆子,杆子有一掐多粗,是杨木;有的人家还养有奶牛,奶牛就拴在木杆子上。奶牛性情温顺,它们三三两两在榆树下悠闲地甩几下尾巴,时而抬头还“哞、哞”叫唤几声。
据传说,很早以前,乌鲁木齐是一条大河,河里住着一个鲤鱼精,后来竟长到十里长、三里宽,尾巴一摆能掀起几十丈高的大浪,经常淹没两岸的田园村庄。有一天,它摇头摆尾地撒野,差点拱翻了一个白胡子艄公的小船。老艄公伸手一抓,从天山博格达峰顶上抓下一块石头朝鱼头砸去,“咔嚓”一声巨响,鲤鱼精脑浆迸裂,从此鲤鱼就在此地化成一座山,便是现在的鲤鱼山。原来是太白金星下凡,惩治这个祸害生灵的鲤鱼精。
那时,我们部队在鲤鱼山上修建有一座水塔,为了保证水塔用水安全,我在的那个班就派到那里值勤。白天参加连队勤务、训练,夜晚站岗负责看护水塔。
那时,鲤鱼山上那纷繁妖娆的野山杏花,灿若烟霞的海棠果树的秋叶,凉如秋水的月色,寂静、悠然的飘雪,都给我留下难以忘却的记忆。
我们班的营房,是个一间半大的平房。里边的一间,是一溜能睡十几个人的大通铺,是用来睡觉休息的;外边半间是开会、学习、活动的场所。里间前后是两个大玻璃窗户,玻璃窗户大得像百货商店里的橱窗一样,我的铺盖就铺在玻璃窗户的下边。到了夜晚,一汪清凉的月光从窗里泼洒进来,我就像睡在月明地里一样。满天的星星好像就要落在我的身上,翻个身好像就要碰得这些星星乱动。冬天,两个窗户玻璃上挂着银亮的霜雪,开满了形态各异的窗花。门外是野杏树,窗后是海棠果树。野山杏也称作山杏,树枝乱蓬蓬的,枝条密密匝匝,像一丛丛的小灌木。海棠果树,树皮光滑,枝丫都在三尺以上,粗壮的枝子枝枝棱棱伸展着。门前是一小块空地,有一张石桌,两副石凳,平时用来下棋、休息或读书看报。房檐下边,一边种了两棵紫丁香树,一边种了两棵白杨树。紫丁香长得与屋檐一般齐,枝繁叶茂。紫色的花穗,芬芳浓烈,常常招引来成千成百的蜜蜂。白杨树高大茂盛,直溜溜的树干高出小屋一大截子,洒下一块厚厚的绿荫。两棵白杨树上拉了一道铁丝用来晾晒被褥、衣服。
出入小屋的是一条深远、悠长、蜿蜒曲折的小水泥路。路面弯弯曲曲的,像一条爬行的蚰蜒,两边是犬牙交错的野杏树。每到早春,野山杏树开花的时节,小路上就会落满了厚厚的一层粉的、红的、白的杏花瓣儿,散发出浓郁馨人的香气。幽远、曲折的小路犹如一条轻轻舞动的彩带,又宛如一条流淌着杏花的小溪。
野山杏花的花朵比杏花稍微小一点,但花朵稠密,花期长,花瓣红多白少,浓郁馥香。早期光秃秃的枝条上还没有长出叶片,只有一朵一朵的杏花,粉的、红的,灿若云霞;还有那一枚枚尚未绽放的花骨朵,它们在那里羞涩地抿着小嘴儿,似乎在那里排着长队,等待着春风掀开它们的花衣。
素有“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之称的新疆,有时候天气说变就变:那边野杏花儿开得正艳,一场纷纷扬扬的春雪就会不期而至。披裹了春雪的野山杏林如诗如画,粉的是花,白的是雪,像云霞,像烟霭,纷繁妖娆。此时,被覆盖了雪的原野、杏林、鲤鱼山,已让整日里缠绕于花间百般风流的雀儿,无处呢喃、嬉戏了,它们不得不站在落满了毛茸茸雪团儿的野杏花枝头上“叽叽喳喳”地脆鸣着,有时是独鸣,有时是合唱。性情急躁的雀儿根本耐不住性子在那里站着,不一会儿,它们就会扑棱着翅膀在落满了雪的枝头上掐起架来,扑棱棱扇动的翅膀惹得杏花瓣儿拌着雪茸儿簌簌飘落。不一会儿,白棉絮似的雪地上就会落满了灿然的杏花瓣。点点滴滴的花瓣犹如镶嵌在白玉上的一点点嫣红,好一幅精美绝伦的图画。真的,漂亮极了!也只有在新疆这样雄浑、广袤、神秘的土地上,才会有这般的豪情,浪漫的诗情画卷。
野山杏花盛开时节,每当执勤站岗到后半夜,鲤鱼山一片幽静、寂寥、肃穆,一切都睡着了,只剩下清凉如水的月色;皎洁如玉的月盘,霞蔚、深邃、悠远的夜空,稀疏的星星挂在天际。朗朗的月晕羞得这些上半夜里还无比璀璨的星儿,这会儿悄悄地隐去了自己的光华,把光彩留给了月儿。但月影里最俏丽的是杏花,浸了月晕的杏花娇羞而恬静,少了日间阳光的炽热,这时的花瓣光滑、圆润、饱满,开得无拘无束,像刚刚沐浴了的美少妇,朦胧里吐露着丝丝幽香。不知何时从月宫里飘来一丝儿清风,婆娑的花儿轻轻地抚弄着月影。花瓣轻轻飘落,这些落花似乎惊了夜的安谧、月的恬静,但也平添了无限情趣。
初夏6月,野山杏熟了。熟透后的杏子,散发出浓浓的香甜之气。这种香气弥漫了整个林子,同时也会塞满我们的小营房。野山杏个头长得比杏要小很多,表皮光滑,淡青中透著黄,吃着稍青涩,微甜,核大,肉薄而柴,因而极少有人食用。在野山杏成熟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们班除了担负执勤、站岗及其他一些勤务外,还要到野山杏林里去采收杏核。杏核晒干后,我们砸杏仁,把杏核立起来,用一块拳头大小的老鸹枕头﹙鹅卵石﹚轻轻地一磕,“咔”的一声就砸开了,杏仁骨碌碌地滚出来。杏仁饱满、圆润,洁白如玉。把这些杏仁送到炊事班,就成为我们连队的副食。到了冬、春季节,把杏仁在凉水里浸泡后,在开水锅里轻轻一焯,去掉那丝丝苦味,杏仁变得清脆,洁白,香甜。那时候,冬季还难以见到青菜,就用杏仁拌海带丝,杏仁拌胡萝卜丝;春季有了时令蔬菜,杏仁拌芫荽、菠菜、黄瓜。杏仁白如脂,芫荽、菠菜青碧如玉,浇上西北红艳艳的辣椒油,既悦人耳目,又开胃、败火。
有一次炊事班磨豆浆时,不知道是谁突发奇想,抓了几把杏仁加在里边,没有想到磨出的豆浆味道出乎预料地好,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味道非常别致。至今,我还常常忆起那种带有杏仁芳香的豆浆。
到了秋天,我们小营房后面的那片海棠果树林子,就像一片燃烧着的云霞。
由于新疆昼夜温差大的特点,还没有到落叶时节,海棠果树就已经红彤彤的云霞一般。单说海棠果树那些红叶,就够你饱享眼福了——它不同于深秋的枫叶展现给人们的是那一抹深红,更不同于柿叶红得那样热闹、火红,它们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瑟瑟秋风里唱着最后的赞歌。这时的海棠果树叶红得滋润,自然,恬静,婉约。一枚枚叶片泛着亮闪闪的光彩,好像充满着无限的生命力。在红叶覆盖的下边是层层叠叠的金黄的叶子,红的像火,黄的似金。这些都不算,还有那树枝上挂满的沉甸甸的海棠果,这些小果子别看个头小,个个都像化过妆一样,粉嘟嘟,亮晶晶的,犹如玛瑙、翠玉一般。海棠果:在我的家乡人们称为“甜子”,新疆有的地方叫“嘎啦果”,个头比苹果小些,熟透后,味道酸甜,香气馥郁,表皮光滑,乳白里透着红,晶莹、柔润。
那时,鲤鱼山这一带居民还很稀少,这片海棠果好像成为了我们部队自己的菜园子一样。每到休息日,就会有战友来到海棠果树林子里玩耍,他们一边欣赏灿烂浪漫的秋叶,一边采摘海棠果。在这里,他们似乎忘记了整日军事训练时的疲劳、枯燥;在这里,他们似乎放松了身心,赏玩秋叶,沐浴秋风,品尝海棠果。有时会玩到很晚,走时还不忘带回去一挎包果子。他们带着满心的愉悦,似乎有了几分薄醉,踏着悄无声息的一地凉月,披着一身的幽静秋夜,背着满包的香气,走回连队。
有一次,连队炊事班的赵班长,到鲤鱼山海棠果树林里欣赏秋色,品尝海棠果。赵班长是山西人,大高个子,黑瘦面皮,乡音浓重,有点探腰;为人实诚,炒一手酸辣土豆丝,烙一手改良了的山西卷饼。他看着鲤鱼山这些红艳艳、亮澄澄,香气扑鼻的海棠果,突然想到:咋不用这海棠果酿醋?这么优良的海棠果,一定能酿出好醋来!山西人喜醋,家家户户都会酿陈醋。柿子、谷糠、黍子、大米、小麦、小米、玉米、高粱都是酿醋的好材料。对山西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不能酿醋的。
后来赵班长还真的用海棠果酿出了果醋。这种醋甜润、柔滑、醇厚、绵长,透着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像又不是醋,有点像是酒。看着这些上等的美醋,有点出乎赵班长的预料。因为在他的家乡都用柿子酿醋,还没有用海棠果酿过醋,没有想到海棠果竟然酿出这般奇妙、口感上乘的好醋,也让这位酿醋能手连连惊叹。这醋比军人服务社里出售的谷糠醋、高粱醋、玉米醋、糯米醋都要好。一时间,海棠果醋在我们部队出了名,从五湖四海来到部队探亲的家属,都喜欢到我们连队品尝品尝这奇特的海棠果醋。就连回乡探亲的老战士,也要捎带两瓶子回去,他们把这醋当成了连队的土特产。
这些酸酸甜甜的海棠果,等入了冬我们还能吃到。那时,我们总是爬到高高的树梢上,看枝条上哪个果子大,哪个果子鲜亮,我们就摘哪个。怕碰坏了果皮,我们都是轻拿轻放,最后用信纸一个一个包裹好,放在床头柜的衣服里边。不几日,一股悠然、甜润的果香就会从床头柜里冒出来,这股香一直在小营房里弥漫。等进入冬季,天气冷了,我们也该换棉军装了,这时候打开床头柜拿出棉军装,顺便拿出存放在里边的海棠果。也到了吃掉它们的时候了,秋天里还是又脆、酸、甜的小果子,经过储存,释放出大量的香气,口感变成酥酥的,松软得就像老家沙土地里种出来的“花里虎”面瓜似的。但那一股子悠长的香气浸润在棉衣里边,我们走在队列里,整个连队都能闻到香味,好几天都飘散不尽。
吃着这沙面、香甜的果子,闻着这悠长的香气,让我想起了老家村西头的那棵棠梨树来。那棵棠梨树冠硕大,碧翠的叶子层层叠叠,遮住了半拉天。一块浓厚的绿荫,不知供多少下地劳作的人在此停脚歇息。粗大的树干上满是黑黢黢的褶皱,一个人都搂抱不过来,我们常常爬到树上摘棠梨。棠梨大如樱桃,圆如盘扣,汁液丰盈;古铜色,上面有黄色的碎斑点;酸极了,咬一口能倒掉牙,要经过捂后才好吃。在乡村也只有我们这些口馋的孩子们,才会想起来摘了棠梨,捂在村头的麦秸垛里。等过了霜降,铜钱厚的白霜包裹了大地、草木、麦秸垛,这时候,我们才想起捂在麦秸垛里的棠梨来。捂后的棠梨,似乎没有在枝头上时那般光洁、丰盈,表皮黧黑、干瘪,像小黑枣。但是,有一股浓浓的水果的香气,咬一点,香甜、沙面,味道绵长,极像熟了的鸭梨味。那时,我们从麦秸垛里掏出这些被捂得甜、沙面的棠梨,稀罕地藏在口袋里,一次拿出一个,一口还不舍得吃掉,要一点一点品,一个扣儿大小的棠梨,我们都要品好几口。
冬天到了,鲤鱼山白雪皑皑,银光闪亮,成为一个雪国。这时候,下雪是家常便饭,一下就是好几天。那些银亮纷扰的雪片,就像缤纷的梨花、樱花、苹果花,像飞舞的鹅毛、棉絮,又像泼洒的水银。鲤鱼山笼罩在银色雪国里,我们的小营房,门口的石凳,两株紫穗丁香,高大的白杨树,以及远远近近不知道名字的树木、枯草,都披满了银白的铠甲。此时的鲤鱼山幽静,肃穆,沉寂。
我们在野山杏林里踏雪、堆雪人、打雪仗、嬉戏,在海棠果树林里捉迷藏,大家闹着,笑着。有时我们脚下踩着两块竹板,沿着山顶上椭圆形的环山路滑跐溜﹙当地人叫滑雪﹚。从“鲤鱼头”的高处一直滑到“鲤鱼尾巴”的低处,滑到那里观赏被大雪覆盖了的胡杨林。
那时,在鲤鱼山西边“尾巴”的位置上,生长着一片高大挺拔、俊逸、洒脱、遒劲的胡杨林。夏天的胡杨枝繁叶茂,葱葱郁郁。秋天,树叶一片金黄。有时夕阳西斜的时候,“火烧云”把树梢涂抹得流光溢彩。一群暮归投宿的鸟儿藏在林子里“叽啾、叽叽啾”欢快地翠鸣个不停,它们似乎忘记了一天的疲劳。冬天的胡杨林,静谧、祥和、寂静,积雪覆盖了树冠,高大粗壮的树杆似乎低矮了许多。有时,纷纷扬扬的大雪一下就是两三天,毛茸茸的雪片把胡杨装扮得圆溜溜的,像故乡打麦场里的麦秸垛;地面上的茅草,枯枝,落叶被积雪覆盖得没有了一点踪迹,就像铺了一层又厚又白的雪毯。用脚轻轻一踩,“扑哧”一下子就把你陷进去。有时我们就势滚进去,凉丝丝的雪屑就灌到我们的脖颈里、脚脖子里。接连几天的大雪,枝头上的积雪越积越厚。有一个枯枝实在是支撑不住这些雪的重量,“咔嚓”一声,这一棵枯枝折了,一团耀眼的白雪“哗哗啦啦”滚落下来,这些雪砸在另一个枝头,一下子半拉树抖动起来,忽然间像是一股雪的瀑布从天而降。这时,落雪的沙沙声惊动了一对在树股子上憩息的夜莺夫妻,落雪也许惊动了它们的睡梦。看它们那个焦急的样子,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四处寻觅着是谁惊扰了它们的好梦。
有月的夜晚,胡杨林里漾着朗朗的青晕。一地的明光,亮如白昼。银亮的月夜里,清冷的月辉勾勒出胡杨林黑魆魆的倒影。这些星星点点,斑斑驳驳的倒影,倒映在白雪里,犹如那荡漾在烟波浩淼湖面里的点点帆船。
听说,现在的鲤鱼山已开发成了乌鲁木齐市最大的公园,成为当地居民游玩的一处盛景。那个水塔也早就移交给了地方自来水公司。 (篇名书法:武凯)
作者简介
孟凡民,河南范县人,现供职于中国石化,《中原》杂志编辑。作品散见于《地火》《西部散文选刊》《作家世界》等报刊。
[栏目编辑:黑正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