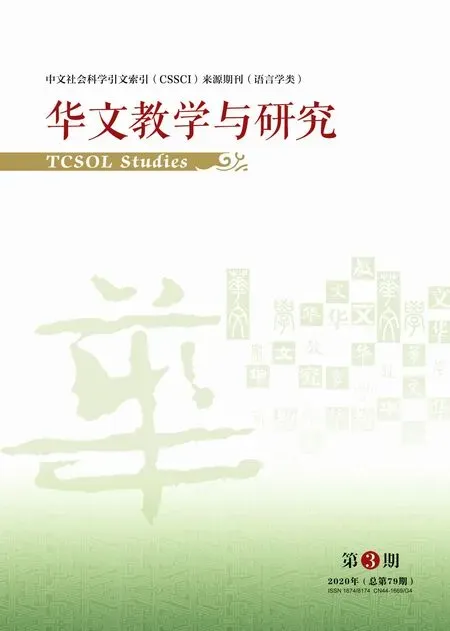欧洲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建设初探①
周敏康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翻译学院,西班牙,巴塞罗那08193)
1. 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名称争议
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从诞生至今,一直处在探索、争议和国际化的进程中。其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体现在汉语教学的学科名称上。在汉语的母语国——中国,近40 年来,就出现了如下各种名称:
1) 教 外 国 人 汉 语 (20 世 纪 50—70 年代),初始阶段,无人重视,认为是边缘课程;
2)对外汉语教学,吕必松于1978 年提出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学科。1983 年成立对外汉语研究学会,标志着这个名称成为正式的官方名称。因其具备学科发展与对外推广的双重特征,是延续至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学科名称。(吕必松,1997)
3)华语教学,关文新(1991)提出,但是该名称没有受到学界的普遍接受。究其原因,第一是与台湾地区的“华语文教学”或“华语”有直接雷同之处,第二是与面向华人华侨的“华文教学(育)”有相似之处。
4)对外汉语教育学,刘珣(1999)提出,因其单纯体现学术特质,至今尚未获得学界和社会的普遍认可,因此,其影响范围很小。
5)对外汉语学,潘文国(2004)提出,该名称是在质疑“对外汉语教学”这个名称的基础上提出的,但是至今尚未有更多学者使用这个名称作为学科名称。
6) 对外汉语语言学,周健 (2005) 提出,是对潘文国“对外汉语学”这个名称的质疑,不过这个名称至今在汉语教学界也没有被接纳或认可。
7)汉语国际教育,这是由国家官方机构——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07 年提出的,随后由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广,希望把汉语作为软实力推向国际。因此,目前汉语国际教育作为一个专业名称已经在大陆落地生根,作为学科名称则还处在学界辩论与探讨之中。
8)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这是借鉴欧美同类学科而引进到中国汉语教学界的一个国际通用的名称。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完整而科学的学科名称(张孝飞,2012),但在中国却没有得到广泛使用和普及。
在欧洲,如果一门外语的学科名称不能融入欧洲同类学科,是无法获得深入持久的发展的,汉语学科名称所携带的向外推广的特征恰恰是影响汉语走进欧洲和美国主流教育体系的主要阻碍之一。
从上述8 条学科名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官方确定的两个名称——“对外汉语”和“汉语国际教育”是目前在中国影响力最大、使用范围最广的,而这两个名称恰恰在欧洲是最有争议的。汉语在欧洲,作为第三外语的教学是极其普遍的现象。欧洲除英国和爱尔兰等以英文为母语的国家以外,第二语言教学普遍是英语教学。而在英国和爱尔兰,第二外语普遍是法语或西班牙语。目前在法国,汉语有趋势成长为第二语言。无论是第二语言教学,还是第三或第四语言教学,作为学科名称,总是以最高目标为宜。因此,汉语教学的学科名称在欧洲只能是、也应该是“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从英文来看,在欧美汉语教学界都普遍能够认可并接受的名称是:Teaching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or Foreign Language)(TCSL,即汉语二语教学)。中、欧在学科名称上的差别体现了中国与欧洲学者在汉语教学学科名称上的认识不同,所处的人文社会背景不同,看待同一事物的角度不同。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笔者认为,汉语若要作为外语走进欧美主流教育体系,其学科发展是必要的,而学科名称便是学科发展首先要解决的课题。
2. 欧洲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建设的基础理论体系
在探讨汉语二语教学的学科基础理论方面,按照时间顺序来看的话,吕必松(1997;1999)、刘珣 (1999;2000)、刘甦 (2000)、邓 守 信 (2003)、 王 路 江 (2003)、 程 棠(2004)、赵金铭(2005)、崔永华(2005)、陆俭 明 (2007)、 李 泉 (2009)、 吴 应 辉(2010)、李向农(2011)、王建勤(2013)、孙德 金 (2015)、 焦 占 威 (2017)、 崔 希 亮(2018)等,就汉语二语教学学科的独立性、跨学科性质、学科定位和发展以及汉语习得和文化传播等问题,已有不少有理有据的精彩见解。但是,从欧洲的汉语二语学科建设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汉语二语教学的学科基础理论体系应该更多地放在欧洲视角下的描述性理论研究上。
第一,欧洲汉语二语学科建设,其学科的独立性、性质和定位等都离不开欧洲其他二语教学学科理论的影响和基本框架范围。我们更加需要探讨并研究的是欧洲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建设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因为在欧洲,每个二语教学的学科发展目标是不同的,这与该语言母语国的政治、经济、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有关。
第二,欧洲有着悠久的汉语教学历史,研究汉语二语教学的学科历史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尽管欧洲四十多个国家的汉语教学发展参差不齐,但它们都是欧洲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国别汉语教学历史研究是欧洲汉语二语教学的学科理论研究所不能回避的领域。目前,欧洲汉语教学协会正在制定的“欧洲汉语教学白皮书”,恰恰是要在学科建设的框架内努力弥补汉语教学史理论上的不足。
第三,欧洲各国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直接影响着汉语学习者的习得心理和汉语学习的持久性。语言和文化心理障碍是汉语习得过程必须要逾越的两大障碍。欧洲各语言与汉语以及各自的文化特征、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对比研究及其成果,可以指导学习者有效习得汉语和中国文化。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有母语与汉语的比较研究,比如英汉、法汉、西汉、意汉、葡汉等对比研究的成果。我们在欧洲汉语二语学科建设中,将这些研究成果汇总起来,加以概括和理论提升,就能够逐步成为欧洲汉语二语教学学科的描述性理论方面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四,从欧洲语言角度来讲,汉语是从遥远的东方而来,具有极大的距离感,属于“远程语言”,汉语所蕴含的儒释道文化与欧洲语言携带的基督教文化更是截然不同。对汉语本质特征的描述性理论研究在欧洲尤其重要,它会形成与欧洲语言的全方位对照,这对欧洲汉语本土教师的培养有着重要参考意义和价值。
上述四个方面的理论研究是欧洲汉语教学界目前所面临的挑战,但是更紧迫的挑战来自应用理论体系的研究。
3. 欧洲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建设的应用理论体系
既然是应用性理论,就更加需要具有实际启发、指导与服务汉语二语教学实践的作用和价值。
欧洲汉语二语教学的应用性理论研究是围绕着“学”与“教”及其相互关系而展开的。欧盟自2010 年在大学全面推行“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以来,改变了大学传统的教学模式,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转移到以学生为中心。学生自主学习和社会实践是获得语言能力的主要途径。课堂教学中心的转移,在近五年来也逐步延伸到中小学的教学中。因此,欧洲的汉语二语教学学科的应用性理论主要研究如何让学生自己或主动习得汉语。为了能够培养学生靠自己或主动习得汉语的能力,就需要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和教材。我们看到,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学者与以汉语为外语的欧洲学者在应用性理论方面的重要分歧之一是语言教学的“一元论”和“二元论”。“一元论”主张以“词”为基本语言教学单位,以此组织汉语教学,同时作为汉语教材编写的主要依据;这是以“教”为中心的应用性理论。“二元论”则认为,汉语教学中有“字”与“词”这“两口锅”,两个基本单位(白乐桑,2018)。欧洲的汉语教学,从1840年诞生之初就以“字”为本位,这是从欧洲语言角度出发,看到了汉语的特殊性,从而认为汉语入门的简易途径是从汉字着手,借助汉字自身所具备的构词功能和表意功能来学习词语。而“一元论”绝大多数支持者的母语是汉语,是从自身母语角度去探索汉语二语教学的入门途径,无法体验以欧洲语言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的困扰与难点。笔者认为,在欧洲的汉语二语学科建设过程中,以“二元论”作为应用性理论,能够有效地构建汉语教学途径与方法,编写出适合欧洲各个阶段学生学习汉语的教材,最终能够符合“博洛尼亚进程”所倡导的以学生为主角的教学模式。
欧盟于21 世纪初制定并大力倡导、推行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CEFR)。对作为远程语言的汉语而言,这种基于近程语言特点的参考框架是对汉语教学发展和学科建设的窒息(周敏康,2017)。来自英国、参与欧盟汉语标准制定工作的张新生曾在2016 年指出:“欧洲汉语教学的发展离不开具有汉语自身特点的评估标准”。德国汉语教学界则指出,汉语水平考试HSK 的六级分类与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的六级语言标准是不能等同的。南欧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汉语教学界则认为,汉语教学与能力测试标准需要符合当地的汉语教学的实际发展现状与社会需求。欧洲汉语二语教学的应用性理论必须研究欧盟汉语能力的评估体系和标准,使其作为汉语教学应用性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大学的汉语专家学者于2010 年参与制定了欧洲汉语能力评估参考标准的A1 和A2。这个参考标准对欧盟境内的汉语教学起到了推动、规范和应用的积极作用,这也是对汉语二学科建设在应用性理论领域的重要贡献。欧洲汉语能力评估参考标准还有待进一步地完善,需要把B1、B2、C1、C2 四个水平的汉语能力评估参考标准制定出来。在这个方面,继续获得欧盟语言发展指导委员会的支持与资助是必不可缺的。
可以说,在应用性理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和研究需要大量人才去开展。欧洲汉语教学发展比较成规模的几个主要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以及这些国家的部分大学与欧洲汉语教学协会等单位和机构,都义不容辞地在积极推动汉语教学学科发展与建设所需要构筑的两大理论体系。
在本节最后,笔者展示两组数据,即中国汉语教学界对汉语学科建设和专业学科建设的关注程度(见图1、图2)。两图显示的关注度曲线,是指有关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和专业建设的论文发表数量。从这两个图我们看到,1985—2015 年,学界对汉语二语教学作为学科建设的关注度一直呈曲线上升趋势,而对汉语二语教学作为专业建设的关注度直到2000 年才开始,然后也一直呈曲线上升趋势,而2016—2017 年对两者的关注都落到低谷,从2018 年起对专业建设的关注度又开始回升。这说明汉语二语教学作为学科和专业的建设和发展并非那么一帆风顺,有曲折,有波动。 这需要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在欧、中之间进行必要的学术合作与共同探讨,才能不断推进欧洲汉语二语学科建设的认知与共识,从而在最短时间内真正建立起为学界大部学者和从业人员能够认同的欧洲汉语二语学科理论体系。

图1 :中国汉语教学界对汉语学科建设关注度

图2 :中国汉语教学界对汉语专业建设关注度
4. 欧洲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终极目标
欧洲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不仅仅停留在完善其两大理论体系上,更重要的是需要看到并找到其终极目标。早在21 世纪初,英国就开始探讨21 世纪汉语是否会像英语那样成为世界通用语言。BBC 在2010 年1 月初报道过英国儿童教育秘书长Ed.Balls 的观点:全英中学生都应有机会学习中文。①参见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education/8439959.stmJoseph Lo Boan⁃co(2011) 在 Linda Tsung 主编的 Teaching and Learning Chinese in Global Contexts②该书中译名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汉语教学与习得》。一书的序言中曾经预见到:中文将会像英文那样,走向国际 通 用 的 语 言 (lingua franca)。 张 新 生(2018)则指出:“汉语国际教育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努力使汉语具有类似英语一样的国际语言地位。”笔者认为,欧洲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也必须是将欧洲汉语教学发展成为与其他二语教学一样的规模与规范,提升汉语在欧洲乃至国际社会的使用率和影响力,最终能够在21 世纪成为国际通用的最主要的交际语言之一。
有学者认为笔者提出的终极目标过于远大。但是只要我们回顾一下国际通用语言的演变历史,就会发现,至今还没有一门自然语言在全球范围内通用几百年的,英语成为全世界范围内通用语言也只是最近一百年的事情。从历史上看,任何一门语言,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与地域盛行与通用,都与其统治的疆域有关,比如古希腊语的盛行时期是公元前1 世纪,其地域范围在今天的希腊及地中海周边岛屿;古意大利语是公元1—6 世纪,其地域范围在今天的意大利及地中海西岸和北岸;古阿拉伯语的盛行时期是7—15 世纪,其地域范围在今天的北非、中东以及地中海东南岸;拉丁语是13—15 世纪,其地域范围是在今天的西欧和南欧;西班牙语的盛行时期则是16—18 世纪,其地域范围是在今天的伊比利亚半岛和拉丁美洲;法语的盛行时期是18—19 世纪,其地域范围是在今天的法国、非洲大部分国家以及法国海外领地。如果加上古汉语,以上各大古代语言的盛行都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以及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一定的通用语言的意义,最后在这些地区演变成当地使用的现代官方语言,尚未有一门古代语言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通行。而英语自19 世纪末起至今,是在全球范围内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人类交际的通用语言,而汉语要发展成为像英语这样具全球通用意义的语言,必须参考三个标准:
使用该语言作为母语的国家数量;
使用该语言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数量;
使用该语言作为中小学官方外语教学语言的国家数量。
从目前全人类作为母语使用语言的人数来讲,汉语始终居首位,西班牙语居第二位,英语居第三位,如图3 所示。

图3 :全球作为母语使用语言的人数
英语在今天的国际通用语言中占首要地位,主要是其母语使用者在全球政治、经济、金融、科技和军事五大领域所拥有的强大力量,推动其自己的母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结果是英语在20 世纪成为国际通用的自然语言。可以预见的是英文的影响力和范围是目前21 世纪任何一门语言所不能替代的。因此,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目前汉语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以及它的影响力和使用率是以人口和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一旦汉语语区的经济发展遇到严重阻碍停滞不前,那么全球汉语热就会迅速降温。因此,欧洲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建设的终极目标就是借助目前中国经济腾飞的机遇,不断巩固汉语已有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引导并推动汉语朝着国际通用的自然语言方向发展。
根据前文提到的三个标准,前两个标准目前显然是做不到的,只有第三个标准可以从现在做起,即张新生(2018)指出的:“汉语二语教学需要进入当地中小学主流外语教学体系和大学汉语本硕专业体系。”另外,推动欧洲本土化教师队伍与培训体系的建立也是汉语二语学科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因为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欧洲汉语教学协会以及在欧洲各国的孔子学院在最近三年中一直不遗余力地合作,坚持每年在欧洲各国举办汉语教师培训班并颁发证书,参加培训的汉语教师均是来自欧洲各国的本土年轻教师。最后,继续推进欧盟汉语能力标准的制定工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目前欧盟汉语能力标准已经完成A1 和A2的标准制定,接下来需要分阶段继续研究并制定出B1 和B2 汉语能力标准,最后完成C1 和C2 的汉语能力标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人工智能呼之欲出的时代,汉语若能够抓住机遇,借科技发展的动力和优势,在21 世纪内将汉语提升到人类的通用语言之一是有可能的,也是有希望的。汉语即使不能成为他国的官方语言,但汉语的使用人数+人工智能应该可以弥补这个障碍。大家都使用自己的母语+人工智能(如自动翻译)进行交流,那么汉语使用人数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一旦汉语使用人数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其影响力的话,那么汉语作为中小学官方外语教学语言的国家数量也就会水到渠成,日益增加。
5. 构建欧洲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建设的几点建议
第一,笔者认为,学科建设不存在海内外之别,也不是以改变目前海内外汉语二语教学研究各自独立的局面为目的。恰恰相反,构建欧洲汉语二语教学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将全球范围内目前有关汉语二语教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项目,依照本文提出的基础理论研究体系与应用理论研究体系进行梳理、汇集和归类,将它们纳入清晰可见的、具有两大理论体系框架的大数据库内。既对以往的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作一个汇总、总结、提升,也为今后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指明方向。这是欧洲汉语二语教学建设的一个继往开来的做法,也是欧洲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建设必须要迈出的第一步。我们所处的大数据和信息科技时代,为欧洲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建设数据库建设提供了机遇和可行的外部条件。
第二,在欧洲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构建汉语二语学科的框架,需要清楚地将李泉(2009)提出的36个“研究”(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尚未提及的研究,如世界各国汉语教学的政策研究、汉语二语教学与其他语言二语教学的对比研究,汉语二语教学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研究、汉语二语教学的国际阻力与困境研究等)分别归入基础理论研究体系和应用理论体系两大框架内,才能体现学科的科学性与条理性。
第三,在构建学科框架的基础上,需要分两个方面来做具体的构建工作。首先,在基础理论研究体系框架内,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再细分成汉语二语教学的描述性理论研究和欧洲国别理论研究。对汉语语言本身特点的描述以及汉语教学特点的理论描述应该属于描述性理论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应该、也必须是跨学科的,因为它涉及到其他众多的人文和社会学科,如语言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社会语言学、国际汉学、国学、人类学、世界历史学等等,梳理欧洲汉语二语教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关系、相互作用以及互补效应应该归属于描述性理论研究领域。欧洲汉语二语教学的国别研究现在是、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必将是汉语教学在欧洲范围内成功、有效、健康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也是构建欧洲汉语二语教学基础理论体系的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在基础理论研究体系框架内不可或缺的是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尤其是欧洲的汉语教育史研究和欧洲的汉学史研究。其次,在应用理论体系框架内,笔者认为,欧洲汉语二语教学的策略、方法、教材、教学辅助手段如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等等都应该归属于应用理论研究体系。在这个体系内,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再细分为实证性研究(empirical study)和实验性研究(experimental study)。实证性研究包括:1)汉语学习者以及习得汉语过程的研究,汉语学习者的母语及其文化背景,汉语学习者的学习目的、动机和社会影响来源;2)欧洲汉语教师的母语及其文化背景与汉语学习者的母语及其文化的课堂与课外互动研究,汉语教师素养对汉语教学成败的案例与分析等。实验性研究包括:1)有关汉语二语教学的数据及其分析结果报告;2)欧洲汉语教学所在国的政治、经济、贸易、社会、文化和就业市场的数据搜集;欧洲汉语教学所在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的数据及其对汉语教学发展的影响趋向和量化分析。
第四,正如上面所阐述的,汉语教学的终极目标是朝着国际通用语言的方向努力与发展,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道路。在尚未实现这个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承认并接受这样的事实:今天全球的通用语言依然是英语。在欧洲范围内要将我们的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建设起来,相关研究成果的发表与传播至关重要。据笔者对中国知网和国际通用的Google Scholar Metrics (2020 版) 的初步调查研究发现,目前98%以上的有关汉语二语教学理论和研究的学术论文都是用汉语撰写并发表在国内的学术刊物上的,用英文撰写的相关论文则寥寥无几。在国际前100 位的中文学术刊物排名中,尚未有一本有关汉语教学理论与研究的刊物上榜。这是汉语教学理论与研究领域的短板,也是在新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即:在21 世纪,我们需要站在国际的舞台上,用国际眼光来继续推动并发展汉语二语教学理论与研究建设,并且能够用英语发表相关的学术论文。同时,笔者认为,需要考虑将国内最优秀的汉语教学理论与研究的学术刊物以汉、英双语形式、用各种途径推向欧洲和国际学术界,从而在国际语言二语教学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这也是构架欧洲汉语二语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学者具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和背景,笔者认为,实现这一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也是中国汉语二语教学界年轻一代学者的责任。同时,本学科领域的英语或汉、英双语学术刊物也为海外广大从事汉语二语教学理论与研究的学者及一线教师提供发表英文学术论文的平台,这对推动汉语二语教学理论研究以及学科建设走向国际化提供了最有效的动力,也为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建设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创造了极其有利的客观、外部条件。
第五,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建设的属性和范畴决定了该学科不仅仅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而且必定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因此,学科建设国际化合作是必经之路。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亚太地区国际汉语教学学会,欧洲汉语教学协会和美国中文教师学会,而且涵盖亚太地区和亚欧美三大洲的三个学会已经结成联盟,在三大洲一起协调汉语教学研究,共同推动汉语教学的理论研究以及学科建设研究,每年定期举办国际研讨会或工作坊。总部设在北京的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也积极联络这些学会,共同探讨更大范围内的合作,一起推动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在欧洲、乃至全球范围的建设工作。其次,我们认为,汉语二语教学学科除了在其母语国家——中国建设以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应该在汉语非母语的国家。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视欧洲各国汉语教学发展情况而分先后推进。比如在欧洲建设汉语二语学科,需要欧洲各国之间区域性的合作,需要欧盟有关机构以及欧洲汉语教学协会发挥推动和协调的作用。尽管欧洲的汉语教学的现状各不相同,但是通过各国学者、教师和科研人员之间的定期性的学术往来、互动交流和科研协调,欧洲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建设必将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共同目标,可以缩短欧洲各国之间在汉语教学学科建设方面的差距。而跨大洋的国际合作,在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建设领域,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实质性的推动工作:
1)以国际三大汉语教学学会的合作为联盟基础,加上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的参与,争取在中、短期内创办一本由全球汉语二语教学界资深学者和专家参与的国际性汉语二语教学学科研究汉英双语学术刊物,搭建全球范围内的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建设的理论研究平台。
2)建立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建设的国际学术论坛,在世界各地定期举办学科建设论坛,其宗旨在于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学术理论研究的发展,扩大汉语二语教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3)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欧、美三大洲的大学汉语教学单位的合作交流、互动与联合,在三大洲轮流举办全球汉语二语教学学科研究者的交流讲习班,为汉语教学研究者的素质提升和升华提供指导性的信息、研究课题以及合作平台,因为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建设最终离不开人的要素。
6. 结语
欧洲汉语二语教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欧洲及国际上需要推手,这个推手包括理论研究推手和教学实践推手。欧洲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建设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明确而可行的,对终极目标的认识是欧洲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充分了解汉语教学的终极目标是汉语教学在欧洲范围内得以平稳发展的必要条件。汉语作为二语教学学科在欧洲范围的建设与发展,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尽快建立描述性基础理论体系以及以“二元论”为依据的、以欧洲汉语能力标准为准绳的应用性理论体系。要做到这两点,需要发展欧、中和欧、亚、美之间的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学术交流平台。最后,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建设走向国际化,需要该领域的学者具备国际眼光和树立长远目标,站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参与学科建设的学术互动、学术探讨和学术研究。三大洲的汉语教学学会组成的国际联盟为汉语二语教学学科建设的国际合作,为该领域的海内外研究学者互动交流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