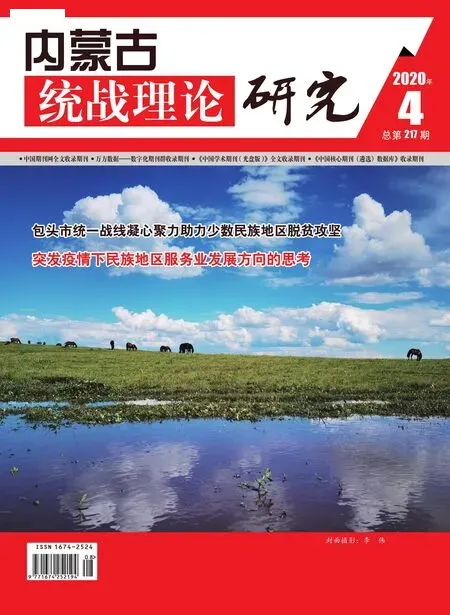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与依法治国研究
◇ 文/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 刘晓霞
自从人类用双手开始创造性的劳动、用人类特有的灵性发出思考后,人类就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探索人类的主观世界,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一系列维系道德人心、维持一定社会秩序的精神规范,更创造了博大精深、义理精微的法律文化。可以这样说,在人类创造的以上诸种精神文化成果中,法律文化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社会现象。作为一项人类的精神成果,法律文化往往集中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身、调节社会、谋求发展的各个阶段中的思想和行动。
一、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涵及其表现特征
中华文化,又称为华夏文化、汉文化,是指以中原文化为基础而经过不断演化、发展而形成的中国特有文化。其经历了千年以上的时间演变,经历了中国各大古代文明长期相互影响与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是随着国家与法的产生而产生的,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法律文化是社会经济基础的直接、集中反映,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源可以追溯到我国原始社会的尧舜禹时期,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其内容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的特征。
(一)在认知结构上,将犯罪与人性恶,将法律与刑罚联系在一起思考。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刑就是法。法家的商鞅认为,法治之所以必要,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法治是基于人性特点而可能采取的最好的治国手段。他认为“好利恶害”是人的天然本性。他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故民生则计利,死则忧民,民利则所出,不可不重也。”人一生忙忙碌碌,总想富贵,这种想法只有到死才能停止:“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这种追求富贵和财富的好利本性不仅存在于一般人,即使有名的圣君也不能例外:“一兔走,百人逐之……尧舜禹汤如鹜焉而逐之。”正是由于“人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矣。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在商鞅看来,好利恶害的本性人皆有之,这种人性,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并且不可改变,因此,不能用所谓的仁义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只能实行法治。
儒家的董仲舒认为,善恶二性的表现是因人而异的,他把人的品性分为三等,即所谓“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他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圣人之性是天生的善性,斗筲之性是天生的恶性,都是不可改变的,因此,都不可以叫做性。只有中民之性,可以叫做性。中民之性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关键在于教化。他把中民之性比作原始材料,把“善”比作加工后的成品。为政必须“以教化为大务”,把教化置于首位,当教化不能奏效时,再使用刑罚。
(二)在心态结构上,强调“礼法合一”、“德主刑辅”。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构成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最本质的特征。“礼”字在殷商时期已经出现,其起源于祭祀。“礼治”的基本原则是“尊尊”与“亲亲”。“尊尊”的要求是小宗服从大宗,下级贵族忠于上级贵族而不许犯上作乱。“亲亲”的要求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管什么人,只要不慈、不孝、不友、不恭,既是礼之所禁,也为刑所不容。这就叫做“出于礼,入于刑”。孔子从“礼”与“仁”结合的思想出发,特别重视“德”的作用,主张“为政以德”。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礼德与刑罚相比,孔子强调的是礼德而不是刑罚。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政令和刑罚这种强制手段来治民,只能使人民暂时免于犯罪,却不能使人民感到犯罪可耻;只有以礼德为治,才能使人民有羞耻之心,而从内心归服。孔子总是强调道德教化,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这就是他首倡的“德主刑辅”说。
董仲舒很重视吸取秦王朝灭亡的教训,他向汉武帝提出“更化”的主张,其基本精神就是强调教化,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不过,在德与刑两手之中,董仲舒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先德而后刑。他说:“刑者,德之辅,”“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以不相顺。”他从儒家的传统思想出发,主张“明德慎罚”,主张“厚其德而简其刑”,反对“刑戮妄加”和“诛杀无罪”。
(三)在评价结构上,主张息事宁人,平争止讼。“息讼”思想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我们知道儒家思想的创立者主要是孔子,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和杰出的思想家。他提出的以伦理为核心,以“礼治”、“德治”、“人治”相结合的一套主张,对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与西方法律更加强调个人权利的保护与重视诉讼权利的行使不同的是,儒家思想更加强调整体的和谐,而往往忽视个体的权利。儒家思想所追求的整体和谐要求人们在发生冲突时不要明辨是非,而是要尽量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儒家主张,在与伦理道德相比时,法律始终是处在次要地位的,所以要以“礼治”作为解决纠纷的主要手段。孔子就曾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由此可见,儒家并不主张人们在发生纠纷时对簿公堂,互撕脸皮,而是通过道德教化这样一种方式来使当事人达成自行和解的道德品质,以此来达到“息讼”或“无讼”的境界。受此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在立法、司法上特别强调“重义轻利”。这里的“义”是指伦理纲常;“利”其实是指个人权益。而反映在立法上则表现为对个人权益的漠视;反映在司法上表现为法官对纠纷作出裁判时要更多的考量伦理道德,尤其要保证伦理关系优于财产关系,以此来达到最高的司法价值取向——“无讼”和秩序和谐。
(四)从法律行为模式结构看,传统法律文化把培养集体导向的人作为一个基本目标。法律行为模式是指在相同法律文化的影响下,大多数人在相同的情境下会做出同样的事情。人们在行为时首先考虑的外界的文化标准、社会对自己的期望、别人的议论、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个人只有接受了社会认可的标准才不会被认为是越轨分子而受到法律的制裁。在西方社会中,法律文化鼓励个人在广泛的范围内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为,自主地安排个人生活,这种选择和安排是以个人为导向,也就是说,行为人首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利益、个人的价值和个人的兴趣。而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主张以国家利益为本位,强调皇权至上,权大于法,法律受权力的支配和制约,是实现君主专制的工具。首先,在立法上,法自君出,君主为最高的法权渊源,“朕即国家”、“朕即法律”;其次,在司法上,行政长官监理司法,司法与行政合一;最后,在法律结构体系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表现为公法与私法不分,诉讼法与实体法不分,以刑法为核心的单一、封闭的法律体系。
二、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存在的根源追溯
(一)经济层面——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方式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不仅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还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中国古代的农业主要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产生于春秋时期,其特点是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精耕细作;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其生产出来的产品用来自己消费或缴纳赋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民以食为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古代中国人的主要生活方式。“国以农为本”,“重农抑商”成为中国古代的基本国策。这种小农经济和小生产方式孕育出一种与海洋民族商业文化热衷冒险、求华求新所不同的重视民生、崇拜君权、追求和谐统一、提倡“中庸”稳定的文化心理。
(二)政治层面——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
广阔的地域、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是集权与专制政体的基础。建立在宗法等级关系上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这种政治制度要求法律文化与之适应,因此,确立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力,维持界限分明的官僚等级机构和对民众的控制,即“治国”、“治吏”、“治民”成为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内容。
(三)社会层面——宗法家族的社会组织结构
在中国古代,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社会关系。宗法制源于原始社会的父系制家长制,是处理家族内部关系的习惯准则,后来与国家政治相结合,家国一体,君父合一,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古代法制维护的重要内容。它注重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伦常关系,以“亲亲”的血缘合同,以“尊尊”的等级差别,强调大宗对小宗的支配,小宗对大宗的服从,尊长对卑幼的仁爱,卑幼对尊长的侍奉,以及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等。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法律文化,不仅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法伦理色彩,而且一直以体现宗法等级的纲常礼义作为中心和指导原则。
(四)意识形态层面——神权思想占统治地位
神权思想是由原始的宗教迷信发展而来的。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差,对周围的事物不能正确地解释,于是就产生了超自然的力量。进入阶级社会后,宗教迷信被打上阶级烙印,形成了“君权神授”、“代天刑罚”说,后来又形成了“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和以宗法思想为核心的“礼治”思想。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国家主义为思想意识的主导,也就是在社会生活与国家生活中坚持重集体轻个人的基本价值取向。
三、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对我国依法治国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执法公正、严明的思想
在执法方面,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素有刚正不阿、执法严明的好传统。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公平”,使部队“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在诸葛亮的调教下,蜀军以弱抗强,在崇山峻岭之中来去自如,“进退如风”,高度的机动力使蜀军屡屡掌握战役的主动权。包拯执法如山、铁面无私、惩治贪赃枉法的皇亲国戚、朝廷要员等,为百姓申冤报仇。海瑞清正廉洁、秉公执法。以上的古代人物的做法都和这一传统一脉相承。他们的事迹,一直为后人称颂,时至今日,仍然受到到广大群众的崇敬与赞扬。这种刚正清廉、秉公执法的精神,也是我们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不可缺少的。
2、德刑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
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重视道德教化,重视犯罪预防,主张先富后教、德刑结合、德主刑辅、刑罪相称,反对酷刑滥罚、族刑株连和轻罪重罚。孔子从“礼”与“仁”结合的思想出发,特别重视“德”的作用,主张“为政以德”。礼德与刑罚相比,孔子强调的是礼德而不是刑罚。用政令和刑罚这种强制手段来治民,只能使人民暂时免于犯罪,却不能使人民感到犯罪可耻;只有以礼德为治,才能使人民有羞耻之心,而从内心归服。孔子总是强调道德教化,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这就是他首倡的“德主刑辅”说。新时代,我们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就是从这里借鉴来的。我们要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3、“息讼”思想
“息讼”思想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与西方法律更加强调个人权利的保护与重视诉讼权利的行使不同的是,儒家思想更加强调整体的和谐,而往往忽视个体的权利。儒家思想所追求的整体和谐要求人们在发生冲突时不要明辨是非,而是要尽量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这种“息讼”思想其实就是主张通过调解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与对簿公堂相比,有利于迅速解决民间的纠纷,防止社会矛盾的激化,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由于大量的纠纷得以通过非诉讼的途径解决,则在客观上减少了审判机关的压力,使审判机关集中精力处理重大或复杂的案件,有利于提高诉讼的效率。
4、因时制法、事断于法的思想
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重视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主张因时制法、事断于法、以法治国,强调法律的严肃性、统一性和稳定性,主张刑无等级、法不阿贵,反对以私害法。这对后世法治理念的形成是有极大意义的。
(二)消极影响
1、人治观念
虽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德主刑辅,但与此相适应,在对待“人”与“法”上,他重“人”而轻“法”,极力夸大当权者个人的作用,相对来说,贬低法律的作用。他认为国家的治乱,全系于当权者是否贤明,而不在于法律制度的好坏和有无。
2、封建等级观念
中国古代的家庭,始终保持以父权为中心,以长子继承权为中轴的宗法制的特性,家长拥有专制的特权。这种家长独裁模式,构成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基础。封建国家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庭,君主就是放大了独裁家长。儒家为此设计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关系,后来又提出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规定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为君、为父、为夫的。于是,整个封建社会,不仅是以家庭为本位,而且被严密地罩上了一张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等级观念为特色的封建伦理网络。
3、特权思想
中国古代的特权思想主要表现为官僚特权,就是官僚依法享有众多特权。官员高踞于民众之上,一贯强行为民作主,实即民之主宰,并按不同级别,在居住、服饰、出行等方面,享受诸多特权。这种本性野蛮凶残、专横暴戾,表面上却打着儒家仁义道德旗号的特权专制制度,在处理狱讼,在对百姓进行横征暴敛时,其滥权的特性表现得特别露骨和淋漓尽致。对待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官员们可因稍不遂意就无端制造罪名,进行抓捕,而一旦投入监牢,又无钱打点,囚犯就会随时面临死亡。
4、重刑法、轻民法
与西方法律相比,中国古代法律表现出重刑轻民,民附于刑,诸法合体,民事法律极不发达的特点。从公元前二世纪秦朝统一中国始到公元二十世纪的清朝,历代王朝的法律都采取以刑为主、刑民不分的编纂形式,即在一部法典中,既包括民事部分,也包括刑法、行政法、商法、诉讼法混合在一起,始终没有颁布过一部民法典。
5、司法与行政合一,司法从属于行政
我国历代司法机关都是从属于行政部门的一个分支机构,是朝廷的职能部门之一,而不具有独立性。从地方到中央,司法都是从属于行政的。在中央,秦汉的廷尉是中央政府的九卿之一,刑部在唐宋明清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六部之一,但这些司法机关都要绝对服从皇帝的命令,一般都要受制于丞相、内阁等中央行政中枢。而在地方上,司法更是处于行政的从属地位。
6、义务本位
古代中国强调个人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义务,在法律条文上多禁止性规范,而少权利性规范,忽略人的独立人格、自由、尊严和利益。义务本位无法激起个体守法和护法的主动意愿,其后果就是压抑了人们的权利观念,有碍法律思想的发展。
四、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对依法治国的借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面临新形势、立足新起点,也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机遇。在十九大报告中,“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被明确作为十四条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当前我们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不能否定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对我国现代法治的贡献,斩断其与现代法治之间的内在关联。既然传统法律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就应该抱着批判继承的态度,既反对对古代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拿来,兼收并蓄;也反对否定一切的民族虚无主义。要在揭露中扬弃,在批判中吸收。只有这样才能继承与发扬历史上的法律文化优秀成果,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为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服务。
(一)立法上要恪守和发扬传统法律文化中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要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推进民主立法。民主立法的关键在于坚持立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使立法反映人民的意志、得到人民的拥护。坚持人民有所呼、立法有所应,加强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领域的立法,用法理呵护百姓幸福生活。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健全立法机关与社会公众沟通机制,做到广察民情、广纳民意、广聚民智。完善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让立法直达基层、直通群众、更接地气。
(二)执法上要充分发扬传统法律文化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传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为政以德就是对为政者的品德方面的要求。今日中国,评价党员干部是否合格,守法是必然的要求,而守德也是非常重要的。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就是要使这个“关键少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这里的“明大德”就是要铸牢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使其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守公德”就是要领导干部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严私德”就是要领导干部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
(三)司法上要牢牢守住公正这个生命线,“公之于法”“得乎其中”,重情明理依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我们常说,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政法机关按照党中央部署,深入推进以司法责任制为重点的司法体制改革,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增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五、总结
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重视历史的好传统。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变革,批判继承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不但可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实行依法治国服务,而且也可以增强我们维护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自觉性,让法治成为全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以此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让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