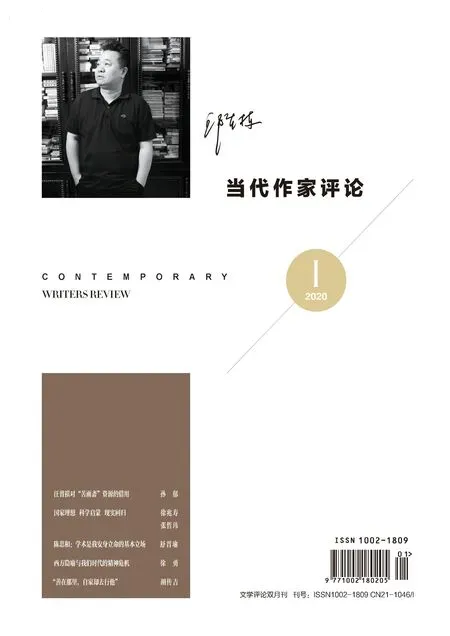弱者的反抗与莫言文学的崇高美学
王金胜
莫言文学的崇高品格,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其与中国历史、现实之间存在的结构性关联。对中国历史、现实的感知,构成莫言史诗性崇高美学的情思质地,轰轰烈烈的历史运动、紧张惨烈的政治斗争、全景式观照视野、与历史紧密纠缠的蛮野生命、超自然的意志和力量,被莫言或轻灵滞重地而勾画、涂抹出来,散发着豪荡、雄浑、劲健的崇高气质。
应该看到,新文学中崇尚“强力”“阳刚”一脉对莫言文学的影响,但阳刚美学难以涵盖莫言崇高美学的全部。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反思革命”和“反崇高”的文化氛围中,莫言亦有与此“反思”取向的呼应,但他又通过汲取以鲁迅为代表的崇高另脉,形成自身另类的“阴性崇高”特质。莫言文学也就成了阳刚崇高美学与阴性崇高美学的双重变奏。
一、“阴性崇高”:莫言崇高美学的重要面向
莫言笔下的人物,即便生命力强悍旺健如余占鳌、戴凤莲(《红高粱家族》),孙国栋(《司令的女人》),司马库、司马粮(《丰乳肥臀》),孙丙(《檀香刑》),在强大的社会秩序和激荡的历史洪流中,也不复经典崇高美学中英雄的神性。但这些“反英雄”的英雄塑造,恰恰体现着莫言“反崇高”的崇高美学,或许,将莫言笔下的这些人物称为英雄的“反英雄化”更为合理。莫言借助“反英雄”的英雄营构崇高美学,笔下常带浓烈情感,人物的豪气侠气与悲剧命运,让作家情有所系、心有郁结,回旋蓄势,终至倾泻而出。英雄之事可以虚构,英雄之气之性却无法作伪。莫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瑰奇悠远的感受力,即是以这有所冲决、有所破除的寄托为泉源,从而超越了历史主义哲学和文化秩序的羁束。
更重要的是,莫言延展了新文学中长期被经典崇高美学排斥和压抑的“阴性崇高”。布拉德雷曾以屠格涅夫笔下的母雀为例阐说“阴性崇高”。他从一只为了维护幼雀而对猎狗进行一次次冲击和殊死搏斗的母雀身上,看到了形体弱小者拥有的巨大道德力量,认为这是客体之为崇高者的原因。母性的爱和勇气,使体态弱小的母雀,在以命相搏、拯救羽翼未丰的幼子的过程中,具有了崇高。爱和勇气构成崇高之“质”,“一次次”展示了崇高之“量”。布拉德雷说:“小小的麻雀因超过或压倒大而来的崇高,毫不亚于苍穹和大海的崇高。然而这大不是范围的大,而毋宁说是力量的大,在这种情况里,是一种精神力量的大。诗云:‘爱的力量比死更大,完全压倒了使其忍痛离开的本能。’”(1)〔英〕布拉德雷:《牛津诗学讲演集》,转引自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第122-12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罗汉大爷(《红高粱家族》)、黑孩(《透明的红萝卜》)、小虎(《枯河》)、暖(《白狗秋千架》)、杨六九和白荞麦(《筑路》)、张扣(《天堂蒜薹之歌》)、上官鲁氏(《丰乳肥臀》)、眉娘(《檀香刑》)、蓝脸(《生死疲劳》)等,都是生活的边缘人物、被欺凌的弱者、沉默的无名存在。他们的生活卑贱、贫困甚至身体也残缺不全,但也恰恰在这些弱者身上充溢着母雀般的爱、善和勇气。
罗汉大爷、孙丙因反抗外国侵略者而遭受残酷刑罚,本身具有感动人心的道德力量,同时又具有忍受酷刑痛苦的精神力量。“二奶奶”(《红高粱家族》)戟指怒骂数日不绝,显示着一种“弱者”的崇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她邪魔附体、诈尸还魂等神异举止的表现,和她从坟墓里跳出来,警示后辈,指点迷途,使“我”获得一种神启力量的叙述,与鲁迅描述的女吊极为相似——“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2)鲁迅:《女吊》,《鲁迅全集》第6卷,第6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神秘恐怖中燃烧着生命的执着和反抗的力量。“二奶奶”也似“仁厚黑暗的地母”,(3)鲁迅:《阿长与〈山海经〉》,《鲁迅全集》第2卷,第24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在死神降临时,沉入土地那幽深宽厚的所在,获得灵魂的安息。“二奶奶”原本是一个弱者,但其生命最后一次次坚韧倔强的举动,却洋溢着一股基于生命意志的愤怒、反抗、复仇的强悍力量。
《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可视为“二奶奶”形象的续写和强化。一个勤劳发家的良善庄稼人,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枪毙,家产、土地和女人被瓜分殆尽。这个在新历史发端之际坠入历史断崖的亡魂,心怀莫大冤屈,鸣冤于阴曹地府,身受酷刑而不改其志,六世轮回于畜生道,冤屈难雪而抗辩不绝。以一己微渺短促之生命,抗诉宏大无情之历史与玄奥无常之造物,是作家悲悯情怀烛照下的崇高美学再造。蓝脸本是新历史的主人,但他同样选择了做“鬼”,而不是“主人”。从农业合作化到“文革”,这个全国唯一的单干户、“黑点”,一直是被斗争、被批判的“异类”。时至改革开放,硬撑着单干了30年的蓝脸,终于也可以在太阳底下种地了,但他却仍然习惯于在月夜中“单干”,直到在月夜,躺在自掘的坟墓中死去,与一亩六分地上出产的粮食同归于土。蓝脸、西门闹和那些光着屁股、只穿一件红肚兜的死孩子的精灵,构成了游荡于高密东北乡的月夜鬼魂,被激荡的历史意志驱逐的鬼魂。一个六世鸣冤的厉鬼、一个终生沉默的游魂,莫言借助这两个“鬼魂”——历史中弱者的反抗,使小说在对阳刚崇高美学的倾覆中“成为永恒的生命意志的庞大隐喻”,(4)李敬泽:《“大我”与“大声”——〈生死疲劳〉笔记》,《为文学申辩》,第8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一个构筑阴性崇高美学的总体性文本。
梁宗岱如此阐述屠格涅夫笔下的母雀:“那受了爱底驱使奋不顾身要从猎犬口里救出它底小雏的渺小的麻雀,已经很动人地证明德行底力——一切发自高贵和真挚的情感的行为底力——和数量比体力更无大关系了。”(5)梁宗岱:《论崇高》,《梁宗岱批评文集》,第111页,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上官鲁氏便是这样一只包含着“高贵和真挚的情感”的母雀,这位与二奶奶性格迥异的女性,却同样是体现阴性崇高的人物。上官鲁氏既是强大历史中的被压抑者,又是历史的反抗者。她是历史暴虐的受难者和现实苦难的承担者,却又以顽强的生命能量、旺健的生殖力和充满勇气的反伦理行为,突破传统规训,在人性和生命欲望层面上,如大地般承受了所有的不公、不义与不幸。莫言塑造这位生活最底层的普通妇女,这位卑微乃至卑贱地过活、饱受痛苦侵扰的母亲,这位既在生理上存活、又在历史和社会中存活、终生被绝望困扰又在宗教中寻求心灵解脱和灵魂庇护的贱民,突破了多重领域的闭锁与禁锢——欲望/私人领域、深镌着公共道德规范的家庭领域和呈恶化趋势的社会历史境遇,显示出对花样翻新的宰制权力的颠覆意义。
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看到母亲作为阴性崇高形象的合理性。梁宗岱曾以两幅名画为例,阐释他与朱光潜崇高理念的差异。在他看来,蒙娜丽莎“空灵神秘的微笑”比她背后隐现的缥缈险峻的群峰和深不可测的幽暗洞穴更摄人心魂。《最后的晚餐》中的耶稣也不是朱光潜认为的“像抚慰婴儿的慈母”,相反,“那简直是彻悟与慈悲底化身,眉宇微微低垂着,没有失望,也没有悲哀,只是一片光明的宁静,严肃的温柔,严肃中横溢着磅礴宇宙的慈祥与悲悯,温柔中透露出一幅百折不挠的沉毅,一股将要负载全人类底罪恶的决心与宏力”。与米开朗琪罗的“矜奇或恣肆”“肌肉底拘挛与筋骨底凸露”不同,达·芬奇画作的“神奇只在描画底逼真,渲染底得宜”,他的“力量只是构思底深密,章法底谨严……笔笔都蓬勃着生气”。所谓美丽、伟大、秀美等字眼都不适合描述这番感受,“唯一适当的字眼,恐怕只有Divine(神妙)或Sublime(崇高)吧”。(6)梁宗岱:《论崇高》,《梁宗岱批评文集》,第104-105、106、110页,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当历史灾难与生活的不幸如疾风骤雨般袭来时,上官鲁氏们并未以激烈的方式控诉历史、对抗灾难,其郁勃的生命意志和崇高品性并未呈现为筋肉棱立、骨骼强健的阳刚之气。她们的崇高,不是以强烈生命力的瞬间迸发或浩瀚涌流为表征,如“我爷爷”“我奶奶”那般接续经典阳刚气质,甚至与“二奶奶”神秘幽邃的“崇高”也不同,而是与暴虐的强度、历史的长度构成内在的对话与比照。她的生命的崇高“缓极了,低沉极了,断断续续的,点点滴滴的,像长叹,像啜泣,像送殡者沉重而凄迟的步伐,不,简直像无底深洞底古壁上的水漏一样,一滴一滴地滴到你心坎深处,引起一种悲凉而又带神圣的恐怖的心情,正是属于姚姬传之所谓‘阴’的艺术的;然而Sublime呀!究竟不失其为Sublime的艺术呀!”(7)梁宗岱:《论崇高》,《梁宗岱批评文集》,第104-105、106、110页,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平和、宁静、神秘与柔性之美,在它们的峰顶,能让心灵敏感深刻者心会、深悟并惊叹、敬服、愉悦于其之为崇高,“对于一颗修养有素,敏感深思的灵魂,那宁静,深邃,和光明的景象会和汹涌,嵯峨,与黑暗一样能够引起精神底集中与反抗;不,它们会比这后者更持久,更耐人寻味。因为宁静是精力底凝聚而波动是精力底交替;因为高山是可测量的而深渊却无底;因为光明比黑暗更神秘,正如生比死还要复杂变幻一样”。(8)梁宗岱:《论崇高》,《梁宗岱批评文集》,第104-105、106、110页,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与《透明的红萝卜》同年发表的《大风》也是一部充分体现莫言“阴性崇高”美学的精致短篇。小说简练生动地描画野外风景和人物内心,悄然氤氲出一派崇高气象。“爷爷”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民,他在割草时漫不经心地哼唱着古调,舒缓悲壮而苍凉,让童年的“我”感受到一种“很新奇很惶惑……很幸福又很痛苦”的情绪。大风骤至,“爷爷”被卷入风的旋涡:“车子还挺在河堤上,车子后边是爷爷。爷爷双手攥着车把,脊背绷得像一张弓。他的双腿像钉子一样钉在堤上,腿上的肌肉像树根一样条条棱棱地凸起来。”(9)莫言:《大风》,《白狗秋千架》,第15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在强大的自然之力面前,人无疑是一个弱者。但在“爷爷”苍老干瘦的身躯内却深蕴庞大的生命能量,一生的辛劳让“爷爷”表情麻木、眼睛茫然,但“茫然的眼睛中间”还有两个让孙子“感到温暖”的“很亮的光点”。这光点是卑微生命的精光,是屹立于狂横粗暴中不能被征服和打倒的勇力与恒力。另一处细节同样是撼人心魄的崇高感的外化。大风过后,庄稼恢复原状,“爷爷像一尊青铜塑像一样保持着用力的姿势”,车上的草被席卷一空,唯有一株再普通不过的老茅草“夹在车梁的榫缝里”,这株草,正像圣地亚哥那副被鲨鱼吃剩的马林鱼骨架,以其凛然与平静,郁勃着抗衡外部横暴的内在力量。
二、沉默的弱者:孩子作为莫言崇高美学的生命承载
如果说,母雀在以一己生命保护雏雀的壮举中获得了崇高,那么,比母雀更弱小的雏雀呢?当失去母亲的保护后,雏雀孱弱的生命肌体是否有着与母亲同样的能量?
莫言小说的孩子仿佛“雏雀”,他们传达着莫言的内心真实,是进入其崇高美学世界的通道。这里说的“孩子”不是指儿童视角或尚未被文明格式化的灵动鲜活的生命感受力,而是莫言小说中游荡在现实边缘的“沉默的弱者”。通过他们,那些被历史之火煎熬、被现实之尘掩埋的物件,包括“崇高”,得以文学地表现。
80年代,历史告别了它的史诗形态,红火热烈的农村壮景转换为荒寒凄凉的“工地风景”。《透明的红萝卜》的故事就在这“风景”中展开。置身于乡村现实中的人们,自有其虽贫穷匮乏却也欢乐的一面,自有其乡村伦理(黑孩一家的状况)、行业规则(小铁匠和老铁匠师徒斗法)和情爱世界(小石匠、小铁匠和菊子姑娘的情爱)。主人公黑孩身体干瘦,布满伤痕,仿佛游离于乡村现实,他与滞重现实之间处于“在而不属于”的状态。“游离”造就了一个充满奇异听觉、视觉、触觉且彼此间被超常的通感贯通的“黑孩世界”,这是莫言对“生活”的重新发现,也是莫言文学世界对常见“苦难叙述”的反拨。莫言曾谈及这篇小说的美学追求:“在坚硬的、冰冷的特异心理成分外边,施放上虚幻的、温暖的感觉的烟雾,是否能使小说获得某种怪味呢?作者远远地躲进云里雾里能否获得某种更大的表现自由呢?”(10)莫言:《桥洞里长出红萝卜》,《文艺报》1985年7月6日。作者并不回避生活中“严酷”和“坚硬的、冰冷的特异心理成分”,但他以“浪漫情调”和“虚幻的、温暖的感觉”来加以处理,营造出一种迷离空灵、飘忽灵动的韵致,不仅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叙事,也接续了中国古典美学传统。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在提示、渲染着一种坚硬的、以苦难为底色的现实场景。“现实世界”与“感觉世界”由此构成黏着不分的对位,隐含着生命/现实、个体/历史、严酷/浪漫、坚硬/虚幻、冰冷/温暖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张力。
经典崇高话语主导的苦难美学,注重将苦难故事纳入整体性叙述,借助总体性历史观的整合和绝对意志的选择、重塑,苦难尤其是其感性细节和场景被大幅缩减,并在既定意义生产链上获得一个指定位置,并在指定的位置上,闪耀着神性光芒。这种苦难体现着“力学的崇高”,(11)〔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卷,第100页,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是一种定向定性的意义生产。与之相比,莫言的“苦难”始终关联着感性生命主体的执着在场,苦难没有理念化的升华进入一个总体性象征秩序并成为这一秩序的维持者与代言人。近藤直子认为:“少年要拒绝自己的过去和培养了他过去的世界的过去。他以拒绝所有一切已经被命名的、被赋予意义的东西,而彻底获得了清澈的原始的眼睛。少年看到的不是世界中的什么东西,他看到的是世界本身的产生。在那里,任何经验的踪影、历史的屏障都没有。所有的一切都像刚刚诞生的那样的鲜嫩,等待着他的观赏、倾听、触摸。”(12)〔日〕近藤直子:《有狼的风景——读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第182页,廖金球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黑孩对社会性现实的拒绝,隐含莫言对既有意义秩序的反思,但需要追问的是,在黑孩那里,是不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踪影、历史的屏障”?黑孩以决绝的沉默拒绝“经验”和“历史”,但“经验”和“历史”不仅没有从生活中消失,而其也从未放弃对他的捕捉,它们在小说最后部分的现身,直接导致了黑孩纯美梦幻的破灭。面对现实对梦幻的粗暴介入,作家让黑孩逃离“历史”,在“自然”中获得自由自在的生命感。逃离历史,即自我生命的获得和对原初、自然的执守。如果说,王一生(阿城《棋王》)借由棋道而悟道家神髓,进入自由至境,开出一派阔大的生命崇高之境,那么莫言则从黑孩身上掘发出一种穿越文化传统的神话般的原初生命能量与元气。
和黑孩相似,《拇指拷》中的阿义也是家境贫寒的沉默的孩子。他在为母亲买药的归途中,被一对神秘的陌生男女用冰冷的拇指拷铐在墓地一株松树上,匆匆而过的农人对阿义的困境和呼救置若罔闻,善心的“黑皮女子”和割麦农妇对其施救未果。这篇小说鲁迅气息浓郁,流灌着《药》《铸剑》的气质,它从情节和“看/被看”的结构上对《药》进行了借鉴与“重写”。不同之处在于,夏瑜作为国族命运拯救者,其崇高品格在信仰和牺牲中获得,而阿义则更多地被作家从贫弱的个体生命内部掘发出超越苦难的力量。在极度的绝望中,阿义被苍凉高亢的孤独歌唱打动,他勇敢地咬掉了自己的两根拇指,奔向鲜花月光铺就的大道,最终却栽倒在冰凉的路面。这时,他看到一个赭红色的小孩从他身体里钻出来,轻灵地在月光中游泳,他用月光包裹起被冰雹打落一地被雨水浸湿的中药,飞跑回家,投进母亲的怀抱。悠远苍凉的歌声、轻柔挥洒的月光、弥漫的花香、花香与月光铺成的大道、母亲的怀抱……平静、温暖的事物,营造出童话般的诗意,虽只在小说最后一节出现,所占篇幅极小,但它们所提供的巨大力量竟然使孩子冲破生命的绝境,达到拯救自己和母亲生命的极境。
小说中凶猛的狼犬、杂草丛生的道路、阴森的墓地、铐住孩子的陌生人,仿佛是人生无法躲避、无法逃脱的命定。见死不救的人,是同样坚硬荒寒的现实,他们的麻木不仁,得到了麦子被冰雹毁坏的结局,这也仿佛是善恶有报的命定。但正是从被毁麦地中飘起的歌唱,将孩子的生命勇气激发出来。歌声、月光、鲜花、赭红色的孩子、母亲等意象超出了“美”“诗意”的通常意涵,它们的宁静、光明、温暖和甜蜜,属于一种内在的弱者的崇高,如梁宗岱所说:“一般粗糙的灵魂容易从刚性美认出Sublime,一篇属于柔性美的自然,尤其是一件艺术品,登峰造极的时候,一样可以使我们惊叹,使我们肃然起敬,使我们悦服和向往,一言以蔽之,使我们起崇高底感觉。”(13)梁宗岱:《论崇高》,《梁宗岱批评文集》,第110页,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枯河》是另一篇笔致与意境让人想起鲁迅的作品,小说将《拇指拷》中笼罩着浓郁神秘色彩的象征性场景,拉回当代中国乡村政治经济结构和日常伦理情境。较之《拇指拷》的刻意形容,《枯河》既可见出莫言对乡村伦理与乡村政治经济相互纠缠情状的写实功夫,更可见出其以淡墨写浓意的异秉。平易简淡的文字与浓稠黏滞的生活质感形成微妙的对应,让冷漠麻木的人群,连同被贫困和权力熄灭了温热亲情者,在孩子苦痛、愤怒而决绝的复仇中,凛然生出一份沉重却明快的崇高。
小说写一个沉默的孩子小虎,为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女儿,爬上高大的白杨树,却不幸坠落到女孩身上,导致其死亡。悲剧发生后,小虎遭到他所信任的、从未打过他的母亲的殴打;父亲同样是掌权者意志无奈而坚定的执行者,他凶狠地惩罚小虎。这是父母、哥哥背叛孩子的故事,也是一个弱者反抗与复仇的故事。小虎不仅被内心荒凉的村人离弃,更被至亲背叛,强横无理的压抑,催动最弱小的孩子产生了“一种说话”的欲望,小虎“听到自己声嘶力竭地喊道:‘狗屎!’”(14)莫言:《枯河》,《民间音乐》,第360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狗屎”是孩子说过的唯一的话,这是弱者的生命控诉。他在干枯河道的死亡,以最无力最无奈最决绝的形式,完成了对亲人尤其是母亲的“复仇”。
80年代前期是经典崇高美学最后的辉煌时代。在此时的历史叙述中,弱者往往作为当代史的“受难者”出现,他们渡尽劫波后,以现代性话语为依据,将弱者在历史中的悲剧命运升华为历史主体的强大精神意志。“伤痕”“反思”“改革”“知青”等文学思潮中的崇高品格多建基于人道主义话语与主流政治话语共同的现代化想象。“寻根小说”改写崇高话语的建构路径,形成了一种别样的崇高书写,阿城的“三王”通过与主流历史叙事的区隔,自有内在的风骨与庄严。莫言崇高美学与阿城相通之处在于,其主人公都是历史中的弱者或被历史放逐的“边缘人”,都是孩子或如孩子般纯净天真,同时,他们也是被轻忽的“强者”。他们或遭受继母的虐待,经受周围人的调谑嘲弄;或被神秘地禁锢;或遭受家人辱骂毒打,为冷漠人群围观。他们既无力或无意撬动历史,但历史却也对其生命的“内在性”无可奈何。“弱者”的崇高源自对自身生命“内在性”的坚持,弱小、单薄、匮乏的他们,偏偏在与历史的周旋中呈现着令人瞩目的崇高。
三、莫言文学的“至境”及其历史维度
莫言文学中的原初、生命、美、诗意,意味着一种抵达“至境”的书写。梁宗岱在反思朱光潜“崇高”论述的基础上,重新界说了“崇高”。针对后者以康德学说为依据,将sublime和grace分别译为“雄伟”和“秀美”,以对应中国的刚柔或阴阳说,梁宗岱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所谓sublime(崇高)与grace(秀美或妩媚)并非不相容,阳刚阴柔偏重美的性质,而sublime(崇高)与grace(秀美或妩媚)偏重美的品格。屠格涅夫的母雀之成为崇高者,原因在美的品格,“‘崇高’只是美的绝境,相当于我国文艺批评所用的‘神’字或‘绝’字;而这‘绝’字,与其说指对象本身底限制,不如说指我们内心所起的感觉”,因此,“崇高底一个特征与其说是‘不可测量的’(immeasurable)或‘未经测量的’(immeasured),不如说是‘不能至’或‘不可企及的’”。(15)梁宗岱:《论崇高》,《梁宗岱批评文集》,第108页,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原初、生命、美、诗意,使莫言文学内在地葆有一种生命性能量和活力,莫言借此拒绝先在的意义设定,立足“本心”,重设意义。
莫言文学洋溢着调配文字、措置形式的淋漓兴致,却殊少“纯美”的执念;有深层的批判性,却不诉诸那种近乎执拗的创痛感,殊少沉重的忧患意识;即便书写暴虐、苦难,也有意回避那种让人痛苦到窒息的沉重感、压抑感。之所以如此,或在作家对生活“欢乐”“温暖”“诗意”一面的体认;或在作家的幽默心性和笑谑才具;或得益于“民间”“狂欢”文艺的启示。在某种意义上,莫言文学狂放恣肆的想象力、纤毫毕现的表现力、铺张繁复的文字与修辞,是对身体匮乏(饥饿)与心灵匮乏(孤独)的想象性代偿。赵园的观点切中肯綮:“莫言并没有缘他丛生的感觉而入于魔幻。剥脱那些如菌如苔如羽毛的‘感觉’,你发现了他所写‘事件’的极现实的性质。”(16)赵园:《地之子》,第12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诗性意象、精妙的感觉和夸饰的文辞,包裹着惨痛的创伤记忆,即便是现实书写也弥漫着历史的鬼魂:《红高粱家族》为招魂之作,《生死疲劳》为鬼魂申冤之作,《酒国》为驱鬼之作,《蛙》为忏悔亡魂之作,《丰乳肥臀》为安魂之作。莫言文学难掩历史情怀。孙郁有言:“鲁迅在反抗旧文明时,更多的是抗拒自己身上的鬼气。所以书的字里行间,有历史的长影。莫言这一代,掘心自食的惨烈被新的东西置换了。历史咀嚼的长度超过自我拷问的长度,他的兴奋点集中在乡民社会的旋涡里,处处显示了单纯的恢宏和浑浊里的伟大。”(17)孙郁:《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概言之,莫言处理文学与历史之关系有其特出之处:将历史/现实纳入个体/生命区域,使之充分主体化、生命化,化解其坚硬的物质性,涤除其“意义设定”,而出之以浸润着主体思情和灵性的文字与形式、修辞。
当反崇高反神圣成为流行时尚时,文学已蜕变为精神虚无的游戏。文学,就像孩子,在这世间,他会自娱自乐,会搞恶作剧,会高声喧闹,但它也会以“沉默”无声地拒绝和抗议。文学无力改变坚硬强大的现实,但它提供了来自别一世界、别一视点的观照和审视。孩子无力为这世界做出更强体力的劳作,奉献更多的劳动成果,但这个世界和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或曾是孩子,都是或曾是沉默或喧闹的弱者。“小说,小说,小人之语也,那些把小说说成高尚、伟大之类的人,无非是借抬高职业来抬高自己的身份”。(18)莫言:《我眼中的阿城》,《莫言散文新编》,第33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在莫言眼里,个体生命都是绝对的弱者,文学亦如是,但弱亦为强,沉默亦是力量。“孩子”昭显本真,文学关乎生命正义。在神圣被亵渎、崇高被解构之时,真正的文学与“孩子”一起,携手走进生命与生存之重,召唤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