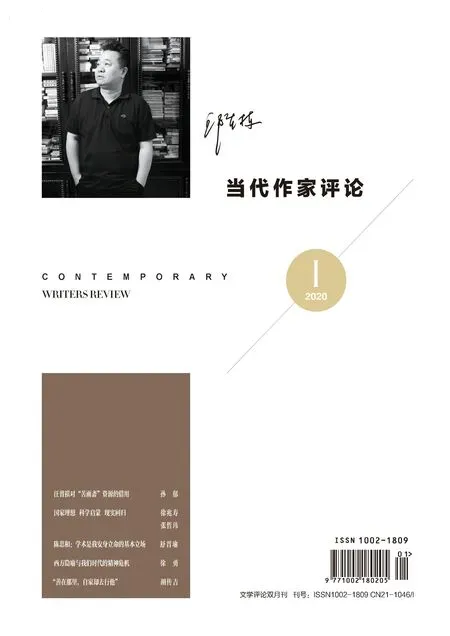从“乡土凝香”到“现实余韵”
——陈忠实短篇小说论
韩 伟
长篇小说《白鹿原》无疑是陈忠实的巅峰之作。这部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作品,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我们如果仔细回顾作家的创作历程,就会发现他的短篇小说亦体现着作家一以贯之的风格,是其创作长廊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优秀的短篇小说犹如一行行坚实的脚印,踏出了作家用笔追寻文学与灵魂的步伐。这些短篇小说凸显了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艺术手法和直面生活的勇气。纵观陈忠实三十多年来的短篇小说创作,作家正是立足关中、魂系乡野,用心感悟现实,才使他的视野逐步扩大,并获得了发现美的眼睛和葆有了敏感的艺术的心灵。从民间到民族的抒写,从生活到生命的体验,他创作出了一系列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短篇精品。本文试从陈忠实短篇小说的创作入手,探寻作家持之以恒的文学法则,展现其三十多年文学生涯执着于斯的点滴变化,并力求透析作家自我超越的历程,以及最终呈现出的丰富博大的精神内蕴。
一、“乡土凝香”:从民间到民族的抒写
陈忠实的短篇小说,大多是以关中平原为背景的,他的笔调凝重浑厚、沉稳劲拔,苍凉悲壮中蕴含着空阔辽远,在粗犷中携带着一抹古气,挥发出一种厚实的感染力,其艺术风格恰恰与他所表现的这块土地相对应。比如早期的《土地诗篇》《土地·母亲》《田园》等作品,乡土气息充溢其中,乡村生活历历在目。陈忠实三十多年笔耕不辍,始终保持着与农村生活的血肉联系。他总是以自我独异而熟悉的视角和描写领域,“代民立言、为民泄情”,(1)畅广元:《负重的民族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白鹿原〉评论集》,第9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体现了贴近人民、关注现实、魂系乡野的写作立场。
乡野情怀激发了作家的写作动机,也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契机。陈忠实创作初期的众多短篇小说,也和《白鹿原》一样,着重于揭示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反右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大跃进’‘四清’乃至‘文革’,都很大程度是脱离中国实际,夸大阶级斗争,伤害了大批干部和群众,人为地造成干部和干部之间、群众和群众之间的矛盾。”(2)陈涌:《关于陈忠实的创作》,《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作家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矛盾并没有回避,而是在作品中多有揭示并加以反思,荣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信任》正是这一反思后的代表作,表现出了作家对于我们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存在与本质有所相悖时的探索和思考。
陈忠实的创作有着明显的独具乡野趣味的性灵之色,而作为一个身怀道义感和底层意识的小说家,那些生活在底层的困难群体理所当然地成为他叙写的主要对象。如创作于新世纪初期的《日子》,小说用平面性的文字图景折射出当代中国农民生活的多维面影,作者把一系列的生活点滴原生态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即农民在物质贫困和精神困惑的双重压力下过着“日子”。胡适曾经对短篇小说做过这样的界定:“短篇小说使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3)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1918年第4期。这里所强调的是短篇小说创作的核心应抓住生活的“横断面”。我们可以看出,陈忠实的《日子》充分做到了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他从这个“过日子”出发,向生活的“纵深度”掘进,高度艺术地表现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绝大多数农民真实的生存情境和精神状态。
在当今文坛,众人关注并痛斥的是人文精神的失落,是道德情操的伦丧,众人呼唤并等待一种超越世俗观念的文学的出现。“现在的文学的第三方面的‘最缺少’是:缺少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作家的根本使命应是对人类存在境遇的深刻洞察。一个通俗小说家只注意故事的趣味,而一个能表达时代精神的作家,却能把故事从趣味推向存在,他不但能由当下现实体验而达到发现人类生活的缺陷和不完美,而且能用审美理想观照和超越这缺陷和不完美,并把读者带进反思和升华的艺术氛围中去。”(4)雷达:《当代文学到底缺什么》,《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7月12日。要获得超越,在我们这个国度,不可能像西方文学家那样,营造一个充满宗教式信仰的文学家园,陈忠实所做的是打通我们对历史及人物的普遍认知,通过对人文精神的张扬,对人类存在本质的揭示,从而营造出一种对现实构成超越和提升的新型美学境界。
当我们仔细阅读陈忠实的短篇小说,把视线停留在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时,往往会发现隐藏于文本中丰富的道德元素以及深厚的民本思想。他们不是那么富有“距离感”,他们“不是历史上的哪二类,而是能够冲出传统形成‘这一个’的人物并通过这些人物,去宣传一种既非历代统治者提倡的道德,也非叛逆者反抗的道德,而是民族固有的祖祖辈辈居住一处的下层农民之间互相依存的道德。”(5)范风驰:《人本性格的深沉张扬——陈忠实创作论》,《渤海学刊》1995年第4期。这样的安排使得其小说叙述显出一种与人促膝长谈的感觉。小说人物以及小说整体传递出来的道德意识,不仅是一种人格风采,更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光辉写照。比如小说《腊月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北方乡村的一个平淡无奇的早晨。郭振谋老汉家的牛被人偷了,而偷牛贼让他们出乎意料。正是儿子秤砣的中学同学小卫,因为国有企业厂长的胡整瞎弄而下岗,为生活所迫,沦落到偷同学家的牛的境地。小说通过时空转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说叙写了国有企业昔盛今衰的情形,揭示了导致国有企业败局的病因,即管理制度的严重缺陷。作品整体笼罩着些许感伤空气,不动声色地描述了小卫的家庭状况,从现实到回忆,从美好到残酷,“温馨的记忆现在不可复制,反复咀嚼的余味却是苦涩的”,当局领导百般客气地来慰问小卫的时候,他显出一副鄙夷的神情。小卫拒绝的不仅是救助,更多的是对现状的不满和愤懑。作品并没有明确地谴责“偷牛贼”小卫的意味,而是通过朴实无华的文笔,传达出对困难群体的深切同情,充满了对现实的忧患意识。
对乡野自始至终的关注,对乡村人物的贴切描写,陈忠实的笔迹始终在民间的大地穿梭回转,他站在自身经验的立场上,通过娴熟的文笔对人类的存在性进行揭示,对一个民族的灵魂进行勾勒,从深层次来讲,他最终抵达至文学的本质世界。在此,陈忠实做到了“既不狂热什么,也不冷落什么,而是用冷色调的笔触,去揭示人物存在的客观实际,人怎样在众生相处中获得直立被人仰望而不俯视的权力,使人能够不断完善自己的理想人格,从而展现作品的独特意蕴”。(6)范风驰:《人本性格的深沉张扬——陈忠实创作论》,《渤海学刊》1995年第4期。比如《腊月的故事》《窝囊》《害羞》等,没有歌功颂德,也没有流于感伤,在把人物推给读者时,常常突出人的悲悯、人的艰难,再现人生的苦辛,从而揭示出人生的幸福与苦难,具体并深化着存在的本质意义。“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它通过艺术与仪式,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展示那些人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诸如悲剧与死亡。”(7)〔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79页,赵一凡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陈忠实力求回避停留表面的浮泛和浅薄,摆脱浮光掠影式的描写,在真情流露中道出存在的本质,形成砥砺人心的力量。
如果按照历史的时钟,把一篇篇精致的短篇小说串联起来,就可以组成一部宏阔的史诗性杰作,由此,作家一步步勾勒出我们民族的灵魂。民族的记忆特殊而久远,我们的历史沧桑荣辱、坎坷多变,并且催生出了别样的民族文化心理,那么,历史的变化对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陈忠实把重心置于我们的国民性上,关注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瞬间激变,是遭受冲击和颠覆,还是更新和嬗变。“我是写小说的,我更有兴趣的就是这些理论的东西遗落到民间,人民的心理、心态经历了什么。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富裕的和穷苦的、男人和女人,形形色色的人,他们的心理是一种怎样的状态,这非常有意思。”(8)《作家的使命,是勾勒民族灵魂——对话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忠实》,《解放日报》2009年8月28日。
《舔碗》是这类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黑娃的主家掌柜有个习惯:吃完了饭要舔碗。黄掌柜要黑娃也舔碗,黑娃拒绝了他,他就苦口婆心地对他讲舔碗的好处。黑娃实在不习惯,一舔就吐,不料这却把掌柜给折磨出病了。黑娃于心不忍,便赔罪似地说:“要是舔了碗能除你的病,那我就……舔。”黄掌柜一骨碌翻身坐起来,双手抓住站在炕边的黑娃的胳膊,抖颤着厚长的下嘴唇说:“黑娃你要是舔碗就把我救下了!”(9)陈忠实:《舔碗》,《陈忠实小说自选集·短篇小说卷》,第125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但黑娃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黄掌柜最终也绝望了。于是他亲自舔黑娃吃过饭的碗,但这更让黑娃恶心。后来情况严重到黑娃看到黄掌柜吃饭时伸出来的舌头就反胃,就想吐,黑娃在一个夜里选择了出逃,小说就此收尾。一主一仆两人,演绎出人性莫大的卑微和底层群体遭遇摧残时的毁灭感。黑娃最后的逃走又平添了一丝经典的意味,暗合了经典意义上的“出走”“逃离”之类的尾声,把国人屈从并习惯了的“奴隶身份”重重地卸了下来。小说的讽刺技巧无疑是圆熟的,对人性的探索让人毛骨悚然,有一种冷峻的深刻。巴尔扎克主张要写出被“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以文学的方式“看看各个社会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永恒的法则,离开了真,离开了美。”(10)〔法〕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文艺理论译丛》1957年第2期。小说写出了我们忘却了的记忆,它让人认识到落后的生活方式,对农民心灵造成的扭曲有多么严重,认识到我们民族在尘封的历史背后还有着多少污垢的东西没有涤荡清楚,还有多少丑恶的积习等待改换。
二、“心物辉映”:从生活到生命的体验
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创作一直是以“现时”主义为主流的,作家的创作大都是“当下进行时”,力求达到对当下社会的介入和干预。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也是这样,现实生活是心灵物化过程的第一站,他近距离观照“当下”,呈现“现时”,比如《腊月的故事》《作家和他的弟弟》《关于沙娜》《日子》等统统是当下性的,它们就发生在作家的身边,是他过去甚至今日还时常看到并体验着的生活场景。“普遍的通常的规律,作家总是由生活体验进入到生命体验的,然而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能由生活体验进入生命体验,甚至可以进入生命体验的只是一个少数;即使进入了生命体验的作家也不是每一部作品都属于生命体验的作品,这是我通过阅读所看到的中外文坛上的基本的现状。”(11)陈忠实:《兴趣与体验——〈陈忠实小说选集〉序》,《小说评论》1995年第5期。以《日子》的结尾为例:“我心里猛然一颤。我看见女人缓缓地丢弃了铁锨。我看着她软软地瘫坐在湿漉漉的沙坑里。我看见她双手捂着眼睛垂下头。我听见一声压抑的抽泣。我的眼睛模糊了。”(12)陈忠实:《日子》,《陈忠实小说自选集·短篇小说卷》,第64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这样的结尾,本身就有浓厚的情感表现性,它表现的既是那个“我”的情感体验,但同时,也是作家自身的情感体验,在这里,“我”是一个隐含的读者。陈忠实把积淀已久的苦难意识有机地融入了对当下生活的观照之中,以对“现时”给予发问和质疑,对生命的意义做出探索和解读。
关注现实,从现实生活溯源进而剖析人的传统文化心理,陈忠实的目光在现实与历史中往复逡巡,不拘泥于历史事实,向历史与人性的纵深处开掘。他着眼于生命个体与历史强大的毁灭力量抗争中的悲剧性处境与命运,通过对个体遭际中精神创伤的冷峻审视,直面人物的生命之痛,来进一步探寻并阐释生命意义和价值尊严,借以唤起人们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关中大地是陈忠实起步的园地,这是一块播撒下了秦风唐韵的热土,历史文化传统和当地民间信仰的力量,都为陈忠实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和强劲的精神动力。“黄土地上传统文化和沧桑岁月的沉淀,尤其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理论架构、价值观念,长期滋养着这块土地上的文人、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范、生存精神和价值理念,他们的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的诉求,带着历史的沉重和疼痛。”(13)马平川:《陈忠实短篇小说的写作伦理》,引自http://www.eduww.com/Article/200901/22837.html。这块土地上曾经的人和事在陈忠实的心里堆积并酝酿,变得更为清晰起来。正如荣格所讲,作家的创作不是作家自己在写作,而是“集体无意识”通过作家而运作。陈忠实的创作正是把小我融入大我的“集体无意识”的书写。比如《娃的心娃的胆》中的抗日英雄孙蔚如,参与“西安事变”又在中条山抗击日军;又比如《一个人的生命体验》中的作家柳青,内心时刻处于挣扎中,后因不愿意“自我侮辱”,而舍弃自己的生命等等。“陈忠实在这块土地上生活长达五六十年,是以小说为‘关中风月’绘形写神的高手,既绘出了这块土地的世相,也写出了这块土地上人的风骨。”(14)刑小利:《关中的世相和风骨——读陈忠实小说新作〈关中风月〉》,《文学报》2007年9月13日。
以《李十三推磨》为例,主人公李十三本名李芳桂,是一个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秦腔剧作家,以其含沙射影的手法宣传反满思想。当嘉庆皇帝派专使到渭南捉拿他进京问罪时,时年62岁的李芳桂正在家中推磨,闻讯后忧愤交加,口吐鲜血,带病逃亡,不久吐血而死。小说浓墨重彩地写了李十三推磨前后的情景,写他对秦腔剧作的痴迷,写饥寒交迫的处境,出逃时的内心挣扎。作者对其高昂的精神是赞颂的,对其悲惨的遭遇是惋惜的。陈忠实觉得,不为李十三写点什么,自己的心情永远无法平静,他还特意去了一趟李十三的老家,凭吊这位他由衷敬仰的艺术家。
《一个人的生命体验》《李十三推磨》说的是真人真事,人名用的都是真名。陈忠实的精彩叙述使他们有血有肉地复活在我们面前。这不仅是对柳青、李十三的祭奠,也是对那一代人永远的祭奠!
陈忠实坚信的是,生命体验值得信赖,并且不听命于陈规教条的指示去阐释生活,他的短篇带上了很强的个人表现性,并通过这种形式来表现自己的生命体验。于是,他的小说就不再是纯粹的再现,而进入一种深广的表现层面。“以自己的心灵和生命所体验到的人类生命的伟大和生命的龌龊,生命的痛苦和生命的欢乐,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脆弱,生命的崇高和生命的卑鄙等难以用准确的理性语言来概括而只适宜于用小说来表述来展示的那种自以为是独特的感觉。”(15)陈忠实:《兴趣与体验——〈陈忠实小说选集〉序》,《小说评论》1995年第5期。作家不需要原本地呈现社会生活,而是通过主观感受,经过心灵化处理后,用心灵写作,用整个生命写作,他们所创造的必须是心灵世界,是打上自己的心灵烙印的独特的心灵世界,并通过这个世界建立和现实世界的联系,抓住整个世界。“小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以为是思想。这不是理论书上说的思想性、艺术性的思想。思想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是作家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独特的思索和独特的感悟。”(16)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第7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三、“现实余韵”:从低沉到高蹈的求索
考察陈忠实的文学创作,现实主义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也是回避不了的,因为陈忠实的文学创作方法与现实主义一脉相承。现实主义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主要潮流,并在诸种文学活动中,取得了最为出色的成绩。正因为有着像陈忠实这样认真追求、执着探索的作家,又表现出不随风逐潮的气度,最终形成尊崇传统又不囿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因此,我们有必要展现作者从低沉到高蹈的求索历程。
陈忠实创作初期的短篇之作,仍显出艺术手法上的刻板和思想的固化,穿过二三十年的风尘去阅读,会发现它们存在的不足,难以获得经典所赋予的余韵。这是因为现实形势的变化制约了作家的艺术探索,七八十年代的短篇小说艺术标准往往在政治、时代、读者舆论等种种声音的夹击下求生存。而究其个人原因,陈忠实初期短篇作品运用的都是写实手法,坚持以生活的本来样式反映生活的创作原则,人物形象还局限在单纯的以政治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视角去塑造人物的樊篱,没有脱离“载道”的传统。在作品的美学意境方面,因思想的固化而显得不够饱满和恒久。正如作家自己所言:“已经惊讶起初几年的一些短篇的单薄和艺术上的拘谨,再显明不过地展示出我艺术探索的笔迹。无须掩丑更不要尴尬,那是一个真实的探索过程,如同不必为自己曾经穿过开裆裤而尴尬一样。”(17)陈忠实:《兴趣与体验——〈陈忠实小说选集〉序》,《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陈忠实的短篇创作并没有戛然而止,他不断尝试着突围,以找到生存的契机,像前人那般“从‘附会政策’转为‘说明人生’”,从低谷中起飞直至高昂地阔步向前,向着短篇精品迈进,“由于作者写作的态度心境不同,短篇小说似乎就与抄抄撮撮的杂感离远,与装模作样的战士离远,与逢人握手每天开会的官僚离远,渐渐地却与那个艺术接近了”。(18)转引自黄发有:《短篇小说为何衰落》,《南方文坛》2005年第3期。
从《信任》到《一个人的生命体验》的艺术掘进,可以看出,作家经过了痛苦的、孤独的自我剥离,最终达到短篇小说艺术的圆熟。这主要表现在叙事技巧的突破和批判意识的增强,人物塑造的多样和主体精神的新变,在作品的主题方面也有所开拓。
故事的精当和巧妙是短篇小说吸引读者的第一要素。陈忠实成熟的短篇叙事,突破了传统强调故事情节完整统一、叙述时间以单向线性时序为主的陈规。往往先交代一个事件结尾,随后引出另一个故事或人物的结局,然后再回头去叙述另一个故事或人物的起由和发展脉络,故事中包蕴着故事,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框架结构,化单一叙事为多元叙事,将读者导向更为广阔的精神领域,读者须经过层层抽丝剥茧后,才能领会作品最核心的旨趣,获得思考的愉悦和审美的满足。“就我的体会,从结构到语言,都是受到所要刻画的对象决定的。作者要寻找到一个适宜表达这个对象的结构,包括语言,如果不适宜,写起来别扭,读者读起来也别扭。”(19)马平川:《精神维度:短篇小说的空间拓展——陇上对话陈忠实》,《文学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5期。比如《关于沙娜》这篇小说,小说借助在郊县挂职生活的著名女作家秦业的见闻和感受,通过对毛遂自荐、坦率热诚的沙娜的描述,表现了时下普遍的社会隐忧——国家干部素质问题。
其次,小说的叙事者有着了较强的主体介入意识,同时也加强了小说的表现效果。《日子》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语言重复和分段简练,试看这样的话语:“男人重复着这种劳动工序。女人也重复着这种劳作工序。他们重复的劳动已经十六七年了。他们仍然劲头十足地重复着这种劳动。从来不说风霜雪雨什么的。”(20)陈忠实:《日子》,《陈忠实小说自选集·短篇小说卷》,第57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一句话作一段落,作家力图通过细微的变化,赋于它更深远的表现力,背后含带着无比的沉重之感,分段又使这种沉重加倍许多。《一个虚脱症患者的发言片断》本身就是一个病患者的独语,小说主人公在大会上发言的题目是《作家和人民》,但从他的发言与绘声绘色地讲述那段“小插曲”的表现大相径庭,流露出作者毫不留情的否定态度。
如果说,《白鹿原》是陈忠实创作的分水岭的话,此前的作者主体精神不可免地具有形式的简单化、内涵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而此后的作者主体精神则是批判意识凸显,自我性增强,思想更为独立,精神更加自由,其创作也呈现为一种深思熟虑和一份文学的自觉。“主要是指摆脱了早期小说创作的经验层面和盲目状态能够从理性的高度来认识文本中的人物和故事,并且更理性地控制自己的笔触。”(21)张国俊:《新的超越——谈陈忠实近期的短篇小说》,《文艺争鸣》2008年第12期。
短篇小说《作家和他的弟弟》中,没有姓名而被作家哥哥和县长同称为“这个货”的农民弟弟,有着改变命运的欲望,但他不像《日子》中那对夫妇那样去苦苦劳作。他利用作家哥哥的名望给县长写字条儿,再让县长给银行行长说情,货款办公司发大财。而后作家弟弟发现一切化为了泡影,在给县长还自行车时,竟将崭新的自行车除三角架以外的所有零部件都换去了,并视其再正常不过。作家弟弟这种无疑具有“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痞性文学人物特征,作者力透纸背地展现了这种当代农村生活环境所造就的令人无可奈何、又真实可笑的思想意识和麻木不仁。“陈忠实不仅从同情角度,关注农民的不幸,而且,还从批判的角度,审视、剖析农民身上的劣根性,省思农民的生存境况,从而提出与农民的未来命运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22)李建军:《廊庑渐大:陈忠实过渡期小说创作状况》,《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小说《猫与鼠,也缠绵》里,作家把叙写的生活面已经拓展到城市,由农业延伸到工业,人物由农民扩展到工人和警察。常年在公安局的烧锅炉工人,竟然是隐藏多年的行窃惯犯,当他被抓住的时候,竟然也显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架势,直言必须让公安局长亲自审问才交代罪行。当然小偷的“罪行”偷出了局长的“罪行”——权力腐败。小说通过对小偷和局长微妙的谈话过程的描述,以讽刺的笔法展示了国家公职人员的丑恶嘴脸,批判了这种监守自盗的虚伪。陈忠实已经用一种批判的精神、个人的视境和价值来面对生活,确立了真正的小说精神,这不能不说是一次潜心求索后的超越。
《白鹿原》以后的短篇小说,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作家切入叙述对象的角度更为巧妙而且提纲挈领,语言更为老辣精到,刻画人物更为简洁有力且入木三分,叙述更为收放自如,张弛有度,有闲庭信步般的从容自若,有庖厅解牛似的游刃有余,体现出一个小说家的真本领和硬功夫。
四、结语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曾作为现当代重要“主流文体”之一的短篇小说走向“边缘”,仿佛一个“时代的孤儿”,遭到冷落,这个事实我们无法回避。经常有人引用美国作家厄普代克二十年前的话来描述短篇小说的命运,说那是“一个短篇小说家像是打牌时将要成为输家的缄默的年代”。(23)王诜:《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第278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无论是对于普通读者,还是职业评论家,短篇小说的阅读接受和研究,一如诗歌在我们时代的命运,境遇十分尴尬,人们的文学焦点悄然转移到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上。这让我们对短篇小说的命运更为担心,然而通过对陈忠实短篇小说创作的透析,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位在现实主义道路上不断掘进的作家形象,这也让我们的担心减少了一些。他坚持认为一个作家对文学的贡献,只能甚至仅仅只能是奉献出可以永存于世的作品。“陈忠实就是怀着这样的思考,才在大陆文坛闹哄哄的‘造星’浪潮中,摔开众人说三道四的压力,迈着沉稳的脚步,回到远离闹市的农村老家,把一家老小统统赶到城里,自己独自一人蜗居在生活条件极其简陋的房舍里,抽着雪茄,喝着醉茶,啃着干馍,进行卧薪尝胆的劳作,打造他蓄谋已久的‘文学航母’。”(24)文兰:《打造经典的耐性——陈忠实创作历程的启示》,《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