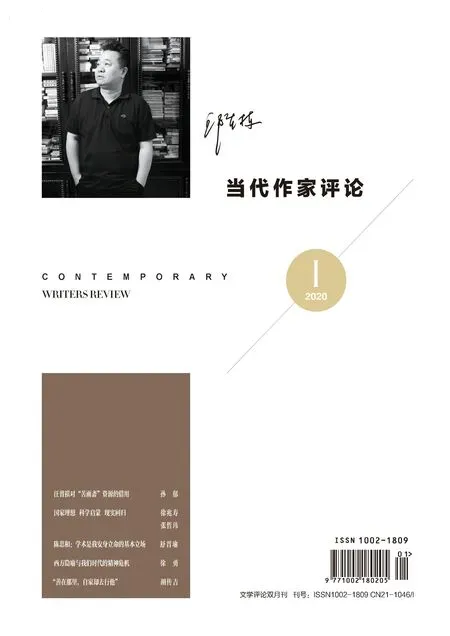至深、至高、至远:当代文学的另一种叙事维度
——论邱华栋极限运动小说
裴 蓓 张箭飞
体育与文学的结缘由来已久、源远流长。被誉为西方文学源头的《荷马史诗》记载了古希腊时期的多种体育运动,如战车、拳击、摔跤、跑步、铁饼、投枪等,其中一些竞技项目后被纳入品达(Pindar)颂歌中“至善如水,璀璨如金,让一切人类财富黯然失色”(1)Pindar,The Complete Odes.Anthony Verity tra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2007,p.3.的奥林匹克赛会,更有甚者一直延续至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我国早期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共有58篇关于先秦时期体育运动的诗篇,约占总数的1/5。中国当代文学亦不缺乏体育题材的作品,然而,体育文学一直被视为一个较小的类型分支,游离于当代主流文学创作和评论边缘。
2018年,中国当代作家邱华栋接连在《人民文学》《长江文艺》和《十月》上发表了《唯有大海不悲伤》《鹰的阴影》和《鳄鱼猎人》,这标志着擅长透视现代人生存处境,书写都市经验和个体生命意识的作家从之前颇为熟稔的都市题材转向从未涉足的极限运动题材创作。这组小说是中国当代极限运动叙事的井喷式亮相,更重要的是,世界文坛中一度“缺席”的中国当代极限运动小说终于初试啼声,并跻身世界体育文学的大舞台。《唯有大海不悲伤》《鹰的阴影》和《鳄鱼猎人》分别以三种极具挑战性和危险性的极限运动为题,于虚实间呈现出一种浪漫的精神气质和科学写作的严谨文风,并放射出情感疗愈、英雄主义和华人身份建构三重主题,既展现出极限运动叙事极欲抵达的至深、至高和至远之境,也实现了当代文学所召唤的“阳刚之力”(2)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和“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感情”(3)何新:《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读〈无主题变奏〉随想录》,《读书》1985年第11期。的复归。
一、至深:大洋之下的自由潜水与情感疗愈
早在五千年前,人类就已经出现潜水活动。早期人们的潜水深度多在20米以浅,主要是为了捕捉海产和寻找宝物。(4)徐伟刚:《休闲潜水》,第3页,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8。潜水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据《尚书·禹贡》记载,夏禹时期淮夷族的贡品是没水而获的“玭珠暨鱼”,(5)《尚书》,第57页,慕平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天工开物》也绘有古人没水采珠的场景,(6)宋应星:《天工开物》,第487页,钟广言注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但潜水作为一种现代体育运动项目则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
遗憾的是,虽然我国潜水运动正方兴未艾,但当代文学对这一热潮的反应却很迟钝,描写潜水的作品只有寥寥数篇。《唯有大海不悲伤》打破了这种冷寂的局面,自称“顶多玩儿过简单浮潜”的作家一边发挥浪漫的文学想象力,一边以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多部海洋纪录片(如《海洋》《蓝色星球》《加拉帕戈斯群岛》)和《美国国家地理》《中国国家地理》中的海洋科普文章为支撑,穿插游走在文学想象与科学写作的虚实之间,别有旨味。
《唯有大海不悲伤》讲述了一个情感救赎的故事:主人公胡石磊全家在巴厘岛度假时儿子意外遭遇直流丧生,其后妻子流产、婚姻破裂,接连的打击彻底击碎了主人公的生活。然而,一部海洋纪录片重新燃起主人公与大海交流的渴望,借由环太平洋的自由潜水,主人公与大海重建亲密情感,内心伤痛被逐渐抚平,最终重获新生。小说中的潜水爱好者们国籍、肤色不同,年龄、职业各异,但不论是美国人大卫、俄罗斯姑娘雅辛娜、日本人西村京太郎还是加拿大华人郭娜,“人人都有自己的隐秘的生活痛点”,(7)邱华栋:《唯有大海不悲伤》,第25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文中所引邱华栋的《唯有大海不悲伤》《鹰的阴影》《鳄鱼猎人》,均出自小说集《唯有大海不悲伤》。以下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一一标注。而这种让人“陷入绝境里”(第7页)的痛点之于胡石磊就是失子之痛。“狂暴、蛮横,居心叵测”(第3页)的大海像发动突袭的水蟒猛地夺走了儿子的生命,大海从代表快乐、令人神往的度假胜地瞬间逆转为一种暗黑的恐惧景观。
半年之后,一部关于革鳞鱼旨悲壮地牺牲自我延续后代的海洋纪录片吸引了情感萎靡的主人公,燃起了他与“又爱又恨、想拥抱又拒斥的大海”(第9页)重新相遇的渴望。通过学习自由潜水,胡石磊“阴沉的内心里渐渐燃起了一簇火星,这是一点点的希望。在大海的深处,去和儿子面影相遇,一点点地将内心的悲伤祛除”。(第12页)
然而,在目前已知极限运动中,自由潜水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仅次于高楼跳伞的世界第二大危险运动。潜水者不使用任何呼吸设备,仅“在一吸一呼之间,去靠近那些自由摇曳的海洋生物”,(第12页)其最大难度在于克服强大的水压。正常人一般最多能够承受水下40米左右的压力,过大的水下压力会引起人体内部的物理变化和生理变化,从而导致各种病症的发生,比如组织器官被挤压造成身体不同部分的出血,耳膜破裂,胸部受压塌陷,肺部形成空气栓塞及其气胸、昏迷、氧气中毒、一氧化碳中毒,体温丧失等。(8)《自由潜水:危险的极限运动》,《科学咨询》2017年第25期。
自由潜水如此危险,然而“海底世界太丰富而美丽了,只有在自由潜水的时候才能揽到眼睛里”。(第39页)《唯有大海不悲伤》在真实记录自由潜水诸多危险因素的同时,更侧重于展现这项极限运动的魅力,例如与鲸鱼母子嬉戏伴游、目睹抹香鲸和大王乌贼恶斗、倾听座头鲸的歌声、海底狩猎凶猛的金枪鱼和梭鱼、在水深超过200米的海域绳潜以及南极冰潜。沉浸在海水包围之中,人类视觉、听觉和触觉的新奇体验是在陆上,特别是城市生活中难以企及的:“摇曳的水草,五彩斑斓的珊瑚礁,各种颜色鲜亮的海鱼、龙虾、海鳗和螃蟹,都在水里,还有如同海妖一样摇动身体的海藻和海带”;(第39页)座头鲸群的合唱如同交响乐般“高音低音,回旋往复,欢快酣畅,美妙生动”;(第34页)小抹香鲸的皮肤“凉凉的,坑坑洼洼的,但有一种油脂般的光滑感,像是滑石粉或者泥子以及胶水混合在一起,涂抹自它身上一样”。(第18页)
法国自由潜水冠军内里(Guillaume Néry)在自传中写道:在令人心醉的深蓝海底,“你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在你自己身上,集中在你的情感和疑问上……此刻时间仿佛停止了一般……内心的旅行收获了它的意义”。(9)〔法〕纪尧姆·内里:《勇往直潜》,第151页,杨森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6。自由潜水是精神完全的自由,是意大利自由潜水专家皮里兹(Umberto Piritz)所描绘的“一次进入灵魂的跳远”。(10)单琦:《问一个自由潜水大神》,《人物》2017年第1期。小说主人公通过自由潜水回到母体,“就像是躺在母亲的腹腔里,有羊水给他提供营养,让他生长”,(第41页)他一边内视自己的生命、思考自己的前世今生,一边通过视觉、听觉和触觉感知大海的景观,进而了悟大海里“真实、残酷,而又天然地具有合理性”(第11页)的生命逻辑——“所有的生命都在繁衍生息,生生不息”。(第51页)自由潜水最终疗愈了胡石磊的失子之痛,他终将自己的悲伤交还给了大海。
《唯有大海不悲伤》是对文学经验维度的有力拉伸,它在绘制环太平洋自由潜水地图的同时,完整地记录了一则人与海洋的情感地理故事。此外,作家亦在尝试拓展极限运动写作的新向度——(海洋)动物与情感疗愈。虽然现代医学已证明,与海豚做亲密接触能刺激自闭症患儿的大脑以达到治疗目的,且当代文学中也有张贤亮笔下马儿“一股湿暖鼻息”的情感慰藉,但是动物与情感疗愈这条线索在当代文学中并未得到充分延展。因此,小说中多次出现的鲸鱼意象,貌似无心实则有意,例如鲸鱼母子间的舐犊之情、抹香鲸与大王乌贼的殊死搏斗、能带来艳遇的鲸鱼之歌、被远洋轮噪声惊跑的座头鲸,以及在南极水域捕食的抹香鲸、灰鲸、蓝鲸和虎鲸,无不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和可能。
二、至高:雪峰之顶的高山探险与英雄主义
起源于18世纪后期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现代登山运动(mountaineering)是一项具有多维度、大空间和多层次开展的户外运动项目,涵盖了从低海拔登山徒步到高海拔雪山探险的所有活动,(11)王文生:《户外运动》,第171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可分为高山探险、竞技登山、攀岩和普通登山活动四种。(12)张建新、牛小洪:《户外运动宝典》,第215-216页,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高山探险中,登山运动员需要克服艰苦的高寒缺氧环境、复杂的冰川地形和恶劣的自然天气等一系列的危险,因此,攀登高海拔雪山被视为人类探索和奋斗精神的象征,堪称极限运动中的“皇冠”。
鉴于我国登山运动的发展变迁,邱华栋笔下的登山故事既沿袭了早期登山文学的英雄主义精神内核,但又有所区别与侧重。《鹰的阴影》中的高山探险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和个性化,它是个人理想信念和价值的实现途径,更是一趟自性的英雄之旅。小说主人公们像神话中的英雄一样踏上历险的旅程,获得某种以象征性方式表达出来的领悟,接着又再度回到正常生活场域,这条首尾相贯的道路是坎贝尔(Joseph Campbell)所谓的“成长仪式准则的放大”。(13)〔美〕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第23页,黄珏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登山是前往人迹罕至之地,“是人体很难承受的极限之旅”。(第128页)相较于一场普通标配时间约为6小时的马拉松长跑,攀登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的一个登山周期约为60天,每天的攀登时间5-8小时不等。同时,登山运动员需要身载大量的装备负重前行,还要面对不停的上坡路段,以及需要上肢力量的技术型攀登,其无一不对登山者的力量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因此,对于登山者而言最重要的运动素质是出类拔萃的肌肉力量。英国作家麦克法伦(Robert Macfarlane)将登山称为一项体现“男子气概”(manliness)的运动,是一个人体力的证明。(14)〔英〕罗伯特·麦克法伦:《心事如山——恋山史》,第97-98页,陆文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主人公陆英勇自大学时代就是运动健将,作为校划艇队的队长,面对哈佛、牛津、剑桥等大学“个个身形高大,如猛虎下山一般把个小小的划艇划得像是离弦的箭一样飞,又像是脱缰的野马一样快”(第129页)的欧美队员们,“这位身高一米八八的划艇队队长,带领他的划艇队员们击败了世界上几所最著名大学的划艇队,取得了冠军”。(第128页)时年40岁的他历经生死考验,征服过全世界各大洲的最高峰,还去过南极和北极点,完成了“5+2”的辉煌战绩。
自1923年英国登山家马洛里(George Mallory)道出传世名言“因为山在那里”(Because it’s there),至今已有4000余名登山者前往珠峰挑战世界的至高点。高山是康德所言“自然界数学崇高”的体现,试图征服它,不仅需要超越常人的肌肉力量,还必须借助人类的意志力量与之抗衡。虽然不乏一些欧美富豪花几十万美元雇夏尔巴人将他们抬上山顶,但是登山铁律之于陆英勇只有一条,“登山,就要一步步地走上去……不是一步步地走上去的,就不算登山”。(第134页)在十二年的登山生涯中,陆英勇循环往复地“进入了变幻不定、难以捉摸的梦一样的地方,在这里他必须经受住一系列的考验”。(第83页)他的登山故事是人类力量欲的宣扬,更是意志力的确据:他曾经感受到来自乞力马扎罗峰顶的召唤,愉快且顺利地登顶非洲第一高峰,但却在第二年攀登珠峰时精神崩溃,功亏一篑;面对荒凉的阿拉斯加大冰原,他战胜了“内心的孤独和枯燥感”(第143页)登上了北美的麦金利峰;他曾经怀着“巨大的自豪感”,(第153页)在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顶展开五星红旗向祖国报告喜讯;也曾出于对家人的思念在抵达北极点后“一下子大哭不止”;(第161页)他曾徒步穿越空旷到令人顿生绝望感的南极大陆,最终一鼓作气登上南极洲的最高峰——文森峰;也曾在印尼查亚峰遭遇致命滑坠,在“经历了一场生死挑战”(第175页)之后,最终成功登顶大洋洲最高峰。
《鹰的阴影》通过虚构主人公与历史真实人物之间巧妙的互文性,向20世纪初首次攀登珠峰的伟大英雄们致敬,陆英勇和周翔身上分别有马洛里和欧文(Andrew Irving)(15)1924年6月8日,英国著名登山家马洛里和搭档欧文在冲顶珠峰时意外失踪,人们最后一次看见他们时,他们正向山巅走去,当时距离珠峰顶峰约244米。至今仍没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早在新西兰籍登山家希拉里(Edmund Hillary)和夏尔巴向导丹增(Tenzing Norgay)成功登顶的29年前就已经创下人类首次登上世界最高峰的世界纪录。“马洛里和欧文是否成功登上世界最高峰”也成为20世纪登山界最扑朔迷离的悬案。的影子。小说故事发生在珠峰冲顶途中,而在登山界,珠峰8000米以上的高度素有“死亡地带”(death zone)之称,该区空气含氧量仅为东部平原地区的1/4,最低气温常年在-30℃至-40℃,12级飓风屡见不鲜,且地形极端险峻。目前,已有超过200具遇难者遗体(16)Strange Remains.The Accidental Graveyard in the “Death Zone” of Mt. Everest,引自https://strangeremains.com/2014/03/02/the-death-zone-of-mt-everest-is-an-accidental-graveyard-littered-with-the-bodies-of-adventurers/.被留在该区,成为醒目“路标”,告诉后继者们“来到这里可能会死的……死得那么平静、平常和安宁,趴在那里再也不能回家,也不能继续向上攀爬,更不能后撤到山下的营地里了”。(第147页)1996年的珠峰山难(17)1996年春季,珠峰共夺去了12名登山者的生命,这是珠峰登山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登山季。再次证明,“攀登珠峰始终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而且毫无疑问,无论登山者是由向导带领登顶的喜马拉雅新手,还是与同伴一起攀登的世界级登山家,这种危险将永远存在。”(18)〔美〕乔恩·克拉考尔:《进入空气稀薄地带》,第186、163页,张洪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高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验室,物竞天择这一过程的加速版本在里面发生”,(19)〔英〕罗伯特·麦克法伦:《心事如山——恋山史》,第97页,陆文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此外更重要的是,人类伦理道德的底线同样也在这一场域中被反复实验。当人类的生存本能与严苛的自然环境在空气稀薄的“死亡地带”角力,自我保全已属不易,面对同伴垂死之际的不作为是否可以用“山下”伦理道德的准绳去衡量善恶,答案似乎不那么显而易见。亲历1996年珠峰山难的克拉考尔(Jon Krakauer)在《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中写道,“在8000米级山峰上,人是无法顾忌道德的”,(20)〔美〕乔恩·克拉考尔:《进入空气稀薄地带》,第186、163页,张洪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那些疲惫到无法帮助队友的登山者选择视而不见甚至是见死不救,不是因为道德的缺失,仅仅是自身能力的不足,而这种不足是值得被理解并且原谅的。正是如此,陆英勇舍命救人的英雄主义行为是人类灵性的高升,是勇气、无私和善念的极致,它给予高山伦理困境一份人文主义情怀,突亮了与山之“至高”相互交映的人性之高贵。
作为“精神上的引领者和兄长”,陆英勇一路上悉心照料周翔,并在他经历命悬一线的滑坠事故时将其生生拽出死亡的领地,“那个过程是周翔刻骨铭心的,就像是一百年那么长的时间”。(第171页)在整个团队遭遇边境极端武装分子绑架,陷入十死无生之际,更是陆英勇牺牲自己掩护周翔成功逃脱。
《鹰的阴影》结尾,陆英勇化身为珠峰上空飞翔的鹰,“在遥远的高空守护着他,使他回到了自己的国土上”。(第192页)关于登山的故事往往会以一个明确的结局为中心,其不外乎以登顶或者创作纪录为标尺,书写后人无法企及的成功,或是浓墨重彩的英雄主义式的失败。陆英勇的登山生涯和生命在第二次冲顶珠峰时戛然而止,他曾言:人们会记住每个死去的登山者,“即使(他们)不是英雄,也是为了心里的理想死在雪山上的,和大多数庸俗不堪、无法挑战自我的庸人是不一样的”。(第138-139页)为理想信念而登山,为救助队友而舍命,陆英勇的登山精神被至高的珠峰所托举,升华为英雄主义颂歌,与此同时,英雄的历险之旅也徐徐落下帷幕。坎贝尔曾言:“英雄人生经历中最后的一幕是死亡或离开。在这里生命的全部意义被集中体现出来。”(21)〔美〕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第320页,黄珏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高山探险(攀登雪山)是一项伟大而壮丽的极限运动,登山者们向着海拔至高的峰顶进发,“那里可能是孤寂的处所——或是伟大成就的舞台。”(22)〔英〕加思·哈廷:《攀登手册》,第6页,北大山鹰社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鹰的阴影》为陆英勇“英勇无畏”的登山故事作传,高山最终成就了他人生的至高之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舞台以供我们去探寻英雄的原型,而这些英雄们无论成功或失败均实现了神话的象征。(23)Clayton M.Gahan:The Highlight with a Thousand Faces:Sports and Our Yearning for Hero and Myth,The English Journal.2014,104(1),p.41.
三、至远:大河之里的鳄鱼狩猎与华人身份建构
狩猎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人类生产活动,古代人类为了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对野生动物进行狩猎。现代的狩猎已转变为以娱乐目的为主的一种运动,称为运动狩猎(sport hunting)。(24)唐谨成、周学红:《世界狩猎业概况》,《野生动物》2013年第6期。作为一个农耕文明发达的古国,我国现存的自然传统狩猎已成为一种将要没落的文化仅存于一些极少数的民族中。当代狩猎文学多从少数民族的原始狩猎传统和风俗中汲取灵感,在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塑造了诸如《七岔犄角的公鹿》(1981)中的鄂温克族猎鹿少年、《蓝幽幽的峡谷》(1982)中与公狼肉搏的蒙古汉子扎拉嘎,以及《额尔古纳河右岸》(2005)中猎杀黑熊的鄂温克族猎人林克等经典的少数民族猎人形象。因此,在此语境之下《鳄鱼猎人》具有别样的分量:中国当代文学首次出现“澳大利亚华人猎人”形象,其颠覆了我们惯有的阅读经验。
狩猎活动并非仅是一场考验技艺与勇气的体力挑战,而是涉及一个更大的议题,即掌控那些被广泛认为具有灵性、速度与力量的动物的能力。(25)〔美〕托马斯·爱尔森《欧亚皇家狩猎史》,第141页,马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鳄鱼猎人》中,主人公团队狩猎的对象是澳洲北部地区特有的咸水鳄。这种现存最大的爬行动物,体格健硕,性情凶猛暴戾,攻击性极强。成年个体全长6-7米,重约1吨,最长可达10米左右。(26)谢宇、成红军、孙军:《冷血残忍:鳄鱼》,第113-114页,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因此,鳄鱼狩猎是对人的智力、勇气和毅力的挑战,是人与自然界中强悍、凶猛的顶级掠食动物的正面冲突,稍有不慎便会命丧鳄鱼口中,其危险性极高。
《鳄鱼猎人》依循两条并置的叙事主线,讲述了两个具有同构关系的鳄鱼狩猎故事:去年夏天,小说主人公——澳洲华人杜飞以身涉险,在墨尔本市区独自追捕杀害中国女孩的凶手,最终将其绳之以法;这年夏天,杜飞远赴达尔文市与同伴一起抓捕吃人的白化鳄鱼,通过与鳄鱼针锋相对的生死较量,终于将其成功捕获。小说中的两个狩猎场横跨澳洲南北,相距3753公里:一个是以“种族熔炉”著称的南部第二大城市——墨尔本;一个是位于北部达尔文市郊区有着史前时代原始风貌的阿德莱德河。小说中,南方大都市的现代城市景观与北方大河的原始自然风貌在故事中交替出现、流畅转场,又围绕“鳄鱼”的象征义(一种隐居在集体无意识深处的灰暗、暴躁的生活态度(27)Hans Biedermann,Dictionary of Symbolism:Cultural Icons and the Meanings Behind Them.James Hulbert trans,New York:Facts on File,1992,p.81.)和本体(自然界中强悍、凶猛的顶级掠食动物)交叉叙事,主人公杜飞在两个并置的时空中穿梭,既是现代都市的城市猎人,又是需要遵循丛林法则的自然猎手。
鳄鱼狩猎是小说的叙事主线,然而《鳄鱼猎人》中又包含了一条更为隐晦的支线,即通过回溯“至远”的澳大利亚华人移民大历史,思考华人移民如何形成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并有效地融入当地的社会和文化生活。据澳大利亚正史称,中国人第一次大批来澳约在1855-1856年,但据澳大利亚的英文野史和大众史书记载,单个中国人抵澳时间早于1829和1830年。(28)〔澳〕欧阳昱:《澳中文学交流史》,第9页,台北,猎海人出版社,2016。澳大利亚华人移民史历经近200年,目前已有约100万华人栖居于此,“华人移民群体也成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第47页)《鳄鱼猎人》在叙事分支上,勾勒出先后三代澳洲华人的生存景象:第一代华人的缩影是淘金镇矿井放映室里所看的19世纪老华人淘金者的立体影像,他们“怀着和那些先期抵达澳洲的欧洲白人移民一样的渴求黄金和财富的梦想,开始了他们艰辛的淘金生涯”;(第78页)第二代华人是以实现了“澳洲梦”的澳洲华商协会会长——福建地产商金志成代表的80年代中后期的新华人移民,他们“适应了当地的文化风俗和法律经济环境,如鱼得水”;(第68页)相较于早期廉价的华人劳工和攻破澳洲主流社会的精英阶层,小说主人公杜飞是后奥运时代的新新移民,“(他)和来澳洲的老华人不太一样了”。(第66页)作为“异乡人”,杜飞之于澳洲的情感倾注和社会活动的参与度在小说中逐步推进,其发展路径可以被理解为海外华人身份建构过程的缩影。英国文化理论家霍尔(Stuart Hall)认为,“应该将身份视作一种‘生产过程’(production),一个从来都没有完结,始终处在进行状态的一种内在而非外在性的再现。”(29)Stuart Hall: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A Reader,ed.Williams Patrick,Laura Chrisman.London:Harvester Wheatsheaf,1994,p.392.因此,杜飞栖居澳洲的十年是澳洲华人新身份的持续生产、建构、定位和再定位的动态过程。
初来澳洲的杜飞兴趣使然,在工作之余拍摄过几部充满人文关怀的纪录片,拍摄对象均是一些澳洲本土物种,如桉树、考拉、小企鹅和大袋鼠。“杜飞拿着自己拍摄的这些纪录短片去参加一些国际影展,获得了几个纪录片单元的小奖,这使他在拍摄动物方面有了点小名气”。(第64页)正是基于澳洲纪录片界的认可和个人良好的声誉,当达尔文市招募鳄鱼猎人时,农场主戴特才会邀请杜飞一同参加狩猎活动。在鳄鱼狩猎“城市篇”中,受到海外华人身份认同中所存在的一种稳定的、连续的、不变的集体无意识,即霍尔所言的融入骨血、代代传承的“存在”(being)身份,杜飞对于当地社会针对华人的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出离愤怒。小说以“鳄鱼狩猎”为题,不仅意在书写抓捕鳄鱼的娱乐性、刺激性和冒险性,而且作为海外华人身份建构方法的极限运动更是作家旨在突出的意义指向和阐释拓展。以移民国著称的澳洲拥有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的移民文化,不同种族、信仰、语言和文化的移民构成了澳洲民族的主体,作为身份“生成”(becoming)方式的体育运动提供了民族认同形成所需的符号、仪式、神话、传统、历史和实践场所,成为整合多元化移民社会的一个重要力量,(30)马军:《体育运动对民族认同的整合作用——美国经验的启示》,《体育学刊》2015年第3期。也为塑造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言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ed community)奠定了群体想象的基础。于此,鳄鱼狩猎“大河篇”中,杜飞的道德、责任和义务不再自我设限于华人群体,基于对新移民身份的尊重和认同,原先的“乡土意识”逐渐深化为一种“本土意识”,他也从聚焦华人群体的“小我”,走向观照整个澳洲社会群体的“大我”,同时也赋予鳄鱼狩猎这项带有娱乐性质的运动狩猎项目更为严肃且深远的社会和文化意义。
邱华栋的《鳄鱼猎人》令人意外地塑造了一个极具正义感的澳洲华人猎人形象,狩猎对象既是现代都市中穷凶极恶的杀人犯,又是原始大河里吃人的鳄鱼,同时借由“至远”的澳大利亚华人百年移民史的支撑,将鳄鱼狩猎这项极限运动视为海外华人积极参与并融入当地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行为表现和身份建构方式,这在当代文学甚至是澳大利亚华人文学中都是极其少见的。
四、极限运动小说:当代文学的另一种叙事维度
每一种体育运动都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极限运动的危险性正是其魅力所在,“此类运动的魅力就在于激发恐惧,从而让人以全新的眼光看待生命与生活”,(31)〔挪威〕拉斯·史文德森:《恐惧的哲学》,第91-92页,范晶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而作家的创作意图也在于此,展现危险的魅力,并指向其背后更为深远的内涵。极限运动能激起一种使人意夺神骇的恐惧感,并指向一种全新的审美愉悦的源泉——一种让人愉悦的恐惧,它可以在黑暗与阴影及恐惧与战栗中、在洞穴和峡谷里、在悬崖的边缘、在层层云雾之中、在地球的一切裂缝中被发掘。(32)〔英〕西蒙·沙玛:《风景与记忆》,第525页,胡淑陈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它使高山、海洋、沙漠、天空甚至是太空这类自然界无限数学的奇观成为人们审美和体验的对象,同时极限运动者们跳脱风险分析的惯常思维方式(人类自保的欲望),携带一种自主感,在大自然的奇观中体验恐惧、克服恐惧,从而产生崇高的审美体验。极限运动充满神奇的吸引力,它所蕴含的那种坚忍不拔和无拘无束的随性生活理念和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是对现代都市人固有的追求舒适与安逸生活态度的一味“解药”。它标志着一种年少轻狂式的拒绝,拒绝怨天尤人,拒绝意志薄弱,拒绝所有的弱点,拒绝缓慢而乏味的生活。(33)〔美〕乔恩·克拉考尔:《进入空气稀薄地带》,第98页,张洪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邱华栋生于“大气和荒凉”的新疆昌吉,他的文学才华早在十四五岁就已初露峥嵘,大学毕业后去北京闯荡,坚持写作三十余载,创作颇丰,体裁广泛,尤其难得的是,作家的阅读面甚广,年阅读量达七八百本之多。刘震云称邱华栋是一个喜欢新鲜和占先的前行者,“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像他那么博览群书和博览生活的人,特别是博览新书和博览新生活的人,还不多见”,(34)刘震云:《前行者邱华栋》,《教授·序言》,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因此他才能驾驭对于大多数当代作家而言如此陌生的写作领域:潜水、攀登雪山和抓鳄鱼。同为记者出身的海明威在53岁发表了举世瞩目的《老人与海》,而刚踏入“知天命”之年的他,其创作心理似乎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北岛曾言“一个人的行走范围,就是他的世界”,近年来,足迹几乎遍布全球的“地图迷”邱华栋,逐渐将目光投向世界地理学,2018年间陆续出版了《行者无疆》《去往归来》和《从东西到南北》三部游记散文集。“他的世界”投射在《唯有大海不悲伤》《鹰的阴影》和《鳄鱼猎人》中,这是大自然的广袤、壮美和作家用世界性视野观照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突围。三幅极限运动的世界地图无一不凸显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结合,而“运动着”的身体通过不同的身体姿势使人对空间的感知和建构成为可能,并赋予空间以至深、至高和至远的物理意义和精神价值。
借由《唯有大海不悲伤》《鹰的阴影》和《鳄鱼猎人》,作家的视线穿过人山人海,迎向山河大海,通过极限运动叙事将现代都市人狭小的内在精神景观引向阔大之境,在广袤的大自然中去寻访内心自我、发掘自我价值,进而体悟生命意义。如果说极限运动抛弃了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舒适与慵懒、沉闷与单调,召唤极限运动爱好者们不断地冲刺极限、冲击自己,那么初尝极限运动写作之趣的作家亦是在打破写作的“舒适区”,勇敢地向自己并不擅长的创作领域发起挑战。《唯有大海不悲伤》《鹰的阴影》和《鳄鱼猎人》让我们看到冷寂的当代体育文学的多种打开方式,“让我们看到当下写作在现实突围中新的方向及可能”,(35)吴佳燕:《邱华栋的高山大海》,《唯有大海不悲伤·附录》,第211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更创造了当代文学的另一种叙事新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