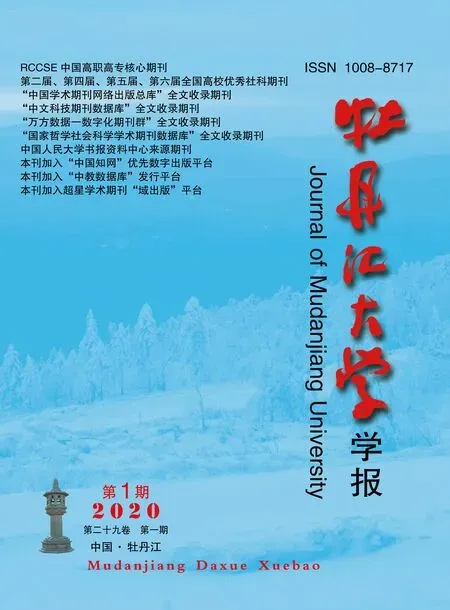加勒比文学的杂糅化书写特征
张雪峰
(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北京 100048)
1492年10月12日,航行了2400海里的哥伦布抵达加勒比地区的圣·萨尔瓦多,发现了这一物产丰富的新世界,也就此开启了西班牙、英国、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对于该地区长达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漫长的欧洲殖民历史造就了加勒比地区独特的文化面貌:随着土著阿拉瓦克(Arawaks)与加勒比(Caribs)本土民族的消失,加勒比人丧失其本土文化源头,陷于纯粹的文化无根性。欧洲文化、非洲文化以及亚裔文化的重新输入又最终形成了加勒比碎片状的、多民族混杂的多元文化体系,文化杂糅性成为加勒比地区最为显著的文化特征,而加勒比作家在书写中也逐步形成了杂糅化书写特征,这其中既有对加勒比杂糅性文化身份的认知流变,又有与英殖民文学形成互文关系的杂糅性书写策略。
一、 加勒比杂糅性文化身份书写的流变
在无根性与异质杂糅性构建的两极文化空间中,对于加勒比故土、家园与民族身份问题,现当代加勒比作家形成了三种书写态度:一是以奈保尔(V.S.Naipaul)为主的悲观书写视角,认为“西印度岛屿的历史从来都无法被令人满意地讲述。①野蛮并非唯一的困难。历史是建立在成就与创造之上的,然而西印度群岛什么都没有创造”。[1]209二是与奈保尔针锋相对又截然相反的乐观书写视角,加勒比诗人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反驳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印度群岛总是什么都创造不了,那是因为西印度群岛即将创造的将是世人从未见识过的东西。”[2]54另一诗人兼评论家布莱斯维特(Edward Kamau Brathwaite)在其诗歌中同样宣称:“从无创造的我们,就必须以‘无’而生存。”[3]79第三类作家群体则是以当代移民、流散作家为主,他(她)们对于其西印度身份持含混的书写态度。在其作品中,他(她)们一方面控诉殖民历史的创伤,另一方面叙述文化无根性与异质杂糅性引发的异化心理。但这种异化心理与奈保尔对待西印度身份的悲观态度又有明显区别,这样的异化心理更多是源于西印度身份在移居地、流亡地被“东方化”而产生的无所适从,“…… 这就是伦敦, 这就是贵族的生活,口袋里有钱走起路来才能像一个国王,对这个世界不会有丝毫担忧……‘妈妈,看那个黑人!’一个孩子抓着他妈妈的手,抬头看着加拉哈德先生。”[4]87于是诸如塞尔文(Sam Selvon)小说中的主人公加拉哈德一样,流亡他乡的西印度人只能依托于美好的回忆与想象来维护、粉饰其西印度人“黑皮肤、白面具”的伤痛。即便如此,无法抹擦的西印度民族身份的缺场却始终是西印度作家书写的叙事内核。因此,“孤独的伦敦人”“流亡的快乐”“无可归依”、“黑暗中的航行”等就成为移居、流亡群体西印度身份含混书写的最恰当表述。②
加勒比文学评论者戴维斯(Boyce C. Davies)指出所有流散作家共同的流亡体验 “只有经历了流离失所的体验之后,才知道家的意义”[5]113,因此,只有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上,家园、故土、民族身份的意义才显得格外突出。加勒比流散裔作家的作品中都具有浓郁的加勒比地域以及文化特色,其作品都叙述了流亡时遭遇的心理异化以及无可归依感,并借此控诉英殖民主义带来的心理创伤,但早期加勒比流散裔作家与后殖民时代流散裔作家对于加勒比故土、加勒比身份以及加勒比文化的态度与流亡的异化感的叙述方式却迥然不同。在塞尔文、里斯(Jean Rhys)等早期作家的作品中,对于西印度家园想象性地回归成为其主人公在伦敦或者其他流亡地生存的心理支撑。流亡的西印度主人公常常保留对于西印度家园美好的记忆,思乡、童年的美好回忆以及对于加勒比世界的渴望与膜拜就成为早期流亡他乡的西印度人抵制移居地或流亡地异化心理的平衡策略,流亡地的冰冷、冷漠与西印度故土的温暖、热情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如《黑暗中航行》(Voyage in the Dark,1934)中安娜的感受,初到英国的安娜就感受到加勒比与英国地域环境的差异,“这里的颜色不同,气味不同,周边事物触及内心的感受已然不同……起初我一点都不喜欢英国,我不习惯这里的寒冷。有时候我闭上双眼,把火或者是被褥的温暖假装为太阳的温暖,或者假装我站在家门外,从马尔凯特市场看向海湾。”[6]7安娜的这种感官认知反差映射出的正是流亡于伦敦的西印度人的心理异化,他们无法融入英帝国的主流文化,又在西印度找不到隶属于自己的民族身份,只能沉溺于自己对于西印度故土的幻想之中,以幻想抵御自己的心理异化。
而以克里夫(Michelle Cliff)、马歇尔(Paule Marshall)、金凯德(Jamaica Kincaid)等20世纪晚期开始写作的第二代加勒比非裔流散作家,在以更强烈的情感控诉英殖民历史对于加勒比民族的心理创伤的同时,却是以更坦然的心态看待自己的民族身份与流亡体验。与早期的流散裔书写不同,加勒比流散作家以加勒比非裔居多,而且在加勒比地区纷纷取得独立之后,加勒比非裔成为主流群体,因此,尽管他们或者她们在后殖民时代依旧难逃殖民历史的阴影,但他们不再借助于对于西印度故土的幻想来抵御心理异化,无需美化与神秘化,而是自然而然地将加勒比非裔文化内化于心,奥比武术、僵尸附身、加勒比狂欢仪式、死亡重生等加勒比文化传统成为他们平衡与抵制心理异化的策略。金凯德在采访中提到奥比巫术在其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它就是我实际生活中的一部分,它不仅嵌入我的记忆,也存在于我的无意识中。”[7]408此外,在后殖民时代,面对已然形成的加勒比多元文化形式,加勒比流散作家不再刻意追求加勒比身份,而是以不归属于任何文化传统与写作传统的“世界公民”的自由视角,坦然接受当代加勒比地区无法回归非洲文化根源的现实。因此,与早期流散作家不同,后殖民时代的加勒比作家与其作品中人物不再焦灼于自己加勒比非裔身份的边缘性,不再刻意凸显加勒比非裔的文化身份,不再纠结于过去还是现在的文化身份选择,而是将流亡与流亡体验本身视为回归家园的一种形式,并以此强调文化身份的流动性与杂糅性。文化的流动性与杂糅性已经成为加勒比文学唯一的叙事特征,也正是这样的流动性与杂糅性将加勒比作家纳入了除却民族、种族以及性别之分的现代流散作家书写的队伍之中,成为消解你们、我们、他(她)们之分的全球性文化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加勒比作家的互文性书写策略
当异质性与杂糅性成为加勒比地区多元文化的显著属性,而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性则成为链接加勒比异质与杂糅文化的核心结点。对于加勒比多元文化的杂糅性,加勒比著名诗人及文学评论家格里桑特(Edouard Glissant)用“一连串的关系”构筑的“关系诗学”来加以描述:“究竟什么是加勒比?它是一连串的关系。我们都能感受到它,我们都会以或隐藏或迂回的方式表达它,或者我们也会强烈地否认它。但是无论怎样,我们都明白加勒比海始终存在于各个岛屿之间。”[8]139与此相对应,另一评论家达什(J.Michael Dash)则以“一连串的文学关系”来界定加勒比文学叙述的多样性:“什么是加勒比文学?加勒比文学就是一连串的文学关系。”[9]20实际上,达什强调的加勒比文学关系与格里桑特强调的文化关系彼此之间相辅相成,都是凸显加勒比地区文化与文学形式的跨文化特性。如果说格里桑特所言的文化关系诗学的实质是打破种族、民族等历史文化范畴的既定约束,强调加勒比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融,那么达什所指的加勒比文学关系诗学的实质则是强调加勒比文学与西方文学、非洲文学以及亚裔文学之间在文学形式层面的互文性,亦如达什所言“新世界(即加勒比世界)这一语境或许比较粗糙甚至有时不尽人意,但它的确提供了一个能够将跨越语言与民族界线的作品与意识形态并置的文化语境……通往加勒比文学唯一有用的方法就是互文性”[9]20。
相比与其他文学的互文关系,加勒比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互文关系则颇为显著。譬如,西塞尔(Aime Cesaire)的《暴风雨》(Une Tempete)改编于莎翁的《暴风雨》(The Tempest),尽管西塞尔的《暴风雨》重点凸显的是卡列班(Caliban)所代表的黑人奴隶的愤怒与抗议;兰明(George Lamming)在其文集《流亡的快乐》(The Pleasures of Exile, 1960)中亦是借用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普罗斯佩思(Prospero)与卡列班的关系,呼吁加勒比知识分子行使西印度黑人话语逆转的权力;而哈里斯(Wilson Harris)《孔雀宫殿》(Palace of Peacock, 1960)中的迷幻航行重蹈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之心》(The Heart of Darkness)的非洲之旅,里斯《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1966)中安托瓦内特的故事则成为《简•爱》中阁楼里的疯女人伯莎的前传,沃尔科特的《奥梅罗》(Omeros, 1990)则是将《奥德赛》(Odyssey)重置于西印度语境。
加勒比文学与西方文学间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互文关系主要归因于根深蒂固的殖民文化与殖民教育的影响。加勒比地区的英语教育体系不仅仅只是要求说英语,而且也全盘继承了英语文化遗产。而接受殖民文化教育的加勒比作家则借助于作品人物的叙述声音表达了这种殖民文化的影响。里斯在《黑暗中航行》借安娜的叙述声音说道“自我能够阅读开始,我就知道英国……”[6]9;金凯德笔下的露西也有着同样的经历,“当我还是维多利亚女王女子学校一个10岁小学生的时候,我就被要求必须会背诵一首(英语)诗歌……”[10]30;而奈保尔在《模拟者》(The Mimic Men,1969)中则借助于辛格(Ralph Singh)的叙述声音指出殖民教育使得加勒比人成为“模拟者”的负面影响:“我们只是假装真实、假装学习、假装为了我们自己的生活而做准备,我们都是新世界里的模拟者。”[11]146
除去殖民文化与殖民教育对于加勒比作家文学记忆的冲击之外,英国文学作品中对于加勒比人形象扭曲的叙述也是促使加勒比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产生互文性的成因。作为英殖民社会现代性与优越性的文化标记,英国文学作品塑造出了诸如普洛斯佩罗、鲁滨逊(Robinson)等大批优秀的“哥伦布后代”的形象,他们无一不是大英民族文化与文明的优秀继承者,而卡列班与星期五(Friday)等加勒比人在主流文学叙述中只能被动地被贴上原始、野蛮的文学标签,等待欧洲现代文明的垂怜与救赎。因此,当西塞尔、兰明、哈里斯等加勒比作家开始写作之时,他们的作品首先就会通过与西方文学之间的互文关系,重新书写加勒比人的视角,言说加勒比人曾经被压制的声音,从而碰撞出对抗殖民话语的反击力量。
然而,殖民与反殖民的意识形态冲突,却使得加勒比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存在的互文关系要么被后殖民理论以对于帝国话语的“逆写”盖棺定论,要么则被笼统地纳入后殖民挪用策略。以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为主的后殖民批评家认为兰明、里斯等人的作品以“逆写帝国”的方式构建起了后殖民反殖民的话语批评范式;[12]189博爱莫(Elleke Boehmer)等后殖民评论家则认为重写这一叙述策略使得后殖民作家得以重新书写自己的民族历史;[13]188而以饶(Raja Rao)为代表的后殖民作家则将“不以自己母语写作但却表达自己民族精神的方式”[14]34,即挪用殖民语言及文学形式的方式,视为瓦解殖民文化霸权地位的有效策略。兰明、哈里斯、里斯等加勒比作家以逆写殖民文学经典、挪用殖民语言与殖民文学形式的方式抗击殖民话语暴力这一后殖民评述观点毋庸置疑亦无可厚非,但忽略加勒比地区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将加勒比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互文关系只是简单地以逆写、重写以及挪用等普适的后殖民书写策略一概论处,无疑是淡化了加勒比作家在殖民时代创作的社会文化语境。而回归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一直是探究不同文学互文关系的必要要素之一,写作主体、接受者和文化语境参照这三种要素构建了一个混杂的复调集团,彼此形成狂欢化式的对话体系。互文体系则是以写作主体-接受者构成的横轴与文本-语境构成的纵轴的交汇共同定位话语位置的符号系统。因此,在跨民族、跨文化文学发展的大语境下,在理性的文化对话中重新审视加勒比作家的互文性书写,厘清加勒比作家互文性书写背后的缘由,展现加勒比民族、种族背后多元、杂糅的文化传统,就显得尤为必要。
三、结语
加勒比地区的杂糅文化现状使得加勒比文学书写呈现跨民族身份、文学文化互文性等杂糅化特征,这也是加勒比文学研究在全球化进程中能够逐步从边缘走入中心的原因所在。当民族、种族身份等逐一被解构之时,流变与杂糅就成为文学文化书写唯一不变的特征,加勒比人对于文化身份的理解变化无疑是对于流变与杂糅文化的最佳阐释。另一方面,当流亡、心理异化成为现代文学以及后殖民文学具有普遍性的叙述时,洞察流亡、异化这一普遍性背后的特殊性、具象的杂糅性才是避免流亡、杂糅性、多元性这些术语走向泛化、本质化与形式化的重要路径。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加勒比杂糅文化与加勒比文学中呈现出的杂糅文化表征对于为当代文学与跨文化研究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注释:
①西印度(West Indies/West Indian)群岛通常指加勒比地区前英属殖民地,如牙买加、特立尼达、巴巴多斯以及安提瓜、圭亚那等。而“加勒比”(Caribbean)一词则指涉该地区所有的岛国。为便于论述,本文文内所提及的加勒比文学或西印度文学均指涉加勒比英语文学。
②“孤独的伦敦人”源于赛尔文的小说《孤独的伦敦人 》(Sam Selvon.The Lonely Londoners.Harlow:Longman,1985);“流亡的快乐”源于兰明的作品《流亡的快乐》(George Lamming.The Pleasure of Exile.London:Michael Joseph,1960);“无可归依”源于莱利的作品《无可归依》(Joan Riley.The Unbelonging.London:Women’s Press.1985); “黑暗中的航行”则源于里斯的《黑暗中的航行》(Jean Rhys.Voyage in the Dark.Penguin Books.1967)。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解读《藻海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