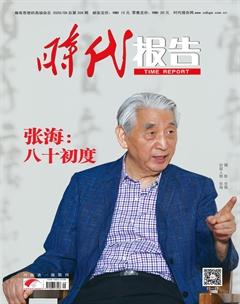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2017年,接手扶贫,接受挑战,接手这项需要在乡村一环套一环落实的政治任务。
那一刻,我知道我投入了一场与贫穷的战斗、一场与物质、精神的战斗。面对贫困县的脱贫摘帽,面对几十年来,农村最底层的面貌和生存状态,我仅仅用三年的脱贫攻坚就能去改变吗?我想自己只有尽全力去改善、去推进,就是最大的问心无愧。
在这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面临习总书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伟大祖国已全面消除贫困的庄严时段。此刻,一幕幕都映到了眼前。
演讲者桂玲
桂玲, 一个门牙有些外张,脸上满是斑点,说话有些蛮,腿因风湿而不灵便的女人在华庄村、陡沟陈村……全乡36个村室拿着塑料花、手链向四周的贫困群众讲解如何制作,估算每天收入,讨论挣钱后的感受。异样的声音,普通的外貌,她的外表我甚至无法用言语去呈现,我怕这些文字会丑化了她的外表,会对其不尊重,但又想展现她的真实状况,想记录她脱贫前后身心产生的巨大反差。
桂玲是我分包责任村的一名贫困群众,丈夫二级残疾,背部犹如长久背着一口锅一样的外貌。2019年夏季,我拉着她,一个村一个村讲解手工制作,她成了我开展扶贫工作的代言人。
桂玲响应政府号召,最初选择居家就业时,她没有能力为这一选择赋予自主脱贫、精神脱贫的意义。她只是说:“政府这样顾咱,让咱做手工,咱得听话去做。”她甚至连居家就业是为了提高自己收入的意识或动力都没有,她只是懂得要听政府的话。但她做着做着,一切内在的、外在的东西都来了。当她在村产业负责人那里验完手工活儿接到32元钱时,激动地说:“我也能赚钱了!”体验到劳动的价值,这是她精神成长的第一步。我又和她商量,把村里和她一样的贫困女性叫到她家中,让她手把手教她们,她说她不会说话,不会教,只会自己做。为了让她少些窘迫,我说:“您只管一点一点去做,我组织她们来看就行。”在这种情况下,她同意了,我清晰地记得当那天下午她家院子里挤了十多人时,她真的就不说一句话,只是窘迫地拿着手鏈、花瓣编织拼接,见这状况,我就让她用手示范,我用话语配合她的手工。
就这样,当其他群众问她时,渐渐地她也能回答交流几句。经过几个小时,她不仅敢说话了,还教会了其他群众。当其他学习群众走后,她说了一句:“吓死俺了,俺就没说过这么多话!”我知道,这时候的认可与鼓励直接关系着她以后的坚持,还有以后能否引导别人。当时我看着她只说了一句话:“都学会赚钱了咱啥不会!”她的表情瞬间放松下来,好似卸下了什么的。接下来的日子,就有贫困群众自发地再次去找她学习。那一段时间她家院子里总是会有三五成群的群众做手工,她也明显开朗大胆许多,成了这个贫困村半(弱)劳动力居家就业的引领者。接着我又带领她去周边村讲,去全乡36个村教,每当她和我一起入村向群众讲花瓣如何拼接时,总是不忘给贫困群众讲,“咱挣个不是都不发愁买馍的钱了嘛,咱挣个不是都不问别人要了,都比别人给咱强”。而她随着“说话”次数的增多,也许是在教别人时产生了价值感和成就感,2019年冬天她像换了个人一样。当全乡半(弱)劳动力居家就业帮扶工作被市县作为创新帮扶措施进行宣传报道时,市县各级部门到她家调研指导时,她不卑不亢地说:“哪怕我一天赚10块钱,就多个买菜买馍钱了,就不让国家帮我了,国家还有其他好多事需要花钱哩!”那一刻,我心里就像被什么扎了一下,这“扎”是感动、激动,那一刻我甚至难以自抑想落泪。“国家还有其他好多地方发展建设都需要钱,咱不能拖国家发展的后腿”,这是我在入村鼓励动员贫困群众自主就业创业时讲的话,没想到她理解得如此透彻且能说出来。
想到她前前后后的变化,我知道她不只是物质脱贫了,她的精神状态也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我知道我所有的利用中午或晚上开车拉住她去加工点学习手工,带领她入村动员其他贫困群众学手工都是无悔的,我对她每一个认可与鼓励都是有力量的,这些要比给她多少帮扶增收资金都长久!
把桂玲和村内其他半(弱)劳动力引领鼓励起来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不再频繁地和她在一起了,可能是相对熟悉了,虽然不见面,但她喜欢给我打电话,不管是儿子“雨露计划”补贴,还是家里事,她都打电话,只要我一说,她都能迅速理解。而我只要去村里,也喜欢去她家看看,感觉自己好像对她也产生了依赖一样。2019年11月份我又去她家,当看到她在做塑料花,丈夫贵得在里屋做彩灯手工时,很是意外,彩灯手工活也是乡里宣传动员鼓励半(弱)劳动力的男性贫困群众居家就业的手工活,看到贵得已操作得很熟练,我问她:“桂玲姐,咋没打电话说这事?您们自己去加工点学,去领的货吗?”她笑着说:“不给你打电话了,你老忙,俺们自己都会去学。”那一刻,我的心妥妥地落下来。如今,在家庭产业发展上,她家春夏两季侍弄一亩葡萄,秋冬两季丈夫做手工彩灯,桂玲做塑料花拼接和手链编织。
在那之后,有段时间都没有联系,因为全乡的扶贫工作,因为扶贫的种种头绪。腊月春节将至,接到她的电话说专门给我磨的面,还有白菜、萝卜……虽然我不会让她跑腿和折腾,但她从见了生人都不敢说话,到面对那么多人自然、不卑不亢地“演讲”,到喜欢跟我联系,再到后来不联系也能独立自主,再到现在能用物品表达心意。想到她前前后后的变化,我知道,对她这样的脱贫户,还有如她这样的一批脱贫户,我已安心放心,因为他们已实现真正脱贫,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脱贫。
面相之变杜海岗
初见杜海岗是2016年年末,他端着一个大瓷碗蹲在房屋后墙角的电线杆下,房屋后樯用三支木棍支撑三块木板,木板再支撑着墙体,严重的危房,其穿着也犹如其房屋。当村干部向我介绍他时,我也只看了一眼就迅速走开了,因为那面相是让女人下意识要躲开的。走村入户,我见到过那么多苦难和贫困的面相,但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有关这方面的东西,他哪怕有些苦难、有些沉重也好,一个游手好闲、无所谓的光棍汉面相更让人心痛。此刻,我找到了一个有些相对符合杜海岗的词——自我放弃,没有人关注他,没有人在乎他,过一天少两晌,生活每天毫无意义地重复,多年来,杜海岗就以这样一副面貌示人。上澧村诸如杜海岗这样的光棍汉将近20人,深入生活实际、深入民众,才真实地感受到他们的生活。那一年,我深刻意识到一个女人、一个正常的家庭,对一个男人以及所有正常人的影响,长久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会影响一个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精神状态。
2017年,扶贫记忆最深刻的除了增收帮扶,要算我无数次地向村干部提到,能不能在村里物色一个合适的人,帮忙为杜海岗这种状况的人牵线,介绍结婚对象,哪怕是介绍一些有孩子的女人也好。因为我知道,与上澧村一河之隔的另一个村,有许多男人殇掉的女人独自带着孩子生活。那一年,在村里、乡里、群众、同事面前,我经常提到关于解决光棍汉生活状况的想法,我希望村里干部能操心做好这方面的联谊,以解决这类人的心理及精神贫困。但三年来,收效甚微,光棍汉长久以来的生活观念及状况改变起来太难,一些女人是不愿意与其一起生活的。杜海岗及他们的家庭生活问题也成了我这些年做扶贫工作的心病。
2017年8月,上澧村扶贫就业创业基地建成后,在乡村干部的反复劝说下,杜海岗同意去基地车间务工。从开始的上班迟到中间溜走,只捡轻活干,到现在的每天严格遵守车间考勤,准时准点坐在自己蹬机器的岗位上;从以往的衣衫不整到现在的干净整洁;从以往的危房、荒草满院到现在的宽敞平房;从以往的说话轻浮到现在的微笑郑重。每月3000元左右的工资,劳动彻底改善了杜海岗的身心。如今的杜海岗让人真切体会到勤奋、自食其力带给人精神风貌的变化。昔日那个谁见谁躲,邻居远远看见就摇头躲开的杜海岗不见了,听村干部说,已有不少人开始张罗着给杜海岗介绍对象了。
我分明看到了杜海岗与孩子、老婆在这个平房宽敞院落生活的景象。
贫困大学生佳宁、晓娟和路倚
佳宁,这两年只要寒暑放假都要来找我,有时是来乡扶贫办,有时在村里,帮我干活,可能是在乡村长期工作的原因,我习惯于说自己是在干活。佳宁似其母般瘦弱,属于极瘦的那种,从无任何过多的话语,但很温暖,表情有着女孩的安静贤淑,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好姑娘,这也是我发自内心喜欢她的原因。
喜欢让佳宁参与一些工作,不仅仅是自己太忙,让她来帮忙的。是真心想让她多些经历、多些实践、多些精神的富裕,在内心深处我总觉得这方面的富裕比任何东西都珍贵。这些年不知是读书的缘故,还是在乡村实践体悟的增多,我越来越喜欢引领、影响周遭的民众,希望能带动他们坚定有力量地前行,所以我喜欢让佳宁在我身边,喜欢让她融入这个氛围,虽然总是忙得顾不上给她沟通一些利于她学习成长的话语,但我知道“人在干中学、在干中悟”是最有力有效的成长。
这几年,乡里鼓励贫困群众发展葡萄产业,佳宁家也种植了葡萄,每到暑假来乡里她总是会带些葡萄,没有什么很高大上的话语,就只是说让大家吃。佳宁从一个很胆怯的女孩,到如今一到假期就主动来村委会、乡扶贫办里帮忙干活,带葡萄让大家品尝,每到节庆也总是会发微信问候。她的思维与待人接物理念已全然成型,已脱贫的家庭再加上她的成长,我已完全放心。
佳宁就读的学校是信阳师范学院,她将来是要做教育引领人的职业,她会是一名社会发展的有力引导者、推动者!
晓娟,苗庄村贫困大学生,母亲在其很小的时候失踪,多年与父亲相依为命,如今已在郑州读研究生。还记得2014年她考上大学那个暑假和父亲一起来乡机关院找我,当时晓娟的父亲直接就说:“你经常去村里,俺就知道你,别的俺也不认识,妮考上学了,钱不够,看能不能帮帮俺?”在乡村20多年,许多群众我虽说叫不上名字,但只要见到就面熟,当听说是考上大学缺学费的事,我是无论如何要呼吁帮助的。2014年,当时的扶贫工作也只是对贫困村有帮扶项目,她所在的村属非贫困村,并没有过多的贫困资金帮扶。8月底在晓娟临开学走时,帮其申请的慈善救助和爱心人士的捐助顺利到位。2016年国家对非贫困村的贫困群众也要落实帮扶政策时,她家也因教育无保障,被识别为贫困户,晓娟享受到国家的教育补贴政策。2018年暑假晓娟和其父亲又一次来到乡里,再次见到她,她已不再是那个怯生生、羞涩的农村丫头,而有了大学生的聪慧与清气,是那种精神面貌的变化。晓娟的变化我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打心眼里喜欢这样的精神状态。也许是因家有女初长成的喜悦,晓娟父亲也较以往精神明亮许多,晓娟又考上了本校研究生,入学还需一部分费用,我又与县域内公益组织、爱心人士联系,在晓娟开学前送去3000元。我们加了微信,她有事也会通过微信咨询我,到校后又申请了助学贷款,同时有国家对贫困研究生的教育补贴。2019年暑假晓娟在微信里说:“姨,我现在基本上不需要再救助了,爸爸进了清洁公司上班,每月700元,家里还有国家的其他帮扶增收资金,您就放心吧!”每次只要是暑假或寒假,我去村里,也总是会去看看晓娟是否回来。每次在这个朴素还略显破旧的院落中看到她清新的面孔,我就欣慰许多,感觉满是希望。
晓娟的成长是这个家庭的希望,是这个家庭脱贫最硬核的条件。
路倚,我一直没有谋面,却想写写她,她现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读研,其弟在本乡中学就读。母亲多年前就远走他乡,父亲、弟弟和她三人多年来相依为命,其父2018年突然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导致腿不能走路,即使现在有些恢复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但即使这样仍然坚持供养姐弟俩读书,路倚很少在家,暑假也很少回来,她英语考过八级,总是兼职做家教赚钱,供自己和弟弟读书。
如果是其他贫困家庭,我可能只与户主联系见面即可,但路倚的勤奋让我心生怜惜,所以2019年在入户时,我让其父亲拨通了路倚的电话,并加了微信。路倚很忙,我们也很少联系,也只是节假日发微信问候,我们约好,2020年这个春节她回家后我们要见面交流沟通,并且我想让孩子多与其交流,也让路倚的勤奋鼓励引导孩子。同时,我还与其父亲谈了一个想法,让孩子约了班级的三个同学,让路倚为他们补习英语,这样路倚寒假在家也可以有些收入。但遗憾的是因新冠型肺炎疫情,见面学习的计划被中断。
路倚父亲每每谈到路倚时眼里总是难掩的喜悦,我也总是喜欢和他谈路倚,也是为了让他多些生活的信心。因路倚父亲以往在服装企业做过工人懂些缝纫机原理,他腿好些之后,2019年秋,我介紹其进入村扶贫车间做维修技术工,每月收入2000元以上,家庭收入明显增多,路倚也可以不用在外那么拼命了,我甚至劝她多休息,要适当休闲一下。
路倚电话或微信里的声音,后半句总是向上扬的,我知道怎样的贫困都压不垮这样积极向上的声音!
强大的连卿叔
连卿叔今年74岁,全家6口人,至今未脱贫。三年来,我一直为不能很好地帮到他而怀有深深的遗憾。儿子去世,他和老伴,抚养三个智障:儿媳智障、一个孙子脑瘫、另一个孙子至今不会说话,只有一个6岁的孙女可以正常入校读书。
这几年来,能为其家中申请的所有的帮扶增收措施,我们乡村两级干部都做到了。但他家的情况依然是压在我心头的一块石头,不知道这个家庭能撑到何时?最终能走向何种境况?我唯一的期盼是,县乡建起福利院,待连卿叔与老伴没有能力去照料抚养时,有专门人员帮护他们。
连卿叔是我最牵挂的人,也是我鼓励自己的榜样。如不去他家,如果在村室或任何场所遇到连卿叔,都不会想到他是贫困群众,虽然衣服不好,但给人利索且整洁的印象,是那种农村俗话说的“情绪”老头,但去到他家中,进院就是不忍,不忍那片“老弱病残”。2017年接手扶贫工作后第一次去他家,我彻底理解了什么是老弱病残,“老弱病残”不再是我写材料、向领导汇报的文字与语言,是连卿叔及如他们一样那部分人的真实写照。
面对这样的家庭状况,连卿叔一天三餐喂养,一天三遍清洗,一年年的坚持,很少向乡村干部哭穷,识大体顾大局,心态良好。三年来,我与连卿叔无数次接触,只要去村里,他家也是必去的,只为给老人打气,只为提高他生活的信心与力量。我总是说:“您是我们最佩服的人,我们谁也比不了您!”连卿叔总是说:“不这样咋办,遇见这种情况也只能这样(接受)!只要我活着能为他们做一天饭就做一天,不饿着他们就行。”
春节前我去村里,因涉及增收帮扶资金到户签字,连卿叔到村室签字之后随口一句:“我就是发愁,我要是有一天动不了,这一堆咋办!”我一下意识到连卿叔有心理负担了,或者这一段肯定是心情不好,我赶紧让其他人员处理相关工作,跟着连卿叔到了村室外,我问连卿叔是不是有啥困难?遇到啥事了?连卿叔说没什么事,只是我这一年不如一年……临近春节,一年年的延续,连卿叔也是在感叹自己以及家庭的生存。我随即意识到,此刻我能帮到这一家的,或者这一家真正需要帮扶的,仍是精神力量,如果没有强大的心力、心智,连卿叔是坚持不下去的,这一家如果他心劲落了,一切都没有了,不只是脱贫不脱贫的问题了。那一天我给连卿叔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连卿叔离开村室时,虽说已宽慰许多,但我仍不能放下。我给县攻坚办的领导、民政等相关部门逐一打电话谈了乡村未脱贫户老弱病残的现状。虽然我知道上级近两年也一直在致力于加强改善福利院建设。但我仍是要进一步传递作为一名一线扶贫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传递乡村的实际状况,我呼吁了遗憾和愧疚就减轻一些,当然我也相信,这方面的工作一定会得益改善的,只是早晚的事。
春节前腊月二十六那天,我去了连卿叔家,那天我只掂了一兜鸡蛋,以示过年的礼节。虽说不能帮连卿叔什么,但能去家中看看,我的心就踏实些。当我看到院子里的绳上已挂上了清洗好的鱼与鸡,心里瞬间喜悦敞亮许多。在乡村20多年,每当看到乡亲们穿得干净上档次,就莫名高兴;看到他们待人接物有礼有节,神采奕奕地参与文化活动;看到他们吃苦耐劳、勤奋地在田间劳作,就发自内心地喜爱感动。
一兜鸡蛋也许微不足道,也许对帮助连卿叔家的困难杯水车薪,但我好像只能有这些了,说实话我买不过来,也照顾不过来,依我待群众的感情,特别是做扶贫工作以来,面对这部分弱势群体,我什么都想做到,我谁都想去看望,但我真跑不过来,也看不过来,我三千多元的工资要为车加油、要交电话费,还要照顾到跟着我经常各村跑,跟着我加班加点的扶贫办、包村干部的午饭或者晚饭。不是哭穷,更不是抱怨,只是这是我实实在在的工作状态。三年的扶贫工作,错过了午饭、晚饭点,夜间下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有时候在离乡政府十多里外的村庄入户核实,整理资料,我们不可能再开车回乡吃午饭或晚饭后再赶回村里继续工作。为了节省时间,为了赶工作,订餐焖面(没有汤水方便好送,不用碗放在桌子上就能吃)让餐馆送到村室,是家常便饭,以至于现在让我们想起来焖面就摇头,甚至有个同事说,“以后谁提焖面,我跟谁急”。我和同事们的手机里保存着保和街、上澧街、卸店街全乡三个相对繁华些街道的凉皮店、热干面、烩面、饸饹面餐馆的电话。面对这些,我知道我根本没法向党委政府报批,机关单位的公务用餐程序的烦琐也是我不愿意去面对的,而作为分管扶贫工作的副职,做为团队的领头人,我不能让他们加班干活再自己掏腰包吃饭。三年来我没有细算过我在扶贫工作上投入的加班用餐花费多少;开着自己的车36个行政村指导督促花费了多少;没有上下班、周末、节假日来回去县攻坚办报材料、开会花费多少。我只知道自己对贫困群众、对全乡的产业发展、脱贫攻坚、对党组织赋予的职责是无愧无憾的。虽然有诸多委屈在内心深处,但所有的责任与使命又是驱赶委屈最好的良药。2017年贫困县脱贫摘帽我乡被省抽中检查的两个村无一错退漏评,无一政策未落实,无一增收帮扶未到位;2018年省成效考核被抽中的村在产业发展、政策落实、增收到户、金融、就业等脱贫成效排在全省前列。
还有……
还有怯弱的黄兰甫,当我帮扶申请危房兜底政策为他家盖起平房时,他精神抖擞地说:“只要房子有了,我就干着有劲了,其他我什么也不要了!”一家4口,房子是他的软肋。他已多年不再来乡里了,再也不坐我办公室不走了,两个儿子现在已上初中。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村里为他申请了公益岗位,他和妻子还主动去产业基地务工,虽然比不上富裕的家庭,但至少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
还有肯替我跑腿的乐,一个有些“酒精儿”智障面相青少年,每年夏秋禁烧,他就去田间地头帮我,骑着电车不停在田间转着看有没有意外火情。乐有时会和别人争吵,也会有人教唆他做些不安全的事,每当遇到这些状况,有时候他谁的话都不听,只要我去乐就不吭声了。
还有“精神病”朱留锁,总是到田间地头给我们送一些南瓜、桃子、甜瓜……跑到乡机关院里给我送儿子学语文的书,因前些年儿子总是周末或节假日跟着我在田间地头禁烧时写作业,他知道儿子学习读书。有人说不管什么都是他“顺手牵羊”得来的,也有人说那是他给别人清理猪圈或者替别人家干杂活换来的,但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他送到地头的这些瓜果来路如何,不管他给儿子送的书是如何破旧,我都高兴并心怀感激地去接受,我知道此刻我的接受是对他最大的尊重。那一年最让我欣慰的是,我为其提前申请上了五保救助,虽说朱留锁不够五保年龄,但因其智障残国家有提前审批的政策,当他和村干部一起来乡里拿存折时,他的喜悦仍历历在目。至今儿子仍记得他双手在路面上写粉笔字的情景,民办老师出身的他,因那个年代民办老师被停止工作,谈的对象又和他分手,这一系列事件刺激其精神出现了问题。每当他和别人吵架,也只有我去劝,他才肯聽。当听包村干部说他去世的那天,我心里五味杂陈,甚至想去见他最后一面,给他送葬,但又怕被议论为异类,最终在犹豫中未了。如今每当想起在乡村的点点滴滴,我都会忆起留锁并深深地祝福他在另一个世界安好。
……
十个贫困村基础设施全面改善顺利脱贫,1200多户3200多名贫困群众生产生活得以提升,实现全面脱贫。我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在与民众朝夕相处的同时,也在被乡村民众教育、治愈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弱势的体恤,对民众的爱戴,对发展的担当,不知什么时候都一一融入了身心。纯朴的乡亲们唤醒了我的初心与使命,让我的精神得以彻底脱贫,得以全面升华。
我愿如习总书记一样“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忠诚履职,上不愧对组织,下不愧对民众,心不愧对自己!
编辑手记
唤醒
读到一篇来稿——《始终与贫困群众的精神融为一体》(后改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副题是“一位女乡干部的扶贫工作感悟”。
“演讲者桂玲”“面相之变杜海岗”“贫困大学生佳宁、晓娟和路倚”“强大的连卿叔”“还有……”几个小标题,密密匝匝的故事感迎面扑来。
读下去!
这是一位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乡镇女干部,一个月三千多块钱的工资,要为一起加班的“队友”买饭,要为一年四季奔忙不断的车子加油,要补贴那些入村入户时见到的贫困户……这家也想进,那家也想进,这个人想帮,那个人也想帮,这件事想跑,那件事也想跑——作者王海方沉浸于这样的人生状态中。
贫困户桂玲,从不敢当众说话,到跑遍30几个村庄给妇女们讲解塑料花和编织手链的做法。王海方关注着桂玲一点一滴的心理变化:从她说“政府这样顾咱,让咱做手工,咱得听话去做”,到她领到第一笔辛苦钱32块时激动地说“我也能赚钱了”;从她不说一句话只是窘迫地示范编织拼接,到她说出“吓死俺了,俺就没说过这么多话”,再到后来说“咱挣个不是都不发愁买馍的钱了吗,咱挣个不是都不问别人要了,都比别人给咱强”……“说话”次数的增多,体现着桂玲身心的变化,也牵动着作为扶贫干部的王海方的心——当桂玲说出“哪怕一天多挣10块钱,就多买个馍买个菜,就不让国家帮我了,国家还有其他好多事需要花钱哩”,王海芳激动地“不能自已,想落泪”。桂玲整体面貌的改变,映照着王海方的步履维艰,也投射着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的初见成效。
扶贫女干部王海方唤醒了桂玲破解贫困的心劲,脱贫攻坚之路唤醒了王海方愈战愈勇的心力。
初见杜海岗,王海方的心痛的,“他哪怕有些苦难、有些沉重也好”,她用了一个词来形容杜海岗的状态,“自我放弃”。作为女人,她深知,一个好女人对男人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的改造,她想到了为杜海岗这样的光棍汉找结婚对象,然而,何其难也。光棍汉的家庭生活问题,也由此成为女干部王海方的“扶贫心结”。直到村里的扶贫就业创业基地成立,杜海岗在村干部的反复劝说下走上了“工作岗位”,从挑肥拣瘦迟到溜号到严守考勤纪律,从衣衫不整到干净整洁,从说话轻浮到微笑郑重——劳动彻底改善了他的身心,从荒草满院到宽敞平房——“已有不少人开始张罗着给杜海岗介绍对象了”。王海方似乎看到,他的老婆孩子在院中生活的情景。
在整个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强大攻势下,光棍杜海岗贫瘠的心灵被唤醒,此举也一步步解锁着王海方的“扶贫心结”。
为贫困大学生的学业护航,成为每个扶贫干部的心头大事。王海方喜欢在“干活”时带着佳宁,虽然“忙得顾不上跟她溝通利于学业和成长的话语”,但她给了佳宁“在干中学,在干中悟”的最深刻历练;在晓娟一家几度因学费揪心受限时,王海方东奔西走为其呼告,朴素还稍显破旧的院落中晓娟聪慧清气的样子,让她生出几多欣慰;从未谋面的路倚,惊人的勤奋和她身所兼备的向上之力,让王海方“心生怜惜”,她甚至敏感地感受到,路倚电话或微信里的声音,“后半句总是向上扬的”,便也知道,“怎样的贫困都压不垮这样积极向上的声音!”
大学生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村庄,都会被当作单个家庭脱贫的最硬核保障。他们被寄予满满的力量和希望,还有长长的未来——个人的,家族的,村庄的,扶贫干部的,整个国家的。
儿子去世,儿媳智障,一个孙子脑瘫,另一个孙子不会说话,只有一个6岁的孙女正常入校读书——74岁的连卿叔和老伴面临着这样的悲苦人生。可连卿叔却是一个“情绪”老头,整洁,利索,一天三餐喂养,一天三遍清洗,一年年的坚持,很少向乡村干部哭穷。这样的境况,成了王海芳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不知道这个家庭能撑到何时,最终要走向何种境况……”也是在连卿叔的家里,王海芳“彻底理解了什么是老弱病残”——“不再是我写的材料或者向领导汇报的文字和语言,而是连卿叔及如他们一样那部分人的真实写照”。她与连卿叔更高频次地交流与沟通,提振他的信心,同时消解自我的忧虑,甚至,“当地建起福利院,待连卿叔与老伴没有能力去照料抚养家人时,能够被专门人员帮护”成了她唯一的期盼。
某种程度上,连卿叔的境况只是农村的一个缩影,而作为个体的扶贫干部王海方正以沧海一粟的渺茫感力融这样的局面,唤醒着她脚下这片干涸的大地,还有人心。
还有,还有……还有许许多多王海方没有呈现出来的故事,可她已然感受到“与民众朝夕相处的同时,也被民众启迪着,治愈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弱势的体恤,对民众的爱戴,对发展的担当”——融入身心。“纯朴的乡民唤醒了我初心与使命”,这是来自一名基层党员干部内心深处的呐喊。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刻在了王海方的脱贫攻坚的道路上,也必将印在新时代的脱贫攻坚的征途上。(董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