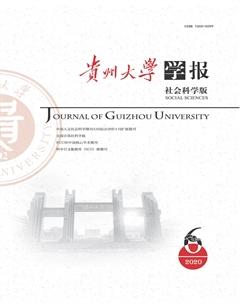关于21世纪东亚研究的几点思考
摘 要:本文旨在探討21世纪东亚研究的必要性、新策略及其所涉及的理论问题。首先指出,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凌之下,20世纪东亚各国知识界丧失了对东亚文化的信心。因此,20世纪东亚学术界思考东亚文化常常采取一种“以西摄东”的思路,以西方经验或理论的最高标准,检核东亚各国之发展,所以导致许多研究论著沦为某种“忠诚度研究”(fidelity study),甚至沦为“折射的东方主义”(reflexive Orientalism),造成20世纪许多东亚研究论著成为不了解“东亚”的“东亚研究”。所以,在21世纪重访东亚,乃成为绝对的必要。其次,提出新时代的东亚研究策略有三:1.研究焦点从东亚文化发展之“结果”转向“过程”;2.兼顾东亚各地文化之“共性”与“殊性”;3.从关键词切入研究东亚思想交流史。接着,再指出上述新研究策略可能触及的理论问题,包括:1.“国家”是否可超越之问题;2.“疆界”之“可移动性”与“可协商性”问题;3.东亚各国民族主义问题。最后指出,中国文化研究在新时代东亚研究中仍居于关键性之地位。本文亦期许,经由新时代的东亚研究,而创造东亚各国人民之一体感,以创造亚洲与世界之和平。
关键词:东亚;忠诚度研究;国家;疆界;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K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0)06-0001-07
Reflections on 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21st Century
HUANG Junji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China,000800)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new strategies and their related theoretical problems in 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21st century. First, the fact is indicated that many East Asian scholars and intellectuals in the 20th century were inclined to take Western experience and theories as the highest models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because the invasion and offense of Western imperialist countries made the intellectuals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in the 20th century lost their confidence in East Asian culture; in this way of thinking, the West became a sort of “Procrustean bed” and East Asian studies were turned into “fidelity studies” or “reflexive Orientalism.” , resulting in “Groundless East Asian studies” . Therefore, we insist that it is a must to revisit East Asia in the 21st century. Moreover, we suggest that the new strategies of research include (a) devot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cess” as opposed to “result”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 (b) visualizing the common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regional cultures in East Asia and, (c) studying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eywords. The research strategies may touch upon some theoretical issues pertaining to the problems of (a) whether “state can be transcended or not,” (b)whether“boundaries” are flexible, negotiable or not, and (c) nationalism in East Asia.This paper concludes by indicating the fact that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in the study of East Asia in the 21st century. Hopefully, with the East Asian study in the new era, people in this region will forest a sense of unity, and the peace of the world and Asia will be achieved.
Key words:
East Asia; fidelity study; state; boundaries; nationalism
本文旨在提出关于东亚研究的若干初步看法,笔者将扣紧以下三个问题展开讨论:第一,为什么在21世纪必须重访东亚社会文化与思想传统? 第二,21世纪东亚人文社会研究有何新策略? 第三,东亚人文社会研究可能触及哪些理论问题? 未来有何研究展望?
一、21世纪重访东亚社会文化传统的必要性
21世纪东亚知识界之所以必须重访东亚文化傳统,虽然有其现阶段国际战略与政经情势的转移等非学术的考量,但是,最重要的学术理由是,20世纪东亚各国饱受西方列强侵略与殖民之凌虐,知识分子丧失了对东亚文化的信心,所以,在国际权力激烈震荡,国际关系舆图换稿的21世纪重访东亚文化,对东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提出一套新解释,乃成为新时代的学术使命。
我们以近代中日两国知识分子为例加以说明。近代日本提倡“文明开化”的精神导师福泽谕吉(1835—1901),他三度游学欧美,著作六十余部,毕生追求近代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民权”“平等”等价值理念。他认为文明的发展有其阶段性,欧洲与美国是文明最进步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则是半开化国家,非洲与澳洲是野蛮国家,所以,日本必须“以西洋文明为目标”[1-3]
福泽谕吉对于当时日本帝国的新殖民地“台湾”所提出的种种论述,充分显示他的帝国主义思想倾向,彻底违背了他作为近代日本启蒙思想家所提倡的各种开明主张。。1921年,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梁漱溟(1893—1988)认为西洋文明善于“运用理智”[4];1926年,胡适(1891—1962)指出西洋近代文明以“求幸福”为人生之目的[5]。这类意见都隐含西洋文明较东方文明优越或先进之看法。从五四以降,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社会政治以及文化问题,随着国族危机日亟而表现出愈来愈激进化的倾向[6][7]178-197。毛泽东(1893—1976)在1940年将尊孔读经的旧思想,与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视为对立之两端,强调“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8]。20世纪,中国的反传统主义者,从五四到“文革”,一步一步走向激进化的道路,这些都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丧失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之一种表现。
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对日本文化信心之沦丧,可以与中国的状况相比拟。19世纪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回国后出任明治时代(1868—1912)首任文部大臣的森有礼(1847—1889),曾提出以英语作为日本国语的主张[9-10]。明六社成员之一、贵族院议员、教育家西村茂树(1828—1902),主张废除汉字与日文而改用英文[11]。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知识分子,在文化与思想取向上,从福泽谕吉所说的“汉学的上半身”,快速地转换为“洋学的下半身”[12]。以上这些中日两国近代知识菁英的言论与主张,都反映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东亚知识分子对东亚文化传统信心的沦丧之一斑。
在上述东亚知识界对东亚文化信心沦丧的思想状态之下,20世纪东亚学者常常采取“以西摄东”的思想进路,以西方文化的价值理念或从西方历史经验中提炼的理论,作为研究者的最高典范或标准,取之以分析东亚文化,检核东亚文化距离西方标准的距离。在这种时代风潮之中,1922年冯友兰(1895—1990)先生关心“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13]的问题,以及1926年傅斯年(1896—1950)先生宣称“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14],就是这种思考倾向的表现。
在20世纪中日学术界,这种类型的研究论著为数众多、指不胜屈。举例言之,20世纪中国哲学大家冯友兰先生撰写《中国哲学史》(旧版)时,就主张所谓的“中国哲学”工作,就是“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15],冯先生的书也是从西方哲学的“新实在论”(Neo ̄realism)立场,阐释中国哲学的发展。20世纪,中国思想史学者侯外庐(1903—1987)先生在1948年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史》,就是以作为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学说的中国版而自豪[16]。
20世纪,日本的汉学大师内藤湖南(1866—1934)提出“唐宋变革说”,以公元第十世纪作为“近世”中国的开始,对日本汉学界与中国史学界影响深远;但是,根据内藤先生笔下的中国迈向“近世”的诸多指标,如贵族政治的式微、君主独裁的出现、相权的低落、人民地位的上升、朋党性质的变化、货币的流通、庶民文学的登场等[17-18],就是以欧洲“近世”历史经验作为参照系统而提出的[19]。战后日本的中国思想史大家岛田虔次(1917—2000)先生受内藤先生启发,在1949年著书指出“中国近代思想的挫折”乃是因为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缺乏强有力的布尔乔亚阶级[20-21],这种说法是以假定近代西欧历史经验是人类历史的普世法则而提出的。
在20世纪东亚知识界,不仅个别学者研究东亚文化与历史,常以西方经验或理论作为最高标准,用以检核并解释东亚的发展,而且20世纪东亚人文社会学界所使用的重要名词或术语,也大多从西方经验中抽离并移植出来解释东亚现象,如“国家”(state)、“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权力”(power)、 “公领域”(public realm)、“私领域”(private realm)等,均出自近代西方历史经验,并随着西方霸权的兴起,而成为东亚人文社会研究的支配性概念。因此,在解释东亚历史与文化的特质时,常常出现不相应,甚至方枘圆凿、扞格难通之问题。1994年,张光直(1931—2001)教授提出“为什么在20世纪的学术研究上,中国对人文社会科学作一般性贡献的潜力完全不能发挥”[22]这个深刻的问题,可以视为面对长期以来西方学术霸权支配东亚学术界之现状,所发出的“东方” 的呐喊。
以上所说的20世纪“西风压倒东风”的东亚学术研究状况,造成至少三个结果。第一,20世纪许多论著常常倾向于以作为“中心”的西方之经验,及其所提炼的理论作为学术典范,检讨作为“边陲”的东亚的发展,而形成某种所谓的“忠诚度研究”(fidelity studies)。这种类型的研究论著,所采取的方法论立场近于“一元论”(Monism),预设人类文明只有单一而直线的发展方向,主张不同文化之间是“从属关系”而不是“并立关系”,在人类文明发展上,西方文明不仅在时间上居于先进之地位,而且在成就上也达到最高之标准。所以,对于非西方文明的研究,最主要的方向就是检核该文明的发展,距离西方文明尚有多远。这一类属于“忠诚度研究”性质的论著,在研究异文化的文化交流时,常常出现许多盲点,其中最重要的盲点就是过度忽视文化交流的接受方实有其主体性这项事实[23]。
第二,这种“以西摄东”的研究论著,预设从西方经验所提炼的价值取向或理论是全球“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从而忽视人类文明的多元多样,也忽视东亚地区的不同文化各有其“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不能完全化约为源起于西方的近代“普世价值”之东方版本。这一项20世纪学术界东亚研究的缺点,已经使西方经验或理论成为古希腊神话中的“普洛克拉斯提之床”(Procrustean bed),使许多研究论著成为了符合西方理论,而不免削足适履、 刻舟求剑,甚至胶柱鼓瑟,其结果则是东亚文化的“分殊”,常在欧洲经验作为“理一”之中被牺牲,所以东亚研究很容易沦为“折射的东方主义”(reflexive Orientalism)。
第三,以上这两种20世纪东亞研究的负面效果,就造成了许多论著成为不了解“东亚”的“东亚研究”。这种现象的形成,可以归因于近代东亚与西方互动的不愉快的历史经验,及其在东亚内部所激发的民族主义的滔天巨浪
孙中山(1866—1925)领导革命时,提倡民族主义,他说:“要救中国,想中国民族永远存在,必须提倡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又说:“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发展和种族国存的宝贝。”(《民族主义》第三讲)参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24]。。20世纪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东亚各国的风狂雨骤的百年,东亚各国人民在抵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时,民族主义极度昂扬,因此,20世纪东亚各国的诸多研究,在民族主义框架之下,成为程度不同的国族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例,20世纪初年,“国史”(nationalhistory)这个概念从日本传入中国,梁启超(1873—1929)、章炳麟(1869—1936)、刘师培(1884—1919)等人批判近代以前中国的朝代史观,而致力于以“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写作[25][7]275-293。20世纪中国史学大师钱穆(1895—1990)先生在抗战时代的1940年撰写了《国史大纲》,致力于以“国史”唤醒国魂,呼吁研读“国史”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26],更是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以历史作为“民族的史诗”(national Epic)的代表性著作[27]。除了中国之外,20世纪日本的史学研究,也是在所谓的“一国史”( いっこくし)的框架之内,跳脱不出国家的视野。日本史学大家远山茂树(1914—2011)就曾说,二战之前的日本的历史研究与教育,是以作为“国家的历程”(くにのあゆみ)而发展的,直到战后“人民的历史”才受到重视[28]。
因为在民族主义思潮之下,20世纪东亚知识界多半聚焦于本国的人文社会研究,所以对东亚邻近国家的经验并不关心,造成对东亚近邻的不了解。 东亚各国之间的互相不了解,更因为“以西摄东”的研究倾向而加强。这种研究倾向就是,东亚各国的历史经验或价值理念中,只有与欧洲经验或价值可类比者或相反者,才能获得东亚学界的重视。凡与欧洲经验或价值无法类比者,就难以进入东亚研究者的视野。这种研究倾向的流弊所及,造成东亚经验在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之中,只能成为作为普世价值或普遍模式的欧洲经验之东亚版本,而东亚文化自身的“内在价值”,就完全被忽略了。正是有鉴于这个东亚研究上的问题,所以余英时(1930—)先生回顾21世纪初年以降国际史学界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时,特别呼吁应重访东亚文化,注重东亚文化作为人类独特经验的“内在价值”[29-30]。
从以上所说20世纪东亚研究常见的三个问题来看,21世纪的东亚人文社会科学界,确实必须重访东亚,以加强东亚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东亚文化不应只是作为欧洲文化的类似品或对立物而被研究,而应是作为“东亚之所以为东亚”而被研究。换言之,新时代的东亚研究者应更聚焦于作为“意义之网”而有厚度的东亚文化之研究,已故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曾说:“人是悬挂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而文化就是那张(意义之)网,……文化研究……就是一种寻求意义的解释性的学问。”[31]作为“意义之网”的东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必涉及中、日、韩、越各国文化与思想的共性与殊性,我们当于东亚各国的文化传统与历史经验之“同”中见其“异”,并于“异”中求其“同”。
二、21世纪东亚研究的新策略
正是有见于20世纪东亚知识界这种不了解东亚的“东亚研究”的状况及其弊病,1994年沟口雄三(1932—2010)、滨下武志(1943—)、平石直昭(1945—)、宫嶋博史(1948—)等人就呼吁提出:“从东亚出发思考。”[32]21世纪“从东亚出发思考”之下的新“东亚研究”之性质,必然是跨文化的、跨国的、跨域的、跨界的、多音的、多元的研究。
这种“从东亚出发思考”的“东亚研究”之研究策略可得而言者,至少有以下三项:
第一,研究焦点从“作为结果的东亚”,转向“作为过程的东亚”[33-34]:过去有关东亚思想的研究论著,虽然研究进路多元多样,但是,整体而言比较倾向聚焦于东亚思想发展的结果,而较少从东亚思想发展的过程来观察。因为重视“结果”远过于“过程”,所以,过去许多东亚思想研究论著,常常聚焦于东亚思想静态的完成态,隐约之间呈现某种“一元论”的方法论倾向。我们如果能将眼光从“结果”移向“过程”,我们就会更注意东亚思想形成与发展中的动态变化,也更能够顾及东亚各地域的文化主体性形成的过程,使过去单色的东亚文化图像,变成色彩缤纷的文化图像。
第二,兼顾东亚各地文化与思想的共性与特殊性:过去的研究成果较为重视的是东亚各地(如中、日、韩)文化的共同要素,正如1969年西嶋定生 (1919—1998)先生所说的东亚世界共有的四大指标:汉字文化、儒家、律令制度、佛教[35]。沟口雄三等人也强调东亚各国的“共同知”(きようとうち)[32]。这样的研究视野,自然是很有创意的,而且充满了悲天悯人的胸襟,因为这样的研究可以在东亚各地文化之间求同存异、有助于建构“东亚文化共同体”,以促进21世纪东亚各国之间的和平。这样的研究也比二战期间津田左右吉(1873—1961)的视野更为宽广。津田先生否定作为整体的东洋世界的“东洋文化”或“东洋文明”这种名词[36]195,但他特别强调中国与日本在家庭制度、社会组织、政治形态、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差异[36]302-303。
然而,笔者想进一步指出的是:我们今日重访东亚,在强调东亚各地文化的“同”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过度忽略各地文化之间的“异”,以致再落入“中心与边陲”或“起源与发展”的旧研究窠臼,成为另类的“忠诚度研究”。自从17世纪后,东亚世界中的日本、朝鲜与越南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在东亚各国之间的交流活动中,所出现的紧张关系也值得注意[37-38]。我们的东亚研究必须既求其“同”,又观其“异”,既求其“一”,又观其“多”,才能举“总”以该“别”,由“别”以见“总”,而不流于一曲之见。
第三,从关键词切入分析思想交流中诠释典范的转移:在东亚思想交流史中,出现许多次的思想典范的转移,如从汉唐时代的声训典范,向北宋以后的字义典范的转移;从“理”学向“心”学的转移,再向“气”学的转移等。这些典范的转移虽然源起于中国,但都波及日本与朝鮮,成为东亚的共同现象。在思想典范转移、旋乾转坤之际,中日韩思想家常采取从“部分”论“全体”之策略,尤其是从各种经典的关键字词,如“道”“仁”“礼”等入手,出新解于陈篇;或申“正”以破“邪”,在破斥“异端”中重建“正统”[39]。因此,在我们的东亚研究中,从关键字词切入,从点滴以观潮流,确实是一个可行的策略。
三、东亚研究中的理论问题举隅
21世纪的东亚研究,强调跨域的视野,必然会触及许多具有理论意趣的问题,兹举其荦荦如下:
首先是“国家”问题。在跨域的东亚交流活动中,“国家”(state)是否可以被超越?这个问题涉及两个层次:第一,东亚各国知识分子,既是各国忠诚的公民,又是东亚普遍价值理念(如“仁”“义”“忠”“孝”)的信奉者。作为各国的公民,“国家”意识在东亚文化交流活动中,很难被超越。17世纪,日本儒者山崎闇斋(1619—1682)对学生提出,如果孔孟率兵攻击日本,则“吾党学孔孟之道者为之如何”[40]这个问题时,已将知识分子的“国家”认同问题完全彰显无疑;但是,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价值的信持者,各国的知识分子胸怀天下,关心人类前途,是可以有超越“国家”的交流与互动的。 第二,所谓“国家”这个概念随着近代欧洲“民族国家”(nationalstate)而兴起,在近代欧洲政治思想中,“国家”这个概念在洛克(John Locke,1632—1704)、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政治哲学中,常常被当作一个空间来思考,但是在中国政治思想中,“天下”这个概念则是“文化认同”的意涵,远大于“政治认同”的意涵。17世纪,顾炎武(1613—1682)所提出的“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41],主要是在“文化认同”的意义上说的。相对于传统中国的“天下”概念,“国家”这个概念是西欧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后的概念,两者并不等同。 抗战时期的1943年,罗梦册(1906—1991)在陪都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演讲后所出版的《中国论》一书,就特别强调这一项事实[42]
Martin Jacques主张应将21世纪的中国视为“文明国家”而不是近代以来西方的“主权国家”,参见Martin Jacques的《当中国统治世界》[43]。。因此,东亚研究中所触及的“国家”这个概念,实有其具有东亚特色的理论内涵,值得深入探索。
其次是“疆界”问题。东亚交流史上所见的“边界”或日语所谓的“境界”(きょうかい)的“可移动性”(fluidity)、“可合作性”(negotiability)及其再固定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深具理论意趣。
笔者在这里所谓的“疆界”,既指东亚各国之间政治的疆界,如日本史上的遣唐使、朝鲜与越南历史上的燕行使,都是跨越政治的国界,而进行交流活动;也指东亚各国之间文化思想的疆界,如各国儒者、和尚往来于国境,进行文化思想的交流。不论是刚硬的政治疆界,或是柔软的文化思想疆界,都高度依赖各种“中介人物”,如外交官、翻译官、商人、儒者、和尚、旅行者,甚至两国战争期间的将军与士兵之交流折冲于其间。“中介人物”的角色及其作用特别值得研究,因为外来文化或思想,在广传本国之前,必经“中介人物”之筛选、简择,甚至重组并赋予新诠,才能“风土化”而融入本国文化之中。“中介人物”正是东亚文化交流中,使“疆界”产生位移的关键人物。
最后是“民族主义”问题。东亚交流活动包括软性的文化思想交流与硬性的作为另类交流活动的军事行动,都必然触及各国“民族主义”的特质及其类型之问题。19世纪中叶以后,东亚各国共同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与殖民,但是在20世纪上半世纪的中国、韩国及东南亚国家,又历经新兴的日本帝国之侵凌,所以各国民族主义极为昂扬。对18世纪以后东亚各国“民族主义”的建构与发展进行深入挖掘,也许可以提出与西方历史经验所见的民族主义[44]不同的理论内涵。
四、结论
在21世纪世界政经情势快速变迁的时代背景中,东亚人文社会研究的重要性与日俱增。20世纪东亚知识界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之下,对东亚文化的信心沦丧殆尽。所以,20世纪的东亚研究终不能免于成为不了解东亚的东亚研究。为了矫正这种状况,本文第一部分指出21世纪的东亚知识界实有重访东亚的必要;第二部分建议新时代东亚研究的三项策略,包括研究焦点从“结果”移向“过程”,兼顾东亚各地文化的“共性”与“殊性”,以及从文化或思想的关键字词切入分析等;第三部分也提出跨域的东亚研究,可能触及的理论问题,包括“国家”能否被超越的问题,“疆界”的“可协商性”与“可移动性”问题,以及东亚各国的民族主义问题等。
[19]MIYAKAWA H.An Outline of the Naito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J].Far Easter Quarterly,1955, XIV(4):533-552.
[20]島田虔次.中国现代思维的挫折(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M].东京:筑摩书店,1949.
[21]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M].甘万萍,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22]张光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该跻身世界主流[J].亚洲周刊,1994,8(27):64.
[23]黄俊杰.东亚近世思想交流中概念的类型及其移动[M]//思想史视野中的东亚.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1-22.
[24]孙中山.民族主义[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5,28.
[25]Y Y S.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M]//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Proceedings of Nobel Symposium 78.Erik Lnnroch et al. eds.,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4:155-174.
[26]钱穆.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信念[M]//国史大纲.修订3版.台北:商务印书馆,1996:1.
[27]黄俊杰.钱穆史学中的“国史”观与儒家思想[M]//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4:223-268.
[28]远山茂树.战后历史研究与历史意识(戦後の歴史学と歴史意識)[M].东京:岩波书店,1968.
[29]Y Y S. Clios New Cultural Turn and the Rediscovery of Tradition in Asia[M]//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Seventeenth Century Through Twentieth Century .vol. 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368-384.
[30]余英时.历史学的新文化转向与亚洲传统的再发现[M]//人文与理性的中国.程嫩生,罗群,等,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619-641.
[31]GEERTZ C.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M].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3:5.
[32]沟口雄三,滨下武志,等. 从亚洲出发思考(アジアから考える):全七卷[C].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4.
[33]黄俊杰.作为区域史的东亚文化交流史:问题意识与研究主题[M]//东亚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经典与理念:互动、转化与融合:第一章.修订一版.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3-38.
[34]HUANG C C.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East Asia[M]//East Asian Confucianisms: Texts in Contexts.Gttingen and Taipei: V&R Unipress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5:237-259.
[35]西嶋定生.总说[M]//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四册:古代4.东京:岩波书店,1969—1980:5.
[36]津田左右吉.支那思想与日本(シナ思想と日本)[M]//津田左右吉全集:第二十卷.东京:岩波书店,1965.
[37]葛兆光.地虽近而心渐远──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朝鲜和日本[J].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06,3(1):275-292.
[38]葛兆光.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第五章[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145-158.
[39]HENDERSON J B.The Construction of Orthodoxy and Heresy: Neo ̄Confucian, Islamic, Jewish and Early Christian Patterns[M].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40]原念斋.先哲丛谈[J].庆元堂、拥万堂,1816,文化13(3):4-5.
[41]顾炎武.原抄本日知录:卷十七[M].台北:明伦出版社,1970:379.
[42]罗梦册.中国论[M].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
[43]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M].李隆生,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12.
[44]SMITH A D. Nationalism: Theory, Ideology, History [M].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0: 60-63.
[45]TIMOTHY J.“Literary Sinitic” and “Latin” as Transregional Languages: with Implications for Terminology Regarding “Kanbun” [J].Sino ̄Platonic Papers,2018(276):1-14.
[46]子安宣邦.汉字论:不可避免的他者(漢字論:不可避の他者)[M].东京:岩波书店,2003.
[47]内藤湖南.支那上古史[M]//内藤湖南全集.东京:筑摩书房,1944:9.
[48]宇野哲人.支那文明记[M].东京:大同馆,1912.
[49]小岛晋治.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M].东京:木摩书房,1997.
[50]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M].张学锋,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182.
[51]西嶋定生.东亚世界的形成[M]//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引文.北京:中华书局,1993:89.
[52]QIAN N X,SMITH R J,ZHANG B W.Rethinking the Sinosphere: Poetics, Aesthetics and Identity Formation: Introducaiton [M].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20.
[53]LIM H T.Sinocentrism in East Asia and the Task of Overcoming It[J]. Sungkyu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08,8(1):71-87.
[54]OKAKURA K .The Ideals of the East: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Hiroshi Muraoka[M].London: John Murray, 1903; Tokyo: Kenkyusha, 1931.
[55]岡仓天心.东洋的理想:特别是关于美术(東洋の理想:特に日本美術について)[M].富原芳彰,译.东京:鹈鹕社,1980.
[56]孙中山.大亚洲主义[C]//国父全集.台北:“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5:306-312.
[57]黄俊杰.孙中山思想及其21世纪的新意义与新启示[M]//思想史视野中的东亚:第九章.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179-202.
(责任编辑:张 娅)
收稿日期:2020-09-20
作者简介:
黄俊杰,台湾高雄人,博士,台湾大学特聘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学术咨询委员,欧洲研究院院士。研究方向:东亚儒学、通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