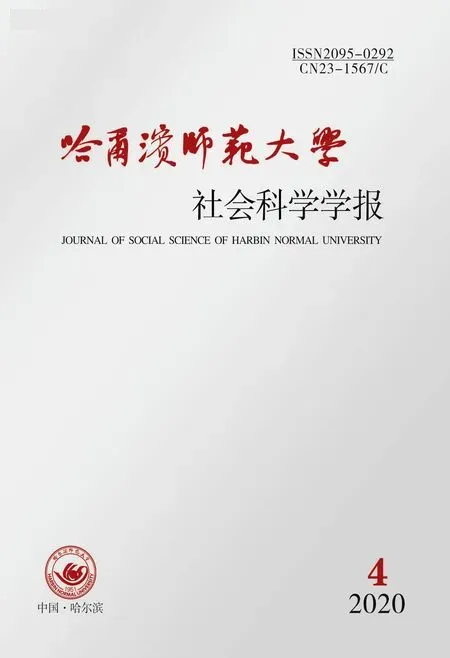价值、实践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属性
苏泽宇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人们通过概念理论对事物属性进行本质规定性的识别与区分,进而把握事物的质[1](P257)。民族意识是个体或群体与民族整体发生作用与互动调试的过程中,经过有意或无意地参照对比,生成自我与他者、个体与民族同一性与类特征的识别、肯定、效仿,并在情感与态度上产生主观亲和的感情与彼此承认、理解、支持、赞同、甚至归属的过程。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指中华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归属与价值体认,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自觉。作为文化价值的内化机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其本质上具备共同体政治中个体与群体、民族与国家相统一的价值属性,彰显民族国家发展独具价值特质,凝聚价值共识、推进物质性转化的实践属性以及认同层级演进与深化的发展属性。价值属性、实践属性、发展属性等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属性。
一、 利益关系调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属性
价值是人们对客体属性的具体评价和主观应用,是人的需要与满足这种需要的客体属性在特定方面的交汇点[2](P124-125)价值具有双重性,表现为功用价值和内在价值的统一。在功用维度上,价值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客体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用关系,它以真善美为最高境界。价值范畴“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3](P406),是客体功能属性符合主体需求,并促进主体朝着积极方向发展的作用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个现代性命题的提出与强调,积淀民族交融,交流与交锋的价值对接,并不在于民族成员相承的内容属于过去,而在于文化的持续与认同的发展对未来的研判,在于民族共同体历史与现实之维的交感与承担,在于现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国与国之间民族竞争的本质与蕴含,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属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命题的提出与强调,是对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多民族国家正反两面治理经验的总结与概括,阐述和创建能最大限度地容纳和协调民族成员个体与群体利益、充分显示共同体内部政治人格平等的国家结构和理论体系,为民族政治理论的发展和民族治理理念的更新创设实践的语境和现实的情境。对于民族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将引导和激发民族共同体更多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创新,促进共同体内部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双向衔接。共同体政治和谐与文化认同休戚与共。认同基础上的求同,强调的是各民族群体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度联结,达致民族内部利益关系的协调一致,深化民族内部群体间的密切交往交流交融以及民族整体意志的体化实践;认同基础上的存异,强调的是各民族群体独具特色的历史传承和政治承认,展示的是各民族群体规范、文化、权利和目标的充分理解和普遍尊重。求同存异基础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但能保证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权利、机会均等的发展空间以及积极而广泛的政治参与,而且使得民族国家整体的价值意识在理性认识和发展融合中进行有机联结与整合,转化为政治资源后,对民族成员个体和群体行为加以协调,促进民族国家政治的稳定,进而为民族关系的和睦与共生,奠定自然同化的文化支撑和心理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命题的提出与强调,为多民族国家的利益调适与利益求解诠释了新的路径与方法,通过共同体意识整合利益关系,发展和完善多民族国家的利益共享机制。共同体支撑的核心要素与共同体成员对所属文化主体精神的认可,是利益调适达成共识的基点。共同体意识承载着社会行为的意义与价值,是个体社会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民族成员的共同体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掌控其对民族国家政治合法性基础、民族利益的认识与理解。只有经过认同筛选的利益诉求和关系形式,才能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推崇和主张。竞争与分配、协作与共享的利益调试机制在反复出现的民族问题中得以成熟,在族群间接触、互动、适应与融合的实践中得以规范,在共商、共建、共享的交往思考中得到深入。在复合型民族国家的利益调试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但影响和规定了民族国家利益调适的路径、方向和旨归,而且影响和规定了各民族群体在国家利益体系中的权限、范围、行为与空间。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用于民族成员对利益标准及其关系的基本认识,通过主观亲和、规则规范以及方向目标的建构,使民族成员对思想、行为的功效、意义、价值认知得到转化、引导和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的利益整合,不仅兼顾利益诉求的多样性,使其可实现的真实性得到保障,还将这种多样性纳入共同体主导性利益体系的框架中加以协同。无论是群体与个体的利益还是大群体与小群体的主张,无论是民族国家的整体意志还是个体成员的思想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推进的利益调适均有所判断、有所要求,通过利益的本质性共有、凝练和提升,使社会个体感受民族、国家和个人的休戚与共,激发他们的情感、意志和社会责任感,锻造民族群体的理想与信念,最终达到利益的协调和行为的一致。在利益调适过程中,共同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把千差万别的利益追求整合为统一的价值要求和利益共识,取决于民族文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总结和提炼各种利益诉求背后的共同意志与基本精神。通过认同,聚集在民族精神的旗帜下,将有力地促进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力的平行四边形”,聚合共同体成员休戚与共的价值共识,生成统一而持久的合力效应,进而达成利益的互补和共赢。
二、 共识凝聚外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属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援引共同体文化一脉相承的价值基因,是民族成员思维习惯和思维规律的外显和表现,其实践属性指涉民族成员对民族文化内核中所蕴含的群体价值推崇与族群发展应然向度的现实体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于群体互动交往的社会实践场域中,通过揭示、阐发和肯定民族成员的特定身份,为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自觉提供价值定向的精神引领;通过认同的观念聚合和情感归属强化各族群具有同一性的价值共识,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整合与动员功能,为中华民族发展提供价值共识与精神动力。精神引领、价值整合、动力凝聚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认识形态向实践形态、由观念形态向物质形态的转化的实践属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多民族国家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固基奠定坚实的心理基础,通过文化成员认同心理的价值整合与区分,生成群体聚合的同类价值共识,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功能,为国族发展提供价值共识与精神动力。认同与多民族国家的群体凝聚具有某种必然联系,其中,价值共识扮演了十分重要价值整合的角色。价值共识是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前提,是共同体成员生成情感亲和、沟通协商、良性互动的重要媒介,是分散的民族族体和民族成员走向亲和与共识的桥梁。作为特定人群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存体现,民族文化同组成社会基本单元的民族和它的特质相关,与民族相差异的组织结构和社会变迁相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达成的价值共识成为民族国家凝聚和社会整合的心理基础,不但决定着复合型民族国家有机团结的广度和深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民族国家整体建构的方式与方法。
同类价值意识对民族社会关系的强调与整合,着眼于共同体成员对民族文化的认同,立足于民族成员对所属文化体系的认可、归属与习得。在纵向维度,是对文化传统与现代连续性与稳定性的认同;在横向维度,表现在空间的向度,主要是地域文化对主体文化的融汇。事实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各个文化分支无序堆积的产物,而是经由共同体文化体系判断与筛选、排斥与吸引而积淀的结果。同类价值意识对共同体文化的映照,在历史的沧桑中得以真正保留和传承,往往得益于文化分支中那些与整体情感、规范和目标相融合的价值要求和思想倾向;各具风格和特色的文化分支之所以能够聚合为有机的整体,总是得益于民族文化基本理念所充当的价值坐标和选择、积累的作用机理。
民族文化通过价值共识以其特有的运行机制影响社会成员的心理定式和价值判断、协调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和利益旨归,是民族成员精神动力形成的重要路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形成的价值共识,以民族共同体的行为准则为介体,影响和制约了民族群体凝聚的方法、层次与结构。回顾历史,民族之所以是民族,不但具备了特定的遗传基因,而且具备了特定的文化内核。价值体系经过共同体成员社会文化的体验与习得而得以遗传和继承,生成个体成员独具民族特质的心理意识、情感方式和思维形式,并在社会教化与规约中成为个体成员稳定的价值观念和心理素质,潜移默化地积淀为民族凝聚的深层动机与力量源泉。尽管在通常情形下,民族成员可以推崇多种不同的价值观、选择多种不同的行为方式,然而,无论是推崇还是选择,归根结底要与特定的民族文化相结合,与民族成员俗定成规的心理定式相一致。认同民族文化,就是要承认民族文化的情感、规范和目标,这就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生成提供了某种程度的现实可能。
一种共识的观点指出,文化承载着一个民族所获成果对自身价值与需求的强调。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同类价值意识对民族凝聚的促进,表现的是共同体成员主观能动性的把握与创造,它支撑着民族个体心灵的慰藉和民族凝聚功能的延伸,维系着民族国家的历史和进步。受此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着个体成员最基本的人格要素,生成个体成员之于群体的最根本的关系形态。有鉴于共同体成员的思想和欲望、要求和动机、对事物的选择和判断,无不受制于同类价值意识的影响,“一个人除非对供他选择的种种生活方向有所了解,否则,他不可能理智地委身于一种生活方式”[4](P6)。这种了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是民族自尊与自信的保证,同时也是民族凝聚的依托。民族文化诠释的信仰和支柱容纳的是共同体推崇的情感、知识、意志和思想,“是一整个阶级、一整个人民集体、一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断”[5](P103-104)。这个判断过程中,民族文化的同类价值意识,充当了连接民族成员思想和意愿的黏合剂,形成了社会凝聚和民众向心力的着眼点。对共同体内部各民族群体和个体成员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功能的发挥,与其说是外在强制力作用的结果,不如说是民族成员自觉自愿的心志和行动。
三、认同层次演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属性
文化认知、文化态度、事实行为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演进的外围—中心结构。文化认同的发展演进源于外围彼此开放的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既相互依存、交互影响,又彼此独立、各有侧重,型构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演进的逻辑框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选择与判定、归属与排斥、观念与行为与自然认同、强化认同和理解认同的层次链接具有重要的联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包含的认同系统整体保持着由自然认同、强化认同再到理解认同的上升趋势与发展脉络。
民族文化认知包含符号系统认知、情节系统认知和价值系统认知,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态度和事实行为转化的基础和起点,也直接限制着认同主体自身价值观念的成熟度与认同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于符号系统的传播与认知。符号认知是文化态度、价值内核理解、事实行为转化的基础和起点,符号认知与情节体验的欠缺直接限制价值观结构的完善与意义感的提升,使认同停留在较低层次且不具有稳定性与抗扰性,难以达到“价值理解”“外化行为”的高度。情节系统认知生成客体的文化态度。文化态度是连接认知、投射现实与指向行为的中间环节,是归属感生成与意义提升的关键,不仅能够激发文化认知的主观愿望,还介入情境构造着行为转化的蓝图。价值系统认知是对民族共同体文化价值的抽象、文化意义的凝练和总括,最终所要实现的是民族成员态度、归属与行为的对象性意旨。价值内核的理解与共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想状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是价值认同。
民族成员对所属文化的态度是民族文化认知的表现,它指向了民族成员族属身份的评价与判定,指向了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族体认同的一部分,指向了民族成员对所属文化的归属感,指向了效忠、责任与义务相结合的情感与意志。从认知的角度研判价值最终所形成的态度,所要强调的是认同主体对所属文化的情感与价值于文化关系内部的判断和反映。换言之,人们关于客体价值的判断和反映是现实价值关系的精神表现形式,具体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伴随的认知态度,则更多地指向了认识主体的兴趣、情感和判定,代表着民族成员个体在结构、目标、能力等客观需要面前的自我存在与自我反映。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事实行为,是民族文化认知与态度的外化终端。作为认同循环过程中的阶段性节点,事实行为的选择、生成与评判检验着认知主体的价值观念与认知态度并形成反作用。在现实生活中,作为民族共同体实践活动的产物,民族文化的事实行为是由主观的、潜在的文化心理、态度外化为现实的体化实践,是文化价值接受、体认、认同与社会实践的贯通与统一,是检验和评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程度的客观依据。它所反映的主客体关系历史地凝聚了认知、情感、意志、信念向行为转化的要素互动和结构统一。如此看来,事实行为的逻辑论证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检验不但是民族文化客观对象的主观反映,而且是人们据此对能力、竞争、事物和主观现象进行文化思考和文化研判的依据,是民族成员思维能力转化为行为动机的重要体现。
层次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种规定性的对立和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一种身份认同意识,内涵一个由自然认同到强化认同,最终进入理解认同的认同系统。这一逐层演进的认同系统用不同的视角诠释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层次等级和发展属性。每一层次的认同总是抽象着交互关系中的具体,奠定着高一层次提升的基础。自然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第一层次,是个体成员在原生环境中自发形成的情感归属和文化适应,在共同体生存模式和文化体系中得以累积和固化。作为民族存在的文化场景,自然认同以民族成员的社会性和民族氛围的内部养成为据,在意识层面上导引民族意义的现实传承,当个体成员通过遗传和模仿养成共同规范时,文化的烙印于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深入和展现。主体需要和群体生活是民族成员自然认同的两大条件。从作用机理来看,主体需要构成了自然认同的内在之源和范式外现;就联系的主体特征和外部表象而言,群体生活构成了自然认同的内在适应和外部环境。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层次,自然认同将民族生活中的约定俗成转化为个体成员赞同和接受的方式与定式,成为“理所当然”的民众心理。
强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第二层次。当文化烙印自然沉积之后,共同体需要对其成员进行认同的诱导和强制,进一步固化个体成员的社会化内涵和文化表征。作为思想层面的承认、认可和赞同,个体成员主观意识和客观体验的可塑性为共同体文化认同提供了教育和强制的可能。从有目的的教育开始,强化认同通过教育、规约、引导、惩治等方式不断激活认同的现实语境和场域,提供认同影响和实施的渠道、媒质、舆论与秩序,使共同体信息和资源的传导告知在民族成员的行为举止中。利益关联和政治权威是强化认同的两大要素。从外在表象来看,强化认同联系着个体成员利益的具体表现和民族忠诚度的政治认可;从作用机理来讲,强化认同直接关联民族成员对利益关系的认知以及共同体政治权威的效忠。在强化认同的社会实践中,把利益关联作为教化和强制的切入点,对民族成员展开主导价值观念的培育以及共同体利益共识的引导,强化共同体政治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力和威慑力,是强化认同得以实施的重要保证。
理解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第三层次。主体间性与文化间性构成了文化成员理解认同的二大特性。从外在表象来看,理解联系着民族成员的感觉与特征;从作用机理来看,理解关乎民族成员内在的本质与精神。作为对话和交流的主要方式,理解的主体间性,并不拘泥于“缘在”的感知对象——“它”,而是将“它”转化为“你”,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我”“你”之间的相遇和对话。伽达默尔分析认为,“理解一个问题,就是对这问题提出问题(Eine Frage verstehen heisst,sie fragen)。理解一个意见,就是把它理解为对某个问题的问答(Eine Meinung verstehen heisst,sie als Antwort auf eine Frage verstehen)”[6](P482)。作为文化认同的最高层次,理解认同是在自然认同和强化认同基础上,通过对话交流,达成民族成员对文化价值内涵的理解——其本质在于视域融合,实现民族成员对文化价值内涵的历史视域和现实视域、个体视域和群体视域的融合,是民族成员对中华文化价值内涵皈依的理性认同。价值认同的外化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7](P286)。在现实性上,中华文化的视域融合,是中华文化价值内涵“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普遍理解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