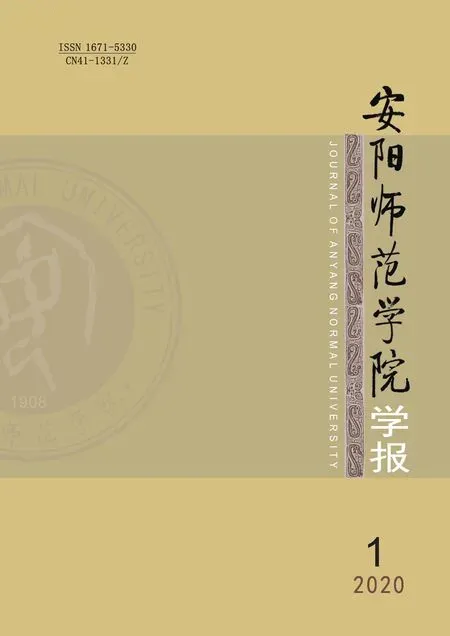刘庆邦小说《神木》的空间批评解读
严雪明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20世纪后半叶,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长期以来以时间为中心的历史决定论受到质疑,空间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74年列斐伏尔发表《空间的生产》,标志着西方思想界开始经历一场“空间转向”,各种空间理论也应运而生。这一思潮迅速波及到文学研究领域,美国文化理论家瓦格纳将这种空间与文化理论相结合所产生的批评模式称作“空间批评”(spatial criticism)。空间批评自诞生以来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列斐伏尔、福柯为代表的理论家主要关注空间的社会属性;到了九十年代,迈克·克朗、瓦格纳等学者开始转向空间的文化研究;近年来,詹姆逊的超空间理论、爱德华·索雅的“第三空间”理论从后现代的视角阐释了空间的属性。空间批评传入中国以后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出现了许多运用空间批评理论对作家创作和文学作品进行解读文章。
《神木》是刘庆邦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以煤矿为主要背景,讲述了发生在底层打工者之间的一个骇人听闻故事。小说的两个主人以挖煤挣钱为幌子诱骗陌生人,带他们到煤矿打工,然后在窑底将人杀死,再冒充死者亲属,从窑主那里领取赔偿金。在这个故事里,作者描写了不同的地理空间,火车站、小饭店、煤窑、乡村等。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指出“空间并非静止的容器或平台,也不是一个消极无为的地理环境。”[1]空间本身是一种强大的社会生产模式、一种知识行为,即所谓的“空间是一种生产”,小说中出现的每一种空间都有其潜在的意义和指向。本文运用空间批评理论对《神木》中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进行分析,同时展现其以时间为线索的线性结构下隐藏的空间叙事模式,以求更加深入地把握小说的主题和作家的创作特点。
一、 不同物理空间中人性的多重表现
物理空间即列斐伏尔所说的感知的、物质的空间,它是文本中故事发生的平台,是小说中人物活动的场所,同时也具有深刻的文化指向意义。它是人物情感世界的外在表现,也激发出人物不同的内心诉求。
《神木》中的主要地点有三个,分别是火车站、老家和小煤窑。故事的开头是化名唐朝阳和宋金明的两个民工在火车站物色“点子”,“点子”是他们的行话,就是指合适的活人,他们将点子带到小煤窑害死,然后以亲人之名,拿人命和窑主换钱。火车站在小说中一共出现两次,随火车站同时出现的还有旁边的敞篷小饭店,在这里他们人性中贪婪的部分被激发同时也被压抑,他们眼睛里露出凶残的光芒,心理盘算着歹毒的计划,但因为是公共场所,又必须装出伪善的嘴脸。在关于火车站的描写中多次出现猎人与猎物的比喻,“他们的心思不在酒上,而在广场前那些两条腿的动物上。两人漫不经心地呷着白酒。嘴里有味无味地咀嚼着四条腿动物的杂碎,四只眼睛透过三面开口的敞篷,不住地向人群中睃寻。”[2](P4)“他们坐在小饭店里不动,如同狩猎的人在暗处潜伏,等候猎取对象的出现。”[2](P5)“钓人和钓鱼的情形有相似的地方,你把钓饵上好了,投放了,就要稳坐钓鱼台,耐心等待,目标自会慢慢上钩。”[2](P11)“唐朝阳已经习惯了从办的角度审视他的点子,这好比屠夫习惯一见到屠杀对象就考虑从哪里下到一样。”[2](P15)在他们的眼中,两条腿的人和四条腿的动物没有区别,他们寻找目标就像捕猎和钓鱼一样,人来人往的火车站就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猎场,小饭店是他们的大本营。在火车站这个陌生的公共空间内,人的自私本质暴露无遗,但同时又要遵守必要的规则,这是一个冰冷的世界,这个世界里人也变成了冷漠的机器。
小说中出现的第二个空间是小煤窑,小煤窑也出现了两次,两个煤窑的位置作者并没有交待,读者也很难从文本中推测出小煤窑所在的地方,这似乎是一个远离正常社会和人性,毫无规则和法律可言的世界。在暗无天日的窑底,人的兽性显露出来,周围漆黑一团,是“天然的杀人场所”,因为远离地面上的社会秩序,他们在这里无论做什么都无人知晓,可以轻松逃避法律的制裁,甚至逃避自己良心的谴责。作者借高中生王风(化名)的眼睛向读者暴露了窑底的可怕,“铁罐像是朝无底的噩梦里坠去......”“这个世界跟窑上的人世完全不同,仿佛是一个充满黑暗的鬼魅的世界。”[2](P84)如果说在火车站人性还遵守着最基本的底线,还会用谎言和伪善做装饰,那么小煤窑则是一个血腥的动物世界,理性和善良荡然无存,只剩下利益和杀戮。
《神木》的发人深省之处在于作者描写了火车站和小煤窑之外的第三个物理空间,即杀人凶手之一赵上河(宋金明的真名)的家乡。小说中对于赵上河回家之后情景的描写只有短短的一章,过年回家的赵上河与火车站外精明的“猎人”、小煤窑里凶残的杀人犯判若两人。回到村子里的赵上河是一个谦和的乡邻、慈爱的父亲、能干的丈夫、仗义的兄弟。见到村民他客气的让烟,给妻子儿女精心准备礼物,毫不犹豫的借钱给交不起学费的邻居,这时的他又恢复了真诚本分的农民本色。在家乡这样一个亲切熟悉的空间里,他人性中的善良被亲情召回,他开始感到心虚和恐惧,以至于在过年的时候长久地跪在老天爷面前忏悔,决定金盆洗手,过踏实日子。然而金钱的诱惑使他再次踏上了那条邪恶的不归路,他又出现在火车站,又来到了小煤窑,如此形成一个循环,三个空间的来回切换,展现了人性的正邪复杂性和主人公在善与恶之间的灵魂挣扎。
二、 社会空间的一种属性认识:“空间是一个权力容器或场所”
所谓社会空间就是空间的社会属性,是文学作品中各种人物之间组成的复杂的关系,它体现为不同群体中约定俗成的规则和秩序、人物的行为方式、阶级的划分、压迫与反抗等。列斐伏尔指出,空间“不是物质中的一种物质,也不是多种产品中的一种产品,它囊括所有被生产出来的事物,并包含有这些事物间相互依存、相互并置的关系。”[3]
《神木》中的社会是一个纷繁复杂、层叠交错的空间,这里不同的群体有各自的生存法则,形成一个个各不相同又相互交叉的世界。乡村世界、打工者的世界、红灯区的世界都有自己的秩序,就连小说主人公所做的血腥的杀人“行业”都有自己的“操守”。《神木》的开头部分有一段关于蛇皮袋子的描写,宋金明就是通过元清平背的蛇皮袋子断定他是从乡下出来的打工者,虽然没有人规定,但蛇皮袋子似乎是打工者的一个标志,是他们这个群体的一种默契,是打工者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在社会的底层除了打工者的世界,还有许多所谓的“红灯区”,小饭店、洗头房、按摩房,这些地方都是暗娼的生意场,在这里又别有一套规则,平日里受压榨的打工者成为上帝,他们满口污言秽语,女性成为他们花钱发泄欲望的对象,而这些靠出卖肉体为生的女性也丝毫不觉得难为情,她们大方的讨价还价,毫不客气的和来往的客人打情骂俏,在这个世界里性交易和别的商品交易没有什么两样。与城镇相比,乡村世界还较多的保留着原始淳朴的风貌,乡村秩序靠传统的礼教维持,无论在外面的社会做了什么,回到家乡之后还是要遵守父慈子孝、邻里和睦的风习。小说中所写的这个算不上行业的行业也有自己的规矩,“他们不要老板,不要干部模样的人,也不要女人,只要那些外出打工的乡下人。”[2](P5)还有所谓的“兔子不吃窝边草”,他们绝不会对熟人下手。由于所做都是见不得光的事,他们忌讳“死”“杀人”之类的字眼,于是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行话,“点子”“办掉”“钓鱼”“做活儿”等暗语是行业内部的沟通方式。《神木》虽然人物不多、情节简单,但它所展现的社会空间的复杂性应该引起关注。
福柯强调空间中的权力关系,认为:“空间是一个权力容器或场所,他指出在权力社会中,每个人都生存在一个巨大的、封闭的、复杂的等级结构中,人们因此而长时间地被操纵和监督。”[4]《神木》中权利空间的建构主要体现在乡村中的基层政治权力和小煤窑剥削制度下的压迫与反压迫。在中国,乡村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受集权政治制度的管辖,同时也是一个受口头和道德约束的非正式组织,在这个组织里,权力更接近于一种权威,它不具有强制性和压迫性,但却比一般的权力关系更易于被群体接受和认同。赵上河在回到村子里以后思想和行为立刻发生了变化,他谦逊低调、忠厚有礼,这种变化不光是因为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并极力忏悔和伪装;更因为乡村这样一个空间里拥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它迫使人们回归本土。过年时赵上河主动带着礼物去看望村支书,村支书相信村子里的人走再远也走不出他的手掌心,这体现了乡村权力的弹性和约束力。我们的目光转移到小煤窑,这里是不同于乡村的另一个权力空间。小煤窑上一直存在着阶级对立和压迫,这些私人煤窑实际上是早期资本主义的雏形。作为资产阶级的窑主残忍地榨取矿工们的剩余价值,而矿工们只能靠高强度高危险性的体力劳动获得微薄的收入。小说的主人公走上这条不归路也一定程度上是对窑主的反抗,他们对窑主的压榨极为不满,“对于每个装腔作势的窑主,他们都从心里发出讥笑。”[2](P22)想通过这种方式敲窑主一笔。但即便在“事故”发生之后,双方为赔偿金谈判时,窑主依然掌握主动权,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依然没有改变,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权力关系。
三、 隐秘的心理空间中善恶的挣扎
“心理空间指外部生存空间和人物生命体验投射于人物内心之后产生的对某事或某人的感悟和认识。”[5]对于心理空间的关注拓展了文本的深广度,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野和角度。心理空间也是空间研究中最难把握和分析的一环,因为人物的心理活动往往具有隐秘性和不确定性,有时甚至不受主体理性的控制,因此才出现了意识流小说、复调小说等形式。“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6]人物形象的丰满往往离不开复杂的心理空间的建构,《神木》对于主人公的心理描写体现了人性的复杂。
小说中写了两次谋杀,在讲述两个主人公周密的杀人计划的同时也对他们的心理活动进行了描写。两个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利益均分,看似相互信任,实则各怀鬼胎貌合神离。在谋害元清平的过程中,按规矩由唐朝阳(李西民的化名)打死“点子”并冒充死者家属,宋金明(赵上河的化名)负责和窑主斡旋,领取赔偿金后两人均分。但宋金明发现了“点子”鞋子里藏钱的秘密,便决定在“点子”死后独吞这笔钱,于此同时唐朝阳也发现了鞋子的秘密,并且对宋金明的心思了如指掌,两个人谁都没有挑明,表面上风平浪静,都遵守着规矩,其实在进行一场波涛汹涌的心理战,最终两人平分了鞋子里的钱。这段心理描写展现了人的自私本质和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缺失。
小说的高潮发生在第二次谋杀时,这次由王明君(赵上河的化名)扮演“点子”的亲人,本来一切进展顺利,但意外的是在几天的相处中王明君和“点子”产生了感情。这个“点子”是一个从农村出来打工同时寻找自己的父亲的高中生,王明君看到他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儿子,他的憨厚老实、单纯善良也使王明君心生不忍。当得知这个“小点子”是上一个“点子”元清平的儿子时,他的良心开始不安,潜意识里想放“小点子”一命,而张敦厚(刘西民的化名)则坚决要求尽快办掉“点子”,两个人产生了冲突。最后一次下矿时,王明君在窑底制作了一个假顶,只需打倒支撑假顶的柱子,顶下的人就一定会被砸死,这时候的王明君和张敦厚都起了杀心,张敦厚想杀死王明君以防他串通“点子”背叛自己,王明君也想杀死张敦厚救下“小点子”以绝后患。这时的两个人犹如两只困兽,你死我活自相残杀,虽然没有具体的描写,但心理活动昭然若揭。最后王明君选择与张敦厚同归于尽,并在死前让“小点子”去找窑主要赔偿金,王明君心中的善最终战胜了恶,用赴死实现了他心灵的亲情救赎。
四、 《神木》的空间叙事
前文讨论了作者在小说中建构的各种空间,是作者运用语言符号根据现实空间所虚拟出来的空间。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小说叙事形式所具有的空间性。空间化的叙事形式是指文本叙事表达所呈现的“空间性”,诸如空间的叙事结构、支离破碎的故事情节等。它所追求的是小说形式的空间化。小说《神木》的叙事模式呈现出传统的线性结构,按时间先后顺序安排情节,但在表面的线性结构之下隐藏着一个立体的叙事空间。
《神木》的情节按下列顺序排列:火车站物色“点子”——小煤窑杀人——回家过年——火车站物色“点子”——小煤窑杀人。如果按正常的故事发展,小说会形成一个情节的循环,这是一种平面化的叙述结构,而作者在这里打破了这个循环,在两次的杀人事件中人物的变化导致情节走向的逆转。第一个案件中的“点子”元清平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工,是唐朝阳和宋金明的理想目标,窑主也是一个比较疏忽的人,此时的两个主人公只想快速办完这个“点子”,讨一笔钱回家过年,因此计划实施的很顺利。到了第二次作案时,“点子”变成了一个单纯善良的高中生,并且是上一个“点子”的儿子,这样就很容易引发人的同情心,为后来情节的逆转埋下伏笔。而窑主也与上一个不同,他极其精明谨慎,控制欲极强,矿上戒备森严,凶手想在这里作案困难重重。更重要的是赵上河心理的变化,第一次作案时他面对的是一个和他差不多的打工者,生活的压力和利益的诱惑使他丧失了人性。而面对一个不谙世事的高中生时他作为父亲的情感被激发出来,开始觉得悔恨和不安,这就导致了小说最后由原计划的杀死“点子”变成救下“点子”,两个凶手同归于尽。从第一次作案到第二次,每个人的身份都在某个方面得到了强化,使得小说的情节不是循环往复而是螺旋上升,最后达到一个高潮。《神木》这种螺旋式的结构展现了叙事的空间性。
本文从空间批评的角度解读了刘庆邦的《神木》。小说中的主人公从火车站到小煤窑再到家乡,物理空间的变化表现出人性中贪婪、残酷和谦逊、善良的交织。空间不是一个静止的容器,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的集合体,同时也生产出各种社会关系,《神木》中的农民工世界、乡村世界等不同的社会空间展现了底层人们生活的艰辛。主人公心理活动的描写表现了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缺失和在善与恶之间人性的挣扎。小说在叙事结构上的空间性展现了作者的现代性追求。总之,空间批评对于我们把握《神木》的主题思想、了解作者的创作初衷具有重要作用,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刘庆邦的艺术世界。
——神木大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