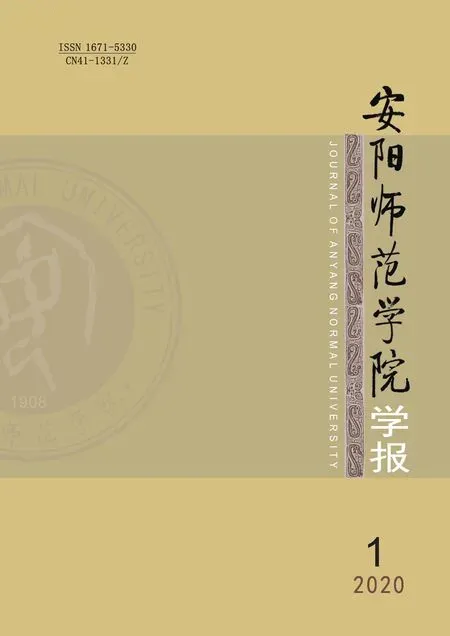现代汉语动态形容词谓语句研究述评
陈晓燕
(河南大学 外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形容词谓语句,是形容词或形容词短语充当谓语的主谓句,它广泛应用于各种文体表达及日常交谈中。形容词作谓语有两种普遍而又特殊的情况:一种是谓语后加上诸如“了”“着”“过”等动态助词或“起来”“下来”“下去”等趋向动词;另一种是谓语后加上宾语,谓语与宾语之间存在 “了”“着”“过”等动态助词。从句法结构上看,这两种形式的形容词谓语句有和动词谓语句极其相似的表现形式;在语义上,形容词谓语句也有动态义。据此,我们将其统一命名为“动态形容词谓语句”。
相对于形容词谓语句的其它形式,动态形容词谓语句具有独特的语法与语义特征,而且动态形容词谓语句内部语法与语义特征也相当复杂。动态形容词谓语句使用广泛,且独特性与复杂性并存。然而,动态形容词谓语句研究却相对匮乏,且现有成果缺乏整体性考量。纵观现代汉语研究,至今还没有出现系统研究动态形容词谓语句的语法专著。但是语言学研究者们都一直在关注这一语言现象,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讨论。
一、 现代汉语动态形容词谓语句研究的开端
现代汉语动态形容词谓语句研究始于黎锦熙先生。在第一部以汉语白话文为研究对象的语法专著——《新著国语文法》中,黎先生(1924:123)指出“国语的句法上有一个特点,就是述语可以直接用形容词”,并且认为,形容词添加助动词后,句子“不但在句法结构上是动性的,即便在实质的意义上,也有了迁变流转的动态了”。黎先生认为形容词谓语句中的形容词后面添加动态助词,整个句子在句法上和语义上就有了动态性的意味,例如:
(1)菊花黄了,天气也凉了。
(2)孩子大了,今年要请一个先生。
(3)你的胡子却也白了许多。
吕叔湘先生(1942:78)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对动态形容词谓语句的语义特征和句法表现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吕先生提到“形容词做表态谓语,有时不是表示一种无始无终的状态,而是表示一种状态的开始,或是表示一种状态的完成,于是这个形容词也就带有动作的意味”。吕先生(1942:37)还注意到了形容词后接宾语的现象,他指出,白话里少数形容词可以用作动词,此时的形容词算是具有了形容词和动词两种性质的词,例如:
(4)说到这里,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一会儿忽然高了起来。
(5)一到十月,这些树叶便红了起来。
(6)这件事情又得辛苦你一趟了。
(7)我告诉你一个巧的儿,你越冷淡他,他越舍不得你。
王力先生(1943:177)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指出“形容词最不适宜做叙述词,在这一点上,它和动词是恰恰相反的,形容词用为叙述词时候,往往是靠‘了’或‘着’的力量”,另外,王力先生进一步指出“起来”和“下去”等趋向动词也可以使形容词带叙述性,例如:
(8)改日宝二爷好了,亲自来谢。
(9)袭人见了也就心冷了半截。
(10)你湿了我的衣裳。
(11)他还不大着胆子花么?
(12)物价逐渐高起来了。
(13)声音慢慢地静下去了。
黎锦熙、吕叔湘和王力三位先生均观察到汉语中形容词依靠添加动态助词、趋向动词和宾语等语法成分做谓语,并敏锐地认识到此时的形容词有了动词的特征,带有动态的意味。但是,至此三位先生均未明确对此类句型冠以名称。丁声树先生(1961)在《现代汉语语法讲话》里根据谓语的性质,把句子类型划分为:体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动词谓语句和主谓谓语句,明确把“形容词谓语句”当作一种基本的句子类型。在该著作里,虽然有关形容词谓语句的论述不多,但是这一术语的提出,为形容词谓语句在现代汉语中作为一种独立的句型争得了一席之地(孙鹏飞,2015:25)。丁先生(1961:7)还明确指出,有时候形容词加上“了”“起来”一类字眼,简直和动词没有区别,并直言,形容词这样用的时候,就可以认为是动词。比较:
(14)花红了。
(15)雨大起来了。
(16)花开了。
(17)雨下起来了。
在动态形容词谓语句研究的初始阶段,几位前辈都对形容词谓语中这种带有动态特征的结构进行了大致的讨论,尤其是对带上动态助词、趋向动词和宾语后的形容词的词类归属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总体上,几位先生一致认为此时的形容词有了接近动词的特征,甚至就把其看作动词。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对形容词谓语句的研究相当一部分仍然集中在带上了动态助词、趋向动词或者宾语的形容词到底是姓“形”还是姓“动”的争论上。
二、关于动态形容词谓语句中形容词词类归属问题的争论
关于动态形容词谓语句中形容词的词类归属问题,学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带上动态助词、趋向补语和宾语后的形容词就变成了动词。除了丁声树(1961),李临定(1990:48)也认为,“起来”等应作为确定动词的一个标准,所以他认为“苹果红起来了”“气球大起来了”中的“红”“大”应看作是动词,称为“形转动词”,也就是说 “从主要特征来看,它们已变成动词”。Shiao Wei Tham(2013:661-662)认为汉语中“病人的血压很高” 和“病人的血压高了”中的两个“高”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表示状态(state)的形容词,后者是表示状态变化(change of state)的动词,两者具有派生关系,后者的“状态变化”义来自动态助词“了”。邢福义(1980:66)首先提出“形容词动态化”这一概念,他认为,形容词动态化现象是指形容词带上了某种表示性状变化的成分,就具有了一定的动态,但是并未完全转化为动词,属于形容词在性质上向动词临时转移的现象。“性状变化的成分”主要包括语法化程度很高的动态助词“了”“着”“过”,语法化程度较高的趋向动词“起来”“下来”“下去”。后来,邢先生在《词类难辨》(1981)和《形容词短语》(1990)中,都设有专节讨论形容词动态化的问题,邢先生所持的观点为:形容词后加“了”“着”“过”动态助词和“起来”“下来”“下去”趋向动词时,形容词有了一定的动态,但并未完全转化为动词;但当形容词后加了宾语,就具备了动词最根本的特征,此时就完成了向动词的转化。刘月华等(1983:122)也持相同的观点:形容词后不能带宾语,一旦带了宾语,就成了形动兼类。吕叔湘(2014:340)详细区分了单音形容词加名词性成分的五种情况,认为“这里的形容词应该说是已经转化成动词了”。朱德熙(1982:55)为区分形容词和动词提出了“前面能不能加‘很’”和“后面能不能带宾语”两条标准,他把形容词和动词分别定义为:凡受“很”修饰而不能带宾语的谓词是形容词;凡不受“很”修饰或能带宾语的谓词是动词。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先生认为形容词不能加宾语,形容词加上宾语后就变成了动词。张斌(2002:310)也明确指出,形容词是不能带宾语的,凡是带宾语的形容词都是形动兼类。
以郭锐为代表的中间派持第二种观点,即认为对于添加宾语的形容词要区别对待。郭锐(2002:192)在词类研究专著里,为了区分形容词和动词纠缠不清的关系,专门提到了形容词添加宾语的几种情况。他并没有把是否带宾语简单作为区分形容词与动词的唯一标准,而是根据不同的用法,细化了几种情况:首先,在诸如“高我一头”“大我一岁”等表达里,此处的“高”“大”是形容词;其次,“红着脸”“硬着头皮”等表达里的“红”“硬”是形容词;最后,词类活用现象中,如“肥了个人,瘦了国家”“苍白了头发”里的“肥”“瘦”“苍白”都是形容词。这些情况下的形容词虽然添加了宾语,但是都被划分为形容词。但在“端正态度”“充实生活”“饿他一顿”等“使动”意义表达中和诸如“可怜他”“奇怪他为什么没来”等“意动”意义的表达中,这些词均处理为动词。由于“端正”“可怜”这些表达又可以被“很”修饰,因此均被处理为兼类。
第三种观点认为,形容词加上动态助词、趋向动词或宾语后,并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形容词。王力(1958:375)在《汉语史稿》中指出有些词在词典中并不属于某一词类,但在句子里它能有这一类词的职能。我们把这种职能称为词在句中的临时职能,比如形容词的“致动”和“意动”用法。王力先生认为形容词的“致动”和“意动”用法如果占了优势,形容词原来的用途被废置不用,就有可能成为正式动词。张志公(1959:39)认为,动词和形容词都可以加上“了”“着”“过”“起来”“下来”“下去”等辅助性成分以表示体的变化。范晓(1983:1)明确指出受印欧语系的影响,学界倾向于把能否添加宾语作为区分形容词与动词的唯一标准。汉语中的形容词带宾语不是非常普遍,但也绝不是个别的或少量的。假如形容词一带宾语就变成了动词,那么汉语中动形兼类的数量就大了。因此,能否加宾语不应该作为区分动词和形容词的硬性标准。自从陆俭明(1994:28-33)的《关于词的兼类问题》发表以后,对后加动态助词和趋向动词的形容词是否发生词类转变的争论,基本销声匿迹了。在该文中,陆先生详细论述了不属于兼类的情况,指出不同类词具有部分相同的语法功能,不看作是兼类。例如动词后能加助动词“了”也能加趋向动词“起来”表示行为动作开始进行,如“花开了”“雨下起来了”;形容词有时候也能加这种“了”和“起来”,如“花红了”“水热了”“雨大起来了”“现在神气起来了”。现在大家不认为这里的“红”“热”“大”“神气”是形容词兼动词的用法,而认为后加“了”和“起来”是动词和形容词共有的语法特征。陆先生还指出,“这儿交通很方便”和“大大方便了顾客”里的两个“方便”在意义上似有差别,前者表示“便利”,后者表示“使便利”。然而这不是词汇意义上的差别,而是由“方便”带宾语这种格式所赋予的语法意义所造成的差别。因此,二者是同义的,都是“便利”的意思,使动的意义是句法格式所产生的语法意义,所以应概括为一个词。又考虑到“方便”这样的词为数比较少,“只占常用形容词总量的6%”,陆先生认为有理由把这类词处理为兼类。
“兼类说”也遭到了国内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反对,陈小荷(1999:67)认为如果彻底贯彻朱德熙先生概括词与个体词的观点,兼类词是不应该出现的,划分兼类词是一种“为了迎合西洋语法的词类框架而削足适履”的行为。周韧(2015:504-516)承认朱德熙先生的词类观和词类体系在学界的深远影响和权威地位,但认为兼类的设置违反了其词类观的重要原则,即“汉语句法成分与词类不是一一对应关系”,而且兼类概念在实践中会引发诸多问题。因此,周文得出结论:汉语词类划分体系中,不宜设置兼类的概念。沈家煊先生(2009:1-12;2016: 403)提出与传统“名动对立说”相对立的“名动包含说”以解决汉语词类划分的困境,认为动词是名词的一个次类,形容词是动词的一个次类,因此不存在兼类。沈先生特别指出,形容词加宾语是汉语自古以来的一个普遍用法。石毓智、白解红(2006:80)认为和英语中的形容词不同,汉语中形容词的语义结构自身具有一个动态的时间过程。因此,在表达时间概念时,和动词一样,只需在形容词后添加一定的语法标记或者时间副词,而无需借助动词。另外,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一部分形容词可以像普通动词一样,带上名词宾语,这是形容词的使动用法。由此可以看出,石、白两位学者主张形容词的语法表现是由其自身蕴含的语义特征决定的,形容词并不因为带了语法标记或者名词宾语就会发生词类的改变。张国宪(2006)把形容词后加动态助词再加宾语作为形容词体形式的重要表现。基于原型范畴理论,李泉(2014:115)基于388个单音形容词的700个词项,考察单音形容词的原型特征后得出结论:带宾语是部分形容词和多数动词“词类家族相似性”的一个体现,是动词和形容词构成一个大的谓词连续统的一个体现,带宾语是动词的典型特征,但不是动词的专利,况且介词也可以带宾语。刘光婷(2016:74-77)也有类似观点,她认为,谓宾结构是一个原型范畴,“Vt+宾语”结构是其最典型的成员,“Vi+宾语”结构的典型性次之,而“A+宾语”结构则处于该范畴的边缘位置,并且整个谓宾范畴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三种成员结构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
由此可见,最初对添加了“了”“着”“过”“起来”“下来”“下去”等语法标记的形容词是否发生词类转变的争论基本已经平息,学界对该问题的主流观点是:添加了语法标记的形容词词类不发生变化。相对来说,对于添加了宾语后的形容词是否发生词类转变的争议略大,尤其是“兼类说”在学界的影响还相当强大。
三、形容词动态化研究中的动态形容词谓语句研究
继黎、王、吕、丁四位先生对动态形容词谓语句的初始研究之后,邢福义先生提出“形容词动态化”这一术语,对形容词动态化的句法表现和语义特征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词类难辨》和《形容词短语》里,邢先生(1980:63-65;1981:132-136;1990:76-80)从句法表现上把形容词动态化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形容词后面带“了”,前面经常加“已经”,表示性状变化的实现,例如:
(18)夜,已经很深了。
(19)这时候,雨已经小了,一路上有脚踩泥水的声音。
第二, 形容词后面带“着”,表示性状正处在持续状态,例如:
(20)不一会儿金宝便掀门进来了,很疲乏,面孔灰暗着,肩膀松连着。
第三, 形容词后面带“过”,前面经常加“曾经”,表示某种性状过去曾存在过,现在已经结束。例如:
(21)他确实曾经神气过好几年。
(22)晚上,雨小过一阵,风也曾平息下来。
第四, 形容词后面带“起来”“下来”“下去”,前面经常加“顿时”“渐渐”“突然”等时间副词,表示性状变化的起始和继续。例如:
(23)我顿时紧张起来。
(24)从潼关到宝鸡的列车到达郭县站的时候,天色暗下来了。
(25)炉火的微光渐渐暗下去。
邢先生指出,上述情况都属于“形容词动态化”现象,其形容词都具有了动态性,但是并未完全转化为动词。但当形容词后面跟了宾语,形容词就完成了向动词的转化,此时就超出了“形容词动态化”现象的范围。例如:
(26)他红着脸说:“我就是爱说梦话……”
邢福义先生(1994)又另辟文对 “A+趋向动词”结构的语义特征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他认为形容词动态化的三种趋向态模式,“A起来”表示“兴发态”,“A下来”表示“垂临态”,“A下去”表示“延展态”。趋向动词本身的语义差别造成了其与形容词的组合能力各不相同,三种模式的使用范围自然也就宽窄有别。总体来说,三种模式都和时间相关,都表示度量的变化和抽象的趋向性。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形容词动态化里的形容词应该一般做谓语,也有少数做状语和定语的情况。在“形容词+着”结构里,如“他在忙着写论文”,在“形容词+了”结构里,如“他穿着一件旧了的衬衣”,带了语法标记的形容词就分别做了状语和定语。
张国宪(1998:403-413)认为汉语中有一部分形容词本身具有动态性,而一部分形容词内部相对稳定,因此根据情状中的[+静态]把形容词分为性状形容词和变化形容词。性状形容词如“名贵”“壮丽”“豪放”,其时间结构是匀质的,缺乏内在的起点和终点,在语法表现上对带“了”“着”“过”等语法标记的变化情状句表现出明显的排斥性;相反,变化形容词如“高”“瘦”“红”,最大的特点是动态性,其时间结构是异质的,拥有内在的起点和终点,与“了”“着”“过”等动态助词表现出较强的兼容性。变化形容词性质灵活,在状态情状句和变化情状句里表现都很活跃。对于变化形容词来说,其内部的动态性是靠语法标记来激活并使之展现出来的。
张国宪(2006:264-283)通过详细考察形容词和不同的语法标记共现的句法格式以及这些句法格式对形容词次范畴的选择限制,扩大了形容词动态化的句法范围,并引发了形容词动态化中形容词的语义限制研究。与邢福义先生提到的形容词动态化的句法表现相比,张国宪把形容词加宾语格式(NP1+A+X’+NP2)也纳入形容词动态化的研究范围。例如:
(27)“我嘴最笨了,我说的是实情。”拾来红了脸。
(28)老马紫着一张脸,正在骂街呢,一抬头,见吕建国跟郭主任进来,就不吭声了。
(29)每个人的手上都亮着手电,那是出门的时候当成工具发的。
关于不同句法格式里形容词的语义限制问题,张国宪认为相对于“NP+A+X”,“NP1+A+X’+NP2”里的形容词自变性减弱,可控性增强。比如“他老了”“他瘦了”里的形容词和“他弯着腰”、“他冷了我的心”里的形容词相比,自变性更强、可控性相对弱。而且,“NP+A+着”结构里的形容词表短暂义的居多,“NP+A+过”结构里,表起始义的形容词居多。尽管关于形容词动态化语义限制的研究成果还较零散,但为我们对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启发。
郑妵妍(2003)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1478个常用形容词与不同语法标记的兼容性进行了穷尽性考查,发现形容词之间的动态性差异较大并且简单分析了形容词动态性与动词动态性的差别。
归结起来,从“形容词动态化”视角为动态形容词谓语的句法和语义研究奠定了基础,并且开始触及到形容词的语义限制问题,虽然研究成果还不够概括和全面,但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和思路。
四、 形容词谓语句研究中的动态形容词谓语句研究
我们知道,“形容词谓语句”首次作为一种基本的句子类型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被提出的。然而,通过纵观以往的相关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大部分与形容词谓语句的相关研究是从“形容词动态化”“形容词+动态助词”结构角度进行的。以“形容词谓语句”这一专门的名称进行的研究早期时候还比较罕见,对动态形容词谓语句的研究也大都是附属性的,对其专门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直到进入80年代,对形容词谓语句的专门研究才日渐增长,对动态形容词谓语句的研究也相应有所增加。对形容词谓语句及动态形容词谓语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句法形式、句法意义、句法功能以及句法自足性等方面。
李临定(1986:284-301)在《现代汉语句型》里设有专门的章节细致讨论了形容词谓语句中不同的附属成分,把形容词谓语句分为15种结构形式,其中包括“名+形+了”和“名+形+起来/下来/下去”这两种特殊的形容词谓语句,认为这两种形容词谓语句都表示“变化”。周有斌(1995:118-122)分别讨论了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作谓语不同的自由度,其中性质形容词作谓语时,后面可以添加“了”“着”“过”表示主语的一种动态属性。周有斌(1996:127)针对当时对形容词谓语句研究的状况,提出形容词谓语句研究要注重与动词谓语句的比较,特别是形容词带宾语问题。卢福波(2005:83)也把“带宾句”作为形容词谓语句的一种下位结构。
在形容词谓语句研究早期时候,由于学界对形容词谓语句及动态形容词谓语句的下位结构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因此对其句法意义的研究还比较笼统。李临定(1986)把形容词谓语句的句法意义概括为表程度、比较和变化,其中动态形容词谓语句表变化。刘月华(1987:14-16)着重比较了含有“起来”和“下来”的动态形容词谓语句,他认为两种下位结构都表示主语性状的开始,但两种结构与形容词结合的范围存在差异。龚晨(2009)以“形容词+动态助词”结构为研究对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总结了添加不同动态助词的形容词做谓语的句法意义,他认为,“形容词+了”结构表示的是一种变化的实现;“形容词+着”表示性状的短暂持续;“形容词+过”表示性状过去的经历;“形容词+起来”表示变化的继续和发展;“形容词+下来”表示新状态的出现与持续;“形容词+下去”表示已有状态的继续发展。而且,作者继张国宪(2006)后对不同下位结构中形容词的选择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详细的探讨。
陈望道(1978:105)认为按照句子功能划分,形容词谓语句可分为叙述句、描记句、诠释句和评议句,其中动态形容词谓语句属于叙述句。赵元任(1979:54)主张形容词作谓语有三种作用:对比、肯定和叙述,他也认为“这瓜熟了”之类的动态形容词谓语句属于有叙述的功能。刘月华等(1983:412)在《实用现代汉语语法》中提到,形容词谓语句主要的功能在于描写人或事物的性状,还可以对人或事物的变化加以说明。正如孙鹏飞(2015:27)所言:从语言事实来看,形容词谓语句的确表达不同的功能,其呈现方式也各不相同,但是相对而言,对其功能的研究仍然有待细化和深化。
学界早在20世纪中期对形容词作谓语的自足性问题就有所注意,朱德熙(1956:26)提出性质形容词作谓语不自由,单独作谓语含有比较或对照的意思,必须放在具体的语言环境里。此后,吕叔湘(1942:54)、李临定(1986:286-290)和邢福义(1990:42-45)也都有提及,但均未详细论述。直到90年代才陆续有学者对该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孔令达(1994:436)提出形容词谓语句里可以通过添加程度副词、介词词组“比……”、句末语气助词“了”等手段来实现句子自足。贺阳(1994:26-38)详细考察了汉语中的完句成分,把形容词谓语句的完句成分概括为语调、语气、否定、时体、程度等语法范畴。李泉(2006:56-63)还把汉语中的完句范畴分为完句成分和完句手段,和形容词谓语句相关的完句成分有助词、副词等,完句手段有重叠。顾阳(2007:22-38)认为汉语的场景体里“定点”存在与否对句子的完句性有重大意义,定点的作用在于充当时空参照点,在语言层面,起定点作用的主要有程度副词、焦点副词及句尾助词。张伯江(2011:3-12)讨论了性质形容词作谓语的三种实现手段,主要有借助判断框架“是……的”、借助程度副词以及借助相应的形态手段。之前的绝大多数研究都在试图描写和总结形容词谓语句的完句成分和完句手段,伍雅清、祝娟(2013:18-24)则开始对从理论高度对形容词做谓语的自足问题进行分析。她们在分析性质形容词作谓语的完句手段的基础上,从形式语义学的角度专门探讨形容词谓语句的不完句效应,认为形容词谓语的各种自足结构都属于焦点位置。熊仲儒(2013:219-304)认为状态形容词和性质形容词在语法形式上表现迥异的原因跟形容词的量度范畴有关。焦点和量度范畴概念的提出,对进一步深入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庞加光(2015:293-302)借助概念语义学的百科语义观和识解理论,提出汉语形容词做谓语能否自足取决于其突显程度区间是否被锚定,也就是说,通过确定区间位置或为程度参照赋值而使相关程度区间拥有确定性。性质形容词作谓语不自足的原因在于其程度参照未被赋值,不同的补救手段均在于设置该参照为不同的值,如基准值、语境程度值或零值。而状态形容词自身便具有对程度区间的定位,即突显程度区间是被锚定的,因此可自由作谓语。韩鑫(2016)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历时的角度把现代汉语中形容词谓语句的相关标记类型分为词组层面的标记形式、句子层面的标记形式和构形层面的标记形式,并探究了形容词谓语句的有界化建立起来的过程及其动因,得出结论:形容词谓语句的有界化与动词谓语结构的类推和扩展密切相关,动词谓语句为相关形容词有界性结构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和促成动因。孙鹏飞(2018:76-86)认为,无论从历时还是类型学的角度看形容词充当谓语都不自足,都需要形式上的标记以实现完句。现代汉语形容词谓语句主要有句法、语篇和形态三种标记手段,这些标记手段的作用在于“有界化”“量级核查”和“认知入场”。
从以上综述可见,对形容词谓语句的研究在经历了长期现象描写的过程后,正开始走向理论解释的阶段,特别是近期的有关形容词谓语句完句手段的认知功能解释,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但动态形容词谓语句的研究仍处于相对被冷落的地位。
五、 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归结起来,以上研究虽然角度各不相同,但都承认一部分形容词谓语句表示动态意义,即承认动态形容词谓语句的存在。从现有动态形容词谓语句的相关研究来看,无论是对动态形容词谓语句里的形容词词类归属问题的争论,还是从形容词动态化角度对动态形容词谓语句的描写,或从形容词谓语句的视角对动态形容词谓语句标记手段认知功能的探索,都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后续的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和借鉴意义。然而,相对来说,动态形容词谓语句仍是一个被忽略的课题,尚存不少问题值得深入挖掘和受到更多关注与重视。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动态形容词谓语句缺乏专门的系统性研究。学界对形容词谓语句的研究大多散见于汉语句型研究的专著里,甚至以形容词谓语句为专题的论文还为数不多,对动态形容词谓语句的研究更是零散,还远远谈不上系统研究。
(2)对动态形容词谓语句还缺乏清晰界定、分类以及细致的描写。迄今为止,学界对形容词谓语句尚未有周全的分类标准,部分学者(朱德熙,1956; 张伯江,2011)把形容词谓语句划分为有系词的形容词谓语句和无系词的形容词谓语句,还未出现明确以情状为标准对形容词谓语句进行的分类。毋庸置疑,对动态形容词谓语句的界定、再分类及其句法表现等问题就有待澄清了。
(3)对动态形容词谓语句形成的认知机制的研究还几乎是一片空白。添加动态助词和趋向动词及宾语本来是动词的典型特征,但在动态形容词谓语句里被添加在了形容词之后。目前对形容词谓语句认知机制的探索除了张克定(2016:11-21)对处所主语形容词谓语构式的认知机制进行的研究之外,还未有学者关注动态形容词谓语句形成的认知机制。
(4)对动态形容词谓语句动态义建构的分析还尚未起步。前人对动态形容词谓语句语义的研究大都依据语法标记“了”“着”“过”“起来”“下来”和“下去”的语法意义,或者简单把“形+宾”结构的语义做了分类,还尚未有研究从整体上关注动态形容词谓语句语义建构过程。
(5)对动态形容词谓语句句法语义结构特征的认知解释还尚未出现。除了上文提到的张国宪(2006)和龚晨(2009)两位对动态形容词谓语句里形容词语义限制所做的初步尝试之外,还鲜有研究对其句法语义结构特征进行较为合理的阐释。
总的来说,目前学界对动态形容词谓语的描写研究还比较零散,对它的解释性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对其认识还尚未差强人意,这就为后续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