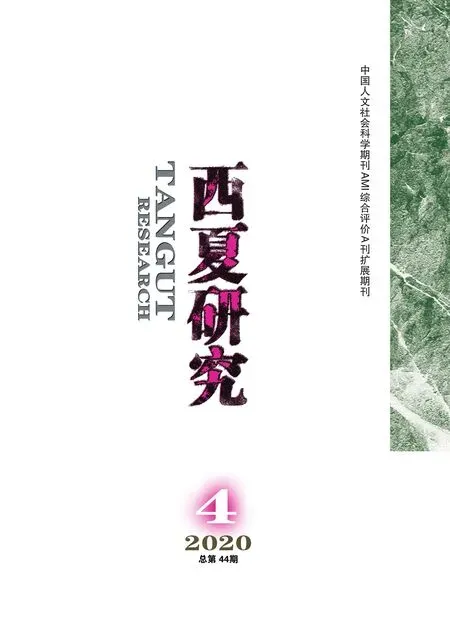北宋泾原路设置刍议
□王一凡
北宋立国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政局纷乱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局部的统一,但来自北方的威胁依旧没有解除。同时,新的威胁崛起于宋廷西北地区,使其同时面临“西、北之忧”。在这一严峻的环境下,宋廷除了构建自身的防御体系外,“不断派人出使高昌、回鹘、高丽、女真等部族政权。在宋的协调下,自西向东,包括西域、漠北、宋朝、高丽在内,一个环绕辽朝边疆的多政权反辽同盟正在酝酿当中”[1]82。而辽国也反过来拉拢周边政权或部族共同对宋,党项、吐蕃等部族都在这一争取范围之内。在辽国扶持下的党项政权不断攻击北宋的“西陲”,使得该地区的气氛逐渐紧张。在这一大背景下,宋廷西北地区的防御策略成为庙堂之上的重要议题,而如何构建西北防御体系的问题变得日益迫切。北宋西北诸路从都部署路到安抚使路的变迁映射出朝廷的大战略和西北情势的变化,而陕西诸路之一的泾原路作为西北防御体系问题诸多的一环,其变化和发展更能反映出一个多世纪以来宋廷在西北地区的经营策略与手段的变迁。泾原路从建置之初就面临着与其他诸路相迥异的问题:秦凤路主要应对吐蕃;环庆路作为被山地屏卫的突出部,相对安全;鄜延路直接面对西夏,其境况也令人堪忧。[2]221-222泾原路除了地形地势上的“川谷稍宽平”[3]1116对守御极其不利之外,还同时要防御党项与吐蕃的双重威胁。除陕西诸路普遍存在的问题外,泾原路自身复杂的状况导致该地区的问题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故泾原路自设置之始,就不得不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
一、唐宋之际的泾原地区
泾原地区自唐中叶“安史之乱”以来,一直是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或部族角力的战场。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十一月,宰相元载“以吐蕃连岁入寇,马璘以四镇兵屯邠宁,力不能拒,而郭子仪以朔方重兵镇河中,深居腹中无事之地,乃语子仪及诸将议,徙璘镇泾州,而使子仪以朔方兵镇邠州”,次月“己酉,徙马璘为泾原节度使”[4]7203-7204,治泾州,领泾州和行原州。这一事件从表面看是为了巩固唐廷边防,实际上与当时暗流涌动的中晚唐政局有着密切关系①,但其作为国家藩屏而被设立原因肯定是首要的。唐代泾原节度使“治泾州,管泾、原、渭、武四州”[5]1390,其中泾州“无险要可守”,其“陇山高峻,南连秦岭,北抵大河”[6]2775。原州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陷于吐蕃,元和三年(808),“临泾镇将郝玼以临泾地险要,水草美,吐蕃将入寇,必屯其地,言于泾原节度使段祐,奏而城之”。唐廷于是年十二月庚戌置行原州于临泾。[4]7648,7656该地“当西塞之口,接陇山之固,草肥水甘。”[5]3411渭州亦于广德元年被攻陷,是年“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4]7146。宪宗元和四年(809),以原州之平凉县置行渭州[7]968,这或许是唐廷在无力夺回原州继续经营的情况下对“元载遗策”所做出的妥协之举[8]。泾原节度使的渭州实际上还在故原州境内。武州,唐宣宗大中五年(851),“以原州之萧关置武州”[4]8056,武州实际上也在故原州境内。所以总的来看,泾原节度使的辖区实际上还是在最初的泾、原二州的范围之内(见表1)。泾原南接凤翔,凤翔“无山谷之险,吐蕃由是径往入寇”[5]3884,也就是说,唐代泾原节度使受到吐蕃来自西北至西南多个方向的威胁。
在马璘为首任泾原节度使之前,吐蕃就不间断地入寇,最严重的一次当属广德元年泾州刺史高晖投降吐蕃事件,此次吐蕃入寇不但导致原州陷落,直接威胁到唐廷中枢。在泾原节度使设置后,吐蕃的入侵频率并没有降低,但每次入寇对唐廷所造成的伤害较设置节度使之前小(见表2)。这一时段泾原节度使与吐蕃的攻防特点有了新的变化,泾原军抵御吐蕃入寇的能力明显增强,有时能够发动较为有效的反击,唐廷甚至在元和十三年(818)和大中三年(849)两度收复原州。吐蕃在这一时期有时与党项合流,但此时党项尚未崛起,泾原地区主要还是受到吐蕃侵扰,唐蕃势力在故原州西北一带反复拉锯,吐蕃在占据后来位于北宋镇戎军境内的唐故原州西北的摧沙堡后进一步占领故原州城。不过这一时期由于“泾州西门不开,京师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严烽火,虽常有侵轶,然卒无事”[3]3021。 进入五代(907—960)后,鲜见泾原地区的相关史料记载,该地区的政治格局呈模糊化。这时由于“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9]1839,吐蕃对于泾原地区的攻势明显减弱,同时五代中原政权对泾原地区的实际控制力也比唐削弱不少,其控制区域依旧没有超出“国家西境极于潘原”[5]3411的范围,而如渭州平凉这样的要地距离潘原才六七十里[5]3917,依旧极易遭受周边民族的侵扰。正如顾祖禹所评论的那样,“唐自广德以后,西陲尽为异域,而泾原之备日棘”[6]2775。

表1 :泾、原、渭、武四州广德后行政区划变迁表

表2 :唐中后期泾原地区唐蕃攻防情况表
入宋后,朝廷在泾原地区的建置基本沿袭唐泾原节度使,泾州治所保持不变,将行原州的治所临泾、行渭州的治所平凉正式定为北宋原州、渭州的治所③。宋人眼中的平凉、镇戎二城为“西陲之机键”[10]289,所以,又于至道三年(997)在渭州以北设置了镇戎军(见表3)。北宋中叶以后扩展的德顺军、怀德军、西安州、会州实际上还是大致恢复了唐代的原州、会州地区,此即宋人吕公著所认为的“先朝(神宗朝)所取,皆中国旧境”[3]9312。也就是说,宋初的泾原路的泾州、原州较唐代大为缩水,辖区缩小不少,所以终北宋一代,泾原路经略西北的结果是最终大致上恢复了唐代的疆理。

表3 :唐代至宋代泾原地区政区变迁表
二、泾原都部署路的设置
北宋立国过程中,采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 的策略,把西、北二边的问题留到了最后。宋太祖、宋太宗时期,泾原地区相对平静,偶然有零星的蕃部作乱。鉴于这一情况,宋廷“仍然依靠节度使等军政合一的统兵官阻止边境防御”[11]180。这一时期泾原地区的布防中心可能位于原州。史载:
宋初,交、广、剑南、太原各称大号,荆湖、江表止通贡奉,契丹相抗,西夏未服。太祖常注意于谋帅,命李汉超屯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领棣州,以拒北敌。又以郭进控西山,武守琪戍晋州,李谦溥守隰州,李继勋镇昭义,以御太原。赵赞屯延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屯环州,王彦升守原州,冯继业镇灵武,以备西夏。[12]9346-9347
上文提到的每一位将领镇守的地区都为当时之要地,泾原地区只提到原州,而其东边的环庆地区的环州、庆州皆榜上有名。王彦升时为原州防御使,“在原州凡五年……戎人畏惧,不敢犯塞”[3]236。防御使自唐至德年间以后,置于“大郡要害之地”,“以治军事,刺史兼之,不赐旌节”[5]1923。“宋朝沿唐制,置诸州防御使。”[13]1776初泾原地区只有原州设防御使,可见,这一时期原州在北宋边防的地位。在太祖、太宗朝,泾原地区的边官多任用“豪侠群体”。除前面提到的“性残忍多力”的王彦升外,还有如“少从军,有武勇”的白重赞,“少以材武应募隶军籍”的张铎,“少不逞”、“为盗于乡里”的谭延美,“有胆气”能游侠四方的魏廷式等人,他们往往能起到安憩边境的良好效果④。真宗咸平二年(999),钱若水论道:“王彦升(等人)在原州,但得缘边巡检之名,不授行营部署之号,率皆十余年不易其任,立边功者厚加赏赉,其位或不过观察使。位不高则朝廷易制,久不易则边事尽知,然后授以圣谋,不令生事,来则掩杀,去则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狄、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屡遣戎使先来乞和。”[3]974这一番论断可谓道出了太祖、太宗时期任用边将的指导思想,在任用长于边事的豪侠将领的同时,使他们位卑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放权,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问题,又巩固了边防[14]1-15,所以,这一时期泾原地区在这些边将的管理下比较稳定,几乎无战事。美国学者罗文认为这些边将虽无藩镇之名,却行藩镇之实,是按照藩镇体制来运作的[15]384。笔者认为这一论断并不正确,因为宋将刘平在宝元二年(1039)的攻守二策中已经提到:
五代之末,中国多事,四方用兵,惟制西戎,似得长策。于时中国未尝遣一骑一兵,远屯塞上,但任土豪为众所服者,以其州邑就封之。凡征赋所入,得以赡兵养士,由是兵精士勇,将得其人,而无边陲之虞。太祖廓清天下,谓唐末诸侯跋扈难制,削其兵柄,收其赋入。自节度使以下,第其俸禄,或四方有急,则领王师行讨,事已,兵归宿卫,将还本镇。[3]2956
宋廷对这些节度使以下的将领仅“第其俸禄”,一旦有紧急情况,还是“领王师行讨”。大臣丁度也说:“太祖时,疆场之任,不用节将。但审擢材器,丰其廪赐,信其赏罚,方陲辑宁几二十年。”[3]3021由于宋初西北较为平静,朝廷依靠王彦升等边帅足以应对,所以,呈现出这些边帅依旧沿袭唐末五代以来藩镇模式的错觉。实际上咸平以后西北局势对宋廷逐渐趋于不利,朝廷也设置过几次临时大帅进行征讨,足以印证上述刘平所论,而北宋初年诸节镇的实力已无法与唐末五代相轩轾⑤。
随着党项领袖李继迁的崛起,宋廷“西陲”不断遭受侵扰。咸平二年(999),宋廷命“王汉忠为泾、原、邠、宁、灵、环都部署”[12]108,此为泾原路设置之开端,王汉忠成为泾原方面主帅⑥。都部署始于五代,宋初承袭后周依旧设都部署。“宋朝马步军都总管以节度使充,副总管以观察以下充,有止一州者,有数州为一路者,有带两路、三路者。或文臣知州,则管勾军马事。旧相重臣亦为都总管。有禁兵驻泊其地者,冠以驻泊之名。”[13]1781都总管即都部署,“避英宗讳改之”[16]228。太祖时期无行营、驻泊都部署之分,而到太宗时期驻泊都部署出现,真宗时又取消所有行营都部署[17]。都部署司是都部署体制下最高级别的边防统兵机构,本是临战而设的权时差遣,雍熙北伐后在事实上已转变为常设职位,但在制度上仍属于权时差遣,直到咸平五年(1002)情况才发生变化,而都部署体制下的“兵官”,除都部署外,主要有副都部署、都钤辖、部署、钤辖、兵马督监、缘边巡检等[11]196-197。
王汉忠不久后“复出为高阳关都部署,进领威塞军节度”。咸平三年(1000)五月壬辰,“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威塞节度使王汉忠自泾原来朝”[3]1016,这时王汉忠已在泾原,但仍挂之前节度名号,可见他赴任泾原之紧急。随后他“又为泾原、环庆两路都部署兼安抚使”[12]9477,王汉忠作为泾原大帅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稍后王汉忠又镇守河北,徐兴于同年接替王汉忠。王汉忠频繁往复于泾原、河北两地,可以感受到宋初西、北两方同时受敌的巨大边防压力,也可以窥见宋廷欲使泾原都部署路常设化的意向。关于接替王汉忠的徐兴,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他时任“泾原环庆都部署、博州防御使”,而《宋史》本传则称他为“泾、原、环、庆十州部署”[12]9504,但他于九月因运送灵武刍粮被蕃部劫掠,被削籍并流放郢州。[3]1029
咸平四年(1001)“八月辛丑,命兵部尚书张齐贤为泾、原、仪、渭、邠、宁、环、庆、鄜、延、保安、镇戎、清远等州军安抚经略使,知制诰梁颢副之,即日驰骑而往”[3]1068。是年乃宋廷西北重镇灵州陷落之前夜,这时庙堂之上对于灵州的弃守依旧争论不休,但出于事态紧急,宋廷火速任命张齐贤赴任。宋人高承认为这一任命是因为“帝以边将玩寇”,而其结果则是“自此始为边帅也”。[18]308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前面提到王汉忠为泾原路首位大帅,而张齐贤的赴任,则是由于灵州危急,宋廷打算集中节制西北诸路而消灭李继迁。同年十二月,宋廷“以马步军都虞候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环庆路部署张凝副之,入内副都知秦翰为钤辖,领步骑六万以援灵州”[3]1102-1103,实际上这一任命已与张齐贤的任命部分重叠。咸平五年正月,张齐贤又为“邠宁环庆泾原仪渭镇戎军经略使、判邠州。令环庆、泾原两路及永兴军驻泊兵并受齐贤节度”[3]1107-1108,这次任命使得张齐贤所辖防区有所缩小,但还是出现了文臣与武将分权的矛盾⑦。从实际情况来看,张齐贤可能无法节制诸将,所以不久朝廷“改命张齐贤判永兴军府兼马步军部署,罢经略使之职”[3]1112。不过张齐贤此次就任,被认为是文臣以知首州要府身份兼任本辖区都部署制度正式形成的标志[19]196。鉴于这种情况,朝廷于咸平五年又任命王汉忠“为邠宁环庆、仪渭州镇戎军两路都部署,东上閤门使李允正为钤辖,如京副使宋沆为都监,领戍兵二万五千人,委汉忠分道控制”[3]1116-1117。这次朝廷指示“合泾原仪渭、邠宁环庆两路为一界”[12]9340,再次肯定了王汉忠作为泾原路面大帅的地位。五月,由于泾原、环庆两路又增兵八千人,朝廷“召汉忠赴阙,罢两路部署及钤辖之职”[3]1138,泾原都部署路独立设置出来,陈兴为第一任部署,至此泾原都部署路的建置趋于稳定⑧。
综上,北宋泾原都部署路的设置是在唐末五代以来唐关内道以西权力争夺纷繁复杂的背景下设置的,其初步设立的时间可定在咸平初,而自咸平五年后其建置趋于稳定,王汉忠和徐兴可以被认为是泾原地区最早的两位最高军政长官,而陈兴则是泾原都部署路设置稳定后的首位最高军政长官。与唐末五代和北宋中后期相比,宋初西北地区的权力真空给泾原都部署路的设置提供了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但是随着其后宋廷与夏州李氏关系的日益紧张,泾原路都部署路变得难以应对逐渐壮大的党项势力,这就为泾原都部署路向安抚使路转化提供了契机。
注释:
①可参看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八镇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 年第2 辑。李新贵《唐代泾原节度使设置原因考辨》,《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5期。刘锦增《关于唐泾原节度使的几个问题》,《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②《旧唐书》的记载略有不同,然同为一事:“十月,李晟遣兵袭吐蕃之摧沙堡,大破之,焚其归积,斩蕃酋扈屈律设赞等七人,传首京师。”详见(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249页。
③顾祖禹亦指出“原州,唐曰原州,宋因之”,“原州地,后移置渭州于此,宋因之,亦曰平凉军”。参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历代州域形势七》,中华书局,2005年第300页。
④详见《宋史》卷二五〇《王彦升传》,卷二六一《白重赞传》、《张铎传》,卷二七五《谭延美传》,卷三〇七《魏廷式传》。⑤如彰义节度使张铎从官马买卖中获利,并“擅借公帑钱万余缗,侵用官曲六千四百余饼”,事发后,“召归京师,本州械系其子保常及亲吏宋习”。由此可见,宋初开封已对西北地区节度使呈压倒性优势。详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开宝九年冬十月庚子条,中华书局,2004年第377页。
⑥有文章认为张齐贤任“泾、原、仪、渭、邠、宁、环、庆、鄜、延、保安、镇戎、清远等州军安抚经略使”时才具有一方主帅的初步形象。详见贾启红《北宋经略安抚使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7页。实际上王汉忠从咸平二年到五年(999-1002)几度接手泾原(有时含环庆)路,已是近乎常驻并且大权在握,可认为王汉忠此时已经具有一方主帅的形象。
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一,咸平五年春正月丁未条载:“始,张齐贤欲引(曾)致尧自助,致尧谓齐贤曰:‘西兵十万,王超既已都部署矣。公徒领一二朝士往临之,超肯从吾指麾乎?吾能以谋付与超,而有不能自将乎?若不得节度诸将,无补也。’齐贤且告于上,诏经略使得自发诸州驻泊兵而已。”
⑧有学者认为泾原路最初的最高军事长官为泾原仪渭都钤辖,而到真宗晚期时,泾原路才设置部署司,并由都部署兼知渭州。笔者认为这一论断不甚妥当。参见李立《北宋安抚使研究——以陕西河北路为例》,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