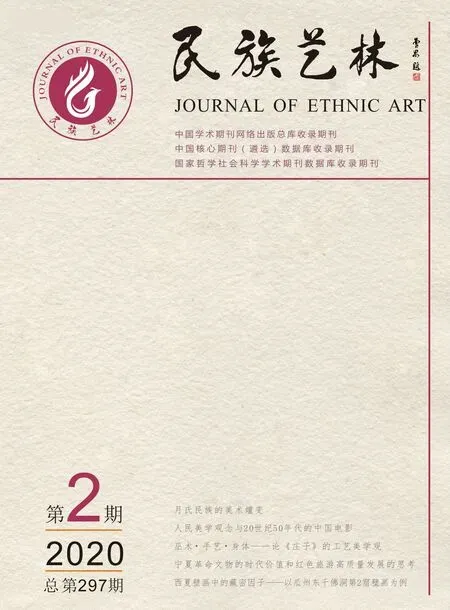电影化过程中昆曲表演假定性的困境
——以舞台版《牡丹亭》和两版电影为例
(北京大学 艺术学院,北京 100089)
一、引言
在戏曲、戏剧、电影等再现艺术中,再现的形象不仅仅是生活中其形态的完全复刻,而要对其作出具有审美价值的改造。改造后的结果又需要令受众“相信”形象的“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假定性是再现艺术的根本要求。因而,从假定性入手,探索戏曲在电影化过程中的得失和困境,是一个自洽的角度。
就戏曲的假定性而言,梅兰芳先生曾表示“(戏曲)动作中有着最宝贵的、最具有生命力的东西。这一切并不仅仅在于假定性。在这一切背后深藏着严肃的戏剧性内容”。梅兰芳先生并不完全赞同以戏剧家梅耶荷德为代表的“戏剧假定性”学说,即是说,梅兰芳先生认为,假定性只是戏曲艺术的冰山一角。诚然,应当明确,本文的研究立场并非将假定性视作戏曲表演与戏曲电影的核心特质,而是选取一个两种艺术形态共同具有的重要特征,以此为参考系,讨论戏曲表演与戏曲电影的异同。
学者对于戏曲和电影的假定性已有了诸多研究成果,但未见对于戏曲和电影假定性的系统梳理,亦未见对具体作品做文本分析,以对比戏曲与电影中假定性差异的讨论。本文将首先探析戏曲和电影中假定性的定义,整合出两者通用的一套假定性概念。其次,以昆曲的舞台表演为基础,探析其中的假定性是如何体现的,具有怎样的特征。随后,将这些假定性段落与电影化后的段落进行对比,分析其中有怎样的变化、形成了怎样的效果。最终,力求为昆曲表演的电影化得出有指导意义的结论。
二、舞台与银幕之间:假定性和《牡丹亭》
戏曲的假定性,是在讨论其虚拟手法时被提出的:“戏曲……它有一种假定性,即和观众达成这样一个默契:把舞台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当作不固定的、自由的、流动的空间和时间……运用自由、富有弹性的舞台空间和时间的含义,完全由作者和演员予以假定——观众也表示赞同和接受。这就是戏曲的虚拟手法的集中表现。”可见,戏曲中的假定性是演员与观众之间达成的一种“契约”,充分作用于时间和空间。
电影假定性是指电影被拍摄对象的非同一性,是电影对现实进行艺术概括的一种方式,也是帮助电影作品达到本质真实、进行典型化的必要手段。与戏曲相比,电影的假定性更强调再现真实与现实之间的差异。
综上,结合“假定性”的词义,对本文中使用的假定性做以下整合归纳:假定性是一种虚拟的手段,一种被观众接受的“契约”,即以非自然状态的艺术形象,指代客观现实。被指代的客观现实既包括形象的状态(如动作、行为、情绪等),也包括形象所处的时空。本文将主要讨论作为一种手段的假定性,即戏曲或电影通过怎样的方式、借助怎样的媒介,完成了为观众接受的虚拟。
《牡丹亭》系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创作的佳作,是最广为人知的昆曲经典作品之一。以《牡丹亭》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昆曲表演电影化过程中的相关变化,是极具代表性的。迄今为止,将《牡丹亭》故事完整搬上电影银幕的作品共四部,其中最为出名的两部分别为:1960年,梅兰芳先生生前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游园惊梦》,以及1986年江苏省昆剧团拍摄的电影《牡丹亭》。这两部电影在昆曲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由于梅兰芳主演的昆曲《牡丹亭》音像资料有限,故本文选取张继青版昆曲《牡丹亭》做研究对象,以保证文本相对的统一性。另外,受到电影《游园惊梦》(1960年)的体量影响,本文仅探讨《牡丹亭》中的“游园”和“惊梦”两折。
三、张继青舞台版《牡丹亭》中的假定性手段
在对张继青1987年剧场版《牡丹亭》的“游园·惊梦”两折做观摩拆解后,发现其中的假定性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类。
(一)语言约定
结合前文讨论的假定性定义:假定性是一种虚拟的手段、一种演员和观众之间达成的“以假代真”的“契约”。在昆曲《牡丹亭》中,有大量的此类“契约”是通过唱词(语言)完成的。
如唱词的第一句——“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既完成了时空(小庭深院)上的假定,又完成了形象(深闺愁春)上的假定。
语言约定这种“契约”的约束力是较弱的:一旦观众无法听懂唱词,假定性便不能成立。亦即是说,这种假定性手段的假定性是很强的:它将不存在的客观现实讲述了出来,依靠观众基于语言的想象,达成假定的“契约”,是一种无中生有。
(二)程式化动作
在假定性一词的原意中,便有“程式化”的意思。程式化,即利用与观众签订的过往“契约”,以某种典型而具有代表性的因子激发观众对于过往“契约”的使用——这个因子,通常是经过提炼而形成程式的动作。
在研究的片段中,有两处较具代表性:
第一,杜丽娘对镜梳妆一处。此处杜丽娘的“三照镜子”,凝聚了观众对于“照镜子”这一动作的长久经验,形成了一个高度程式化的动作。加上镜台的布景,使观众很容易便能够接受“演员在照镜子”这一假定。
第二,杜丽娘进入花园一处。此处,杜丽娘在花园门前的停顿,以及前后的步速,充分调动了观众的既往经验,暗示观众:演员正在进行两个空间之间的调度;加上春香与杜丽娘的两句语言约定——“(春)来此已是花园门首,请小姐进去。/(杜)进得园来,你看”——空间转换的假定最终被确定为“进入花园”。
不难看出,较语言约定,程式化动作的“契约”约束力要更强。它的根基不再是观众对于语言的理解,而是一种更为普世的、关于行为的生活经验。因而,程式化动作的假定性是稍弱的。
另外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由上两例可以发现,程式化动作多需要与其他假定性手段同时出现,以完成精确的假定。第二,演员在表演程式化动作时,时常会使用扇子、水袖等道具,来放大或艺术化程式化动作,这与后文讨论的典型布景应当区分开。
(三)典型布景
典型布景,是一种不依赖演员的假定性手段。观众对其的接受,源于对于客观现实的规律性总结,这是一种接近共识的经验。
在讨论片段中,对于梳妆台的运用最为突出。
“游园”一折起初,梳妆台位于台右,暗示舞台空间为杜丽娘的闺房。行至中段,梳妆台搬到台中,暗示杜丽娘回到闺房。“惊梦”一折中,梳妆台全程在场,暗示表演空间的花园实际是虚假的梦境。
在三种假定性手段中,典型布景的“契约”约束力是最强的。观众最容易接受“梳妆台”对于“闺房空间”的指代。因而,典型布景的假定性是最弱的,它将客观环境中最具代表性的道具摆在那里,就几乎将整个客观环境呈现了出来。
(四)小结
舞台版《牡丹亭》的前两折中,存在的三种假定性手段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以三种假定性手段为结构单位,可以发现舞台版《牡丹亭》的前两折中共有12个假定性段落,如下表所示(为方便后文行文,在提及相关段落时仅标注表中序号):

表1 舞台版《牡丹亭》的假定性手段
从上表可以看出,昆曲表演《牡丹亭》,大量依靠语言约定这种假定性极强的假定性手段。使用频次次之的是程式化动作,最少使用的是假定性最弱的典型布景。从这个意义上说,舞台上呈现的昆曲表演,是一种假定性很强的艺术形式。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对于两部电影的解读将以12个假定性段落为单位,探究两部电影各有哪些假定性手段上的差异,这样的差异形成了怎样的效果,以分析昆曲电影化过程中的得失。
四、1960年版《游园惊梦》:视点干预,造成假定性对冲
诚如导演许珂所言,1960年版的电影《游园惊梦》充分使用了剧情片的拍摄技巧,其中唯有摄影才能赋予、拍摄技巧中最为核心的,就是视点的使用。
从启幕镜头开始,电影镜头就镀上了一层主观的窥探色彩。启幕镜头是一个前推运动镜头,从闺房的窗外推进窗内,具有很强的指示作用,将空间交代了出来。随后的横移镜头补充了环境的特征。随之,又是一个前推镜头,从闺房的深处推到杜丽娘面前。当观众看到杜丽娘的愁容,第一个假定性段落就已经完成了。
与昆曲表演的《牡丹亭》不同,1960版《游园惊梦》中第一个假定性段落不再依靠语言约定,而是凭借典型布景和运动镜头完成。观众本能地跟随运动镜头进行观看,即镜头就是观众的视点,因此,运动镜头直接为观众指明了他们需要观看的内容。观众从窗外看进窗内,再从房间深处看向门厅的杜丽娘,从而接受了时空和形象两项内容的假定性“契约”。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典型布景与舞台呈现有明显不同。电影中的闺房虽然也不是实景,但较单一的梳妆台而言,它更为逼真,其目的是与运动镜头一起,共同为观众签订一项更稳固、假定性更弱的“契约”。具体而言,观众在视点的引导下,不需要再“想象”那是一个闺房,而是直接将布景“错认”为一个闺房。在视点的保护下,观众的观看意识来不及从这种错觉上移开,因而假定性契约也就确定下来。也就是说,《游园惊梦》中的第一个假定性段落,其“契约”更稳固,假定性也削弱了很多。
然而,在杜丽娘随后的唱词中,演员将这个假定性段落的语言约定重复了一遍。这不仅造成了意义的重复,更造成了契约的破裂。第一个假定性段落需要规定观众能接受的假定性强度:观众或是接受电影化后极弱的假定性,或是舞台表演中极强的假定性。但当两者同时出现时,观众迅速感受到其中的差异,并意识到“契约”的存在。因而观众便不再信假作真。这种假定性的对冲,在其他段落中也有体现,比较明显的是第3个段落——杜丽娘梳妆。
在电影《游园惊梦》中,第3个假定性段落是通过一组杜丽娘与镜面的正反打镜头完成的。这组镜头不仅引导观众看到了照镜的杜丽娘,更让观众看到了镜子中的杜丽娘,这是一个极强的“契约”,其假定性是很弱的。同样,演员的语言约定和程式化动作将这一段落重复了一遍。观众迅速意识到,视点中的照镜子并不是真实的动作,而是一种表演,因而造成了些许“矫揉造作”之感。这一段落的电影化也充分暴露了假定性对冲的问题。
然而,电影《游园惊梦》并非只有假定性对冲的弊端,也有诸多镜头填补假定“契约”强度的例子。
例如,在第4个段落,视点从窥探闺房到窥探花园,完成了杜丽娘进园之假定。此处视点的加入,是增强了“契约”的强度。其根本原因在于,舞台呈现中使用的语言约定和程式化动作并不充分地支撑杜丽娘进园的假定,因而视点的补充成了点睛之笔。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第7个段落。电影中将月老改为花神,并且补充了花神的唱词,巩固了“杜丽娘入梦”的“契约”。随后在视点上作的特技处理将该“契约”强化得更加可信。可以看出,上述两个例子都是舞台表演中的假定性存在不足,在电影化过程中,通过视点的介入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补充。
综上所述,在1960年版的电影《游园惊梦》中,对于拍摄技巧的运用,使得镜头成了一个视点。在视点的干预下,虽然形成了一些对于昆曲表演《牡丹亭》中假定性的补充和巩固;但总体来看,视点的干预,造成了电影中假定性的对冲,大量假定性手段表意重复,并且自相消解。
五、1986版《牡丹亭》:作为舞台补充的镜头与“电影感”缺失
与张继青舞台版《牡丹亭》相比,1986年版的电影《牡丹亭》在表演上大部分复刻舞台版;同1960年版一样,改进了布景,使之更为逼真;但与1960年版明显不同的是,该版的镜头更加稳定——仅有推、移两种运动方式,并不具有强烈的主观视点意味。因而,1986年版《牡丹亭》达成了一种类似“舞台记录”的效果。
与舞台版对比,1986年版《牡丹亭》中的12个假定段落,仅有布景和镜头呈现的区别,而前者在上文已有过讨论,故主要探讨本部电影中镜头的运用。总体而言,1986年版《牡丹亭》的镜头运用,主要承担的是说明和强调的客观功能,是对舞台表演的一种补充,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全景与中景的转换,完成对于形象神态和情感的突出。作为两种镜头运动,全景和中景的转换,是对于程式化动作的补充。在舞台表演中,观众只能看到演员全身的动作,这与全景的功能一致;镜头推进成中景,演员的情绪就能为观众所感知。对于电影化的昆曲表演来说,神态和情感不再仅仅依赖语言约定,还可以通过表演展现出来。
第二,蒙太奇剪辑,完成对于舞台表演中非必要时间的剪切。这种镜头运动又分为两种:其一,同场间不同角色的镜头剪辑。例如,在第3个假定段落,春香要站远,为杜丽娘打量全身样貌。在舞台表演中,需要两位演员分别到达合适的位置,才能继续表演,而在电影中,演员走位的时间大大缩短——春香只需走出画框,再另起镜头,便可继续表演。其二,不同场之间的镜头剪辑。例如,在第4个假定段落中,杜丽娘也只需要走出画框,在花园中另起镜头,就能完成“进入花园”的假定动作。这种蒙太奇手法打断舞台表演中时空的连续,但却对其流畅度做了“修饰”。这种“修饰”无关好坏,但无可厚非的是,比起长镜头,蒙太奇更加贴合当今电影观众的审美。
总体而言,1986年版《牡丹亭》中,镜头的运用并未向1960年版那样创造新的假定性表意,也没有造成新的问题。该电影中,镜头的运用尽量维持视点的客观,只是对于舞台假定性的补充和修饰。
然而,如此保守的电影化方式,较1960年版而言,又欠缺了“电影感”。在电影主流审美的考量下,1986年版《牡丹亭》之所以更像“舞台记录”而非电影,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电影观众更加适应那套丰富的镜头使用原则。如本片般客观、冷静的镜头运用,具有很强的解释功能,甚至是装饰的意味。其次,在上一点的基础上,观众很容易意识到镜头中呈现的内容是一种表演。这背后蕴涵着自然主义与假定性的一对矛盾。
在主流电影审美导向下,电影观众希望在客观、冷静的镜头下,看到的是“客观真实”,即一种自然主义倾向。当观众透过镜头,看到的假定性很强的语言约定和程式化动作,他们便迅速意识到那不是“真实”,而是一种舞台表演。总之,从舞台到银幕,观众不能接受的假定性阈值下降了;换句话说,比起戏曲舞台观众,电影能接受的假定性更小。
六、结语:戏曲艺术电影化之困与之思
回顾关于昆曲《牡丹亭》的两部电影作品的讨论,可以发现戏曲的电影化,会在假定性层面遇到系统性的困难:
首先,戏曲电影化时遇到的是“电影感”的问题。为在主流电影审美下看起来像是电影,必定要使用多样的拍摄手段(1960年《游园惊梦》),如此一来,将造成假定性的对冲,使得大量假定性手段表意重复,并且自相消解。若是在“电影感”上作出让步,使用较为简单和客观的镜头语言,一方面,作品会呈现为“舞台记录”般的说明样貌;另一方面,作品将触及戏曲和电影观众关于假定性的根本问题——后者比前者能接受的假定性更低。因而,在“电影感”上作出让步的电影化作品也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然而,纵使存在上述系统性问题,也并不意味着戏曲电影化是不可能成功的。笔者特在以下三个方面作了思考。
第一,从讨论中可以发现,戏曲的电影化过程中,有着一些实例,说明了戏曲的电影化能补充舞台表演上假定性手段的不足。例如1960年《游园惊梦》中的杜丽娘入梦,以及1986年《牡丹亭》中的中景镜头。这些实例说明,戏曲的电影化并非全然灾难,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注意和挖掘的裨益。
第二,诚如梅兰芳先生所说,假定性只是解读戏曲的一个很小的侧面。悲观而言,纵使假定性层面的系统性矛盾不能得到解决,戏曲的电影化,也或许能在其他更为重要的维度上得到补充和提升。
第三,本次讨论,是在当下主流电影审美的标准下进行的。一方面,主流电影审美在不断变化,关于假定性的系统性矛盾或许在审美标准的变动中会自消解,身为学者或行业实践工作者,我们应保持乐观的态度;另一方面,针对戏曲电影、而区别于其他主流电影的美学标准也值得重视。一些学者已对“戏曲电影美学”进行了讨论,但尚未见成体系的梳理。完善戏曲电影美学理论,应是解决戏曲电影化困境的重要方向。
——马鞍山市博物馆馆藏契约展
——并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