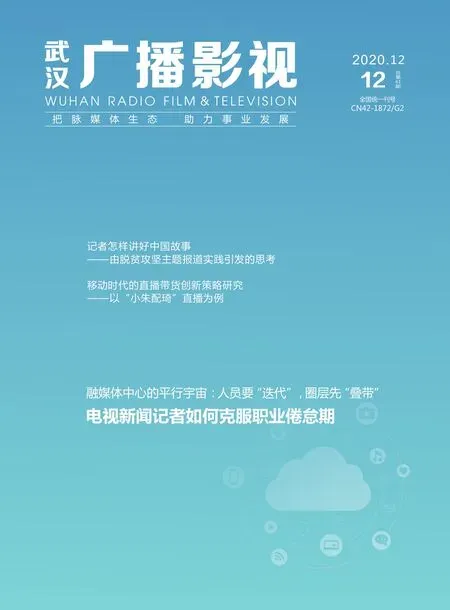灾难影像书写的哲学思考
——以纪录片《2020春天纪事》为例
王光艳
2019年底,一场疫情不期而至。新冠肺炎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一场全球性大流行病,对全世界是一次严重危机和严峻考验。
作为最先遭遇疫情并率先迎战的国家,中国果断打响了疫情防控阻击战,武汉是这场战争的重中之重。中国以坚定果敢的勇气和决心,以武汉为主战场,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果断封城抗疫,阻断疫情蔓延,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1]。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抗疫斗争中,一批纪录片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记录了武汉抗疫过程中的人和事,还原了抗疫的艰难过程,显耀着人性的光辉,也激发了人们对灾难的反思。
一、历史与现实:天人关系的反思与重构
新冠肺炎是疫病,而且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全球流行的疫病,类似的疾病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世界各国应当携手战疫,共克时艰,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尽快展开疫后重建,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另一方面,人类还应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深刻反思人与疫病之间的关系。

1、历时共生的博弈
人类与疫病斗争的历史非常悠久,人类与疫病相伴而生。关于疫病的记载很早就有,甲骨文中的“疾年”就是疫病流行之年。春秋战国时期赵国和秦国等地多次发生大疫[2]。从历史记载来看,几乎每隔数年,就会出现一次疫病流行。这些疫病流行的范围、造成的影响或大或小,但最终都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销声匿迹。从历时性来看,疫病就是人类与病毒(或细菌)之间共生的博弈。
作为一部反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纪录片,《2020春天纪事》首先要承担的是历史责任或者说历史使命就是揭示疫情中凸显出来的天人关系哲学思考,因此,纪录片的开篇就以历史的眼光,点明了人与病毒之间历时共生的关系:
2020年1月7日晚,中国科学家通过透射电子显微镜在寻找。此时,一种未知的病毒已经悄然来临。在人类与病毒交锋的历史中,这将是又一个影响深远的时刻。
病毒,地球上已知的最小的微生物,已经存在了亿万年。空气、土壤、海洋里,它无处不在,病毒的演化,孕育和影响着世间万物乃至人类。病毒创造,病毒也破坏,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完全了解病毒的奥秘,也无法预知病毒何时会再次改变我们的生活。
这一段富有哲理的解说阐述了一个道理:人类与病毒是历时共生、相伴相随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类与病毒共同生活在地球上,须臾不可分离。有研究表明,正是因为包括病毒在内的微生物的存在,人类的进化才成为可能。当然,人类真正认识病毒的时间并不长,影片通过介绍人类认识病毒的过程,点明“人类对病毒的认识还不到两百年”的事实,充分说明了人类对病毒的认识还相当有限。共同生活、互相影响,“人”与包括病毒在内的自然或“天”密不可分。这不禁让人想到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之一,也是历代哲学家孜孜以求的话题。关于天人关系有几个突出的观点:“顺天而无为”(老子)、“顺天而有为”(孔子)、“制天而用之”(荀子)、“天人感应,天人合一”(董仲舒)、“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彭富春教授对儒道禅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新的中国智慧将是古老的儒道禅思想在当今时代的新生,这种智慧“就天人关系而言,它主张天人共生”[3]。
天人共生的哲学思想充分尊重了“天”与“人”的个性,“天”与“人”的关系绝不是“人胜天”、“天胜人”或“天人相分”,而是以某种方式共同生活在一起。天人共生客观上要求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并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系列纪录片《2020春天纪事》的价值在于认识到天人共生的现实,并细致入微地讲述了中国科学家从病毒病原学、流行病学、临床救治、疫苗研发等方面对新型病毒的探索、研究与应对,通过历史的回顾和今天的发现,以大量的科学知识和鲜活的实例,揭示了病毒与人类的关系,思考面对病毒侵袭的应对之道。

从历时性来看,病毒与人类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彼此共生。如果说自然界就是所谓的“天”的话,这个“天”显然包括病毒在内。疫情暴发就是天人关系失调,人与病毒之间的生存平衡被打破,抗疫就是关乎天人关系的博弈。
从抗疫来看,新冠病毒是人类的敌人,人类与病毒之间的博弈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可以预料的结果就是战争的结果必然是达到一种新的平衡,而不是灭绝某一方,也就是历时共生的博弈关系。
“正常的灾难意识,其实正是生命意识,而生命意识的本质则是敬畏”[4],认识到了人类与病毒之间的历时共生关系,接下来,我们的抗疫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认识病毒、改造病毒,并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那种所谓的灭绝新冠肺炎病毒的想法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取的。同样,新冠肺炎病毒也不可能完全杀死宿主——人类。
2、共时隐形的战争
疫情暴发,人与新冠病毒之间的战争打响。这种战争具有共时性,也就是在同一时空里,人与病毒相互搏杀。战争是残酷而冰冷无情的,更为可怕的是,病毒很小,人类肉眼根本看不见它。在疫情暴发的初期,人们甚至不知道疫情为何突然发生,患者该如何救治。
这究竟是什么病毒?它的传播规律是什么?究竟该如何控制住疫情?……一连串的问题考验着人类。随着疫情的扩散,众多的医护工作者投入防治一线,大量的社区工作者投身防控一线,更有优秀的科学家立刻参与科研一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
2020年1月2日,中国科研人员拿到采样。在分离出新冠病毒后,细胞生物学科研人员朱娜说:“终于抓到你了!”[5]1月3日晚11点半完成了病毒的基因测序工作,得出了全基因组序列,这是中国确定病原的第一个里程碑。
影像客观记录了科研人员分离出病毒时的喜悦情态,也展示了他们寻找病毒的艰辛。在这场没有硝烟甚至看不见对手的战场上,人与病毒之间战争的残酷性可见一斑。影片通过这一过程的共时记录呈现了人类认识隐形对手的第一步,也是至为关键的一步。1月7日,中国科研人员以令世界称赞的速度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毒株,找到了致病“凶手”并公开研究成果,这让全球科学抗疫成为了可能。
客观记录并呈现“抓”新冠病毒的过程,最让人揪心的医院挤兑画面并没有在影片中出现,但是,隐形的病毒始终牵扯着观众的心。当影片呈现出病毒被锁定的那一刻,通过特殊摄像,病毒原形毕露,为了这一刻,科学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当时我们心里边也有点打鼓,因为按照我们平时积累的经验来说,从这种临床样本中能够拿到全基因组,其实是很困难的。”[6]
从与病毒赛跑的人群来说,除了患者、医护工作者、科研工作者外,还有这一群纪录者,他们都是共时隐形战争上的突击队。纪录片《2020春天纪事》的拍摄与人类抗疫过程同步。面对人眼无法直接看到、摄像机无法直接拍到的病毒,摄制人员冒着极大的风险,克服了重重困难,才完成了影片。

微纪录片《2020武汉樱花:久违盛放 不负春光》(导演:喆FILM)则通过拍摄疫情期间武汉樱花绽放,但是无人赏景的场景拍摄,通过大美春光反衬出疫战的残酷,“你和我说过,春暖花开时我们再相聚,最浪漫的事就是在樱花树下,看到你摘下口罩的模样。”[7]
社会学家孙本文先生在分析文化传播过程时,把文化传播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的文化传播,一种是有组织的传播[8]。拍摄纪录片显然就是有组织的传播行为,这种传播具有目的性、计划性、组织性和步骤性,它不仅要记录战争的过程,揭示隐形战争的残酷,还要完成纪录片价值的建构。
记录的价值在于共时记忆的分享,纪录片所记录和承载的人与病毒的战争固然有多种表达方式,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种隐形的战争将持续,并有可能伴随人类直到永远。因此,人与病毒之间的共时隐形战争并不可怕,它需要我们保持足够的理性。
3、科学理性的重拾
“灾难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只有认识它,而不能控制灾难的发生。它往往难以预测,即使在爆发前有些丝的预警,但也不能改变它发生的必然性”[9]。从唯物辩证法来看,灾害暴发具有客观性,这就决定了人类首先应该建立起认识灾害的科学态度。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人类完全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与新冠病毒的战斗,终极解决方案就是科学理性地认识它,并寻求与之共生的途径和方法。
灾害“对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有着极大的破坏性,每次不经意的发生,就会夺取无数条鲜活的生命,给人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等造成重大的影响和冲击,改变了个人的生活状态。”[10]反思中国抗疫过程,在疫情面前,盲目恐慌毫无意义,也显得幼稚可笑。回归理性,回归科学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看似不经意,其实背后一定有其客观原因,因此,纪录片《2020春天纪事》就带着辩证思维,跟踪拍摄了科研人员四处寻找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蝙蝠的故事。
辩证思维就是基于现实问题出发,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反思活动。因此,分离出病毒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后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就包括寻找病毒的来源、流行病学调查以及病毒的特性研究等等。

病毒的特性和传播性是怎样的?如何控制疫情的态势?新型病毒的致病机理是什么?为何同为冠状病毒,临床表现却与SARS和MERS不同?该如何进行科学救治?……一连串的谜题等待着科研人员去破解。
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向全国蔓延,每天新增的病例都在刷新着记录,也在考验着人们敏感的神经。此时,科学理性地看待疫情显得格外重要。2020年1月19日,有武汉旅行史的深圳患者一家人被确诊,很快,没有去过武汉的一名家庭成员也出现相似的症状。钟南山院士说:“作为一个临床医生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表明它会产生很严重的疫情。”他和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判定:“肯定存在人传人。”这种科学理性的判断为中国抗疫提供了制订一连串应对措施的根本指针。
在病毒疯狂扩散的同时,而中国的科研人员逆行向前,一个一个攻关,拿出了中国方案。一套、二套、三套……直到第八套中西医相结合的诊疗方案,这也表明中国科研人员、医务人员对病毒的认识不断在突破。《2020春天纪事》的这段记录不仅再现了疫情调查的全过程,更展示了以钟南山院士为代表的科学家严谨求实的态度,体现了科学理性在抗疫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任何纪录片,不管其目的如何,都是倾向于表现现实的”[11],在表现现实的过程中,纪录片的创作者应当保持足够的科学和理性,《2020春天纪事》记录了不同的人对待生命的不同态度,这是客观现实,也是科学理性的。这提示我们,科学理性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科技的工具理性的反思逐渐加深,特别是对人类命运前途的忧虑,大量的灾难电影被拍摄出来,成为当今世界电影的一大奇观。这些电影表现灾难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是都有一个对人类命运前途担忧的宏大主题,“它的积极作用在于把人类从‘自我’中心主义的自大自恋中唤醒,回到‘认识自我’的轨道上,恰当地确立我们在这个尚属未知和神秘的宇宙自然中的位置,认识到人类仅仅是这个世界的平等一员,甚至只是‘沧海一粟’,并不是自然界的主宰,也不可能征服自然”[12]。抗疫纪录片《2020春天纪事》同样带着对天人关系的理性反思和对人类命运前途的关注。
二、生命与人性:生命价值的体认与放大
价值问题历来是哲学所关注的重点,不同的人对价值有不同的看法。综合国内外学者对价值的讨论,有学者认为“价值是主体与对象关系的中间质,它能满足主体的欲望并被主体的意识所觉察”[13]。由此可知,价值是一种中间状态,它的主体是人,且必须满足人的欲望。灾难影像的价值也具备同样的特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生命和人性,相信最终会对生命的价值产生新的认识。思考生命的价值应该成为灾难影像的责任。
1、重新认识生命
在灾难面前,最宝贵的是生命,没有生命,一切都没有价值。价值是联系主体与对象的中间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录片的价值也要体现在纪录片所记录的内容与受众的感受之中。
《2020春天纪事》成功地记录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发展的情况,而且通过对普通市民,特别是患者与家属之间生活的记录,立体地呈现出在灾难面前复杂的生命情态。正如第三集开篇所说的那样:
这个故事关于一座城市,也关于这座城市里的一些人。
(现场音)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可能这辈子再见不到这个人了,感觉是一个特别痛苦的抉择。
这样的开篇意味着这一集讲的就是普通人的故事。在新冠疫情的阴影下,关于生命似乎很直接地与“生离死别”联系上了。在这一集里面先后讲述了参与医疗救治的护士胡雪珺、一家三口人感染新冠肺炎的阿念、社区工作人员黄恒和丰枫、志愿者李小熊等人的故事,他们都是生活在疫情中的普通武汉人。他们勇敢地站出来,接受疫情考验,主动服务社会,也面临着随时都有可能被感染的风险。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2020春天纪事》通过记录这样一批普通人的抗疫生活,其实是在提示我们应重新认识生命。生命如此脆弱,以至于阿念在获知89岁的外婆感染了新冠肺炎后绝食求死的时候,蹲在地上嚎啕大哭。生命又如此坚韧,志愿者李小熊的爸爸妈妈都感染了新冠肺炎,处在生命的危急关口。当她得知自己因做志愿者而感染新冠肺炎时,坦然地说“一点都不后悔”。这些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场景和真实的叙事撼动了无数观众的心。
巴赞宣扬关于真实的导向性原则有三个:表现对象的真实、时间空间的真实和叙事结构的真实[14]。这是他从摄影影像本体论出发对现实主义电影审美的要求。记录真实的生命过程,让观众在“窥视”他者生活的同时有所体悟有所反思就是纪录片的价值。重新认识生命关键在于: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如何让生命有价值?如何让生命的价值得以弘扬?
2、记录人性光辉
当下,我们的手机也能拍摄出画质不错的影像,能记录下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一切。置身于近百年来人类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之中,每个人都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心态也会随着疫情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疫情期间,很多人通过手机拍摄并发布纪录短片,这些短片在朋友圈里被转发和观看。那么,作为专业的纪录片创作者,究竟该记录些什么呢?
那种纯自然、流水账式的纪录影像并不具有很大的价值。纪录片绝不是纯自然记录,而是在确保真实性的前提下,讲好创作者眼中的故事。价值的主体是人,纪录片的价值在拍摄之初就被“人”锁定。
纪录片《2020春天纪事》较好地把握住了“人”,围绕疫情中的“人”展开记录。整个摄制团队近50人,他们在疫情一线连续拍摄80多天,以坚持理性,不失悲悯的创作态度,记录下了人们求生的努力以及在灾难面前善良与爱的力量。
事实上,在灾难面前,靠打“悲情牌”“惊悚牌”走红网络的记录者不乏其人。可是,悲情并不能解决掉人类所遭受的苦难,更不利于人类战胜困难,因此,灾难纪录片的价值并不能集中于记录苦难,而应记录人类在灾难面前的抗争,从而展示出人性的光辉。
从历史来看,中国历来就有以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论”、以荀子为代表的“性恶论”和以告子为代表的“性不善不恶论”三种人性理论,这些理论都有其特定的产生背景和独特价值。无论是哪一种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希望修养完善人性。换句话说,就是都崇尚人性美,不管这种美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
人性美是对人的本性的赞美和歌颂。人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质,既有自然的属性,又有社会的属性,因此对人性美历来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只有不断地完善自我的人性,人性美才能得到充分实现和肯定。《2020春天纪事》通过记录,立体地存留了一份社会各界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宏伟画卷,多侧面展现了人性美,揭示了人性的光辉,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3、放大社会效应
在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特大灾难面前,个体的命运与经历无疑具有标本价值,能够折射出灾难的某些细节。可是,群体抗争更具有价值,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先声,也体现了人类共同克难攻坚的智慧。
《2020春天纪事》以铁的事实说明,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能独善其身,全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15]。
纪录片除了真实记录事件外,还具有放大社会效应的作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流行于网络的各种声音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浪潮,其中夹杂着诸多的对中国的误解甚至偏见。中国纪录片人有责任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还给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从而消除世界对中国的误解。
《2020春天纪事》既是重大事件中不可缺席的见证者,在突发公共事件体现中国电视纪录人的参与和责任担当,又是突发事件中的信任构建者,以纪录者第一视角深度呈现中国“战疫”主题,用事实展现中国在疫情防控中的积极作为和进展成效;既有国家视野的宏大叙事,也有见功力的小中见大,深入浅出,准确把艰涩医学科研内容转化为动人心魄的故事,把对生命的关照拓展宽度,把中国人抗疫的故事升华为全人类在大灾难的考验下捍卫生命的史诗,真实、平实,却感动山河、感动世界。

可以说,《2020春天纪事》以影像纪录的方式将中国抗疫实践经验传递给了当代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为世界各国抗击疫情提供了一份鲜活的解决方案,也为今天和未来,留下了一部中华民族应对灾难的弥足珍贵的影像样本,成为科学“战疫”国家级珍贵影像志。
一部优秀的纪录片要展示的不仅仅是一个好的故事,更要揭示故事背后的哲学话语。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哲学就是心的耕种”[16],从哲学意义上说,纪录片就是在观众心田上播种。系列纪录片《2020春天纪事》没有延续主流纪录片宏大叙事的风格,相反,它通过精心选择的一个个小故事,记录了寻找病毒、医疗救助、心理援助、社会互助等多个方面的抗疫过程,展现了众多普通人在疫情中的生存状态,揭示了现实的残酷与温暖。这种来自于生活本身、充满质感的故事给观众造成的冲击和心灵的洗礼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艰苦历程酿造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2020春天纪事》通过影像记录成功地实现了“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目标,使人们对抗疫的过程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也提供了一个反思灾难的哲学向度。“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17],灾难影像书写应当自觉成为哲学表达的一部分,成为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一道门径。
注释:
[1]王光艳在《疫情防控背景下的武汉抗疫阶段研究》(发表于《武汉广播影视》2020年第8期)一文中,将武汉抗疫分为三个阶段:遭遇战(2019年12月27日-2020年1月23)、阻击战(2020年1月23日-2020年4月8日)、决战决胜(2020年4月8日-2020年6月2日)。
[2]张剑光:《中国抗疫简史》,新华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3]彭富春:《论儒道禅》,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第14页。
[4]何东平:《灾难的影像与反思》,《南风窗》(双周刊)2008年第12期。
[5]纪录片《2020春天纪事(1)》,CCTV.节目官网https://tv.cctv.com/2020/09/09/VIDERwrTu0zIPaKeHgknh rqI200909.shtml?spm=C55924871139.PT8hUEEDkoTi.0.0
[6]纪录片《2020春天纪事(1)》,CCTV.节目官网https://tv.cctv.com/2020/09/09/VIDERwrTu0zIPaKeHgknh rqI200909.shtml?spm=C55924871139.PT8hUEEDkoTi.0.0
[7]微纪录片《2020 武汉樱花 久违盛放 不负春光》,BILIBILI网站.
[8]杨善民、韩铎:《文化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89页。
[9]赵海艳:《影像中的灾难、死亡与生命——罗兰·艾默里奇灾难片分析》,《中国报业》2012年4月下。
[10]赵海艳:《影像中的灾难、死亡与生命——罗兰·艾默里奇灾难片分析》,《中国报业》2012年4月下。
[11][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10月第255页。
[12]王小平:《后现代“灾难电影”的叙事策略——评近年来灾难片的影像书写》,《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10月。
[13]杨善民、韩铎:《文化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61页。
[14][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8月,第005页。
[15]习近平:《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求是》2020第8期。
[16]杨善民、韩铎:《文化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5页。
[17]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