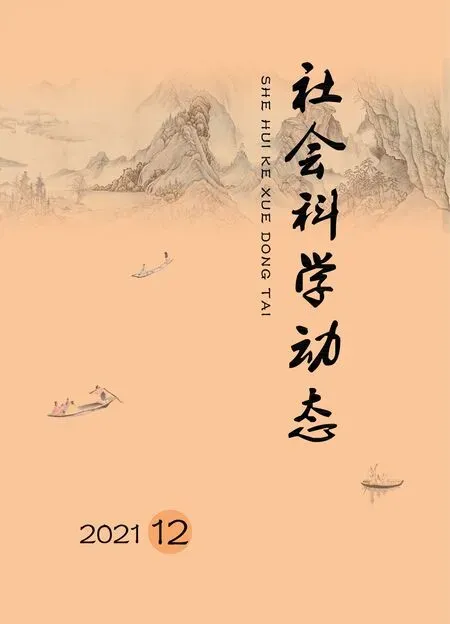论艾丽斯·扬对当代西方流行的正义理论的批判
殷张晴
艾丽斯·扬是当代西方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她倡导多元文化和差异政治,通过对当代流行的正义理论的系统考察,形成了以差异为核心的正义理论。本文拟通过分析艾丽斯·扬对当代西方流行的正义理论的批判,阐明其差异正义理论建构的逻辑与当代价值。
艾丽斯·扬对流行的正义理论的批判主要表现在:(1)对流行的正义理论所认为的社会正义即分配正义的批判,这是其批判的出发点;(2)对流行的正义理论的逻辑根基——同一性逻辑的批判,这是其批判的核心;(3)对基于流行的正义理论所建构的各种政治理想的批判,这是其批判的落脚点。
一、对流行的正义理论中分配范式的批判
“分配正义”的概念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旨在将社会资源按照道德功绩(moral merit)的比例分配①。密尔之后,流行的正义理论将社会正义与分配正义视为同延的概念,这构成了当代分配范式的特征②。扬认为,这一特征意味着将社会正义简化成分配问题,而这种简化存在两个关键错误:其一是对制度语境的遮蔽与预设;其二是对分配概念的过度扩张。
就第一个方面来看,将有关社会正义的讨论集中在有形之物,不仅忽略了社会结构和制度语境,而且还常常预设了决定物品分配的制度语境。扬认为,在当代西方社会,有关正义问题的公众活动并非都指向物质资料的分配,也有许多指向权力归属和决策过程的正义。如果仅从分配角度理解社会正义,将会忽略权利归属和决策过程,忽略影响人们参与决策的能力及其实现自身潜能的关键制度因素,从而将制度语境的含义和范围缩小在一个静态的平面中,形成对制度语境的遮蔽。此外,许多政治理论家还常常预设某种制度语境,例如,理所当然地设立拥有征税权利的现代国家机构,却并没有对这些制度结构是否正义加以考察。
因此,杨认同沃尔泽的观点:“正义应该关注分配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而非分配本身。”③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民主决策作为社会正义必不可少的组成成分和前提条件,它不仅涉及决策者的权利与自由,而且需要依赖相应的社会机构和过程,而这些问题并不能被简化为分配问题。二是劳动分工的问题,它涉及一些非分配问题。例如对职业本身的定义,女性主义者质疑分配范式下将工作划分为工具性的或情感性的,会对女性的工种选择产生压迫。三是文化的问题。文化的范围最为广泛和复杂,以文化帝国主义为例,它将占宰制地位的群体的经验和文化予以普遍化和标准化,从而在其主导意识下,将处于标准外的差异群体视为“他者”,由此产生了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歧视、边缘化等。这诸多问题也不能简单化为分配问题来阐释和解决。
就第二个方面来说,扬认为将分配的概念延伸至非物质之物的错误在于没有意识到分配范式具有有限的适用范围。比如自尊,虽然对于物质资料的占有构成了自尊的重要条件,但并非全部前提。自尊涉及许多非物质条件,并植根于个体行动的关系和过程中,无法简单地从分配中获取。比如权利,罗尔斯将正义视为在社会基本体制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方法,但扬认为,这扭曲了权利的概念,至少暗示了权利是个人可以占有的物品而非关系,且暗示着权利将像财富那样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此外,对权利的分配具有原子化的倾向,即将权利化为二阶的关系——统治者和臣民的模式,着重关注了权利的拥有者及其作用的对象,忽视第三方的支持或中介作用。例如,虽然法官对于犯人拥有审判权,但这一权利的运作需要基于由狱警、记录员、律师等角色组成的关系网。
此外,将分配的概念错误地延伸至非物质之物还会产生一些消极后果。首先,一切可识别的东西都将纳入分配概念的范围之中,自尊、权力、机会等也将被错误地分配,从而将这些概念所依附的上层建筑“物化”——主要指社会关系和制度规则的“物化”。其次,为了与“物化”的社会相适应,杨认为,过度的延伸还将正义转变为对个人之间物品的分配,在分析层面上将个体与物品分离,个体成为逻辑上先于社会关系和制度的原子④。这种原子论观点的错误在于未能理解个体是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的产物。个体不仅不能独立于社会过程之外,且只能与社会紧密关联。因此,社会正义的分配绝非是将物品分配给独立于社会过程中的个体。
基于分配范式对社会过程的忽略和对个体的原子化,对正义的讨论变成了对个体所占有的物品份额的比较,这暗含了一种静态的社会形而上学。扬借用罗伯特·诺齐克的话说:“这种静态的正义观是非历史的。”⑤一方面,不基于社会过程讨论正义与分配,所分配的物品似乎是凭空出现的;另一方面,它预设了个体先天地具有了物品占有权,并且可以自由交易,如此一来,从分配的结果讨论社会正义也将变得毫无意义且自相矛盾。这种资格理论(entitlement theory)反映了一种占有性个人主义的社会形而上学⑥。
扬认为,静态的社会形而上学关键的错误在于忽略了社会过程。因为,个体作为一个有目的的行动者优先于作为一个物品的占有者,个体的行动永远是在关系中进行。一方面,个体的行动在所处的制度和结构下产生;另一方面,众多个体的行动的集合又将影响结构性的再生产。因此,扬认为只有通过关注过程,才能理清社会结构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同时,关注过程并不意味着对结果的漠视,在此,扬反驳了诺齐克的观点——最终状态模式与正义无关⑦。扬认为,如果某种分配的结果造成了对他人的宰制或压迫,那么无论其过程是如何“合理的”,都必须对其提出质疑。例如,如今大部分国家都实行男女平等的政策,国家和个人也注重女性教育和培养,越来越多女性的素质和能力并不亚于男性,但在实际结果上,高层岗位上的男女比例分配依然重男轻女。所以问题是,为何我们努力地改变男女的不平等,不平等现象却依然普遍存在?扬认为,这正是由于分配范式所暗含的原子化、静态的社会形而上学强化了压迫等非正义现象,因此我们必须对生产和再生产这一分配模式的社会过程进行重新界定,包括规则、交往、态度和政策等构成因素。
当然,扬并不是完全反对分配范式,而是主张将分配的概念限制在物品、金钱、自然资源等物质资料中。她认为正义的概念应该扩展至与政治的概念重合,因此,正义的范围要比分配宽泛,且一个充分的正义概念,应该是基于社会过程的动态图式⑧。为此,扬主张转换正义的视角,即从传统的分配范式转为基于社会制度规则和社会关系的社会正义,将宰制与压迫作为讨论社会正义的出发点。宰制即对个人自我决定的制度约束,压迫即对个人自我发展的制度约束⑨。二者作为不正义的社会条件,常常交叠在一起影响个体的发展,阻碍个体实现自身潜能与表达自我需要。因此,社会正义意味着消除制度性的宰制和压迫。
二、对流行的正义理论之同一性逻辑的批判
后现代主义者将否认、压制差异的逻辑称之为同一性逻辑,并认为整个西方流行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都被同一性逻辑所统摄。同一性逻辑的特征是对理性与同一的强调,通过对实体的概念化,将万物做同一思考并纳入到一个整体当中,在这个过程中相似性化为同一性,差异性被否认、排除在整体之外,形成了理性与情感、客体与主体、描述与评价等概念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
扬认同后现代主义者对同一性逻辑的批判,并进一步指出同一性逻辑在正义理论中的错误。首先,同一性逻辑预设了与被同化事物相对立的事物,将差异定义为绝对的他者。多元化时代,扬认识到差异对于正义理论的重要性,它是追求权利平等、文化承认、自由民主、人的解放的必要条件。扬认为,任何事物既不是一致的也不是相互对立的,只有在差异性中才能发现相似性;相似性并非同一性,如果将相似性还原为同一性,实际上是将单纯的差别转换为了绝对的他者,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二元对立而非同一。在扬的理论中,差异是一种关系性的、结构性的差异,而非本质化的实体性的差异;差异应该被正确认识,并在实践中尊重差异而不是被遮蔽或者消除。
其次,同一性逻辑高举理性,用思考客体的一律性方式思考主体,用普遍理性的标准界定主体的多元性,从而否定了感性的个别经验,否定了主体之间的差别,更否认了主客体之间的区别。通过同一性逻辑,思想欲掌握所有的实在(the real),消除不确定性和差异性。在此逻辑下形成的各种规则和政治理想的特征都是不偏不倚、非人格性的,必然忽略、边缘化某些弱势群体,形成新的宰制与压迫。
具体而言,同一性逻辑的问题在于由其统摄而形成的道德理想范式——公正理想和市民公共理想——展现出诸多不合理和不正义。
作为对差异之否定的公正理想,其所追求的普世化、客观化的结果体现的正是同一性逻辑。一则,为了追求公正性,道德理性要求道德判断保持客观中立,为此,以理性为标准,情感成为理性的对立面,与情感密切关联的范畴如欲望、关怀、归属感等都被排斥在普世化标准之外。然而,情感等并不会因为被排斥在普世化标准之外就不发挥作用,甚至与正义无关,也没有人能够完全非人格化、无情感、独立于具体语境之外。二则,为了追求这种道德观,同一性逻辑诉诸对道德理性所反映的所有情景的所有个别化加以抽象,实现对具体的主体的社会性或关系性的抽象化,由此形成超然、客观、中立的道德判断者。
扬认为,这样形成的公正理性人也将是无感情的超验主体,并将以三种方式压制差异:一是为了使规则具有公正性和普适性,其推行的将是高度抽象化的规则,忽略主体的个别性和特殊性,根据统一规则处理所有情境,从而否认情境的个别性;二是为了达到理性、客观的目的,规则中将排除情感等相关因素,消除以情感形式呈现的异质性;三是道德主体为了适应乃至迎合抽象化、普世化的规则将逐渐抛弃自我的个别性,从而将道德主体的多元性还原为独一的主体性⑩。扬认为,第三点是最具“欺骗性”的方式,它甚至影响了那些坚持道德主体多元性的学者。以罗尔斯为例,他虽然前置了自我的多元性让所有个体进行讨论,然而“无知之幕”下依然移除了所有个体之间的差异,并保证所有个体从统一假设出发,在同一普世观念下博弈;如果按照罗尔斯的假设——原初状态下所有个体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将对主体彼此之间的利益表达产生消极影响。
此外,公正理想所追求的公正性不仅是不可能的,相反,对公正理想的追求还会产生消极的意识形态后果。例如,公正理想所追求的普世化、客观化规则使科层制权威和等级化的决策过程合法化了。科层制作为新形式的宰制使公共生活逐渐被少数特权者和专家掌控,这就阻碍了民主决策的要求,使少数特权群体的观点普世化并强加于其他群体,其结果必然是一部分群体被排斥或被压迫。同时,科层制上层为了赢得下层的支持,将制定更多详细的规则管理下层人民,科层制上层者的主观意识将不可避免地通过这些规则施加给下层人民,将宰制的范围从公共领域扩展到日常生活的私人领域,使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渐趋向普世化、标准化。
在同一性逻辑统摄下,与私人领域相联系的市民社会也存在诸多不正义。受传统理性哲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影响,市民社会也将与情感密切关联的人视为他者排除在外,特别是女性,因为她们被视为是情感、欲望和身体的看护者。基于此,女人被认为是欲望的、异质的、不理性且易堕落的,一个体面的女人应该是纯洁、忠贞、温和且整洁的;而男人则是理性、力量、太阳的代表,一个体面的男人应该是理性、克制、不屈服于激情与欲念的。从这些定义中显然可以看到严重的性别压迫。
大部分女性主义者认为,传统理性哲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暗含着一种价值等级观念和统治逻辑,加剧了女性在公共社会和家庭领域中所遭受的压迫,使女性被排除于公共领域之外,而限制在私人领域中,从而维护了父权制统治⑪。例如,(1)基于价值二元对立,女性被认为是情绪的、主观的,男性被认为是理性的、客观的;(2)基于价值等级逻辑,被认为是情绪的、主观的东西的价值要比被认为是理性的、客观的东西的价值低,因此,男性的价值高于女性的价值;(3)基于统治逻辑,男性统治女性在道德上是正当的。
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扬认同上述观点。扬坚持“个人即政治”的原则,拒绝将女性及其相关的讨论限定在私人领域。然而,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已有300余年,主流规范仍将那些人尽皆知且与女性密切相关的活动,例如,月经、哺乳、堕胎等限定在私人领域讨论与解决,尽可能地阻止这些问题的探讨进入公共视野。扬认为,不应该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对立且将私人领域视为公共领域的排斥物,而应该对公与私及其二者的关系重新概念化,从而告别自启蒙时代以来的公私对立传统;“私”并不意味着他者地位,也不能被公共制度排斥,它将是个人选择从公共领域中撤出的领域。
基于上述讨论,扬认为对于正义的探讨并不能站在个人需求、欲望与情感的对立面,而是应该探求使个人需求与欲望得到满足的制度条件,因此需要重申差异的概念,肯定差异性的公共生活原则,使个人需求可以在异质性公共空间中得以表达。扬的异质性公共空间为我们提供了两条政治原则:第一,任何人、任何人的各个方面、各种行为都不能被“私”化;第二,任何有关社会制度和实践的探讨都不能被先验地排除在公共讨论和相关主体之外⑫。然而,扬认为当代流行的各种政治理想并没有很好地尊重差异,践行这两条原则,从而偏离了正义理想。
三、对同化主义、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理想的批判
自启蒙运动以来,社会解放运动致力于追求自由与平等,反对等级特权和实现政治平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也为近现代的政治运动描绘了蓝图和指明了方向。然而,法律所赋予的政治平等并没有彻底地消灭宰制和压迫,诸多的不正义依旧存在于社会语境和文化意识中。扬认为,曾经那些反对差别特权的政治运动如今对于差异的忽视或错误认知反而阻碍了人的解放。
同化主义理想假设所有政治地位平等的人都根据相同的原则和准则对待所有人,希望通过平等对待所有人达到正义的理想,将自由界定为对群体差异的超越。以理查德·瓦塞斯特罗姆为代表,他认为,肤色、种族、性别等差异仅是生理差异,并不影响或关联政治权利与义务。据此,人们在制定政策时将没有理由考量种族和性别等因素,差异的存在变得没有实质意义。瓦塞斯特罗姆给出了三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第一,同化主义理想为社会平等与正义提出了一个清晰、易于实践的标准,在此标准中,任何对于群体差异的歧视和偏见都是不正义的;第二,揭示了社会群体差异的任意性,使差异不会上升为社会差异;第三,将个人选择最大化,当差异仅仅是差异而不是一种社会定义,社会群体规范将无力限制个人的选择和发展,每个人都可以发展成为独特的自我⑬。杨认同同化主义曾经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为女性、黑人及其他因差异处于弱势的群体之自由和政治平等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近年来,那些处在同化主义理想压迫下拒绝同化的群体开始了反抗运动,他们意识到积极的自我组织和群体文化认同作为一种较好的手段,有助于争取权利和参与主流政治。以黑人、印第安人、犹太人为例,他们坚持种族身份的特殊性与积极意义,追求自我文化、政治组织和政治目的的特殊性。在女性主义者内部,也反对曾经的雌雄同体、分离主义的进路,更多地关注女性特殊的身体与经验价值,如关怀。
扬认为,同化主义对差异的错误认知将在三个方面产生压迫。其一,没有意识到差异并不仅仅是生理或先天差异的无关政治的问题,差异群体将在经验、文化、社会能力等方面有别于主流群体或特权群体,因此,差异并不会因为忽视而消失,差异的存在必然导致差异者成为真实的弱势群体。在同化规则下,这些弱势群体和主流群体之间的真正差异往往使他们在同一标准下处于劣势,因为规则是由主流群体所制定的,符合主流群体的利益。且在同化规则作用下,弱势群体的劣势地位被固定,而这却被认为是不歧视差异的正义。
其二,同化主义理想中存在一些预设,而这些预设是错误的。首先,它希望通过相同的原则和准则对待所有人,希望通过平等对待所有人达到正义的理想,预设了存在一种普遍善的人性;其次,它将自由界定为对群体差异的超越,预设了脱离具体情境和群体的人类能力。扬认为,这些预设本身便是不可能的,不存在脱离具体情境和群体的观点,如果有的话,那将是主流群体或特权群体基于自我的情境和经验来界定的规范,并通过中立性、客观化的表达普遍化地施加于其他群体。在这套程序下,对差异的无视会压迫弱势群体且标记他们的差异,固化成文化帝国主义压迫。
其三,对同化的强调将使人们渴望同化并参与主流群体,然而这种渴望会使主体产生自我厌恶和双重意识。以黑人、犹太人等种族问题为例,一方面,参与意味着去接受那个它所不是的身份;另一方面,试图参与意味着提醒自己成为它所是的身份。而那些偏离主流标准的群体将遭受诋毁,导致群体成员的内在化贬值,例如,贬低或歧视女性的关怀意识,批评她们爱哭、软弱的天性。
杨也对秉持中立规则的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以罗尔斯为代表,上文提及,他假设的“无知之幕”将超越个人特殊性和差异性,以中立的方法达到正义且普遍的原则。在此,中立性否认了情境与个人的特殊性,以理性为标准将情感与欲望从中立标准中驱除,将标准内的主体的多元性归为同一性,从而否定或压制差异。从这种意义上,中立规则是同一性逻辑的产物,也将产生上述二元对立的压迫。
自由主义者拒绝承认其否定差异,他们认为罗尔斯预设的国家将“确保所有公民享有公民的机会及其发展他们自由确认的任何善观念”⑭。然而,这种对差异的肯定是通过对公私领域的界定实现的,他们将混乱复杂的价值划到私人领域,将人们对善的追求局限于私人领域,而在公共领域追求普遍、客观的标准,“从而将自由与多元价值的关系转为权利与善的问题”⑮。扬批判关系的转换暗示了“权利优先于善”,并认同社群主义者桑德尔批判自由主义设想下主体“无来由”(transcendental view from no-where)的先验观点,即“自由主义对正义的强调中,预设了一个作为先在个体的自我概念。这个自我先于欲望和目标而存在,其自身便是独立的、整全的”⑯。扬认为,自由主义所假定的主体因坚固性和自足性而不被其之外的任何事物和人所定义,这本身也是在否定差异。
此外,在自由主义的设想中个人处于私人、独立空间之中,仅被其私人欲望所推动。扬认为这是一种关于人性消费导向的预设,在此预设下,有两方面关键错误:一方面,社会和政治关系将被视为满足私欲的手段,导致政治私人化而非公开民主化,由此社会参与与民主公开变得更为困难;另一方面,在自由主义的设想中社会群体的视角被排斥和压制,从而强制剥离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扬认为个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个人与群体关系无法分离。
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并不意味着扬倒向社群主义,扬也批判社群主义存在对差异的否认和压制。作为对自由主义理想的矫正,社群主义的共同体理想强调人的社会性构成及其相互性关系的确认。以桑德尔、巴伯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将社群定义为共享的主体,构成性主体分享着共同的自我理解,其特征是共同意识;以本哈比为代表的另一些社群主义者,将社群定义为互利互惠、互相理解,即承认每个主体的个性。
扬认为,他们的共性是都表现了主体的“共现”(copresence)⑰,即每个人都按照其理解自身的方式来理解和承认他人,并且同样认识到他人也是如此认识自己。然而,人并不可能完全地相互理解和互惠,主体间也或多或少存在着不能被完全理解的差异。对于共同体理想的欲求同样会导致对差异的否认和压制。首先,过度强调个体在共同体中的共享性和融入性,将使个体的自主性、独立性淹没在共同体之中;其次,共同体使外在于自身的一些差异演变成可以相互理解的总体性,实际上拒斥了主体之内和主体之间的本体论差异;最后,对共同体理想的欲求将会强化同质化,存在严重的政治后果。这是扬着重批判的问题。
实际上,社群认同本就可能导致个体对某些群体认同,而对其他群体恐惧、排斥乃至贬低,社群主义理想将会强化这种二分的情感,从而助长社会中的种族和阶级歧视的行为和政策。理查德·塞内特认为这种“社群神话”产生了严重的防御性排斥行为。例如,强迫那些想在白人区域买房的黑人离开。此外,强化社群认同将会强化相互认同这一要素,当相互认同越来越占据社群的核心要素时,将会产生许多小团体,使社群维持在较小且对外封闭的状态,从而加强同质性、排斥多样性。以女性主义团体为例,某些女性主义团体将性别、种族作为衡量政治团体的重要标准,而忽略其他因素,这将会偏离曾经多样性的目标,且她们认同某些女性的视角本身隐含着排斥其他女性。
总之,在扬看来,同化主义试图超越差异,却使与主流群体之间存在真正差异的群体在同一标准下处于劣势,进而遭受压迫;自由主义预设先验的个体,但通过将这些分离的个体聚集在一个公共的中立标准下否认差异;社群主义则以高度融合的共同体为目标,强调社群的共同意识或相互理解,拒斥主体之内和主体之间的本体论差异。扬对当代西方流行的正义理论的批判旨在揭示各种正义理想对差异的否定和压制,指出它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正义。扬认为,正义理论并不应该致力于构建某种抽象的普遍规则,而是应该基于一些合理差异和多元社会下的过程性社会结构提出具有差异性与包容性的政治理论,这也正是扬的理论批判的目的。
四、艾丽斯·扬批判流行的正义理论的价值与意义
霍克海默说:一种理论是批判的,很大程度上在于其追求人类解放,以“将人从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作为实践目标⑱。从批判出发重申差异的意义,通过差异政治实现正义,是扬的理论批判的价值。
扬认为,受同一性逻辑的统摄,传统观念将群体差异定义为绝对他者从而排斥为对立面。在扬的差异政治中,群体差异是一种含混的、关系化的、没有清晰界限的结构性差异,而非本质化的实体性差异,它既不是无形的团结也不是纯粹的个性。受压迫群体通过对自己身份的积极认可从而获得命名差异的权利,将差异转变为只是群体间的“比较函数”⑲,对差异实现语境化和关系化的理解,从而,差异既不会被本质化地忽略,又将得到积极认可。例如,在医疗保健方面,既要看到残疾人与正常人的不同,给予特殊关怀照顾,又要看到除此之外的相同之处,做到平等性。在此,差异不再意味着群体之间的隔离和封闭,群体之间依然保留着交叠与共同点,从而使差异不再作为规范的对立面,取而代之的是肯定个体特殊性和多样性。
对差异的强调是扬正义理论的突出特征。此外,扬认为,追求正义的关键不是having而是doing⑳,即如何从批判流行的正义理论揭示非正义现象导向正义观念,如何从理论正义转到实践正义,如何从西方福利资本主义社会延伸至国际正义。这些都是扬的正义理论于批判之后所要探讨的。因此,实践性也是扬正义理论的突出特征。
总之,基于批判,扬将要探讨解决的问题是——差异政治何以正义?如何推进实践正义?对此,扬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更和平、公正的未来世界的可行性方案,即放宽心理倾向、文化表现形式和正义制度的边界,宽容更多群体的差异及其在公共领域的代表性,使群体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边界更具有渗透性和不确定性㉑。
注释
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47页。
②③④⑤⑥⑦⑨⑩⑫⑬⑯⑰⑲⑳㉑[美]艾丽斯·M·扬:《正义与差异政治》,李诚予、刘靖子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19、31、32、32、33、44、121、145、193、275、280、208、8、314页。
⑧[美]艾丽斯·M·扬:《作为正义之主题的结构》,《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4期。
⑪V.Spike,Peterson&Anne Sisson Runyan Global Gender Issues,Westview Press,1993,p.25.
⑭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192.
⑮马晓燕:《差异政治:超越自由正义与社群政治正义之争——I·M·杨的政治哲学研究》,《伦理学研究》2010年第1期。
⑱ Max Horkheimer,Postscript,In Critical Theory:Selected Essays,trans.by Matthew J.O’Connell and others,New York:Continuum,2002,p.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