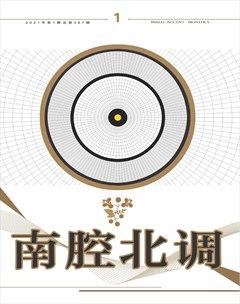在场的文学
张翼 安庆

2019年11月,我与安庆老师在一次研讨会上结识。我们既是同乡又是同好,虽是初识却天然亲近,因此当我萌生邀请作家参与课堂的想法时,最先想到的就是邀请生在新乡、写在新乡的安庆老师。2020年11月12日,安庆来到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面向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就创作经验、文学观念等问题举办讲座。这场讲座条件非常简陋,地点就是我们上课的教室,桌椅斑驳、空间狭窄,然而文学和作家使我们精骛八极,神游万仞。我一直在思考,文学究竟能对人、对人生产生何种影响,从他的述说中我得到了一部分答案。
——张翼
张翼:(以下简称张)您取得了丰硕的文学成果,多部小说曾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刊物转载,获得过“河南省文学奖”“杜甫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也是河南小说界的“八大金刚”之一。您能否谈一谈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你走向文学创作这条道路?
安庆:(以下简称安)首先,我的创作不敢说丰硕,虽然自己已不年轻,但一直都还是“在路上”的心态。转载呀,获奖啊,包括短篇小说入选全国十几家年选,这都是过去的事情,要毅然地翻过去,决不沉湎。
我写作的萌芽或者契机,可能来自于我一个时期的苦闷。我高中毕业回到村庄,但内心不服气,特别地想读书,想找到一个发泄口,心里有好多的话想诉说,像有一条大河要冲出闸门,必须找到一种发泄的方式,想倾述。我可能就是那时候想到了写作,因为内心的压抑需要找到一个爆发点,简单来说,就是有话想说。
具体开始的时间记不清了,也许开始于我第一次离开家乡。那一年我17岁,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就像余华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情景,不同的是我坐的是绿皮火车,我要去我叔叔所在的一个城市里打工。火车哐哐啷啷地响着,车窗外掠过一片片庄稼和土地,掠过一条条河流。我忽然感到非常地迷茫,非常地伤感,特别地难受。我要去的是一个工地,从此我就是一个社会人了,我带着包裹,在我去异乡的途中,有一种强烈的表达欲望。我去到了叔叔所在的一个工厂,跟的是林州的一个盖房班,每天早上5点多钟起床去工地,下午到很晚了才下班,干的是筛灰和搬砖的粗活。几个月后我逃了出来,我拒绝了再继续打工,我的内心告诉我,那不是我要的生活,那种生活成就不了我的未来。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去叔叔家告别,叔叔拍着桌子骂我逃避劳动,不能受苦,一辈子什么也干不成……叔叔说,你让你爹养你吗?我没有争论,我在第二天早晨一个人悄然地背着包裹离开了那个地方,后来我又经历了很多,做过蜡烛,卖过衣服,做过代课老师……我一直在寻找可以实现理想的道路,我之后打工都是在家附近,这样可以在晚上看书。一个人要找到你冥冥之中的东西,要敢于朝着接近你心灵、灵魂的方向努力。
我就是在苦闷和彷徨中开始了在文字上的训练。其实很多作家的写作都是在苦闷中产生的,包括余华无数次地说到他开始写作是特别地不想再做一个牙医,阎连科也是已经从部队复员又重新被招了回去,这是命运的安排,一定和努力有关。
我最初的写作是盲目的,那时候主要的目的是有话要说,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倾吐。但写作要找到一种路径,一种突破口。怎么办?那就是读书和练习,或者说,我能把写作作为人生的目标和方向,也是读书导致的,那些你读到的书在诱惑着你,冥冥之中在給你指路给你带路,先让你进入阅读的迷宫,再让你在迷宫里寻找。成就一个作家的是他自由地阅读,他在自由阅读中找到符合他情绪的文字。一个作家的小说叙述方式是很重要的,而他最早的小说叙述方式,肯定会受他所读的书的影响,最初写作所受的影响一定是受语言的影响。
张:您谈到了阅读对您写作的影响。您对文学的崇拜,对知识的崇拜,从《朋友》里老麦对老包的仰视里可见一斑。其实您对文学的态度挺复杂的,既有作为精神出口的需要,也夹杂着作为改变现状的手段。我这种理解是否适当?
安:最初的阅读和写作就是一种单纯的精神需要,是寻找一种灵魂的出口,想在内心找到一种安慰,没有任何功利,或许还不知道什么叫功利,心净如水,从阅读或从一次心灵的触动开始了我漫长的写作训练。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文学机构,甚至不知道报刊杂志,还有可以发表的渠道。至于改变现状是后来形成的,带着一种内心的挣扎。
我最初的阅读是猥琐甚至是卑微的,带着乞讨的意味,有一种饥饿感。我那时候非常内向,好像除了用眼睛观察我能看到的世界外,不愿意用嘴巴说话,可能和家里穷有关。我在其它场合说过两句关于我读书的感受,一句是:和书有关的屈辱都不算屈辱!另一句是:书是我暗中的贵人!我想起我在路边等投递员,眼巴巴地看着他邮袋里的报刊杂志,我羡慕和想象着那些报刊上的文字,那是我十几岁的时候,阅读开始成为我的一种寄托。我畏缩地跟在投递员的后头,当他把报纸投入村部的一个门里后,我找到一根木棍,把那些报纸从门缝戳到门口,找到我要阅读的《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文汇报》的“笔会”版,慌张地把它们揣在怀里,匆匆地跑出来,跑到家如饥似渴地展开,阅读,摘抄……我记得我的狼狈,有一次那个投递员杀了回马枪,突然站在我的身后,瞪着我,让我颤抖,还没来得及揣起的报纸落在地上,眼泪大滴大滴地掉下来,我惭愧地低下头抽泣,我知道我这条阅读的路从此断了。然而,之后,那个投递员再见到我,主动从邮袋里抽出一本杂志或一张报纸给我,对我笑笑,说,看完还我!我现在还记得他的面容,记得他姓王,有一头自然卷的头发,村里人当时都叫他小王,他人其实很好,脸上总带着浅浅的笑容。
后来,我告别了这种乞讨式的阅读,我开始走进县城,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县城的书店,那么多书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的第一感觉是特别想哭,那一刻,我知道了这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就是书店,最美好的东西就是书,最好闻的就是书香。后来,我每次去县城都要进一次书店,好几次把家里给我吃午饭的钱买成了书,回家的路上就迫不及待地坐在路边读起来,直到看不见了才匆匆回家。
我想起我最初读路遥的《人生》,我骑着自行车走在从村庄到县城的路上,一路上心潮澎湃,心血来潮地发誓,要写出像《人生》这样的作品,写出类似于《人生》的续集,去体验高加林的生活,把他没有走成的路走成……多少年来,我就是这样怀揣少年的梦想,怀揣我的一颗“初心”,懵懂而坚定地走着,有过很多挫折,有过很多艰难,很多痛苦,也忍受过很多屈辱,在外打工时,用一双胶鞋换过别人的一本书,自己穿着露脚指头的鞋干活。但我没有停下来过,我知道,要实现一个目标,必须要有异于常人的付出,绝不可半途而废。我一直把海明威的那句话作为我的座右铭:“人可以被毁灭,但不会被打败!”我还特别喜欢一句话:“少年须勤奋,文章可立身。”这是我后来看到的,那时候我想“立身”是什么?就是你可以堂堂正正地站起来,不蹲、不矮、不仰人鼻息,你才可以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多少年,我就是靠这样的坚持走过来的。
世界是慢慢地向你打开的,一次我贸然地参加了县工会举办的迎春诗会,结束了才知道我是唯一的从农村来参加活动的。我很懵懂,我不知道工会的诗会是办给城里职工的,我好像是在文化馆大门口看见了一张启事就混了进去,一个人也不认识,我出来以后还要骑自行车走几十里土路回家。记得十多天后我又一次去县城,在大街上被一个文友拉住,说你是不是那天晚上参加诗会的青年农民?接着他说,你上报纸了,市报的一个记者那天来采访,把你写在报道上了,说一个青年农民跑几十里地来城里参加了诗会。那张报纸我到底也没有见过,但我和县城的接触慢慢地开始了,逐渐地接触到了县城里的几个文友,我们在一起谈文学,他们中有各个行业的,但都是喜欢文学,记得还有一个部队的文友,老家是湖南的,他喜欢哲学,动不动就是弗洛伊德、黑格尔、荣格,我当时就是受他的影响买了弗洛伊德的书。文友中有一个在邮政局的分拣室工作,我一次跟他到分拣室去,哇,原来他们的工作就是分发报纸杂志的,满地都是一捆捆的报纸杂志,我在那里见到了大量的文学杂志:《十月》《当代》《收获》《人民文学》《青年文学》《诗刊》等,在杂志上看到了王蒙、莫言、张承志、苏童、余华、毕飞宇、刘索拉、李佩甫、张宇等等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才知道原来每个人写的东西还可以有这么多的刊物可以发表。当然,那个时候我还在阅读阶段,或者刚刚找到了更宽的阅读渠道。但邮政局的分拣室,让一个乡村的孩子看到了另一个世界,避免了一个乡下孩子的闭塞。
后来,这个文友家人在大街上承包了邮政局的一个报刊亭,他每天晚上要去报刊亭里替换父亲,我就每隔几天的晚上骑几十里的自行车去报刊亭里找他看书,看杂志,聊文学,也在他的报刊亭里结识了县城更多的文友。关于这段生活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留在县城的痕迹》。
慢慢地写作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赌注,我要写作,要倾吐,也要改变命运。我更加贪婪地看书,每天尝试着写作,甚至给自己制定写作的字数,我曾经有一个小本,封面上写着:日写一千字。这种做法当时也是看到了哪个作家的叙述,受到的启发。父亲不理解,家族里的人,街坊邻居也都在用质疑的目光看我,那两年母亲已经不在了,父亲反复对我说的话就是“你要养活你自己”。前几年,一家杂志发表了我的中篇小说《父子花》,那是我20岁左右时写的一个作品,小说的原题目叫《梦中的父子花》,是写两代人的代沟,从误解到沟通的过程,小说的最后,我梦见一棵树上开出了并蒂的花朵,那些花就叫“父子花”,是两代人最后相互理解后開出的花,小说写的就是我当年的那种状态。
文学对我是有馈赠的,我曾经说过,文学是我的亲人!我一直感谢文学,我在写作中逐渐看到了鼓励,看到了前方的风景。我因为不断地发表作品被招聘到乡政府工作,在乡政府一直工作了十几年,之后被借调到过组织部、宣传部,再之后因为我的作品获得河南省文学奖,小说连续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选载,入选全国小说排行榜等,历经周折按特殊人才被调到了新乡,至今在新乡落脚快20年了。回顾走过的文学道路,文学帮助了我,也因之遇到了挺身相助的人,他们帮我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这一直是我前行的动力,每每想起都充满了感激,也借此对那些帮助过我的贵人,深深地道一声感谢!
张:从您刚才谈到的作品来看,您的阅读量是非常大的。现在这些青年学生也面临着如何读书的问题,一是读什么?二是怎么读?三是如何将所读内化为自己的所得?您能否就这些问题给些建议?
安:关于读书,怎么读?也有一个领悟的过程。对于写作者来说,阅读的过程尤其重要,读书大概有两种,一种是要耐着性子去读的书,一种是快餐式的阅读。作家读书和一般的读者会有一定的区别,读者就是顺着自己的兴趣去读,有的人一辈子都喜欢读武侠,有的人喜欢的就是那种励志书情感书。而作家读书大都是带有挑战性的,读的大都是要耐着性子去读的书,他是带着获得营养的需要,学习的需要,提升写作水平的需要去读,伟大的书不一定是好读的书,比如博尔赫斯,比如乔伊斯,比如鲁尔茨,比如略萨,阅读他们的书都不是一般的读者,他们的小说给同行的提醒可能更多,想象空间可能更大。
阅读好的作品往往有意外的收获,我常常在阅读中受到启发,触动我写作的灵感,从那些作品中找到自己写作的视角。
读书也受个人经历、经验、情绪的影响,有些书你当时读不下去,可能过一个阶段或过几年,你在拿起来的时候完全可以接受。当你开始有选择性地阅读,说明你的阅读已经有了固定的兴趣或者志向的需要,甚至带着研究的性质,而读书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你读到了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也是你对读书有了相对更深的领悟。
暂时读不下去的书,不妨先放一放,也许过一段时间你就会读得下去,还会非常受益,有时候读书需要心性放开。有些书需要耐着性子去读,在书中的某个章节你可能会开始读得顺畅,并获得阅读的快感,会有收获。
张:您的小说语言非常讲究,特别是题目和人名蕴藉丰厚、耐人寻味,比如《父子花》、比如《扎民出门》里的“许多”等等。请您就这方面介绍一下心得?
安:小说的题目其实就是小说的开始,它影响整个小说的基调,甚至写作的心境。有的题目是随着写作的意念产生的,会在灵感产生时先迸出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对作者的写作,有着启悟引领的作用,实际上基本的思路已经出来了。很多情况下标题就是一个文本的题旨或者提示,是与内容、主题、意义相关的,是对主题的一种提炼,这是对作者而言。而对读者来说,有着引导、了解、对内容猜测的作用。
很多小说家是很讲究题目的,比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妻妾成群》,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好的题目可以引导你的叙述,也可以影响读者的阅读,比如我多年前的《一个冬天的狼狈》《现在广播爱情》《我们和一头驴的生活》《飞过城市的麻雀》……这几年的《父亲在自己的夜晚》《受伤的鸽子》《父亲背走的秋季和冬季》《卜者之卜》等。而每一类型的题目又和作者的叙述风格有关。
短篇小说的题目可能来得比较直接,因为短篇小说表达的就是一种感觉或生活的片段,在你抓住感觉的同时,题目或许同时就产生了。而长篇、中篇的题目有的是先定下来,在小说完成后对题目再进行推敲。比如我的长篇小说《镇》,它最开始不是这个书名,备用的书名有好几个,我进行修正时最后确定了《镇》这个题目。我有一个写作的理想,就是在时机成熟情况下,写几部以一个字命名的长篇小说,它们可能是一个系列,目前有了大致的方向,还在酝酿之中。
你问到的关于小说中人物的名称,我在确定开始写作一个小说时,接着考虑的就是小说中人物的名字,人物的名字是要和小说的主题、小说的意念、小说的基调相搭配的。我有一个笔记本是专门用来记备用地名和人名的,我把我想到的地名和人物名记在那个笔记本上,写作时去里边挑选。更多的情况,是你在准备写作小说时就会有相应的人名蹦出来,感觉合适就拿来作为人物的名字用上了,等小说发表出来,再看人物的名字感觉还是贴切的,比如《扎民出门》里的“许多”,作为一个跑车司机,这个名字是有寓意的,我也奇怪当时怎么就想起了这个名字,可见一个成功的作品与各种因素相关联。
张:我们也了解到现在年轻的读者群体都比较关注作品的情节,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情节更能够吸引读者。在您看来,一部作品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是人物,还是情节?您在创作中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安:小说的要素是人物、情节、环境。在小说的多种元素中,最核心的还是“人物”,所谓“人物”就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一篇成功的小说怎么可能没有主人公呢?从众多成功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列出一个巨大的人物长廊,情节、环境等都是为“人物”服务的。
一篇好的小说有很多复杂的成分和元素,人物的塑造考验的是一个作家的功力,一个小说家重要的贡献就是人物。托尔斯泰《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巴金《家》中的觉民、觉新、觉慧,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少平与少安,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小娥,余华《活着》中的福贵,苏童《妻妾成群》中的颂莲等。一个成功的人物身上寄托着作家的表达,要表现的内心生活,对一个时代的思考。作者对人物是有倾注的,人物是小说中不可少的借体。
现在似乎有一种淡化人物的现象,小说创作也在多元化,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发生了变化,可能和作品太多有关,一般的读者很少谈到人物,他们更多记住的是书名和情节。但好的小说一定还是会写出成功的人物。你认可的小说,回过头去看,它一定是有一个人物在带动你的阅读,你记住的一定还是人物。
张:您刚才谈到了陕西作家的创作精神。文学豫军与文学陕军,同是当代文坛上的劲旅,也都受到黄河滋养,您觉得这两个群体在创作形式和方法方面有哪些相似之处,又有哪些不同呢?此外,您认为地域生活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相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文化中心,河南处于文化的边缘的地带,而在河南的内部,新乡更是文化边缘地带。在新乡写作,您觉得对您有哪些好处?又有哪些局限?您是如何突破这些局限的?您又是怎么将“地方”化成自己的文学经验?
安:这个问题我曾经有过思考。陕西和河南两地有相同的点,两省相邻,都是传统历史文化大省,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多年来陕西和河南的文学成就不相上下,甚至难分伯仲,两地都有自己的代表性作家。真正以地方文学实力成为军团可能是在20世纪90年代,记得有陕军东征之说,那两年陕西接连出了几个大部头的作品,包括后来都获了茅奖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京夫的《八里情仇》,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等。
两地作家的区别在于,陕西作家的使命感特别强,有一种孤注一擲、孤军一战的拼命劲头,甚至有苦行僧极端化创作的投入行为。比如,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时,去到一家煤矿区闭关写作,几乎与世隔绝;贾平凹写《废都》去到一个乡镇的计生办,也是封闭式的创作;陈忠实写《白鹿原》的理念就是要写一部可以枕棺的小说,完成的那天在家乡的河滩里放了一把大火……没有听说河南的哪个作家有过这样的极端化创作行为,河南作家相对比较沉稳,在心里不服和较劲,埋头创作,李佩甫老师就是这样坚持几十年完成了他的“中原三部曲”。而从近年来的文学创作势头来看,河南可能更占优势,无论从代际衔接和作品质量上都不亚于陕西,河南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已经累计达到九人,是全国之最。
但两地作家的内核还是大致相同的,无论怎样的写作方式,投入的劳动是不可省略的,最终衡量的标准还是作品的质量,留下来的还是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作品。
关于地域对个人创作的影响,肯定是有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学故乡,每个人的故乡在内心的凝结是有一些区别的,为什么一个人一生都在写他的出生地,或者把出生地当做他作品的地标,这也许就是地域的影响,他们的写作甚至成就了一个地方的旅游业和经济发展,沈从文、汪曾祺、莫言,河南的刘震云、刘庆邦、周大新、阎连科等都是一直在坚持对故乡的书写,但故乡已经是放大了的故乡。刘震云笔下的延津不仅仅是新乡的延津,也不仅仅是河南的延津,而是对整个中原的乡村书写;李佩甫老师的“中原三部曲”不仅仅是他生活过的许昌,而是广大的中原乡村,作家写作总要找到一个地标;而河南作家中邵丽和乔叶没有太多的地域痕迹,作品却在全国产生影响。地域是经验写作的营养,也是心灵的故乡,但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做地域性的作家,在城镇化的发展形势下,以后也恐难再出典型的地域性作家了。
对于我,我的写作属于进行时,我自知自己的影响力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地域对我当然也是有影响的,但我不想成为地域符号的那类创作者。至于影响我的作品体现的元素,乡俗、亲人的生活都会不同程度体现,但不太严重,我喜欢把作品逐渐地放大,比如《加油站》放在另外一个地域也是能够成立的。
至于是否感觉新乡是文化边缘地带的问题,我没有那么强烈,一个作家的创作是不会被地域局限的,将地域文化化成作家的文学经验,我一直都在这样写作,一个作家是挣不脱地域文化影响的。况且,一个作家的作品肯定也不是单单反映一个地域的文化,我只想好好地思考自己的创作,找准自己的强项和关注点,在自己的点上纠结出尽可能大的成果。
张:您的小说中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中国乡村的转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乡民的生活内容、精神内核也正在发生着剧烈变化。比如您在作品中多次提到乡村边的“加油站”,作为一个交通枢纽,它联结着乡村与外面的世界,然而当外面的世界席卷而过的时候,它留给乡村的究竟是什么?乡村是否有能力又如何消化这些外来的刺激?
不知道您自己是否察觉到了,您的作品里还有另外一个潜在的主题,就是“寻找”。《朋友》里进城务工的老麦寻找在城里失踪的孩子,《扎民出门》里老扎民寻找将孩子丢弃在乡村的父亲,《父亲的迷藏》里父亲也在找着什么。这是否意味着您也在“寻找”着什么?
安:你问的是两个问题,我也要从两个方面来回答,其实第一个问题涉及的是乡土文学或乡土题材创作的话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势必会影响到乡村,乡民的精神内核也势必发生变化,这是必然的,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会受到经济发展的冲击,时代在不断地变迁,但无论怎样变迁,人永远是时代的主要因素。不仅仅是中国,西方的一些国家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不认为乡村原来的东西都失去了,由于我和乡村的关系,我要不断地回到乡村,家族里的婚丧嫁娶,我还要参与。事实上传统的伦理,传统的礼仪还在延续,乡村也逐渐富裕,拿我生活过的那个村庄来说,很多家庭都有了小汽车,经济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关于乡土文学,它的内核的确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当大量的农民工背上包裹踏上外出的旅程时,新的乡土文学实际上就已经诞生了,关于这方面的思考,我在十年前就写过几篇小说,比如《倾吐者》《飞过城市的麻雀》《紫外线》《杨木头的低保》等,这些小说的人物都是当下的农民工,有我对农民工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外边的世界对乡民的诱惑究竟是什么?也是我在思考的问题,比如谈到节气,对节气的尊重,从乡村出来的人对乡村的礼仪抱有怀念和敬畏,包括我,我的孩子基本上是在城市长大的,每到春节,还是愿意回到村庄去,因为那里的传统礼仪还在,还有一种亲情的热闹。中国的礼仪和伦理价值的载体是在农村,也可以說是从乡村开始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些传统的礼仪正在逐渐地消失,经济的刺激对传统和文化是双刃剑,消失之后再恢复是很难的,即使恢复也是带有摧残性的。
那么城市对乡村的诱惑是什么呢?我觉得可能是就业、教育和卫生等,城市的繁华和热闹,城市的文化活动,对孩子教育和未来教育的考虑都是因素。对待这种诱惑怎样拒绝和平衡,这有个时间问题,到商场或到某个服务行业问问,很大一部分的工作人员都是来自农村,在城市就业,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他们内心的向往和欲望。
现在,很多农村家庭在县城里有房成为了一种趋势,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年轻人结婚,女方提出的条件就是县城里有房,他们考虑得越来越远,中国的城镇化是在攀比和欲望中迅速被推进的,这种欲望和需求,比政府号召还要有力。但也有一部分较早去到城市的人回到了乡村,他们的回归也有各种复杂的因素,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深层原因,也许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创作题材。
第二个问题,我的确写过一批关于“寻找”题材的小说,你举的这两篇小说也是我比较满意的,它们都分别被《小说选刊》转载,入选多种年选或获得奖项……寻找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们总有遗落的东西,遗落的困惑,怅然若失,写作或者阅读也许就是一种寻找,我们要找到的是关乎我们心灵和灵魂的东西,包含着我们的怀念、遗憾、愧疚、疼痛、泪水……我们的呼唤、追寻、反思……一篇好的作品就是要写出人和时代的疼痛,我常常在阅读写作时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其实衡量一篇好作品很简单,就是读者被打动。
这几年,我一直在写关于乡村老人的生活,以父亲为题的就有《父亲在自己的夜晚》《父亲的迷藏》《父亲背走的秋季和冬季》《父亲的声音》等,正在修改的一个中篇也是写乡村老人的。我的母亲是1986年去世的,去世时50多岁,母亲走后父亲一直独自地生活了几十年,后来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在父亲最后的几年忽然感受到老人身上的好多东西,他的孤独、无望、无助、怀念、依恋……我想象他这么多年自己做饭的时光,每一次一个人在小锅里添那么一点水,看着水顷刻间就会沸腾。到老了,他对和我们在一起有了企求,那是怎样的心情,怎样的无奈……在乡村像父亲这样的老人有很多,关于乡村老人的题材我还会写下去,社会进入老龄化,乡村老人的生活状态是我为此挂念和想书写的。
你聊到的关于乡村伦理或伦理重建的问题,我的很多小说都牵涉到了,这也是我想在下一步创作中多去考虑的题材。谢谢你的提醒。
张:你提到文学作品也可能代表一种思潮,也要承担社会责任,那您觉得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安:能引领思潮的作品,一般都带有一个时代的先锋性和思考性,这里所说的先锋,代表的不是怎样写的范畴,是说它在那个时代那个时期是前卫的,有带动性的作品,包括延安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那一大批的作品中至今还留下很多优秀的小说、戏剧、音乐、美术等,包括萧红的出现及其作品产生的长期的影响力,张爱玲作品的恒久性……之后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先锋文学、寻根文学,这些所谓的文学时代或文学时期,是先有作品,再被命名为思潮或流派的。每个思潮都带有革命性,都是对文学形式和文学操作实质性地推进,每个时代或时期都会有可以留下的作品,凡是留下来的,都是内容比较宽泛,政治烙印不太过分和局限不大的作品,它们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人心和那个时代的变革,有那个时代的烟火气,影响过一个时代的潮流,否则就没有较强的生命力,或者就没有生命力。
张:您近期有没有新的作品与读者见面呢?今后将会出怎样的作品呢?
安:我会坚持以中短篇小说为主的创作。我要考虑的是怎样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一个作家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突破也是不容易的、艰难的,但我一定要去努力,尽力做到,我之前的创作也算有几篇自己至今还不脸红的作品,比如《加油站》《扎民出门》《棉花棉花》《老顾头的温暖》《麻雀》《卜者之卜》等,这些大都被选载和获得奖项以及入选排行榜,但过去的只能代表过去。目前刚写好的有几个中短篇小说,正在修改之中。接下来即将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是我两年前创作的首部长篇儿童小说《月亮女孩》,如果正常会在2021年的上半年出版,还有一本短篇小说集,是以《扎民出门》为书名的,也会在2021年出版发行。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系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新世纪河南青年作家乡土创作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0BWX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