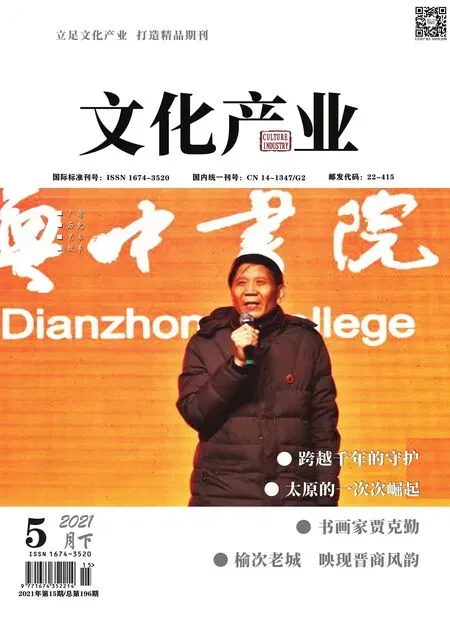摩崖造像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研究
——以弹子石摩崖造像为例
夏艳臣 北京市文物建筑保护设计所 北京 100000
一、引言
文物保护规划是指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为代表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规划,在城市规划体系中属文化遗产类保护专项规划,其性质属于资源保护技术。从1990年开始,经过30年的发展,保护规划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完善的学科门类,由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和不同学科构建而成的复合集成体系[1]。
根据国家文物局2019年对第一批至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规划编制情况的统计数据来看,目前已经获得同意并公布实施的文物保护规划共计981项,其数量仅占第一批至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的22.8%,可见其通过难度之大,对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的要求之严[2]。
2017年,笔者作为主要参与者完成了《弹子石摩崖造像保护规划》的编制,并于2018年获得国家文物局同意经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实施。本篇文章以弹子石摩崖造像为例,阐述摩崖造像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的评估要点和主要规划措施,以期为同一属性的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编制提供参考。
二、弹子石摩崖造像的基本情况
(一)概况
弹子石摩崖造像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街道集翠村1号,根据文物相关档案记录,弹子石摩崖造像主要由大佛造像、五佛造像和五佛殿组成。大佛造像开凿于元末,高7.5米,左、右二弟子高2.3米,佛像面对长江,背依山崖,面像方圆,表情庄重而敦厚。五尊佛造像开凿于明代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中央为三佛并坐,左、右各雕一弟子。五佛殿兴建于清代,建筑面积290平方米,占地面积145平方米,主体建筑标高187米,高差11米[3]。
2016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弹子石摩崖造像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新发现有摩崖题刻、钟鼓亭、石碑以及其他建筑遗址及台基,对清代时期形成的寺院格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弹子石摩崖造像是我国唯一可确认的由农民起义军政权所开凿的,其丰富的文物类型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历史沿革
《巴县志•疆域》条云:“江水过鹧鸪石,弹子石至观音碚,两岸有大石佛,明夏都察院邹兴所凿也。”明夏就是元末农民起义军明玉珍所建的大夏政权(公元1329年-公元1366年)。明玉珍率农民起义军攻占重庆称帝建立大夏国后,为“镇水妖驱鬼怪”,命都察院邹兴于大夏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在人头山对面高崖之上雕凿弥勒大佛,以镇江中水妖保黎民平安。故此,大佛造像距今已有650多年的历史,是唯一有资料记载可确认的农民起义军政权所作的佛教造像。
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雕凿五尊佛,即五佛造像。大佛寺于清代开始鼎盛,历史上香火极盛时,寺内僧人曾高达数百之多。五佛殿始建于清代,门楣正中横匾额书写“法眼观澜”四个大字,系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四川布政使献立,后五佛殿毁。
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五佛殿得以重建,寺庙再次兴盛。至20世纪30年代,寺中建筑有五佛殿、大雄宝殿、观音殿、玉皇殿、毗卢阁、望江亭、僧房、念佛堂、禅堂等,占地面积约30亩。清代学者王尔鉴诗云:“静域凌霄汉、高深一览中。江流天地转,山泛水云空。石像生苔绿,崖花落照红。禅关何处叩?拂壁度春风。”
民国时期寺庙渐衰,但曾作为重庆佛教华严学校的旧址,有50多名青年僧尼在此读书习经。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兵工厂内迁至此,大部分寺庙被占,佛殿、僧房受到破坏,僧人逐渐星散。1942年,韩国临时政府改朝鲜义勇队为光复军一支队,支队总部也曾设在大佛寺。
新中国成立后宗教活动场所被政府取缔,部分房屋又分别为废品公司、华康纱厂所占据。“文革”期间,大佛寺被严重破坏,正殿泥塑佛像被捣毁,经书付之一炬,文物散落。除大佛造像、五佛造像及五佛殿和钟鼓亭幸存外,其余殿堂亭阁先后被拆毁,大片僧房变成民房或职工宿舍。直至2013年,弹子石摩崖造像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大佛寺历史格局研究
2016年,为配合“川渝石窟寺保护工程”项目,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组织对弹子石摩崖造像区域的摩崖造像进行三维扫描测绘,并对周边遗留的建筑遗址开展初步考古调查。在规划编制过程中,通过查阅相关文件,结合考古调查,并与周边居民进行座谈,以口述史作为佐证,综合研判,现对大佛寺的历史格局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初步确定了清代大佛寺的历史格局。
根据《大佛寺记》记述,主要建筑有大雄宝殿、观音殿、玉皇殿、毗卢阁、五佛殿、望江亭、念佛堂、禅堂、僧房等,占地三十余亩。大佛寺在鼎盛期虽占地30亩,但应包含了土地、园林等全部庙产。调查结果显示,原寺庙建筑区占地面积约10000平方米(15亩)。西至江岸,有上、下两道条石砌筑的寺墙,寺墙与大佛造像所在山岩连为一体;北部寺墙尚存,根据历史地形图可知寺墙外即为山谷;东部尚可见有上殿所在台基的局部,应是寺庙东界;南部边界则根据走访调查得知的山门位置判定。
鼎盛时期的大佛寺可分为4个区域:①大佛、五佛区。大佛位于西北角,临江而立,朝向约310°,前有平台和踏道直入江中;大佛右侧有踏道通往五佛殿,踏道顶部为现在山门所在,但我们认为原山门亦应在此;五佛殿所在区域共三层台基,最高一级台基上修筑五佛殿;五佛殿左侧崖壁上可见有题记4处;沿向南踏道与大殿区相连。②大殿区。为大佛寺的主体建筑群,面江约290°,以呈中轴线布局,由低到高沿地势共有4层台基,各台基间海拔相差约3米。1号台基上为现代建筑(原为天王殿),其历史布局不详;2号台基应为下殿外平台;3号台基为下殿所在(观音殿)、4号台基为上殿所在(大雄宝殿)。③大殿区北为僧侣墓葬区,因后期建设已不存。④大殿区南应为附属建筑区,包含放生池、望江亭等,现为南滨路及弃土区,情况不明。
(四)核心价值陈述
1.历史价值。重庆地区目前发现的元代造像较少,仅有四处。与其他三处摩崖造像采用的方层平顶单层龛不同,弹子石摩崖造像中的大佛造像龛采用竖长方形。大佛造像为大夏初年的邹兴主持雕凿,年代约公元1361年至1366年间,内容为弥勒佛携二弟子像,其形象取材于唐宋时代弥勒倚坐的式样,严肃、古朴,摒弃了宋元以来流行的玩世不恭,喜笑颜开的大肚弥勒佛的形式,是该地区元代造像的典型代表,为研究中国南方地区元代时期摩崖造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4]。
“大夏”是元末农民起义军明玉珍(公元1329年-公元1366年)在重庆建立的政权。明玉珍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7年)入据重庆,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即“陇蜀王”位于重庆之行邸。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即大夏国“皇帝”位于重庆,其势力控制重庆达14年。清代学者王尔鉴所纂《巴县志·疆域》记载,“江水过鹧鸪石、弹子石至观音碚,南岸有大石佛,明夏督察院邹兴所凿也”。邹兴为明玉珍手下将领,大夏立国时任大司徒,后改任中书省平章,其在明玉珍命令下开凿的大佛造像,是目前可确认的唯一一处由农民起义军政权所制作的佛教造像。
五佛造像中的“三佛”应是弥勒成佛前的过去三佛,或以阿弥陀佛为主尊的三佛,主佛骑牛的形象殊为罕见。在传统佛教造像中,只有大自在天骑牛护法,其来源于婆罗门教。文殊菩萨骑狮子、普贤菩萨骑大象已成定式,此处以头戴风帽者骑之,出典亦不祥,因此,五佛造像的主题和形象,在全国同类摩崖造像中亦为罕见,是研究佛教造像史以及当时其他宗教信仰的重要材料。
元末时期,农民起义频繁,徐寿辉领导的红巾军是一支重要的起义力量。明玉珍加入后,皈依了白莲教。建大夏称帝后,“下诏除释、老二氏教,然犹令民间持弥勒佛号”,并命邹兴主持开凿了大佛造像。明洪武四年六月(公元1371年),大夏灭亡。明代永乐年间,增加了五佛造像。至清代以后逐为佛教寺院群落,占地三十余亩。民国时逐渐衰落,“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弹子石摩崖造像反映了重庆南岸地区元末至清末民国初年的政权更替历史事实和宗教信仰文化的发展演变。
弹子石摩崖造像在清朝时期发展到巅峰,形成了包括雄宝殿、观音殿、玉皇殿、毗卢阁、五佛殿、望江亭、念佛堂、禅堂、僧房等在内的占地三十余亩的寺院格局[5]。虽然在抗日战争、“文革”期间遭到破坏,但仍保留有大佛造像、五佛殿、五佛造像、摩崖题刻、钟鼓亭以及其他建筑遗址,可以较为清晰地辨明清代寺院的历史格局,为研究该区域的宗教寺院布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2.艺术价值。弹子石摩崖造像造型丰富,雕刻精美,具有传统宗教中特殊的审美意境,有较高的艺术和研究价值。大佛造像为弥勒佛像,善结跏趺坐于方形座上,左手抚膝,右手举至胸前,结无畏印,肩宽2.4、高1.5米。桃形肉髻,螺发,眉间有白毫,嘴角略上翘,面带微笑。戴手镯,外披袒右袈裟,内着僧祗支,跣足,神态安详宁静,衣着纹饰线条自然流畅,整体形象简洁明快,生动有力。五佛造像为中央三坐佛,两侧为二弟子,主佛坐于卧牛之上,牛有耳有角,回首相望,袈裟衣纹覆于牛背上,形象生动。左侧弟子骑狮子,穿交领袈裟。狮子前爪伏地,头近地面,作俯冲形,似是下山之状,生动有力。右侧弟子面相方圆,光头,有圆形风帽及帽箍,穿交领袈裟坐于大象背上,大象跪卧,长鼻、双耳、四牙、尾巴刻于壁上。造像整体雕刻精美,形象生动,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较高。
五佛殿建筑装饰和木构件细部造型细腻,传统寓意丰富,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五佛殿为三重檐歇山式屋顶建筑,一层底部为砖墙,上部为木板墙镂空花窗,二层为木板墙隔扇花窗,所有结构涂红色,庄严肃穆;柱础为鼓形雕花石质柱础;撑弓为动物、花鸟图案造型,生动形象;脊饰为玉净瓶两侧云龙环绕,具有一定的宗教建筑艺术价值,是西南地区山地佛教建筑的代表。
3.科学价值。弹子石摩崖造像是山地区域独特佛教建筑规划的重要体现,其充分依托原有山形水势,依山而建,利用山体受力,将山形与建筑建造融合一体,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摩崖造像并不按照传统意义上的正南北方向开凿,而是以面江为原则,依山就势布局。寺庙格局充分考虑了长江走向、山形地势等因素,既反映出寺庙的修建具有严密的规划设计,也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建筑思想。
作为地标和水文标尺的重要作用。弹子石摩崖造像是川江航运的重要地标,来往的船只通过大佛造像来判断长江的水位。每到春夏江水上涨时佛脚便浸入水中,成为天然的长江洪水标志,当地民间有“大佛洗脚、大佛洗手、大佛洗脸”等谚语来表示长江水位的变化。
4.社会文化价值。弹子石摩崖造像是重庆市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加强其保护和利用工作,有利于深化重庆市历史文化内涵,提高重庆市城市知名度,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弹子石摩崖造像是重庆市目前发现的仅有的四处元代造像之一,反映了重庆市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社会文化,是让公众感知佛教文化、中国佛教建筑及造像艺术,体验佛教文化的重要基地。
弹子石摩崖造像中的大佛造像具有镇水的象征意义,体现了当地祈求平安的传统民间风俗和淳朴的民间信仰,在民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加强弹子石摩崖造像的文物保护、展示与利用工作,可以促进当地的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发展,促进重庆市南岸区经济、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
(五)保护对象的认定
保护对象即为遗址价值的承载体。根据对弹子石摩崖造像的研究和现场调研,确定其保护对象包括文物本体、附属文物、文物载体和历史环境。
文物本体:根据文物类型的不同,分为摩崖造像、摩崖题刻、文物建筑、建筑遗址与台基以及围墙等五类。
附属文物:石碑1通,断为两段,位于五佛殿西侧,清代道光年间立。
文物载体:弹子石摩崖造像雕凿所依附的山体,沿长江呈南北走向。
历史环境:自清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佛教寺院群落格局与弹子石摩崖造像雕凿相关的山形地貌,长江水系、植被景观等其他历史环境。
三、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导致文物保存堪忧
与其他文物类型不同,石窟寺及石刻对环境的反应更为明显,自然因素首当其冲。而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及特定事件,大多数的摩崖造像受到严重的破坏,弹子石摩崖造像亦未能幸免。
弹子石摩崖造像的岩体材质为砂岩,其岩性本身较为松软,具有毛细孔和吸水性,因此易受到风化和污染。由于位于长江东岸,且暴露于自然环境中,充沛的降水除了会对造像本身形成冲刷危害外,还会滋生微生物,形成水锈结壳;太阳光线直接辐射造成温差变化引起矿物颗粒涨缩、干湿变化诱发矿物吸水、失水变化等作用,使得岩体表面岩石产生微裂隙或起层,造成造像表层岩石呈颗粒状、鳞片状剥落等自然风化破坏;同时,酸雨的危害也不容小觑,水和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大大提高,加快了文物本体的残损速度。
人为因素影响方面,道路建设直接将原有寺院格局人为切分为两部分,其行车引起的震动也对摩崖造像的安全产生威胁;因缺乏专业保护知识,人为不当维修也是造成摩崖造像残损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南岸区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之一,燃香焚烛等行为也造成摩崖造像表面的污染,且增加了火灾隐患。
(二)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矛盾突出
弹子石摩崖造像所处的南岸区是重庆市重要的核心区之一,城市建设活动频繁,无论是道路建设、居住区建设、桥梁建设等都对文物安全和文物历史环境风貌产生非常大的威胁。主要体现在:1.城市主干道南滨路和沿江水泥步行道路的建设,从原有寺院中部穿过,对原有的历史格局造成了人为的切割破坏;2.从弹子石摩崖造像的整体区域地形来看,鼎盛时期的大佛寺从长江可沿台阶一直登到沿江大佛,并经东侧的上山道路,到达五佛殿,后经过东侧道路进入大殿区,最终到达上殿,即大雄宝殿,整体呈西低东高,逐级抬升的地貌环境。但是居住区的建设导致整体的区域地形已经趋于平缓,无法再呈现其原有的寺山一体的壮丽景观;3.大佛寺长江大桥位于弹子石摩崖造像南侧,距离大佛造像约160米,高大的桥跨和设施对景观风貌产生破坏性影响;4.在重庆市南岸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弹子石摩崖造像所在区域将被打造成综合性的城市商业中心,规划的相关基础设施、建筑设施等皆对弹子石摩崖造像的安全和景观风貌造成不良影响。
(三)缺乏有效管控和引导导致野蛮生长下的文物利用途径
大佛寺于民国时期开始没落,新中国成立后,此处的宗教活动也被取缔。2008年,大佛地段被纳入重庆洋人街旅游项目,美心集团出资对弹子石摩崖造像区域进行了建设,新建建筑包括佛恩亭、值班房、美心亭、围墙,并对整体区域进行了水泥硬化,开凿了新的登山台阶。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文物保护理念和技术的指导,新建设施极大地破坏了大佛寺的原有格局和地形地貌,影响了文物整体的景观风貌。随意摆放的石质、砖砌和铁质香炉,距离文物较近,每到重要的宗教节日,信众甚多,浓烟滚滚,火光冲天。2004年,五佛殿东侧区域曾出现严重的滑坡危害,为保障文物及游客安全,管理部门封闭了弹子石摩崖造像区域。但直至2017年,仍可见信众在围挡外围燃香焚烛,烟灰满地。
(四)“两线”划定不合理导致无法确保文物安全和环境控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市、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第十八条规定:“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划定文物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是保障文物安全和文物环境风貌协调的重要举措,是国家文物局进行审批和执法的直接依据[6]。
弹子石摩崖造像虽然划定了保护区划,但保护范围仅包含沿江大佛和五佛殿,其他的保护对象,如围墙、遗址及台基、钟鼓亭等都未纳入其中,出现遗漏,不能满足保护的完整性要求;建设控制地带范围较小,未将大佛寺的整体格局纳入其中,无法有效地遏制区域内的建设活动对历史格局的破坏;保护区划的边界也没有结合地形地貌和建设现状进行划定,不具备管理上的可操作性。
四、主要规划措施
(一)规划目标
以摩崖造像本体及其相关环境为保护对象,力求真实、完整地保存和延续弹子石摩崖造像的历史信息及价值,合理利用和充分展示其文化价值和历史内涵,实现摩崖造像的有效保护和科学管理,建立川渝石窟综合保护利用示范基地和重庆市一流文化景区,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谐发展。
(二)解建立综合防控体系解决文物残损的根本问题
石质文物的技术保护历来是文物保护行业的重点和难点,在经过了多年的发展以后,由于化学保护的不可逆性,目前行业内基本摒弃了大规模化学保护的方式,开始从解决石质文物所处环境及微环境的调整入手,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摩崖造像的各项病害都与水密切相关。无论是自然降水和空气中的水汽,还是地下毛细水和岩石裂隙水,这些都是造成摩崖造像各种残损的主要原因。因此,解决弹子石摩崖造像各种形态的水的问题,是保护弹子石摩崖造像本体的重要手段。通过现场勘察,规划提出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1.解决摩崖造像顶部排水。结合城市排水系统,在文物载体东侧沿道路设立干渠、支沟、毛沟等排水系统,汇集雨水疏导至山体两侧,减少造像区的渗水,所在排水沟均应有防渗和防冲刷措施;2.防止裂隙渗水。在顶部或壁面有裂隙渗水之处,进行防渗堵漏灌浆。防渗堵漏灌浆要选择最适宜的防渗灌浆材料,采用压力注浆的方法,封闭岩体中的各种渗水通道。灌浆材料应与岩体强度相近,并有一定韧性;3.完善窟前排水。大佛造像西侧设置主、干、支沟组成的统一合理排水系统,并与山顶排水系统相衔接,使雨水能尽快排出文物所在区。通过对区域整体的排水处理,降低各种形态水对摩崖造像的危害。
除了改善弹子石摩崖造像所处的环境外,还需对石质文物本体进行技术处理。对于表面风化严重的造像区域,应进行病害发展监测,根据监测结果进行专题研究。在实验证明科学可行的前提下,对继续发展的病害问题进行防风化加固。依据文物的具体材质和病害形式等特点,对目前本体存在的裂隙病害进行灌浆加固修复。
建设完善的防护体系是保障文物安全的另外一个重要手段。通过建设安防系统,划定安防区的方式,消除区域内的安全隐患;针对火灾隐患突出的情况,结合城市整体消防设计,建设区域内的消防系统,并安排专人进行巡查;在地势较高区域建设引雷设备,降低雷击风险;由于地处长江沿岸,结合历史记载,存在洪水威胁,因此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建立预警机制,第一时间取得雨水、洪水等相关预警信息,定期演练,密切监视因强降水和洪水造成的次生地质灾害。
文物检测和监测是石质文物及时发现问题,将隐患消除于萌芽状态的重要手段。它可以更加及时地了解文物本体及其历史环境的危害因素,准确地分析其保护条件和需要,并可以为保护管理提供依据,加强文物的预防性保护水平,提高管理决策的科学性。监测报告可以记录文物各个时期的变化数据,为开展科研工作提供资料。弹子石摩崖造像的监测工作应由重庆市南岸区文物管理所直接负责,配备专门的设备,对文物保存状况、管理状况和游客状况等进行监测,形成专业的监测报告成果,定期分析研判。
(三)突出核心价值来发挥自身优势实现因地制宜实现保护与利用的协调发展
巴蜀地区是中国古代摩崖造像较为集中的区域。根据文物普查统计,重庆市范围内尚存的摩崖造像数量为200余处,主要分布重庆大足、潼南、合川、江津、荣昌、南岸等25个区,分布较为集中,可以形成良好的集聚效应。在重庆市发现的所有摩崖造像中,元代造像仅有4处,弹子石摩崖造像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弹子石摩崖造像位于南滨路西侧,南滨路是集防洪护岸、城市道路、旧城改造和餐饮、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城市观光休闲景观大道。作为重庆市的重要窗口,南滨路正在整体提档升级,开展的慈云寺-米店街-龙门浩传统风貌示范区建设,是重庆市首批启动的五大历史文化街区及传统风貌示范区之一,展示资源包括巴渝文化、宗教文化、开埠文化、码头文化、抗战遗址文化等。
根据弹子石摩崖造像所处位置及周边环境特点,规划将弹子石摩崖造像所在区域建设成为以摩崖造像为核心的文化公园,主要展示文物本体、历史格局以及历史文化内涵。文化公园以“一区、两线、多点”为结构,构建展陈分区,将原本的宗教活动场所功能换变为文化、教育、休闲、旅游以及专业研究为一体的综合性利用场所。尤其是对于大佛寺的历史路线的深度挖掘,提供了新的展示视觉。游客可通过原始的登山路线进行参观,以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场景,进行沉浸式的参观体验。
(四)调整“两线”从而将文物保护嵌入到城市发展中实现双赢
原有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无法满足文物保护和文物环境风貌控制的需要,割裂了周边的地形地貌之间的联系,且不利于城市发展及建设。此次将保护范围扩大,把所有的文物本体皆纳入到保护范围中,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安全;结合周边地形地貌,衔接已经制定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在保持文物环境风貌协调的前提下,根据建设内容和控制强度的不同,将建设控制地带进一步划分为一类建设控制地带和二类建设控制地带,并分级制定管控措施,既满足了文物环境风貌保持的要求,又与城市建设保持了协调[7]。
五、结语
通过此次文物保护规划的实践,总结出石窟寺及石刻类文物保护规划在调研和编制过程中应注意的主要四个方面:
(一)厘清原有格局是重要前提
摩崖造像的保护多不是独立存在的,一般都会与寺院、塔林或其他的宗教设施共存。因此在前期研究和现场调研的过程中,应对包括摩崖造像本体在内的整体格局认真梳理,仔细研究,尤其是各个时期的历史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能够反映文物的历史沿革,更重要的是可以揭示文物的内在价值。摩崖造像的保护应是与寺院、塔林、其他宗教设施以及依附山体、地形地貌的整体保护。
(二)细化分析文物病害从而解决根本问题是重要内容
石质文物的保护历来是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难点,所具有的手段单一、工艺复杂、可逆性较差等特点,要求保护措施的制定应当非常慎重,因此前期文物病害的勘察,病害原因的分析则显得尤为重要。摩崖造像的病害除与本身岩性相关外,还极易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如光照、温差、降水、风、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等。准确区分判断影响保护对象的最主要,影响最大的破坏因素,并针对性地予以干预,从根本上消除或减缓破坏,是摩崖造像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的重要内容。
(三)因地制宜地展示利用策略是发挥社会价值的重要手段
根据对目前国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摩崖造像的调查,绝大多数的摩崖造像区域已被辟为景区,或作为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放展示,如重庆大足石刻、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等,这些都是摩崖造像的典型代表。但并非所有的摩崖造像都具备开辟为景区的条件,同时,鉴于石质文物对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较高,较大程度的环境改变也会对文物的安全造成影响[8]。因此,因地制宜地选择展示利用策略和手段,是发挥文物价值的重要手段。此次弹子石摩崖造像的展示利用充分考虑了其原有的历史功能、所处的江边绿带位置、相关规划中的定位、目标指向人群以及周边土地和交通情况,以“减法”的形式对所处环境进行调整和规划,保障文物安全,完善展陈配置,丰富展陈内容,提升参观体验。
(四)城市区域内规划衔接是重要保障
城市范围内的文物保护规划编制一直是规划编制的难点之一。由于城市更新速度快,建设活动频繁,建设强度大等原因,文物的保护、管理和利用往往与城市的发展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要守住文物保护的“底线”,同时也要敞开文物的“胸怀”,文物的保护与城市的发展并不冲突,是可以达到和谐共生的。只有做好如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旅游规划、道路交通规划、产业规划、空间规划等相关规划的衔接工作,才能确保文物保护规划的顺利实施[9]。
可以预料的是,十几年后,在重庆市弹子石区域高楼林地的商业中心区周边,一处幽静安详的文化公园必将成为当地居民重要的教育和休闲场所,公众在游览的同时,也会为我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而感叹,被古代先民的聪明才智以及高超精湛的雕凿技术所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