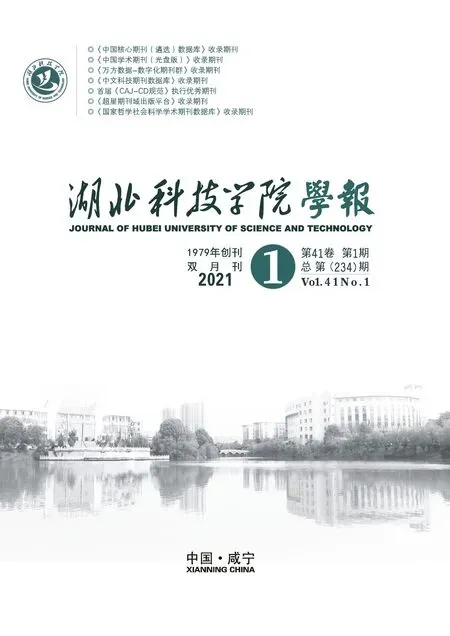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犯罪问题的媒体呈现
——以《泰晤士报》涉谋杀案报道为中心
王宇平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社会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犯罪率迅速上升,犯罪及其治理成为贯穿维多利亚社会的重要议题,犯罪问题由一项个体的安全问题深化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紧要层面。19世纪蓬勃发展的报刊业,为犯罪问题社会角色的成熟提供了必要的生存土壤。作为全国性报刊的《泰晤士报》将谋杀案及其刑事司法进程作为呈现重点,建构起探讨转型时期工业社会道德争议与司法困境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目前国外学界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犯罪史的研究已比较成熟,犯罪报道是其重要分支,相关成果颇丰,但对谋杀案报道未给予足够重视,对谋杀案报道特征及影响论述不足。国内学界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犯罪问题已有一定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陆续涌现。陈力丹、姜德福等学者对19世纪英国新闻传播发展情况予以关注,但尚无对维多利亚时期犯罪报道及其影响做出论述的相关论著。基于此,本文试图将谋杀案报道置于社会转型期的特殊背景下加以考察,对维多利亚时期发行量最大、受众最广的《泰晤士报》的谋杀案报道进行文本分析与内容阐释,勾勒出中产阶级对谋杀行为的道德与法律阐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谋杀问题公共领域的建构,如何重塑家庭、性别等价值观念,并成为延续英国法治精神的开拓性实践,试图为理解中产阶级如何从道德、法治双重层面推进社会控制进程提供新的视角。
一、谋杀狂热:《泰晤士报》犯罪报道概况
19世纪,英国大众传媒时代拉开序幕。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与识字率的提升,报刊阅读超越上层阶级的特权,成为各阶级公众获取信息主要渠道。凭借着雄厚的资本优势与先进的管理经验,《泰晤士报》成为这一时期发行量最高、受众最广的公众读物,逐步确立起了国家报刊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泰晤士报》是英国历史进程的见证者与引路人,其对社会事件的关注与呈现,深刻影响着维多利亚社会的演进。谋杀案作为 “低俗怪谈”(penny dreadful)、“犯罪大字报”(crime broadsheet)等廉价读物为博取眼球而贯用的主题并不罕见。这一时期,以追求真相、用词严谨著称的主流报刊《泰晤士报》却也对充满“人情味”(human interest)与“轰动性”(sensation)的谋杀案给予了密切关注,围绕谋杀案及其刑事司法程序,呈现出社会犯罪问题的拟态现实。
(一)《泰晤士报》犯罪报道主题的谋杀案转向
1. “第四等级”报刊与社会犯罪报道
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由于社会制度建设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贫困、犯罪等问题频发,社会问题严重。与此同时,随着印刷技术水平的进步,维多利亚时期报业发展迅速,各类社会问题成为报刊探讨的重要内容,由此,严肃报刊被称为对政治和社会事务产生重要影响的,独立于议会之外的“第四等级”(The Fourth Estate)。其中,《泰晤士报》逐步确立起全国报刊的地位,依托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成为中产阶级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泰晤士报》由约翰·沃尔特创建于1784年,起初定位为以刊登商业信息为主的经济类报刊,19世纪以来,在沃尔特二世与托马斯·巴恩斯(Thomas Barnes)的管理下,《泰晤士报》开始成为一份自由、独立的日报。《泰晤士报》凭借其坚实的资本优势引进蒸汽印刷机,率先采用轮转印刷机技术,抢占了报业技术革新的先机。到1847年,(沃尔特二世)率先采用轮转印刷机技术,同年就使报纸达到每天12版,这在当时整个世界上都是少见的[1]。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工业社会突飞猛进的时刻,但与此同时,各类社会矛盾也陆续爆发,犯罪率迅速提升。作为一项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犯罪及其治理的探讨占据了《泰晤士报》核心报道的一席之地。发生于社会贫困阶层之中的财产类犯罪,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主要犯罪类型。经济结构变化导致失业问题严重、基础设施建设缺乏导致的生存环境恶劣,是底层阶级为解决生存问题进行小规模偷窃的重要原因。维多利亚时期评论家们所描绘的犯罪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是贫穷工人阶级的同义词,尤其是那些靠临时工作生存的工人阶级。社会上层人士普遍认为,在底层阶级中,存在着一个犯罪阶级。这一犯罪阶级极度贫困且道德感低下,生活在一种“及时行乐”的氛围之中,不懂得延缓欲望与享受。他们在贫困、酗酒的累积之下,最终走上犯罪道路。《泰晤士报》也对犯罪问题的呈现与探讨给予了较大关注。《泰晤士报》每日发行一版,从1830年每版4张到1890年每版12张,综合而言,犯罪报道与议会讨论、重要社论同处于报纸的中间页面。
2. 由抢劫到谋杀:《泰晤士报》犯罪报道选题的转变
相比于创刊初期,维多利亚时期《泰晤士报》的犯罪报道主题明显呈现出一种“谋杀案转向”。在各类犯罪行为中,谋杀案及其司法程序得到了《泰晤士报》的青睐。从报道数量上来看,涉谋杀案报道数量远高于其他犯罪(参见图1)。《泰晤士报》年均涉谋杀报道约741篇,远高于同时期从数量上看更为严重的“偷窃”(Theft)、“抢劫”(Robbery)等的年均报道数,分别仅为117篇、338篇。从变化趋势上看,报道数量波动上升。19世纪80年代报道数量整体较高,年均报道数量达1 051篇。这与80年代以来“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的兴起密切相关。文学要素被引入新闻创作之中,为犯罪报道提供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彼得·金(Peter King)在对18世纪谋杀案报道开展研究后认为,报道一半以上都关注拦路抢劫……谋杀及谋杀未遂的报道只占百分之五左右[2](P101)。可见,密切关注谋杀案是一种始于维多利亚时期的新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谋杀案的数量在维多利亚时期并未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这便与《泰晤士报》的报道重点产生了一种矛盾。维多利亚时期,以偷盗为主的生存型犯罪是较为严重的犯罪类型,谋杀案并未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相比于欧洲其他国家,19世纪英格兰谋杀率更低。在1857-1890年间,在警察处得以被记录的谋杀案每年基本不高于400起,而在1890年前后,平均数量则低于350起[3](P42)。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谋杀率仅在1865年达到了万分之0.2。通常情况下,谋杀率仅保持在约每万分之0.15,至1880年下降到万分之0.1,在19世纪末期,谋杀率更低[5](P42)。谋杀案的社会影响范围也日益缩小,多发生于底层社会熟人之间,发生于陌生人之间的谋杀案件数量下降。有学者十分确信地指出,暴力犯罪开始受到更多的社会限制, 虽然到1800年还不完全是下层社会的特权,但贵族或城市精英肯定不太可能参与其中[6]。 由此可见,维多利亚时期,犯罪报道呈现出了一种“谋杀案转向”,即报道重点由发生频率高、所影响社会范围相对更广的财产类犯罪转向了发生频率低,所涉社会范围相对有限的人身侵害类犯罪,对犯罪行为本身的关注超越对犯罪行为社会危害的关注。基于此,《泰晤士报》涉谋杀案报道呈多层次展开。

图1 《泰晤士报》涉“谋杀”(murder)报道文章数 (1830—1910)
(二)《泰晤士报》涉谋杀案报道的内容概述
现代英国早期,木刻版画(woodcuts)、小册子(pamphlets)、犯罪大字报(broadsheets)、叙事民谣(ballad)等公众读物是公众接触谋杀案的主要途径。以上读物的犯罪叙事要点可归纳为两方面。第一类,如木刻版画、犯罪大字报等仅强调刑罚结果以达到威慑、警示作用。第二类,如小册子,则将犯罪过程文学化,注重案件本身的道德教化目的。维多利亚时期,在社会转型造成的道德争议与司法困境成为新的社会问题这一背景之下,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主流报刊对谋杀案的关注也呈现出了新的视角。
1. 勾勒刑事司法体系
《泰晤士报》涉谋杀案报道分布栏目广泛,体裁丰富,基本勾勒出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刑事司法体系概貌,从制度与执行两个层面作出了详细记载(参见图2)。19世纪,英国设立中央与地方各郡两级体系负责受理全国范围内的“可诉讼案件”(indictable offence),谋杀是这一级别犯罪行为受审的重要内容。在中央层面,伦敦设“老贝利”(Old Bailey)负责受理情节严重的刑事案件。在18世纪50年代,‘老贝利’一年约开庭八次。1834年起,‘老贝利’扩大并移建,成为我们如今所知的中央刑事法庭(Central Criminal Court)”[5](P14)。而发生在地方各郡的刑事案件由中央刑事法庭下设的“巡回法庭”(Assizes)受理,由两名法官分理民事与刑事案件。在18、19世纪,英国每年会设立两次巡回法庭,在大多数郡的郡县举办(county towns),时间分别在‘大寨节’(Lent)以及夏季[5](P14)。《泰晤士报》在巡回法庭方面设有“北方巡回法庭”(Northern Circuit)、“米德兰巡回法庭”(Midland Circuit)、“牛津郡巡回法庭”(Oxford Circuit)等专栏,对开庭期内涉谋杀案情况只做简要概括。从程序上看,从警察获知消息、侦查、审讯、处决各内容均有所涵盖。对特别关注的案件,以上四方面进程篇幅均较长。一般案件,则侧重报道庭审过程,忽略其他信息。社论则多从道德、法律两个层面对案件进行舆论导向极强的评论。通过报刊阅读,英国刑事司法体系的设置及运作得以再现。配合读者来信的刊登,以报刊为载体,以谋杀案为中心的相对完善的“公共领域”初步形成。

图2 《泰晤士报》涉谋杀案报道分布概况(1830-1900)
2. 内涵外延丰富的报道内容
《泰晤士报》以独特的视角重构谋杀案,报道主题多样,内涵外延丰富。曼宁夫妇凶杀案,即柏蒙西谋杀案(Bermondsey Murder)发生于1849年8月9日。曼宁夫妇被指控因财谋杀并于自家厨房处理了曼宁夫人的情夫欧康纳(O’Connor)的尸体。该案件曾轰动一时,《泰晤士报》对此共作出了52篇详细报道,报道具备完整性、连贯性。以此为例,《泰晤士报》重大刑事案件报道基本遵循以下逻辑推进。案发初期,集中于对案情的回顾,包含对案发过程、逮捕过程的冗长叙述,遵循理出案件疑点、对执法人员进行监督批评的框架。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追捕凶手成功的消息。这可怕的事件所引起的兴奋还没有消退,房子简直被渴望看到它的人包围了。大门由警察把守,看来以警察的能力只能压制公众的好奇心”[8]。“追踪潜逃者的过程缺乏警惕,令人遗憾”[9]。对凶手、被害人生平的叙事同样占据了大量版面。女性杀手玛丽亚·曼宁(Maria Manning)被描绘为“一个勾心斗角的女人”[10],并称曼宁先生“与玛丽亚·曼宁结婚的唯一诱因是想要在政府中获得一席之地”[11]。审判前,二者的形象已被提前判定。在漫长的庭审记录后,便是对“死因裁判法庭”(Coroner’s Court)、“中央刑事法庭”(Central Criminal Court)庭审过程的客观陈述;随后,记叙死刑过程,包括行刑当天凶手的心理描写及细微的动作描写、现场的公众反应等;最终是对案件细节的回顾与评议,包括对刑事司法程序、涉案双方的探讨。以上内容中,对追缉、审判过程的记述符合重大刑事案件呈现的基本逻辑框架。在此基础上,与案件本身无关的细节轰动性描写也占据了大量版面。
《泰晤士报》谋杀案报道主题复杂,其轰动性描写可以看作对英国传统犯罪读物风格的继承与延续。但其所呈现出的对刑事司法体系的专业性记录,却是一种维多利亚时期的新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得益于司法体系与传媒界的密切结合。司法体系中的个人与新闻界中的个人是《泰晤士报》谋杀案报道的两大重要来源。“律师新闻记者”(lawyer reporter)是《泰晤士报》谋杀案报道中与刑事司法进程相关部分的主要撰写者。律师新闻记者为报刊供稿,是维多利亚时期法律界默许的现象。“在我们的法庭上,可以看到,在一个特殊的隔间里,一个忙碌的笔记员正在记录诉讼过程,这个人也同样正在为新闻界准备稿件”[12]。聘用律师新闻记者为报刊撰稿符合司法界与传媒界的共同利益。19世纪二元律师制度确立,成为一名出庭律师(barrister)所耗费的时间、金钱成本极高,“在律师界谋生绝非易事”[13]。由此,为报刊撰写法律新闻成为律师谋生的重要手段。这与《泰晤士报》强调报道专业性的需求不谋而合。1847年约翰·德兰恩(John Delane)任总编辑以来,多次对报刊进行改革,聘请最好的作家为报刊撰写稿件,努力使报纸办得高雅不俗[1](P116)。法学对专业性要求极高,英国历来采取会馆制培育法律人才,正规的法律教育是唯有少数精英得以享有的奢侈品。19世纪抗辩制、交叉问询融入刑事司法体系,愈发加大了普通文人撰写法律新闻的难度。以上背景下,都认为自身具有社会道德维护者使命的法律界与新闻界一拍即合,律师群体撰写法律新闻这一专业、高效的举措由此诞生。
通过《泰晤士报》的谋杀案呈现,英国刑事司法体系跃然纸上。在早期现代社会中,作为谋杀案载体的犯罪大字报是一种简短与虚构性并存的文学体裁,公众与谋杀行为保持疏离感。《泰晤士报》谋杀案的媒体呈现拉近了公众同犯罪及其法律问题之间的距离,建构起一个对社会犯罪问题进行探讨的公共领域,为探讨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争议与司法困境提供了绝佳素材。
二、《泰晤士报》谋杀案报道的三重维度
彼得·金指出,在英国人眼里,一提到“犯罪”便会联想到“谋杀”[4](P105)。直至18世纪末期,谋杀案作为低俗怪谈、犯罪大字报等廉价读物的重要主题,在道德教化、社会娱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与社会矛盾的转变,犯罪问题及其治理愈发复杂。尽管少数读物仍注重谋杀案博取眼球的商业利益,各类严肃报刊已开始对谋杀案加以利用,作为形塑舆论、有力传达其编辑理念的秘密武器。19世纪致力于提升政治与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执掌《泰晤士报》,承担着辩白中产阶级身份合法性、开化获得政治权利的底层阶级的双重任务。从这一层面而言,谋杀案被赋予了独特的写作意义与传播价值,成为一种多维、复杂的叙事文本。
(一)对维多利亚时期主流价值观的宣传与强调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中产阶级迅速发展,并形成了一套专属于自身的价值体系。在工业文明迅速推进的背景下,中产阶级标榜自律、审慎作为自我新兴阶级合法性的象征,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独特的家庭观及性别观。《泰晤士报》是中产阶级宣扬自身言论立场的重要阵地。在《泰晤士报》对谋杀案的报道过程中,以上因素也通过新的方式得以呈现。
1. 维多利亚时期家庭观念的反面教材
以家庭观念为核心,以性别分工为主要内容的中产阶级道德观念,是《泰晤士报》谋杀案报道的重要指导思想。谋杀案件性质是否符合中产阶级对转型社会的道德关切点,是报道主题抉择的重要依据。维多利亚时期,谋杀案类型可划分为发生在熟人之间即夫妻、母子、主仆之间的谋杀行为,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由公众斗殴、工作冲突、抢劫、罢工等行为引发的谋杀两类。其中,发生在家庭内部的谋杀案比率较高,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之间约占谋杀案总数的55%,而18世纪这一比例仅为28%[14]。发生在熟悉成员或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杀案、毒杀案是《泰晤士报》谋杀案报道的重点。1855年被害者为凶手好友、兄弟、岳母、孩子等七人的鲁奇利毒杀案、1842年凶手残忍肢解情人的罗汉普顿谋杀案等,都是《泰晤士报》的重点报道案件,报道篇数分别为48篇、20篇。报刊对情杀、毒杀案的聚焦,使家庭内部矛盾可视化。
谋杀行为暴露了发生在“家庭领域”(domestic sphere)的通奸、暴力等行为,对维多利亚时期赖以维系的家庭观念提出挑战。工业革命促成了传统农业社会经济模式的瓦解,家庭手工业被工厂手工业代替。家庭的生产职能弱化,情感职能增强,成为中产阶级道德观念中的核心内容,被称作工业生活巨大压力下的私人避风港[15]。情杀案与毒杀案意味着家庭领域背叛者的出现……只有家中熟人、密友才能执行这一亲密举动[16]。实际上是一种家庭领域的叛国罪(Domestic Treason)[17]。值得注意的是,毒杀案在维多利亚时期发生概率极低。在1849年英格兰及威尔士地区超过20 000起的无法解释的非自然死亡中,有415件被认为与毒杀有关。在排除自杀行为及误食毒药之外,只有11件被指控为毒杀案,且并非所有案件最终都被判处有罪。因此蓄意毒害大概只占据非自然死亡中的3‰[18]。 由此可见,经由《泰晤士报》的呈现,对案件细节与人物矛盾进行详细描写,提升了以往相对隐蔽、社会影响力较小的两类谋杀行为的可视性。
2. 维多利亚时期性别角色的异类
《泰晤士报》谋杀案叙事文本建构过程中,强调了维多利亚社会赖以维系的性别观念。社会预期的性别角色内涵,成为报刊平行于法律程序外,对案件嫌疑人进行“道德审判”的“不成文法律”。19世纪工业社会赋予了“男子气概”(masculinity)新的内涵,“自控”(self-control)成为理想男性气质所应具备的重要内容,为整个社会所推崇,正如马丁·威纳(Martin Weiner)所言,“正在形成的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使个人自律、秩序和非暴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宝贵和必要”[19]。自律即拥有理智的头脑、控制自身的暴力倾向,成为中产阶级男性所推崇的重要特征。1855年,医生帕尔默被指控毒杀其好友、兄弟、岳母、孩子等七人,以骗取保险金。在这一轰动事件尘埃落定后,《泰晤士报》在评论中写到,“他的一生和他所犯下的罪行,是一个可怕的教训。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下滑如此生动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实属罕见。我们唯有以此案为例,以警示那些即将酿成大错的人”,“从赌博到资不抵债,从资不抵债到伪造文件,从伪造文件到谋杀,他成为了最下流的人。他充满戏剧性的一生,令人深思”[20]。由此可见,赌博、伪造等自律丧失的行为,被与谋杀行为建立直接联系。
《泰晤士报》谋杀案的详尽报道使女性经历以人物外貌与社会经历为对象的道德审判。维多利亚时期的理想女性被称为“家庭天使”,她“最大的功能是赞美”[21]。她们被要求保持优雅,并拥有“克制容忍”[22]的态度。对女性犯人的描述可大致划分为两类,“受怜悯者”与“性别异类”。出身高贵举止优雅或柔弱的女性是典型的“受怜悯者”。同样是毒杀丈夫的案件,并涉通奸行为,《泰晤士报》对待出身高贵的梅布里克夫人(Mr.s Maybrick)与夏洛特·哈里斯(Charlotte Harris)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梅布里克夫人被称为“绝不是低能或愚笨的,相反,不管她那迷人的头脑所要达到的目的有多坏,她都是相当聪明的”[16]。这样的评价很大程度上由于梅布里克夫人出身高贵,并在庭审过程中注重自身优雅克制的形象。而夏洛特的行为则被称为“一种迄今为止闻所未闻的暴行”[23]。 另一类“性别异类”,她们的谋杀举动被与性别倒错特征相联系。玛丽亚·曼宁被称作“既不端正,也不女性化”[10],“作为一个女人,她具备一切女性不该拥有的异端特质”[24]。这种“道德审判”与划分显然以“家庭天使”标准,即中产阶级对理想女性的期许为依据,使女性罪犯在刑事司法进程中的一切细微举动备受关注。
(二)对维多利亚时期司法体系的还原与评述
除涉及潜移默化的道德要素外,《泰晤士报》对谋杀案的报道还是转型时期司法改革的镜像。依托谋杀案报道,《泰晤士报》将各项刑事司法进程的运作过程详细呈现在公众面前。在案件发生初期,《泰晤士报》会对嫌疑人做出迅速判断,“我们怀疑犯下这项可怕罪行的是丹尼尔·古德”[25],并在“附加细节”(Additional Particulars)中刊登嫌疑人的基本信息。在案件的侦查取证阶段,警方公正执法的工作态度得以详细展示,“督查”(superintendent)“巡视员”(Inspector)“小队长”(Sergeant)“巡警”(Constable)的工作汇报各占特定篇幅。报道以“警方正以全力追击凶手”[25]为报道收尾,对各方作用的发挥给予肯定与强调。同时,报道注重引导公众对案件的理性参与,在刊登悬赏令的同时,对小报的不实信息予以核实勘正。在案件的审讯阶段,报道对庭审过程全盘再现,法官、辩护律师身份、开庭时间得以详细记录。法官、嫌疑人、陪审团宣誓、交叉质询、验尸报告被全文刊登,但与《中央刑事法庭审判集》所记载庭审资料略有区别,报道往往融合了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的方式,在适当时刻对当事人做出特写。在罪犯的处决过程中,读者基本能够坐在家中“观看”到罪犯如何从监狱走向刑场。这一过程中罪犯与狱卒、长官、行刑者进行的对话、罪犯的情绪变化等细节被详尽刻画。绞刑现场的血腥场面也被细致描绘。在案件结束后,《泰晤士报》会在观点与社论中对案件法律环节的得失做出评判。
《泰晤士报》注重引导读者从专业视角解读相关案件,对案件中司法程序及判决疑点提出质疑,为司法改革设置舆论导向。以柏蒙西谋杀案为例,在中央刑事法庭进行公开审理前,《泰晤士报》浓墨重彩阐明这一审判结果在刑法史中的重要意义。报道提出,“我们应该已经观察到了。丈夫和妻子将会同时站在法庭上受审——这一情况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夫妻同时受审十分罕见,而且这关乎如何划定案件中的法律行为责任。在英国法律中,已婚女子享有很多特权,同时也受到诸多限制。而在目前的这一案件中,存在如下可能性,即尽管她已犯下犯罪的罪行,但她可能免于法律的惩罚”[26]。 法律判决的性别差异在维多利亚时期备受争议。诸多研究者达成共识,“一直以来,易被判以人身侵害罪的多为男性而非女性”,“在刑事司法进程中的任一阶段,女性都倾向于被从轻处置”[27]。 这与当时犯罪学家对女性特质的诠释与女性法律地位的模糊性密切相关。维多利亚时期犯罪学家认为“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讲,女性一向柔弱,相比男性她们不易犯罪”[28]。而从具体的法律规定而言,“已婚女子(feme covert)婚后没有独立的合法身份……这意味同丈夫一起犯下重罪的已婚女子,可以此为理由获得赦免”[5](P94)。《泰晤士报》借曼宁夫妇二人受审这一事实,敏锐地捕捉到了维多利亚时期法律执行过程中的争议,引导公众对此作出思考。在1889年发生的利物浦毒杀案中,《泰晤士报》提醒公众注意毒杀案证据模糊性及审判程序的漏洞。“我们相信,大部分人不会相信对梅布里克夫人(Mr.s Maybrick)作出的有罪判决……在证据如此有限的情况下,理应因‘无法证明’而作出无罪判决”“如果法庭允许对梅布里克夫人实施交叉问询,我们大概会更接近真相……希望这悲惨的一切至少能够换来一场法律的改革”[16]。 由此可见,通过对刑事司法进程的详细记录,谋杀案成为公众司法教育的重要素材。对刑法争议的合理把控,也使《泰晤士报》成为转型时期刑事司法改革的辩论场。
(三)对轰动氛围的创造及渲染
《泰晤士报》谋杀案报道作为新闻产业化的产物,在工业化迅速推进的背景下,商业利益固然成为其追逐的重要价值。在谋杀案报道过程中,《泰晤士报》以文学性极高的笔法,提升了报道的轰动性与可读性。1828年红谷仓事件的凶手威廉·科德(William Corder)在谋杀情人案件中,《泰晤士报》运用各类描写手法,直接引语、间接引语混用,描绘了一个在审讯过程中“声音略有颤抖”地为自己开脱,在交叉询问环节“垂头丧气”的狡猾、受教育程度低、带有愧疚与心虚的罪犯形象。在行刑日对其的报道中,主要采取叙事抒情方式。“在行刑的前一晚,他讲述了自己婚姻的细节。”报道提及了在杀死情人后,他通过报纸广告征集另一半提出“会穿特定的裙子去教堂,并且会坐在特定的地点等待”“他说他按照要求前往了教堂,但由于记错了礼拜的时间没能见到那位夫人”[29]。 该报道还刊登了他给现任妻子的信,临行前的凶手变成了一个忠于婚姻、有血有肉甚至令人同情的“人物”。《泰晤士报》犯罪报道文学性极强的报道方式的形成,是自由主义经济背景下,报刊商业竞争的产物。19世纪,以谋杀案为对象的非虚构类作品颇丰,轰动性叙事是犯罪小报、廉价报刊等读物的惯用手法。在应对以上读物在犯罪报道领域对《泰晤士报》提出的竞争的过程中,《泰晤士报》对轰动性的报道方式加以扬弃。
综上所述,《泰晤士报》谋杀案报道特征极为复杂。在早期现代社会中,读者能够接触到的谋杀案十分有限,对谋杀行为保持疏离感。在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主流报刊的建构下,谋杀案在日常社会中的“可视性”提升。高发于家庭领域内,紧扣维多利亚时期备受争议的道德与司法争议的谋杀案,拉近了一名普通公众与谋杀的距离,也拉近了其与刑事司法体系的距离。当距离被拉近,无论是因谋杀案产生的恐慌情绪,还是对社会司法体系的认知,都将产生重大变化。
三、诫与罚:文明社会下谋杀案角色的转变
在西欧社会,约从17世纪早期开始,致命暴力行为显著下降,诺贝特·伊莱亚斯(Nobert Elias)称此为“文明的进程”(civilizing process)。通过国家集权的建立及随之而来的各类“规训机制”(disciplining institutions)对社会生活的渗透,自制(self control)得以维持,这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社会诞生的关键因素。自制与否实质上成为衡量不同历史时期个体行为是否符合主流价值观念的标准。内在思想与外在形制控制的加强,是实现自制的重要途径。维多利亚时期,《泰晤士报》对谋杀案的关注与解读赋予了谋杀案在推进文明社会进程中新的作用。
(一)中产阶级价值观入法的催化剂
《泰晤士报》的谋杀案报道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向刑事司法领域渗透产生了一定影响。从立法层面看,维多利亚时期法律对家庭领域的干预显著增强。即使到19世纪初期,家庭内部暴力问题仍是一项法律边缘问题。1830年,格拉斯哥地方法官在对一名家庭暴力者的判决过程中指出,“如果被起诉者对其他人而非他妻子施行了家庭暴力,他确实应被严惩,但他殴打的不过是他妻子”[30],最终施暴者仅被处以较小数额的罚款。对家庭领域(domestic sphere)的维护,即是对中产阶级身份合法性的辩护。《泰晤士报》向来提倡对丈夫对妻子的人身侵犯行为加以严惩。在一次家庭暴力案件后评论道,“人身侵犯行为目前并未在法律中得到适当的惩罚”[31]。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中产阶级眼中,家庭领域发生的谋杀行为是维多利亚时期一项极具道德争议的问题。维多利亚男性被认为是家庭与道德的守护者。19世纪以来,打妻子的人越来越被妖魔化,被认为是一种工人阶级的问题[5](P104)。家庭领域的暴力行为与工人阶级酗酒、暴力的形象相联系,成为中产阶级道德规训的重要层面。依托对家庭领域内谋杀行为的关注,《泰晤士报》提升了这一类谋杀行为的可视性,为国家立法对家庭领域加以干预提供了舆论基础。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直至维多利亚末期,特别是从1853年开始,基本每十年便会通过一部新的立法。以上立法以保护柔弱的女性与改造暴力的男性为主旨,成为规范家庭领域道德秩序的强制性力量。
从司法实践中看,《泰晤士报》谋杀案报道对女性杀人犯形象的塑造往往激起强烈的舆论反应,是否具有社会公认的性别特质,成为影响女性罪犯司法判决的重要因素。这种舆论导向对司法判决施以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判决结果。以巴恩斯悬案和利物浦毒杀案为例,两案在审判过程中均面临着证据不足的困境,而舆论对于审判的预期却大相径庭。在巴恩斯迷案中,凯特·韦伯斯特的异邦、非女性化特质被反复强调重点,无疑增加了公众先入为主的厌恶感。《泰晤士报》称,凯特·韦伯斯特一案的证据是“尽管冗长却不薄弱,形成了间接证据链,陪审团完全有勇气由此判定她就是这一罕见暴行的实施者,不会有人怀疑他们判决的正确性”[32]。而在梅布里克案判决后,《泰晤士报》指出,“我们相信,大部分人不会相信对梅布里克夫人(Mr.s Maybrick)作出的有罪判决……在证据如此有限的情况下,理应因‘无法证明’而作出无罪判决”[16]。舆论影响了面对女性犯罪者的司法实践的差异,这一差异进而成为维持主流性别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
萨义德在论及东方主义时曾言,“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与维系均需要另一种相异、相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存在”,“身份的建构……涉及建立一种相反的‘他者’(opposite),而这种差异性实质上是通过不断解读、重释与‘我们’的区别建构起来的”[33]。《泰晤士报》借谋杀案对社会道德的“他者”加以曝光、探讨,推动了部分中产阶级视角下的家庭观念与性别观念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成为影响司法实践的重要因素。由此,在某种程度上,《泰晤士报》的谋杀案报道成为核心价值观影响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重要途径之一。这赋予核心价值观权威性,强化了主流价值观念的道德规训作用。
(二)维多利亚时期法制现代化的灯塔
1. 揭露维多利亚时期的司法改革困境
19世纪被认为是“英国及其司法制度同初步实现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的社会现实之间的一次整合运动”[34]。面对经济基础的变革,司法体系面临的困境接踵而至。在一个阶级矛盾激化的社会中,司法公正性成为激进报刊质疑的对象,法律权威性岌岌可危。“北极星报”(the North Star)“宪章通讯”(the Chartist Circular)等报刊作为传播工人阶级理念的前沿阵地,作为阶级权力象征的法律是其质疑重点。质疑论调在其刑事案件报道中显而易见,“北极星报中充斥着穷困潦倒的被视作受害者的罪犯,这让其读者产生尽管法律不会令人挨饿,但它经常把濒于饥饿的人逼向谋杀和自杀的绝境”[35]。 囿于社会改革的滞后性,以地方治安官为基本单位的刑事司法体系在日益严峻的犯罪问题面前捉襟见肘。尽管1829年罗伯特·皮尔起草《1829年大都市警察法》,但受制于传统地方与中央权力争端等因素,其实际执行阻力重重。现代警察被上层社会与统治阶级政治精英嘲讽为“一个在君主控制下的常备军”[36]被底层民众蔑视作中产阶级的“家仆”(Domestic Missionaries)。从犯罪问题的刑罚方式来看,以轻罪重罚为特征的“血腥法典”(Bloody Code)不再适用于新的犯罪现实,针对新的刑罚制度的定夺与死刑废止问题的争论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总之,对英国司法体系的改革贯穿于整个维多利亚时期,涉及法院组织及相关司法制度、诉讼程序等各层面。改革过程中,《泰晤士报》的谋杀案报道搭建起了一个对刑事司法体系呈现、探讨的平台,并有意识地制造、引导舆论讨论热点。
2. 提升公众法律素养的有力素材
《泰晤士报》谋杀案报道对提升公众法律素养、提供司法监督渠道具有重要意义。19世纪以来,随着选举权的扩大,“法律界人士均认识到将刑事司法体系及相关变革更为方便快捷地传递给政治上十分活跃的城市居民的重要性”[37],限于精英阶层的传统司法教育已无法满足公民权扩大的社会现实,司法教育被提上日程。从《泰晤士报》读者来信区域中对刑事案件及刑事司法改革的探讨来看,其提出的通过阅读使读者“领会司法过程的艰辛,评价司法程序”[38]的意图获得了极大成功。读者从证据有效性、程序争议性、判决有效性等多个层面发表意见,如“出于对公正与真理的追求,我冒昧地对此案的证据作出如下评判……”[39]。利物浦毒杀案判决后,海伦·丹斯莫尔(Helen Densmore)在1898年专门撰书回顾此案,正是在日常阅读报刊时瞥见该案的读者来信引起了他的兴趣,从此之后“每天阅读该案的法律细节,对庭审过程中记载的不公正十分在意”[40]。该案引起的公众舆论压力,使最初的绞刑判决更正为终身监禁。由此可见,谋杀案极大提升了读者参与刑事司法体系探讨的兴趣,《泰晤士报》借谋杀案建构了一个对司法体系展开广泛探讨的公共领域。通过《泰晤士报》的谋杀案报道,公众获得了司法监督的有效途径。在《泰晤士报》的引导下,公众与刑事司法体系进行理性沟通,感受到舆论对追求正义与真相的力量,这有效地疏导了公众对司法体系的不信任情绪,对于重建司法体系的权威性至关重要。
3. 延续英国法治精神的开拓性实践
《泰晤士报》还借由谋杀案报道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转型时期英国刑事司法体系的失序状态,加强了刑事司法体系对犯罪的有效控制力度,成为延续英国法治精神的开拓性实践。1842年《泰晤士报》对罗汉普顿谋杀案中警察办案不力加以批判,提出“公众有权要求看到一个更好的警察队伍——如今这支队伍数量庞大,且对国家大规模的人财物力仅是一种平白浪费”[41]。这一公开谴责激发了社会各界对警察制度侦查凶手能力的不满。迫于舆论压力,结案两月内,梅恩便向内务部要求在警察内部新设一个专门负责侦查工作的新部门。1842年,一个侦查分支建立了,这一警察队伍中的分支有八名长官。1868年增为十五名[42]。 1829年建立的现代警察制度采取分区监管制度,主要目的是维持公共秩序并对扰乱公共秩序的潜在罪犯加以控制。《泰晤士报》通过罗汉普顿谋杀案发觉到了警察制度的功能漏洞,影响了警察职能由巡逻向侦查的转变,警察制度的有效性显著提升。在刑罚制度层面,公开处刑制度与死刑制度的废止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主要问题。《泰晤士报》对行刑过程的细致描绘,以言语的形式延续了法律的威慑力,解决了提倡保留者的担忧。《泰晤士报》敏锐地捕捉现有刑事司法体系中的各项问题,有效引导改革舆论,刑事司法体系日趋完善。维多利亚末期,英国犯罪率得到显著控制,这是作为社会控制重要手段的法律体系有效性的最佳证明。
维多利亚末期,报刊迫于经济压力对轰动性案件的密集报道与细致关注,使相关案件的社会影响扩大,以轰动案件为原型的大众文化产品层出不穷。这难免催促了一种基于阶级、性别的刻板印象及针对特定“危险个人”群体恐慌在公众脑海中形成。家庭中的危险女性成为社会防范的对象。1851年《销售砷管制条例草案》在上院进行三读讨论。这一过程中,卡莱尔伯爵认为法案应该明确规定砷只能售卖给成年男性,因为多起凄惨的事故都是由被派去买砷的儿童、女性家仆所制造的。女性毒杀犯玛德莱娜·史密斯也被认为是乔治·艾略特《掀起的面纱》(the Lifted Veil)悬疑小说的灵感来源。这种对于罪犯标签化的方法,在遵从判例法的英国尤其危险。
德与法是社会调解体系中的两种重要调节杠杆。同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规训社会的方式相得益彰。维多利亚时期《泰晤士报》谋杀案报道是融合道德与法律治理作用的的开拓性实践,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工业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价值观念与刑事司法体系的整合。对推进中产阶级话语体系下的社会文明进程意义重大。
马特·库克(Matt Cook)曾指出,“刑事案件有利于树立社会规范,并重新定义性别、阶级、国家观念。”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走向工业化社会的重要时期,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以道德习俗、法律制度等为代表的社会上层建筑也正处于自我调适与重塑过程之中。在这一背景下,《泰晤士报》起到了一种灯塔的作用。《泰晤士报》在谋杀案报道过程中,通过切中时代痛点的案件选取标准、极具可读性与引导性的案件报道技巧、注重法律专业性的案件分析方式,发挥了谋杀案实现社会道德规训与法律控制的双重作用。由此,转型时期,传媒的社会控制作用得以发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媒体时代,各类媒体是激发刑事案件蕴含无限潜能的关键。公众对刑事案件有着普遍的好奇心,媒体对刑事案件的呈现方式,决定着谋杀案究竟仅是一种“娱乐至死”的感官刺激,还是发人深省,从而对社会控制具有潜移默化影响的有效素材。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可为公众提供有效的价值引导,从而加强法制建设。另一方面,提高公众法律素养也是深化依法治国的重要手段。从这一意义上看,刑事案件是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全盘颠覆,其刑事司法进程则是检验刑事司法体系合理性的照妖镜。利用好刑事案件报道,使其成为兼具道德法律双重意义的社会控制工具,对加速实现社会文明进步与依法治国进程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