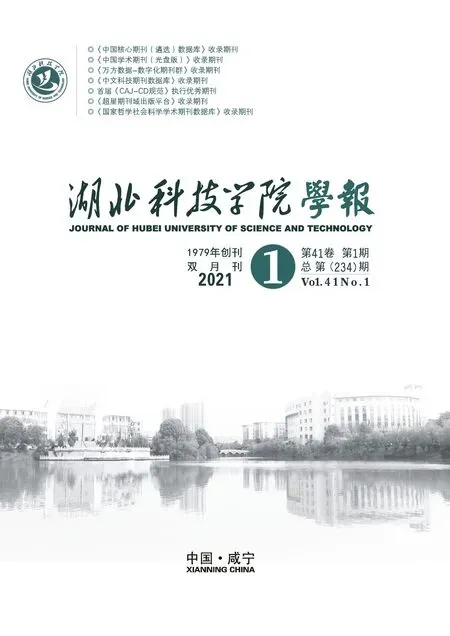论李叔同的爱国词
曾 玥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李叔同是晚清民国时期难得的全才,诗词歌赋、音乐声律、金石篆刻等靡不精工。文学方面,李叔同一生存诗九十七首,词十四阕,歌词四十首。其存词虽不多, 但“大都按谱倚声,恪守毋越”,竟“几于无字不叶,无音不谐矣”[1](P88),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其中最为感人的当属为数不多作于其青年时期的爱国词,高歌家国理想,展示李叔同的爱国主义精神。
结合薛祥生在《南宋词人的爱国悲歌》一文中对爱国词的界定,爱国词当“和时代风云密切相关,和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通,和民众疾苦血肉相连”[2](P5),是文本中含有家国、山河、故土等爱国意象,并且表达心系祖国、激励国民、勉励自我的家国之情的词作。本文所要重点论述的具备上述爱国词特点的李叔同词按作年先后排列如下:《金缕曲·将之日本,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1905年)、《喝火令·故国今谁主》(半阕)(1905年)、《喝火令·哀国民之心死》(1906年)、《满江红·民国肇造,填此志感》(1912年)。
已有学者就单篇李叔同爱国词文本进行细读,亦有学者从李叔同诗词作品中考察其家国情怀的文学书写。然对李叔同爱国题材词作的主要内涵、艺术特点和意义尚缺乏宏观把握。故本文拟就内涵、艺术、意义三个方面试论李叔同的爱国词。
一、李叔同爱国词的主要内涵
李叔同的爱国词主要作于其青年时期,尤其集中于其赴日深造前后。另有《满江红·民国肇造,填此志感》一阕,为1912年元旦再度南下上海,同许幻园、雪子、曾孝谷于寓所谈话,有感于上海的新气象和天津的旧风貌差距之大而作。李叔同爱国词带有鲜明的身世之感和时代风貌,总起来看,具有以下主要内涵。
(一)对祖国的深情
1905年,李叔同生母王氏盛年而逝。后事安排妥当后,李叔同深感国内动荡,难以重振,为寻救国路,远赴日本,希望找到振兴中华的途径。诣日本前,他作《金缕曲·将之日本,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以“留别祖国”,表达了誓报国恩的满腔豪情。录其全文如下: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 。愁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辜负
起句“披发佯狂走”,直欲让人联想到诗仙李白的“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在太白诗和《论语》中,都未对楚狂接舆作细致的外貌描绘,《金缕曲》中此句不仅得几分接舆、太白之狂,亦得几分李叔同之率性。辽阔无际的中原大地,只有日暮昏鸦啼叫不已,草木不生,唯有几株衰败的柳树,不复春日里青春烂漫的婀娜多姿。李叔同心里的祖国大地,生灵涂炭,举目凄凉。开篇即奠定了悲哀、茫然的底色。面对满目疮痍,词人发出悲愤的“破碎河山谁收拾”一问,无人回应,只有西风依旧,祖国的苦难和落后依旧,徒惹得将要赴日的词人比黄花更瘦。临行前的李叔同,带着报国之豪情,临流太息不已,仿佛千年之前的三闾大夫重又行吟泽畔,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主角,带给我们的是同样的沉重。过片笔锋一转,转入对过往的回忆。“漾情不断淞波溜”是词人在追忆沪上生活。彼时其“二十文章惊海内”,好不自豪,然此时却感到只是空谈罢了,并无实质意义,彻底地否定了自己数年前风流才子的惬意生活,是思想上的一次自我超越。将别生养自己的祖国,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心中不灭报国强国的热望。结句“是祖国,忍辜负”在回环不尽的悠悠别绪之中,喷薄而出,为了祖国,宁赴重洋,付出所有,无怨无悔,赤子之心可见一斑。
(二)对国民的感愤
李叔同青年时期,国家落后,数度见欺于外敌,乃于1905年赴日本深造图强。抵日之后,家国之思无日不萦绕心头。然1906年,当其患严重肺结核归国养病期间,国民的愚昧无知却比家国之辱更使他悲愤。他写下了“尤温婉有致”[1](P565)的《喝火令·哀国民之心死》:
故国鸣鷤鹆,垂杨有暮鸦。江山如画日西斜。新月撩人透入碧窗纱。 陌上青青草,楼头艳艳花。洛阳儿女学琵琶。不管冬青一树属谁家,不管冬青树底影事一些些。[3](P146)
起句化用 “终古垂杨有暮鸦”(李商隐《隋宫》),借隋炀帝典故,借古伤今,深寓荒淫亡国的历史教训。面对如此大好江山,陌上楼头却尽是醉生梦死,不问家国主权归属,只图享乐的国民。“洛阳女儿学琵琶”,学到的却是“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的况味,殊不知“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刘禹锡《台城》),李叔同从对祖国的深情转向了对国民麻木的反思和批判。即便李叔同诗词向来遵从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传统,文本当中也并无激烈的用词,我们仍然可以从词题“哀国民之心死”当中,读出李叔同对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愤。此前所作的《喝火令·故国今谁主》就没有此阕针对现实,反思深刻。可以看出:李叔同爱国词在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之下已注入了更为自觉的理性思考。
总之,从词作的作年背景和词作的文本内容考察,李叔同爱国词并非无病呻吟的游戏之作。它们紧密结合了词人的人生转折和特定历史时期,包涵了其对祖国的深情和对国民的感愤,在李叔同的词作当中尤为引人注目。
二、李叔同爱国词的艺术特色
1905年,二十六岁的李叔同携眷扶柩回津,处理完母亲的后事,于同年秋赴日本。在日本,迎来了他艺术上的全面进展和飞跃。他在东京以“息霜”之名包办了《音乐小杂志》的封面设计、美术绘画、社论、乐史、乐歌等栏目,并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创作,作品得到绘画界的高度认可。多艺术门类的基础和水准使李叔同拥有一般文学家所难以具备的艺术敏感性,尤其是其音乐才华,有助于其掌握词体的节奏和含蓄不尽的抒情方式。总起来看,其爱国词主要艺术特色有三。
(一)问句的大量使用
在李叔同为数不多的词作当中,带有反问语气的句子频繁出现,形成了李叔同爱国词的一大特色。在四阕爱国词中,问句共出现了五次,录之如下:
破碎河山谁收拾?(《金缕曲·将之日本,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3](P146)
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金缕曲·将之日本,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3](P146)
故国今谁主?(《喝火令·故国今谁主》)[3](P154)
记否天津桥上杜鹃啼?(《喝火令·故国今谁主》)[3](P154)
记否杜鹃声里几色顺民旗?(《喝火令·故国今谁主》)[3](P154)
在李叔同爱国词中,问句出现的位置有起句,如“故国今谁主”;有中间位置,如“破碎河山谁收拾?”“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有结句位置,如“记否杜鹃声里几色顺民旗?”。
问句的使用,打破了单纯使用平铺直叙的叙事语言和流畅跳跃的抒情语言的束缚,使得读者在吟咏时停下来,思考词人的发问,并复归文本,寻求答案。而李叔同所提出的问题往往带有警醒和追忆两种性质。警醒句如“破碎河山谁收拾?”“故国今谁主?”,从江山、国家的宏观层面上发问,警醒读者家国即将沦陷、主权即将丧失的现实,激励有志青年奋发图强,去收拾祖国破碎山河,去做国家的主人,把主权握在自己的手里。这种振聋发聩的提问,让读者在文本接受的过程中,完成了对李叔同爱国思想的深化体验,是文本在读者接受中的再一次完成。另一种发问句是追忆式的,如“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记否天津桥上杜鹃啼?记否杜鹃声里几色顺民旗?”这是针对个人微观层面的发问,有所不同的是,前者是词人自我的追忆,回忆沪上城南草堂的诗酒年华,此时回忆,非但没有了当年的书生意气,而且对其进行了否定,认为只有于振兴国家有用的言论方才不是空谈。后者是启示读者追忆,两个记否连问,却不像李清照的“知否,知否”给出“应是绿肥红瘦”的解答,没有下文,留下大片空白,让读者有创造性接受的空间。因之,问句在李叔同爱国词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深化爱国主题作用。
(二)巧用叠字
李叔同作词,喜以口语和散句入词,灵动跳跃,不拘一格。形成了清新活泼、风骨凛然的艺术风貌。这种风格形成的内在原因在于其充沛的爱国主义精神,外在原因在于文学语言的使用,叠字的巧用即是一例。在李叔同爱国词中,均用到了叠字,这在历代爱国词人的创作中是少见的。录之如下:
愁黯黯,浓于酒。(《金缕曲·将之日本,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3](P146)
朝朝暮暮笑迷迷。(《喝火令·故国今谁主》)[3](P154)
陌上青青草,楼头艳艳花。(《喝火令·哀国民之心死》)[3](P146)
不管冬青树底影事一些些。(《喝火令·哀国民之心死》)[3](P146)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满江红·民国肇造,填此志感》[3](P156)
叠字也即重言,将两个形、音、义完全相同的字连接在一起,用以摹写人或物的某种情态、形态、声音、颜色等。李叔同爱国词中叠字的类型丰富多样。表时的如“朝朝暮暮笑迷迷”,摹状的如“陌上青青草,楼头艳艳花”“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不管冬青树底影事一些些”“朝朝暮暮笑迷迷”,写情的如“愁黯黯,浓于酒”。
不同类型的叠字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首先是使描摹的物象更为生动。在《金缕曲·将之日本,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中,以“黯黯”形容愁,“黯,深黑也”。愁本是人的一种情绪,无可名状,此处以深黑色来喻愁,一面表明词人内心的灰暗色调,对前途的茫然无知,一面暗喻祖国前途的危机,一片黯淡。此后,又以“浓于酒”来形容愁,再添一份凝重,使得虚无缥缈的愁形象生动,意蕴丰富。其次,增加词的音乐美。闻一多先生曾提出诗歌有“三美”,其中一美便是音乐美,指的是诗歌在听觉上带来的美感。《喝火令·故国今谁主》中“朝朝暮暮笑迷迷”,一个七言的句子,六个叠字,两个叠字一个音步,极具跳跃性,在吟诵时带来一种音乐上的美感。再次,深化意境。如《喝火令·哀国民之心死》中的“陌上青青草,楼头艳艳花”,词旨本是要哀叹国民心死,本是低沉的情绪,昏暗的色彩,但是词人着力描写秦楼楚馆的浓艳色彩。“青,东方色也”[4](P101),“艳,《春秋传》曰:‘美而艳’”[4](P98)。“青”“艳”都是积极正面的形容词,与词旨情感色彩的背道而驰,从反面深化了意境,陌上楼头越是艳阳高照、争奇斗艳,国民之心越是无可救药。
叠字是汉语中独特的修辞传统,历代文学家有过许多成功的尝试:“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周南·桃夭》)、“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王维《积雨辋川庄作》)、“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白居易《琵琶行》),无不取得了极佳的表达效果。但在厚重的爱国题材中大胆使用如此密集的叠字,恐是李叔同的独特构造。
(三)以所要抒发的感情为依据,擅用中长调
词体形式多样:小令含蓄不尽,语短情长;中长调篇幅增大,铺叙自由。选择合适的形式和词调抒写特定的情感,是对词人创作功力的考较。本文以《草堂诗余》所主张的三分法为依据,以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对李叔同的十四阕词作分类统计,结果如下:

表1 李叔同词词调统计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四阕爱国词共使用了三个词调,《金缕曲》和《满江红》属长调,《喝火令》属中调。而李叔同用于酬赠友人、抒发儿女之情、感叹经历的词作则绝大部分采用了小令的形式。现以《清平乐·赠许幻园》和《满江红·民国肇造,填此志感》为例:
城南小住,情适闲居赋。文采风流合倾慕,闭户著书自足。 阳春常驻山家,金樽酒进胡麻,篱畔菊花未老,岭头又放梅花。(《清平乐·赠许幻园》)[3](P150)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满江红·民国肇造,填此志感》)[3](P156)
前者作于李叔同一家首次南迁,与许幻园夫妇同住在沪上城南草堂之时。词人自忆那是其一生中最为愉悦的时光,母慈妻贤,词人日日与知音好友赏玩文章佳什,内心无比满足自适。豪放词人辛弃疾也曾用此词调写下《清平乐·村居》,备述乡村生活的惬意。“清平乐”为双调,四十六字,篇幅短小,在视觉上给人轻巧精致的感受。上片四句,四仄韵,下片四句,三平韵,属平仄转换格。听觉上音调和婉,有不尽之余韵,适合抒发轻松闲适的情感。
后者为辛亥革命后,经历过沧桑变幻的词人,还是热切地相信并期待祖国的未来,身为男儿,愿为祖国奉献出自己的一切。这首词是四首爱国词中创作时间最晚的,经历过数年的奔波,李叔同更明白了祖国的未来在哪里,更明白了自己努力的方向,发出了“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的豪言壮语。在“满江红”的词史上,接受程度最高的莫过于岳飞的《满江红·写怀》,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词人的报国信心,是一首典型的爱国词。此词调为长调,在篇幅上既有小令不具备的容量,又有为《戚氏》等字数更多的词调所没有的精炼。除此之外,多短句的特点使得这一词调格外铿锵有力,如词作开篇即尽是短句:“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再如过片“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以短句的形式用典,最后发出“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的壮语。若以之吟诵,则句句如短剑,扎中听者的心。梁启超先生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小说对人产生四种作用,即“熏”“浸”“刺”“提”,诗词亦然。李叔同的《满江红·民国肇造,填此志感》吟诵起来对人产生“刺”的作用,这得益于其中短句的大量使用。
以中长调驾驭爱国题材,不仅需要有足够充沛的爱国主义情感,而且需要有把握宏观结构的能力,此外还须有用字用词的审慎。以中长调写大爱,以小令写小情,是李叔同以所要抒发的情感为依据所作出的选择,可见其选用词调的匠心。因之,中长调的选用是其爱国词中的一大特点。
三、李叔同爱国词的意义
家国情怀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穿中国诗词三千年的优秀传统。爱国诗在《诗经》、《楚辞》中已有表现,如“乐只君子,邦家之基”( 《诗经·小雅·南山有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然爱国题材在词体中的萌芽,却迟至李煜才出现,如其《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等。由于词体本身的进化、宋代内忧外患不断的社会历史条件、词人个性气质的蜕变以及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爱国词的产生当属必然。
词自隋唐肇端,直到李煜的出现才在“绮筵公子,绣幌佳人”的题材之外开辟了家国情怀的新内容。其《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等一批作品,饱含深沉的故国之思,尤为感人,可视为爱国词的萌芽。北宋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将守边将士爱国的情怀、思乡的苦闷、韶华的易逝等复杂的心态描写得雄浑壮阔,是爱国词在北宋的新发展。词至苏轼,题材近乎扩大到与诗同样的宽度,为后世爱国词奠定了基础。南渡以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催生了大量爱国词人和爱国词。后世爱国词人有文人志士,如朱敦儒;有闺阁女性,如李清照;有爱国将领,如辛弃疾。他们从各自的经历出发,丰富了爱国词的视角,为词史提供了《相见欢·金陵城上西楼》(朱敦儒)、《永遇乐·元宵》(李清照)、《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陆游)、《贺新郎·梦绕神州路》(张元幹)、《满江红·写怀》(岳飞)等一大批传唱不已的优秀爱国词。
晚近乱世,烽火不断,内忧外患,正是爱国词成长的好气候。晚近词史中的爱国词,是时代的歌哭,激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爱国词至近现代为一变,其爱国主义精神虽与此前无异,但其矛盾性质已发生了变化:由王朝皇权更替产生的民族内部矛盾转化成了外来侵略者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近现代爱国词人摈弃了前代爱国词人对一家一姓王朝的忠诚,转而忠于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国家。
在李叔同稍前,龚自珍以一卷“剑气箫心”的《定庵词》翻开了晚近乱世爱国词史的第一页。此后邓廷桢、林则徐以忧虑时局的大臣之心真切传神地展示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臣子心性,谢章铤评此二人“固不必以词见,而其词则与嘉、道间诸大老可以并驾齐驱。”[5](P282)此外还有周闲的《范湖草堂词》、孙超的《秋棠吟馆诗馀》、姚燮的《疏影楼词》等等,它们“无不足称词史,堪为长短句大增异彩。”[6](P380)
与李叔同近乎同时的爱国词人有秋瑾、高旭、庞树柏、檗子等,其中秋瑾以馀力填词,最为感人的同样是为数不多的忧国忧民、向往共和的爱国词。试看秋瑾的《鹧鸪天》: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7](P133)
全词大气磅礴,大处着眼,洋溢着敢于为国献身的大无畏革命爱国精神,叫人难以相信此为女子所作。而李叔同的爱国词则从其自身的经历出发,在其远渡日本前后和辛亥革命期间两个特定的时期集中问世,为我们提供了宏大历史背景之下,孤立无援又渴望以微薄之力救国于水火的知识分子的内心写照。我们可以从李叔同爱国词中看到风雨飘摇的国家,可以看到面对国家危难个体国民的悲慨。如果说秋瑾式爱国词是苍茫的山水画卷,那么李叔同爱国词恰似山水之中的点景人物,不失为大处落墨的爱国词的补充。
李叔同之后,仍有不少爱国之士绵延不绝地书写爱国词史的新篇章,如文廷式的《云起轩词》中就保留了他的爱国词作,它们负载着时代的凝重与苦难,向时人和后人展示着动荡年代的急促脉搏。如《广谪仙怨》:
玄菟千里烽烟,铁骑纵横柳边。玉帐牙旗逡遁,燕南赵北骚然。
相臣狡兔求窟,国论伤禽畏弦。早避渔阳鼙鼓,后人休笑开天。[8](P142)
可见,在爱国词史上,“屈原、杜甫、白居易、陆游、岳飞、辛弃疾、陈亮、文天祥、元好问、陈子龙、夏完淳、顾炎武、王夫之、屈大均乃至林则徐、龚自珍、黄遵宪、丘逢甲等一颗颗巨星辉耀青史,其精神代代承传,在沧桑易代之际、国难深重之时,爱国情怀与忧患意识表现得格外鲜明强烈。”[9](P17)李叔同的爱国词不仅延续了自先秦以来的优秀爱国主义传统,而且丰富了词体在爱国题材领域的个体表现,同时为爱国词史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是爱国词史当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李叔同的爱国词,有利于其时以及后世爱国精神的弘扬。
四、结语
李叔同为罕见的艺术全才,中年出家,人生经历富有传奇色彩。在文学方面,诗词歌曲数量可观,然地位却不甚平等。其歌词创作最为人所熟知,《梦》《忆儿时》等感人至深,广受肯定,一曲《送别》至今被交口传唱。李叔同诗作多为酬唱赠答、口占以及题画之作,难见其鲜明情感。其《护生画集》配诗以四五言诗居多,语言浅近,极少用典,喜引古文原文入诗,与丰子恺画作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亦得广泛流传。李叔同词因数量少,又不与其他艺术形式相配合,流传度显然不如诗和歌词。然其词清新自然,兼有风骨,尤其是爱国词中对祖国的深情,对国民的感愤,既警策,又感人。虽不如古代神品浑然天成,亦有擅用问句、叠字、中长调的艺术特色。李叔同的爱国词量少质高,上承辛弃疾、陆游、张元幹等古代爱国词人,下启高旭、檗子、文廷式等近现代爱国志士,在新时代有其文学史意义和社会意义。
——《李叔同—弘一大师年谱长编》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