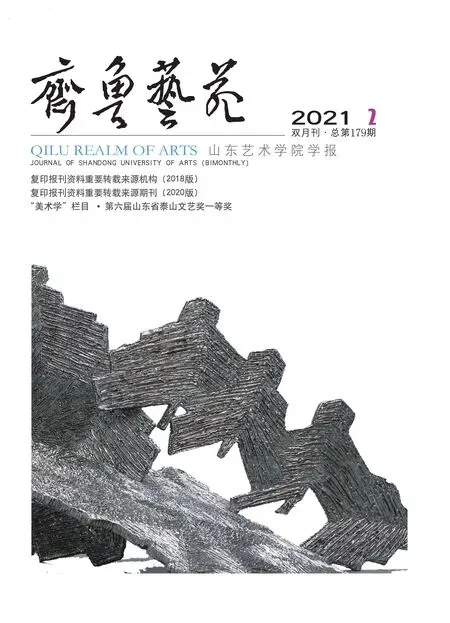明代《诗余画谱》中的“汪君”身份考辨
魏亮亮
(陇东学院美术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诗余画谱》是明代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年)刊刻的一部融词、书、画为一体的木刻词意版画集。该画谱的版本流传甚少,(1)郑振铎曾指出,《诗余画谱》的存世刻本至少有原刊本和翻刻本两种,见:郑振铎.西谛书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20;从相关研究看,至今可见的《诗余画谱》版本有上海图书馆藏万历四十壬子(1612年)刊残本、国家图书馆藏王立承鸣晦庐旧藏残本、郑振铎旧藏二残本、傅惜华旧藏残本,见:王晓骊.文学接受视角下的词意画研究——以《诗馀画谱》为例[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5);[明]汪氏.诗余画谱[M].孙雪霄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前言。今日所见均为残本,而且残本中画谱的创作者均未著录具体名氏。关于该画谱的创作者,残本提供的信息有:一是黄冕仲跋文(下文简称黄跋)中出现频次很高的“汪君”称呼;二是郑振铎藏本版画画页的“玉钅官”(王钅官或王、钅官)“佐山堂”(佐堂)印章。相关研究或认为,“宛陵汪君”为编者,“王钅官”(字佐堂)为画师[1](P139);或认为编者为新安汪某(未悉其名)[2](P121);或认为“汪琯画”[3](P266);或认为“宛陵汪君”也许就是新安汪氏一家,“王”“钅官”或“佐堂”想必便是绘画者之名号[4](P1050)。很明显,上述著述一致认为:“汪君”或“汪某”是《诗余画谱》的一位重要创作者,但对“汪君”身份的具体认识很模糊,表述存在分歧,均未作严密论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除《诗余画谱》外,其他关于“汪君”的文献资料和刻本尚未发现。
目前,学界对《诗余画谱》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2)《诗余画谱》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陈琳琳《论中国古代诗词的图像诠释——以明代<诗余画谱>为中心》(《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8年第4期);陈琳琳《诗词画谱与晚明徽州版刻——以<诗余画谱>为中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7年第3期);侯力《<诗余画谱>比较艺术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陈文分别从木刻词意版画对宋词的图像诠释及画谱的版式设计、刊刻工艺等方面论述了《诗余画谱》的艺术价值;侯文从词画对等视角,比较了《诗余画谱》所辑词与画的关系。但尚未对“汪君”身份有明确表述与论证。《诗余画谱》在版画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当前的研究成果,一方面要求我们深入探究该画谱的创作者,另一方面也使“汪君”的身份显得更加神秘。本文拟依据画谱的序题跋、文本与图像及隐现于画谱中的出版策略、受众等信息,结合晚明时期的社会文化,对“汪君”在《诗余画谱》创作中的作用和真实身份进行讨论。
一、《诗余画谱》序题跋中的“汪君”身份
对《诗余画谱》的研究,其最原始直接的资料是吴汝绾序(下文简称吴序)、汤宾尹题(汤题)、黄跋等。从画谱的接受角度论,为画谱书写序题跋者,应是除作者之外,最熟悉画谱内容和编者创作意图的人,是画谱最早的读者,并且与画谱的编者有一种直接的关系。故以画谱的序题跋作为研究的基本依据,有一定的可行性。需要说明的是:画谱的序题跋有可能存在过度褒美画谱艺术价值和编者出版意图的现象,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这是一种建立在对编者的出版意图和画谱核心价值的认识基础上的肯定,有一定的适度性。为防止认识的偏差,文本在选择画谱序题跋为资料时对有明显褒美倾向的语句给予特别说明。
《诗余画谱》黄跋中标有三处“汪君”称呼,先后顺序为:
余尝见吾松顾仲方所镌《咏物诗选》及虎林杨雉衡《海内奇观》,……不意宛陵汪君(第一处)复出《诗余画谱》见示……汪君(第二处)独抒己见,不惜厚赀,聘名公绘之而为谱……余是以之诗余之变,变自汪君(第三处)也……[5](P2-5)
第一处交代了“汪君”兼画谱编辑者与出版者的身份,由“宛陵”知“汪君”为徽州人。明代版画研究者董捷称:“兼画谱编辑者与出版者之任于一身者”为“刻书家”(publisher)[6](P17)。本文在行文中将沿用这一说法。第二处在第一处的基础上再次交代了“汪君”的刻书家身份。“汪君独抒己见”是强调“汪君”“诗余而为画谱”的创新性,“不惜厚赀,聘名公绘之而为谱”暗含“汪君”的商人刻书家身份之倾向,此句明显存在过度褒美画谱的意味,这是明代商业刻书一贯的手法。第三处在第二处“汪君独抒己见”的基础上,进一步交代了“以词入画”(诗余即词)的画谱创作是“汪君”的首创。由此可知:“汪君”是一位徽州商业刻书家,“以词入画”是《诗余画谱》的创新,也是“汪君”的首创。此外,吴序有一处“好事者”之称呼,当指“汪君”的刻书家身份。吴序曰:
《诗》非圣人不能删也……旧刻有《草堂》一集……好事者删其繁、摘其尤,绘之为图,且征名掾点画……[7](P1)
此处,吴序还交代了《诗余画谱》的部分创作过程。从删词、摘词、绘词的过程看,“汪君”有一定的诗词和绘画素养,是一位读书人,即有文人身份。毫无疑问,删词、摘词应是“汪君”完成的,关于删词、摘词的标准,吴序并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只是用孔子删诗作譬喻,对“汪君”删词持赞许态度。至于画稿是否由“汪君”图绘,此处没有明确的信息。结合黄跋“不惜厚赀,聘名公绘之而为谱”之语推测,“汪君”聘画师的可能性很大。需要说明的是:“汪君”即使不是《诗余画谱》的绘图者,没有专门的绘画技能,至少也是一位能够鉴赏绘画的人,因为他在选词时,势必要考虑词作转化为画稿这一创作环节。关于这一点,王晓骊认为:“汪氏所选词作,必然要受其‘画谱’功能的约束,其选词的标准也就必须是能够转化为画面的词作”[8](P49-53)。由此可知,“汪君”是一位有一定诗词和绘画理论素养的文人,可能没有专门的绘画技能,不是画谱的画师。
至于“好事者”,宋代米芾《画史》曾记载曰:“好事者与赏鉴之家为二等。……近世人或有资力,元非酷好,意作标韵,至假耳目于人,此谓之好事者。”[9](P115)此处“好事者”是指有一定经济实力却无鉴赏能力的人。此外,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三也有“好事者”之记载:“吾湖明中叶,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旧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于是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10](P39)此处可见,“旧家子弟好事者”所刻之书确实作为商品出售,即“好事者”是对商业刻书家之称呼。由此可推知,吴序中所谓“好事者”(汪君)与“旧家子弟好事者”应该有同类身份,当指“汪君”的商人刻书家身份。
对于“汪君”“以词入画”的画谱创新,汤题用“谓诗中画,即是无形之图绘;谓画中诗,即是无言之歌咏”之评语给予充分肯定。其实,结合汤题的评语看,“汪君”“以词入画”的画谱创作基础即是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郭熙“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11](P500)等艺术创作观念。由此可知,《诗余画谱》“以词入画”的立意暗含“汪君”对中国诗词与绘画互融性理论的深刻理解和实践运用,这也进一步显示了“汪君”的文人身份。
综上可知,“汪君”是一位兼有文人和商人身份的徽州刻书家。具体表现为:“汪君”有深厚的诗词与绘画理论素养,尤其对中国诗词与绘画的互融性理论有深刻理解,可能没有专门的绘画技能,不是画谱的画师。此外,《诗余画谱》“以词入画”的画谱创作是“汪君”的首创。当然,这一结论只是依据《诗余画谱》序题跋中的部分资料得出,与其说是一个结论,倒不如说是一个问题,因为此结论过于宽泛,一些具体问题需要结合画谱的文本与图像进一步明确。
二、《诗余画谱》文本与图像中的“汪君”身份
作为文本的词作与图像的木刻词意版画共同构成了《诗余画谱》的主体内容,对词作与木刻词意版画的考察,表面上是考察画师与刻工的绘图镌刻手艺,实际却是探究隐藏于画谱中的刻书家身份,因为在画谱创作过程中,画师与刻工都由刻书家雇佣,刻书家应是画谱创作的中坚力量。关于刻书家与画师、刻工之间的雇佣关系,黄跋“不惜厚赀,聘名公绘之而为谱”已有提示。另外,刻书家与画师、刻工之间的雇佣关系是晚明刻书业的一种普遍现象。故从画师与刻工及画谱的文本与图像视角探究刻书家(汪君)身份,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通过考察《诗余画谱》的词作文本,发现画谱所录之词基本上是词史上首屈一指的名家词作,且全部选自《草堂诗余》。当然,《诗余画谱》的选词也有一些“误署作者、误标词调”[12](P146-148)之类内容上的错漏。但整体而论,所选之词基本反映了南宋之前的宋词概貌,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宋词选本,这也进一步揭示了“汪君”深厚的诗词素养。
《诗余画谱》词文本书写的突出特点是:书写的书法家数量庞大,多达90余人,书体较为丰富,行草楷体居多,隶体偏少,单幅作品有较强的完整性,作者题款、木刻钤印应有尽有。从庞大的书法家数量推测,“汪君”应有广大的书画交际圈,有广泛的交游活动。书法家中,董其昌、陈继儒是生前身后皆享盛名的大家,许光祚、秦舜友、罗廪、自彦(释自彦)等少数几位生平可考知[13](P242-254),其余或许是万历时江浙一带稍具声名者,或为编者相熟之人等,其生平已不可知。不过一些作品真迹的可信度不高。如署名董其昌的两幅作品,第八幅《浣溪沙·春恨》(一曲新词酒一杯)(图1)、第七十幅《汉宫春》(云海沉沉)(图2),其中第八幅用行书体左右对称地把“浣溪沙调”四字书写在“董其昌印”右侧,更有意思的是,将晏殊“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么有名的一首词署为“李景”,传世词人中并无“李景”者,“景”或为“璟”之误,像董其昌那么学识渊博的一代尊师,不可能出现这种书写错误,也不可能用极不符合书法规范的行书体左右对称地书写“浣溪沙调”四字。第七十幅题款为“其昌”,从董其昌传世作品看,董氏的题款一般为“玄宰”“董其昌”等,若题款为“其昌”一般在“其昌”后会有“书”字,即“其昌书”。若将两作品放在一起比较,很明显两幅作品出自两人之手。由此可推断,此两幅作品不是董其昌的真迹。再如第七十七幅《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图3)书法作品,将“云亭李玥书”的题款书写在作品右侧下方,这种落款,很明显不可能出自书法家之手,而是工匠的托名伪造。若深入考证,《诗余画谱》的书法有好多是伪造作品,这其实正显示了《诗余画谱》的商业性刻书及“汪君”的商业刻书家身份。若将书法家的知名度与黄跋“笔笔俱名贤真迹”予以对照,便发现“笔笔俱名贤真迹”之说完全不符合实际,其意在于吹捧画谱,是典型的广告用语。

图1 《浣溪沙·春恨》 图2 《汉宫春》

图3 《念奴娇·赤壁怀古》
通过考察《诗余画谱》所辑木刻词意版画,发现木刻词意版画整体呈现风格多样的特点。其主要特点可概括为:其一,每幅画作基本呈现独立的面貌,画面的完整性较强,“画作大多都能很好的诠释词意”[14](P6-13);其二,《诗余画谱》临仿古代传统绘画和前人画谱的作品较多,据统计,画面标明“仿XX”的画作有29幅, 临仿《顾氏画谱》的画作有20余幅[15](P77),临仿《百咏图谱》的画作至少4幅[16](P135-136);其三,有40余幅作品钤有“玉钅官”联珠印章或“佐山堂”葫芦形印章,其余作品均无印章。从画作风格的多样性推测,《诗余画谱》应由数名画师和刻工创作完成;从画作的独立性和画面的完整性看,画师和刻工的绘图镌刻手艺整体较高;从对前人画谱的大量临仿看,画师中,不乏有一些投机取巧、手艺低下者。与同时代的《唐诗画谱》相比,《唐诗画谱》直接临仿其他画谱的作品数量明显较少[17](P139),从两画谱画作的构图特点看,《诗余画谱》一些画作的构图有明显的拼凑痕迹,如秦观的《桃源忆故人·冬景》(玉楼深锁薄情种)(图4)画面左下方的松树和右下方的房屋,左上方的山石和右上方的城阙,四部分明显出现视点不一、不协调的感觉。而《唐诗画谱》画作的构图基本没有明显的拼凑痕迹[18](P139)。因此,《诗余画谱》画师的绘图手艺当在《唐诗画谱》的绘图者唐世贞、蔡冲寰等之下。关于《诗余画谱》的刻工,郭味蕖曰:“一望而知为徽派名手。”[19](P139)此语尽管评价至高,但过于笼统。若将《诗余画谱》临仿《顾氏画谱》的20余幅作品与顾谱相比较,便发现《诗余画谱》的刀刻线条明显更胜一筹。如《诗余画谱》的第五十幅苏东坡《蝶念花·离别》(春事阑珊芳草歇)图(图5)以《顾氏画谱》的《米友仁图》为粉本(图6),两相对比,《诗余画谱》山体的轮廓线更有力度,米友仁所擅的“点子”皴法表达更为明确。故可推知,《诗馀画谱》刻工的镌刻技艺在《顾氏画谱》的刻工刘光信之上。

图4 秦观《桃源忆故人》

图5 苏东坡《蝶念花·离别》
从“临仿”看,《诗余画谱》对《顾氏画谱》的“临仿”,可以看作是《诗余画谱》的画师与刻工向中国古代绘画的间接学习,因为《顾氏画谱》本身就是古代传世名画的“缩小样”[20](P20),而以《诗余画谱》工匠的身份地位,他们很难亲眼目睹巨然、刘松年、夏珪等大家的真迹。分析《诗余画谱》“仿XX”的29幅画作与临仿《顾氏画谱》20余幅画作发现,《诗余画谱》仿《顾氏画谱》的画作,大多同时也是仿古代绘画之作。《诗余画谱》对《顾氏画谱》的临仿更多的是“变仿”[21](P65-70),而不是直接搬用。而更有意思的是,《诗余画谱》变仿《顾氏画谱》的作品,既能阐释词意,也能在这些作品上或多或少地找到被仿历代名画的风格特点。如第五十一幅词意画王安石《渔家傲·春景》(平岸小桥千嶂抱)(图7),画面的全景式构图,主体山脉的千岩万嶂、崇山峻岭及山石的刀刻点与范宽山水画“近取其质,远取其势”的全景构图,主山的峰峦浑厚、势状雄强及“雨点皴”等特点极为吻合。同时,画面下部的山间云雾、溪水、茅屋、小桥等点景与王安石《渔家傲》词“平岸小桥千嶂抱,揉蓝一水萦花草。茅屋数间窗窈窕”等写景相映。从《诗余画谱》对《顾氏画谱》与历代名画的临仿及对词意的诠释看,《诗余画谱》的画师、刻工应该是有一定文化素养,且善于学习古代绘画的工匠,有一定的文学及传统绘画基础,不是普通的民间工匠。

图6 《顾氏画谱·米友仁图》 图7 王安石《渔家傲·春景》
从40余幅词意画页面的“玉钅官”联珠印章或“佐山堂”葫芦形印章的钤用看,“玉钅官”和“佐山堂”应该不是“汪君”的印章和字号。《诗余画谱》的画师、刻工是一些善于向古代绘画学习,且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工匠,尤其是“汪君”,有深厚的诗词和绘画素养。中国古代绘画印章的钤用非常讲究,有严格的规范,而凭“汪君”、画师、刻工的文化素养,应该知晓传统绘画印章的钤用规范。就《诗余画谱》钤印的40余幅作品,印章的钤用无规律,在画面左下角、左上角、右上角、画面左右边空白处,“仿某某”之下等不同的位置都有出现(图8)。从印章的钤用位置看,“玉钅官”和“佐山堂”印章的钤用与《诗余画谱》“汪君”、画师、刻工的文化素养不符,更与画师画稿和刻工镌刻技艺不符。若与《唐诗五言画谱》相比较可发现,蔡冲寰的印章总是钤在“蔡汝佐写”之下或“仿XX笔意”处,非常规律,十分讲究。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诗余画谱》的出版说明指出:“郑氏所藏各画页钤有‘玉钅官’‘佐山堂’朱印,当有此为编者名号,然不见于原刊初印本,或为翻刻者别名。”[22]对此,王伯敏在《中国版画史》一书中提出了质疑:“宛陵汪君或许就是新安汪氏一家,可能不会作画”[23](P105),但并没有详加论证。由此可推知,“玉钅官”和“佐山堂”不是“汪君”和画师的印章与名号,有可能是翻刻者别名,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诗余画谱》的出版说明可信度较高。此外,与《顾氏画谱》相比,顾谱画作页面没有钤印,从《诗余画谱》对《顾氏画谱》的大量临仿及两画谱装帧形式的相似看,《顾氏画谱》应该对《诗余画谱》的创作有很大影响,这也为“玉钅官”和“佐山堂”不是“汪君”、画师的字号提供了一条证据。结合王伯敏的质疑:“宛陵汪君……可能不会作画”,黄跋“汪君……聘名公绘之而为谱”及“玉钅官”和“佐山堂”不是“汪君”的印章与名号综合推测,“汪君”很可能没有专门的绘画技能。

图8 从左到右依次是苏东坡《蝶恋花·离别》、李清照《如梦令·春景》、黄庭坚《西江月·劝酒》、苏东坡《满庭芳·吉席》、苏东坡《卜算子·孤鸿》、张耒《风流子·秋思》、秦观《菩萨蛮·秋闺》、苏东坡《八声甘州·送参廖子》、秦观《分流子·初春》等词意图。
综上可知,“汪君”是一位有深厚诗词素养和经济实力的刻书家。具体言之,画谱中词作选择的质量表明“汪君”有深厚诗词素养;从聘请画师、刻工的数量、绘图镌刻手艺及文化素养可知,“汪君”应是一位很有经济实力的刻书家;词意版画页面的“玉钅官”和“佐山堂”印章应不是“汪君”和画师的印章与名号,“汪君”很可能没有专门的绘画技能,不是《诗余画谱》的画师。整合《诗余画谱》序题跋及文本与图像两方面的论述,并结合晚明社会文人的“弃儒就贾”与徽商“贾而好儒”等特点,可以认为,“汪君”乃是一位“亦儒亦商”的徽州刻书家。
三、《诗余画谱》隐现因素中的“汪君”身份
基于对画谱认识的需要,可以引进“显—隐”这对对偶范畴解读《诗余画谱》,由此能够发现,前文论述的序题跋,词作与木刻词意版画是画谱构成的显现因素,隐藏于画谱的出版策略、受众等信息是画谱包含的隐现因素。挖掘画谱的隐现因素能为探究“汪君”身份提供更多信息。因隐现因素涉及画谱的创作性质,因此,有必要先对《诗余画谱》的创作性质作一探索。
按传统的官刻、家刻、坊刻分类,《诗余画谱》应属于坊刻刻本,有商业刻书的特点。这从选词内容的讹误、书法作品的伪造及一些词意画对其他画谱的临仿都能看出。“按刻书内容和书商身份分类,徽州存在着‘刻工书坊’与‘文人化书坊’两种不同类型的书坊。”[24](P99)《诗余画谱》应属于“文人化书坊”的刻本,“汪君”的资金实力,画谱“以词入画”的内容创新,“徽派名手”的精刻,“案头展玩”的功能等与明代徽州“文人化书坊”的一些特点极为吻合。如:“书坊的经营者大多资本雄厚;内容求新,注重学术价值;文人读物较多;刊刻技术求精”[25](P99)等。细审“文人化书坊”不难发现,其自身包含一些矛盾与复杂性,如所刻作品的文人化与商业化,雅化与俗化;刻书行为的射利与射名,自娱与销售;刻书家的文人与商人身份等。其实,晚明时期,一些比较有名气的书坊和刻书家几乎都属于“文人化书坊”和“文人化书坊主”,如玩虎轩、环翠堂、美萌堂等书坊,汪道昆、汪廷讷、程君房等刻书家。从“书坊”属性视角观照《诗余画谱》的刻书性质,《诗余画谱》应兼具商业性与文人化属性,是典型的文化消费性书籍。《诗余画谱》的这一刻书性质,不但是我们探究画谱的出版策略、受众等隐现因素的基础,还是证实“汪君”亦儒亦商身份的依据,因为刻书家的身份与所刻作品的性质有密切关系。
面对市场与受众,《诗余画谱》隐含了一些吸引读者的出版策略。首先是以热点题材吸引读者。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诗余画谱》的出版说明“郑氏藏本中书口有《草堂诗画意》字样”,及吴序“旧刻有《草堂》一集……好事者删其繁、摘其尤,绘之为图”可知:《诗余画谱》,初名《草堂诗画意》,所录词作选自《草堂诗余》。有研究表明:“今存的明代《草堂诗余》版本就有35种之多,另外见于著录的还有4种。”[26](P91-93)可见《草堂诗余》在明代传播极盛,有广泛的读者群体,是明代文人圈的热点读物。从《诗余画谱》与《草堂诗余》的这一关系看,《诗余画谱》有依托《草堂诗余》读者群体的刊刻出版之意,其目的是吸引更多读者,提高书籍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诗余画谱》的另一出版策略是,以图吸引读者。晚明是中国版画发展的“光芒万丈”[27](P51)时期,也是书籍插图发展的“鼎盛时期”[28](P100-101)。有学者指出:“晚明书坊的商业竞争手段,一定程度上是以插图的描绘吸引读者”[29](P100-101),《诗余画谱》也不例外。《诗余画谱》虽名为“画谱”,但实际是以插图来配词作的宋词与插图合集。《诗余画谱》通过“仿XX”的方式强调“图”的艺术性与风格来源,使“图”有了绘画史依据;同时,通过“以词入图”“以图释词”的方式,使“图”有了诗意与文学内涵。这种做法,一方面强调“图”的审美属性与诗意内涵,另一方面,也是以高质量的“图”吸引读者的出版策略。此外,《诗余画谱》以暗含大量广告之语的序题跋过度褒美画谱,以吸引更多读者。如黄跋曰:“此谱之刻,姑无论洛阳纸价,可卜千秋而下,邺侯当珍藏矣。”此语用“洛阳纸价”“邺侯”(3)邺侯:唐李泌父承休,聚书二万余卷,戒子孙不许出门,有来求读者,别院供馔。事见泌子李繁所撰《邺侯家传》。后来以邺侯代人身份,而“汪君”能够抓住社会的一些热点题材及吸引读者与宣传画谱的方法刻书,可见指藏书家。等典故,鼓吹《诗余画谱》应该受到读者的欢迎和收藏家的珍藏。复如:黄跋的“篇篇皆古人笔意,字字俱名贤真迹”“不惜厚赀,聘名公绘之”;汤题的“从径山披此图,了然解情景者,遂书此以往”;吴序的“且征名掾点画”等语都或多或少的有过度褒美画谱之意。通过对《诗余画谱》隐藏的出版策略探析,可知“汪君”应是《草堂诗余》的热心读者,这也进一步证明“汪君”具有徽州“文人化书坊主”的特点,当是一位典型的徽州“文人化书坊主”。
《诗余画谱》的受众,吴序“案头展玩”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结合画谱的文本与图像分析,《诗余画谱》之词、画、书法融为一体的装帧设计及富有诗意的木刻词意版画创作,强调画谱的观赏与审美功能,指向的受众群体应是“展玩”与“清玩”者,尤其是词作的书法书写设计带给受众的是对词作的“观赏”接受。结合晚明社会的实际看,“案头展玩者”主要指“弃儒就贾”的文人和“贾而好儒”的商人等群体,这两类人群构成《诗余画谱》的主要受众。将这两类人群与“汪君”亦儒亦商的刻书家身份联系在一起看,“汪君”应有这两类人群的特点,“汪君”应是晚明“弃儒就贾”的文人刻书家,或“贾而好儒”徽商刻书家。董捷的博士学位论文《明末湖州版画创作考》,通过对湖州闵、茅、凌三氏刻书家的研究指出:“湖州刻书家心目中的读者,正是与他们自己相仿佛的阶层。”[30](P113)“明末湖州的刻书家具有‘半儒半商’的身份。”[31](P11)这说明,“汪君”亦儒亦商的刻书家身份在晚明时期并非孤例,是晚明刻书业群体的一个普遍现象。
明代文人的“弃儒就贾”已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与明代人口的剧增和科举录取率的低下有直接关系。文徵明《三学上陆冢宰书》云:“略以吾苏一郡八州县言之,大约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贡不及二十,乡试所举不及三十。以千五百人之众,历三年之久,合科贡两途,而所拔才五十人。”[32](P338-341)此外,有学者统计,“成化至嘉靖年间,乡试录取率平均在3.95% 以下,隆庆以后更降至3.1% 以下”[33](P77-84)。这些数据表明,明代社会有一庞大的未能进入官僚阶层的基层文人群体。对于这些基层文人而言,著书、刻书等应是他们较为理想的工作。如汲古阁主人毛晋“早岁为诸生,有声邑庠,已而入太学,屡试南闱,不得志,乃弃其进士业”,“刻汲古阁书,风行海内”[34](P65-67)。而杨尓曾走上商业刻书之路的原因也是“科举仕途的蹭蹬不前”[35](P27)。
“贾而好儒”既是徽商的一种文化品位,又是一种社会行为。内涵丰富、包罗万象的徽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崇儒尊儒为主的思想观念,这一思想观念赋予了徽商“贾而好儒”的文化品格,这一文化品格使徽商有了投资和参与刻书业的文化自信,同时,也赋予了徽商在刻书业行为中的射利与射名并重的行为。“明中叶后,商品市场拓宽,‘贾而好儒’的徽商乘时射利射名,群起藏书刻书……涌现出一支成分多样的巨大藏刻并举队伍……而书商汪济川、吴勉学、程仁荣(均歙人)、汪世贤、吴馆(均婺源人)等,更以藏刻著称。”[36](P11-17)这表明,在晚明时期,“贾而好儒”的徽商从事刻书业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
然而,“汪君”到底是“弃儒就贾”的文人刻书家,还是“贾而好儒”的商人刻书家,因资料缺失,在此很难明确断言。实际上,也没有必要过多的追究,因为在晚明这个特殊的时代,“士商之间在日常人生的世界中已融成一片”[37](P532),“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38](P687-688),“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39](P419-420)。更进一步讲,对于晚明,我们很难判断有盐商、书贾、学者等称呼的汪廷讷及出生于业医世家,且博学多文的胡正言是“弃儒就贾”的文人刻书家,还是“贾而好儒”的商人刻书家,只能笼统地称他们为“亦儒亦商”的刻书家。
结语
对艺术创作者身份的探究是典型的艺术史研究课题,据艺术史研究的传统,应运用文献学的方法对创作者的家世、生平、官职等资料进行考证。然而,这类研究中往往有像本文所论之《诗余画谱》一类的难题:其一,画谱未著录创作者的具体姓名,且版本为残本;其二,除该画谱外,少有画谱及创作者的其他文献资料;其三,创作者成份比较复杂,有刻书家、画师、刻工等;其四,画谱的创作性质模糊。而该画谱在版画史上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尤其是“以词入画”的内容创新在画谱及词意画史上有开创之功,对其创作者身份的讨论又很有必要。
如此以来,本文无法运用传统的文献学研究法考证《诗余画谱》的创作者,而只能运用文本分析及其他方法,从相关文字与文本中查找画谱创作者的信息。因画谱创作者成员组成复杂等原因,本文将目光聚焦于画谱创作的主要参与人——刻书家,认为:黄冕仲跋文中的“汪君”正是《诗余画谱》的刻书家。通过对画谱序题跋、词文本与木刻词意版画图像的分析认为,“汪君”是一位亦儒亦商的徽州刻书家,有深厚的诗词及绘画理论素养,很可能没有专门的绘画技能,不是《诗余画谱》的画师,木刻词意版画页面的“玉钅官”和“佐山堂”印章应不是“汪君”的印章与名号。在此基础上,结合晚明士商合流的社会特点,通过对《诗余画谱》隐现的出版策略及受众的分析认为,“汪君”是一位“弃儒就贾”的文人刻书家,或“贾而好儒”的商人刻书家,即一位“亦儒亦商”的徽州刻书家。通过对晚明刻书家群体的整体观看,认为“汪君”“亦儒亦商”的刻书家身份并非孤例,“亦儒亦商”是晚明刻书家群体的普遍身份,“弃儒就贾”“贾而好儒”是晚明刻书家群体的普遍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