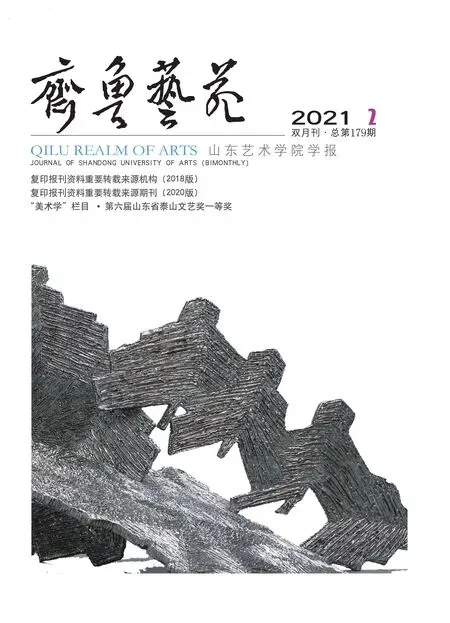从厚涂表现的形成看日本画的战后转型
陆 乐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上海 200000)
日本文化受到中国的深远影响,人们总爱将两国的艺术相比较,而中国画与日本画是其中非常鲜明的一对坐标。但如今提及日本画,人们便会联想到其厚重的颜料层与丰富的色彩,却很难从中看到传统绘画的影子。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日本画基本保持着与中国画相似的以线造型、薄涂淡染的绘画手法,虽也有少数画家用如油画般厚涂颜料作画,但并非主流。二战后,厚涂表现的形成致使日本画与中国画在观感上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样貌。那么,为何战前一直保持传统画法的日本画在战后突然改走厚涂之风?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与绘画观念乃至社会的变迁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厚涂表现的形成
如果像社会学所说,艺术是社会的一面镜子,[1](P25)那么日本画一定是其中最明亮的一面。纵观日本画史,可以说每一次社会的变革日本画都从未缺席。不论国粹主义引发的新日本画运动,还是大正民主带来的表现主义热潮,亦或是军国主义掀起的新古典主义。毋宁说,日本画的整个发展史都可看作是日本社会跌宕的回响。而伴随着二战的失败,社会再次迎来巨变,日本画亦随之翻开新的篇章。
战后,由于战时以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思想向美式民主的转变,推崇欧美、贬低传统的风气再次弥漫,如同明治的“全面欧化”时期一样,带有明显矫枉过正的倾向。当时,被认为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传统文化形式一一遭受审查,甚至歌舞伎表演也大都不被允许。[2](P310)紧张而又对立的气氛中,饱受“国粹主义”(1)国粹主义:明治20年代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之一,在日本近代发展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国粹主义是日本近代由全盘西化走向民族化、本土化的一个历史拐点,同时它也是日本由谋求民族独立转而走向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这一过渡性阶段中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日本画,自然也无法逃脱严厉的打压与批判。此时,以往美术学校中看似理所当然的日本画科,亦面临着被取消的危险。(2)1948年武藏野美术学校(现武藏野美术大学)重开时,就有部分教员不赞成设立日本画科。其中,儿岛善三郎最为激进,认为日本画实在过于简单,但如果非要教授,一两个礼拜也足够了。参见:[日]日本美术院.日本美术院百年史(第八卷)[M].东京:日本美术院,2004.与日益蓬勃的西洋画相比,日本画逐渐被贴上“弱势”“过时”“缺乏现实感”的标签,将其归为二流、三流艺术的声音也日渐高涨。[3]
来自外部的压力,在日本画内部以世代交替的方式所演绎。从1890年代开始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支撑、奠基、自我变革、推动发展的画家们大约跨越了四个世代。[4]至战后,第一代画家早已陨殁。幕末到明治出生的第二代日本画家如横山大观、川合玉堂都已相继去世或至暮年。而以小林古径、铃木清方为代表,明治中期出生的第三代画家也并没有在战后改变固有的画风。此时,日本画的战后变革便落在了正值盛年的第四代画家手中。1947年43岁的福田丰四郎于《读卖新闻》发表了《日本画的危机》一文,直击痛点,指出日本画因循守旧的弊端,并决心打开视野走向国际。[5]以此为开端,画坛逐渐涌现出一些具有开拓精神的美术团体,求新求变,力图通过学习西方现代绘画,以帮助自身摆脱困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属“创造美术”和“泛真实美术协会”(パンリアル美術協会)。
于1948年成立的“创造美术”,由东京、京都的13名画家组成。其宗旨在于抵制日本画坛的封建因袭势力,追求立足于东方美基础上的新美,以创造出具有世界性的日本绘画。[6](P15)而以三上诚、下村良之介、大野崇为首的“泛真实美术协会”也于同年成立,并在次年发表的宣言中写道:“打破因袭的殿堂,从广阔的、科学文化的视野中发掘传统的生命力,以世界为基础对传统进行再审视……不论是主题还是肌理都应冲破传统的局限性,为开拓胶彩(3)胶彩:1930年玉村方久斗结成的方久斗社,就将日本画按照材料与画法称为胶彩画,意在使脱离一些既成的概念,特别是作为日本画概念的束缚。将日本画称为胶彩画的观点,在如今的日本画坛其仍占有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做出更多的努力。”从二者的宣言与纲领中不难看出,打破因循守旧的牢笼,而将本民族的艺术推向世界是二者共同的夙愿,亦或是当时日本画坛的共同夙愿。在创造美术与泛真实美术协会的引领下,西方现代油画中的色彩、肌理与造型语言被引入到日本画中,尽管这种偏向于西方绘画的倾向受到了种种批判,却也给予“日展”“院展”的画家以刺激,致使一种类似于油画厚涂的表现开始流行起来。
但艺术是一个集体的行为,[7](P1)一个新表现的确立仅仅依靠画家的意愿是难以支撑的,绘画材料上的支持也同等重要。然而战后初期的颜料开发相对于绘画的发展是滞后的。战前作为主要颜料的天然矿物颜料,不仅价格高昂、色相单一,而且限于自身属性也无法进行油画般的混色与调和。(4)天然的矿物颜料由于每种颜色都出于不同的材料,同等颗粒大小的颜料同时融于胶液中,会出现明显的分层。质量重的向下沉,质量轻的向上浮,从而影响发色效果。对于颜料所带来的掣肘,当时的画家川端龙子就曾抱怨:“提及颜料的不自由,我亦深有同感。如果如绿松石一样的宝石也能被制成颜料,那该多好!”[8]实际上,川端的话反映了当时画家创作时一种普遍的矛盾心理。既渴望如同油画颜料般的自由表达,但又难以避免矿物颜料所带来的局限,而要消除这一矛盾,若只是通过开发更多的矿物颜料亦是很难解决的。
需求带动生产。依托于本国良好的化工基础,日本画颜料迎来了空前的发展。随后,1952年中川惠次以胡粉着色制出的水干绘具(日语名词,指绘画颜料)开始投放市场,1955年后以人造原石粉碎制得的新矿物颜料亦得到蓬勃发展,1968年上尾绘具工房也开始了以方解末着色为基础的合成矿物颜料的开发,加之后续树脂颜料的相继问世,战后的日本画颜料体系逐渐成形。[9](P153-154)(图1)而其中的新矿物颜料不仅通过高温技术具备了如天然矿物颜料般的稳定性,还通过粉碎釉料的手段获得了与之相似的折光性及砂状的显性特征。(图2)不仅较大程度上还原了天然矿物颜料的显性特征,还实现了与油画颜料相同的色域及可调和的物质属性,为日本画厚涂表现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图1 战后日本画的主要绘制材料图像来源:《日本画入门》
不可否认,一个表现形式的产生绝不是由某个天才或组织凑巧创造出来的神秘事物,而是与生产它、消费它的社会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样的论调中虽然充斥着极端解构主义的色彩,但日本画的厚涂表现就是在这样的不断磨合中形成与发展的。借用美术评论家弦田平八郎的话来说:“战后的日本画,提高了西欧近代的造型意识,更加趋近于西洋,同时伴随着战后新颜料体系的形成,更使得可以与油画相媲美的厚涂表现成为可能。”[10]

图2 显微镜下的岩绘具(左侧为天然岩绘具, 右侧为新岩绘具)图像来源:《日本画的传统与继承》
二、与“传统”的疏离
社会巨变下孕育出的表现方式,也同样反映出极具革新性的色彩。与中国的水墨相似,厚涂表现并非特指某种专门的技法,而是战后日本画在表现上的一种共同倾向。事实上,在江户时期尾形光琳等画家的屏风画或是贴了金箔的隔扇画中也多见厚涂颜料的手法。[11]但与之不同的是,光琳的厚涂主要是平涂色块,意在配合画面中的平面装饰效果,而战后日本画的厚涂则是通过反复堆叠颜料来塑造对象,并追求丰富的色彩与肌理效果。(图3)而这种表现方法,亦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主要影响分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传统线条的消失。实际上,日本画的发展便是不断提倡色彩、弱化线条的过程。自明治初期,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5)费诺罗萨(Ea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西班牙裔美国人,1882年在龙池会名为《美术真说》的演讲中首次提出“日本画”概念,之后与冈仓天心等人领导了新日本画运动,被称为“日本美术的恩人”。就提出日本画改良的主旨是模仿西洋绘画“Painting”,贬低以水墨为主的“Drawing”,致力于推广日本画的“色彩化”。[12](P486)而明治中期“朦胧体”(6)朦胧体:一种绘画表现形式,从明治时代的横山大观、菱田春草等人的某些试验性绘画演变而来。“朦胧体”受到西方绘画的刺激,直接表现自然空气和光线,并进而把技法的重点从线条转移到色彩。的出现也更加深刻地履行了这一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战前的“色彩化”浪潮虽风生水起,却未动及线条根本,甚至到了大正、昭和时期,由于小林古径的推崇,曾一度有复兴的趋势。[13](P18)

图3 日本画厚涂表现横截面示意图图像来源:作者绘制
直至战后,厚涂表现的流行,才使得线条彻底失去了在日本画中的主导地位。而这一点,通过东山魁夷的作品《残照》便可窥见一斑。(图4)画面中,画家以重叠群山为对象,不拘泥于细节,更专注于整体氛围的把握,运用色面替代了线条,传统的留白亦不见踪影。而不断叠加斜接的色层,更是形成了丰富而又微妙的色阶,由近及远,营造出氤氲的暮丘之气,无疑是日本画“色彩化”的完美呈现。亦如日本学者河北伦明所言:“如果说战前的日本画还多少残存着东方传统线描之余晖的话,到了今天线描的影子则日趋淡薄,无疑与中国国画的差别比过去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明显了。”[14](P4)

图4 东山魁夷 《残照》 1947年图像来源: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
其次,是绘绢的边缘化。在绘画中,艺术技巧的嬗变也会使得某种材料获得或失去艺术资质。[15]战后的日本画家们为了承载较厚的颜料层并防止绘画过程中支持体潮湿所引起的褶皱,通常会选择在较为厚实且富有韧性的云肌麻纸、麻布甚至是木板上进行绘制。而作为传统日本绘画中重要支持体的绘绢,因其遇水变软易皱、轻薄易破,难以承载厚重的颜料层,在战后不再是日本画绘制的首选。
但绘绢的边缘化不仅仅是一种绘画材料的衰落,更是一类绘画的失语。刊登在1991年《艺术新潮》中的一篇文章就写道:“现代日本画中几乎遗忘了绢本技法。虽然如今的日本画几乎都画在纸上,但据自平安时代的大和绘以来,绢上作画都一直被作为日本画独特的表现手法,灵活的晕染技艺和由自然而生的空间表现都是其画面的特点。到了大正时期,欧洲学画归来的年轻画家们,在摸索如何使日本画活用西洋式的远近感与空间表现的同时,习惯性地选用古老的绘绢作为载体。在他们的画面中通透的空气感,以及风景、人物,甚至于整个空间的氛围都在绢布上得以完美呈现,展现出独特的魅力。而这是现代日本画中麻纸上厚涂的方法绝对无法表现的。”[16]而今虽在日本画展览中依旧可见绢本绘画的身影,但也多是作为画家的个性之选。
再次,是卷轴装裱的隐退。装裱方式的改变,一直以来也是日本画变革的重要标志。明治初期,在“文明开化”风气的推动下,绘画由壁龛艺术向展厅艺术转变,致使传统的卷轴装裱(轴装)也开始被西方的额框装裱(额装)所取代。(7)1882年和1884年先后两次举行的内国绘画共进会,都明确要求画面需要进行额装,禁止使用轴装绘画参加展览。参见:[日]古田亮.日本画とは何だったのか——近代日本画史论[M].东京:株式会社KADOKAWA,2018.但至昭和,由于军事与政治上的成功,民族自信高涨,卷轴又被作为传统文化重新纳入绘画展览的范式中(8)1907年开办的文省部展览,又重新将屏风、卷轴画纳入展览会的艺术形式之中。参见:[日]古田亮.日本画とは何だったのか——近代日本画史论[M].东京:株式会社KADOKAWA,2018.(图5)。而战后,厚涂表现在物理上因绘制的颜料层较厚,又多用动物或植物胶进行粘合,故而彻底风干后质地坚硬且脆,一旦成画便决定了其不能卷折的特性,使得轴装彻底隐退,额装终成为主流。(图6)
由此,从画面到选材再到装裱,日本画实现了战后初期对于固有“传统”的打破,并通过吸收西方现代绘画完成了战后的转型。但此时的日本画也无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趋近于西方,日本美术评论家桑原住雄生动地将其比作由“日式点心”向“西式点心”的转变,意指战后日本画虽内在仍富有日本精神,但在各个方面已与油画非常趋同。[17](P175)

图5 1909年第三回文展展览现场,可见当时还有轴装 展示的作品图像来源:日展公益社团法人

图6 1958年第八回日展展览现场日本画展厅 全部都是额装作品图像来源:日展公益社团法人
三、厚涂表现的反思
实际上,日本对于西方的移植本就是功利的与实用的。不论是从明治初期的欧化主义风潮之后出现的传统与国粹主义,还是从大正民主主义之后兴起的法西斯主义,抑或是从战后欧美化风潮之后引发的回归传统的倾向都可以看出,当日本为了摆脱民族危机与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时,他们迅速吸收外来文化以壮大,但一旦目的达到,或当西方的文化移植危及日本的根本利益时,他们又会进行反击与批判。[18](P7)而进入20世纪50年代,日本社会和生产秩序初步恢复,工农业生产增长很快,情况就如1955年《经济白皮书》所宣布的那样,日本已经度过了战后的艰难时期。[19](P110)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人的自信也有所恢复,社会中再次出现了“回归日本”的现象。
这种“回归日本”的风潮映射在日本画上便是对于“传统”的再重视。事实上,经历过战后初期的洗礼,日本画不论在画面、选材还是装裱上都已更加趋近于西画。评论家水尾比吕志更是在看完第八回日展后直言不讳地说日本画与西洋画的展览分类都是多余。[20]这种对于日本画西化倾向的质疑不断发酵,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潮。此时的日本画家受到西方现代绘画的影响,在厚涂表现的基础上,大胆地将油画、坦培拉、水彩等应用到创作中,打破了日本画与洋画之间材料的界限。如阿多诺所言:“艺术材料缺失或更新也将带来艺术技巧及其构造形式的更迁。”[21]伴随着厚涂的“失控”与材料的多样化,关于“什么是日本画”的诘问亦引发了画坛的广泛讨论。
1984年5月印发的《美术手贴》杂志,便刊载了以《作为二十一世纪美术的日本画》为主题的座谈会纪实,邀请了著名画家加山又造、川崎春彦与平山郁夫进行讨论。会中三人就战后日本画的厚涂表现进行了反思性的探讨:
川崎春彦:(现在的日本画)颜料依旧涂得很厚,画面也显得很脏。
加山又造:那应该叫做肌理,主要受到了美国材料观念的影响,追求画面的触感。肌理、材料、色阶都进入了日本画。(后略)
平山郁夫:相较于油画强烈的肌理效果,线条的表现力确实明显处于弱势。如今的日本画中充斥着各种各样折衷的表现。为了适应这些,厚涂似乎也会必然出现。
加山又造:对此有许多争议,他们并非非要厚涂颜色,而是出于与洋画画面效果的对抗。但即使像委拉斯贵支画中那种类似于晕染的手法,最厚处也不过就是一厘米左右。这样说来,我们到底该如何定义日本画呢?似乎又很不甘心。(节选)[22]
就像对话中所指出的,画家们对日益“失控”的厚涂表现不仅表达了担忧与质疑,甚至面对着日趋西化的日本画,连其概念似乎都变得难以定义。80年代的一则展评更是批评道:“如今的日本画,失去了具象的目标,为了变形而变形,为了抽象而抽象,而厚涂也仅仅是为了获得与油画一般的肌理而已。”[23]至此,这是否就意味着战后日本画向厚涂表现的转型是失败的呢?
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日本画作为一种文化称谓其本身就缺乏明确的界定标准。在区分油画与胶彩画时,由于材料与表现间的辩证关系,答案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如果区分西洋画或是日本画则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人们通常要使用形式、构图、色彩等更专业的词汇,对画面中代表“传统”的符号进行甄别,借以界定二者相异的文化内涵。但日本所定义的“传统”又是极为暧昧的。就像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所言:“人们开始讨论所谓的‘国粹’——尽管对于该如何定义国粹,人们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共识。”[24](P187)同理,如若询问日本人何谓传统绘画,自古以来的大和绘、南画、琳派绘画等似乎都可以作为日本传统绘画的象征。
正是基于这种不确定的“传统”,亦造就了日本画特殊的发展模式。如日本学者丸山真男总结的,日西融合一直以一种庸俗化的佛教哲学方式在进行——“某物即某物”,或“物物一如”等。[25](P15)诚然,从菱田春草将琳派与印象派结合,以及竹内栖凤运用水彩技法革新南画一样,日本画的发展近乎于遵循着“西洋”与“传统”相对应的原则在进行。介于这样的规律,二战后,由于西方现代绘画的冲击,日本画也同样开始重视与挖掘材料本身的美。这种艺术的物质化趋势和日本画材料自发的特殊性相辅相成,厚涂表现的形成似乎也是必然。
但与战前不同的是,厚涂表现并未与传统的绘画形式相衔接,而是将绘画材料特别是颜料当作“传统”的载体。以至于有激进者言之:“‘现代日本画’画坛为了强调出传统绘画与其他画种的区别,硬是加上了‘传统’两字,这就变成了‘现代的传统日本画’。不过这里的‘传统’所包含的内容仅仅指那些如今不值一谈的颜料、绢、纸等绘画载体的特性罢了。”[26](P27)而后,随着20世纪80年代材料界限的打破,在绘画形式与材料上日本画都较之以往更加趋向于西洋,“传统”也变得越发难以辨识,而这也是引发画坛激烈探讨的根本缘由。
然而,困境亦带来机遇。可以说在日本画发展道路上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日西融合,虽然推动了日本画的发展,但无疑也打破了日本绘画发展中原有的常性,将自身限制在了西方的语境中,造成了“西洋”与“传统”间难以调和的历史困境。(9)黑川雅之在其《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现在的日本人都已经沦为西方世界观的奴隶了。”但自厚涂开始,在形式与材料上对于西洋的模仿走向极致后,画家们不得不开始直面自身。他们或者拓展新的表现领域,或者在传统领域中寻求发展。表现手法或以日本传统绘画为基础,或受中国传统绘画启示,或学习西方(特别是意大利中世纪)壁画、蛋彩画,或受西方当代艺术造型影响,甚或积极吸取传统设计乃至动画艺术要素。[27]就如画家西山英雄的观点:“我认为日本人画的画都可称为日本画。”[28](P3)此时,人们也开始以更加宏观的角度看待日本画,其概念也从狭义的日本画引向广义的日本画,定义也越发开放且具有包容性。
小结
事实上,东亚的美术都带有相同的烦恼,亦可称为一个命中注定的共同问题。那就是两者都拥有着传统美术与外来美术并存或对立的格局。[29]与日本不同的是,以水墨画为代表的中国画传承路径更具有连续性,相对固定的材料及绘画语言也造就了中国画中不可动摇的笔墨体系。而作为明治后出现的近代日本画,一方面汲取西方“现代”的养分,寻求自己身的发展与蜕变;另一方面,又极力延续着传统日本画的形态。基于日本画中传统的不确定性,日本画的画家也以极其矛盾的心态在“传统”与“现代”的绘画形式之间摇摆徘徊,甚至呈现出传统绘画形式与西方绘画一一对应的发展形势。而厚涂表现的确立,无疑打破了这一局面,虽然在绘画表现、材料选用及装裱都更加趋近于西方绘画,但随着西方架上绘画的衰弱,同样也标志着以厚涂表现为开端的对油画的模仿走到了尽头,日本画也不得不从自身出发,选择属于自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