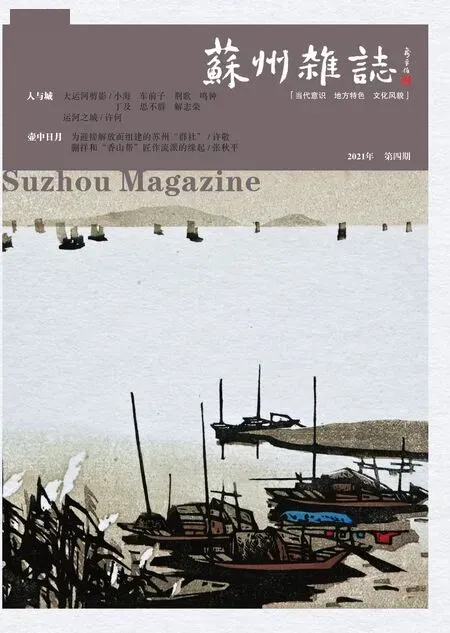花山:另一种叙事
杜渡
1
记不清和夕颜这是第几次爬山。
2
后来的夕颜似乎得了社交恐惧症,从密集的人群、烟火里不断后撤,身上那层坚硬的金属铠甲,被打磨、缩小成一只手指盖大小的甲虫,游荡于田园阡陌、丛林山水间;越来越怕见人,即使只与三五人相遇,惊恐得像只无助的小兔子,转身、躲闪,然后远远遁逃。
这样一来,城市就成了她的对立面。因为城市是人的海洋。每到节假日,就像一条决堤的河流,撕开了巨大的口子,黑压压的人群,大包小包,挤满了城市的汽车站、火车站、地铁等公共交通场所。而城市的大型商场、培训机构、菜市场、疫苗接种中心、奥林匹克公园,还有医院等这些大大小小的物理空间,在高楼的挤压下,像一个个透明、薄脆、封闭、不规则的玻璃容器,它们鼓胀着两只眼睛,随波游动。
我们从清早就开始收拾行李,带好面包、水果、水杯、纸巾、手机充电器,还有那柄绿色遮阳伞,从密不透风的工业园区出发,穿过人头攒动的容器,向花山逃离。
道路蜿蜒,像是某种撤退或溃败的延伸。进城、出城,我或者我们都在不断地尝试着逃离,成为我们生活空隙里的焦虑。夕颜常说,要是有一个静处,没有喧嚣车马,没有蔽日高楼,灌木绿植漫山遍野,此生也算是有了栖息之地。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图景下无意中与花山相遇。说是相遇,因为我们无法肯定是佛家所说的缘分,还是她有选择性地与我们相见,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一见欢喜,再见倾心。相对于闹市而言,她太遗世独立了,侧身在一处不易发觉的山坳里,等待遗忘或享受遗忘。
车子驶入建林路,再掠过几座弯月般的石孔长桥,然后拐入白墙黛瓦、花木掩映的小径,随着一个不经意的转弯,一尊高大的灰色水泥牌坊矗立在眼前,那是进入花山的第一道门楣,在墨绿色天空的映衬下,清幽与神秘瞬间漫漶过来,犹如禅定之境,人不免恍惚。

☉ 花山风景
山门就在不远处。门额前挂着一块横匾,上有“花山”两个红底金字,自右向左,那是康熙皇帝的御笔,而古意的写法,把花山引入幽深、古朴、久远。
驻车后步行。浓阴匝地,密林伴随,三五间苏式建筑依山而建。这里人烟稀少,三两人影在山石花木间偶尔晃动,半天没听言语。我和夕颜一下子就醉倒在花山的光景里。
3
对于花山,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解读。有人称之为世上最后的“桃花源”,有人说是江南地理的“终南山”,隐逸是它的灵魂。我对市隐持以怀疑的态度,整日在市井喧嚣之中,想坚守三寸灵台,也许只是一种理想状态。
据说,花山最早的一位隐者,是东晋时期名叫支遁的和尚。支遁,也叫支道林,道林是他的字号,花山有洞叫支公洞。从字面看,这样的名字,分明带着宿隐的意味,事实亦是如此。支遁这个人,出身于佛教家庭,少年时期才华卓著,常往来于京城名流之中,后隐居江南花山,安心佛学著述。他和众多隐士一样,于山野之中养马、放鹤。这也许是隐士们的标配。单说“放鹤”一事,除了历史上记载北宋处士林逋的“梅妻鹤子”,还有同时期隐居于徐州石佛山(现名云龙山)的山人张天骥。张天骥一生与鹤为伴,终身不娶。这一性情,吸引了当时徐州知府、大文豪苏轼的好奇。两人时常杯觥交错,不亦快哉!醉醺处,苏轼饱蘸山野之气,大笔一挥,写下千古名篇《放鹤亭记》:“……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
说起支遁养鹤,他与千百年后的张山人在山巅上放鹤不一样。支遁养鹤,担心鹤振翅高飞,一去不归,于是乎就弄断鹤的翅膀。
折翅,是因为惧怕孤独。孤独,是隐士最大的致命伤。
这也许正契中支遁隐居的调性。因为支遁潜研佛学,却好与世人讲经说法,晋朝皇帝派人请支遁到京城讲经,他欣然前往。没人请的时候,支遁自己也会主动出山,与当朝名士们谈经论道,打打嘴炮,一解寂寥隐逸之生活,所以有人把支遁和尚的隐居称之为半隐。支遁圆寂,葬于花山北峰。
“道人有道山不孤”。自此,历代名僧高士纷纷前来花山,诸如禅学宗师敏膺、晓青,文人隐士赵宧光、王芥庵,帝王卿相康熙、乾隆等人。明清易代之时,江南士子多归隐山林或剃度为僧,以示明志。
夕颜也爱读经诵卷,这不只是职业的习惯,也是与她内心物象相吻合的,比如钟声、粉笔、生词、琅琅的读书声和早晨的露珠,这些事物不染纤尘又晶莹剔透。夕颜自嘲道,士子隐居山林,是从“治国齐家平天下”退守为“独善其身”,我们这算什么呢?万人如海一身藏。
就隐居话题,我和夕颜从眼前的支遁和尚,到不远处隐居东山陆巷古村的明朝内阁大学士王鏊,屡屡展开清谈。王鏊在历经庙堂江山种种风云之后,在太湖边开启归来隐居故乡的时光册页。他以“守溪”自居,抛却建功立业之心、泽被天下之志,甘心像西晋姑苏前辈张翰学习,以“莼鲈之思”为名,返回故乡,日以酿桃、浇书度余生。
可贵的是,在人间隐居的王鏊,没有消沉于酒,而是携带几个文雅少年,即文征明、祝枝山、唐伯虎等人,寄情山水纸墨庙堂案牍中,用东山下的湖水、溪水、涧水、墨水、酒水洗尘。想必是受到《易经》的熏染:“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
退藏,洗心,守清流,好一个大隐王鏊!
4
自夕颜从鬼门关闯过来后,陪她登花山,成了我日常里一件十分紧要的事。姑苏美景繁复丰富,如盛名的拙政园、狮子林,粉墙黛瓦融合的平江路、山塘街,还有梦幻、现代和潮流的月光码头等等,都是神往、诗意的地址,一种生活在别处的寄托。天南海北的游客到了姑苏,必去打卡。可夕颜唯爱花山,花山静寂、隐逸和氤氲的自然之气,是她一次次奔赴的理由。
夕颜和我,出身寒门,白手起家,无所依靠。我们从山沟沟披荆、斩棘,然后一路跌跌撞撞、辗转颠沛。这一路上,岂是一个“累”字道尽?我和夕颜以为从此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于晨钟暮鼓之中尽享城市的歌舞升平。然而,夕颜却病倒了,坍塌的不只是身体,还包括身体内部的、千淘万漉堆砌起来的墙垣。
拾阶而上,扑入眼帘的,是众多的石刻,迈步即有“坠宿”“出尘关”“邀月”……这些大大小小、或隐或显的石刻,多达三百多处,那些刻着磨盘大文字的石头背后,一段段人文典故和名士风流,应和着词语的生气,在野草、树木、山石、光影和虫鸣的协奏里,漫漶着幽深古朴与原始混沌的气息。我以为夕颜不会有兴致的。毕竟我们来过好几次,一切景致,均了然于心,再游花山,说是看山,不如说是享受看山看水的过程。
我们走走停停,或于山道上极目四望,或坐于凉亭内小憩,无所事事的样子。时间开始慢了下来,山里的花草树木、鸟语溪水也都慢了下来了,只有慢下来的事物,才会扎根心上。
溪水潺潺,沿着水道独自静流,鸟声在每一片绿叶间脆响,一棵树在风中呼唤另一棵树。恍惚间,我和夕颜都进入了植物的时空之境。
夕颜驻留在“隔凡”石刻前,灵魂出窍般的迷离和发呆。
这些字都长进石头里了呢!夕颜叫道。我轻触了下夕颜的前额,她拂去我的手,指着石刻“隔凡”二字说,她没有说胡话呢!隐痛涌来。化疗期间的一幕从我的大脑褶皱里跳出来。
我带夕颜去医院负一层做肠胃镜检查。我们选择的是无痛手术。夕颜不同意,痛就痛些,不然太费钱。我没同意,坚持麻醉无痛手术。我知道夕颜疼痛感很强,再说这半生时光里吃的苦与痛还少吗?麻醉一次,至少能给予她短暂的解脱和安宁。手术结束后,夕颜躺在手术车上,推进了唤醒室,麻醉手术后,为了安全起见,需要等待麻醉性能退了患者苏醒。苏醒的最快方法,就是亲人在旁边唤醒。
医生告诉我,此时的夕颜,像个醉酒的人,一切纷扰、缠绕和困境都不复存在,只有酒精带来的愉悦和兴奋。可不久,我和医生就被夕颜的阵阵梦呓吓坏了。
夕颜在睡梦中不住地喊,上课了!哎呀开会迟到了!班里的课没人上呢、上面来检查了……夕颜闭着眼睛喋喋不休。我忙不迭地惊呼“夕颜”“夕颜”,夕颜不睬我,继续她的疯狂梦呓。
这是麻醉后的正常反应。医生告诉我,现在是病人最放松的状态,正常的人,是呼呼大睡,睡得香睡得沉;只有那些生活、工作压力大的人,才会在麻醉中释放内心的紧张……夕颜属于后者。医生面色看上去有点忧郁。
花山,人影寂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鸟语浓密。山道上,绿叶间到处是鸟影、鸟声。我们踩着绿阴,在鸟声鸟影里前行至大接引佛处。在一块巨大的石壁上,刻着“向上大接引佛”几个字。哦,接佛,向上,两个词语一下子击中了我和夕颜。指引我们去接佛,还是昭示教义:向上即佛?
一二游客从山上下来,至屡遭劫难、涅槃重生的佛像旁,双手合十。我们仓促攀谈了几句,竟然得知是从魔都而来,假日清修,住于山脚下。惺惺相惜间,我们就此别过。
5
我小心翼翼地陪着夕颜,走在碎石铺就的花山鸟道。道名为明代文学家赵宧光所题,巨大的石块上,小篆“花山鸟道”几个古朴之字,把花山推向幽远。
劫后重生的夕颜,与以前截然不同,在碎石铺就的花山鸟道上,学古人扶筇而行。
我为这根筇担心。山中青竹遍是,作为手杖颇佳。夕颜拒绝我的好意,甚至喋喋不休地与我谈论以一节翠竹的牺牲,成全她鸟道行走的罪过。后来的筇,是一节枯枝,这也是夕颜的意思。
隐居寒山的高士赵宧光曾借着酒意,多次在夜深人静时走在这花山鸟道上,与他同来的,除了妻儿与好友,还有徐徐清风和朗朗明月。
别走啦!
不怕!夕颜在前面回答着。
看好脚下!小心摔跤!
知道啦!夕颜拎着裙裾,蜻蜓般的舞步,腾挪、跌宕在碎石上,看上去比一只鸟还要轻盈,嘴里碎碎念。
夕颜说,她走完了所有厄运,剩下的就是平平安安了。
鸟道尽。我们来到花山翠岩寺前。夕颜略有疲惫。我指着寺庙前的石凳,示意坐下歇歇。夕颜头摇摇,目光指向大雄宝殿,说身体弱的人,是不能进寺庙朝拜的。夕颜就在门外,身不能至。
信?还没等我说出几个字,夕颜的手堵住了我嘴唇,不可胡乱妄语。

☉ 花山风景
高大森严的庙宇,一种神秘玄幻的物质缭绕而来。我把目光转向身后的一口古井,名字叫怡泉。井是石井,水位低,这与江南地域有关。据说“怡泉”二字出自晋人王羲之的手笔,作为行书大家,笔意酣畅、衣袖婉转间,两个字也就有了水的神谕。碑文记载,“怡泉”开凿于1700年前,系东晋高僧支遁和尚所凿,水清见底,久旱仍有泉流,千年不枯,是供佛、沏茶之上水。
山深有泉。我对夕颜说,来拜拜泉水吧。本是随口一说,谁知夕颜真的跑过来,凝视怡泉,眼睛里是满满的敬畏。
这还是我认识、朝夕相伴的夕颜?一个焚膏继晷、通宵达旦、工作狂的夕颜?
6
黄昏沿着太湖漫卷过来,翠岩寺里的钟声拨动了几下,该下山了。一个人在山里待得太久,会不会像山上的树根一样,伸出遒劲逶迤的根系,环抱着山石,树石合一,山有了树的生命,树有了山的骨骼。
我拉着夕颜的手,执意向山脚下走。主治医生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让她累着。步入中年的夕颜竟然耍起孩子气,执著得很。来都来了,这次我们一定要把五十三参走完,爬到山顶。从翠岩寺登上山顶莲花峰,中间要经过一条天梯般的石路,有五十三级石梯,俗称五十三参。
夕颜婴儿般的目光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五十三参,其典出自《华严经·入法界品》,指的是菩萨、佛母、比丘等五十三位善知之尊,在花山化身为五十三个台阶。“五十三参,参参见佛”。现实与经书上有出入,我在五十三参的铭牌上,赫然看到它的另一种说法。说康熙二十八年,欲驾幸花山登莲花峰,可是山路陡峭,无法登顶。于是方丈发动僧众数百人,连夜在这里凿出五十三个台阶。
姑且不去论证传说真伪,眼前的景象确实令人称奇。整个“五十三参”,完全是由一整块耸立的巨石雕凿而成,在悬崖深谷的映衬下,越发凸显出这五十三参的超凡脱俗。走在石阶上,你稍微跺一下脚,石头内部就会清晰地传出“咚咚”之声,就像寺庙佛堂里小僧敲打木鱼的声响。
真爬?我对赏风亭里休憩的夕颜明知故问。现在的夕颜,不怕吃苦,不怕山野里的各种小动物。她把肉身的每一次出汗或疼痛,当作是一种自我的修行,把与每一只小昆虫的遇见,视为是一种善念的闪现。
病好了之后,夕颜在阳台上种了几棵西红柿秧子。夏季的西红柿长熟了,像挂着的红灯笼。不幸的是,全被阳台外的不速之客小鸟们偷吃精光。夕颜竟然无动于衷,人吃,鸟吃,对西红柿来说,还不是都一样?
我们爬过五十三参后,一块巨大的莲花状山石屹立在山巅,上面刻有三个大字,“莲花峰”。这真叫造化,一块巨石,以莲花般的模样立于天地间。
夕颜不解,不是叫花山吗?怎么名为莲花峰?
我告诉她,莲花峰即莲花山,名取其后两个字:花山。莲花在佛教里视为圣洁之花,象征神圣与不灭,以莲喻佛,莲性亦佛性。
那我们也是修成正果、脚下生莲?坐在莲花峰旁,夕颜靠着我,一脸梦幻。
7
我对花山铭刻在心的,还是那句“吴西界有华山,可以度难”,语自春秋时代老子的《枕中记》。这琥珀般的文字,像隐秘的太湖石,有风八面,膨胀、空寂、玲珑,凝结于心,又洞穿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