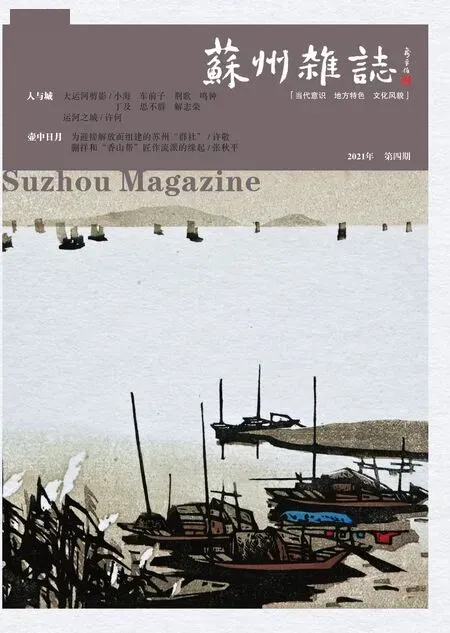亲切的味道
王啸峰
外公如果活到今年,正好一百岁。外婆比外公小两岁。他们都高寿。一个八十八,一个九十三。
今年为纪念外公百岁诞辰,大家想了好多纪念方式,一项内容始终没变。到纪念日那天,全家聚一次餐。
外公是教师,还是书画家、书画教育家。外婆是绣娘,后来被精简下放做了大半辈子家庭妇女。他们普普通通、简简单单,随着岁月流逝,越走越远,远得面目模糊、背影依稀。
我的许多梦,都以老宅为背景,客堂里、天井中、枇杷树下,外公、外婆都在。梦似乎与他们无关,我忙我的,他们做他们的。有一点我能确定,他们见到我,总是笑眯眯的。如果我坐到八仙桌前长凳上,眼前会出现我喜欢的各色饭菜,都是亲切的味道。
每次年夜饭,把圆台面压上八仙桌,全家就聚拢了。我特别关注两个冷菜。皮蛋和龙虾片。有一年,外公的刀工派不上用场了。外婆学会了用丝线切割皮蛋。绣娘对丝线的感情,细腻而敏感。她说,刺绣时,一般把丝线劈成十六股,高手能劈出六十四股。线越细,绣出的图案越生动细腻。她一手托蛋,稳住。另一只手拿丝线一端,牙咬另一端,绷直,慢慢下压,切进皮蛋。平滑地两下,四片大小均匀的皮蛋轻快落入虾子酱油中。外婆省油,我央求外公氽龙虾片。外公小时候家境富裕,常被外婆奚落家道中落,还一直有“少爷脾气”。他放油几乎是外婆的两倍。龙虾片冷油下锅,开始没动静。我们还在打趣时,龙虾片突然白花花地翻滚、膨胀起来。我兴奋得手足无措。外公用笊篱捞,盘子装不下,锅里还像在爆米花。外公也急了,问我放了多少。我举起空包装盒。他敲我一粒“毛栗子”。微焦的、黄的,外公不装盘了,我抓在手上“咔嚓、咔嚓”吃起来,声音响亮,抚慰心灵。
平日里,皮蛋吃不到,龙虾片更不可能。春节前,外婆戴着老花镜仔细地把备用券、公用券、专用券等票证用途、使用日期记下来,按时间节点,带上我去排队。她把我领到肉摊前长队伍里,跟前后打好招呼,自己去排短队。买好豆制品、蔬菜、干货后再回来。一次,外婆带着我买到一张大大的油炸猪肉皮,她开心地告诉我,荤腥可以吃很久了。猪皮被我扛在肩上,走回家的路上,我神气活现。她把肉皮挂在房梁钩子上。没肉吃,就去割一块,跟白菜一起煮。我喜欢在边上看她切菜。白菜脆生生地断在砧板上。我想白菜如果生吃,味道也应该很好。外婆切肉皮就没这么轻松了。她用力的时候,喜欢努嘴,越用力,嘴越使劲。我想帮她,可是不行,他们都不让我碰刀。每年冬天,外婆手上都长满冻疮。涂药膏、戴手套都没用。她手天天接触冰冷的水。我吊井水给她洗菜,井水有热气,包裹住她贴满橡皮膏的十指。外婆朝我笑着,继续做手上的事情。她也不让我端盛满烂糊白菜的大红花碗,说自己手上老茧多,橡皮膏多,不怕烫。不管有肉丝还是只有肉皮,我都喜欢吃烂糊白菜。白饭上舀两三勺热乎乎的烂糊白菜,再拌一拌,酥烂柔滑,白菜被少量肉丝或肉皮衬托得格外香甜。那张肉皮被挂了好几个月,梅雨来临后,外婆才取下最后一片,有点发齁。她用抹布一遍遍地擦,擦完再浸水,却并没有烧给我们吃。可我知道,她是不会扔掉的。

☉ 江南人家
周六傍晚,是我最盼望的时分。二十八英寸永久自行车发出响亮铃声,那是外公让我去拎东西的信号。永久车刚在天井里停稳,我就开始解书包架上的绳扣。细麻绳两端挂着竹篓、网线袋。篓里装虾,网线袋里是鱼。唐山大地震那年,我去外公学校“避震”。自行车带不动我和外婆,外公选择从胥门出发,坐机帆船沿运河北上,到公社后,再坐手划船去大队。一位学生家长骑着三轮车把我们从小码头接到学校。学校位置有点偏,远离大队部,三面临水。只有一排校舍,两位教师。我在黄昏的土操场上狂奔,蛙叫蝉鸣响成一片。几个学生家长裤腿挽到膝盖,踏着夕阳,大桶小缸送来鱼鲜。于是,我知道自行车上竹篓、网线袋里的鱼和虾也是他们送的。鱼是最普通的白鲢。红烧鲢鱼、鲢鱼烧粉皮等,是传统家常菜。后来,外公学会水乡人家的烧法。水烧开,把鲢鱼汆入,改小火慢熬,鱼汤渐渐发白像牛奶,简单加盐、黄酒、葱姜后盛起,碗里撒白胡椒粉,鱼香满屋,滋味极鲜。外婆拣出活蹦乱跳的虾,做盐水虾,其余红烧。外公带回来的酱油,我总觉得有股特别的味道,比老街酱园店拷来的酱油更咸,甚至有股煤油味,做出来的菜富有“野性”滋味。学生家长知道老师家里人喜欢吃甜食,凑准时间,在小陶钵里做酒酿。外公把网线袋网住小钵,穿在车把上,靠着黑色人造革拎包,一路颠簸三十里。来到我手上时,正是酒酿发酵最佳时。酒酿中心有个浅浅酒窝,照得出我馋兮兮的笑脸。没食物垫底的小肚子,一下子承受这么多酒酿,不到天黑透就发作。我只觉天旋地转,不停呕吐,浓浓酒糟味在老宅里弥漫。隔天,我却又期盼下一钵酒酿的到来。
外公带回来的竹篓里,更多的是小杂鱼,杂鱼里又以小鲫鱼味道最鲜美。外婆把小鲫鱼收拾干净,搭配自己亲手腌制的雪里蕻。老街上,外婆“腌手好”出了名。每次启缸后,她要把咸菜送亲戚、朋友、邻居好多份。看上去相似而简单的工序,因为不同的手,腌出的滋味大不相同。大雪节气过后,外婆买回大棵雪里蕻,摘黄叶洗净,撑开后,挂在竹架上晾干。腌菜大缸表面脱落了大部分漆,岁数比外婆还大。我卖力地帮外婆抬缸、洗缸。一层雪里蕻,一层粗盐,快满的时候,外婆取一块大黑圆石压住,最后封缸。冬至,开缸。外婆拎起一棵咸菜,放在鼻下闻,摘一小段进嘴尝。我也会偷摘一段来吃,爽脆咸鲜。她点点头,轻轻拍缸沿,感谢腌出好菜的老伙计。厨房里,起油锅。外婆将新鲜小鲫鱼两面煎透,倒入切成寸段的雪里蕻。咸鲜味道最能下饭。好几次,我贪快,被鲫鱼刺卡了喉咙。吞白米饭、喝醋、掐无名指等一系列祖传动作做完,喉咙竟然畅通无阻了。
外公有时会驮一些蔬菜回来。其中,我最爱吃茭白、大青菜、白萝卜。外婆不碰韭菜、大蒜、洋葱等气味浓烈的菜。可我没想通,她连茄子都不让进门。茭白最好切丝后炒肉丝。外公施展手艺,先斜切薄片,再细切成丝。两丝下锅煸炒时,他见我在边上看,还会突然颠勺、翻锅,在我的喝彩声中,加入一小匙虾子酱油,微微着色的茭白炒肉丝,清香清鲜。他的山水画也是如此,水墨底色,总会点染些许色彩:青苔、赭石、红枫等。排骨、蹄髈不常吃,外公带回的白萝卜要搭配荤腥。外婆便去菜场买最便宜的筒骨、扇骨,萝卜骨头汤上漂着一层油。我不时被看似平静的油下汤烫到嘴。春节前,外公在老街上买好几支新毛笔。学生家长们等他回去写春联、写诗词。提前约好的,他会在老宅书房里完成。我帮他按宣纸,随着他写字节奏往下拉或向上送。一幅字,他要写好几遍,挑最好的拿去给队里的朋友们。他抱怨自己一行诗写下来总不直,气头上,扔了笔抽烟。他抽烟不往肺里去,只是喷在空中。我见烟雾腾起来像条龙,更像他行云流水的书法。慢慢地,他平和下来,继续写字、作画。放寒假时,外公写春联任务也完成了。队里腌制的咸肉也好了,他们割一大块绑在永久自行车上。有了大青菜、咸肉,外婆会做一顿菜饭。哪天,我放学回来,吵着肚子饿冲进客堂,发现八仙桌上没有任何菜,那么肯定有菜饭吃了。一碗白玉凝脂被放在桌子当中。我迫不及待地舀大一勺荤油拌进菜饭。然后端到东厢房里。阳光射进来,菜饭亮晶晶,荤油香气看得见,正随水汽不停翻滚,温暖寒冷冬季。
外公常说:“名人书画,名人才有书画流传下来。”他并不著名,他的书画,一直挂在我家里、办公室。就像他和外婆做的那些家常菜那样,滋味似乎正在淡去,在我心里却越来越醇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