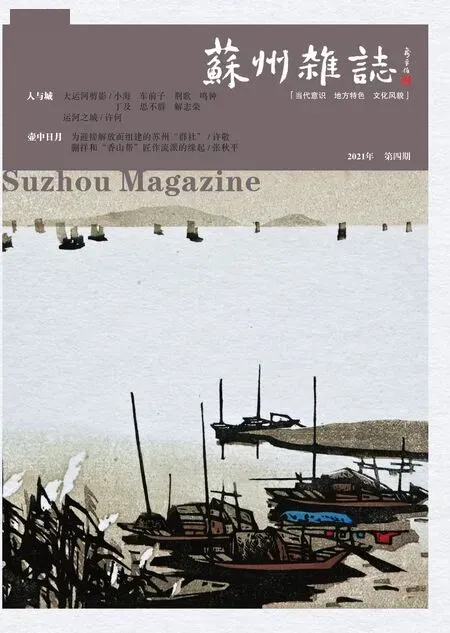莫共吴儿侧帽游
黄恽
1933年夏,范烟桥写了一篇短文《吴儿》,发表在上海的报纸上,从此把“侧帽吴儿”这个“梗”传播到了上海:
吴儿
费韦斋赠诗苏炳文将军之秘书郭竹书,有“莫共吴儿侧帽游”之句。某报倍致揶揄,韦斋移书辩护,一时引为谈资。韦斋高(原文如此,疑当为崖)岸不阿俗,尤好于文字弹人,勉郭固不失朋友相规之义,惟措辞似不为吴儿留余地,宜吴儿之不甘受矣。
竹书豪于饮,雄于谈,短小精悍,南人中之健者也。能诗词,惟不甚工,近居城北芳草园,雅有林木之胜,惜久荒芜,户外老梅数本,花时当携酒访之。
文中讲到苏州士绅费树蔚(韦斋)赠和郭竹书一首诗,里面有一句“莫共吴儿侧帽游”,引起了“吴儿”们的不满,引发了一场对费树蔚的文字攻击。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从头说起
先介绍费树蔚:费树蔚(1883—1935),字仲深,号韦斋,又号愿梨、左癖、迂琐等,祖籍江苏吴江同里。19岁中秀才,娶吴大澂七女吴本静,成了“洪宪太子”袁克定的连襟,此后与袁世凯发生了密切关系。1909年,费树蔚入邮传部,任员外郎,兼理京汉铁路事。1915年7月,费树蔚任北洋政府政事堂肃政使,同年11月退隐苏州。
郭竹书,字朱书,江苏省阜宁县人(一说丹阳籍),幼习商,弃商就儒,寒窗十年,曾在上海度其文字生涯,参军后历任军职,北伐之役,充曹万顺部团长,曾到过日本,后1929年入苏炳文部,任为秘书长。苏炳文部因为抗日在东三省溃散后,1933年春,郭竹书追随苏炳文来到苏州。
郭竹书到苏州后,相当活跃,他和苏州官宦和文人交游频频,还在苏州报刊上刊登诗词和文章,并在《大光明》报上连载其旧体诗集《残灰集》。
1933年夏天,郭竹书和几个文人、记者同游虎丘,写了一首题壁诗:
吴中山水太温柔,容易销沉不敢留。
忽忆韵松亭子好,伤心几度梦中游。
这首诗把吴中山水和日本京都的韵松亭相比较,吴中山水是软水温山,容易使人消沉,而韵松亭呢,如今也只能在梦中萦回,倍感伤心,心情沉郁。
费树蔚游虎丘,看到了这首诗,就忍不住依韵和了下面一首:
纨绮笙歌水样柔,岂如山水慰淹留?
茂宏壮语君应记,莫共吴儿侧帽游。
费树蔚这首诗,还得稍作解释一下。首两句是说:吴地的锦绣和笙歌像水波一样柔绵,难道像山水一样能给人慰藉和流连?第三句下一转折,用了新亭对泣这个典故,说西晋渡江诸高官显贵,在新亭饮宴,大家怀恋着当年洛阳的美好,丞相王导(字茂弘,为避乾隆的讳,改称茂宏,这里用茂宏,并不能说费树蔚还在遵守清讳,只是习焉不察造成的)对大家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第三四两句,费树蔚告诫郭竹书:你作为抗日英雄,应当牢记王茂宏的话,以收复东三省为职志,不要和苏州的少年们一起嬉游于山水之间,消磨了自己的壮志。
费树蔚这诗一出,郭竹书倒没有什么表示。被费树蔚捎带上的“吴儿”们却被惹恼了,立即跳起来:吴儿怎么啦?
侧帽吴儿
莫共吴儿侧帽游,来自费树蔚赠和郭竹书绝句中的第四句。所谓侧帽,就是歪戴帽子。吴儿,指的是苏州少年。这句诗的意思是说:不要和苏州歪戴帽子的年轻人到处游玩。

☉ 费仲深
侧帽用了一个典故。《周书·独孤信传》:“(独孤)信在秦州,尝因猎,日暮,驰马入城,其帽微侧。诘旦,而吏民有戴帽者,咸慕信而侧帽焉。其为邻境及士庶所重如此。”用现在的话来说,一件发生在偶像身上的偶然,被当成了时髦,为“粉丝”纷纷效仿。
古代秦州,原指甘肃天水一带。歪戴帽子这一形象,发展到后来,往往带有儇薄轻佻的意味,我们过去常说“流氓阿飞”“流里流气”这类词,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地痞流氓,他们的形象中往往就是歪戴着帽子。费树蔚写这句诗,把“侧帽秦儿”换作“侧帽吴儿”,在他的眼中,苏州少年的形象也是轻佻儇薄、不学无术的。不承想,就是这么一句诗,费树蔚等于主动抓了一只虱子到身上,摊上事了。
费树蔚的个性
范烟桥在《吴儿》中谈到费树蔚的个性:“高(崖?)岸不阿俗,尤好于文字弹人”,确属知言。
费树蔚在清末科举时代只博得一个起码的秀才功名,却在袁世凯北洋政府中做过高官(肃政使,相当于如今的监察部部长)。他生平很喜欢用文字捉弄一下别人,特别是送匾及送挽联,他往往别出心裁,弄点可作别解的词句,戏谑调侃一下对方。这里姑举一例:有一次,苏地银行界闻人国华银行经理潘子芳的爱姬去世,潘氏乃设奠而祭,并广讣亲友,征文赐唁,以示哀荣。费仲深写了一副挽词:如是如是。潘子芳张之厅堂,吊客读了议论纷纷。
客曰:人有言,一年如是,百年亦如是。费氏之词,殆指此耶?
或曰:费氏或谓潘氏如是家庭,则有如是变故,其意乃存贬箴。
或又曰:今虽死矣,而他人也不免一死,潘氏能作如是观,则当杀哀减痛,费氏意在慰藉潘氏。
各种解释似乎都说得通,据说费树蔚自己的解释却是用佛典《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如是如是,这般这般。然而,谁能确定费树蔚的这两个如是如是,到底是哪个意思,或包含了几个意思呢?费树蔚往往给人高深莫测的感觉,又让人体验到居高临下的傲慢和疏离。
费树蔚和苏州文人、记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这次正好给记者攻击他创造了机会。
吴儿的战术
范烟桥笔下的“某报”即指苏州小报《大光明》。这是张类似沪上《晶报》一样的小报,自1929年8月创刊,开始是三日刊,1933年后改版成为日刊,它的编辑、记者没几个人,且经常换,它的特点是很喜欢惹是生非,并借此吸引读者的眼球。
再回到“莫共吴儿侧帽游”这句诗上,“吴儿”指谁?哪个“侧帽”了?明显有打击面太广的问题,使得苏州的年轻人看了不受用,要和费树蔚较量较量。“吴儿”们战费树蔚却另有出人意料的章法。原因就在诗无达诂,这就给诗句的解读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你这么看,我那么看,都有道理,都说得通。谁叫费树蔚的文字意蕴丰富,能作多种解释呢?
《大光明》记者的战法不是以“吴儿”自居,跳起来大骂费树蔚,而是故意把火引向苏州名绅张一麐,说张一麐才是费树蔚笔下的那个“吴儿”。理由是此前费树蔚在一次讨论吴县市政的会议上,与张一麐意见相左,不欢而散,而郭竹书前些日子正好与张一麐在一起,且交往密切。这样的解释似乎怀有恶意,即从费树蔚处引燃了一根火柴,直接丢向了张一麐身上。说这是费树蔚耿耿于怀,借诗指桑骂槐,以泄心头之忿。他们意图让张一麐和费树蔚两虎相争,拼个你死我活,自己则坐山观虎斗。
说到张一麐与费树蔚的矛盾,《大光明》(1933年8月18日)有一篇署名翡翠的文章《费仲深虔心修身》,作了这样的介绍:
邑绅费仲深先生,道德文章,早为人所钦仰。前仅以县政会议上,与某公龃龉。发生芥蒂后,费乃愤而携眷赴平(引者按:指北平,即北京),对于苏地一切,不问不闻,态度异常消极。嗣榆关失陷,平津危急之际,费始南返,但知者殊鲜,乃费氏对于苏地各事,依然不问不闻,且目睹社会一切表现,颇不乏虚伪奸刁,人面兽心之徒,而以怨报德之风,尤成普通一般社会之积习。佛说因果,脱为事实,日后整个社会上之人物,均将陷入十八层地狱矣。因此费氏决心入同善社为社员。日前大宴亲朋,到者均执法人员,盛极一时。闻入该社后,可保个人健康,故费氏在其寓所,特辟静室一间,作长夜静坐,为修养身心之所焉。
这篇短短的文字,看似为费树蔚张目,却暗暗为他埋下了很多坑。
费树蔚辟谣
对此,张一麐置之不理,费树蔚却无法缄默,写信给《大光明》报,对“莫共吴儿侧帽游”等焦点问题,一并作了自己的解释,试图澄清被记者搅乱的浑水。然而话语权不在自己手里,他的信寄给了《大光明》报,《大光明》报把这封信冠以《牢骚满腹之费仲深》并把《仲深和郭竹书虎阜题壁》一诗作了附录,刊登出来。以下是费树蔚致《大光明》编辑信的全文,见1933年8月21日《大光明》,诗已前引,此不录。
大光明报编辑诸君鉴:前闻人言,贵报字里行间,时时关念鄙人,但多溢美之词,亦有传闻之误。鄙人道德文章,不足言,但所见迂拘,耻与流俗为伍。然如贵报所称与某公失欢,则绝无其事。一年以来,累劳贵报作雀燕之低昂。记曾作诗二绝,送登报端,仰代更正。而贵报言之不已。纵鄙人与某公胸怀坦然,决不因此发生芥蒂,而道路传言,漫成市虎,谓廉蔺之有争,谓洛蜀之有党,际此正气日消,浮言胥动之时,似不必平地掀波,添此一重公案。鄙人敢郑金(引者按:当为重字)为贵报告者:贵报所云某公,似指张仲仁先生,鄙人于仲仁先生,为三十年昆弟之交,敬之爱之,视如家督。仲仁先生,亦视鄙人若弱弟。平生针芥之契,曾无纤发抵(引者按:当为牴字)牾。近年外人颇疑吾二人之不合,实则吾二人皆生性耿直,论学论事,质疑问难,容或有之,此自书生常态,而神经过敏之流,遂谓大风起于苹末矣。即如鄙人去岁北上,为国历五月初旬,曾诣仲老话别,仲老亦来送行。到平即入西山避暑,寄以两诗。仲老亦和诗见忆。洎国历九月下旬抵家。第二日即相见。其行也,何所谓愤争?(苏人见无故出门以为奇事,岂知鄙人厌倦尘嚣,蓄念已久,且子女在北,迎请甚勤乎?)其归也,亦不因国难。(山海关之失陷,在今年一月三日,热河之失,平津之扰乱,时日大近,渺不相关。)换言之,鄙人何至因愤争而出走?何至因国难而奔逃?(甲子至壬申,吴下兵事严重时,何尝一步离开苏州?)立身行事,自有本末。似不必轻于揣度。故前日报载鄙人修书与某公通好,殆不甘寂寞,将作攘臂下车之冯妇。有人举以见告,鄙人哑然失笑曰:某公如指仲仁,则向为至好,何用乎“通”?若疑鄙人将问鼎于地方公事,何其浅视鄙人也。身非吴县籍,自先人以迄今兹,凡关于吴县人之权利绝不触犯,(即故乡吴江,亦复如是。鸡虫得失,蚊虻扑缘,何足邀予一?)但于国计民生有大厉害者,亦从贤达之后,以为邪许之呼。凡苏人之知我者,必有相当之认识。试问此言然乎否乎?近岁感于世运之消极,清议之缺乏,知杞人何必忧天,楚囚亦无须对泣。钳口结舌于当世之事,偶以文字之饮,遣此有涯之生。自谓与世相忘,世亦忘我,不图贵报仍时时以鄙人为谈助。夫鄙人为谈助,原亦无关轻重,但望勿再牵涉他人。昨见贵报云:鄙人虔心修身,入同善社为社员。日前大宴亲朋,到者皆执法人员。以入社可保健康,特辟静室,长夜静坐等语。此间有无同善社,吾不之知,至大宴亲朋,而到者皆执法人员。自思三年以来,未有此事。静室夜坐,修养身心,虽有此祈向,而无此事实。凡此皆不必深辩。所亟欲告贵报者,鄙人非“邑绅”,“道德文章”不足称,“县政会议”,开国以来,从未到过。“与某公龃龉发生芥蒂”某公不论为何许人,吾既未赴会,自无龃龉芥蒂之可言。“愤而携眷赴平”“愤”字不敢当。携眷似无可指摘。“儿辈皆在平沪,本不在苏”“对于苏地不问不闻态度消极”,既北行矣,岂有遥制苏政之理?况本不问苏政事耶!“榆关失陷平津危急”,鄙人归已久矣。以下尚有一段议论,曾否对客泛论及此,殊不记得。鄙人崖岸颇高,少所许可,独于仲仁先生少壮石交,老而弥亲,不欲使人造言诬蔑。然造言诬蔑,亦正无损于吾人之交愫也。贵报心无成见,有闻必录,故不惮覙缕,直言奉上。幸即据以更正。嗣后遇此等谣诼,祈为审慎登载。鄙人前日虎丘晚眺,见郭君竹书题壁一诗,颇有感慨。“吴中山水太温柔,我畏销沉不敢留。忽忆韵松亭子好,伤心几度梦中游。”即次韵和一首:“纨绮笙歌水样柔,岂如山水慰淹留?茂宏壮语君应记,莫共吴儿侧帽游。”盖销沉远志,与吴下沓拖之风气与山水何关?故为郭君进一解。贵报同人观此即可知鄙人怀抱之所存,而无任何对人问题也。率布,即颂撰祉
费树蔚 二二,八,一九
简单来说,费树蔚刊文辟谣,澄清了这几个问题:我和张一麐关系很好。我不介入地方事务。我去北平避暑,去和回来概与时局无关。我与同善社无关,也没大请其客。
费树蔚这封信真是放低身段,谦逊有礼地对待这些小报记者,也算说得明明白白了,应该能取得大家的谅解。
“吴儿”的围猎
然而,如今的人们对舆情的发酵都有所知,很多事情冷处理一下,自然淡忘,而偏要趁热辟谣,即使句句在理,也往往闹出绝大风波,因为言多必失,必然会扯出意料不到的事情。费树蔚的这封信正是如此,记者欺他示弱,对他的围猎开始了。先是署名一索的一篇《吴儿》,扳住了费树蔚信中的一点差错,向他叫板,并且坚持把“吴儿”扳扯到张一麐身上,说如果不是,难道您另有所指?
吴儿(一索)
费仲深先生虎丘晚眺,看见郭竹书先生的题壁大作,就了原韵,和诗一首。但是我们看见郭先生原句是:“吴中山水太温柔,容易销沉不敢留。忽忆韵松亭子好,伤心几度梦中游。”岂知费先生给郭作原句“容易销沉”“容易”二字改了“我畏”。诗曰:“纨绮笙歌水样柔,岂如山水慰淹留?茂宏壮语君应记,莫共吴儿侧帽游。”
费先生这首和诗,当然是有感而发。不过“吴儿侧帽”四字,费先生未免太小看我们苏州人了。有人说,费先生贵籍吴江,吴江属治于苏州,苏州通称吴下。这笼统“吴儿”二字,费先生下笔感慨,似乎欠思量一些。尤有进者,费先生对于本报所载消息,一辟再辟,矢志否认。本报读费先生来书,正如道路传闻,漫成市虎。对于费先生已往所载消息,一面不无怀疑,一面颇引为憾事。现在根据费先生所说一番话,和费先生借题发挥那首诗末句“莫共吴儿侧帽游”,我们认为费先生对于苏州人,是的确有不能谅解的一个或一般。但是张仲仁先生,他老人家,已经年近古稀,谓为吴老,似乎还对。张先生衣冠齐整,侧帽更谈不到了。况根据张费三十年之交,情如手足,一定另有所指。意者,费先生虚怀若谷,吴儿或系夫子自道,但费先生并不侧帽,而且据闻费、郭素昧平生,向未过从,实令人莫测费先生的原意了。
【编者按】目下吴门中人,侧着帽儿的儿郎,据我所知,其人实少。那么费先生或心有所指,并不是指我们正其衣冠的苏州人啊,请费先生有以语我来。
《大光明》1933年8月23日
26日,《大光明》又连发数篇关于费树蔚的文章,继续攻击他。其中一篇《费仲深之见客》(署名地虎),又提出费树蔚生活中官气十足的傲慢,说他对不管什么人都要摆架子。一篇署名“记者”的文章《答费仲深兼答二索》还有一个副题《有目共赏的借典骂世》,又责问费树蔚:
“吴儿侧帽”是不是借典骂世,未尝不有目共赏。并且“莫共”二字译句,苏州土话叫做“不要轧”。不要轧三字,是不但自己表示不愿和不屑的意思,并且还含有忠告警戒的立场。像“不要轧流氓乌龟等等”,就是明显的例子。
苏州小报文人最擅长的就是一人分饰几角,或几人合作,社里社外,分唱红脸白脸。既显示人多势众,又能收放自如,让对方摸不清究竟。现在很难厘清这些笔名之下的真实作者究竟是谁。这些作者骂得尽兴,一时刹不住车。不过文字之讼,也往往迷失焦点,沦为无谓的胡闹,同时也进入了无聊之境,最后还需自己收篷落帆。这么一闹之后,费树蔚知道再回应,只会更加招惹是非,万言万当,不如一默。
为什么费树蔚一句“莫共吴儿侧帽游”,竟会惹出这样一场风波来?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相当复杂,上世纪30年代前后的苏州,士绅阶层正在崩塌,新生力量的崛起,必然会和士绅阶层产生冲突,费树蔚无意中成了他们的靶子。而“侧帽吴儿”也因此成了一个“今典”,被记者们用来指代苏州的“富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