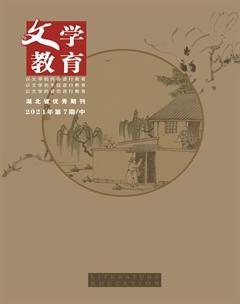撬动郧阳崛起的支点
一
我们称之为报告文学的体裁,是一种泊来的文体,按照教科书所下的经典定义,报告文学是新闻与文学的结合体。郧阳汉江二桥2008年破土动工,2012年竣工通车,李兴艳、赵峰合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河飞鸿》出版于2018年,不难看出,这部书送达读者手中时,“新闻”已然旧闻,这一堪称巨大的时间差最明显不过地凸显了其新闻属性的尴尬,尤其是当我们面临的是社会前进的步伐,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迅疾的信息时代,而数字化的传媒足以让地球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瞬间传遍整个地球村。正是基于这种现状,报告文学界对自己操持的文体的新闻性产生了动摇,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打算掉过头去与新闻作别,去投入文学的怀抱,而潜意识中不同文体的价值差异,或许也为这一转身提供了心理动因。
阅读《大河飞鸿》,作者的履历引起了我的注意,两位作者均是土生土长的郧阳人,而且在撰写本书之前,均有写南水北调的长篇纪实文学出版,而郧阳汉江二桥则可视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一个衍生物。不仅如此,李兴艳还借调二桥建设指挥部,成为亲自参与二桥建设的一员。2014年8月,指挥部正式责成李兴艳主笔,为这座大桥撰写一部报告文学。受命伊始,作者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未来作品的前期准备中,踏上了漫长的采访之路,郧县——十堰——武汉——北京——成都……寒暑易节,不知几度来回,二桥项目的动议者县长(后任县委书记)柳长毅及指挥部一班人自不待言,举凡审批二桥项目的从中央到湖北省到十堰市的各个职能部门,再从二桥的设计方到施工方、监理方、监测方、监控方,很难一一细数她采访了多少人,记录了多少文字,更何况作者面对的是桥梁工程这一技术含量极高,专业术语繁多的陌生领域,不修炼成“半个专家”,采访何以进行,其间甘苦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一言以蔽之,她陪伴着这座大桥从无到有,从蓝图绘制到大河飞鸿,走过了一段不算短的青春岁月。
依我看,上述成书过程便彰显了报告文学之于其他(例如小说)纯文学体裁的根本区别,即建立在采访基础上的纪实性,而采访环节的前期投入是否扎实到位,是保证报告文学成功与否的前提性条件。小说创作当然也可以通过采访收集素材,但虚构及其仰仗的不可或缺的想象力则是一篇小说(更遑论体量巨大的一部长篇)优劣成败的关键。以此观之,报告文学永远无法割舍新闻脐带的地方,正在于此。
我曾将采访环节细分为“介入型采访”(或曰“体验型采访”)与“旁观型采访”两种类型。新闻记者与大多数报告文学作者都属于旁观型采访者,与采访对象总会保持一定距离,通常持客观的、中立的立场和态度,而介入型采访者则与采访者零距离,甚至与之同呼吸共命运。毫无疑问,李兴艳、赵峰属于前者,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比局外人更能体验这座横跨汉江的桥梁,给自己,给每一个生活在郧阳山区的男女老少带来的切切实实的福祉,这就很容易理解他们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乐此不疲的辛劳和付出,而读者则能在每一页文字里感受到他们的体温和心跳了。
二
六十三万郧阳人对一座桥梁的感情,需要有人代言,不妨从书里摘录若干片段,感受作者用诗的语言,对一座桥梁挥洒的激情:
这是一座发展之桥,这更是一扇标志郧阳新世纪的时间之门。
六十三万双手啊,一起打开这扇时间之门——长风裹朝暾浩浩而升,阳光携春潮渤渤而盈。山川迅猛生长,汉水长舞霓裳。百花绽放,凤鸣呈祥。一路向南,蓝图溢出梦想;迎面北上,天地开阔浩荡。一个新的纪元,再启玄黄,风姿万方。
时间开始了。
郧阳,让世界对你重新想象……
汉江二桥建设若是一篇波澜壮阔的诗篇,那两弯高高悬起的钢管拱就是其中最经典的诗行。每一节钢管拱就像是诗行中散佚的一组组诗句,它们从远方来,跋山涉水,踩着整个诗篇的韵律,找到自己最恰当的位置,腾空、归位、歌唱。
走进这激越的诗行——大河飞鸿。
这是抚今追昔,从厚重的郧阳热土上升腾起来的激情和诗情,专家学者称郧阳为汉文化的摇篮,楚文化的源头。单是考古发掘出土的地下文物,连缀起来,便是活生生一部人类通史,中间略无断代,这就是作者为这座桥梁铺设的宏大背景,不写则全书势必单薄,铺展开来,篇幅必大不说,恐难免与焦点脱节,何況写郧阳的历史沿革、人文物理,有冷遇春、邢方贵、马富国的史志,梅洁的报告文学,杨菁的小说、蓝善清的散文,冰客的诗歌,王太国的历史小说、报告文学,兰士华的国画,等等,前人之述备矣。作者的应对之法,是点到即止,不多做驻留,而笔锋调转,思路为之一变,从“县域经济”这一政治经济学新课题切入,痛陈在这个龙腾虎跃的年代,僻处大山腹地的古老郧阳的落寞与凋敝,以及对前景的迷茫与期盼,而这不过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从而制约湖北经济发展一大瓶颈的例证,以此建立起全书的逻辑起点,便跳出了一桥一地,有了宽阔的视野和典型性。
动笔之初,梅洁就以老大姐的身份鼓励李兴艳:“一定要写一部像作家王宏甲《无极之路》那样的《郧阳之路》;一定要像《无极之路》里写县委书记刘日那样写郧阳的柳长毅”。梅洁看似平常的寥寥一语,却为全书奠定了基调。从上述引文即可看出,像李兴艳这样年青的女作家,胸中不乏充沛的诗情,这既是十分宝贵的,却也是应当适度警惕的,梅洁的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不能眼睛只盯着“桥”,而应该看到桥后面站立的“人”;还可以理解为,诗情画意的语言,行云流水的表达,甚至宏大深远的背景设置等等,这些为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文学性”,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只不过是行走在“接近文学”的途中罢了,“文学性”的内涵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归根结底,文学性的兑现,只能落实“文学是人学”上,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三
李兴艳显然是悟性很高的年轻人,这部报告文学的焦点,对准的是郧县的县委书记柳长毅。
在中国的政权层级体制中,县委书记是一个极为特殊、极为重要的角色,说一方兴衰系于一人也不为过。早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阶段,柳长毅就对县域经济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学术兴趣,他不仅参加过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调研,还参与了《县域经济研究》一书的撰写。机缘巧合,风云际会,当他先后以县长、县委书记的身份主政一方后,时代就给了他不仅坐而论道,而且起而行之的机遇,给了他把胸中抱负化为指点江山的实践的平台。
从古至今,地方官员到任,必先踏看县情民情,而所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李兴艳记录了柳长毅细读地方史志,了解了郧阳由一山野区区小邑,一跃而为华夏雄藩巨镇的历史,了解了他的历任前辈先贤留下的治郧得失,在栉风沐雨踏访汉江南北各乡镇的行程中,他的治鄖方略逐渐明朗了。作者在叙述此情此景时,将一部浓缩的地方简史穿插其间,与前之概述相映,颇得开合之妙。
谈到治郧方略,历届县委领导的思路竟是高度一致,一言以蔽之曰“依托二汽(十堰)”,待壮大自身体量后“改县为市”。岁月不居,作为老、少、边、穷的郧县,头上仍然戴着一顶“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柳长毅跳出前任窠臼的思维,李兴艳称之为“政治想象力”,她以熟悉的行当作喻:“柳长毅像一个出色的小说家,有着丰富的想象力,更是个谋篇布局的高手。一环环、一层层埋下一根根线,绵密地编织。环环相扣,紧密联系,高潮迭起,波澜壮阔,引着你,拽着你,怀着无限的紧张,期待,好奇,看下去,看下去……”这个方略的脑洞大开之处,是变“依托”为“融入”,即从地理位置上融入十堰,实现市县对接,如此则不但能从根本上改变郧县面貌,还能给十堰市的城市发展带来新的生机活力。具体实施,是在距离汉江一桥不足一公里处建一座二桥,桥南修一条通衢大道,穿山越岭,以25分钟的车程直通十堰,在丹江水坝加高至175米后,形成“一江二桥三镇”的崭新格局。李兴艳引用中国联想集团的一句广告语:“如果郧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一盘大棋,那二桥,就是这盘棋的‘棋眼,就是最为构建的那一颗子,一字落下,满盘皆活。”
四
阅读《大河飞鸿》,一个章节安排令我印象深刻:这部320页码的报告文学,二桥立项部分有103页,整整占去了三分之一篇幅,更令我惊讶的是,立项的过程竟然长达6年之久,用作者的话说,是一条“漫漫长征路”。这与办事效率无涉,只是因为汉江二桥虽然“对于一个地方的发展和百姓幸福来说‘重于泰山”,放在整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大局中却“轻如鸿毛”,何况一个山区贫困县,在不到1公里的河面上耗资两个亿架设第二座桥,谁听了都会摇头。有句话说世上最难的事情之一,就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子里,柳长毅要干的就是这件事。首先,全县干部要达成共识,其次,要取得市委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再次,是跑长江委、湖北省移民局、水利厅、交通厅、发改委,最后是上北京,到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国家水利部、国家发改委、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理顺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一家家跑,一趟趟跑,任何一个环节都困难重重,任何一家卡壳就会前功尽弃,整整花了6年时间,把“摇头”变成“点头”,办成了这件天下难事。
当我读到六年长征路的复杂过程书写后,不由悟到,纵横大江南北的每一座桥梁,都会有一个故事,都会牵动一批人的喜怒哀乐的。就汉江二桥来说,如果硬要说突破了哪个禁区,刷新了哪项纪录,大概可以说它突破了体制的硬壳,刷新了申报立项时间之漫长,过程之曲折,工作难度之大,惊动领导之多的记录吧。李兴艳花费全书三分之一篇幅叙述这一“流汗流泪”的过程是值得的,非以此不足以表现柳长毅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在道阻且长的困境中,顶着压力,承担风险,“拼死一搏”的决心。人生苦短,一辈子能干成一件大事是不容易的,而作为主政一方的官员,在任其间能切切实实的干成一件造福一方百姓的事,而非花拳绣腿地搞点所谓形象工程,更是不容易的。县委书记诸事繁杂,说日理万机,应该不算夸张,但柳长毅行起坐卧,心心念念,不忘造桥,因为兹事体大,在他心中,这就是阿基米德撬动地球的那个支点,其坚韧执着,甚至介入到桥型设计的专业领域。二桥设计评审会一节,不过是一个小插曲,着墨不多,但对今日二桥以何样面目示人,则至关重要。与会专家属意的是最为普通的平梁桥,柳长毅心仪的却是外形美观的中承式系杆拱桥,柳长毅又一次打破“业主”旁听的惯例,率先讲话,以肺腑之言,打动了在座每一位专家,终至峰回路转,而今这座壮观而又美丽的拱桥,已成为十堰市外宣中一个反复出现的背景元素。
以线性叙事展开的《大河飞鸿》,让其他人物随着桥梁进度次第登场,虽事有巨细,笔有详略,但都是围绕一座桥的倾心竭力,在各司其职各展其能的实打实的具体工作中,把人物一点点推到读者面前。李茂勇着墨不多,柳长毅从鲍峡镇党委书记任上将其调来,出任城投公司经理,为建桥筹措资金,干起了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口袋里的天下另一最难之事,角色转换,涉足陌生金融,竟干得风生水起,一番苦心加匠心的运作,给二桥化来了真金白银,在建桥各个阶段,都能及时兑付工程建设、拆迁、修路等各项资金,更令人称奇的是,其间操作的模式,即是后来红火的“BT项目模式”。这里明写李茂勇,其实也见出柳长毅的知人善任之明。
担任二桥建桥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的,是县人大副主任左文学,这个角色决定了他将与二桥建设全过程紧紧捆绑在一起,自然也成为全书书写最多的人物之一。这是个上过战场、蹲过猫耳洞的转业军人,透过这一人物,可以直观到中国基层干部的干练和勤奋。上任伊始,首先遇到的就是工程需迁坟1700多座的难题,这不仅触及到几千年的民间习俗,更在于坟主散居各地,且有大量回族群众。为了在敏感的民族问题上不至于出错,左文学甚至埋头典籍,成为了解回民和穆斯林文化和风俗的速成专家,遂得以拉近彼此距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使迁坟得以顺利完成。在二桥建设的几年间,遭遇过三次洪灾,一次龙卷风,尤以2010年“7.19”50年一遇的洪灾损失惨重,因为上游多艘失控船只撞击桥墩,致使“密密麻麻矗立着的边拱支架轰然倒塌”,在此后的清障、复建过程中,指挥部提供的“全天候、全过程、全方位的保姆式服务”,彰显了左文学高超的组织、协调能力。
五
作为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若能为该文体的建设提供一些经验,或者提供一些带有启发性的东西,那么其价值就超出著作本身了。比如前面提到的所谓“介入型采访”,比起走马观花的“旁观型采访”,在深入细致方面会有许多长处,但是一旦天长日久,成为作者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是否会淡化最初的新鲜感,可能是一个足以引起后来者警惕的问题。与此相关,《大河飞鸿》记录了许多编年体史书中常见的日程,甚至各机关逐日的会议安排,这是一种“立此存照”式的记录,在还原现场真实感的同时,却不免会阻断阅读的快感,也使行文略显拖沓,我推测性急的读者多半会跳过去,因为“文学性”并不等于材料的堆砌和冗长的过程描述。
细节描写。只要是写人,无论是小说还是报告文学,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小说的细节描写可以借助想象,那么对报告文学来说,就是一个考验作者捕捉细节的能力问题了。往往一个精彩的细节能让人久久不忘,甚至一个细节写活一个人,都是常有的事。《大河飞鸿》写到柳长毅到武桥重工集团,现场了解二桥钢管拱生产状况,在仔细对比了100多种颜色之后,选定了R02朱红色,这既是后来展示世人的“飞鸿”,“为了避免把颜色搞错,柳长毅小心地裁下一小块色卡样本,夹在笔记本里带了回来”;军旅生活摔打出来的左文学,面对特大洪灾,众人望水兴叹之际,奋战两天一夜一身泥水的副指挥长,却换了新装,“走出办公室的他,笔挺的浅粉色衬衣,黑色西裤”。前者是一个小小动作,后者是一句简单的外貌描写,展示的人物精神风貌,就胜过许多抽象说明的文字,我觉得像这样传神的细节,在书中还显得太少,当然捕捉细节的能力,即便是大家、名家,也都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修炼过程。
心理描写,是小说中人物描写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现代小说,借助于现代心理学的进展,在这方面业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遗憾的是这些经验却很难移用的报告文学中来,依我保守的观点,违背报告文学真实性的原则,钟情于小说笔法,随意编排人物的心理活动是不可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报告文学在这方面就毫无用武之地,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总是能另辟蹊径的,这里面名堂很多。
张弛之道。作为长篇叙事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报告文学,有几个大场面的支撑是十分必要的。在《大桥是怎样建成的》一章中,辟有一专节《“7.19”边拱支架之殇》,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洪灾的惊心动魄,清障的艰难凶险,工期的时不我待,环环相扣,都写得浓墨重彩,有声有色。当一桥飞架,通车在即时,作者突然插入一节闲笔,一个“出生40天就和爸爸妈妈一起从四川来到工地”的“小江湖”,2岁的“小妞儿”小雨来,也无多少故事,只是一个工棚前劳累一天的母亲,将其泡进塑料桶内洗澡的场面描写,挥洒了两页文字,是地道闲笔,读来却使人心生暖意,温馨之情,溢出纸页。其实闲笔不闲,若无闲笔调控,文章不但内容单一,节奏也必然显得呆滞,如同大江大河有峡谷险滩,也有静水深流一样,一张一弛,方合文武之道。
吴平安,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湖北武汉。
——记郧阳区水土保持局局长郑全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