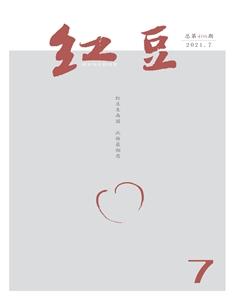个性独异的万物学与时光书
张德明
诗人吴少东的《吴少东诗选》较为生动地体现着诗人所具有的生命观、世界观和诗学观。作品中的“万物的动静”之“动静”,是诗人对大千世界充满生机和韵味的自然与人生的高度概括,而“万物”则凸显着诗人别具特色的诗学理解方式和审美表达路径。诗人借助“万物皆备于我”的自由化诗性思维,既能将世间的各种事物从容自如地纳入书写笔端,让它们发生联络和关系,碰撞出诗意的火花和光焰,又能令人惊奇地呈现不同性状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借助诗人的巧手点化,“万物”在诗的文学空间里,常能奇迹般地集聚组合在一起,一点也不显得隔阂和尴尬,也不显得突兀和荒谬。
世界上的万般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着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哲学结论。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交织起来的画面。”也就是说,吴少东所秉持的“万物关联”思维,首先是一种世界观和哲学意识,是遵循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所主张的一种基本的理解世界的态度与方式。与此同时,“万物关联”也是一种生态意识和生态精神。人类学家和控制论专家贝特森这样指出,人类和其他生物以及非生物在最高层面上相互关联,共同生活在一个超级生态系统中。这段话强调的就是“万物关联”的生态学意义。在当代诗歌创作中,生态诗已然成为一种显在的诗歌形态,吴少东所持有的“万物关联”理念,无疑是与当下方兴未艾的生态诗歌热潮相合拍的。当然“万物关联”的思想,更多的还是一种突出的诗性思维,是由诗性逻辑而促发的某种人文理念和情怀,因为诗歌创作向来就钟情于“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严羽《沧浪诗话》),向来就钟情于“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陆机《文赋》),那种超常规的物象串接令人匪夷所思的时空穿越,一定程度上更能将诗歌表达“无理而妙”“韵味无垠”的美学优点尽可能发挥出来。由此可见,吴少东在诗歌创作中,鲜明凸显的“万物学”精神征候,是哲学思维、生态思维和艺术思维三者合一的结果。这种综合性精神质素,赋予了吴少东诗歌开阔的情绪发散空间和自由的思维拓展路径,确立了其诗作独特的美学辨识度和个人化特色鲜明的艺术质地。
在吴少东的诗歌中,“万物关联”的表现形态是丰富而多样的,既体现为物物关联,也体现为物事关联,还体现为物人关联。多样化的关联形式在他的诗歌中自如组合,不断翻新,令人炫目的诗意光芒就在这些形态各异的组合与翻新之中不断闪现出来。《烈日》一诗中,“斧子落下”与“光亮漏下”,“杨树倾斜倒下”与“阳光轰然砸在地上”等,都可以视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在物理世界里,它们彼此似乎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但在美学世界里,它们却密切关联在一起,因为它们超越寻常逻辑的相互关联,诗歌的美学趣味也得以彰显出来,使诗歌的内涵和意蕴变得更加丰厚。
毫无疑问,展现物与人的密切关联,是吴少东诗歌中体现“万物关联”的万物学最为突出的书写形态。如《缓慢的石榴》,进入中年的诗人吴少东,对某种时间哲学有了独特的体认,因此将缓慢生长的石榴引为同调,对石榴“在暮春的高枝/点燃火焰”的迟缓式声明方式的极力礼赞,这体现的正是诗人由青春年少成长为中年人的过程中,经过长久的人生历练与意义追问而形成的某种相对成熟的时间观和生命观。
吴少东诗歌所凸显的万事万物相互关联的万物学,其让事物之间发生关联的方式也是各自不同的。有些时候,诗人采用了自然联想的方式,在诗歌创作自由随性、无迹而行的灵性化表述逻辑引导下,诗人发挥了善于联想与想象的思维特长,由一种物象很自然过渡到另一事物,串接自如,毫无滞碍。“我当然会分开最后一层薄纱/让光线一下子涌入,那时/我已适应这黑白渐变的世界/会带着普照的阳光,看待/所有的树木、人群与过往”(《晨起的惯性》)中敞现的“万物关联”都是由自然联想而生成的。更多时候,吴少东展示“万物关联”的诗性言说,都是启用了隐喻修辞,诗人借助不同事物在性质或情态上所具有的某些相似性、类同性等特征而将它们彼此扭结串联在一起,从而生成葱茏的诗意,如《快雪时晴帖》《通讯录》等。
在独特的万物学诗性思维之外,吴少东诗歌中的另一特征也格外醒目,那就是对于时光的烛照与书写。吴少东的许多诗歌,诸如《七月初的一天夜晚》《清晨》《晨起的惯性》《圆月高悬》等,标题上都有明确的时间符号,从中便不难发现诗人对诗情生发的特定时间节点的异常关注和格外重视。吴少东在那些时间线索特别明晰的篇章之中,时间在诗歌情绪散发和意义伸展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各有差别的。
有些时候,时间构成了诗人表达某种别样情绪的特定氛围,《七月初的一天夜晚》即如此:“此刻,城市上空,白云被灯火/烧得通红,像一张隐忍的脸。/大雨初歇,暴涨的江水开始回落/像常发完脾气的我。/没顶的石马从皖南探出/半个身来”,这是该诗的最后一节。由此可以看出,“夜晚”这一事件符码,在诗中充当了物象呈现和意蕴吐露的某種背景和氛围,有“黑夜”作为背景,雨后城市富有情味的独特景观才被诗人生动地勾画出来。有些时候,时间构成了诗人展示独到的季节感知和生命领悟的光阴节点,诗人将自我对特定时间节点上的个人化感知和历史记忆形象地表述出来,一定意义上构成了诗人吴少东表达某种富有纷繁复杂的情绪与思想的历史语境,昭示自己日渐平静和成熟的中年心境的特定历史语境。
诗人吴少东忠信的“万物关联”这一观念,促使他将大千世界的纷繁物象自如地纳入艺术的笔端,从而组构成异彩纷呈的生命景观和美学图式。从某种层面上说,诗人所持的这种“万物关联”的万物学认知,其实是现实世界所具有的诗性秩序在诗歌文本中的具体反映。也就是说,“万物关联”的万物学认知一定意义上体现着诗人的空间意识,是诗人对所处世界的人文景观和社会情态进行的审美演绎。与此同时,诗人对不同时间符码所具有的外在特征与内在意蕴的艺术书写,体现的毫无疑问是诗人的时间意识,是诗人对人生之中点点滴滴的时间刻度下具体而微的生活体味与情感投射的诗化呈现。
我们知道,时间和空间是构成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两个重要维度。它们彼此关联、相辅相成,共同编织起我们存在的场域和生命的经纬。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曾指出:“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关联的构架,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这段话强调了时间与空间对人类生命理解与历史建构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吴少东诗歌中的万物学与时光书,分别对应着诗人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二者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从而将诗人真实的存在样貌、精神境遇和生命情态艺术地呈现出来,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人文价值无疑是不可被低估的。
责任编辑 韦毓泉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