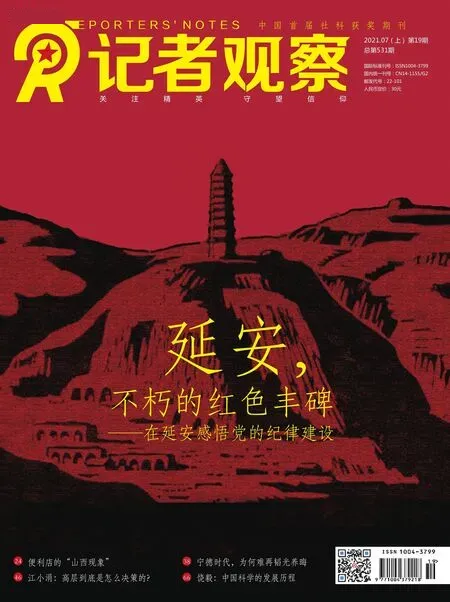被遗忘的洋务先锋时势造英雄,英雄湮没于时势
文 王亚晶

历史学家罗新认为,要掩埋重大历史事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缄默,一种是喧哗。他说:“比起记忆的历史,更重要的是遗忘的历史,它们是被精心排斥出集体记忆之外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晚清肯定不是被遗忘的历史,天朝梦碎的鸦片战争、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全民皆醒的甲午战争、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可就是在这如此喧嚣的局势中,还是有些政客被遗弃。
事件决定历史的走向,历史研究必须还原于事件,否则一切毫无意义。1875年,晚清的“马嘉理事件”(又称“滇案”)不仅影响了中英关系,也改变了三个人的命运。他们分别是郭嵩焘、张荫桓、许景澄。他们是推进历史进程的人,也是被历史遗弃的人。他们在史书上只有草草几页,百年后更是无人知也无人提。时势造英雄,英雄湮没时势,在“形势比人强”的晚清,他们从登场到落幕,一切都是那么始料未及。
思想超越时代的人被时代吞噬
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员马嘉理被打死在云南边境,英国对此大作文章,史称“滇案”。次年,清廷派李鸿章就此案赴山东烟台与英国进行谈判,并命当地道员张荫桓协助。张荫桓拒绝了英国人的一些无理要求,其强硬的外交态度深得李鸿章赏识。此次谈判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以“英国得到入侵中国西南边境特权”为结果,终结了“滇案”。然而,英国事后仍借口不断,任人宰割的清政府被迫决定派遣公使赴英国正式道歉。这个烫手山芋最后扔给了郭嵩焘。郭嵩焘欣赏许景澄的外交之才,想让他一同前去,却遭到了拒绝。一个“马嘉理事件”,张荫桓、郭嵩焘、许景澄三个人在这个极端的时代得以有了第一次交集。
1818年郭嵩焘生于湖南湘阴,17岁考中秀才后就读于岳麓书院,在这里他结识了一生挚友曾国藩。1840年,曾国藩已经进士及第两年,郭嵩焘却经历了两次名落孙山。失意的他经友人推荐来到浙江,成为浙江学政罗文俊的幕僚。这一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军队登陆浙江。当英国的坚船利炮兵临城下时,郭嵩焘认识到落榜的打击远比不上清醒看到时局的震撼。
1847年,郭嵩焘终于考上进士,为了这一天,他辛苦了9年,而他的同榜——李鸿章仅用了两年。好在二人后来成了知己,始终共进退。就在郭嵩焘将要踏上仕途时,父母相继离世。按律,他要回湘阴丁忧。此时,他的同乡好友左宗棠恰好从安化返回湘阴,不久后曾国藩也回湖南丁忧。历史就是如此巧合,让他们能顺理成章地相遇。
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太平军一路北上,于1852年9月围攻长沙。危难之际,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携带重金,邀请左宗棠守卫长沙。心高气傲的左宗棠没有答应。是郭嵩焘劝他出山:“公卿不下士久矣,张公此举,宜有以成其美。”左宗棠一战成名,建功立业由此发端。1853年,郭嵩焘发现,湘军水师与太平军实力相差甚远,致使湘军同时要应对陆路和水路的进攻,腹背受敌,于是建议曾国藩大力兴办水师。曾国藩听后把水师作为建设重点,逐步赢得水上作战的主动权。湘军在对抗太平天国中立下汗马功劳。可提起威名在外的湘军,世人只知曾国藩、李鸿章,又有谁知道郭嵩焘也是湘军的创建人呢?

马嘉理事件发生地

马嘉理

左宗棠
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声名显赫,搅弄得帝国政界天翻地覆,很多事已经和郭嵩焘无关,可“局外人”郭嵩焘却说,“三位中兴元辅,其出任将相,一由嵩焘为之枢纽”。时也命也,或许是时机不对。1876年,郭嵩焘终于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高光时刻”,“滇案”让他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驻外大使。这一次,郭嵩焘有了姓名,可殊不知却是骂名。
出使英国时,郭嵩焘已年逾花甲,但他仍苦学英语。他在伦敦看到了真正的“日不落帝国”,不同于当时国人描述的“鬼蜮伎俩”,这是完全迥异于古老中国的另一种伟大文明。他由此自我反省,感叹国家迟暮,每天用日记的形式写下来自己的见闻,他想让国人明白,真正的西方文明在郭嵩焘的文字里。他考察了牛津大学,出席了各种学会,参观了大英博物馆,看到了电蒸汽机。他的笔下,至今还留有150年前的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无以复加”。此外,他还适应了欧洲各种社交场合中的女性参与,并鼓励自己的夫人参加公使夫人聚会,在当时,这堪称是了不起的胸襟。按照朝廷的要求,他很快以《使西纪程》为名,寄回了自己从上海到伦敦51天行程的日记,还小心谨慎地删改了其中觉得可能“不中听”的话。

郭嵩焘
然而,《使西纪程》却让清廷开展了一场针对郭嵩焘的大批判,朝野上下纷纷骂郭嵩焘崇洋媚外、美化西方。王闿运说,郭嵩焘大概已经“中洋毒”,李慈铭说,郭嵩焘“诚不知是何肺肝”。民间百姓也大骂郭嵩焘“卖国贼”。1879年,郭嵩焘被召回,心灰意冷的他对朝廷绝望,决定告病回乡。回到湖南,“郭嵩焘当卖国贼”的骂声依然随处可闻。他仿佛成了过街老鼠,所到之处一片喊打之声。就这样,郭嵩焘背着骂名出访,又在一片骂声中黯然退出了政治舞台。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无论他做什么,说什么,都会被贴上“通洋卖国”的标签。他只得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实践汇编成《罪言存略》。“罪言”二字,足以说明他的愤恨与无奈。
郭嵩焘为通“夷情”,以洋务之“罪”,负独醒之累,是中国近代化的先行者。他曾公开提出“办洋务,应率先循习西方政教”等观点,成为当时士大夫阶级中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作为洋务先知,他的思想已经超越清廷所有人,把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名臣远远甩在身后。“生世不过百年,百年以后,此身与言者几具尽?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明哲保身不是他的性格,他决定飞蛾扑火。
出使之日,郭嵩焘也曾壮志满怀,期望以此行引进西方治国之道,无奈铩羽而归。1891年,中国近代化的先驱郭嵩焘带着满腔悲愤溘然长逝。好友李鸿章上奏朝廷请求为他赐谥号,但遭到了拒绝。他死得无声无息,可他的亡灵却还不得安息。在他去世后9年,也就是多灾多难的庚子年,义和团运动高涨,八国联军侵华,有京官上奏请求开棺鞭戮郭嵩焘的尸体以谢天下,认为这是他“崇洋媚外”罪有应得的惩罚。
思想超越时代的人会被时代吞噬。那时,郭嵩焘走得太远了,无法为主流接受,反而被时代唾弃。当时人觉得郭嵩焘独醉而众醒,但在今日看来,实乃众醉而斯人独醒,郭嵩焘是那个时代中勇于挽澜之人,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能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挫折对应的正是那个受挫的时代。
个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就在郭嵩焘郁郁不得志时,张荫桓和许景澄等年轻一辈外交家开始在晚清的政坛崭露头角。1837年,张荫桓出生于广州,史料记载:“幼而奇特,博究书法,锲意于学,无所不窥,性故通聪”。可生性聪慧的他却在科举之路上接连败北,直到27岁也没有考中秀才。于是他决定放弃科考,转而苦学外语,研究洋务。与持之以恒的郭嵩焘相比,张荫桓可谓是典型的反面教材,但从这一点不难看出他骨子里的变通。
1863年,张荫桓的舅舅李宗岱独辟蹊径,先后通过捐纳为他买到了监生出身和山东济南的候补知县。因是候补,张荫桓整日无所事事,时而在大明湖上泛舟下棋,时而去茶园听大鼓戏。那时候,谁都无法料到,济南的大明湖竟成了一时落魄的张荫桓的从政起点。1876年,张荫桓因得到李鸿章赏识,自此一路青云直上,入职总理衙门,旋升户部左侍郎。他是晚清政坛的一个“异类”,不是科举正途出身,也没有赫赫军功,全凭个人的能力脱颖而出。
1885年,清廷任命张荫桓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此后张荫桓侨居华盛顿三年,主要办理华工被害案,并对西方社会进行全面考察。美国自由女神像举行落成典礼之时,各国政要云集,张荫桓是唯一受邀的中国人。张荫桓主持洋务多年,又遍游南北美洲和欧洲各国,他的思想受到巨大震动,这在他出使期间作的《三洲日记》有所反映。回国后,他聘请美国人林余等编译《西学富强丛书》200余卷,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进行详细介绍,对开启民智功不可没。

张荫桓
1894年8月,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海陆两线接连溃败,清廷不得已派张荫桓等为全权大臣向日本求和。为了推迟议和,在战场上获取更大的利益,日方蓄意挑剔和刁难中国议和使臣。他们狂傲地指责中国与世界各国几乎完全背道而驰,称中方的外交文书不合规格,张荫桓等不具有缔约的全权,张荫桓等无奈回国。张荫桓在出使前就断定此行必会无功而返,果不其然,能看清时局的人,时局也不会辜负他。这就是弱国之下的外交官,虽清醒,却还得做糊涂人,这不知是张荫桓的悲哀,还是时代的悲哀。
张荫桓的出使历程让他提出依靠外国资金筹固国防等富国强兵主张,光绪帝对张荫桓的意见极为重视。1898年,戊戌年,也是晚清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年。闻名中外的戊戌变法在这一年6月拉开序幕,后人熟知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只是报幕人,张荫桓才是幕后推手,康有为的奏折都是交由他转递给光绪。变法的前4个月里,光绪帝13次单独召见张荫桓。召见频率之高,让朝中大臣怀疑,张荫桓必有耸动圣听之言。历史学家何炳棣也说,如果没有张荫桓给光绪帝“启蒙”,戊戌变法就不可能发生。
被架在火上烤的张荫桓很快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注意。时任军机大臣廖寿恒对慈禧说:“总理衙门所称能办事者,惟张荫桓一人,实亦非伊不可。”慈禧听后怒问:“若张荫桓死了,则将如何?”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张荫桓被捕,并被冠上了“汉奸”的骂名,慈禧准备将其与“戊戌六君子”一起处决,但在英国和日本政府的极力斡旋下,改为流放新疆。作为中国的外交官,却被洋人救了一命,这不知道是他的幸还是不幸。但此劫注定难逃,两年后的庚子年,因“庚子之乱”杀红了眼的慈禧又想起了三千公里之外的张荫桓,命令将其就地正法。时年63岁的张荫桓就这样枉死在了新疆这片沃土。
史书上可能会有不公,但人心不会
同样冤死在1900年的还有许景澄。在那个时代,每个人的命运都自带悲剧色彩,但如果1876年,许景澄没有拒绝郭嵩焘,或许他们两个的死亡都不会如此壮烈。历史不允许有如果,在拒绝了郭嵩焘后,许景澄在翰林院任编修。在这份闲差上,许景澄并没有停滞不前。对政治十分敏感的他,预感到未来的国家大事必重邦交,于是,他刻苦学习国际法和外交,“外交强国”的理想由此萌发。
1880年,郭嵩焘被召回的次年,许景澄的外交生涯刚刚起步。清政府派他出使日本,但因父亲亡故,只能返乡守孝。1884年,重返政坛的许景澄开始在外交圈发挥出惊人的才干,先后出使法、德、意、荷、奥等国。后来又兼任驻比(比利时)、驻俄公使,成为晚清著名的“七国公使”。作为一个传统中国读书人,许景澄担任外交官的同时,还钻研近代西方的科技、军事技术,编出了中国第一部世界海军通鉴《外国师船表》,并奏请朝廷加强海防。此外,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惨状,许景澄明知徒劳无功,仍据理力争。1890年许景澄被派到俄国、德国、奥地利和荷兰当公使,参与了当年和俄罗斯的帕米尔交涉。最终使中俄双方达成协议,在边界未划定前双方军队维持现状。
可风雨飘摇的清廷容不下清醒的人。许景澄与清廷的矛盾在“庚子之乱”中达到了顶峰。当时,义和团运动爆发。义和团觉得洋人都该杀,不分青红皂白,一路烧教堂、杀教士,最后威胁到了很多在华的西方人。端王载漪也提出攻打外国使馆的建议,无人反对。在危急时刻,许景澄表现出一个职业外交家的素养。他说,“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遭到了主战派的攻击。1900年5月28日,西方八国列强以保卫使馆的借口出兵中国,并于6月10日登陆塘沽口,“庚子之乱”爆发。慈禧太后对八国宣战,许景澄又说:“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此时,朝中主战派早已占据了绝对上风,自我吹捧的喝彩声淹没了真话,许景澄成了标新立异的异类。在一片喊打喊杀声中,许景澄的进言最终都成了他人头落地的罪名依据:“勾结洋人,莠言乱政,语多离间。”

许景澄
许景澄在出使俄国时,陆徵祥是翻译官,他曾对陆徵祥说:“不要依恋正在没落的体制,更不要去追随它,也不要指责它,而是要尽己责……为此,要学会缄默,不管遭遇怎样的侮辱和欺凌。”29年后的巴黎和会上,陆徵祥记住了。可在国家的危急关头,许景澄自己还是以逆耳忠言打破了沉默。
1900年7月28日,许景澄被砍头于北京菜市口,时年55岁。死前他的职务是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校长。但就是这位教书育人的校长在赴死时,还被前来围观的许多市民大骂:作为朝廷大臣,不为国家,反为洋人。”就这样,在人们的一片欢呼雀跃声中,许景澄含冤而去,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吾以身许国,无复他顾。”据相关史料记载,许景澄被斩首时,因为行刑前刽子手索贿不成,便故意把刀砍在许景澄的脊椎上。颈椎断裂而气管犹存,许景澄死前历尽折磨。在许景澄死后的第17天,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仓皇离京,狼狈奔逃西安。举国上下顿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耻辱中。一切就像许景澄预言的那样。
许景澄死后,他的继任者、北大校长严复为他写下挽联:“善战不败,善败不亡,疏论廷诤动关至计;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皇天后土式鉴精忠。”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这八个字便概括了许景澄的一生。史书上可能会有不公,但人心不会。人心就像一杆秤,拎得清是非,秤得起公正。百年过后,“卖国贼”的罪名已经洗去,他成了鲜为人知的许景澄,这样也罢,对他而言,或许已是最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