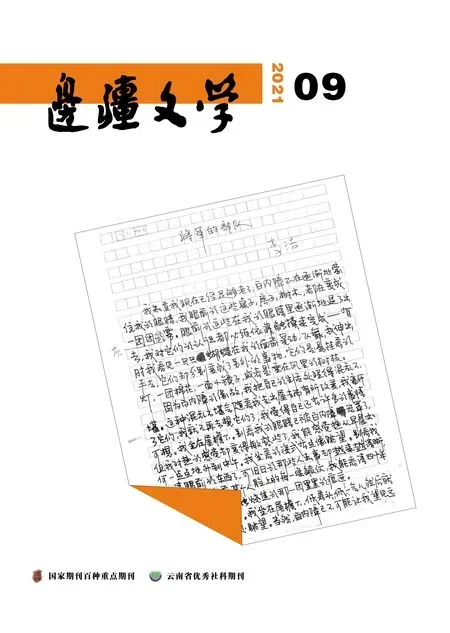夜读哀牢
苏轼冰
一
夜深人静,我独坐在离鄂嘉街不远的空龙河畔,听着深谷里的空龙河瀑布传来雷鸣般的水声,凝望星光灿烂的天空,面对眼前巍峨雄浑的哀牢大山,一时浮想联翩,思绪云游。
天开混沌,岁月悠悠。面对这本莽莽苍苍、寥廓千里的哀牢巨书,我读到了一个信奉“九隆神话”的哀牢部落,读到那片被称为“绝域荒外”的古哀牢国地,读到了古哀牢国人的祖先哀牢夷建立家园的艰辛,读到了古哀牢王“出入射猎,骑马,金银鞍勒,加翠毛之饰”的八面威风,读到了古哀牢国地域的广阔与强大,读到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司马相如、陈立等通僰道,破夜郎,置越雟、牂牁等郡,读到了诸葛孔明羽扇纶巾,凭智慧平息永昌乱世,设立云南郡,“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今祥云)、建宁(今曲靖),以实二郡”的明智之举……
哀牢系山名,亦为国名,与古滇国齐名,比南诏国早,原为古西南夷九隆氏居之,未通中国,汉明帝时内属,置哀牢。
关于古哀牢国,东汉史学家杨终在《哀牢传》(又称《九隆传说》)中有这样一个说法:大理洱海边上住着一个美貌的妇人,名叫沙壹,后人称她为沙壹母。她天天在海里捕鱼,有一天不小心掉进水里,触千年沉木后怀孕,生下十个儿子。沉木化作龙用人言问:“我的儿子何在?”九子闻之惊走,唯独幼子不走,背龙而坐,因而取名九隆。九隆长大后,雄桀威武,天资出众被推为王。当时山中有一个妇人,名叫奴波息,也生有十个女儿,个个花容月貌,九隆兄弟就娶十姊妹为妻,子孙繁衍,分别在山中溪边居住,子子孙孙逐渐强大为哀牢。
据有关资料记载:距今约2400年前,以今保山为中心的怒江中下游区域曾经有过一个支系庞杂的强大族群,族属多达二十多种,称为“哀牢夷”,是古“西南夷”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创立了风靡数百年的古哀牢国,还创立了影响极大的哀牢文化,是云南历史上的文明古国之一。
古哀牢国从最初的哀牢部落发展而成,历史悠久,疆域辽阔,物产丰富,民族众多,文化发达,历时400 多年,西汉以前古哀牢国的版图东起今天的大理洱海区域,西抵印度,东北部接梁水郡(今红河),南与交趾(今越南北部一带)毗邻,范围远远比《华阳国志》记载的“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要广袤得多,所辖也不仅仅是“54660 户,人口571370 人”,而是随着战争的不断变化而变化。最强大时,已扩大到了滇池(现在的昆明附近)及滇中、滇西等地区。
西汉时期,汉武帝开疆拓土,中原王朝不断扩张,经略西南。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率77 邑王、5 万多户、55 万多人举国“内附”,使古哀牢国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入了封建社会。汉王朝借机将“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的哀牢地域纳入中央集权统一管辖,设立永昌郡,鄂嘉属于古哀牢国的重要领地。
哀牢归汉在当时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举国欢腾。著名史学家班固在其《东都赋》中记载:“绥哀牢,开永昌。春王三朝,会同汉京……内抚诸夏,外绥百蛮……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浃,群臣醉。”
哀牢归汉是当时朝野上下一心、顺时应变、向往先进文化、积极进取的结果。柳貌内附有功,汉明帝按汉武帝赐的“滇王之印”的字体、样式、性质颁赐他“哀牢王章”,为他举行盛大宫廷庆典。从此,中原文化迅速入主,曾强盛一时的古哀牢国随着历史的岁月烟飞灰灭。班固《东汉记》中记载“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徼外哀牢王率众慕化,地旷远,置永昌郡。”杨终的《哀牢传》中亦有言“哀牢内属,汉朝得地,一时盛事”。二者所记,便是这一盛事。
云南古无汉民,千百年来,原始的夷人部落在这块神奇而荒蛮的土地上繁衍生息,自生自灭。庄蹻入滇建立滇国,同时也将汉文化融入原始的少数民族文化,创造了神奇古朴的古滇文化。然而,古滇王国毕竟势单力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宝剑一挥,昔日的古滇国灰飞烟灭,只留下一枚沉甸甸的“滇王印章”供后人回忆。
古滇之南远离中原版图,但因与交趾(今越南)等地接壤,地理位置特殊,一向为中原王朝关注。为此,双柏就与古哀牢国一起被划入中原版图,从此纳入了中原王朝郡县管辖之下。东汉末年,蜀相诸葛亮亲率大军平定南中,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双柏属之,鄂嘉归属永昌郡。
鄂嘉是从昆明等地进入古哀牢国的门户,也是哀牢大山中一个最为古老的驿站。
鄂嘉,这地名的由来十分神奇。据清《乾隆鄂嘉志》记载:“元大定间,大星殒于鄂嘉之黑初山,化为黑石,状如冬瓜,有点如星,击之锵然有声。人不言举之则动,言则举不动,土人以为怪,积薪焚之,雷雨交作,众惧而止。”当地彝话呼石为鄂,彝话中鄂嘉为天上降下吉祥美丽陨石的地方之意,故取名为鄂嘉,鄂嘉之名从此而始。
然而明末清初,以鲁魁山为中心的彝、汉、傣各民族大起义,烽火遍及新平、鄂嘉、双柏、峨山、墨江、景东等数十县地,长达数十年之久,明、清政府几度调集官兵镇压,至康熙六年(1667),鄂嘉古城全部毁于战火。
二
读哀牢山这本大书,翻阅鄂嘉这一章节,罗仰锜是绕不开的重要部分。
清雍正十年(1732年),鄂尔泰用重兵镇压了农民起义军,鄂嘉才恢复其统治,改设州判,江西吉安府泰和县贡生罗仰锜曾两次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到此上任。
在鄂嘉,罗仰锜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个人物。只要到民间查访,很多民间“野史”都把罗仰锜的故事演绎得精彩万分。关于罗仰锜,好多年过去了,我笔记本里仍有记录。
那是雍正十年八月底的一天傍晚,正值壮年的罗仰锜身背几件换洗衣服,带着一路上好心的山民为他准备的饭团和半升多包谷炒面,肩上挑着两捆旧书,正急匆匆地赶路。
突然,一声炸雷般的吼声把他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随着声音,山林中突然冲出一队人来。来人个个头戴树叶帽,脸抹锅烟子,大多赤裸着上身。
“你们是谁?”罗仰锜知道是碰上拦路抢劫的了。他身上只有不多的几文路费,不怕抢,但着实吓得不行。
“少废话,想活命就把钱拿出来。”走在前边的一个毛贼上前一步,边说边就把刀放在了罗仰锜脖子上。
“我乃江西吉安府泰和县贡生罗仰锜,被举荐到鄂嘉州任职,只有微薄的一点盘缠,你们看得上就拿去吧!”
几个黑脸人不相信地忙活了大半天,真的只从罗仰锜身上搜出了几文花钱,领头的把钱丢还他,高声说道:“耽搁了,罗老爷!等你养肥了归来,我们再会面。”说完,带着手下的人一溜烟隐入了密林。
十三年过去了,当罗仰锜因积劳成疾,拖着患病的身体回归故里,又踏上了这条森林茂密的深箐时,当年的一幕居然又出现在眼前。
“站住,想活命就留下买命钱。”还是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黑脸赤身,罗仰锜一下子竟还以为是在梦中。
“快拿出钱来。”直到有一个黑脸人用火药枪戳了他一下,罗仰锜才知道这不是梦。
“我是十三年前从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到鄂嘉任职的罗仰锜,今天告老还乡,身上只有微薄的盘缠……”
“哦,罗大人,十多年不见,久违了!”领头的一个上前,一脚踢开用火药枪顶着罗仰锜的黑脸人,大声说:“快让开,谁不知道罗大人是出了名的清官。”说完还吩咐手下给罗仰锜送上路费。罗仰锜死活不依,黑脸人只好吩咐手下一齐跪下,目送罗仰锜迎着黄灿灿的夕阳一路远行。
以上所记的这些是否真实,志书上没有记载,但在百姓中却广为流传。我曾查阅了很多志书,那上面有很多有关罗仰锜在鄂嘉13年廉洁做官,两袖清风,被百姓称为清官、好官的真实记载。
罗仰锜出生在江西吉安府泰和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是一个一生不得志的读书人,母亲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大家闺秀。他自幼聪明伶俐,饱读四书五经,却屡试不第,人过中年才考中了一名县岁贡生,到云贵广西三省试用,这才谋得一份官差,离妻别子,到远隔千山万水的鄂嘉,做一个小小从七品州判。
罗仰锜上任后,他一面为鄂嘉绮丽超凡的山水而着迷,一面又为鄂嘉因连年战乱,匪患无穷,导致百姓缺吃少穿,民不聊生的现实而焦虑。才能卓著的罗仰锜在几乎被外界遗忘且长期得不到官府重用的情况下,始终坚持禁烟、剿匪、发展生产,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地为民办实事。他以兴利除弊为己任,十几年如一日地在鄂嘉建城垣、设防卡、薄赋税、抚汉夷、兴汉学、建桥梁、通商道、倡耕织、促商旅,倡导清贫为官,清白做人。
鄂嘉地处隘区,古为两迤通衢,是昆明、楚雄、玉溪等地通往普洱、临沧、德宏,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古驿道,南来北往的马帮络绎不绝。罗仰锜坚持禁烟,严厉打击烟贩,曾有不少的马哥头、烟贩子给他送来钱物,都被他严厉拒绝。他的这些德行让很多烟贩子和财主伤透了脑筋。有一伙势力较大的烟贩子勾结当地财主,在一起商量对付罗仰锜的办法。
钱物他不要,除之又怕惹怒官府,再说罗仰锜亲自培养训练的卫队也不是好惹的,他们个个精明强干不说,而且都对罗仰锜死心塌地。几个人一合计,给罗仰锜送来一位百般挑选,年轻貌美的绝色女子和一些钱物,说:“罗大人远离家乡,几十年出门在外,生活清苦,钱物用于改善伙食,女子供你使唤。”
罗仰锜一声大笑,朗声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好色,你情我愿,我为人为官自有其行。自己拿着朝廷俸禄,该为百姓办事,禁烟乃我分内之事,只要我在位一天,一两大烟也别想从我管辖的地面上过去,你们送的金钱美女我更是消受不起,你们请回吧!”
罗仰锜为官清廉,滴水不进,使众多烟贩子奈何不得,有的骂他是“憨官”,有的污蔑他“有病”,但老百姓心中却有一杆秤,人人称赞他是清官、好官。
罗仰锜在鄂嘉任职多年,得罪了许多达官贵人,但他却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为子民,大力提倡“优商以礼,恤民以宽”的政策,对地方田主虐待民众的不法陋习一一革除,并以先进生产技术促进农耕,发展生产。
当时鄂嘉少数民族群众种田地以施人畜粪为耻,广种薄收。罗仰锜自己出钱购田数亩,亲自耕作,带头将人畜粪便窖熟后施于田间,以作示范,并撰劝农条目,把中原先进的耕种技术传给鄂嘉民众。他还从四川、广东引进红薯栽培技术,使之获得大丰收。他还大力推广种植桑麻果木,倡导栽桑养蚕,使之蔚然成风。在他任职期间,不但民众能温饱,衙中存粮还备足3年支用。
他还十分重视教育,兴办书院5 处,对学生给予赏封、保荐,对各族学生一视同仁,使辖区内出现了“野无不耕之田,户多朗诵之声”的“人皆德之”景象。
在当地的老百姓中还有这样一个传说:有一次,罗仰锜亲自带着兵丁挑茅厕里的粪水浇菜,附近民众听说后都跑来看,很多人还捏着鼻子议论纷纷。罗仰锜不但不生气,还当众向百姓讲授人粪尿、牲畜粪对庄稼生长的好处,大讲特讲“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的道理。几个月后,当自己种的庄稼蔬菜长势喜人时,他又组织百姓实地观看,并给每人都送上蔬菜,拿回家比较品尝。
鄂嘉地处偏僻,当地少数民族历来受歧视,罗仰锜上任前,当时的学堂是不允许少数民族的子女上学的。罗仰锜上任后,首先在卫队里吸纳当地少数民族青年,并且到处游说,要求学校将少数民族子女与汉族子女同样对待,招收少数民族子女。对于贫困学子,他还拿出钱财给予资助,大力提倡贫困农民的女子上学读书。
罗仰锜主张各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鄂嘉自古就有农历七月十五“赶鬼街”的跳笙习俗,历来做官的都对当地这种习俗很鄙视,以“有伤大雅”为名严厉禁止,罗仰锜却不这样做。他认为民间的节日习俗谈不上什么“有伤大雅”之说,相反还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和睦,应该大力提倡。节日期间,他带着兵丁前去观看,记录下不少民间山歌小调,使这一极具地方民族特点的节日流传至今,声名远扬。
由于罗仰锜对鄂嘉治理有方,成绩不凡,乾隆六年二月,他奉旨调往另一个民族地区中甸任州判。可他走后几年,鄂嘉匪患突出,鸦片走私猖獗,百姓苦不堪言,经过层层举荐,乾隆八年正月,罗仰锜又奉旨调回鄂嘉任州判。
罗仰锜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大有爱惜民众之心,颇有民主思想。他常常拿出自己的钱物扶贫济困,救灾救济,还亲自修志,撰风物,写诗文,真实地反映鄂嘉的山川河流、自然景物、民风民俗、矿物资源和地理、社会情况,为后世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为后人所敬仰。他编纂的《乾隆鄂嘉志书草本》至今还有十分珍贵的价值;他写下的不少诗词、对联,至今还被人们传诵。
清乾隆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因多年的积劳成疾,罗仰锜深感体力不支,上书告老还乡。他走时,鄂嘉民众以泪洗面,长跪在地十里相送。后来,鄂嘉麻嘎河的一块石头上刻了一首题诗,曰:“好个鄂嘉州,西水向东流;富贵无三代,清官不到头。”有人说是罗仰锜所作,有人说是百姓写给罗仰锜的,众说纷纭,但鄂嘉百姓却早已在心中为这位远道而来的“父母官”立下了一块永恒的丰碑。
几年后,罗仰锜在江西吉安府泰和县贫病而死,数年后消息传到鄂嘉,上万民众悲恸大哭,纷纷为他烧纸钱,说:“罗大人在世时一生清贫,在阴间不能让他再缺钱花……”
时至今日,鄂嘉的老百姓每年清明上坟烧纸钱的时间都比别处早,从农历二月初八就开始。当时我问其原因,有一位老人笑着对我说:“我们给祖先上坟烧纸钱,也得给早年在鄂嘉做过官的罗大人烧纸钱。他一生清贫,缺钱花,迟了会带不到的。”
历史风云早已被岁月的风雨涤荡得干干净净,但有些东西岁月的风雨也冲刷不了。在鄂嘉,不少地方至今还遗存着1734年罗仰锜率民众在城东卧象山之南大村修筑的石城遗址。
夜读哀牢,读哀牢山下的古镇鄂嘉,回想历史的天空下的昨天,那些已经停熄久远的战火似乎还在我心中熊熊地燃烧,此时此刻,哀牢大山留给我的,除了神奇秀美的大自然让我顶礼膜拜之外,更多的是咀嚼和沉思,对过去,也是对未来。
夜很深了,我的阅读还没有结束。仰头望,浩瀚天宇,月华如水;低头看,四周独我,遍野无物,顿觉得阵阵清风拂面,似饮了一壶哀牢大山独有的原生古树茶,爽心润肺,才思敏捷。起身伫立河畔,耳际水声如雷,如千军怒吼,万马奔腾,更感悟哀牢大山的博大奇雄,伟岸超凡!
鄂嘉的“鄂”字,实为石字旁,但因原字过于生僻,输入法无法显示,故以“鄂”暂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