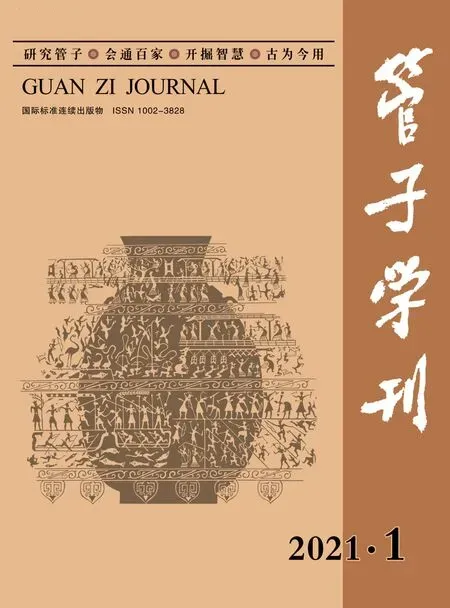慎到的“齐物论”
周丰堇
(湘潭大学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0)
“齐物论”是先秦诸子普遍探讨的一个论题,不仅庄子有传世的“齐物论”,而且墨子(1)墨子提倡“兼爱”“尚同”“僈差等”,荀子批评墨子说:“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19页)蒙文通认为,墨子和田骈、慎到的贵齐思想相近,是能做什么的人便让他做什么。(蒙文通:《佛道散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5页)、尹文(2)《群书治要》引《尹文子·大道》篇说:“为善使人不能得从,为巧使人不能得为,此独善独巧者也。未尽善巧之理。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贵工倕之巧,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魏征等编,《群书治要》学习小组译注:《群书治要译注》[第二十二册],北京:中国书店,2012年版,第64页)此派贵齐之论,反对独善、独贤、独事、独行、独治,而崇尚共治、共巧。其所谓“齐”,指社会政治中的分工而共事,因万物之不齐而各得其用为齐。、彭蒙、田骈、慎到、《吕览》(3)《吕览·不二》说:“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68页)此贵齐之论,同慎到“不两”和“各得其用”之齐物观,详见后文。等都有贵齐思想,或者说有不同于庄子的“齐物论”,而荀子对贵齐思想也有一个整体性的批评(4)荀子除了批评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之外,还认为:“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52页)荀子是从社会等级和分工必要性来反对贵齐之论。,足见贵齐思想或“齐物论”在先秦之流行。蒙文通认为,尹文、田骈、慎到等人的贵齐学说是从墨子来,墨学“大俭约而僈差等”可能是这一派“齐物论”的初旨(5)蒙文通:《佛道散论》,第75页。。傅斯年认为慎到也有“齐物论”:“《天下篇》所云‘去知弃己’、‘舍是与非’、‘块不失道’等意义均与《庄子·齐物论》相合,而‘齐万物以为首’简直把《齐物论》的篇名也揭了出来。”(6)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05页。容肇祖赞同傅斯年的主张,他认为“齐物论”即《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慎到所著的“十二论”之一(7)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第505页。。顾颉刚赞同傅、容二家,他认为《吕氏春秋》记“陈骈贵齐”,陈骈即田骈,亦是“齐物论”作于他们那一派的证据(8)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第505-506页。。然而庄子的“齐物论”历来被广泛关注,目前学界对“齐物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庄子“齐物论”,而墨子、尹文、彭蒙、田骈、慎到等人的“齐物论”却罕被注意,除蒙文通、傅斯年、容肇祖、顾颉刚和李凯等明确指出,彭蒙、田骈、慎到等人创作了“齐物论”或持有不同于庄子的“齐物论”之外,皆未能有意识地将慎到等人的贵齐思想视为另一种“齐物论”,但蒙、傅、容、顾和李诸家对这一派的“齐物论”也未能展开论述(9)参见蒙文通:《佛道散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9-101页。李凯:《慎到“齐物”思想管窥》,《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1期,第12-14页。。另一方面,关于慎到的思想,学界一般认为慎到“本黄老,归刑名”(10)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92页。,他持有以道为本、以刑名法术为用的思想,是从黄老道家转变为法家的关键人物。郭沫若认为:“慎到、田骈一派是把道家的理论向法理一方面发展了的。”(11)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页。历来研究者多聚焦于慎到的法家思想,尽管高亨先生认为慎到思想是“法家之齐物”(12)张丰乾:《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也有部分学者论述了《庄子·天下》中慎到的贵齐思想(13)如金东洙:《田骈、慎到的哲学思想(上)》,《当代韩国》2003年第3期,第31-36页。,但尚未明确阐述慎到不同于庄子的“齐物论”,对慎到的“齐物论”在道法转关中的作用也关注不足。我们以稷下学者慎到为中心来考察其不同于庄子的“齐物论”。《庄子·天下》论述了慎到的“齐物”思想,为理解慎到的思想渊源提供了新视角,如果结合《庄子·天下》和《慎子》的相关论述,从理论基础、政治模式、主体心理和处世方式来阐述慎到的“齐物论”,分析他从“齐物论”到“齐民论”的思想转变,应该能展示慎到一派北方道家关于“齐物论”的一种新理解,也能揭示“齐物论”在道法转关中的作用。
一、“齐物论”的多重意义
按照《庄子·天下》的评述,彭蒙、田骈和慎到皆有不同于庄子的“齐物论”。庄子“齐物论”至少有两种含义:如果对象是客观事物(物),那么“齐物论”就是“均齐万物”的思想;如果对象是学说言论(物论),那么“齐物论”就是统一思想标准或消解学说争论。王应麟认为庄子“齐物论”的实质是齐“物论”,他说:“《齐物论》非欲齐物也,盖谓物论之难齐也。是非毁誉一付于物,而我无与焉,则物论齐矣。”(14)王应麟:《困学纪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1页。由于“物之不齐”是客观事实,所以庄子的本意不是均齐事物,而是以“无所参与”的态度来消解各种“物论”。王夫之说:
当时之为论者多矣,而尤盛者儒墨也;相竞于是非而不相下,唯知有己,而立彼以为耦……勿论其当于道与否,而要为物论。物论者,形开而接物以相构者也,弗能齐也。使以道齐之,则又入其中而与相刃。唯任其不齐,而听其自己;知其所自兴,知其所自息……则见其不足与辨,而包含于未始有之中,以听化声之风济而反于虚,则无不齐矣。(15)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三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93页。
王夫之也认为“齐物论”的对象是以儒墨思想为代表的“物论”。不仅“物”不可均齐,而且“物论”也各有不同的形成结构而难于相齐。如果以“道”来统一“物论”,会使“道”降为“物论”的层次。唯有以“听任”其自生自灭的方式,才能消解“物论”之争。钟泰进一步认为,“齐物论”既齐“物”又齐“论”:
“齐物论”者,齐物之不齐,齐论之不齐也。言论先及物者,论之有是非、然否,生于物之有美恶、贵贱也……齐之为言非如孟子“比而同之”之云也。美者还其为美,恶者还其为恶;不以恶而掩美,亦不以美而讳恶则美恶齐炙。是者还其为是,非者还其为非;不以非而细是,也不以是而没非,则是非齐矣。(16)钟泰:《庄子发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钟泰将“物”理解为主观认识中的内容,而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认识内容存在美恶、贵贱、是非的差异,所以“物之不齐”必然导致“论之不齐”。据此,“齐物论”其实是既齐“物”又齐“物论”。钟泰认为,“齐”的含义不是孟子的“比而同之”,而是从“物”的美恶比较和“论”的是非争论中退场,从而实现价值判断的自然消解。王应麟、王夫之和钟泰所理解的庄子“齐物论”,皆非均齐万物或统一物论,而是消解学说的是非争论。
田骈和慎到皆“学于彭蒙”(17)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91页。或“禀业彭蒙”(18)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下),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14页。,三家有相近的“齐物论”。《庄子·天下》篇论彭蒙、田骈和慎到三家共同的“齐物”思想为:
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趋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19)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086页。
“公而不党”和“易而无私”是公正无偏、均平无私之意,“趋物而不两”和“于物无择”是随顺事物、公平待物之意,“决然无主”和“不谋于知”指主体具有无我无知的特征。与庄子“齐物论”相比,彭蒙、田骈和慎到的“齐物论”在对象、方式和主体上均有所不同,“齐”的对象偏重“物”而非“论”,“齐”的方式是公平地对待事物而非解构物论,“齐”的主体不是通过消除成心来消解争论,而是以无我、去知的态度去随顺万物。《庄子·天下》中借彭蒙之师的口吻说:“彭蒙之师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风窢然,恶可而言!’”(20)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091页。彭蒙之师推崇的“齐物论”,是主体以“虚怀忘我”的方式而达到无是非争论的境地,这种主体态度和庄子“听任不齐”的方式似是而非,因为前者的“齐物论”更强调“随顺万物”而非“解构物论”的意思。
田骈还发展出广义的“齐物论”世界观。《吕览·慎势》载:“陈骈贵齐”,高诱注曰:“齐生死,等古今也。”(21)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下),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67页。蒙文通对高诱注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田骈和慎到的“齐物论”应当相近,“高诱注以齐生死作解释,这是把庄周的齐物和田、慎的齐物没有分别清楚”(22)蒙文通:《佛道散论》,第74页。。但如果高诱注比较准确,那么田骈的“齐物论”是将“齐”的对象扩大为生死和时间等终极存在,“齐”的方式带有一种视一切存在和变化无差别的人生态度,这其实是一种形而上的“齐物论”。
相比之下,慎到的“齐物论”则具有现实的政治关怀。《庄子·天下》的“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23)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086页。主要指慎到的思想,这在《慎子·民杂》中有相应论述:“大君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24)慎到:《慎子》,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3页。“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是从世界整体说明大道能包容而不区分万物,让天地万物各随其性分。“大君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则从社会政治角度指君王包容万民,让万民各随所能而任事,具有强烈的政治实践倾向。慎到的“齐物论”还通过另一角度表现出来。《慎子》载:“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25)慎到:《慎子》,第13页。高亨认为这种思想是“法家之齐物”(26)张丰乾:《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第200页。。“法”是由“道”转化的法则制度,能公正裁断一切物情或民情,以法“齐物”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方式(27)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1页。,“齐天下之动”体现了法家无所偏私、依理裁断的贵公主张。所以,慎到的“齐物论”具有两种思想特色:一种是君王对民众的“包容不辩”和随顺民情,为道家消极的“齐物”;另一种是以法裁断民情,为法家积极的“齐物”。
庄子“齐物论”未否定事实上的“物之不齐”和“论之不齐”,而是以“听任不齐”的方式从“物”的美恶比较和“论”的是非争论中退场,从而实现“物论”自息自齐。而彭蒙、田骈和慎到三家“齐物论”则是消极地随顺万物。慎到“齐物论”更具有政治实践性,“齐”的对象为民众和民情,“齐”的方式兼有道家对民众的“包容不辩”和法家对民情的“依法裁断”。所以,慎到的“齐物论”其实是一种政治上的“齐民论”。
二、“齐万物以为首”的世界观和政治图景
慎到“齐物论”走向“齐民论”的理论基础是“齐万物以为首”,由此可以确立一种“齐民而治”的政治模式。《庄子·天下》载:
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28)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086页。
蒙文通认为这一段所表达的意思是黄老学派的大义,与庄子“齐物论”之旨全无相同之处(29)蒙文通:《佛道散论》,第73页。。其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确立了“齐万物”的目的论。慎到“齐物论”的逻辑起点是“齐万物以为首”,“齐万物”为其思想的首要目的。一种说法认为“首”或为“道”,应当是“齐万物以为道”(30)陈寿昌云:“其学以齐万物为首务,小大如一,不起分别也。”奚侗云:“首,借为道。”马叙伦认为:“陈、奚二说是也。”参见张丰乾:《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第272页。,但这不妨碍以“齐物”为第一原则的意思。其次,确立了“道”是能“包容”和“齐万物”的最高实体和标准。天、地、万物和人为教化皆存在不能周遍的限度,唯有“道”才具有包容无遗的无限性,以及对万物不作区分、一视同仁的公正性,所以“道”才是“齐万物”的最高标准。相比荀子强调以“尊卑贵贱,亲疏长幼”的等级差别为礼法治理的基础,慎到更主张以“道”的自然性和公平性为依法齐民的基础。其三,明确了以“道”来“齐万物”的世界观。慎到以“道”来“齐万物”的思想为法家“齐民治世”确立了理论前提,只有在理论上以“齐物”为目的,并认为“道能齐物”,才能在实践中包容万民,公平地对待民众,依法公正地裁断民情。所以刘泽华认为:“‘道’与具体事物的关系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包容万物,二是对万物一视同仁。慎到认为法与‘道’相对应,法也有两个特点,一方面是包容一切人事,另一方面对不齐的人事一视同仁。”(31)刘泽华:《论慎到的势、法、术思想》,《文史哲》1983年第1期,第15页。慎到的这种“齐物论”具有浓厚的宇宙秩序和政治秩序色彩,与庄子以化解成心来消解物论的齐物思想不同。
关于慎到的“齐物”思想,《庄子·天下》多言“齐物”之本,而《慎子》多言“齐物”之用。《庄子·天下》中慎到“齐万物以为首”和“大道包而不辩”的世界观,在《慎子》中皆有相应的治国理论。《慎子·民杂篇》载:
民杂处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无能去取焉。是故不设一方以求于人,故所求者无不足也。(32)慎到:《慎子》,第3页。
《庄子·天下》中慎到的“齐物论”是从理论上讲大道和事物的关系,而《慎子》则从政治上讲君王和百姓的关系,大道对应君王,万物对应百姓。《慎子》的“民杂处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即《庄子·天下》说的“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意思是从“道”或君王的角度看来,万物和民众皆各有其性分。《慎子》的“大君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即《庄子·天下》的“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指君王如大道一样对民众包容而各任其所能。《慎子》的“不设一方以求于人,故所求者无不足也”,即《庄子·天下》的“道则无遗”,比喻治道无定法,随人之性分而任用。如此,道家“齐物论”的世界观就转化为法家“齐民治国”的理论,由此构建出现实社会中以君王为首、君王包容并均齐万民、依法公平决断事情的政治图景。
另一方面,慎到“齐万物为首”和“大道包而不辩”的思想体现了自上而下的体用秩序,如同老子“道生万物”的逻辑,慎到也认为“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33)慎到:《慎子》,第3页。。处于下位的事物都是“道”的派生和运用,而天道的“太上”地位和“齐万物”的作用,也会相应转化为君王处于权力顶点的“势力”和“势能”。对大道至上位势的强调是“重势思想”和“势治主义”的理论来源。君主和权势好比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云雾才能高飞,君王有权势才能“令则行,禁则止”。如同“居高声自远,非是籍秋风”所谓的声音传播籍势不借风一样,政令推行的一个主要条件就在于威权的势能,而非其他外在因素的推动。因此侯外庐等人将慎到的治国理论称为“势治主义”(34)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04页。,突出了“天道”的势能或“君王”的位势在慎到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三、“齐物论”的主体心理
慎到“齐物论”中的“大道”在政治实践中分化为君王和“法”,分别形成政治主体和政治原则。君王秉承了“道”包蓄天下的特性,在政治实践中体现为对万民的“包容不辩”和公正无私。“法”秉承了“道”的理则性,在政治实践中法的作用就是“齐天下之动”和对民情的“依法裁断”(35)君王的无我性和法的原则性其实源自对老子“道法自然”的两种理解。若“道法自然”指“道”本自然无为,不承认世界背后有一个主宰,那么“道”体现的是无为而顺自然的非实在性。若“道法自然”指“道”效法自然,则认为世界有一个最高原因和主宰实体,那么“道”就具有效仿、遵循“自然实体”的实在性。这两种思想既发展为稷下学的“莫为”与“或使”思想,也会影响慎到的“齐物”思想。。相比《慎子》突出以法“齐物”的作用,《庄子·天下》更强调“齐物”主体“无我”“弃知”和“不两”的心理特征。庄子通过化解主体的心理根基来消解“物论”,慎到也通过消解主体的心理根基来适应“法”的主宰性。“齐物”主体的心理特征是理解道法转关的思想关键。
君王的一个特征是“无我而顺物”。在“齐万物以为首”和“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的主旨下,君王需要无区别地对待万物和民众。如何能做到这一点?慎到的主张是“决然无主……于物无择,与之俱往”(36)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086页。,“泠汰于物,以为道理”(37)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088页。。在慎到看来,“齐万物”或“齐万民”首先需要齐物主体具有“无我”的心理,做到“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38)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4页。,摒弃自身意志或主观意愿,随顺万物之情或万民之性,这样才能在主观上对万物一视同仁。高亨认为慎到的“无我而顺物”其实是法家的思想:“物为人。法家不尚贤,于人无择,有去己之意。”(39)张丰乾:《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第198页。如果“物为人”,那么“齐物”的实质上就是以无我的心理去“齐民”。君王一方面对民众无价值选择,另一方面又以听任民情为道理,这种心理恰好适应了“法”的主宰性,而一切依于“法”的裁断。可以发现,慎到虽然和庄子一样通过主体无我的方式来实现“齐物”,但庄子是以心的境界为“齐物论”的终极方式(40)如王博认为:“齐物的关键其实不在于物,而在于心。物是不齐的,但是如果无心于不齐的话,这不齐的物的分别于我又有何意义呢。”(王博:《庄子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而慎到的无我心理只是政治实践的一个前提,它为法家“齐民而治”创造了条件。
君王的另一特征是“弃知”、否定尚贤和教化。《庄子·天下》认为彭蒙、田骈和慎到的共同特点是对知识持否定态度:“不顾于虑,不谋于知”(41)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086页。。而慎到尤其表现为“弃知去己……不师知虑”的态度。《庄子·天下》载:
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輐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42)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086-1088页。
慎到对知识和圣贤提出三种主张。其一,在慎到看来,相比自然法则,人的主观认识和知识显得浅显和有限,有所知则有所不知。既然可以通过顺应“法”来齐物或裁断民情,则人不必有知识。所以慎到对待知识的态度是“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他放弃主观意愿和知识,“洗涤一切对事物的偏见和误解”(43)蒙文通:《佛道散论》,第71页。,以听任万物活动为道理,只顺着事物本身的自然之理而行,这就是“而缘不得已”的方式。其二,由轻视知识,进而否定选贤任能和道德教化。慎到认为“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选贤和教化都是有限度的人为活动,选贤不能让人人得到度量,教化也不能让人人都拥有知识,皆不能实现普遍的“齐物”效果。而“道则无遗”,由“道”化生的“法”就是普遍的标尺,以“法”任官和教民则能普遍应用而无所遗漏。因此,慎到主张“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若随顺物情而不刻意任用贤能,则物各自得,人各尽性,而不必尚贤。若不为仁义之事,则天下之圣人不必存在。慎到认为否定知识和圣贤是符合“齐物”之道的,即“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蒙文通说:“慎到、尹文他们把齐物、尚法不尚贤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44)蒙文通:《佛道散论》,第80页。其论断依据就在于慎到的“弃知”和“笑贤圣”合乎“齐物”之道,具有“齐民治国”的目的,只有否定自私用智的知识,否定自逞其能的行为,否定与众人不同的圣贤,才能均齐万民而依“法”行事。其三,慎到认为否定知识和圣贤还能实现合乎自然的境界,这就是上文所谓的“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无建己之患”指没有标新立异来自成一派的忧虑,“无用知之累”指没有穿凿附会、脱离实际的劳累,而“终身无誉”则是无宠辱若惊的心理烦扰。同时,放弃知识而随顺万物也具有“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等保全自然性命,不滋生过错的功用。
君王还有“不两”的特征。慎到主张“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45)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086页。。“趣物”是舍己而顺物之意,而“不两”则具有双重意义,体现了君王在政治实践中身心分裂的矛盾。一方面,“趣物而不两”有去己而顺物之意,取消了心理主体的“我”,而与外物相适应。这时“不两”是无我而顺物、与物不二的意思。另一方面,君王又保留了权势主体的“我”,通过“不两”而否定两个权力中心。《慎子·德立》说:“两则争,杂则相伤……故臣有两位者国必乱。臣两位国不乱者,君在也,恃君不乱矣。失君必乱。子有两位者家必乱。子两位而家不乱者,父在也,恃父不乱矣。失父必乱。”(46)慎到:《慎子》,第5页。无论是家国还是天下,有两个权力中心必会导致相争和混乱,而保持君父独尊的权势,则家国不乱。这时“不两”就是维护君父的权威,杜绝两个权力中心的意思。可见,《庄子·天下》中的“不两”是取消心理上的“我”,而《慎子》中的“不两”是主张权力上的“我”。君王“不两”所体现的矛盾,其实是取消了心理主体而保留了权力主体。
君王的心理特征是慎到法治思想的心理基础。如果以道家“无我”“弃知”和“不两”等方式来取消君王的心理主体,那么反过来会更好地适应“法”的主宰性。《慎子·君人》载:“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望于君。”(47)慎到:《慎子》,第6页。如果君王无自我私见而依法处事,则百姓各安“法”的赏罚裁决而不必期待君王之决断。同样,君王“弃知”也有助于实现无为而治。《慎子·民杂》载:“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故事无不治。”(48)慎到:《慎子》,第4页。为政的关键是君王不用知识,不参与事为,听任臣民各凭其天赋能力而完善其事,则能达到无为而治的效果。
君王的心理特征还是慎到“重势”的一个缘由。“齐物”主体虽然心理上“无我”,但在政治位势中仍“有我”。君王身心的分化,一方面消解了心理主体以适应法则,从而走向法治主义;另一方面又保留了权力主体,而走向势治主义。慎到之所以重势,不仅因为“势”是天道至上的地位在政治实践中的体现,而且因为君王是无我、弃知的。若君王怀有无我、弃知的心理,而且不欲借助治理之术,那么只有依靠至上的“权势”才能保持政令畅通和推行政治愿景。如果说天道是势治主义的形而上来源,那么君王无我、弃知的特征则是势治主义的心理基础。
四、“齐物”和“因循”
君王“无我”“无知”的心理在政治实践中会体现为“因循”的方式。君王要面对“民”和“法”这两种对象,如何能在自身“齐物”的同时适应“法”的“齐民”,便是君王需要解决的问题。“因循”是君王协调两者的处世方式。“因循”即顺应、效法之意,以“因循”为处世态度,君王既能包容、顺应民情,同时也能遵循“法”的主宰安排。
从理论渊源而言,老子“道法自然”的两种意义,稷下学的“莫为”与“或使”的两种思想(49)《庄子·则阳》载:“季真之莫为,接子之或使。”(郭庆藩:《庄子集释》,第916页),黄老学的“重因”传统和“静因之道”(50)《管子·心术上》:“礼者,因人之情。”“因也者,舍己以物为法者。”以上两处见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47、164页。,会影响慎到或相互影响,在这种思想关联下,慎到会兼有顺应物情和遵循主宰的“因循”思想。但“因循”其实和“齐物”也有思想联系。庄子“齐物论”不主张以最高标准来统一物论,但慎到主张以“道”来“齐万物”和对万物“包容不辩”,“道”就具有主宰万物和包容万物两种功能,君王如果效法“道”的作用,会相应产生遵循“法则”和顺应“民情”两种态度。遵循“法则”和顺应“民情”面临的对象虽然不同,但主体“因循”态度是一致的。
《庄子·天下》未直接使用“因循”一语,而是用“于物无择”“趣物而不两”等语词来表达和“因循”相同的意思。高亨从法家角度来理解“趣物”,认为法家不尚贤故能于人无择,所趋向者唯法。与此不同,马叙伦从道家角度来理解“趣物”,认为这是“随物而往,不持己意,与物为一”的意思(51)张丰乾:《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第198、270页。。无论哪种解释,“趣物”都是“无我而因循”的方式,都是顺应物情或法则的符合论。当然,这两种解释也能体现法家和道家在“因循”思想上的差异,道家是因顺物情,法家是遵循法则。
高亨和马叙伦对所趣之“物”的不同理解,实际上就是慎到“齐物论”主体(君王)所面对的两种对象——民和法,而二者都统一于君王的“因循”方式。若君王的对象是民情,则相应表现为“莫为而因循”的处世态度。《慎子·因循》载:“因也者,因人之情也。……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唯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52)慎到:《慎子》,第3页。君王无为而因顺人情,就能达到民众“自为、得用”的治理效果,这时君王“齐民情”的实质就是“因民情”。若君王面对的对象是“法”,则相应表现为“遵循主宰”的处世方式。《慎子》载:“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至法不可阙也。”(53)慎到:《慎子》,第13页。“法”不可缺离,一切社会活动和人士皆不得违背法则。这时,君主“齐民而治”就是遵循法则的裁断。
慎到还提出“性分”的思想来统合“齐物”和“因循”。从“性分”的角度看“齐物”和“因循”,民情和法则的关系就不是简单的以后者裁断前者,而具有内在一致性。《慎子》载:“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54)慎到:《慎子》,第12页。“法”除了具有“道”的主宰性之外,还具有“人心”的现实自然基础,因而法则和民情其实是一致的。如何实现一致?慎到主要通过“分”的思想来实现,也就是说,法则的施行要合乎人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性分”,此“性分”即《庄子·天下》所谓的“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即《慎子·民杂》所谓的“民杂处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55)慎到:《慎子》,第3页。,而合乎“性分”即《慎子》所谓的“因人之情”。具体而言,君王所因循的民情包括人因不同“性分”而形成的政治职位和社会分工,慎到说:“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则事省,事省则易胜;士不兼官则职寡,职寡则易守。故士位可世,工事可常。”(56)慎到:《慎子》,第2页。对待人从自然性分而形成的社会分工和政治地位,慎到主张依法依情而治理,并非简单地采用均平主义。《慎子·君人》载:“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望于君。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57)慎到:《慎子》,第6页。这是说,法则礼节虽然是“齐天下之动”的公共法则和制度,但是君王不是任用法则对民众和事情实行一刀切的裁断,而是以合乎人心方式,在“各以其分”的基础上施行法治。“各以其分”即能做什么的人便让他做什么,事情是什么样便相应采用什么手段,这就是慎到这一派“因循性分”思想下的“齐物”。从贵因的角度看,“齐物”的含义就不是思想层面的消解物论,而是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诉求,而这种社会政治主张也非简单的均平主义,而是在公平基础上,以法则来裁决民众“各以其分”而形成的民情,以法则来维护事物各以其情,民众各以其性、各得其用的秩序和治理思想。如此,慎到不仅以“因循”方式将因顺民情和遵循法则统一起来,而且还通过“合乎人心”和“各以其分”为民情和法则建立了内在统一的人性基础,从而协调了两种“齐物”方式,为“本道而归法”寻找到契合处。
另一方面,贵因思想和齐物思想的结合,还可以发展出一种“自足其性”的逍遥思想和政治理想。虽然没有证据表明郭象的思想受到慎到一派“齐物论”的影响,但是从思想关联的可能性来说,慎到的“齐物论”既然不是用法则去整齐划一地裁断物情或民情,而是实现“合乎人心”和“各以其分”的政治理想,那么就和郭象的“自足其性”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庄子·逍遥游注》载:“夫大小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各住其性,事称其能,各节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58)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上),第1页。这种逍遥是通过“齐大小”来实现的。郭象所谓“齐大小”不是以一种标准来裁剪大小以使其整齐划一,而是通过“物各住其性,事称其能,各节其分”的方式来实现“称性之齐”,也就是说,不是达到物情或物性的均等,而是让事物能平等地适性。若实现了“齐大小”,也就实现了不同事物“自足其性”的逍遥境界,如此,“齐物论”和“逍遥游”就统一于郭象“大小俱足”的思想中,而这种“齐物”也表达了和墨子、尹文和慎到一样的政治理想:万物的存在都是各足其性的,人在社会中也应各安其位,各尽其性(59)如墨子说:“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吴毓江:《墨子校注》[上],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4-75页)这是以人各尽其性为齐。如尹文说:“因圆之自转,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转,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贤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无用,使不得用。用与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与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乱乎!”(魏征等编,《群书治要》学习小组译注:《群书治要译注》[第二十二册],第66页)这是因万物之不齐而各得其用为齐。。
五、慎到思想的内在困境
慎到思想兼有道家和法家的特征,以“无我”“无知”的主体作出因顺人情而遵循法则的实践,可谓“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而从“齐物论”走向“齐民论”,也体现了慎到“本道而归法”的转变。但慎到“齐物”主体的“无我”,“弃知”“不尚贤”“后物而动”等思想,用于政治实践会相应产生四个问题,除了君王存在心理主体和权力主体相分裂的矛盾之外,还有荀子所批评的“尚法而无法”“蔽于法而不知贤”和“有见于后而无见于先”三方面问题。
1.尚法而无法。“尚法”和“无法”的矛盾事实上源自“主体无知”和“齐物原则”“主体无我”和“因循”的矛盾。从“主体无知”的角度看,慎到既主张以法“齐民情”,又主张以“弃知去己”的方式来遵循法则。可在实际生活中,知识具有规范性和标准性,而建立法则的行为规范和赏罚标准需要知识基础,对法则的执行和遵循同样需要知识储备来理解法则。如果在建立、执行、遵循法则的同时否定一切知识和教化,那么不仅“法”的规范性和标准性无从建立,人们能否合理地执行法则或理智地遵循法则也成为问题。慎到通过否定知识和教化来依法齐民的思想,势必会导致连“法”本身也被否定的极端情况。从“主体无我而因循”的角度而言,也存在“尚法而无法”的矛盾。荀子批评慎到说:“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60)王先谦:《荀子集解》,第93页。荀子认为慎到虽然崇尚法则,但又存在不循旧法的情况,而是以苟顺的态度听取于上、取从于俗,所以他虽然著书立言而成文典,但察之无所指归,这样就使得法度难以确立。
2.蔽于法而不知贤。这一冲突源自慎到将“法”与“人”对立,而不知“法”也需要“人”来实施。由于万物存在“有所可,有所不可”的限度,而道(法)则具“包容无遗”的普遍性,所以慎到认为与其崇尚圣贤,不如遵循法则。《慎子》载:“学之于水,不学之于禹也。”(61)慎到:《慎子》,第12页。慎到通过否定墨家崇尚的大禹,来表达尚法而不尚贤的思想。《庄子·天下》认为慎到是“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62)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088页。。儒家举贤,墨家尚贤,而慎到则是“笑尚贤”和“非圣”。荀子认为慎到“蔽于法而不知贤”(63)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92页。,慎到简单地认为只要明确法则、因循法则,虽然无圣贤也能得到治理,这是不知圣贤的作用在于建立和执行法则。王先谦认为:“但明得其法,虽无圣贤亦可为治,而不知法待贤而后举事。”(64)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92页。如果将“法”的普遍性和人的有限性对立起来,凡事都因循或取决于“法”,似乎不需要圣贤的治理,但事实上“法”也要通过贤能者来施行,否则“法”的赏罚公正性和执法完善性就缺乏理智的执行主体,而无法合理地实施。
3.有见于后而无见于先。如果说慎到的前两种问题与“法”相关,那么这一问题则源自慎到思想中齐物主体极端无我而因循的方式。道家“因循”的诀窍在于能把握事态的时机,所谓“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65)司马迁:《史记》,第3292页。蒙文通认为,“虚无为本”是南北道家之所同,“因循为用”则为北方道家之精义,亦是黄老道家虽然后起却能压倒百家之原因,而“因循”不仅是“因物”,还是“因时”(66)蒙文通:《佛道散论》,第70页。。从根本上说,“因循”的目的不是因循具体的事物,而是遵循事物所体现的自然天道,从而能实现“物物而不物于物”的自在性和主动性。这就要求主体具有一定的洞见来把握事物的活动规律及活动时机,并在政治实践中保持一定的主观能动性来选择恰当的时机,而不是简单地随顺事物。但慎到却是“不知前后”“推而后行,曳而后往”。他将“因循”消极地理解为随顺形而下的事物,而不是遵循自然规律和把握活动时机,所以不仅表现为处处落后于事物和形势,而且毫无主观能动性。这表面上是因循自然,其实是不知几、无先见的表现。荀子对此批评道:“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67)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19页。如果在政治实践中,君王处处落后于事物的变化,无治国远景和对事态变化的预见性,则民众生活无门路可遵循。甚至,这种极端的因循方式已经泯灭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然生理,所以《庄子·天下》评论道:“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王夫之也认为:“此逆人之心,而绝其生理。”(68)王夫子:《船山全书》(第十三册),第470页。慎到“弃知去己”“后物而动”“若无知之物”的因循方式不过是极端消极而无生理的“道”。这种极端消极的方式已经不类似道家或法家,而被后人视为近似于佛家,《四库总目提要》载:“慎子之学近乎释氏,然后志列之于法家。”(69)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1页。这是认为慎到之学极端消极无为的思想近于佛家所谓钝根声闻者,反而不像道家或法家的思想特征。
4.有我与无我。慎到的“不两”思想,以权力上的“我”来行道,又否定主体上的“我”来因顺道、法和万物,这种取消心理主体而保留权力主体的方式,体现了君王在政治实践中身心分裂的矛盾。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慎到未能明于“天人之分”,对天人关系或道人关系处理不当。在人君、天道、万物三者的关系中,慎到将天道视为高于人君和万物的终极存在,主张以无我之君适应主宰之道,并听任天道来施行人间之治。可是一方面,人不能完全去己而适应天道。唐君毅认为:“老庄则弃一般之知与己,而亦有其不弃之知,不去之己。”(70)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香港:新亚书院研究所,1973年版,第276页。老子之归根复命,也是以“玄览”“玄鉴”而体道,持“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之“玄德”,并非像慎到那样取消精神自我而成块然一物。另一方面,即使是通过天道来施行人间治世,也需要以人作为行道载体。但是慎到泯灭人的主观智识来适应天道,而不知“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7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页。,“人能弘道,非道弘人”(7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67页。,最终会导致“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这其实和庄子一样是“蔽于天而不知人”(73)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93页。。既不明人之职分,又要以人君身份替天行道,就会造成人君的身心分裂。事实上,天道与人是不离不混的关系,各有其分,只有明于“天人之分”,才能恰当地处理天人关系或道人关系。